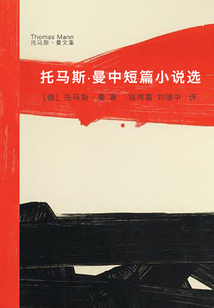
托馬斯·曼中短篇小說選(托馬斯·曼文集)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者前言
二十世紀初,德國文學界出現了一顆光燦奪目的巨星,它華光熠熠地照亮了歐洲整個文壇,贏得了世界各國千百萬讀者,這就是一九二九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托馬斯·曼。
托馬斯·曼于一八七五年六月六日生于德國北部呂貝克城的一個富商家庭,父親托馬斯·約翰·亨利希·曼(1840—1890)是經營谷物的巨商,后任參議及副市長;母親尤莉亞·曼(1851—1923)生于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出身富貴,有葡萄牙血統。父親嚴肅、冷靜,富于理智,而母親則熱情奔放,愛好藝術。他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哥哥亨利希·曼以后也是一位舉世聞名的大作家。一八九〇年十月,父親去世,商行倒閉,全家遂于一八九二年遷至慕尼黑定居。翌年,他在文科中學畢業,后即在一家火災保險公司當見習生。托馬斯·曼早年即愛好文學藝術,博覽群書;學習期間,他曾用保爾·托馬斯的筆名在《春風》及《社會》雜志上發表詩歌與論文,但并不為人注目。在保險公司當見習生時,他仿效法國作家布爾熱和莫泊桑的風格寫了一篇以女演員和大學生的戀愛為題材的故事,這就是一八九四年十月在《社會》雜志發表的中篇小說《墮落》。著名作家理查·戴默爾看到這篇作品,大為贊賞,曾去信鼓勵他,并邀請他在雜志上共同協作,從此托馬斯·曼投身于出版與寫作事業的意志更為堅決,創作欲也越來越旺盛了。
一八九五年,他離開保險公司,在慕尼黑高等學校學習,當一名旁聽生。他不但旁聽了藝術史和文學史等課程,而且對經濟學也甚感興趣。與此同時,他為哥哥亨利希·曼主編的《二十世紀德意志藝術與福利之頁》審稿,并撰寫書評。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間,他曾數次去意大利,到過威尼斯、佛羅倫薩、那不勒斯及羅馬等地,但對意大利并無多大好感這一時期,他閱讀了德國哲學家尼采,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法國作家福樓拜、龔古爾等人的作品,而俄國文學在他心中留下了尤為深刻的印象。托爾斯泰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和《戰爭與和平》,是他偏愛的兩部作品。一八九八年,他又回慕尼黑,任諷刺雜志《西木卜利齊西木斯》編輯。
一八九六年及一八九七年,他繼《墮落》之后又寫了短篇小說《幻滅》及中篇小說《矮個兒弗里特曼先生》等,這兩篇小說與其他短篇小說一起于一八九八年以《矮個兒弗里特曼先生》的書名出版。
早于一八九七年夏季,托馬斯·曼就著手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準備工作。他收集了家里的舊卷宗、家庭的各種傳說和書信,作為這部巨著的素材。小說中的許多人物均以他家的親友為原型,并將呂貝克故居的許多具體情景寫進小說內。一九〇〇年夏秋之交,小說定稿,于翌年出版。這是一部描寫資產階級家庭從繁榮走向沒落過程的史詩式的作品是德國社會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發展的縮影,人物眾多,場景廣闊,筆觸細膩,是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力作,出版后受到廣泛的好評。從此作者一舉成名,為他一九二九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奠定了基礎。到一九七五年止,它已被譯成三十種文字,在德語國家里·它已印行四百萬冊以上。
此后數年,托馬斯·曼仍埋頭于中、短篇小說等的創作。一九〇二年寫完了中篇小說《特里斯坦》、短篇小說《饑餓的人們》及《上帝的劍》等。一九〇三年,他的著名中篇小說《托尼奧·克勒格爾》又在《新德意志展望》雜志上發表。同年,他將一些中、短篇(包括《路易絲姑娘》、《去墓地的路》等)匯成一集出版,書名即冠以《特里斯坦》。
這時托馬斯·曼已是將近三十歲的人了。他結識了慕尼黑大學數學教授阿爾弗雷特·普靈斯海姆的女兒卡塔林娜(1883—1980),當時她正在攻讀數學與物理,對音樂也有較深的造詣。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熱戀,兩人終于在一九〇五年二月結成伉儷。婚后,他們有六個子女,即莫尼卡、戈洛、米哈伊爾、克勞斯、伊麗莎白和埃利卡,以后都成為文學、藝術和歷史學方面的人材。
從婚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主要發表了三部作品,即一九〇九年的長篇小說《王爺殿下》、一九一二年的中篇小說《死于威尼斯》及一九〇六年的三幕劇本《菲奧倫察》。《王爺殿下》描寫的是貴族亨利希與一美國百萬富翁的女兒攀親的故事,展示了德國資本主義發展中貴族與資本家相互依賴、相互勾結的丑惡畫面。《死于威尼斯》則是托馬斯·曼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觀與藝術觀。
一九一二年五月至六月,作者的妻子卡塔林娜因肺部炎癥,在瑞士的達沃斯肺病療養院住了三星期左右。在這段時間里,他對療養院的生活和各式各樣的人物細心作了觀察,長篇小說《魔山》的素材即由此而得。托馬斯·曼于一九一二年開始執筆寫這部巨著,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寫作中斷,以后時斷時續,終于在一九二四年問世。這是他第二部最重要的作品,在國際上影響之大不亞于《布登勃洛克一家》。有的評論家甚至認為他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主要是《魔山》對世界文學的影響。美國大作家辛克萊·劉易斯在一九三〇年曾說,“我覺得《魔山》是整個歐洲生活的精髓。”在這部巨著中,托馬斯·曼描寫了療養院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反映了當時流行的各種思潮,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社會的各種病態現象作了深刻的描述。作者本人認為這部作品有雙重意義,既是一部“時代小說”,又是一部“教育小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托馬斯·曼的心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認為“這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對于這次非正義的戰爭,他一面感到疾首痛心,認為這是“布爾喬亞文化的結束”,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觀的局限性,他對戰爭的性質認識不清,于一九一五年撰寫了一篇《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的論文。該書于一九一八年出版。書中他從衛護“德意志精神文化”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多方為德帝國主義的參戰辯護,同民主主義者的哥哥亨利希·曼的觀點針鋒相對。盡管此書內容政治角度上是不足取的,但其中卻包含了有關文化、文學及個人作品的精辟論述,對研究托馬斯·曼有一定參考價值。在《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中,他對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贊譽備至,對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和果戈理的《死魂靈》等作品也十分推崇。
俄國的十革命,在托馬斯·曼的思想和世界觀上引起了深刻的變化。盡管長期以來他對無產階級革命懷有某種抵觸情緒,但他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社會必須變革。他頭腦中的民主主義成分愈來愈多,對自己的過去逐漸采取否定態度。一九二二年,他作了《論德意志共和國》的演說,推翻了自己以前不問政治的觀點,表示擁護魏瑪共和國,同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取得和解。經過艱苦而曲折的思想反復,托馬斯·曼在前進的道路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托馬斯·曼多次出國旅行,先后到過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布達佩斯、布拉格、馬德里、倫敦、哥本哈根、佛羅倫薩、雅典、君士坦丁堡、開羅、巴黎及華沙等地。這使他大大豐富了知識,擴展了視野,并為他以后的創作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題材。長篇小說《約瑟和他的弟兄們》,就是在一九二六年醞釀成熟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后,國際反動勢力日益猖獗,歐洲大陸陰云密布,法西斯主義蠢蠢欲動。這時,托馬斯·曼已是一個覺醒了的民主主義者和激進的人道主義者了。一九三〇年,他在柏林作題為《告德國人》的演說,矛頭直指法西斯主義。他認為能抗拒法西斯野蠻暴行的唯一力量是社會民主主義,并號召德國市民階層站在它的一邊。同年,他又發表了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說《馬里奧和魔術師》。
一九三三年,為紀念德國作曲家理查·瓦格納逝世五十周年,托馬斯·曼在慕尼黑大學發表講演,題為《理查·瓦格納的苦難與偉大》。由于他從德國文化的人道主義傳統出發論述這位作曲家,沒有贊揚瓦格納的民族主義傾向,受到親納粹的一批文人的責難。希特勒攫取政權后,托馬斯·曼被迫流亡,在瑞士等地居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反動當局進一步迫害這位作家:他的財產被沒收,國籍被剝奪,而波恩大學也取消了他在一九一九年獲得的名譽博士學位,因而他給波恩大學文學院院長寫了一封公開信,譴責納粹政府踐踏德國文化的罪行。這封信在反法西斯陣線中起了鼓舞斗志的作用。
還在希特勒上臺之前七年,托馬斯·曼就開始寫作一組以《圣經》中約瑟的故事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即《約瑟和他的弟兄們》四部曲。前兩部《雅各的故事》和《年輕的約瑟》在作家移居國外之前即已完成,而后兩部《約瑟在埃及》及《贍養者約瑟》則是在希特勒政變后寫畢的。
在從事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之前,托馬斯·曼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參考了許多科學專著,并努力追溯《圣經》傳說中的歷史根源。在對神話傳說進行藝術處理時,他不僅依靠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許多作品,還借助于弗洛伊德的學說。小說的某些內容表面上是諷刺埃及人民的民族自大狂,實際上卻是針對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分子的。在這“四部曲”里,托馬斯·曼力求從神話中找到人道主義因素,以達到借古諷今的目的。正如托馬斯·曼在一次學術報告中所說我在內心準備把類似約瑟傳說的材料當作與我的創作興趣相吻合的東西來接受,是由于當時我的趣味發生了變化,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厭棄和對神話的愛好。”許多評論家認為它與《魔山》一樣,也是一部發人深省的“教育小說”。
在托馬斯·曼看來,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民主、自由的象征,因而于一九三八年遷居美國。不久他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先后發表各種演說。一九三九年,他的又一部長篇小說《綠蒂在魏瑪》問世。
《綠蒂在魏瑪》的寫作技巧頗為新穎,完全擺脫了傳統的藝術結構。小說沒有多大情節,只是著重描寫歌德與青年時代熱戀過的女友夏綠蒂于一八一六年重逢時的各種場景。在第七章中,作者對歌德的心理狀態刻畫入微,巧妙地再現了這位大詩人生活的年代及其復雜矛盾的性格。顯然,作者想借歌德來確立并發揮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矛頭也是針對當時橫行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的。
同年五月和六月,世界作家大會和美國作家大會開會,托馬斯·曼均前往參加。這年夏天,托馬斯·曼又回到歐洲,先后在蘇黎世、倫敦及斯德哥爾摩住過。九月,第十七屆國際筆會在斯德哥爾摩開幕,這位杰出的作家在會上作了題為《自由問題》的講演,從他的發言中,可以看出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
從一九四〇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托馬斯·曼每月定期通過美國廣播公司對外廣播,直接參加反法西斯宣傳。他先后發表題為《德國聽眾們!》的廣播演講五十五篇,對打擊法西斯主義起了一定作用。在這些演講中,他對英勇抗擊法西斯的蘇聯人民懷有深摯的敬意,而對社會主義社會也懷著滿腔熱情。一九四二年,他被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德國文學顧問,一九四四年取得了美國國籍。
早于一九〇一年,托馬斯·曼就想寫一部“浮士德”式的大型作品。一九四三年五月,他開始寫作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該書于一九四七年出版。它的主題與中篇小說《死于威尼斯》等一樣,是一部描寫藝術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以悲劇而告終的小說,同時也是一部德國走向法西斯、走向戰爭與毀滅的“時代小說”。小說中,作曲家阿德里安·萊弗爾金不滿現實,在音樂上試圖有所創新。他同魔鬼訂約后,寫出了許多反傳統的新穎作品,但由于萊弗爾金的人性尚未泯滅,受到魔鬼的懲罰,最后他認識到藝術不能單純追求形式的完美,主要應有益于人類。可惜他覺悟得太晚,靈魂已為魔鬼所占有,終于變成癡呆。據作者在一九四八年發表的日記透露,萊弗爾金的思想、氣質和經歷,與尼采的情況十分相似,《浮士德博士》的主人公無異是尼采的化身,而音樂家與魔鬼的談話,則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這部小說的寫作技巧也與托馬斯·曼的傳統寫法不同,具有現代派小說的許多特點。
自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間,作家往來于歐洲大陸及美國。一九四九年,為紀念歌德誕生二百周年,作家回德國,在法蘭克福和魏瑪兩地發表演說,兩地都給他頒發了歌德獎金。由于他對日益猖獗的麥卡錫主義十分不滿,而美國報刊又猛烈攻擊他同情共產主義,他于一九五二年忿然離開美國,移居瑞士蘇黎世附近。他不止一次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同兩個德國的文化界保持聯系,成為溝通易北河兩岸文化的信使。
托馬斯·曼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雖然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仍孜孜不倦地埋頭寫作。一九五一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被挑選者》,取材于中世紀詩人哈特曼·封·奧埃的史詩《格里高里烏斯》,描寫一個青年因不明真相,竟娶了自己的生母為妻,后來贖了罪,成為羅馬教皇。一九四五年德國投降后,托馬斯·曼曾不遺余力地宣揚對戰敗的德國采取寬大政策,這部小說就是一個例證。
一九五三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受騙的女人》,則是一部對女人的情欲進行心理分析的作品。書中寫的是一個年逾半百的女人因情欲驅使,竟愛上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作者以寬容的態度描寫了這種反常的愛情和變態心理;在作者的心目中,“愛”與“死”本是一家,而大自然卻具有愚弄人的性質。
托馬斯·曼最后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大騙子克魯爾的自白——回憶錄第一部》。此書的個別章節曾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七年發表過,第一卷在一九五四年問世。作者以回憶錄的方式描寫了克魯爾招搖撞騙的一生,文筆犀利、幽默,語多諷刺。從題材上看,這部小說與托馬斯·曼的早期作品也有一定聯系,即涉及資本主義社會中藝術與藝術家的問題。小說的某些章節寫得十分精彩,思想性與藝術性均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除各類小說外,托馬斯·曼還寫了許多散文,其中有自傳性文章和政論,而很大一部分則是文學評論。在文學評論中,較著名的有《論席勒》、《歌德與托爾斯泰》、《藝術家與社會》以及《從我們的經驗看尼采哲學》等。他對萊辛、史托姆、契訶夫、馮塔納、弗洛伊德、塞萬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席勒等人都很有研究,在一九四五年瑞典出版的《高貴的精神》一書中,他對這些作家都有精辟的論述。俄國作家中除托爾斯泰外,契訶夫也是他最為傾心的作家之一。他認為“契訶夫唱的是深深地打動他的人民的社會悲歌”。《時代的作品》則收集了有關他的自傳性文章、日記以及重要的政論共八十八篇,是研究這位文學大師的重要文獻。
席勒是托馬斯·曼最喜愛的作家之一,早于一九〇五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沉重的時刻》中,他就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刻畫這位大詩人在創作過程中嘔心瀝血、備嘗艱辛的形象。在長篇小說《魔山》、中篇小說《托尼奧·克勒格爾》和《顛倒錯亂和早年的傷痛》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借主人公之口贊揚席勒和他的名劇《唐·卡洛斯》。為了紀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作家于一九五五年夏逝世前不久分別在兩個德國宣讀他所撰寫的《試論席勒》一文。他說:“人類要求道德與秩序,正義與和平,而不是互相辱罵,野蠻欺詐和殘忍仇恨。”在《試論席勒》的結尾部分,托馬斯·曼號召德國人民“要相愛,和平,珍惜自己的品德”,反對現代軍國主義者。
托馬斯·曼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還在醞釀新的文藝作品。但他未能實現自己的計劃,就以八十歲的高齡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與世長辭。
二
托馬斯·曼最大的成就,無疑是《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舉世矚目的長篇小說,但他的中、短篇小說,特別是早期的中篇小說寫得非常出色,在德國文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托馬斯·曼在十九歲時發表的中篇小說《墮落》是使他嶄露頭角的處女作,第一次發表在一八九四年十月的《社會》雜志上。小說的布局和寫法上可以看出十九世紀法國作家的痕跡,文筆簡潔、流暢,結構嚴謹,故事性強。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大學生和一個女演員,兩人熱戀了一陣后,女演員因經不起金錢的誘惑而墮落,大學生失戀之余,憤世嫉俗,痛苦不堪。作者告訴人們,在金錢萬能的社會中,藝術家要潔身自好是難以做到的,而女藝人則更加處處受壓抑,遭欺凌,在金錢的淫威下屈服。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根本談不上什么“婦女解放”。托馬斯·曼對女演員韋爾特納的墮落既有譴責的意味,也有同情的成分。
由于托馬斯·曼受叔本華、尼采及某些作家的影響,他的早期作品明顯地流露出悲觀的色彩,從一八九六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幻滅》和一八九七年發表的《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在《幻滅》里,作者以不大的篇幅刻畫了一個窮愁潦倒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屢遭不幸,郁郁不得志,因此灰心喪氣,對前途不抱任何希望。這篇故事一方面固然說明了作者的思想傾向,另一方面也較為典型地反映出小人物苦悶彷徨的心情。《死》中描寫的那個病人,情緒則更加陰暗,整篇小說籠罩著一片慘霧愁云,使人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一八九七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矮個兒弗里特曼先生》,是托馬斯·曼早期作品中的力作之一。作者在《三十年故事集》的序文中,也稱它是“我早期作品中的有典型意義的成就”。在作者筆下,矮個兒弗里特曼不但是個生理上有缺陷的畸形人,而且思想上也是“畸形”的。他誤以為美麗動人的林林根夫人鐘情于他,于是利用在溪邊散步的機會向她求愛,不料這位冷若冰霜的貴婦人輕蔑地把他推倒在地,揚長而去,矮個兒經不起這一沖擊,萬念俱灰,就讓自己沉入水中,與世永別。顯然,作者對病弱而命運坎坷的主人公是寄予同情的,而對林林根太太之流的上層人物則持鄙夷態度。從這里,我們也可隱約窺見托馬斯·曼人道主義思想的萌芽。
托馬斯·曼在許多早期作品中,著力表現“局外人”的處境以及他們的孤獨感。他筆下的一些所謂“局外人”,有的像上面提到的弗里特曼那樣,是發育不健全的畸形人,有的則是酗酒成性或貧苦失意的小人物。《托比阿斯·敏德尼克爾》中的主人公和《去墓地的路》中的羅布哥德·匹普桑姆就是這樣的人。在前一篇中,生性怪僻、落落寡合的敏德尼克爾由于生活困頓,在灰心絕望之余竟親手殺死他所寵愛的一條小狗;而后一篇中,匹普桑姆因為一件小事與別人爭執,最后落得瘋瘋癲癲的下場。這兩篇小說雖然字數不多,但作者向人們展示了社會的一幅陰暗畫面,讀后心情異常沉重,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小說。一九〇三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饑餓的人們》,同樣描寫了擯棄于生活之外的那種“局外人”:這是一個生活富裕、孤芳自賞而渴求真理的知識分子,整篇小說通過他的內心獨白,展示了他復雜而矛盾的精神世界。在小說的結尾部分,他遇上了一個饑餓的窮人,這個窮人在寒風中縮成一團,用紅炎炎的眼睛瞅著他,這時他忽然認識到他們彼此是“同病相憐的兄弟”,對方的饑餓是在肉體方面,而自己的饑餓則在精神方面。最后,主人公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們得不到安寧的受苦難的人啊;……需要另一種愛,另一種。”顯然,這也正是托馬斯·曼本人的觀點。
托馬斯·曼生長在上流社會,對其中形形色色的丑惡現象耳聞目睹,十分熟悉。他對這些現象切齒痛恨,因而在作品中不遺余力地用諷喻的筆調加以譴責。在短篇小說《路易絲姑娘》中,作者在描寫雅各布律師、律師妻子安瑪洛亞和安瑪洛亞的情夫洛伊特納以及三者的愛情糾葛時,用的都是揶揄的語調,在他犀利的筆鋒下,這三個人各自的丑態(雅各布的怯弱、顢頇;安瑪洛亞的淫蕩、任性;洛伊特納的輕浮、自負)都顯得活龍活現。寥寥三四千字的《神童》也是一部絕妙的諷刺作品。彈鋼琴的“神童”彼彼盡管還是一個孩子,卻懂得惺惺作態,嘩眾取寵;聽到他的演奏后,商人想的只是生意經,認為這場演出“凈余足足有一千個馬克”,把藝術看作是一樁有利可圖的事業;在一個妙齡女郎的心目中,他演奏的主題不外乎是愛情,希望他像小弟弟那樣吻她;一個鋼琴女教師聽了后,心中則不無妒忌,認為神童的演奏缺乏創造性,應當“拿戒尺來對付他”。在《在預言家的屋子里》,寫的是各式各樣病態的人物,這里有小說家、畫家、音樂家及愛出風頭的貴婦人等,他們大多是不滿現實的文人,妄想改革社會,但又找不到正確的方向與出路,反映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在這篇作品里,作者對那位小說家的諷刺尤為辛辣,此人思想空虛,作風浮夸,他前來預言家的屋子里集會的目的,無非是見見世面,找尋一些刺激,并通過貴婦人跟她的女兒談情說愛。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文人是有一定典型意義的。另一篇《火車事故》是他膾炙人口的佳作之一,這里,作者的諷刺手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小說雖短,卻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一個上流人物的嘴臉。這位高貴的紳士剛上火車時,顯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竟違反禁令把小狗帶入臥車車廂,一不如意,就罵別人“兔崽子”,但火車一出事故,他卻高呼救命,還口口聲聲叫“偉大的上帝”、“萬能的上帝”,真是丑態十足!
下面我們要談談托馬斯·曼三個以藝術家為主題的重要中篇小說。
《托尼奧·克勒格爾》是托馬斯·曼二十八歲時的作品,發表于一九〇三年。據說這是作者最喜愛的作品之一,或多或少帶有個人自傳的成分。托尼奧的家庭出身和經歷,有許多地方同作家本人的情況相似。小說揭示了藝術和社會的關系以及理性與生活的關系,表達了一個正直的藝術家的心聲,指出了一個作家應當選擇的道路。作者借托尼奧之口道出了他的藝術觀:“如果說,有什么能使我從一個知識分子變成一個作家,那正是我這種對人性、對生活、對普通事物的平民式的愛。一切溫暖、善良和詼諧都來自這種愛。”這說明了托馬斯·曼的寫作態度是嚴肅的,是面向生活,面向社會,面向人民的。
同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特里斯坦》,也是一部描寫藝術與生活之間相互關系的光彩奪目的作品。故事以一座療養院為背景,通過德特雷夫·史平奈爾與科勒特揚夫人之間的曖昧關系的描寫,反映了一些上層社會的人的病態生活的一個側面。這里,作者一面借商人科勒特揚之口,揭示了人們崇拜金錢、蔑視藝術的丑惡本質,另一方面則精心刻畫了作家史平奈爾的形象,把上世紀末那種脫離生活、逃避現實的藝術家的本質生動地勾勒出來。托馬斯·曼是以冷嘲熱諷的筆調來描寫這些人物的,對這種無病呻吟的唯美主義藝術家顯然持否定態度。藝術家應當如何正確對待生活——這就是我們在讀這篇小說后應當仔細思索的問題。
托馬斯·曼寫了不少中篇小說,其中最負盛名的首推《死于威尼斯》。像《托尼奧·克勒格爾》和《特里斯坦》一樣,它也是一部以藝術家為題材的作品,不過它所反映的社會面更加廣闊,主題思想也更加深刻。西方文學界很推崇這篇小說,目為世界文學名著,而托馬斯·曼本人也認為是自己的得意杰作。他曾說:“《死于威尼斯》的確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結晶品,這是一種結構,一個形象,從許許多多的晶面上放射出光輝。它蘊含著無數隱喻;當作品成型時,連作者本人也不禁為之目眩。”這篇作品是他于一九一一年從意大利歸國后所寫,一九一二年問世。故事的主人公阿申巴赫是一個正直清高的名作家,他數十年來孜孜不倦地獻身于創作,一心想攀登藝術的高峰。長年累月辛勤的勞動使他心力交瘁,他很想松一口氣,到國外調劑一下疲憊的身心。他選中威尼斯作為目的地,在那兒度過了不少炎熱的夏日。他在飯店里遇見一個非常俊美的波蘭籍男孩,他認為孩子就是美的化身,因而陷在一種反常的情愛里,不能自拔,甚至為他神魂顛倒。不久,威尼斯疫癘橫行,外僑紛紛回國,而阿申巴赫明知有染疾身亡的危險,卻偏偏不肯離開,寧愿守在孩子身邊,最后終于死在海灘旁。許多評論家都認為阿申巴赫的原型就是作者本人,這樣的人物在當時的知識界有一定的代表性。雖然他孤芳自賞,遠離人民群眾,但寫作態度十分嚴謹,對當時的社會抱批判態度。他對社會上種種庸俗、淺薄的東西都看不入眼,對那個社會的種種陰暗面更感到疾首痛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在托馬斯·曼的心靈上打下了烙印。戰后,歐洲普遍出現了經濟蕭條,德國當然也不例外。馬克貶值,通貨膨脹,人民生活每況愈下,而青年們在動蕩不安的現實下顯得十分消沉。一九二五年的《顛倒錯亂和早年的傷痛》,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寫成的。作者除真實地描寫了當時青年一代的思想動態外,還以精湛的藝術技巧向我們展示了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書中的歷史教授科內利烏斯,許多評論家都認為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故事環繞青年們一次家庭舞會層層展開,這里既有載歌載舞的熱鬧場面,又有發人深思的哲理。作者本人很欣賞這篇小說,認為它是自己中篇小說中最佳的作品之一。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引起了托馬斯·曼的關注與憂慮。他曾說過:“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必須組成統一戰線,使戰爭狂人不敢輕舉妄動。”一九三〇年初發表的中篇小說《馬里奧和魔術師》,就是作者投向法西斯的一把利刃。小說以作者的一次意大利旅行為素材,描寫正直、樸實的侍者馬里奧與魔術師奇博拉之間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在奇博拉魔鞭的呼嘯聲中,群眾只能俯首帖耳,一切聽憑他的擺布,馬里奧最初也中了他的魔法,但不久就清醒過來,認識了對方的猙獰面目,毅然把他一槍打死。很明顯,魔術師奇博拉是法西斯分子的象征,而馬里奧則代表人民。小說的結尾清楚地告訴我們:人民開始時很容易受法西斯的蠱惑和愚弄,但一旦清醒過來,就威力無窮,并起而反抗,置它于死地。由于這是一篇意味深長的政治小說,出版后不久即被墨索里尼政府列入禁書名單。這個中篇小說不但有鮮明的政治內容,也有較高的藝術性。作者對許多場景都作了繪聲繪色的處理,讀來扣人心弦。可以說,《馬里奧和魔術師》使他的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三
托馬斯·曼深受叔本華、尼采、瓦格納等人的哲學思想和文藝思想的影響,早期創作上難免有一些唯美主義的痕跡和其消極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說作為藝術家,看來我是異乎尋常地早熟的……可是就政治而論,我敢斷言我的成熟十分緩慢。”但在人民風起云涌的革命斗爭中,他的頭腦日趨清醒,逐漸成為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三十年代后則更為進步,能用他的文章和演說同法西斯主義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他對社會主義也有一定認識,曾撰有《反布爾什維主義是我們時代的大蠢事》一文,明確闡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場。當然,由于種種原因,他對革命和社會主義尚持保留態度。他以真知灼見和敏銳的觀察力看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并通過各種體裁的小說和文章對帝國主義敲響了喪鐘,不愧為二十世紀德國繼往開來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師。
托馬斯·曼又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由于世界觀的局限性以及受某些古典作家的影響,他青年時代的人道主義是抽象的,消極的,其表現形式僅僅是同情弱者和不幸者及譴責惡勢力,這在他早期的一些中、短篇小說中歷歷可見。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他的人道主義有了積極的、進步的內涵:他支持西班牙人民反對佛朗哥政權,還尖銳批評某些國家在慕尼黑的出賣行為。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在紐約的一次群眾大會上說和平力量應當強大,為的是能給那些除暴力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暴徒們以反擊……自由應當強大,它應當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權自衛……一切希望德國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的人,應在這個自由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在演講中說德國的聽眾們,歐洲一旦解放,就會成為社會主義的歐洲。社會的人道主義已提上議事日程,當法西斯主義的丑臉剛在世界上露頭,它便已出現在優秀的人們的眼前。它,這個人道主義,是真正新的、年輕的和革命的事物,一旦它砸爛了惡棍的腦袋,它便將決定歐洲外在和內在的面貌。”在他七十五歲壽辰之前舉行的一次講演會上,他也強調要在這“反人道精神的時代”中“保衛人道主義”。
在創作上,托馬斯·曼的風格是多種多樣的。他的中、短篇小說的結構都經過精心的設計,在情節、構思及人物的塑造上均下過一番功夫,每個詞都經過仔細的斟酌,文筆細膩生動,人物形象也十分鮮明,被公認為二十世紀德國的語言大師。傳記作家德·德·門德爾松把他譽為“語言的魔術師”,也許并不過分。他的中、短篇小說既保留了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某些優秀傳統,有完整的故事性,情節納入一目了然的時間與空間范疇之內,又采用了現代派的某些寫作技巧(如意識流、內心獨白、象征和隱喻等),因而能贏得世界各國廣大的讀者群。例如在《死于威尼斯》中,作者善于把現實與夢境、真實與幻覺、記憶與印象交織在一起,其中還穿插了主人公阿申巴赫對人生與美學問題的思考和精神生活的探索。阿申巴赫在確切地得悉威尼斯瘟疫流行的那天夜間,曾做了一個噩夢,作者是這樣來描述這個怪誕的夢境的:
……在破霧而出的霞光中,從森林茂密的高原上,在一枝枝巨大的樹干之間和長滿青苔的巖石中間,一群人畜搖搖晃晃、跌趺撞撞像旋風般地走來。這是一群聲勢洶洶的烏合之眾,他們漫山遍野而來,手執通明的火炬,在一片喧騰中圍成一圈,蹁躚亂舞。
這些人興奮若狂,高聲喊叫,但叫聲里卻有一種柔和的清音,拖著“烏——烏”的裊裊尾聲。這聲音是那么甜潤,又是那么粗獷,他可從來沒有聽到過。它像牡鹿的鳴叫聲那樣在空中回蕩,接著,狂歡的人群中就有許多聲音跟著應和,他們在喊聲下相互推擠奔逐,跳起舞來,兩手兩腳扭擺著,他們永遠不讓這種聲音止息。但滲透著和支配著各種聲音的,卻依然是這深沉而悠揚的笛聲。他懷著厭惡的心情目睹這番景象,同時還得不顧羞恥地呆呆等待他們的酒宴和盛大的獻祭。對于此時此地的他,這種笛聲也不是很有誘惑力么?他驚恐萬狀,對自己信奉的上帝懷著一片至誠的心,要竭力衛護它,而對異端則深惡痛絕:它對人類的自制力和尊嚴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喧鬧聲和咆哮聲震撼著山岳,使它們發出一陣陣的回響。這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近,幾乎達到令人著魔的瘋狂程度。塵霧使他透不過氣來——山羊腥臭的氣味,人們喘著氣的一股味兒,還有一潭死水散發出的濁氣,再加上他所熟悉的一種氣味:那就是創傷和流行病的氣味。……
這里,作者把主人公的現實生活與夢境、感覺與幻覺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加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文中,“烏——烏”的“烏”字是阿申巴赫所依戀的美少年塔齊奧的“奧”字的變音,白天里,他常聽到塔齊奧的母親或別的家人總是用這副腔兒叫喊這個少年;而山羊和野蠻人的腥臭味,則顯然是他白晝聞到的消毒藥水的氣味了。
對自然界與景物的描寫,也是托馬斯·曼所十分擅長的。例如在《死于威尼斯》中,作者對旭日從海面上升起的景象作了如下描繪:
天際開始展現一片玫瑰色,煥發出明燦燦的瑰麗得難以形容的華光;一朵朵初生的云彩被霞光染得亮亮的,飄浮在玫瑰色與淡藍色的薄霧中,像一個個佇立在旁的丘比特愛神。海面上泛起一陣紫色的光,漫射的光輝似乎在滾滾的海浪上面翻騰;從地平線到天頂,似乎有無數金色的長矛忽上忽下,閃爍不定——這時,熹微的曙光已變成耀眼的光芒,一團烈焰似的火球顯示出天神般的威力,悄悄地向上升騰,終于,太陽神駕著疾馳的駿馬,在大地上冉冉升起。……
從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托馬斯·曼的深刻的觀察力和高超的語言修養。他所選用的每一個字,看來都是經過推敲的。
再看《特里斯坦》里的一段描寫:
——天氣一直晴好。附近一帶的山巒、房屋和園林,都沉浸在無風的恬靜和明朗的嚴寒中,沉浸在耀眼的光亮和淡藍的陰影里,一切都那么雪白、堅硬和潔凈。萬里無云的淡藍天空,穹頂似地籠罩著大地,成千成萬閃爍的光點,發亮的晶體,在天空中飄舞嬉戲。……
寥寥幾筆,一派凜冽的冬景就躍然紙上。
關于人物形象的刻畫,托馬斯·曼也匠心獨運。他善于通過主人公的言詞(包括對白和獨白)和行動來突出人物的特性,因而他筆下的人物如阿申巴赫、史平奈爾、托尼奧·克勒格爾、科內利烏斯和弗里特曼等均有鮮明的個性,讀后給人以深刻難忘的印象。
在世界文學的寶庫中,德國詩歌堪稱獨樹一幟,從歌德、席勒到海涅幾乎獨占了一個世紀的詩壇。德國戲劇也不乏巨匠佳作,萊辛、席勒、霍普特曼和布萊希特,都對各國的戲劇和舞臺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托馬斯·曼以前,除了歌德、霍夫曼、馮塔納與史托姆外,德國小說基本上只停留于德國本土,未能像美國、俄國、法國的小說那樣在世界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托馬斯·曼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后德國以他的小說創作成就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德國文學史上劃時代的重要作家。一九八四年,歐洲五家影響較大的報紙曾評選出十位歐洲最受歡迎的已故作家,其中屬于二十世紀的則有卡夫卡、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和喬伊斯四人。匈牙利杰出的文藝評論家盧卡契和德國當代著名學者漢斯·邁耶都撰有《托馬斯·曼》的專著,對這位大作家倍加贊賞。蘇聯、日本和西方許多國家都早已翻譯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或多卷本。我國的出版界早于一九六二年就介紹了他的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之后又陸續出版了《魔山》、《綠蒂在魏瑪》和《大騙子克魯爾的自白——回憶錄第一部》等書。深信今后各國研究托馬斯·曼的學者將愈來愈多,而他的作品也將在世界文壇上永放異彩。
錢鴻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