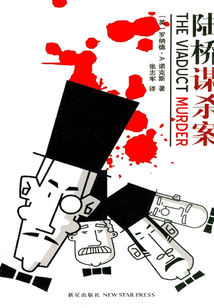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諾克斯:推理小說中的摩西
背叛教會的“神父大人”
信仰對于一個人有多重要?比至關重要更重要。如果說性格決定命運,那么信仰是可以決定性格的。越是天才式的人物,信仰的作用越是舉足輕重。萬事如此,推理小說更是如此。推理圈內的大師有不少,但能稱為“天才”的卻寥寥無幾。很幸運,在推理小說處于崛起的關鍵階段,有一位叫做羅納德·A.諾克斯的天才出現了。
諾克斯出生于一個富足的宗教家庭,父親是曼徹斯特的主教大人。諾克斯理所當然擁有宗教信仰。但問題在于,父親老諾克斯是英國國教主教,而令年輕的小諾克斯神往的卻是羅馬天主教會!沒人能說清在國教環境里長大的諾克斯為什么會滋生出如此“離經叛道”的信仰,也許是父親過于嚴厲,也許是“物極必反”的必然作用,也許是因為諾克斯畢業于那座該死的牛津大學……反正,諾克斯的宗教信仰把自己赤裸裸地擺在了整個家族的對立面。
每天以勸說別人加入英國國教為工作的老諾克斯自然不能容忍親生兒子的“背叛”,而“懂事”的兒子也沒有讓父親過于為難——諾克斯非常干脆地宣布和整個家族脫離關系。從此,父親的榮耀、父親的財產以及父親本身,和諾克斯再也沒有扯上半點關系。一九一七年加入天主教會的諾克斯因為出色的才能和“破釜沉舟”的忠心,很快便得到了羅馬教皇的賞識。一九一九年,諾克斯成了教皇的第一助理,官方稱謂叫“諾克斯主教大人”。
按常理分析,以“背叛”整個家族為代價換得的天主教榮譽,應被諾克斯視為生命。如果真是這樣,諾克斯也就不會擁有今日在推理領域的地位了。一九二五年,主教大人靈感突至,揮筆創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推理小說《陸橋謀殺案》。這部“游戲之作”雖然被一些評論者評價為“情節拖沓,構思離奇”,但這并沒有影響到它的熱賣。《陸橋謀殺案》以幽默的風格、絕妙的布局,確立了諾克斯特有的推理創作風格。
諾克斯受此鼓舞,推理創作的“欲望”一發而不可收拾。他先后創作了《三個水龍頭》、《閘邊足跡》、《筒倉陳尸》、《死亡依舊》、《雙重反間》等推理小說,部部皆為經典的古典本格推理大作。而他筆下塑造的“難以形容”保險公司調查員麥爾斯·布萊頓則成為整個推理小說歷史上最經典的偵探形象之一。
不管怎么說,推理小說在世人心目之中始終難改“小道”的地位。而在以正統、嚴肅、正大光明著稱的羅馬教會眼中,推理小說更是永遠不應該和神職人員扯上關系的。諾克斯創作的推理小說接二連三的熱賣,讓很多教會中人大呼“人心不古”。但礙于諾克斯的才華和地位,也不便和這位大人鬧翻。
但“無法無天”的諾克斯在一九二八年做出了一件讓教會無法容忍的“罪行”——他居然代替上帝,撰寫了一份屬于自己的“十誡”!偉大的“十誡”,是只有上帝才有權制定的!即使是摩西一般賢明的人物,也只能手捧“十誡”,亦步亦趨地領著苦難的同胞走出埃及;而諾克斯居然敢以“十誡”的形式闡述推理小說的創作規條,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在諾克斯之前,推理小說創作處于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階段。雖然也誕生了許多偉大的作品,但基本上屬于自發狀態。是諾克斯大人第一次從理論上闡明了推理小說的創作規則,將這一文學形式規范化。如果說埃德加·愛倫·坡告訴了世人推理小說是什么,那么諾克斯就是第一個告訴人們推理小說應該怎樣寫的人。
“不能借助超自然力”、“不能杜撰不存在的毒藥”、“不可以監守自盜”、“助手智商不能高于常人”、“不能在無預告狀態下使用雙胞胎”……如果沒有美國的史密斯博士制定的最初的十三項籃球規則,那么今天我們看到的就不是NBA而是十人群毆;同理,如果不是諾克斯寫出了“十誡”,也許今天的推理小說會像《封神演義》一樣變成神仙斗法式的神怪小說,會像《弗蘭肯斯坦》一樣變成人造人式的科幻小說,會像《魔戒》一樣變成魔法傳說式的玄幻小說……總之,如果沒有“十誡”,推理小說的今天是不可想像的。
但天主教會顯然懶得站在推理文學的角度上贊嘆諾克斯的不朽貢獻。他們除了覺得這位主教大人罪該萬死之外,沒有意識到“十誡”的任何價值。在教會的重壓之下,諾克斯不得不放棄了推理小說的創作和研究。可以說,他因為推理背叛了教會,又因為教會背叛了推理。
遠離推理小說的諾克斯專注于宗教文化的研究和整理。他是第一個將拉丁文版《圣經》翻譯為英文版的人。天才的光芒是世俗無法掩蓋的——即使遠離推理,諾克斯依然是當之無愧的先知。
游戲福爾摩斯的“福爾摩斯學之父”
對于推理小說而言,諾克斯不僅僅是一位創造者,還是一位出色的繼承者。在別人眼中看來已經有些脫離時代的“遠古課題”,到了諾克斯手中卻被雕琢得熠熠生輝。讀者應該知道,我指的“遠古課題”名叫福爾摩斯。
阿瑟·柯南·道爾筆下的大偵探在誕生之初可謂風光無兩。不僅在一夜之間“粉絲”遍及全球,更是改變了推理文學在整個文學領域的地位。但沒有什么人物的風光可以戰勝時間的侵蝕。來到諾克斯所處的時代,這位住在貝克街的大偵探地位已經相當尷尬(一生偵破的六十個案件已經被世人背得爛熟于心,一個個偵探后生的崛起更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當行動落后于時代,當功績愈發虛無縹緲,尷尬也就自然而然地難以避免。還能指望人們談論福爾摩斯什么?《血字的研究》還是《巴斯克維爾的獵犬》?這些故事早已被時代淘汰。
作為福爾摩斯的信徒(該死!主教大人的信仰的確多了一點),諾克斯選取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詮釋爵士筆下的偉大偵探。一九二八年,諾克斯在當時的暢銷雜志《藍皮書》上發表了《福爾摩斯文學研究》一文,確立了其“福爾摩斯學之父”的地位。
福爾摩斯的原型是哪位高人?福爾摩斯的父母是怎么樣的人?華生醫生結過幾次婚?莫里亞蒂教授到底有多么深不可測?貝克大街藏在倫敦何處?華生的小狗為什么會不翼而飛……如果你自信將福爾摩斯的故事背得滾瓜爛熟,那么上面的問題你能答對幾個?在諾克斯的帶動下,“福爾摩斯學”迅速走向成熟。經過近一百年的歲月,這門科學魅力依舊,而且研究范圍在不斷擴大。索隱、探佚、原型研究……可以說,是福爾摩斯啟迪了諾克斯,是諾克斯挽救了福爾摩斯。
諾克斯的福爾摩斯學的功力在《陸橋謀殺案》中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甚至讓人瞠目結舌。也許一切技藝的巔峰境界,都是以近乎游戲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在《陸橋謀殺案》中,諾克斯好好地將福爾摩斯先生調侃了一番。從煙斗理論到板球手的帽子,從兇手的木腿到華生的懷表,最后,諾克斯干脆把小說的一章直接叫做《福爾摩斯的方法》。故事中的偵探們爭先恐后地將福爾摩斯的手段“嫁接”到自己的偵探過程中,可這些偵探都忽略了一個比方法更重要的問題(偵探的智商)所以偉大的福爾摩斯因為他們而名聲掃地就不足為奇了。
福爾摩斯的擁躉者不必咒罵神父大人諾克斯又一次的“大逆不道”,事實上還有什么比得上創建“福爾摩斯學”更能表示對阿瑟爵士和福爾摩斯的尊敬呢?諾克斯不惜血本的惡搞無非是想告訴讀者,福爾摩斯的方法,功力不足的半吊子偵探切勿模仿,否則稍有不慎,必將走火入魔!
顛覆推理的“推理先知”
諾克斯的一生可以用兩個字概括——糾結。
糾結于英國國教和羅馬天主教之間,糾結于宗教信仰和推理情結之間,糾結于福爾摩斯的是與非之間……在《陸橋謀殺案》中,諾克斯返璞歸真,在推理與反推理之間著實地糾結了一把。
就像從上帝制造出光的那一刻起,一種叫黑暗的東西就同時存在一樣,推理誕生的那一天,“反推理”就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推理小說,尤其是早期的古典本格推理小說,其內容并不具備太多的現實意義,就像現實中沒有哪個兇手會使用密室或消滅足印來掩蓋罪行一樣。推理小說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兇手要聰明到可以設置一般人無法破解的謎團,卻又要傻到只有靠殺人才能解決問題。”
這一特性決定了推理小說中的推理橋段同樣架空現實。一方面這個橋段精妙得讓人拍案叫絕,另一方面卻讓人在拍案之后不禁皺眉:“這些推理在現實中管用嗎?”于是,一種“反推理”情結醞釀生成。不管一部多么經典的推理小說,總有人會質疑推理的真實性和可行性。就像人們總在議論的那樣:“書中的偵探們運氣總是很好,總是可以找到兇手遺失的煙斗。”
早在《陸橋謀殺案》以前,以“反推理”為最高目的的推理小說便層出不窮。大名鼎鼎的G.K.切斯特頓寫出了《奇職怪業俱樂部》;E.C.本特利創作的《特倫特最后一案》作為一部反推理作品,更是成了開啟推理黃金時代的不朽之作;而羅納德·A.諾克斯的《陸橋謀殺案》,則是古典本格派中此類作品的最高成就。
一個自以為是的偵探,或是智商有限,或是運氣不好,或是為情所困,總是在一番嚴密謹慎的調查和推理之后,得出一個與真相相差甚遠的結論——這是所有反推理小說共同的模式。作者以此來嘲諷所謂的精妙推理在現實中根本是“水中撈月”。而諾克斯大人似乎覺得由一位偵探的失誤所得出的結論有著太多的偶然性,不足以證明“推理無用論”。所以,在《陸橋謀殺案》中,主教一共安排了四位偵探登場。“四大名捕”面對一樁離奇的謀殺案,各顯神通,不斷提出自己的推測。但現實不斷地擊碎了四個熱血青年的名偵探夢想——此種殘酷對于稍有自尊的偵探來說,無疑比命案本身更難以下咽。我自認是推理小說的狂熱愛好者,反推理小說也讀過不少。但誠實地說,在合上《陸橋謀殺案》之后,我的確對所謂的經典推理小說產生了一絲質疑——即使只是一瞬間,我不得不承認,諾克斯大人反推理的設置扣動了我的心弦。但這并不說明諾克斯大人對推理帶有任何的成見,而《陸橋謀殺案》只是天才小憩時的游戲之作。之后諾克斯創作的《閘邊足跡》、《筒倉陳尸》等作品都是布局絕妙、推理神奇的正統推理大作。
這就是羅納德·A.諾克斯,天才的叛逆者,推理的先知,福爾摩斯學之父,“十誡”的書寫人。
褚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