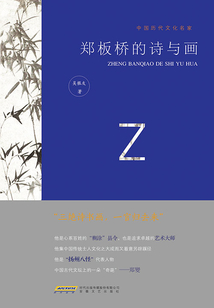
鄭板橋的詩與畫
最新章節(jié)
- 第12章 注釋
- 第11章 跋
- 第10章 參考文獻(xiàn)
- 第9章 流風(fēng)余韻話板橋——板橋?qū)笫赖挠绊?
- 第8章 “呵神罵鬼之談”——《板橋家書》及其文論
- 第7章 “無古無今之畫”——板橋繪畫 題識(shí)及畫論
第1章 板橋魂
中國農(nóng)業(yè)文明歷史悠久,發(fā)展充分。兩千多年的歷史孕育出了具有世界農(nóng)業(yè)文明典范性質(zhì)的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管理、教育、哲學(xué)的思想體系,產(chǎn)生了以表意、抒情為突出特征的文學(xué)、藝術(shù),發(fā)展起了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中心的天文、水利、耕作、交通運(yùn)輸、建筑等科技體系。這樣龐大而近乎完備的農(nóng)業(yè)文明體系,在十六世紀(jì)中后期,自發(fā)地產(chǎn)生了帶有近代文明萌芽的手工業(yè)、商業(yè)文明。在這歷史嬗變過程中,士人及士人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同時(shí)也在其中悄悄地改變著自身特質(zhì)。
鄭板橋,既是這一偉大的農(nóng)業(yè)文明孕育出的藝術(shù)家、思想家,又以他個(gè)人特有的才華,推動(dòng)了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文明向近代工商業(yè)文明轉(zhuǎn)變的歷史車輪。他身上所表現(xiàn)出的精神氣質(zhì),既是傳統(tǒng)士人文化精神的個(gè)性化表現(xiàn),又有時(shí)代精神的折光。他身上所具有的新舊思想雜陳、進(jìn)步與落后因素并存的特征,基本上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在歷史的嬗變過程中所具有的復(fù)雜性的具體表現(xiàn)。板橋魂,即是士人魂在新時(shí)代的再現(xiàn)。
一、“士”與“士人魂”
(一)原士
“士”在中國是一個(gè)特殊階層。其來源及其最初含義均屬頗為復(fù)雜的學(xué)術(shù)問題。[1]大體來說,遠(yuǎn)古之“士”,乃是從事耕作之男子。商、周時(shí)代,“士”則可能是指“知書識(shí)禮”的貴族階層。顧頡剛先生認(rèn)為,古代之“士”皆起源于武士;余英時(shí)則認(rèn)為,“士”不只是單純地起源于武士,還可能起源于古代軍事教官——“師事”。這些教官既可能是馳騁沙場的武士,亦可以是懂得禮樂的文官。那些只懂得禮樂的文官發(fā)展到后來,便變成了儒士。概而言之,“‘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門掌事的中下層官吏”[2]。
(二)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士”及其精神品格
從影響秦漢以后士人靈魂和政治理想的角度看,以孔子及其弟子、老子為開山鼻祖的“士”,是我們?cè)诒緯凶钪匾奶接憣?duì)象。他們對(duì)士的本質(zhì)及其屬性的認(rèn)識(shí)與界定,最能影響后來的士人精神及其靈魂。
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論語》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yuǎn),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yuǎn)乎?”又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也。”“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這些有關(guān)士的特征的論述,高度地肯定了士的超越品格。
老子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在此處所說的“上士”,即是《論語》中所說的“任重道遠(yuǎn)”的“弘毅”之士。在老子的思想體系中,“道”在人類社會(huì)即是公正、合理的代名詞。最具有士之德行的“上士”,是以謀求社會(huì)公正、合理為己任的人物。老子所說的“上士”與《論語》中所說的“弘毅”之士,在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都具有關(guān)懷社會(huì)、救濟(jì)蒼生的超越品格。因此,“士”從此種超越品格意義上說,即代表了“社會(huì)良心”。
“士”的超越品格是就士的理想性品質(zhì)而言的。“士”亦是人,他必須生活在特定的社會(huì)歷史之中,因而,他們總是表現(xiàn)為具體歷史中存在的“士”,受到特定社會(huì)的政治、經(jīng)濟(jì)、教育、文化體制的影響。在周王朝的政治體制下,士分為三等:上士、中士、下士,整個(gè)士階層是當(dāng)時(shí)周王朝各諸侯國下面最低一級(jí)的官員,而在周天子的宮廷里,士是沒有爵位的。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士的經(jīng)濟(jì)收入狀況是:“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3]在周王朝的朝廷里,元士享受的經(jīng)濟(jì)待遇與子、男相等,“元士受地視子男”[4]。
按照孟子所設(shè)想的理想狀態(tài)來推算,上等農(nóng)夫耕種百畝之田,再加上足夠的肥料,可以養(yǎng)活九口人,稍差一點(diǎn)的亦可以養(yǎng)活八口人;中等的農(nóng)夫可以養(yǎng)活七口人,差一點(diǎn)的可以養(yǎng)活六口人;最差的亦可以養(yǎng)活五口人。[5]那么,一個(gè)下士,其祿足以代耕,則他的年收入最次可以養(yǎng)活五口人,最理想的狀況可以養(yǎng)活九口人。而一個(gè)上士的年收入是下士的四倍,則上士的理想狀態(tài)可以養(yǎng)活三十六口人,最差的狀況亦可以養(yǎng)活二十口人。因此,從經(jīng)濟(jì)的角度來看,士基本上是一個(gè)不事農(nóng)工商賈而僅靠俸祿生活的食稅階層。他們的經(jīng)濟(jì)收入來源于統(tǒng)治者給的俸祿,在利益上基本傾向于維護(hù)統(tǒng)治者;但他們又是處在社會(huì)統(tǒng)治階層的最底層,掌管各種具體事務(wù),對(duì)民生疾苦有比較真切的了解,且與一般民眾的生活沒有多大差別,也會(huì)經(jīng)常遇到一般人的生計(jì)麻煩,在感情上有同情民眾的傾向。這就決定了正直士人的內(nèi)在人格往往是二元的。從維護(hù)社會(huì)秩序的角度出發(fā),他們既批評(píng)統(tǒng)治者的苛政,亦反對(duì)下層民眾造反。
事實(shí)上,春秋以降,士的社會(huì)地位不斷下降。老子的具體生活狀況不知,但有一點(diǎn)是肯定的,他是從貴族階層的劇烈權(quán)力之爭中抽身出來的,故有生命的危機(jī)感,主張“保身全生”。孔子則一生恓恓惶惶,沒有固定收入,靠周游列國,教育學(xué)生來謀取生活之資。當(dāng)然,這可以說是因?yàn)榭鬃訄?jiān)持自己的“士”人理想導(dǎo)致的,體現(xiàn)了“士”的理想性品格。不過,在孔子及其弟子生活的時(shí)代,“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基本社會(huì)條件對(duì)于士人來說,還是存在的。士可以通過自己所掌握的知識(shí)去謀取俸祿。孔子的弟子子路、冉有等人都曾出仕。
戰(zhàn)國以降,士的成分就復(fù)雜起來,其內(nèi)部的分化也劇烈了。像子路、宰我、墨子及其弟子,均是由下層社會(huì)庶人上升為“士”的,而像稍后一點(diǎn)的孟子、莊子則又是屬于沒落貴族的士人。整個(gè)戰(zhàn)國時(shí)代的士人成分頗為復(fù)雜,有像蘇秦、張儀一類的策士,也有像墨子、魯仲連這樣的義士,還有像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等“稷下士人”。他們雖列于上大夫之列,但都是一些“不治而議論”的人物,與諸侯王之間沒有君臣關(guān)系,相對(duì)地保持著人生與思想的自由。還有像孟子、莊子一類的士人,他們既非隱士,又因?yàn)椴缓献约旱睦硐攵鴽]有或不愿去做官,靠周游列國,教授門徒,有的甚至是靠自己的勞動(dòng)來謀生,同時(shí)又關(guān)懷現(xiàn)實(shí),著書立說,猛烈地抨擊社會(huì)的黑暗。
像蘇秦、張儀之流,他們并無政治信仰,主要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軍事知識(shí)來謀求個(gè)人的榮華富貴,應(yīng)屬于墨子所說的“別士”之列。而像墨子、魯仲連之類的士人,則可以說是謀求天下利益的“兼士”。騶衍、淳于髡之類的士人則比較特別,他們雖列于士大夫之列,但保持著士人的相對(duì)獨(dú)立性。而像孟子、莊子等人,則更多地帶有古代自由知識(shí)者的特點(diǎn)。他們有自己的政治理想,關(guān)懷天下,批判現(xiàn)實(shí)的不合理,同情民眾的苦難,表現(xiàn)出一定的超越性品格。
就士的超越性品格來說,孟子的一段話最有典型意義,他說:“民無恒產(chǎn)而無恒心”,“無恒產(chǎn)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這當(dāng)然是或然判斷,意思是說,民無恒產(chǎn),就可能“放辟邪侈”,無所不為。而“士”當(dāng)中的有些人則可以遵守社會(huì)規(guī)則,堅(jiān)持自己的理想,有所不為,更不會(huì)胡作非為。孔子曾經(jīng)就說過:士若以惡衣惡食為恥,則不足以與他談?wù)摯蟮馈K约簣?jiān)持了這一原則。莊子則為了保持自己的個(gè)性堅(jiān)決不仕。無論是關(guān)懷天下,還是為了保持自己的獨(dú)立個(gè)性,先秦的理想之“士”都有一定的超越性品格,這是“士”之所以為“士”的原因。
可以這樣說,春秋戰(zhàn)國以降的“士”,從其價(jià)值取向來看,主要分為“兼士”與“別士”兩類。兼士以關(guān)懷天下為己任,代表社會(huì)良心;別士則主要謀求個(gè)人利益。從社會(huì)地位和經(jīng)濟(jì)收入來看,有上士、中士與下士三類。與上層貴族接近的“上士”,有的人直接為統(tǒng)治者服務(wù),屬于政治體制下的官僚,大多數(shù)已喪失了士的超越性品格;而那些“不治而議論”的士人,則保持著一定的獨(dú)立性。下層之士,或與庶民接近,或與庶民為伍,或受人接濟(jì),或自謀生路,務(wù)農(nóng)、經(jīng)商,均有人在,這便是后來的隱士。總而言之,這一時(shí)代理想的士人精神,當(dāng)是“關(guān)懷天下”和“獨(dú)持操守”的結(jié)合。理想中的儒家士人,是以守志弘道為己任;理想中的道家士人,則是以保持個(gè)性為主而關(guān)懷天下的治亂,發(fā)出言論批評(píng)現(xiàn)實(shí)的不合理;理想中的墨家士人,則是“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理想中的法家士人,則是按照法治來治理國家的“能吏”,這些“能吏”主要是幫助國君治理諸侯國,防止貴族、大臣、一般民眾私竊國君的權(quán)力和財(cái)富,他們比較缺乏士人的超越性品格。
先秦時(shí)期所奠定的理想的“士人魂”,其基本的內(nèi)蘊(yùn)即是:堅(jiān)持自己的政治理想,獨(dú)持操守,以關(guān)懷天下為己任。
(三)秦漢以后的“士”及士人理想
秦漢以后,伴隨著以農(nóng)業(yè)為主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的確立,政治與文化上的大一統(tǒng)局面的形成,“士”的產(chǎn)生途徑、社會(huì)作用、自身內(nèi)涵,均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粗略地說來,秦漢以后,魏晉以前,儒、道、墨、法四家漸趨合流,而以儒、道兩家思想為主。士人的個(gè)人理想表現(xiàn)為修身與治世的統(tǒng)一。戰(zhàn)國中晚期“稷下道家”的“內(nèi)圣外王”理想,正好是融儒、墨、法三家的入世精神的新道家在較高層次上對(duì)原始道家——老子思想的回歸,這一“內(nèi)圣外王”的理想,將個(gè)人的人生理想與社會(huì)理想融為一體,并逐漸成為漢以后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中士人的普遍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和人格范式。魏晉以后,隨著佛教的進(jìn)入,這一“內(nèi)圣外王”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得到了充實(shí)、豐富和發(fā)展,“內(nèi)圣”的成分由道家的修身更偏重于修心修性方面,從而使這一人格理想和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更偏重于“內(nèi)圣”,即個(gè)人的道德心性修養(yǎng)。
就士的社會(huì)作用而言,西漢社會(huì)中的士主要扮演了循吏的角色[6];東漢時(shí)期,士則形成了特殊的貴族階層;直至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形成了“士族”階層而漸趨腐化。就士的產(chǎn)生途徑而言,西漢社會(huì)中的士多是秦漢之際的貴族子弟;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的士,既有貴族子弟的上品之士,亦有中下層地主家庭培養(yǎng)出來的寒士。由于曹魏集團(tuán)實(shí)行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制度,魏晉之際士的內(nèi)部分化達(dá)至極點(diǎn),一度出現(xiàn)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嚴(yán)重分裂局面。
就士的超越性而言,西漢一代的士人主要在循吏傳統(tǒng)中得到了落實(shí),他們?cè)诠龍?zhí)法過程中實(shí)現(xiàn)了關(guān)懷天下的理想。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士的超越性品格最為模糊。東漢時(shí)期,只有在像王充這樣的下層寒士身上,才能看到先秦理想型之士的光芒;東漢末年的太學(xué)生及所謂的士之“清流”,在維護(hù)皇權(quán)、反對(duì)宦官專政的斗爭中,多少體現(xiàn)了一點(diǎn)關(guān)懷天下的現(xiàn)實(shí)內(nèi)容;兩晉南北朝時(shí)期,像陶淵明、鮑敬言等下層士人代表了社會(huì)的良心。陶淵明高唱“先師有遺訓(xùn),憂道不憂貧”;鮑敬言著書立說,猛烈抨擊君主對(duì)社會(huì)的危害性,表現(xiàn)了對(duì)下層民眾憂樂的關(guān)懷。自道教興起,佛教傳入并受到一些士人的喜愛之后,士的超越性品格在宗教之中得到了一定的表現(xiàn)。道教著作《太平經(jīng)》中所表現(xiàn)的對(duì)婦女及女嬰的同情,對(duì)當(dāng)時(shí)殘殺女嬰的惡劣社會(huì)風(fēng)俗給予了猛烈的批評(píng),從一個(gè)方面代表了社會(huì)的良心。
隋唐之后,伴隨著科舉制的建立、完備,中國的士人文化傳統(tǒng)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它使士的產(chǎn)生有了合法化、正規(guī)化的途徑。真正意義上的士大夫傳統(tǒng)從隋唐科舉制開始。其次,隋唐科舉制把儒家經(jīng)典以及詩詞、書法、歷史作為考試的內(nèi)容,使得與科舉考試相關(guān)的一系列部類的學(xué)說、文化獲得了高度的重視,儒家學(xué)說獲得了真正的法定地位。從西漢董仲舒開始理想的“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的學(xué)術(shù)一統(tǒng)局面,在政治、教育、用人制度中得到了落實(shí)。傳統(tǒng)各學(xué)派之間的學(xué)術(shù)爭鳴,由自由、平等的狀態(tài)一下子變成了“正統(tǒng)與異端”“官方與民間”“在朝與在野”的爭論,使學(xué)術(shù)爭論更加容易與政治糾纏在一起,不利于學(xué)術(shù)的自由發(fā)展。百家之流的學(xué)說在士人及一般的百姓心中自覺不自覺地變?yōu)榉钦y(tǒng)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教思想,這時(shí)便真的成了士人們失意時(shí)的個(gè)人精神鎮(zhèn)靜劑。“窮則獨(dú)善其身,達(dá)則兼濟(jì)天下”的人生理想模式,在正直士人心中變成普適化的心理結(jié)構(gòu)。
隋唐宋元明時(shí)期,士大夫傳統(tǒng)基本上堅(jiān)持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他們的政治實(shí)踐中程度不一地踐行著“兼濟(jì)天下”的理想。像魏徵、張九齡這些名相,李白、杜甫、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陸龜蒙這些士大夫兼文人,基本上是有唐一代的社會(huì)良心的代表。兩宋時(shí)期,像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蘇軾,在民間傳說中被理想化了的包公、辛棄疾、陸游等人,便成為這一歷史時(shí)期的社會(huì)良心的代表。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后期封建社會(huì)正直士人關(guān)懷天下的精神標(biāo)志;而被理想化了的“包青天”,就成為民眾心中“公正”的代名詞,是士人精神的重要維度。
應(yīng)當(dāng)看到隋唐儒學(xué)發(fā)展的另一方面。伴隨著隋唐佛學(xué)的發(fā)展,特別是中國化的佛教——禪宗的出現(xiàn),對(duì)宋明儒學(xué)的精神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一方面,“新禪宗”的入世踐履精神直接地影響了宋明士人的入世心態(tài)[7];另一方面,“新禪宗”心性理論,華嚴(yán)宗的“法界緣起論”,對(duì)兩宋的“新儒學(xué)”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新儒學(xué)”以內(nèi)圣、涵養(yǎng)為主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原始儒家的“入世精神”。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儒學(xué)的政治化傾向加重,原始儒家的活潑精神遭到扼制。特別是倫理方面的理性自覺,由于受到政治化傾向的影響而異化為“理性專制”,變成了權(quán)威主義的東西,成為壓抑個(gè)性、扼殺新生事物的代名詞。
明中晚期以后,伴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城市文明與商業(yè)文明也得到了較快的發(fā)展,帶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zhì)的工場手工業(yè)在江南一帶蓬勃興起。農(nóng)村的土地商品化過程也在加劇,部分開明的中下層地主也加入了新興的商業(yè)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之中。中國社會(huì)和思想界均發(fā)生了新的變化。首先,正統(tǒng)理學(xué)中的“心學(xué)”,發(fā)展到陽明的“致良知”學(xué)說時(shí),開始走向反面。重功夫,重實(shí)踐,重入世、救世,重經(jīng)驗(yàn)的思想,伴隨著新興市民階層的產(chǎn)生,手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又逐漸成為該時(shí)代進(jìn)步士人的主流思想了。“原儒”思想活動(dòng)成為思想界的一大奇觀,特別是“王學(xué)左派”的出現(xiàn),正式地展開了對(duì)傳統(tǒng)權(quán)威主義的批判。被衛(wèi)道者稱為“異端之尤”的李贄,用犀利的筆鋒批判了以“四書五經(jīng)”為代表的經(jīng)學(xué)獨(dú)斷論,初次揭開了十六世紀(jì)中葉中國思想界的反傳統(tǒng)序幕。這一時(shí)期的進(jìn)步士人,不僅代表了社會(huì)良心,還代表了社會(huì)發(fā)展的新方向,成為將要來臨的新型社會(huì)的理論建設(shè)者。從這一層意義上說,秦漢以后的士大夫傳統(tǒng)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歸到先秦“百家爭鳴”時(shí)期的士人傳統(tǒng)上來了,表現(xiàn)出思想自由后的新的活力。這一反傳統(tǒng)的思潮大體上有三方面的主題:個(gè)性解放的新道德、初步的科學(xué)思想、批判君主專制制度的初步民主思想。[8]具體說來,個(gè)性解放的新道德,在理論層面,主要表現(xiàn)在理欲、情理、義利、古今、個(gè)體的情和思與傳統(tǒng)權(quán)威之關(guān)系的哲學(xué)論說;在現(xiàn)實(shí)層面,主要表現(xiàn)在對(duì)殘害婦女的節(jié)烈觀、“吃人”的忠孝觀、踐踏人性的尊卑貴賤等級(jí)觀以及納妾行為的批判。科學(xué)思想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1.純粹的求知態(tài)度;2.“緣數(shù)以求理”的科學(xué)方法;3.由傳統(tǒng)的“重道輕器”觀向近代的“由器求道”的經(jīng)驗(yàn)論方向發(fā)展,科學(xué)技術(shù)得到了一定的重視。初步的民主政治理想主要表現(xiàn)在對(duì)封建君主專制的批判方面,在批判專制主義的同時(shí),提出了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代表歷史發(fā)展方向的“新人文精神”——個(gè)性解放、平等、自由等意識(sh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
晚明之后,中國傳統(tǒng)思想自身發(fā)展出現(xiàn)了儒、道、釋合流的趨勢。“內(nèi)圣外王”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又漸漸傾向“外王”一面。這與明清之際江南地區(qū)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萌芽密切相關(guān)。原始儒家的“社會(huì)功利”傾向在新的時(shí)代成為統(tǒng)治階級(jí)內(nèi)部開明官吏要求發(fā)展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理論武器。道家的“自然人性論”思想成為反對(duì)倫理領(lǐng)域里“理性專制”“倫理異化”的思想源泉,而且也是個(gè)性解放的思想武器。原始儒家的“仁愛”精神、道家的“自然主義”、佛教的“慈悲意識(shí)”和墨家的“兼愛”思想,共同構(gòu)成了新時(shí)期的“人道主義”和“自由意志”的思想源泉。
西學(xué)的傳入,在當(dāng)時(shí)雖不占重要位置,卻加重了“外王”的砝碼,而且在日后的歷史進(jìn)程中越發(fā)顯示出其重要性。
就斷代史的情況來看,明清之際的先進(jìn)歷史人物,雖然在整體上還保持著“內(nèi)圣外王”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但已偏向于“外王”。而“內(nèi)圣”的思想內(nèi)涵也已經(jīng)稍稍發(fā)生了變化。道家的原始自然主義逐漸蛻變?yōu)樽杂芍髁x;儒家的人格、氣節(jié)逐漸蛻變?yōu)閭€(gè)性主義;而佛教的慈悲情懷、儒家的仁愛思想、墨家的兼愛思想,逐漸蛻變?yōu)閹в薪鷼庀⒌娜说乐髁x;儒家的愛民、民本思想,道家的惠民思想,墨家的利民思想,逐漸蛻變?yōu)椤懊裰鳌彼枷耄憩F(xiàn)出極大的人民性特征。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文化所形成的士人處世原則:“窮則獨(dú)善其身,達(dá)則兼濟(jì)天下”,就逐漸蛻變?yōu)楸3謧€(gè)性、伸張個(gè)性、救世濟(jì)世、批評(píng)世俗的處世原則。道家的批判色彩,儒、墨的入世精神,佛教的慈悲情懷,非常奇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了反對(duì)封建等級(jí),反對(duì)束縛個(gè)性的新人文精神和關(guān)懷現(xiàn)實(shí)、改造社會(huì)的新的社會(huì)理想。板橋魂,正是奠基于傳統(tǒng)士人魂基礎(chǔ)上,又表現(xiàn)出鮮明的時(shí)代特征,那就是:積極的批判精神,追求自由意志、平等理想和個(gè)性精神。
二、板橋魂與士人魂
鄭板橋,這個(gè)竟然能將“四書”默寫得一字不差的人,其靈魂深處首先打上的是儒家精神的烙印。在他血管里流淌的主要是原始儒家的民本理想。
(一)“大丈夫立功天地,字養(yǎng)生民”——板橋的責(zé)任意識(shí)
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中的正直士人,大都帶有強(qiáng)烈的“責(zé)任意識(shí)”和入世情懷。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學(xué)說,使得傳統(tǒng)的中國士人在極其困難的人生處境里不易逃脫到宗教之中。特別是在儒家學(xué)說浸淫秦漢以后的中國文化之后,士人的這種“責(zé)任意識(shí)”就更為強(qiáng)烈。生在清朝盛世的鄭板橋,在科舉取士而又以朱熹集注的“四書”為考試內(nèi)容的時(shí)代氛圍下,不能不感染這一傳統(tǒng)文化精神。他以自己獨(dú)特的個(gè)性和獨(dú)特的人生經(jīng)歷,使這一抽象、普遍的文化精神,獲得了個(gè)性的生命形式,從而展示了這一文化傳統(tǒng)的生命力。
八股取士及其用人制度,固然扼殺了一大批不羈之才,也培養(yǎng)了一批官場蠹吏。然而,對(duì)于那些下層寒儉之士,科舉途徑則是他們改變自己身份,為民為國效力的唯一“正途”。他們長期居于下位,經(jīng)受著生活的磨難,“四書”“五經(jīng)”中所蘊(yùn)含的“民本思想”、憂國憂民意識(shí),恰恰教給他們以強(qiáng)烈的責(zé)任情懷。鄭板橋,這位出生于下層士人家庭的寒儉之士,正是從這些經(jīng)典中汲取了憂患天下、立功天地、字養(yǎng)生民的思想精華。尤其是在他獲得了七品縣官的職位,能夠施展個(gè)人經(jīng)世才能的時(shí)候,他的這種責(zé)任意識(shí)更為強(qiáng)烈。縱觀板橋詩歌、家書,其中表達(dá)強(qiáng)烈經(jīng)世意識(shí)的作品,均是在做吏山東時(shí)所作,揭露現(xiàn)實(shí)矛盾的詩歌如《逃荒行》《還家行》《孤兒行》《姑惡》等代表作,均創(chuàng)作于任職范縣和濰縣的時(shí)候。在《與舍弟書十六通》中,板橋大講關(guān)心民瘼、字養(yǎng)生民的道理。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板橋告誡其弟:“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后,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并認(rèn)為這是正直的讀書人高于農(nóng)夫一籌的原因所在。而那些“銳頭小面”的人物,“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jìn)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多置田產(chǎn)”,對(duì)這種人,板橋最為痛恨。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中,板橋借論詩大談“憂國憂民”的道理。他認(rèn)為杜甫的詩之所以“高絕千古”,就是因?yàn)樗诿}時(shí)“已早據(jù)百尺樓上”,那就是或“悲戍役”,或“慶中興”,“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墟,關(guān)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在《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五書》中,板橋大談文章經(jīng)世的道理,并衷心地稱贊諸葛亮為民立功的人生,不同意一般文人或幫閑文人所認(rèn)為的那樣,把“寫字作畫”看作是雅事。板橋說:“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yǎng)生民,而以區(qū)區(qū)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為心,以其余閑作為枯竹石,不害也。”至于像王摩詰、趙子昂等,只是“門館才情,游客伎倆”,不足稱道。他認(rèn)為,只有諸葛亮才真正稱得上“名士”二字,而當(dāng)時(shí)街上“寫字作畫”之輩也妄稱名士,真是令人可羞。板橋這種偏激的“功利”藝術(shù)觀念,固有其不妥之處,但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了他的責(zé)任意識(shí)與濟(jì)世情懷。
在為官山東之時(shí),板橋在權(quán)勢與金錢的夾縫里,為民眾辦了不少好事,艱難地踐履著“立功天地,字養(yǎng)生民”的人生理想。他在任范縣知縣時(shí),“愛民如子,絕苞苴,無留牘”。調(diào)任濰縣時(shí),恰遇荒歲,人人相食。鄭板橋“開倉賑貸”,“發(fā)谷若干石,令民具領(lǐng)券借給,活萬余人”。這一系列的“字養(yǎng)生民”的政治行為,充分地展示了板橋的“責(zé)任意識(shí)”。
相比稍前的蒲松齡、同時(shí)代的吳敬梓來說,鄭板橋在科舉制度下算是幸運(yùn)者,畢竟,他還中了進(jìn)士。雖然他發(fā)跡很遲,五十多歲才得了七品縣令之職,但他還是獲得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jī)會(huì),實(shí)現(xiàn)了那個(gè)時(shí)代絕大部分士人的美夢。但板橋與一般士人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沒有把當(dāng)官看作是個(gè)人發(fā)財(cái)之道,沒有喪失正直士人的良心。在板橋身上還流淌著道家批判現(xiàn)實(shí)的熱血,還存留著陶淵明、蘇軾等士人“不為五斗米折腰”、不阿附權(quán)貴的正氣。還有道家那超越的氣質(zhì),使得板橋有一種不屑與現(xiàn)實(shí)同流合污、不怕辭官歸隱等傳統(tǒng)士人的優(yōu)秀精神氣質(zhì),這一精神氣質(zhì),使得板橋無論是未仕之前,還是既仕之后,都能保持一種獨(dú)立的精神品格和追求自由的超越意志。
(二)道家的批判意識(shí)與遁世情懷
在陶淵明、蘇軾等人身上,集中地體現(xiàn)了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中國傳統(tǒng)士人的自由意志。他們?cè)诂F(xiàn)實(shí)的種種束縛中,往往借酒和藝術(shù)來抒發(fā)心中抑制不住的自由意志。板橋亦如此,他雖不善酒,卻十分愛酒,時(shí)時(shí)離不開酒,且善書、善畫。在做官之余,在牢騷之際,詩、酒、書、畫就成了他發(fā)泄心中感情,抒發(fā)心中苦悶的最好工具。未仕之前,他一方面自與心競,發(fā)憤攻書,精進(jìn)于藝;另一方面用詩歌、酒來發(fā)泄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不滿,用道家的超世精神來批評(píng)現(xiàn)實(shí),否定現(xiàn)實(shí)的意義,如在《道情十首》中,板橋高唱“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用遁隱到山中去的人生閑適來代替現(xiàn)實(shí)的仕途進(jìn)取。既仕之后,為了排遣官場上應(yīng)酬之苦,舒展被壓抑的人性,亦借詩、書、畫、酒來宣泄心中的郁悶。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往往在人生失意之時(shí),板橋?qū)Ψ饨ㄉ鐣?huì)的致命病根反而有更清醒的認(rèn)識(shí)。組詞《瑞鶴仙》中的《官宦家》《帝王家》兩首,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家天下必然滅亡的命運(yùn),比起他早年創(chuàng)作的《道情十首》具有更鋒利的批判鋒芒。《官宦家》說道:“羨天公何限乘除消息,不是一家慳定。任憑他鐵鑄銅鐫,終成畫餅。”對(duì)封建家天下必然滅亡的趨勢有清醒的認(rèn)識(shí)。《帝王家》則批判了禹、湯以私廢公的政治行為,歌頌了理想中“廢子傳賢”的陶唐時(shí)代的“公天下”,并朦朧地意識(shí)到了私有制家天下的根本毛病:“藩王”“戚里”是造成封建家天下滅亡的根本原因。這與明清之際大思想家對(duì)封建政治的批判思想,在精神上基本一致,體現(xiàn)了板橋批判意識(shí)的時(shí)代特征。
在為官不順之時(shí),道家的歸隱意識(shí)往往成為板橋抗拒官場誘惑的精神動(dòng)力。如在濰縣之時(shí),由于不堪官場的束縛,他氣憤地唱道:“烏紗擲去不為官”,歸隱揚(yáng)州,寫字作畫,自謀生路,自暢性情。可以說,道家的批判意識(shí)與遁世情懷,為板橋提供了精神家園,在特定的時(shí)代,為他的積極進(jìn)取提供了精神的動(dòng)力。正因?yàn)樗慌職w隱田園,他在官場上就有敢作敢為的膽量,就有為民做主的精神動(dòng)力。道家的遁世情懷,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消極的,但在特殊的歷史人物身上卻表現(xiàn)為積極的精神。
(三)佛教的“和世意識(shí)”與板橋的寬容情懷
板橋?qū)Ψ鸾滩o研究。他雖也一再表示要拒斥佛、道二教的誘惑,“不燒鉛汞不逃禪”,但并不反對(duì)佛、道二教,不僅與僧人、道士唱和,而且還為佛教辯護(hù)。他認(rèn)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的和尚是“佛之罪人”,佛教本身并無過錯(cuò)。他并不贊同當(dāng)時(shí)人將僧人斥為“異端”的觀點(diǎn),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的僧人,大多是“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叱為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而在“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jīng)》《四子》之書,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的時(shí)候,再言辟佛,“亦味同嚼蠟而已”。
從現(xiàn)存的文字資料來看,板橋只是粗略地接受了佛教的“和世思想”和帶有辯證意味的寬容意識(shí)。如在板橋的印章中有“多種菩提結(jié)善緣”“結(jié)歡喜緣”“歡喜無量”“隨喜”等印,這些印章表明了板橋企圖以佛教的和世思想來改變自己與世抗?fàn)幍男愿瘢憩F(xiàn)了晚年的板橋與世俗妥協(xié)的心理。他在《為松侶上人畫荊棘蘭花》的題識(shí)中寫道:“不容荊棘不成蘭,外道天魔冷眼看。門徑有芳還有穢,始知佛法浩漫漫。”這是板橋從佛教中汲取的寬容意識(shí)的表現(xiàn)。當(dāng)板橋魂里的和世意識(shí)、寬容情懷與儒家的“天道觀”結(jié)合在一起的時(shí)候,就表現(xiàn)為一種朦朧的追求自由的意志。他在《家書》中所表達(dá)的“善惡俱容納”思想,實(shí)質(zhì)上就是對(duì)專制政治的一種抗議。如《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便大談天道“善惡俱容納”的寬容意識(shí)。在題畫詩中,他用形象的語言說,要讓荊棘與竹共長,并稱這與張載的思想是一致的:“莫漫鋤荊草,由他與竹高。《西銘》原有說,萬物總同胞。”[9]非常巧妙地將佛教的和世意識(shí)、寬容情懷與儒家的仁愛思想結(jié)合起來了。
(四)傳統(tǒng)意義的出處原則——“兼濟(jì)天下”與“獨(dú)善其身”的統(tǒng)一
板橋的靈魂里,其基本的人生態(tài)度是傳統(tǒng)士人的“出處原則”。在他未中進(jìn)士之前,一種強(qiáng)烈的用世情懷時(shí)時(shí)在心中激蕩;而他中進(jìn)士之后等待做官的一段日子里,這種心態(tài)表現(xiàn)得更為急迫。在這段時(shí)間里,他與京城里的達(dá)官貴人乃至于一般的小官,多有詩作唱和。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四首,其中第四首便是干謁之詩。而《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zhí)政》一詩云:“常怪昌黎命世雄,功名之際太匆匆。也應(yīng)不肯他途進(jìn),惟有修書謁相公。”從自己干謁的親身經(jīng)歷中理解了韓愈為何上書宰相大人求官,一個(gè)正直的士人,又不能用賄賂的方法去謀取官職,只有上書王公大人,方為一條不失體面的上進(jìn)之路。板橋就這樣直率地表達(dá)了自己求官時(shí)曾有過的急迫心情。
可是,一旦真的為官之后,官場的污濁,事務(wù)的紛擾,長期的不得升遷,又使他感到十分失望。一種歸隱之意涌上心頭。從乾隆十四年(1749年)為載臣作《自詠》詩起,板橋便開始對(duì)官場產(chǎn)生厭倦之情了。其首要原因是多年不得升遷。該詩這樣寫道:“濰縣三年范縣五,山東老吏我居先。一階未進(jìn)真藏拙,只字無求幸免嫌。”當(dāng)立功天地、字養(yǎng)生民的理想化為泡影之后,失望的情緒便油然而生。時(shí)至他五十九歲那年,這種為官與歸隱的矛盾達(dá)到高潮。是年九月作“難得糊涂”橫幅,又作《梅蘭竹菊四屏條》,其中“菊”條的題識(shí)寫道:“進(jìn)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菊,歸去秋風(fēng)耐歲寒。”該年十一月,書舊作《濰縣竹枝詞》,回憶起乾隆十二年“告災(zāi)不許,反記大過一次”的不快經(jīng)歷,退隱之志更加堅(jiān)決了。特別是當(dāng)時(shí)濰縣連年災(zāi)荒,板橋在救災(zāi)活動(dòng)中也已深感疲倦了,他需要休息,需要放縱自己束縛已久的個(gè)性,于是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思?xì)w行》詩,《思?xì)w》和《思家》兩首詞,又作七言聯(lián):“作畫題詩雙攪擾,棄官耕地兩便宜。”乾隆十七年秋九月,六十歲的鄭板橋作《蘭竹石圖》,其題識(shí)曰:“世間盆盎空栽植,唯有青山是我家。”清醒地意識(shí)到只有擺脫官場的束縛,才能獲得自由。這時(shí),再加上濰縣的豪紳、不法大商聯(lián)合攻擊,誣告板橋貪賄,板橋?yàn)榱吮Wo(hù)自己,“獨(dú)善其身”的傳統(tǒng)意識(shí)最終占了上風(fēng)。在板橋的靈魂里,“兼濟(jì)天下”與“獨(dú)善其身”就這樣巧妙地統(tǒng)在一起。
三、板橋魂的時(shí)代意蘊(yùn)
受過明末清初反理學(xué)、反權(quán)威思想運(yùn)動(dòng)的洗禮,傳統(tǒng)士人魂的內(nèi)涵已經(jīng)悄悄地發(fā)生了變化。一種反權(quán)威的理性精神在該時(shí)代進(jìn)步的士人心中生根發(fā)芽了。特別是那些下層士人,因?yàn)槠渖硎赖钠閸绮黄剑菀捉邮苄滤枷搿K麄儚母髯蕴厥獾娜松?jīng)歷出發(fā),自覺地尋找自己的精神同路人或表達(dá)自己思想的合適方式,在不同的領(lǐng)域展現(xiàn)著時(shí)代精神。板橋在他的前輩中則找到了與自己精神氣質(zhì)相近的徐渭、高鳳翰,從他們二人身上吸取了一股“倔強(qiáng)不馴之氣”。
(一)“倔強(qiáng)不馴之氣”
板橋認(rèn)為,自己身上有著與徐渭、高鳳翰在精神上的相通之處,那就是都擁有一股“倔強(qiáng)不馴之氣”。這種“倔強(qiáng)不馴之氣”實(shí)是板橋魂的時(shí)代內(nèi)蘊(yùn)之一,它是板橋個(gè)性的生動(dòng)體現(xiàn)。在板橋的詩文、題識(shí)中,多次以不同的語言形式表達(dá)了這一追求個(gè)性的思想。在《板橋自序》中他說“自憤激、自豎立,不茍同俗”,在《劉柳村冊(cè)子》中講要“怒不同人”,在《板橋后序》中說自己的詩詞“亦頗有自鑄偉詞者”。他一再強(qiáng)調(diào)自己的詩歌是“自出己意”,“直攄血性”,反對(duì)別人用“高古而幾唐宋者”的復(fù)古主義的標(biāo)準(zhǔn)來評(píng)價(jià)自己的詩歌,自信地認(rèn)為自己的詩文若能流傳,必將以清詩、清文而流傳。在《與江昱、江恂書》中,他告誡后學(xué)說:“學(xué)者當(dāng)自樹其幟。”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中,告誡其弟道:“豎儒之言,必不可聽,學(xué)者自出眼孔、自豎脊骨讀書可爾。”在他的印章中便刻有“橫掃”“江南巨眼”“心血為爐熔鑄古今”等印,表現(xiàn)了板橋不為人所囿,折中古今的個(gè)性特征和歷史批判精神。
(二)“詩書六藝,皆術(shù)也”
重視百姓日用,重視器、術(shù)的作用,反對(duì)空談性命、性理,是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想的內(nèi)涵之一。在板橋的思想中,這種思想亦很突出。在《板橋自序》中,他公開地批評(píng)理學(xué)空談無用:“理學(xué)之執(zhí)綱紀(jì),只合閑時(shí)用著,忙時(shí)用不著。”他稱自己的《十六通家書》:“絕不談天說地,而日用家常,頗有言近指遠(yuǎn)之處。”在《焦山別峰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中,他雖稱“‘六經(jīng)’之文,至矣盡矣”,但他又認(rèn)為只有那些關(guān)系到家常日用的務(wù)實(shí)篇章才最為有用:“渾淪磅礴,闊大精微,卻是家常日用,《禹貢》《洪范》《月令》《七月流火》是也,當(dāng)刻刻尋討貫串,一刻離不得。”這實(shí)際上是借“六經(jīng)”之名而抒發(fā)自己重視家常日用的思想,把作為權(quán)威主義的“六經(jīng)”變作為家常日用服務(wù)的工具性“六經(jīng)”。在康雍乾三朝極力抬高“四書五經(jīng)”,又動(dòng)輒興起“文字獄”的時(shí)代,說話不能不小心,非經(jīng)非圣要在尊經(jīng)尊圣的前提下進(jìn)行,不能像李贄、黃宗羲等人那樣直截了當(dāng)?shù)嘏u(píng)經(jīng)典、反對(duì)權(quán)威。在板橋印章中,刻有“麻丫頭針線”“吃飯穿衣”“私心有所不盡鄙陋”等印,這些印章,從精神實(shí)質(zhì)上與李贄的思想是相通的。在“活人一術(shù)”印章的題識(shí)中,比較充分地表達(dá)了板橋鄙視“詩書六藝”,重視實(shí)際技藝的思想,這與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重器”“重技”的新思想一脈相通。板橋說:
詩書六藝,皆術(shù)也。生兩間而為人者,莫不治一術(shù)以為生,然第賴此以生,而非活人之術(shù)。有術(shù)焉,疾痛困苦,瀕亡在即,而以術(shù)治之,無不安者,斯真活人之術(shù)矣。吾友蕉衫,博學(xué)多藝,更精折肱之術(shù),因?yàn)橹鞔擞。①O以頌曰:存菩提心,結(jié)眾生緣,不是活佛,便是神仙。
板橋本人的書畫技藝,也可以說是“活人一術(shù)”。《清史列傳》中記載,晚年的鄭板橋,“時(shí)往來郡城,詩酒唱和。嘗置一囊,儲(chǔ)銀及果食,遇故人子及鄉(xiāng)人之貧者,隨所取贈(zèng)之”。而這些贈(zèng)人的銀兩,乃是他賣書賣畫所得。這種重技、重藝、重視百姓日用的思想,恰是那個(gè)崇尚“社會(huì)功利”,反對(duì)離器言道,認(rèn)定道不離器,器中有道,提倡由器求道的時(shí)代精神折光。
(三)人道情懷
十八世紀(jì)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在他的《百科全書》中曾收錄了“人道主義”一詞。該詞條(作者為無名氏)認(rèn)為:“人道主義”是“百善之源”,它是指“一種對(duì)一切人的仁慈情感,而只有那些具有偉大而敏感的靈魂的人,才會(huì)被它所激動(dòng)”,“有著這種感情,一個(gè)人就會(huì)愿意寬恕整個(gè)世界,以求消滅奴役、迷信、罪惡和不幸”。“人道主義的感情使我們不去看他人的缺陷,但使我們疾惡如仇。”將這一“人道”的定義用在板橋及中國早期啟蒙學(xué)者身上,亦是恰如其分的。
在《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中,板橋認(rèn)為所有的人都是黃帝、堯、舜之子孫,那些不幸為臧獲、婢妾、輿臺(tái)、皂隸之輩,并非天生如此卑賤,應(yīng)該同情他們。即使是盜賊、囚犯、殺人犯,也應(yīng)同情,“盜賊亦窮民耳”;世上僧人,也多是“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無須“叱為異端而深惡痛絕之”。在《濰縣署與舍弟墨第二書》中,板橋告誡其弟,教育子弟“務(wù)令忠厚悱惻,毋為刻急也”,“不要屈物之性以適吾性”。天生萬物,一蟲一蟻,皆是上帝愛心的體現(xiàn),“蛇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但人仍然不能隨意殺戮它們,更不能將它們斬盡殺絕,“亦惟驅(qū)之使遠(yuǎn),避之使不相害而已”。真正的“天道”,乃是“善惡無不容納者”。而且也只有體“天道”之心,方能保持永恒的生命活力。
與口頭上的仁者不同,板橋是實(shí)踐的“人道主義”者。還在他當(dāng)秀才時(shí),就揀出家中的券契,暗自燒掉,以免當(dāng)面退還,添人難堪。在《家書》中,他告訴其弟,對(duì)待佃戶要寬厚,他們有所不便之處,要周給幫助,借債不能按時(shí)償還的也不要去硬逼,要寬讓期限;不要以主戶的姿態(tài)去對(duì)待佃戶,要平等待人,“主客原是對(duì)待之意”;在對(duì)待自家子弟時(shí),不要過于溺愛,分發(fā)果食之時(shí),亦要分發(fā)一些給家人的孩子,以免這些孩子遠(yuǎn)遠(yuǎn)而望,十分可憐,而他們的父母在遠(yuǎn)處望見,有剜心割肉之痛。他出任范縣縣令之后,要求其弟把一部分官俸分派給族里窮人、往日的落第同學(xué)、村中無父無母的孤兒。在濰縣當(dāng)縣令時(shí),由于災(zāi)荒,百姓無法交納賦稅,板橋便帶頭捐獻(xiàn)官俸,以充賦稅。所謂“橐中千金,隨手撒盡,愛人故也”(《淮安舟中寄舍弟墨》)。在印章中,他曾刻有“恨不得填滿了普天饑債”“痛癢相關(guān)”等印,真切地表達(dá)出板橋的“人道”情懷。
板橋之仁,還澤及枯骨。《焦山雙峰閣寄舍弟墨》中,板橋購買一塊墓地,這塊墓地,其先人亦曾想買,因考慮到有無主孤墳一座,不忍刨去,遂而作罷。板橋想到,如若他不購買,將來必有人買,這座孤墳仍然被刨,不如買下這塊墓地,留此孤墳,“以為牛眠一伴”,“刻石子孫,永永不廢”,“清明上冢,亦祭此墓,卮酒、只雞、盂飯、紙錢百陌,著為例”。他告誡其弟:“夫堪輿家言,亦何足信!”這顯然是在向當(dāng)時(shí)的世俗迷信勢力挑戰(zhàn)。在《新修城隍廟碑記》中,用巧妙的散文筆法將“人神”“天神”還原為人的形象,揭示了所有的神乃是人的異化的道理,顯示了板橋破除迷信、醇化民俗的革新精神。
板橋好罵人,疾惡如仇,“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體現(xiàn)了君子能愛人能惡人的勇氣。
板橋博大的愛人情懷,已遠(yuǎn)遠(yuǎn)地超逸了傳統(tǒng)儒家,特別是后來政治化儒家的“仁愛”思想。在實(shí)際生活中,真實(shí)地踐履著原始儒家“泛愛眾而親人”和宋儒張載“民胞物與”的理想。這一愛人情懷,雖然奠基于傳統(tǒng)仁愛、兼愛、道家的自然主義、佛教的寬容意識(shí)基礎(chǔ)之上,但又是這些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綜合、創(chuàng)新,表現(xiàn)出具有濃郁近代氣息的“人道主義”情懷。
(四)朦朧的自由意志
板橋魂中的時(shí)代意蘊(yùn),還表現(xiàn)為朦朧的追求自由的意識(shí)。他在題畫詩中一再反對(duì)盆栽蘭花,也很少畫盆中之蘭,而是多畫山中之蘭,要成全蘭花的天趣、野性,“畫蘭切莫畫盆罌,石縫山腰寄此生。總要完他天趣在,世間栽種枉多情”。又說:“烏皮小幾竹窗紗,堪笑盆栽幾箭花。楚雨湘云千萬里,青山是我外婆家。”他不愿因循舊跡,而要表現(xiàn)自己拂云擎日的高遠(yuǎn)意志,故而打破常規(guī):“畫工何事好離奇,一干掀天去不知,若使循循墻下立,拂云擎日到何時(shí)?”他晚年追求“亂”的境界,即是自由的境界,是通過審美活動(dòng)而表現(xiàn)出來的自由意志。
(五)寄情未來
馮契先生曾多次說過,近代思維的一大特點(diǎn)是寄情未來,而不再是歌頌遠(yuǎn)古。在板橋魂里,雖然還沒有明確的寄情未來的詞句,但在畫竹的題識(shí)中,對(duì)新竹、新篁的贊美,便朦朧地表現(xiàn)出憧憬未來的理想:新竹高于舊竹枝。如詩句云:“渾如燕剪翻風(fēng)外,此是新篁正少年。”“新篁數(shù)尺無多子,蓄勢來年少萬尋?”又有詩云:“春雨春風(fēng)正及時(shí),亭亭翠竹滿階墀。主人茶余巡廊走,喜見新篁發(fā)幾枝。”
但是,新生事物需要扶持,否則便難以成才,如板橋畫竹題詩所說:“養(yǎng)成便是干霄器,廢置將為爨下薪。”故鄭板橋寄情未來,并不是簡單地否定傳統(tǒng),而是保持著“新舊相資而新其故”的辯證態(tài)度:“新竹高于舊竹枝,全憑老干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龍孫繞鳳池。”
板橋魂所包含的以上五個(gè)方面內(nèi)容,是他與傳統(tǒng)士人的不同之處,體現(xiàn)了時(shí)代轉(zhuǎn)折時(shí)期進(jìn)步士人新的精神特質(zhì)。這五個(gè)方面的內(nèi)容絕不是簡單地相加,而是有機(jī)的統(tǒng)一體。就板橋思想的時(shí)代傾向性來看,板橋魂實(shí)際上包含著個(gè)性、平等、自由的新思想內(nèi)涵,這正是板橋魂超越傳統(tǒng)士人之處,也是板橋精神的時(shí)代價(jià)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