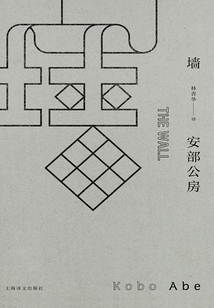
墻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S·卡爾瑪先生的罪行(1)
睜開 眼睛。
早上睜開眼睛乃平常事,不稀奇。但是,怎么怪怪的呢?這有點不對勁。
我這樣想著,覺得完全搞不清哪兒不對勁,的確是怪,莫名其妙……洗過臉、刷了牙,更覺奇怪。
嘗試著(為何想試,也不甚明了)打了個大哈欠。這一來,那種奇怪的感覺突然集中在胸口一帶,我感覺胸腔里空蕩蕩的。心想這是空腹之故吧,便去了食堂(即便不是因這感覺也會去的吧),吃了兩碗湯和一斤半面包。之所以特地寫明數量,當然是為了顯示這并非我的通常食量。
然而,這么做期間,那種怪異感加深,胸腔里更空了,所以我不再吃下去。肚子早就飽了。
我站在柜臺前,接過店里姑娘遞上的賒賬的賬簿。我正要簽名,突然有些遲疑。感覺這種遲疑的確與那怪異感有關聯,我眼望窗外的無限大,想將自己投影于其上。
突然,我察覺自己手拿著筆卻不能簽名,正在為難。我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姓甚名誰。這正是遲疑不決的理由。但是,我沒太驚訝。我知道,正經學術書(并非中傷該學者的書)上明明白白記載著,正熱衷于研究的學者,也總是忘掉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大大方方掏出了名片夾。然而,不巧的是,里面一張名片也沒有。我反復看身份證。奇怪的是,就姓名那一部分沒有了。我慌忙掏出老爸寄來的信——夾在筆記本里的。只有收信人的部分沒有了。我翻起上衣里子的刺繡看。繡的東西也消失了。我不安起來,將褲子、上衣的邊邊角角掏遍,所有紙片過目一次,希望找到啟發自己回想起姓名的東西。但這些東西要不根本沒寫我的名字,要不就是有我名字的部分沒有了。
我焦急起來,試探地問柜臺的姑娘我的名字。挺面熟,她不會不知道的。可是,姑娘只是為難地笑,沒想起來。無奈我只好付了現金。
一回到房間,我就把抽屜翻了個底朝天。剛剛印的名片盒空了。書的藏書印全部消失。晴雨傘的名字牌、帽的里側、手帕的邊角,總而言之,所有記有我名字的地方,那一部分都消失了。
我的臉映照在門玻璃上。一臉非同一般的驚訝表情,我覺得要想一想。但是,除了明白這怪現象應該與胸腔空蕩蕩的感覺有關系之外,什么也不清楚,所以也不去想了。我告訴自己:“這種事情總要時間來解決。而且,明白了的話,肯定沒啥大不了,所以,這事肯定也沒啥了不起。”
紙漿廠的信號笛響了,告知時間是七點半。是上班時間了,得出門,我這才發現包沒了。包里裝著幾份重要的文件,而且這個牛皮包是三個月分期付款買的,所以,焦急之下,我把本無處可找的房間,角角落落翻了個遍,最終只能得出此乃小偷所為的結論。我打算立刻報警,走出了房間。但又放棄了。因為我記起來自己失去了名字。沒名字報不了案吧?我想:“這么說,可能名字也被那小偷拿去了。”如果是這樣,那小偷確實厲害。我很佩服,又很生氣,然后茫茫然就那么向著事務所走去。
交通高峰期的大街,看起來極狂暴未知。自己沒有名字這件事突然讓我非常不安。沒名字走在街上,這體驗絕對是頭一次,一想到這個,就很難為情,太丟臉了。感覺胸中的空虛感擴大了點兒。
抵達事務所似乎比平時稍晚。
在事務所,我首先要做的,是看前臺的姓名牌。第三排左邊第二個,是我的姓名牌。
S·卡爾瑪
S·卡爾瑪……我嘴里反復念叨。這似乎不是我的名字,可也像是我的名字。不過,即便反復念,也沒帶來想起了遺忘之事該有的安心感或感動。漸漸地,甚至不由覺得,是我搞錯了吧?這真是我的名字嗎?但是,那肯定是我的名字,所以,若是堅信如此,就又開始懷疑我之為我,是否也是一個誤解。我晃晃腦袋,想甩掉干擾思考的東西,但還是不能如愿。非但如此,每次晃腦袋,似乎胸中的空虛感就會擴大,所以,我決定不再往下想了。
我按平時習慣,要將姓名牌翻到正面,但令人吃驚的是,它已經正面朝外了。這種錯誤極有可能出現,而且不必去碰那個感覺不是自己的姓名牌的放心感已經涌上心頭,我興沖沖地上樓去自己桌子所在的二層三號室。
三號室的門開著。我的桌子在門口即可看見的地方。我的心走得比身體快十米左右,所以已經在椅子就座,松了一口氣。但我的身體則剛好在門口處突然為原因不明的奇怪感覺所襲,站住了。
令人吃驚的是,我的椅子上端端正正坐著另一個我。
不可能看得到心。我想,這是幻覺。但是,心也慌忙撤了回來,當明白那并非幻覺時,我感到毛骨悚然般的羞恥,不禁使勁把身體縮到門和隔扇屏風背后。因為我不由覺得,被人看見是不可挽回的事情。
很湊巧,從藏身處看,另一個我的情形盡收眼底——他正向打字員Y子口述水泥磚耐火建筑的報告。那個包就放在桌子旁邊。他左手在文件上描畫,右手輕撫Y子的膝頭。看見這些的瞬間,內心深處的羞恥一瞬間爆發,我感到兩眼通紅濕潤。
確實是我。但是,跟看到姓名牌時一樣,承認那是我,就相當于承認我不是我。
耳畔突然響起一聲:“你在這兒干什么!”
遭到了勤雜工的盤問。我想鎮住對方,回視他一眼,對方完全沒認出我,態度蠻橫。我張皇失措,點頭哈腰地答道:“我找卡爾瑪先生……”以這種方式說出自己的名字,實在太難為情了。勤雜工不屑地抬起下巴,說:“有事的話,那位口述打字的,就是卡爾瑪先生。”
似乎另一個我聽見了他的話。他猛地回頭,銳利的目光射來,與我的視線相遇。在這一瞬間,我識破了另一個我的真身——它是我的名片。
如此想來,眼中的它就是一張名片,不管怎么看都不會看錯。它確實就是名片,不覺得是名片以外的東西。
我急忙試著左右眼交替閉上,要查明這雙重影像的理由。在右眼,是我自己的照片,清晰如照鏡子;但左眼中,無疑只是一枚紙片而已。
N火災保險·資料科
S·卡爾瑪
我清楚記得印那張名片時的情況。我豁出去用一百二十日元買了最好的瓦特曼紙,在工會印刷部印制的。我要Y子去取回來,請她喝了七十日元的維也納咖啡作為答謝。
這樣想的時候,名片把文件遞給那個Y子,耳語幾句,堅決地從椅子上站起來。說來它就是張名片,所以用左眼看的話,就像是滑落到地板上。
“有話說的話,到外面去。”
名片說著,唰地從我面前過去。我偷瞥一眼Y子,她專注于打字,看樣子沒注意到我。來自同僚們的兩三道并不和善的目光停在我的上方,但那是偶然、沒有含義的,并不是看我的。我覺得很奇怪,他們竟然沒有識破名片的真身,而認不出我也很奇怪。
名片在走廊盡頭的庫房前回過頭,很粗暴地說:
“你跑這里來究竟要干什么?這里一開始就是我的領地。不是你這種人管閑事的地方。如果被私下對你有興趣的俗物看見了,我們的關系就穿幫了吧?那可就不可收拾了啊。你說,你究竟有什么事情吧!你趕緊給我走吧。說老實話,跟你這樣的人有關系,我實在太難為情了。”
我感覺自己該說的話沉入空蕩蕩的胸腔深處,怎么也出不來。我們面面相覷,沉默了數秒鐘。其間,因為我混亂的思考與感情無關聯地自作主張,甚至像哥薩克舞蹈一樣歡快地跳躍,但有點表達不了。最后,當我想“但是,右眼和左眼看起來居然不同,真太滑稽了。肯定是馬克思的影響”時,名片突然發火:“混賬!”我不禁伸出手去抓他。在我頭腦里面,撕毀的名片業已形成。我甚至有閑情開玩笑,在下面畫一條下劃線,寫上“花費一百二十日元”。
然而,名片意外堅韌,突然變成純粹的名片——哪只眼睛看起來都一樣。名片哧溜一下從指縫之間滑落。我攤開雙手,小心翼翼將其逼至墻邊。而對方一邊惡意地笑,一邊嗖地溜過門縫。庫房總鎖著,鑰匙在勤雜工手上。我明知如此,懊惱之下仍猛拉門把,弄出嘩嘩聲響,結果又被聞聲而來的勤雜工抓住了。
“怎么了?這是怎么回事?”他急忙上前推開我,問道。我好不容易答道:“卡爾瑪先生……”“開啥玩笑!這是庫房。”對方流露出明顯敵意,我無言以對。心情再次由憤怒轉為羞恥,進而轉為恥辱。我默默地擺一擺抬到面前的手,逃跑似的離開了事務所。我不禁把手放在胸口:空虛感越發加深了。
盡管如此,我內心仍抱有希望。名片撤離事務所,肯定得回家。即便是名片,仍是“另一種我”,所以回家的話,肯定是這個房間吧?“它要是回來了,得對它說點什么。必須對它提出嚴重抗議。決不能模糊過去、丑上加丑。本事件的確屬于要徹底追究的種類。”因為最后的臺詞極具權威,很合我意。如果當時沒有拍一下胸口,讓我嚇一跳,我一定熱衷于幻想種種、設計種種說法,最后在斗爭的狂熱中忘乎所以。(不好意思,我性格里面似乎還有這樣的東西。)
然而,我來勁地拍了一下胸口,那異樣的聲響卻讓我猛然醒悟。敲空桶似的空洞響聲,實在不像發自人的胸部。那是一種冷漠、干巴巴的聲音,仿佛只要耳朵聽一下,嘴唇即片片開裂。
我敞開襯衫前襟,學著醫生的架勢,試給自己診斷一下。咚咚的聲音傻傻地響著。我突然寂寞起來,在床上耷拉著腦袋,雙手按著胸口。并不只是空虛感,是我胸口真的空了。我對什么都沒有了自信,對名片必定歸來的信心,也開始動搖。不僅如此,心中不安的話,即使名片回歸,反而是我要被逐出這房間,也并非不可想象吧?要比拼的話,一兩張瓦特曼紙是不在話下,但因為我失去了名字,所以萬事皆不利于我。至少,法律是站在名片一邊的吧。因為這不是失竊,是名字自己出逃了……
馬路對過的肉店開始做油炸土豆餅。差不多十二點了。但我毫無食欲。心情寂寥,想去看醫生。假如胸腔空了,可能醫生會幫我弄清原因。如果知道了原因,名字溜掉的理由也許就知道了。腦子里浮現出動物園角落的那間黃色屋頂的醫院。去動物園的話,搭藍色巴士就一站,即便走路,也就十分鐘。
終于,在法國梧桐的樹影之間,看到了醫院的尖屋頂。
那些林蔭樹下,一個年約五旬的畫家面對空白的畫布,定定坐著。他腳旁蹲著一個流浪兒,正在抓虱子。
醫院寂靜無聲。掛號處的小窗口露出一雙噘著的嘴唇,說道:“什么名字?”
好像還說了別的什么話,但那問題堵在我胸口,我沒聽清。“要名字干什么用?”我只是吃驚,并不生氣,可那嘴唇噘得更高了:“開病歷本要的。”“你說病歷?”“對,病歷。”我感覺這詞兒聽過。
“非要不可吧?”“對,當然。”
果然非說名字不可了。說實在的,一開始我就打算說名字的,然而,我察覺時,已經忘記了。我本想,說說話,中間或許會想起來。于是勉強找話說試試,卻只明白了果真還是不行。但是,我想過了,即使病歷很重要,總不是具有法律意義的東西。所以,簡單說,名字不過是必需的分類記號。因此,就是假的名字,應該也無礙吧。于是,我信口說了一個名字:“卡爾特[1]……”
“嗯?”嘴唇又噘得高了一點。“糟了!”我想,慌忙改口說,“不,是阿爾特。”但是,我覺得這名字也怪,所以又改口。這回雖然意識到音調完全不同,但還是說出了相似的名字:“不,不是阿爾特,是阿爾瑪。”嘴唇噘到最大限度了。看起來像用藥水泡脹的鴨嘴巴。確定無疑是表示不滿的意思。我心里頭也并不十分滿意這名字,所以,我決定最后一次改口:“嘿嘿,又弄錯了。不是阿爾瑪啦,叫阿克瑪[2]才對。”
“阿克瑪……?沒錯吧?呵呵……”嘴唇只留下誦讀寫下的字似的笑,縮了回去(是只有嘴唇,還是整張臉,我不甚清楚)。之后,出現了大眼球。我腦海里分明浮現出在水族館被金魚瞪視的情景。但仔細看,那畢竟是人的眼球。我很明白,一個人名叫“阿克瑪”,的確是搞笑。也想過再次訂正的,但覺得弄多少遍都是一個樣,而且那么干,反而會暴露我沒有名字。相較之下,被人取笑名字倒沒什么,所以,我說聲“是的”,不再多話。
大眼珠縮回去,一聲“請拿著這個”,遞過一張寫著“No.15”的卡片。
在灰暗的候診室,我在彈簧斷了的沙發坐下,等了一會兒。
沙發前有張桌子。桌面上有煙灰缸和西班牙的插圖雜志。我點上一支煙,在膝蓋上攤開雜志。因為我不懂西班牙語,便瀏覽畫作和照片,只挑說明里的固有名詞看。有暴民被警察包圍的照片。有女人伏在被射殺的男人身上痛哭的照片。薩爾瓦多·達利的骸骨,和跳著天鵝之死的芭蕾女演員形象并列。斗牛照片和科涅克白蘭地的廣告并置。緊身胸衣的圖解和雷蒙·拉迪蓋的肖像放在一起。跳過只有文字的頁。然后,翻到了第二十三頁。
這下子,我的眼睛像被那一頁吸住似的動不了了。滿滿一頁曠野風景,從沙丘之間無邊無際延伸到地平線為止。沙丘上的瘦弱灌木、天空中的厚厚云層,像箱子般堆疊。沒有人的影子。不用說家畜,甚至看不見烏鴉的身影。覆蓋曠野的草,像金屬絲一樣又瘦又短、稀稀拉拉,幾乎可透過草看見地面。在草的根部,沙子隨風流動,形成皺褶。
我不禁重重嘆一口氣,發現自己完全陶醉于這幅風景。我沒去過西班牙,不可能見過這個景色,可實在似曾相識。那畫面簡直就像在記憶底部開了個窗口。
不知什么時候,我真站在了那片荒蕪草原上。巨大的云團,正以可怕的速度向這邊崩塌下來。嘩嘩流動的沙子眼看要埋掉鞋子。左手邊的中景有沙丘,沙丘下升騰起帶狀沙塵。竟是饑餓的野鼠群開始轉移。我蹲下來,證實一下腳邊的沙子。沙子從指間簌簌滑落,什么感觸也沒有留下。茫然張開的手指上,落下了一滴水珠,濡濕了。是我的淚水。
我慌忙揉揉眼睛,卻發現我還坐在候診室的沙發上。再嘆一口氣,然后又把目光移到畫上。這是怎么回事?那曠野風景消失了,形跡皆無。只剩光潔的銅版紙亮晃晃而已。是我做夢嗎?
不,不會的。不可能設計成只印上了“23”和該頁標題,整頁空白吧?肯定又是什么事情降臨我身上了。我緊張起來,定定盯著空白頁,努力用全身心去感知是什么事情。
這時,候診室正面的門無聲地打開了,在燦爛的光線之中,出現了醫生的身影。因為逆光,他的身影看上去漆黑。我慌忙擱下雜志,心想被人看見可不得了。醫生漆黑的臉上金牙閃爍。“十五號先生,請過來。”
聽了這話,我不禁微笑了。從早上醒來到現在這段時間,我第一次感到幸福。現實中,像“十五號先生”這種喊法,用來喊人最是安全了吧?人們若能都拋棄名字,以辦事的號碼相稱呼,實在是愉快之至!
即使進入明凈的診室,雖然醫生的身影還是影子般漆黑,令我納悶,但我實在喜歡醫生,不覺得有多可怕。
“怎么啦?”“胸口不對勁……”“哦。”醫生下巴一抬,轉向一邊,“說是胸口異常,寫下來。”隔扇屏風后坐著剛才那個金魚眼。大概在寫病歷吧。“還有呢?”“還有……”我開始逐一說早上發生的事情,但醫生不快地打斷我,說:“說得這么亂,我就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了。回答我的問題就行。嗯,發燒了嗎?”“沒有。”“哦,說是沒發燒,寫下來。咳嗽呢?”“沒有。”“沒有。寫下來。頭疼呢?”“沒有。”“說沒有。寫下來。那么,是肚子疼吧?”“不,不疼。”“哦,不疼。別忘了寫下來。那么,食欲呢?”“不大好。”“不大好!這很重要,寫下來了吧?那,就這樣?”“不,其實……”“簡單說。”“好的,一句話,就是胸口不對勁。”“那就奇怪了。”醫生側著腦袋沉思起來。“想請您診斷一下……”“對了,這樣吧,也只有這樣了。”醫生在椅子上手忙腳亂,很夸張地拿起聽診器,右手食指戳在我胸口上,左右拂開。我連忙解開襯衣扣子。醫生用左手拇指將聽診器按在我胸口上。
醫生瞪著聽診器,眉間開始擠出深深的皺紋。那些皺紋時時刻刻加深起來。而到了左右眼幾乎緊貼在一起時,醫生慌忙摘下聽診器,咳嗽一下,生氣似的說道:“不認為出現異常。”金魚眼叮問道:“沒異常,對吧?”“不是,是不認為異常。你按我說的寫。”
然后,醫生將左手按在我胸口,開始按照慣例叩診。他砰地敲一下,歪著頭聽。然后每敲一下,左右晃晃腦袋。這空洞的聲音,好像把醫生也嚇了一跳。“很難說不異常。”
金魚眼說話了:“醫生,用壓力計測一下胸壓怎么樣?”“你說什么?”醫生也瞪大了眼睛,但馬上又小聲說,“對,試一下看看。”二人在架子上找出蒙了塵的壓力計,金魚眼噗地一吹,醫生嗆著了,咳嗽起來。足有十厘米長的注射針用膠管連接起來。金魚眼往我胸口中央抹了酒精。我的膝頭有點發顫。醫生把注射針哧地扎進我胸口。
水銀柱唰地下降。“一百三十。”金魚眼讀出刻度。“好可怕的負壓!”醫生呻吟般說道。“一早就感覺胸里頭空蕩蕩的。”我解釋道。“一早就是!你為什么不早說?”醫生很生氣的樣子。我很害怕,什么也答不上來。“這情況你得一開頭就說才對啊。”醫生喋喋不休,戴上反射鏡窺看我的眼睛。“咦!”他說著,這回貼上鏡片。“你胸腔里真是空的。”他姿勢不變,對金魚眼說:“巨大的空洞、格羅塞·卡百那的形成……不、不對,這很奇怪嘛。看得見景色。是一個廣闊無邊的沙漠!不,不用寫。我們醫學工作者不能容許非科學的事實。實在太荒唐了。對實證精神這般侮辱,是要搞亂市民社會的秩序的。不用寫。”“用X光查查看怎么樣?”“好主意。你過來。”
X光室內亮著紅色的燈。“你敞開胸部,像抱著這塊板似的,吸氣……”嘎吱一下響起開關的聲音,燈滅了,一片漆黑。
變壓器開始像蟋蟀一樣叫起來。“你看……”響起了醫生的聲音。“哎呀呀……”金魚眼叫喚著。“難以認為這并非異常。”醫生說道。“真的哩。”金魚眼回答。
“這景色感覺見過呀……”
“我也覺得。”醫生的聲音低沉下來。
“啊啊,我想起來了!”金魚眼一拍巴掌叫起來,“是候診室的照片雜志上……那里面有的景色嘛。”“非科學現象!可是,為什么呢?”“這是我的想法啦,正因為他胸壓嚴重負值,一下子就吸進去了吧?”
“喂!”醫生捅一下我的手臂說道,“你有那樣的感覺嗎?”我一籌莫展,絕望地答道:“實在對不起。原想事后道歉的,是這么回事。我沒想要這樣做的,但看得入迷時,照片就消失了。是被我吸走了啊。可是,好意外……”“意外?哦,是吧。照片還好說,按你的說法,喜歡上什么東西了就把它吸走,人家可麻煩了。”紅燈亮起,金魚眼一臉不高興地逼近我。這時,醫生走了樣的聲音像膽怯似的:“算了算了,責備患者也沒用。我們注意什么也不讓他看見就是了。十五號先生也可憐啊,不是出自本身意愿的話,你自己也很麻煩吧。所以,請你馬上離開這里吧。”
兩人同時撲向我,左右把我按住,拽到窗邊,使勁從后把我扔了出去。我腦袋著地摔倒在混凝土人行道上,疼痛和晃眼讓我淚濕臉頰。金魚眼把我的外套丟出來,嘭地關上窗戶。我拍拍外套的塵土站起來,胸腔的空虛感越發深重,悲哀讓周圍的景色更顯得蒼涼。
在法國梧桐的林蔭樹下,剛才的畫家仍以剛才的姿勢,一動不動。在他腳旁,流浪兒仍在捉虱子。走過去時,一回頭,見畫布仍舊雪白,我不禁問一句:“您怎么不畫呢?”“我在等。”畫家眼盯前方,生硬地答道。“您在等什么呢?”“假如明白等什么,誰還會等。”
我覺得很對,又邁開了步子。
告示牌——
之所以向箭頭方向邁步,除了想看動物,也沒有說得上來的理由。我感覺,失去名字的不幸,也許能通過看沒有名字的野獸得到安慰吧。另外就是覺得還有時間,這些時間是用來做什么的,連我自己也不明白。
動物園擠滿小學生,很熱鬧。野獸身上的臭味令人覺得空氣黏黏糊糊的。我決定按以小字標有號碼的告示牌的順序走。除了鳥類籠子,每個獸籠周圍,都是鐵絲垃圾桶、寫有藥品公司廣告的長椅和顯擺飯盒的孩子們。人山人海之處,是鉆進洞里不出來的獅子籠前。而最終,誰都覺得自己一走,獅子馬上會出來,都在依依不舍中轉到下一個獸籠去。我明知如此,也想在空空蕩蕩的籠子前站一會兒,就在它前面停了下來。
這時候,獅子出現了。
獅子伸個懶腰,打了個大大的哈欠。孩子們歡聲雷動。獅子環顧四周,舔一下嘴唇,孩子們互相說:“一定是想吃我們啦。”
突然,獅子的視線跟我的視線相遇。獅子猛抖一下身子。我不禁屏住氣息。獅子靜靜向我走近來。它的臉挨著籠子,瞇縫的眼睛定定地看我,眼神柔和。然后,它輕輕趴下,頭擱在前腳上。感覺它注視我的瞳仁溫潤起來。“叔叔,你是馴獸師嗎?”我身邊的小孩嚇了一跳,說道。
我感覺很混亂,后退兩三步,因自己也理解不了的沖動,也不理會獅子哀傷地發出撒嬌的聲音,急急離去。它想必帶著分不清是羞恥還是不安,抑或二者兼有的悔恨和屈辱留在原處定定地目送我。
熊、大象和河馬對我完全沒興趣,但在斑馬、狼和長頸鹿跟前,情況與剛才相似,我不得不轉過臉,匆匆走過。難以理解的興奮催促著我。很快,我來到了最后的籠子跟前。
這是駱駝的籠子。
雙峰駱駝臟兮兮的,有點禿,躲開垃圾臥在角落里,無聊地啃著木片。這里是動物園最偏遠處,隱藏在廁所后面的樹叢里,所以幾乎沒有觀看的人。而且,大家都看夠了,誰都沒有興致特地在這樣臟兮兮的駱駝籠子前駐足吧。三個頑皮孩子與我錯身而過時,往獸籠里扔石子,然后跑開。于是這里靜悄悄的,好一會兒就我一個人。
籠子前有長椅,蒙了灰塵,更顯寒磣。我突然感到疲乏,拂去灰塵坐下。可這里也發生了跟獅子同樣的事情。
駱駝霍地站起來,腦袋不慌不忙探過這邊來;它怪異地張開嘴唇笑。如果不是它的眼睛那么藍、那么美,我一定很煩吧。但是,那眼睛非常美。大大的,寶石般澄澈。
我和駱駝彼此打量好一會兒。但這一次不可思議,我沒有感覺到任何混亂。非但如此,我滿心歡喜,鄭重其事。一定是沒有人在看的緣故吧。
突然,后面樹叢有腳步聲靠近。我不禁站起來,胸口怦怦跳,像做了壞事似的。那是一個小個子駝背老人,他身穿黑色豎領制服,腋下夾一把掃帚。他走過長椅旁,瞧也沒瞧我一眼,就消失在廁所那邊。我又在長椅坐下,點上一支煙,悠然自得地觀察駱駝的眼睛。
我想,真是不為人知的樂趣。
然而,不知何故,我突然從這種歡喜中聯想到在醫院的那番不祥的經歷。這一來,那種歡喜里面開始萌芽丑陋的懷疑。“是野獸們嗅出了我胸中的曠野嗎?”接著,逐個列舉了對我尤其在意的野獸們的名字。獅子、斑馬、長頸鹿、狼,以及這頭駱駝……全都是草原或者曠野的野獸。歡喜一下子變成了不安。有種被背叛的感覺。
突然,籠子里的駱駝消失,被我吸收到體內的場面浮現心中。
我慌忙挪開視線,因感覺還不夠,所以緊閉雙眼。這么一來,我察覺到自己的歡喜,只不過是一種欲望,希望吸收駱駝是胸腔的負壓導致。為了不去看駱駝,我必須付出極大毅力。
立即,胸中的空虛感猛烈抓撓胸壁內側。胸腔的負壓,并不理會我的感覺,如醫生所說,只圖填滿空虛,一味吸收而已吧。然而,我的胸腔雖說只不過是曠野,豈能允許野獸們為所欲為?“為什么不允許?”耳畔也有竊竊私語之聲。但是,我使勁晃晃腦袋,堅持抵抗著誘惑。我仍希望我就是地道的我。
“在這里!”隨著一聲大喊,我兩側突然伸出四只強健的胳膊,把我按住。兩個身穿綠色套裝的大漢,胸前反戴著徽章。他們身后站著醫生的助手金魚眼。他嘲諷地說:“終于倒霉了吧。厚顏無恥。坐在這兒策劃作案。”大漢中的一人拉扯我的胳膊,說:“走。”
“我干了什么?”我這么一說,另一個大漢捅捅我的腋下,說:“明擺著嘛,現行犯。”
拿掃帚的老人冒了出來,開始領我們走。大漢從兩側抓住我的手,金魚眼跟在我們后面,不時推我后背一下。我盡量假裝沒事,但這架勢騙不了人的眼睛。很快,孩子們包圍了我們一行,嘰嘰喳喳,走到哪里跟到哪里。“那家伙是馴獸師哩!”是剛才獅子籠前的孩子的聲音。“厲害呀,偷動物的馴獸師吧!”說話的,一定是他的朋友吧。“對呀,被偵探抓住啦。”我一回頭,孩子們一哄而散。他們遠遠躲在長椅后面、告示牌下和獸籠之間,只露出一張臉。我想顯示自己是無罪之人,挺了挺胸,叼上一支煙,對左邊的大漢說:“你有火柴嗎?”大漢一言不發,只是輕推一下我的胳膊,示意快走。我丟盡了臉,目光落在地面上。
一張廣告單飄落我腳下。
歡迎遠行!
世界盡頭
演講和電影的盛宴
一瞬間,廣告單再次被風吹卷起,飛向后面。但是,它已在我心上留下深刻印象。
“是這里。”老人說著,一行人停在水族館背后的大籠子后門。寫有“白熊”的牌子已開始褪色。老人一邊在鑰匙串里嘩啦嘩啦找,一邊諂笑著說道:“老白患大腸黏膜炎死掉啦。暫時空著,就用這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