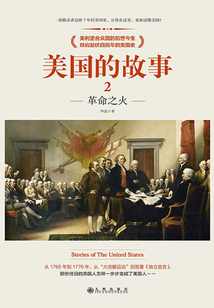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革命前夜
剛剛興起的美利堅民族似乎是上帝的寵兒。遼闊富饒的北美大陸滋養著它,大英帝國寬松的管理方式放縱著它,它那與生俱來的狂野和熱情得到無拘無束的發展。然而,這個任性的孩子還不太習慣理性的思考。它追求自由,卻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它渴望幸福,卻不知道怎樣到達理想的彼岸;它需要權利,卻不懂得爭取這些權利的理由。它就這樣跌跌撞撞地走著,無知,也無畏。但它并沒有在蒙昧中徘徊太久。一道曙光從東方升起,開始照亮這個孩子的靈魂。這就是把人類從黑暗引向光明的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正式興起是在18世紀初,一直延續到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幾乎貫穿整個18世紀。但在此之前,荷蘭的斯賓諾莎、法國的笛卡兒、德國的萊布尼茨、英國的牛頓,已經掀起了“理性主義”的思潮。
什么是“理性”?在狄德羅的《百科全書》里,“理性”是“人類認識真理的能力”。人的理性是大腦活動的自然結果,人們從對事物的觀察、判斷和推理中獲得知識。“理性主義者”們不僅僅是思想家,他們還是數學家或科學家。他們傳遞給世界的信息是:人,可以通過理性的思維認識真理,而不必依靠神的啟示或君主的諭旨。卑微的“人”第一次意識到,他們也許有能力探索上帝創造的這個世界。后來的啟蒙思想家們,無一例外地高舉“理性”的大旗,向“神權”和“王權”發起了猛烈的進攻。
啟蒙運動的兩位先驅都是英國人,他們是托馬斯·霍布斯和約翰·洛克。霍布斯最早提出“社會契約”的理論。他說,國家是人們根據社會契約創造的,君權是“民授”而不是“神授”。君主得到授權后,要為人民謀幸福,而人民也要服從君主,不能反悔。霍布斯摘掉了君主頭上的光環,卻沒有摘掉他們的王冠,他認為君主專制有利于社會的管理。霍布斯不相信有神,但認為宗教是維持統治的必要手段。
經歷了“英國革命”洗禮的洛克顯然比霍布斯走得更遠。他認為,根據“社會契約”建立國家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而私有財產是“人權”的基礎。他說:“我的茅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也許是對“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好的描述。洛克繼承了弗朗西斯·培根的理論,認為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是通過感覺和認知而積累的經驗,因此,他也被稱為“不列顛經驗主義”者。
洛克是現代自由主義的奠基人。他說,人的自然屬性是自私。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和獨立的,“生命權,健康權,自由權,財產權”是“天賦人權”。他的自由主義的另一個方面是政教分離。他認為,既然人沒有能力確認哪一種宗教是絕對“正確”的,就應該允許宗教自由,而不能由政府強迫人民遵循某種信仰。一個寬容的社會才能長治久安。
洛克最著名的政治理論是“分權”理論。他說,國家的立法權應該屬于議會,而行政權和外交權屬于君主,這是“二元論”。在洛克心中,君主立憲是最好的統治方式,議會與君主“分權”,可以保證政治結構的穩定。洛克不再像霍布斯那樣,認為人民一旦授權給君主后就不能反悔,而是認為“革命”不僅是人民的權利,在某些情況下,它也是人民的“義務”。
洛克的理論啟迪了后來的啟蒙思想家們,如伏爾泰和盧梭,并深深地影響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他是對未來的美國影響最大的人。美國最重要的幾位“國父”,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托馬斯·杰斐遜等,經常引用洛克的觀點。杰斐遜把洛克與培根、牛頓合稱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三個人”。他在起草《獨立宣言》時,把洛克的“天賦人權”延伸為“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洛克的政教分離和分權思想完美地體現在美國憲法中,他提倡的自由主義更是美國人至高無上的法寶。在他之后的兩個多世紀里,以基督教精神為底蘊、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美國文化,在全球大行其道,魅力無敵。
繼洛克之后,啟蒙運動漸漸進入高潮,接下來的幾位大腕兒都是法國人,巴黎也就成了啟蒙思想的中心。第一位出場的是孟德斯鳩。孟德斯鳩出身貴族,是位法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他對古希臘、羅馬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霍布斯和洛克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體系。他著述不多,卻字字珠璣,主要著作是《論法的精神》。他試圖設計一個理想的政府,使人民充分享受“政治自由”。他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種人人自感安全的心境的平安狀態。為了享有這個自由,就要建立一個政府,在這個政府的統治下,一個公民不必懼怕另一個公民。”
那么,什么樣的政府結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呢?孟德斯鳩提出了他最為世人所熟知的“三權分立”理論,這是對洛克分權思想的發展。他認為,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應該分開,由不同的政府機構掌握。三權互相平衡,互相制約,任何一權都不能凌駕于其他兩權之上。只有這樣,才能維持政治的協調和社會的穩定。
孟德斯鳩的理論對西方政治體制的影響顯而易見,今天世界上的主要民主國家都是三權分立政體。美國是第一個實踐三權分立的現代國家。可以想象,“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在構思美國憲法時,滿腦子里飛的一定全是“孟德斯鳩”。孟德斯鳩的著作也是被北美政治家們引用得最多的文字。但是,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是在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經驗中得出的結論,適用于“城邦共和國”,也就是“小國寡民”。它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能否適用,美國“國父”們心里壓根兒沒數。盡管如此,這幫天不怕地不怕的移民的后代,還是硬著頭皮把貌似有理的三權分立搬上政治舞臺,這玩意兒到底管用不管用,就聽天由命了。沒想到,這個“四字咒語”不但極靠譜,而且法力無邊,整得美國政治超穩定,一部憲法二百多年不變,羨煞旁人。美國人在給“孟老爺子”燒高香的同時,也對自家“國父”的“膽大包天”佩服得五體投地。
與孟德斯鳩同時代的另一個法國人,就是被譽為“思想之王”“歐洲的良心”的伏爾泰。人們說,18世紀是伏爾泰的世紀,他的光輝有如日月。伏爾泰不僅是哲學家,還是才華橫溢的文學家、詩人、戲劇家、歷史學家,上至國王、下至百姓都是他的粉絲。伏爾泰在科學上的造詣也很深,特別喜歡研讀科學家們的著作,對牛頓情有獨鐘。他一生連書帶小冊子共出了兩千多本,寫過兩萬多封信,恨不得連說夢話都在作詩。好像地球人都知道他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其實,這話不是伏爾泰說的,卻準確地表達了他的思想,所以人們也就樂意借伏爾泰之口把它傳揚天下。
伏爾泰首先攻擊的是天主教會。他說:“天主教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可笑、最血腥的宗教。”像其他啟蒙思想家一樣,他是個“自然神論者”,認為上帝在創造了世界之后便不再作為,而是由“自然”主導人們的生活。他說,信仰不是基于教義,而是基于推理。他提倡的“宗教自由”遠遠超過了以往所有的思想家。以前的“自由”只是基督教的不同派別之間的互相寬容,對非基督徒并不包容。伏爾泰卻主張對所有宗教的寬容,這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雖然伏爾泰痛罵天主教會,但他卻沒有指責上帝本身。相反,他認為上帝不但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有存在的必要。他的名言是:“如果沒有上帝,那就有必要創造一個上帝。”他認為宗教是人類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伏爾泰的著作處處閃爍著理性和人性的光芒。他說,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上帝賦予他們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權利。他宣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決反對奴隸制。伏爾泰還對歐洲以外的社會形態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不同尋常的寬容。他多次提到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不信上帝的世俗國家。他說,一個世俗的中國照樣可以繁榮富裕,人們有什么理由相信只有依靠上帝才能獲得幸福呢?
伏爾泰是啟蒙運動的領袖,法蘭西的“國寶”。他生前備受追捧,死后享盡哀榮。1791年,當他的遺骸被送進“先賢祠”時,一百多萬人見證了這個光榮的時刻。而另一位一點也不比伏爾泰遜色,又與他同年去世的偉人,似乎就不那么幸運了。這位讓人又愛又恨的思想家就是盧梭。
盧梭沒有孟德斯鳩那樣顯赫的身世,也不像伏爾泰那樣左右逢源。他出身貧苦,歷盡磨難。但他的才華卻像純凈的金子一樣,即使在最黑暗的夜色里,也能發出耀眼的光芒。他在哲學、政治學、教育學、文學上的成就幾乎超過了同時代所有的人,他還是個天才音樂家,譜寫過兩部歌劇。
也許與他的出身和閱歷有關,盧梭是“啟蒙時代”最激進的思想家,他對舊制度的抨擊是最猛烈的。在他的名著《社會契約論》和《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里,盧梭把“社會契約”和“授權”理論闡述得淋漓盡致。他說,政府的出現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締結“社會契約”的結果,人們愿意放棄某些個人自由而接受統治的唯一原因,就是使自己的權利、快樂和財產得到保護。政府不應該只保護少數人的利益,而應該著眼于每個人的權利、自由和平等。當政府不能做到這一點時,它就破壞了社會契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當同時代的大師們還在迷戀“君主立憲”時,盧梭已經在追求一種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政體;當“人民”在別的思想家心中只包括充滿理性的“精英”時,盧梭卻讓社會最底層的“群眾”也走進“人民”的行列。他提出“主權在民”(或稱“人民主權”)學說,第一次向世人宣稱,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革命,不僅合理,而且合法。
盧梭熱烈地追求自由和平等。他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也特別強調法治,認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遵守法律的行為就是自由的行為。
與其他啟蒙思想家不一樣的是,盧梭在追求“理性”的同時,也盡情地歌頌“感性”的魅力。他的《感性時代》和《懺悔錄》,把一個孤獨、敏感、痛苦的靈魂誠實地展現在人們面前,那細膩、激揚的情感成為“理性”至上的啟蒙時代中最優美的不和諧音。
盧梭的激烈言論為他帶來無數的災難和譴責,貴族、教會、精英們罵他是“瘋子”“野人”,而最有殺傷力的攻擊來自與他同樣偉大的伏爾泰。盧梭對下層人民的肯定使伏爾泰覺得很不舒服。他認為,那些沒有知識、缺乏理性的“群眾”很容易走向極端,對自由的過分追求反而會產生獨裁。不幸的是,伏爾泰的擔心變成了現實。在法國革命中,盧梭的思想簡直被當作“圣經”,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就是盧梭的狂熱信徒。隨著革命熱情漸漸失控,革命領袖變成嗜血魔頭。“民主”不再是權利的保障,而成了專制的溫床。當“自由”肆無忌憚地揮舞著屠刀時,人們才發現,原來,“革命”還有一個名字叫“恐怖”。
當塵埃落定,人們在歷史的痛苦中開始反思,他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是“革命”曲解了盧梭,而不是盧梭誤導了“革命”,他依然是那位燃燒自己照亮世界的英雄。盡管他得到的謾罵和贊揚一樣多,在他去世16年后的1794年,他的遺骨還是像伏爾泰的一樣被迎進“先賢祠”,巴黎以同樣的熱情擁抱了他的英靈。藝術家設計的盧梭棺木里伸出一只舉著火把的手,他就算在長眠時也沒忘記照亮世人前行的路。
啟蒙運動的其他大師,還有法國“百科全書派”的狄德羅、德國的康德、蘇格蘭的休謨等。他們對神學、哲學、倫理學、科學的貢獻啟迪了整個時代,使人類從此告別愚昧,走進理性王國。在北美,啟蒙運動有它自己的名字,這個名字是“本杰明·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是北美與歐洲之間的紐帶,他長期旅居歐洲,與伏爾泰成為密友。就在伏爾泰去世前一個月,平時已經很少外出的他還專門陪富蘭克林參加哲學俱樂部的活動,他的幫助使富蘭克林在巴黎如魚得水。思想極為活躍的富蘭克林以最快的速度捕捉著歐洲最前沿的理論,源源不斷地把啟蒙思想的火花傳播到北美。他利用自己創建的印刷與出版系統,把殖民地人帶進了啟蒙時代。
除了介紹歐洲的思想,富蘭克林自己也是北美啟蒙運動的主將。他對北美社會最大的貢獻來自他對“美德”的追求。出身于虔誠的清教徒家庭的富蘭克林,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背離了清教正統,宣布自己是“自然神論者”。可是,他雖然反對刻板的宗教禮儀,卻堅信上帝的權威,積極投身到清教徒提倡的事業中,其中包括平等、教育、創業、節儉、誠實、節制、慈善、社區服務。富蘭克林對“美德”的理性思考和熱情贊頌,成功地為美利堅民族打上永久的道德烙印。即使在物欲橫流的瘋狂年代,美國人也從未喪失過道德底線。很多歷史學家認為,正是富蘭克林提倡的“清教主義”美德,培育了讓“資本主義精神”茁壯成長的肥沃土壤。自由的思想和保守的道德相偎相依,譜寫了美國社會的主旋律。
跟很多其他北美人一樣,富蘭克林還有個本事,就是把歐洲的“貴族”思想平民化,原因很簡單,新大陸沒有貴族。雖然啟蒙運動鼓吹“人人平等”,但歐洲啟蒙思想家們所設計的抽象的“共和”體制還是以歐洲現有的等級制度為基礎,國王、貴族、平民涇渭分明,只不過尋求一種力量的平衡而已。可是,富蘭克林說,人的價值取決于他的德行,而不是他的等級。在歐洲,“平等”是“王謝堂前燕”;在北美,它隨著富蘭克林的筆,飛進了“尋常百姓家”。
作為北美思想和知識界領袖的富蘭克林,憑借他的巨大影響力,讓美利堅民族變得成熟和理智,也引導了一大批“精英”探索新大陸的未來。就像“國父”約翰·亞當斯所說,“革命”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就開始了,“它就在人們的思想和心靈中”。
啟蒙運動讓自由、平等、法治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自我,認識世界。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都是啟蒙運動的直接結果。如果沒有啟蒙思想的指導,獨立戰爭只不過是一場民族解放運動,跟“革命”沾不上邊兒;戰爭的結果也絕不會是“美國”,而只是另一個拉美。歷史的長河中,“戰爭”數不勝數,“革命”卻寥寥無幾,因為并不是每一場戰爭都有靈魂。
1730—1740年,在北美的13個殖民地,與啟蒙運動交相輝映的,是“大覺醒運動”。這是一次基督教復興運動,喚醒了殖民地人對宗教的極大熱情,他們與上帝的關系從來沒有這么親密過。這次橫掃北美的“大覺醒運動”是從傳教士喬納森·愛德華茲在新英格蘭的布道會開始的。
愛德華茲看到,傳統的牧師在布道時照本宣科,死氣沉沉,大家聽得都快睡著了,根本談不上心靈的溝通。去教會成了一種毫無樂趣的負擔,即使去了,也體會不到圣靈的感動。宗教變成說教,上帝變得陌生。愛德華茲覺得有一種強大的力量驅使著他,讓他把基督教信仰再次變成人們永恒的追求。
從1727年起,愛德華茲開始在馬薩諸塞的北安普敦布道。他完全放棄了其他牧師刻板的模式,用淵博的知識和生動的語言,滿懷激情地講述著圣父、圣子、圣靈的神妙救贖和奇異恩典。人們被他的話深深地感動和震撼,從四面八方趕來聽愛德華茲布道。愛德華茲最著名的布道詞是“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他在宣講時語氣平靜,但聽眾卻反應強烈,有的因恐懼而發抖,有的因激動而淚流滿面,他們看到了上帝的絕對權威,真切地感受到對圣靈的渴望。
愛德華茲的布道詞和演講風格很快就風靡北美,很多其他牧師也開始摒棄傳統的說教,用感性與情感去喚醒沉睡的靈魂。愛德華茲的影響甚至傳到英國,引起了英國人的共鳴。一個年輕的英國傳教士,名叫喬治·懷特菲爾德,在英國也掀起轟轟烈烈的“傳福音”運動。他說,“整個世界都是我的教區”。1738年,24歲的懷特菲爾德來到北美,開始在13個殖民地傳教,他傳播的“福音”把“大覺醒運動”推向高潮。
懷特菲爾德在傳教時非常有激情,聲音洪亮,語言極富感染力,聽者無不動容。他所到之處,人們趨之若鶩,如饑似渴地聆聽他的教導。懷特菲爾德講的內容與愛德華茲不太一樣。愛德華茲強調人的原罪以樹立上帝的威嚴,懷特菲爾德則宣揚上帝的慈悲,讓人感到獲得救贖后的無限喜樂。他們都鼓勵人們依靠自身的靈性去感受上帝,而不必通過官方的教會。人和上帝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連沒有社會地位的女人、黑奴、印第安人也感到了愛的尊嚴。
“大覺醒運動”還有一個推波助瀾者,就是那位無風三尺浪的本杰明·富蘭克林。懷特菲爾德的所有著作都由富蘭克林的公司印刷出版,他認為懷特菲爾德傳的“福音”體現了平等、民主和宗教自由的觀念。有富蘭克林煽風點火,大家想不“覺醒”都難。在“大覺醒運動”中,大量基督教新派別、新教堂平地而起,無數人受洗成為基督徒,特別是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也接受了基督教,還建了自己的教堂,給他們苦難的生活帶來一線希望。
看上去,“大覺醒運動”似乎是對啟蒙運動的反動。啟蒙運動強調“人”,“大覺醒運動”強調“神”。但實際上兩者相輔相成,一點也不矛盾。雖然大多數啟蒙思想家,包括富蘭克林在內,都是“自然神論者”,但他們沒有一個是無神論者。他們反對天主教會代表的“神權”,卻不反對上帝本身,也沒有懷疑上帝的權威。他們都認為宗教信仰是人類社會的支柱。當富蘭克林請伏爾泰祝福他的孫子時,伏爾泰用英語說:“上帝與自由,這是給富蘭克林先生的孫子的最好的祝福。”這可能也是給所有美國人的最好的祝福。
“大覺醒運動”對北美殖民地的影響一點也不亞于啟蒙運動,它讓基督教精神滲入人們的血液,啟發了北美人對自由和平等的追求,為美國革命做好了精神準備。18世紀的這次“大覺醒運動”也被稱為“第一次大覺醒運動”,美國至今已有四次“大覺醒運動”,幾乎每隔六七十年就有一次,最近的一次是1960—1970年間。每一次“大覺醒”都讓美國人對上帝的信念更加堅定,大大加強了美國社會的宗教文化,凈化了人們的心靈。
經過啟蒙運動和“大覺醒運動”熏陶的北美人,開始以全新的思維認識世界。雖然他們還不完全清楚自己的歸宿到底在哪里,但輝煌的英帝國似乎不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就在革命蓄勢待發的時候,大洋彼岸飄過來的一陣疾風暴雨立刻引發了殖民地人內心壓抑已久的驚濤駭浪。
是什么讓革命不再遙遠?殖民地人能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嗎?請看下一個故事:《抗稅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