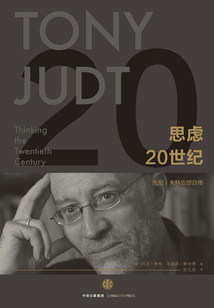
思慮20世紀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1)
蒂莫西·斯奈德
這是一本歷史、傳記和道德論著。
這是一部有關歐美現代政治理念的歷史。其主題是權力和正義,一如19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所理解的那樣。它也是歷史學家和評論家托尼·朱特的精神傳記,他20世紀中期出生于倫敦,彼時“二戰”和大屠殺的動蕩剛剛過去,而共產黨則正在東歐奪取權力。最后,這是一份關于政治理念之局限(和更新能力)與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之道德失敗(和道德義務)的沉思。
在我心目中,托尼·朱特是有能力對觀念的政治進行如此廣泛探討的不二人選。截至2008年,托尼著有多部熱烈而富有論爭性的法國史研究著作,并發表了多篇論述知識分子及其介入的評論文章,他還是一部取名為“戰后歐洲史”(Postwar)的宏偉的1945年后歐洲史的作者。他運用其教化和史學的天分,來探索介于簡短評論與長篇學術研究之間的獨特表達方式,并使這兩種形式都完美至臻。不過本書的產生,某種程度上緣于那年11月我明白托尼將再也無法寫作了——至少在傳統意義上如此。在我意識到他再也無法運用雙手之后,我提議我們共同來寫一本書。托尼患了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癥(ALS),這是一種退化性神經疾病,它一步步讓人癱瘓,并終將(且通常迅速地)致人死亡。
本書采用的是我與托尼之間長時對話的形式。2009年的冬、春和夏三季,每個周四,我都搭乘8點50分從紐黑文到紐約中央車站的那班火車,然后換乘地鐵到托尼所在的街區。他和妻子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及兩個兒子丹尼爾(Daniel)、尼克(Nick)一起住在那里。我們的會面安排在上午11點,通常我會在咖啡館里花個10分鐘左右來整理有關當天話題的思路,并做一些筆記。我在咖啡館里用熱水洗一遍手,然后到托尼的公寓里再洗一遍:托尼的病況使他飽受冰冷之苦,我希望能握一握他的手。
我們的對話始于2009年1月,當時托尼還能行走。他雖然無法轉開公寓門上的把手,但還能站在門內歡迎我。很快,他便在客廳的一把扶手椅上歡迎我了。到了春天,他的鼻子和大部分頭部都被呼吸設備罩住了,他的肺已經不能工作了。夏天我們在他書房里碰面,被群書包圍,托尼在一架高大的電動輪椅上俯視著我。我有時會操控它,這當然是因為托尼無法辦到。托尼此時除了頭部、眼睛和聲帶以外,已幾乎完全動不了了。但對本書的目的來說,這已足夠。
親眼目睹這一毀滅性疾病的進程,著實讓人難過,尤其在病情急轉直下的時候。2009年4月,看到托尼的腿和肺短短幾個星期內就相繼失去功能之后,我確信(據我的印象,他的醫生亦如此認為)他已活不過幾個星期了。我始終很感激珍妮(詹妮弗的昵稱)和兩個孩子在那樣的時候還能將托尼分給我。不過對話也是精神支撐的重要來源,它帶給我們專注的愉悅、交流的和諧及工作順利進展的滿足感。致力于手頭的話題,跟上托尼的想法,是一項很有趣也很快樂的工作。
我是一名東歐史學家,在東歐,口述作品有其深厚的傳統。這一類型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apek)【1】與托馬什·馬薩里克(Tomá? Masaryk)的系列訪談,后者是兩次大戰之間捷克斯洛伐克的哲人總統(philosopher-president)。該書恰好也是托尼從頭到尾讀過的第一本捷克語作品。也許最好的口述作品是《我的世紀》(My Century),一部關于波蘭猶太詩人亞歷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的宏偉傳記,由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在加州根據錄音記錄整理而成。我第一次讀這本書是在一趟從華沙到布拉格的火車上,當時我剛開始歷史學的博士研究。當我向托尼提議寫出一本口述作品時,并未想到這幾個實例,我也不自視為恰佩克或米沃什。作為一名讀過眾多此類作品的東歐研究者,我只是想當然地認為,一些經久不衰的東西出自對話。
我向托尼所提的問題有三個來源。我最初或者說大體的計劃是從頭至尾討論托尼的作品,從其關于法國左派的歷史著作再到《戰后歐洲史》,探尋有關政治知識分子的角色和歷史學家的職業技藝的一般性論爭。我感興趣的是諸如托尼作品中對猶太問題的回避、法國歷史的普遍特征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和局限性這樣的話題,它們事實上在本書中都居于重要位置。直覺告訴我,東歐拓寬了托尼道德和精神的視野,但我不知道這一直覺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我了解了一些托尼在東歐的熟人的信息,而且,因為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2】和馬爾奇·肖爾(Marci Shore)的建議,并經過托尼本人的同意,我們把一些會面用于討論托尼的生平而非其作品。最后,托尼透露他一直想撰寫一部關于20世紀智識生活的歷史。我利用了他的章節梗概來作為第三類問題的基礎。
本書的對話特征要求其作者必須熟悉成千上萬本其他著作。因為我和托尼是當面交談的,我們沒有時間查閱參考文獻。托尼事先并不清楚我要問的問題,我也無從預料他會做出何種回答。這些文字所反映的是兩顆心靈有意通過言談來介入的自發性、不可預期性和偶爾的趣味性。但每一處,尤其是歷史部分,它都依賴于我們的大腦圖書館,尤其依賴于托尼那不可思議地廣博而井井有條的頭腦。本書為對話進行了辯護,但或許也是對閱讀的更為有力的辯護。我從未和托尼一起做過研究,但他大腦圖書館里的卡片目錄與我有相當多的重合之處。我們此前的閱讀創造了一個共同的空間,在這里面,托尼與我一道探險,當別無他路可行時,我們會注意到路標和遠景。
不過,言談和出版純屬兩碼事。這些對話究竟是如何成書的?每一次會面我都做了錄音,并保存為一個電子文檔。青年歷史學者耶迪達·坎費爾(Yedida Kanfer)之后承擔了文字轉錄的工作。這本身是一項艱巨的腦力活,因為要從不盡完美的錄音中搞清楚我們所說的內容,耶迪達必須了解我們所討論的話題。沒有她的奉獻和學識,本書的完成將困難許多。按照一個經托尼首肯的方案,從2009年夏至2010年春,我將文字稿分成了九個章節。2009年的10月和11月,我從維也納飛到紐約,在那里度過了2009—2010學年,如此我們便能就進展進行討論。我在維也納用電子郵件將各章的初稿發給托尼,他加以修改再返還給我。
每一章都各有一部分傳記和歷史的內容。因此本書貫串了托尼的一生,并穿越了20世紀政治思想中某些最為重要的場景:作為猶太問題和德國問題的大屠殺(Holocaust),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及其歐洲起源,英國例外論與法國普遍論,馬克思主義及其誘惑,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作為倫理學的自由主義在東歐的復興,以及歐美的社會規劃。在每一章的歷史部分,托尼的話均以純文本出現,而我的則以斜體表示。【3】盡管傳記部分也產生自對話,但我將自己的內容已盡數刪去。因此每一章都以一小段托尼的傳記開場,采用托尼的口吻,并以純文本表示。在某些時候,我以提問者的形式出現,用斜體表示。接著便進入歷史部分。
將傳記和歷史拼接在一起的意義,顯然并不在于托尼的關切和其成就可以用任何簡單的方法從其生平中推演而出,仿佛那么多桶水都汲自同一口井。我們更像是連自己也未曾涉足的巨大的地下涵洞,而非直接掘入土中的小孔。那種堅持認為復雜只是簡單之假面的沖動,是20世紀的通病之一。在詢問托尼其生平之時,我并沒有指望平息對一種簡單解釋的渴望,而是輕叩墻壁,尋找地下暗室間的通道,這些暗室的存在,我最初只是隱隱約約地感覺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