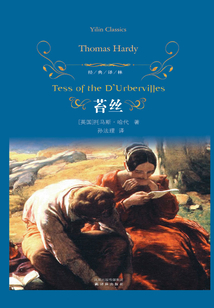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譯序(1)
一
托馬斯·哈代的《苔絲》之為英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瑰寶,現在是沒有人會懷疑的了,但是它當初出版時卻有過坎坷的經歷。
哈代寫《苔絲》時原是說好交波爾登城的梯洛岑父子公司連載出版的,但是書稿還沒有交齊,梯洛岑公司卻因為小說里有騙奸和私生子的情節拒絕出版。哈代無可奈何,只好把書稿送到了《慕萊雜志》,卻又遭到拒絕;他只好另謀出路,又把它送到《麥克米倫雜志》,結果仍然碰壁。看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是不會容許《苔絲》照原樣出版的了,哈代只有再辟蹊徑,跟一個家庭辦的報紙《圖像》達成了協議,半是高興半是嘲弄地向傳統讓了步,執行了一個不能算是很嚴肅的折衷方案。他把獵苑騙奸部分和私生子的情節刪去了,把安琪兒·克萊爾抱四個姑娘通過積水地段的部分也做了修改,讓他使用手推車把她們送了過去。這樣,小說《苔絲》才得以以每周一期的連載形式跟讀者見面,從1891年7月4日起直到當年的12月26日載完。與此同時,《苔絲》也在美國的《哈珀市場》雜志上連載。被刪去的那兩章也分別換了名字發表。獵苑騙奸一場于1891年11月14日在愛丁堡的《國民觀察家》文學增刊上以《阿卡地周末之夜》的標題發表;苔絲為私生子施洗一場則于1891年5月在《雙周評論》上以《夜半施洗,基督教世界速寫之一》的標題發表。
《苔絲》雖然遭到這樣的閹割,發表后仍迅速取得巨大的成功。1891年11月《苔絲》連載尚未完畢,麥克米倫公司便把它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在短短的一年之內連續再版五次。
《苔絲》出版之后哈代又對它做過多次修改,不但把刪去和改寫部分恢復原樣,而且又根據哈代自己思想的變化對角色、事件、地理、時間和方言等等方面反復作了修改,直到1912年(即初版發表二十一年后)《苔絲》才算最后定稿。本書便是根據1912年版翻譯的。
《苔絲》不僅在出版前命途多舛,出版后也遭到了種種非難,但是由于《苔絲》本身的生命力、說服力和藝術魅力,這本書三年之內便征服了輿論界,獲得了崇高的評價,成了英國文學中的不朽之作。這場斗爭的過程可以從哈代為幾個版本所寫的序言中清楚看到。
哈代在1891年11月《苔絲》初版說明中很含蓄地駁斥了對該書的某些攻擊。他說:“我只需補充一點:寫作本書的目的是完全真誠的,是企圖以藝術的形式表現一連串的真實事件。這本書說的是現在大家都感覺到而且想說的話;對于反對本書的意見和情緒,我只好請求那些太高雅的讀者記住圣徒杰羅姆的一句名言:‘若是真理對誰有了冒犯,那就讓它冒犯好了,真理是不能掩蓋起來的。’”
1892年哈代又為《苔絲》的1892年版寫了一個序。這個序較長,列舉了一年來對《苔絲》的主要批評意見。有的人認為《苔絲》故事不宜作小說材料;有的人認為副標題“一個純潔的女人”中“純潔”二字礙難接受;有的人則覺得哈代沒有對苔絲作批判;有的人則受不了小說中那把撒旦的鋼叉、公寓里那把切肉的刀和那把來得骯臟的陽傘;有的人則說哈代不應當表現出對神靈的大不敬。對這些哈代都一一做了回答。而對那些“打擊異端的摩登棍子”的斷章取義和有意歪曲,哈代也略帶譏諷地進行了反擊。他模仿哈姆萊特在墳場那句名言說:如今的世界實在擁擠,每前進一步都難免碰痛了某些人腳后跟上的凍瘡。
不過,世界畢竟要在碰痛凍瘡中前進。三年后哈代又在1895年版《苔絲》的序言中說:“在本書出版幾年之后那些當初迫使我作答的評論家們自己倒噤若寒蟬了。這似乎是讓大家想起:他們當初的議論和我的回答其實都無必要。”
1912年,即又過了七年,哈代為《苔絲》的1912年版寫了個序,告訴讀者兩點:一、這一版里補進了川特里奇那個灰塵飛揚的舞會的描寫。這一部分原是最初手稿中就有的,只是在1891年單行本出版時忘記補進去了。二、本書的副標題“一個純潔的女人”是作者當初看完校樣后根據女主人公留在心里的印象補上去的。對此“現在大約是不會有人提出異議的了。其實這問題在書中的議論最多,Melius fuerat non scribere(拉丁文:原可不必再提),但副標題仍保留了”。
副標題“一個純潔的女人”的舊話重提標志了一場爭論的結束和一種觀念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改變。不過在貞操觀念很重的華夏古國,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也許還不是毫無意義的。
二
正如哈代所說,苔絲是否是個純潔的女人在書中議論最多,實際上輿論界的分歧也最大。許多人只承認“純潔”一詞的引申的、人為的含義,卻無論如何也難以承認這個既不貞潔、又殺了人的女人是純潔的。
其實,一部《苔絲》寫的就是社會如何把一個純潔、質樸、正直、刻苦、聰明、美麗的農村姑娘逼得走投無路,終于殺人的故事。她的失貞主要是阿歷克的責任;她的第二次落入阿歷克之手是她的父母、安琪兒和阿歷克的責任,而她殺死阿歷克則是受盡欺凌的弱者的最后反抗。
在苔絲身上我們自始至終看到的是她純潔的本性對逼迫她的力量的苦苦掙扎。最終她被逼得上了絞架,做了祭壇上的犧牲品,而社會和讀者卻還在冷漠地議論著她的貞操,這是何等麻木的世情!
撇開社會環境這個大因素不論,造成苔絲毀滅的主要是兩個人:阿歷克·杜伯維爾和安琪兒·克萊爾;一個“撒旦”和一個“天使”。
阿歷克·杜伯維爾是自稱撒旦的,他在黑原谷黃昏燒枯草的滾滾黑煙中映著火光出現時手執了一柄鋼叉(耪地用的齒耙),自稱是“那幻化作低等動物來誘惑你的老家伙”(即撒旦)。這話他雖說得玩世不恭,卻也道出了他的本性。他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有名的獵艷能手、負心漢子。老克萊爾一到川特里奇便聽說了他的劣跡。黑桃皇后卡爾·達爾其和她的妹妹紅方皇后都跟他有曖昧關系。他作風下流,利用苔絲的貧窮,假冒母親的名義騙她去飼養家禽;利用高速趕車嚇唬她,占她的便宜;在獵苑趁她精疲力竭的時候奸污了她;以后又乘人之危利用她一家老小無家可歸時霸占了她。盡管他也曾做過“回頭浪子”,現身說法狂熱地宣揚過福音,但正如哈代所說:“他的陣地其實不堪一擊。他那心血來潮式的轉變跟理智并沒有關系,那只不過是一個吊兒郎當的人由于母親逝世心里難過、在尋求新刺激時搞出的一種怪花樣罷了。”他的信仰經苔絲轉述的安琪兒幾段懷疑主義的邏輯一吹便倒塌了;他的轉變在重新見到苔絲的美色之后便也消失了。他還是他,活脫脫一個花花公子,花幾個小錢蓄養個情婦的冒牌貴族子弟。
苔絲對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她在從愛明斯脫回來跟他路遇時就斥責過他:“你們這種人在世界上盡情地玩樂,卻讓我們這樣的人受罪,讓我們悲傷絕望。等到你們玩夠了,卻又想保證自己在天國里的幸福,于是又皈依上帝,成了回頭浪子。”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苔絲才一任他的糾纏追求,不肯遂他的意。但是悲劇卻在,她終于在克萊爾的冷酷和家庭的困厄這雙重壓力之下做了犧牲品,向他屈服了。
而最帶悲劇反諷意味的是:苦苦逼她走向撒旦的力量之中也有號稱天使的安琪兒·克萊爾。
安琪兒一詞原是天使的意思。在西方傳說里,安琪兒是在云端里彈奏著豎琴的仙靈。那個夏天的晚上,安琪兒·克萊爾就是用他的豎琴彈奏得苔絲的靈魂飛升,繞著琴音飄蕩的。他在苔絲心里也的確是個天使。苔絲在鄉社游行時就曾對他一見鐘情,因他沒有找她跳舞而久久悵然若失。在泰波特斯奶場兩人再度相見之后,苔絲便如癡如醉地愛戀著他——那是她的初戀,也是她唯一的一次戀愛。
安琪兒·克萊爾忠實于自己的思想。他因為懷疑基督教義便毅然放棄了上劍橋讀書的機會。他博覽群書,有獨立的思想;他瞧不起等級、財富等差異,對社會習俗和禮儀明顯地表示冷淡。為了獲得精神上的自由回避宗教事業,他決定從事比較艱苦的農業,而且到農村去學習各種農事勞動。他能克服中產階級身份感,跟奶場的人打成一片,像理解朋友一樣理解他們,不但不把他們當做所謂的鄉下“哈甲”,而且能欣賞他們的性格和才能。他欽佩父親老克萊爾對教會事業的虔誠和自我犧牲精神,卻也明白他的狹隘和局限。對兩個哥哥他看得更清楚,盡管兩人“渾身上下無一處不是中規中矩”,他卻看出了兩人思想上的局限和庸俗。他在他們面前我行我素,毫不掩飾自己因在農村生活而產生的變化。對于兩人那種自命不凡的淺薄,他言詞犀利,寸步不讓。
他對苔絲的愛具有初戀的純潔、熾熱與真誠。苔絲在他眼里達到了物質美和精神美的極致。他對他母親夸耀苔絲“真是渾身上下都洋溢著詩意,她就是詩的化身……她過的就是詩的生活,她那種生活舞文弄墨的詩人只能在紙上寫寫而已”。他對她的愛是純潔的、柏拉圖式的、帶著田園牧歌的情調。因此他尊重苔絲,抱著鄭重的婚姻意圖跟她接近,在遭到拒絕時雖很痛苦卻總耐心等待,盡力去說服。他的不懈努力終于打動了苔絲,她同意了他的婚姻要求。
一切的阻力都沒有了。苔絲克服了精神上的壓力,克萊爾準備在婚后開始創建新的生活。他們的婚姻原是可以十分幸福美滿的,可是,就在新婚之夜當純樸的苔絲向克萊爾講述了她的過去之后,一切卻突然變了樣,苔絲的悲劇,還有克萊爾的悲劇開始了。兩人生活中風和日麗的日子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一向思想開明的克萊爾此時痛苦極了。他傷心、失望、苦惱,一籌莫展,遭受到嚴重的精神折磨,甚至半夜跑進苔絲屋里抱起她夢游,走過佛魯姆河,幾乎把兩人都淹死,口中念念有詞:“死了!死了!”在他痛苦時苔絲向他解釋過:她是受害者,出事時又還是孩子。她也向他表白過:她一心只想讓他快樂,愿意像奴隸一樣服從他,甚至為他去死。她也質問過他:“我既然愛上了你,我就要永遠愛你——無論發生了什么變化,無論受到了什么羞辱……那么,你又怎么可能不愛我了呢?”但是這一切他都聽不進去,仍然苦惱萬分。這是為什么?哈代說:
“他溫文爾雅,也富于熱情,但是在他那素質的某個深奧莫測之處卻存在著一種生硬的邏輯積淀物,仿佛是橫在松軟的土壤里的一道金屬礦脈,無論什么東西要想穿破它都不免碰得口卷刃折。”
這一道積淀是什么?克萊爾對苔絲說:“不同的社會是有不同的規矩的。你幾乎要逼得我說你是個不懂事的農村婦女了。你根本不了解這種事在社會上的分量。”他說:“在那個男人還活著的時候,我們怎么能夠生活在一起呢?”他甚至想到了孩子們,說他們“會在一種恥辱的陰影之下生活,而那種恥辱的分量會隨著他們的年齡的增加而被他們充分地感覺到”。他又說:“我原來認為——任何男子漢也會這么想的——我既然放棄了娶一個有地位、有財富、有教養的妻子的全部打算,我所得到的自然應當是嬌艷的面頰和樸素的純潔。”
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溫情脈脈的土壤剝開了,骨子里還是利己主義、男性中心的金屬礦脈,中產階級的體面、門風、地位、利害。純潔無私的愛情在這道礦脈面前卷口了。
作為一個思想開明的青年,他倒是應當懷疑一下自己的邏輯。首先,一個十七歲的少女遭到了那樣的不幸難道是她自己的錯?如果只把愛看做男性的占有,那和阿歷克·杜伯維爾的態度又有什么區別?何況他自己也并非白璧無瑕。為什么苔絲可以原諒他一時的放縱,他就不可以理解苔絲的不幸?
正如哈代一針見血所指出的:
“這個具有善良意圖的先進青年,這個最近的二十五年的樣板產品,盡管主觀上追求著獨立思考,實際上在遭到意外事故的打擊因而退回到早年的種種教條中去時,仍然是個習俗和傳統的奴隸。”
看來小克萊爾雖然名叫安琪兒,實際上遠遠不像在云中彈奏豎琴、給人世帶來幸福的安琪兒,相反,他跟撒旦所起的作用近似。也許苔絲從那兒所受到的打擊和產生的絕望并不亞于阿歷克的禍害。
安琪兒·克萊爾的悲劇不光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我們通過他看到了一定時代、一定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如何頑固地窒息和污染著人的心靈。這一“先進青年”在神學上、社會學上和許多問題上都可以抱開明的觀點,蔑視傳統,在這個問題上卻無法逾越歷史的障礙,鬧得他自己痛苦萬分,也殘酷地折磨了苔絲。等到他歷盡辛苦在一年半之后明白過來后,苔絲的新的悲劇又已釀成,再也無法挽救了。
哈代在苔絲被絞死之后寫了一句驚心動魄的話:“那眾神之首結束了他跟苔絲玩的游戲。”最具有反諷和悲愴意味的是:眾神之首這場游戲的一個主要工具竟然是跟苔絲彼此愛得銷魂蝕魄的安琪兒·克萊爾。
哈代在這里深刻地揭示出了中產階級的意識、習俗、輿論是如何扭曲了人的心靈,給人們帶來了痛苦。這便是安琪兒·克萊爾這個文學形象的深刻的社會意義。從這個角度看他,他比拈著髭須冷笑的典型壞蛋阿歷克·杜伯維爾深刻得多,甚至不亞于曾引起眾多爭論的苔絲。
苔絲的悲劇是家庭和社會造成的。從她在小說中露面的時候起頭上就懸著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