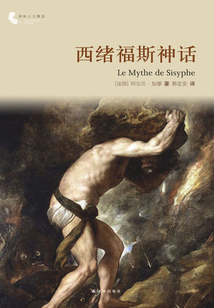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西緒福斯神話》:荒誕·反抗·幸福(1)
郭宏安
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成長起來的那一批西方作家,大都有一種哲學的野心,他們不滿足于觀察和再現生活,而是試圖對生活給以本體論的解答。他們當中自然有不少人流于空疏、抽象,甚至玄妙,但也的確有人成為一代青年的精神導師,例如薩特和加繆。這兩個人的名字常常被人擺在一起,但他們之間的距離實在不可以道理計。如果說薩特以其艱深復雜的體系令人敬畏,加繆則以其生動樸實的經驗使人感到親切。薩特曾經指責加繆“痛恨思想的艱深”,對他的抽象思維能力頗有微辭。這當然不能完全歸之于兩個人的反目。雖說加繆也曾在大學中主修哲學,但阿爾及爾大學顯然不能與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相比,他也沒有跑到德國去研究海德格爾的本體論和胡塞爾的現象學。加繆對哲學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本來也很有理由指責薩特背離了法國哲學的傳統。加繆是在貧困中長大的,很早就被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中,因此,他始終在具體經驗的描述中尋求哲理,用生活智慧的探求代替抽象概念的演繹。有人說加繆的書是寫給中學畢業班的學生看的,話雖說得尖刻,透著淺薄甚至惡意,卻也道出了幾分真實,即加繆試圖為步入生活的人提供某種行為的準則。因此,《西緒福斯神話》一出,立即受到在戰爭的廢墟上成長起來的那一代青年的歡迎,成為他們在人生旅途上繼續奔波的某種指南。
加繆的哲學是一種人生哲學,他關心的不是世界的本源或人的本質之類的問題,而是諸如人生是否有一種意義,人怎樣或應該怎樣活下去等倫理問題。我們讀他的《西緒福斯神話》,得到的不會是思維的快樂和邏輯的滿足,而可能是心靈的顫動和生活的勇氣;我們記住的不會是有關“世界是荒誕的”等哲學命題的論證,而可能是“征服頂峰的斗爭本身足以充實人的心靈”等格言式的警句。作為一部哲學論著,《西緒福斯神話》也許缺少思辨的色彩,但是作為一種人生智慧的探求,《西緒福斯神話》顯然不乏啟迪的力量。
有些以樂觀自得的人讀《西緒福斯神話》,很可能一開始便會被加繆的立論壓得喘不過氣來。什么?“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判斷人生值得生存與否,就是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為人生勾勒出這樣一幅圖畫,不是過于陰森可怕了嗎?不是過于悲觀絕望了嗎?也許某些訓練有素的哲學家更會跳起來,他們會說加繆偷換了哲學的基本問題,用生死觀取代了宇宙觀,抹殺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的區別。對于前者,我奉獻一句加繆本人說過的話:“希望和希望不同,我覺得亨利·波爾多先生的樂觀的作品特別使人泄氣。”亨利·波爾多(Henry Bordeaux,1870—1963)是一位傾向保守的作家,以維護傳統的、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自命,他的希望自然是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之中。對于后者,我則勸他們不必動肝火,應該允許有人把哲學的基本問題歸結為生死的問題,而不管什么物質第一性或者精神第一性。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慘絕人寰的浩劫的人們難道沒有權利問一問:這樣的人生值得過還是不值得過?加繆是一個與蒙田有著深刻的精神聯系的作家,后者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識自我。”加繆的《西緒福斯神話》無疑是“認識自我”的一種努力,是關于人和人生的一種探索。他要回答的問題不是“人是什么”,而是“人的命運是什么”,已然存在的人應該如何對待他的命運。
在西方,西緒福斯的故事由來久矣,他一直被當做勇氣和毅力的象征。波德萊爾有詩曰:“為舉起如此的重擔,得有西緒福斯之勇;盡管人們有心用功,可藝術長而光陰短。”這“重擔”的名字叫“厄運”,西緒福斯縱使舉得起,心中卻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悲哀。然而加繆筆下的西緒福斯不同,他不但有毅力和勇氣,還有一份極難得的清醒,他知道他的苦難沒有盡頭,但他沒有氣餒,沒有悲觀,更沒有怨天尤人。于是,西緒福斯成了一位悲劇的英雄,成了與命運搏擊的人類的象征。
據希臘神話,柯林斯國王西緒福斯在地獄中受到神的如下懲罰: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石頭因自身的重量又從山頂滾落下來,屢推屢落,反復而至于無窮。神以為這種既無用又無望的勞動是最可怕的懲罰。關于西緒福斯為什么受罰,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有的說西緒福斯捆住了帶他去地獄的死神;有的說他泄露了宙斯的一樁艷遇;有的說他生前犯了罪,如劫掠旅行者;還有的說他死后從冥王那里獲準還陽去懲罰不近情理的妻子,然而,“當他又看見了這個世界的面貌,嘗到了水和陽光、灼熱的石頭和大海,就不愿再回到地獄的黑暗中去了。召喚、憤怒和警告都無濟于事”。于是,神決定懲罰他。
諸種原因之中,加繆更傾向于最后一種,而在這最后一種中,他的興趣又專注于西緒福斯的重返人間之后。加繆告訴人們,使西緒福斯留戀人間的,是水,是陽光,是海灣的曲線,是明亮的大海和大地。他所以受到神的懲罰,是因為他不肯放棄人間的生活,而人間的生活雖然有黑暗的地獄作為終點,但其旅程究竟還是可以充滿歡樂的。
然而,加繆無意深究西緒福斯受罰的原因,他要探索的是受罰中的西緒福斯。請看在他的筆下展開的是一幅多么悲壯、多么激動人心的畫面:“……一個人全身繃緊竭力推起一塊巨石,令其滾動,爬上成百的陡坡;人們看見皺緊的面孔,臉頰抵住石頭,一個肩承受著滿是泥土的龐然大物,一只腳墊于其下,用兩臂撐住,沾滿泥土的雙手顯示出人的穩當。經過漫長的、用沒有天空的空間和沒有縱深的時間來度量的努力,目的終于達到了。這時,西緒福斯看見巨石一會兒工夫滾到下面的世界中去,他又得再把它推上山頂。他朝平原走下去。”好一個“他朝平原走下去”!極平淡,極輕松,極隨便,然而這高度緊張之后的松弛蘊含著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感到,一種充滿了智慧的哲學家的冷靜牢牢地控制著瀕于爆發的小說家的激動。這時的西緒福斯是一個勇敢地接受神的懲罰的人,是一個與注定要失敗的命運相抗爭的人,是一個使神的意圖落空而顯示出人的尊嚴的人。他沒有怨恨,沒有猶豫,不存任何希望。他明明知道勞而無功,卻仍然“朝平原走下去”,準備再一次把石頭推上山頂。
然而,加繆真正感興趣的還不是把石頭推上山頂的西緒福斯,因為這還不是懲罰的所在;他真正感興趣的是眼看著自己的努力化為泡影卻又重新向平原走下去的西緒福斯,因為這才是真正的懲罰:“用盡全部心力而一無所成。”加繆寫道:“我感興趣的是返回中、停歇中的西緒福斯……我看見這個人下山,朝著他不知道盡頭的痛苦,腳步沉重而均勻。”這時的西緒福斯是清醒的、坦然的,準備第二次、第三次、第無數次地把巨石推上山頂。無數次的勝利后面接著的是無數次的失敗,他不以勝喜,亦不以敗憂,只是每一次失敗都在他的心中激起了輕蔑,而輕蔑成了他最強大的武器,因為“沒有輕蔑克服不了的命運”。
就這樣,加繆把西緒福斯的命運當做了人類的命運,把西緒福斯的態度當做了人類應該采取的態度。他的結論是:“征服頂峰的斗爭本身足以充實人的心靈。應該設想,西緒福斯是幸福的。”這就是說,人必須認識到他的命運的荒誕性并且以輕蔑相對待,這不僅是苦難中的人的唯一出路,而且是可能帶來幸福的唯一出路。對于西緒福斯來說,“造成他的痛苦的洞察力同時也完成了他的勝利”。勝利的喜悅和失敗的痛苦原本是一個東西,使它們分裂為兩種經驗的是盲目的希望,而使它們化合為幸福的則是冷靜的洞察力。有了這種洞察力,人就可以在奮斗的過程中發現幸福,而不把希望寄托于奮斗的終點,因為終點是沒有的,或者說終點是無限的。加繆指出:“失去了希望,這并不就是絕望。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西緒福斯的幸福在平原上,而不在山的頂峰上;在他與巨石在一起的時候,而不在巨石停留在山頂的那一剎那間。
西緒福斯的喜悅表現為沉默,他在沉默中“靜觀他的痛苦”。西緒福斯的沉默和靜觀包孕著加繆的荒誕哲學的完整的幼芽,這棵幼芽將通過他的另一部著作《反抗的人》而長得枝葉繁茂。這是后話,我們這里面對的還只是西緒福斯和他的巨石,即人和他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