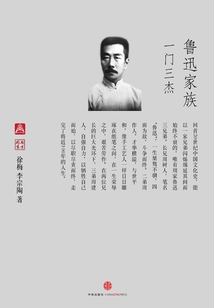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8章 周作人之謎——止庵談周作人的國事與家事(2)
- 第7章 周作人之謎——止庵談周作人的國事與家事(1)
- 第6章 周作人之“苦”(2)
- 第5章 周作人之“苦”(1)
- 第4章 魯迅的后人們
- 第3章 被遮蔽和高懸的魯迅(3)
第1章 被遮蔽和高懸的魯迅(1)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北發表長篇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并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區的語文教材中大量增選魯迅的“戰斗雜文”,而國統區則禁止學生閱讀魯迅,禁止發行魯迅的一切出版物。魯迅不再是獨立于任何黨派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共產黨高擎的一面意識形態大旗。
1996年前后,周令飛客居臺灣,父親周海嬰和母親馬新云來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燈泡忽然滅了。周令飛站在高凳上換燈泡,“我就跟太太張純華開玩笑,說‘不好!我要掉下來了!’黑暗中我母親跟我父親說,‘你看兒子你一樣,老是搞惡作劇。’”
“我父親回了一句,他說,‘我爸爸也是一樣的。’意思是他跟我爺爺魯迅一樣,喜歡開玩笑。”
周令飛說自己當時“心里咯噔一下”,雖然他由祖母許廣平一手帶大,但祖母極少同他講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樣,魯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來自學校、來自課本的。小的時候,我學習到魯迅那些作品,通過老師的教訓,也覺得我的祖父是很兇的,有的時候甚至慶幸祖父不在了,否則回到了家里祖父會罵我、打我的屁股。”
“魯迅太偉大了,我小的時候,在學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動物一樣到我們班扒著窗子看我。每次學到爺爺的課文,同學就會對我說:‘是你爺爺寫的。’口氣很羨慕,但聽多了,心里就覺得怪怪的,總想逃脫出來。想遠離他,站在遠處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稱是“一個普及魯迅、宣傳魯迅的義工”。讓他在不惑之年從眺望變為追隨的,正是父親黑暗中的那句無心之言。“過去在我心中的魯迅形象,在那一瞬間被顛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飛扭轉魯迅形象轉播中的“空洞、扁平和意識形態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周令飛到學校演講,這句話一出口,臺下馬上響起會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做過一個統計,從小學到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總計約20篇,但孩子們談論魯迅的時候往往不知道說什么,一些老師甚至怕教魯迅,不知道在當下該如何闡釋魯迅,“上海有家以魯迅名字命名的民辦學校,校長號召孩子們‘學習魯迅的戰斗精神,攻克學習的堡壘’。”
他想改變魯迅形象傳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識形態化”,他在自己的演講和訪談中,常常要將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們看到的魯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魯迅有多高,我父親是1米78,我是1米80,我兩個弟弟一個1米83,一個1米85,我妹妹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計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實際上魯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講時他愛給大家看魯迅不同歷史時期的照片,以實例說明,魯迅先生并非“過去大家經常看到的,短發豎立,目光犀利,眉頭緊蹙,面龐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沒有笑容,凝重而嚴峻……”
我和我父親共同編輯了一本《魯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魯迅的照片,統計之后發現100多張中有20多張的魯迅是面帶笑容的。
蕭紅筆下,“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里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么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的連煙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來”。
我祖母也說過,說我爺爺的笑聲,三間屋子外都可以聽見。
有這么一個故事,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魯迅的像,請祖母提意見,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說,“我很喜歡您的雕塑,不過魯迅是不是太嚴肅了一點,太兇了一點?”這個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許大姐,我也想雕塑一個您心目中的魯迅,但是群眾不答應。”我祖母聽了這話就走開了,沒再說什么。
他不喜歡那個刻意被塑造為斗士、革命導師的魯迅,他樂意同大家談論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電視臺《悅讀會》節目錄制現場,主持人委婉閃爍地問及魯迅先生與蕭紅的關系,他直言快語地接過話茬,“你直接說,他倆是不是好過?是這意思不?”
他的定義是“知己”,“這很正常吧!優秀的男女之間,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賞,很美好啊!”他給大家講魯迅跟豬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聲傳到三間屋子之外。
1926年魯迅到廈門教書,思念在廣州的祖母,他一個人在相思樹下想念愛人,一頭豬不識相,跑過來,啃地上的相思樹葉,我祖父很惱火,擼起袖子就跟豬搏斗,一個老師跑過來,問他你怎么跟豬打架,他說老兄我不能告訴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個有個許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給她,多浪漫多可愛的一個人!
許廣平在周揚的指導下回憶魯迅
“關于我祖父的各種回憶錄,1949年之前的更為信實。”
2010年初,周海嬰和周令飛父子將許廣平1959年寫成的《魯迅回憶錄》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嬰、馬新云夫婦在該書序言中寫到,“當時已60高齡且又時時被高血壓困擾的母親來說,(寫這本書)確是一件為了‘獻禮’而‘遵命’的苦差事。”
魯迅逝世后,許廣平常應邀寫各種回憶文字,“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只不過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強,比較起許多他的老朋友,還是知道得不算多,寫起來未必能周到。不過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為研究這時代的中國思想者,就是一飲一食,也可資參考的。為了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拿起筆來了。”
這種回憶常使她傷慟,“時常眼睛被水蒸氣蒙住了,以致擱起筆來”。
她的文章平實動人,她眼中的魯迅絕無后來人工演繹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絕對要穿布制的,破的補一大塊也給一樣地穿出來。為了衣著的隨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他到醫院給朋友當翻譯,醫院里面的人就當他是吃翻譯飯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鋅版,人家當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計;到外國人的公寓去拜訪,電梯司機人就當他是BOY,不準他乘電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層的樓上。(《魯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飾這個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為我不加檢點地不知什么時候說了話,使他聽到不以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紛繁,和友朋來往,是毫不覺得,但到夜里,兩人相對的時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他不高興時,會半夜里喝許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時候。更會像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萊謨斯一樣,跑到空地去躺下。
……
就這樣,沉默對沉默,至多不過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陽光出來了。他會解釋似地說:“我這個人脾氣真不好。”“因為你是先生,我多少讓你些,如果是年齡相仿的對手,我不會這樣的。”這是我的答話。但他馬上會說:“這我知道。”(《魯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習慣及飲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學習》雜志上發表文章,題為“瑣談”,直言她為程式化的魯迅回憶文章所苦,“似乎類于八股式的命題了,每有紀念魯迅特輯的刊物的時候,就很榮幸地直接間接得到通知,許我也參加一分說幾句話。其實這是很窘苦的事,我們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經過,有什么可記述的呢?”
1959年,為慶祝建國10周年,各行各業都須“獻禮”,許廣平受命再憶魯迅,“魯迅逝世已經二十三年了,雖則音容宛若,但總覺言行多所忘記了。為著對歷史的忠實,為著對讀者的負責,都不應孟浪而為,因此頗感苦惱。”
她的真實一如從前,說自己記不得魯迅大段的談話,也沒有什么“猛料”,因為家庭生活中“不是講整套話的時候”,“每每朋友一來,我就張羅些家務:或添菜吃飯,或看顧小孩之類,往往聽到片言只語,未必能全,時日一長,便多忘記了。”
在周揚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導之下,許廣平“深深學到社會主義風格的創作方法”,“就是個人執筆,集體討論、修改的創作方法。我這本小書,首先得到許多同志的直接指導和幫助。他們重視這一項工作,關心指出何者應刪,何者應加,使書的內容更加充實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許廣平寫道,“大躍進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獻禮的洶涌熱潮又鞭策著我;在總路線多快好省的號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勁;工人階級大無畏的堅決創造意志又不斷做我的榜樣,于是就下定決心試試寫作了。”
這個極具時代話語特色的序言在新版手稿本中一字未動。周海嬰在新書發布會上說:“我母親和父親生活了十幾年,從學生到終生伴侶,她說她死后她的文稿可以一個字不修改發表。當年,中國發表文稿、書籍是有‘紀律’的,能不受約束的只是極少數人,我母親沒有豁免權。很多作家都有被修理過的地方,研究中國近50年歷史的學者,可以比對兩個文本,看看作者的原意如何受一種規定話語模式的擠壓,如何變形的。”
《魯迅回憶錄》第十二章,許廣平原題為“在黨領導下的活動工作點滴”,后被改為“黨的一名小兵”。
毛澤東將魯迅神圣化
“魯、郭、茅;巴、老、曹”,將魯迅推上現代文學頭把交椅的不是別人,正是一生從未與魯迅謀面的毛澤東。
1934年初,馮雪峰在瑞金見到毛澤東,向毛匯報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毛澤東對魯迅的事情尤其感興趣。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馮雪峰告訴毛澤東,魯迅看了毛澤東的幾首詩詞后,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聽后,并不生氣,反而開懷大笑。
從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便養成常讀魯迅的習慣。1938年1月12日,他給當時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的艾思奇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華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
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20卷本《魯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這是我國第一次出版《魯迅全集》。通過黨的地下組織,從上海輾轉送到了陜北根據地,毛澤東得到了一套。
這套20卷本的《魯迅全集》一直伴隨著他,從陜北帶到了中南海。毛澤東逝世后,報紙上發表過一張他站在書柜前看書的照片,他手里翻看的正是為他及其他視力減弱的中央領導同志特印的大字本《魯迅全集》。
魯迅的作用和影響力,毛澤東看得很準。1934年與馮雪峰熱議魯迅時,他正受到王明勢力的冷落和打擊,被排擠在中央領導層之外,聽說中央局有意請魯迅主持中央蘇區教育工作時,他搖頭說:“真是一點不了解魯迅!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魯迅的作品1923年便開始入選中學語文教材,民國時期選入教材的多是小說、散文。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蘇維埃中央政府致電許廣平,稱魯迅為“民族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于抗日救國的非凡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
南京當局雖未采納為魯迅“舉行國葬并付國史館立傳”的要求,但孔祥熙以個人名義送了挽聯——“一代高文樹新幟;千秋孤痛托遺言。”
10個月后,“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緊迫的時局淡化了魯迅知識分子的獨立形象,“戰士”、“斗士”的形象被高揚起來。郭沫若以他慣有的充沛激情疾呼,“魯迅并沒有死!目前在前線上作戰的武裝同志,可以說個個都是魯迅,目前在后方獻身于救亡活動的人,也可以說人人都是魯迅。魯迅化為復數了。”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北發表長篇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并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區的語文教材中大量增選魯迅的“戰斗雜文”,而國統區則禁止學生閱讀魯迅,禁止發行魯迅的一切出版物。魯迅不再是獨立于任何黨派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共產黨高擎的一面意識形態大旗。
愈學習魯迅,愈沒有魯迅
建國之后,魯迅作品的解讀朝著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記者身份回到大陸,這一年恰是魯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到“魯迅的神話化和庸俗化的笑話,那是隨處可見的”。同年,他的《魯迅評傳》在港出版,影響巨大,但因為這是一本“人化”的魯迅傳記,直至1999年4月,才在大陸出版。
中國社科院魯迅研究室研究員張夢陽終身致力于魯迅研究的“科學化”,“1957年,馮雪峰、陳涌、李長之、許杰等研究魯迅的學者陸續被打成右派,魯迅研究的學理精神完全被扼殺。背離真實性和魯迅精神的極左傾向,統治了整個中國的精神文化界,魯迅研究領域首當其沖,成為了重災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