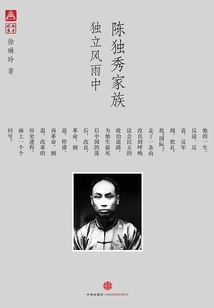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6章 陳氏家族一言難盡的悲愴(2)
- 第5章 陳氏家族一言難盡的悲愴(1)
- 第4章 陳獨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4)
- 第3章 陳獨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3)
- 第2章 陳獨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2)
- 第1章 陳獨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1)
第1章 陳獨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1)
1933年4月20日,國民黨南京最高法院對陳獨秀“叛國罪”案進行第三次公開審判。
在章士釗為他做了長達53分鐘的辯護后,陳獨秀站在被告席上要求自辨,并發表了自撰的《辯訴狀》,對自己三十多年的追求和革命生涯做了一次自我總結。
“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于今三十余年”;五四以后,他組織中共之“終極目的”,是“實現無剝削無階級人人‘更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
這是陳獨秀一生中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獄,距他1919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廈散發傳單的第一次被捕,已14年整。這14年間,他從“新文化運動”統帥,到中國共產黨“開山鼻祖”,到頭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到中國“托洛茨基派”首領,大起大落。
創辦《新青年》時,他決心“不談政治”,希望以“思想和文化的啟蒙”為使命,從改造國民性入手,把國民改造成有“獨立自主人格,自由平等權利”的新青年。
他高舉“德先生”與“賽先生”兩面大旗,呼吁:“國人而俗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
這以后,他回歸到“不隸屬于任何黨派”的獨立思想者。在生平最后一次開創政治局面的嘗試受挫后,他退回書齋,對政治理論進行新的探索和反思,重新評估他曾信奉過、追隨過、批判過的“理論和人物”。這些思考總結成他“最后的政治意見”。
最后,他遠離了馬克思主義,摒棄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核心——“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退回到五四時期他所高舉的“民主”和“人權”。
縱觀陳獨秀的一生,隨著世界政治大勢和國內政局動蕩變幻,他反清、反袁、反軍閥、批孔、批黨、批“國際”,走了一條由改良——民主革命——啟蒙——馬列主義革命——呼喚議會民主的政治道路。為他生前死后中國的落后,改良,革命,倒退,停滯,再革命,倒退,改革的歷史進程,畫上一個個問號。
他自認,“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且以“失敗”告終。
一根南瓜藤爬在門上,幾朵黃花兀自綻放。
東城區箭桿胡同20號門口蹲著一對小石獅子,斑駁的紫黑門開了半扇。從門縫朝里望去,能看到過道里一側堆積著各類雜物,一側停著自行車。一個光著膀子的男子走了出來,看到陌生人,“砰”地一聲關上大門。大門右手貼著牌子:“居民住宅,謝絕參觀。”
箭桿胡同的一側,是民政局高高的圍墻,有一扇緊閉的門。墻角下,蹲著一對農民模樣的老夫婦。
看到記者拿出紙筆,他們跟了上來,說,他們從河北某縣來,是為一樁6年前交通肇事逃逸案來北京上訪的。6年里,只要地里沒活,他們就到這里排號“遞狀子”。
正談著,一白胖壯碩、基層干部模樣的四十多歲男子走過來,狐疑地打量著我們,盤問老夫婦從哪里來,接著又盯上了我,問我是做什么的。我說:我在寫一篇關于歷史的文章,這是陳獨秀在北京的故居。
從1917年初到1920年初,他攜第二位妻子高君曼租下了這座院落,這里也是《新青年》的編輯部,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經常到這里討論、爭辯。
你一定知道吧,在陳先生的倡導下,以“民主”與“科學”為旗號的新文化運動開始了。
選學余孽,康黨,“亂黨”
千里之外,安慶老城喧鬧、破敗,窄窄的老街上,小摩托隨時飛馳而過。
這個如今顯得有些落后的古城,曾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之地。清咸豐十一年,湘軍攻占安慶后,曾國藩即著手建安慶內軍械所,由此揭開了洋務運動的序幕。
光緒五年,陳獨秀出生于安慶一詩書寒門,原名慶同,學名乾生,子仲甫。祖父陳章旭是稟生,為人精明強干。咸豐年間,太平軍占領安慶,他與長子衍藩投筆從戎,輔佐官府,在清軍收復安慶后,獲“以鹽提舉銜候補知縣”的空缺;衍藩被太平軍刺傷,不久身亡。
陳獨秀生父衍中是陳章旭第三子,曾在江蘇做過幾年小官,后以塾師為業,33歲客死蘇州,那年陳獨秀3歲。后因其叔父陳衍庶無子,他過繼到四房做了嗣子。陳衍庶舉人出身,官運亨通,從知縣升至道員,由宦致富,在多處置有田地、商鋪。
陳獨秀6歲跟著祖父讀書。陳章旭在家族中被喚為“白胡子爹爹”,素以威嚴著稱,對天資聰穎的陳獨秀管教尤為嚴格,背不出經書,就拿板子打他。每次被打,他總是倔得不出一聲。祖父不止一次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
光緒二十二年,陳獨秀參加秀才資格考試,勉強過了縣試和府試。院試時,考題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他把《昭明文選》中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中的古文拼湊到一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填滿一篇皇皇大文”。捷報傳來,陳獨秀被取為院試第一,寡母查氏高興得幾乎掉淚,陳獨秀卻由此“更加一層鄙薄科舉”。
1897年8月,陳獨秀隨大哥慶元赴南京參加江南鄉試。他們背了考籃、書籍、文具、燒飯用的鍋爐和油布,擠進臟亂的考棚里。天氣奇熱,在高墻圍住的號門里,士子們熬過3場9天的考試,自己生火做飯。陳獨秀吃著半生不熟的怪面,晚上則睡在考棚里。
鄉試期間,他看到一位從徐州來的大胖子一絲不掛,踏著一雙破鞋,手里捧著試卷在巷子里走來走去,搖頭晃腦地讀著他的文章,念到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翹起大拇指說:“好!今科必中!”這副怪異的考生形象強烈地刺激著陳獨秀,“我看呆了一兩個鐘頭,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由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這般毛病”。
他在《實庵自傳》中說:“這便是我由選學余孽,轉變到梁康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在往后十幾年的行動。”
南京鄉試期間,陳獨秀結識了來自安徽績溪的秀才汪希顏。汪習讀新學,崇尚維新,此時剛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陸師讀書。從此,陳獨秀開始接觸維新思想,并和汪希顏的胞弟汪孟鄒等安徽維新派人士往來密切,常常在一起討論康梁文章。
鄉試后,陳獨秀撰寫了第一篇政論文章《揚子江形勢論略》,向政府獻策。洋洋灑灑近萬字長文中,他分析了揚子江的地理、人文和軍事設防問題,提醒清政府和海內有識人士認清國家的嚴峻形勢,并采取相應的救國措施。
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隨叔父在東北做官府書記的陳獨秀大受震動,由此萌生留學念頭。1901年,他第一次東渡日本,就讀于高等師范學校。不久,他和留學生潘贊化等人一同加入旅日學生進步團體——勵志會,后因與章宗祥、曹汝霖等“穩健派”分歧擴大而脫離該組織。接著,他又加入留日學生中最早的民主主義革命團體“青年會”,結識了黃興、鄒容、陳天華、章太炎等人。
清廷為了管束這些不安分的留日學生,特派遣學監姚煜到日本。陳獨秀想教訓這個專與他們作對的學監,和幾位同道潛入其家,由張繼抱住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剪去了他的辮子。事發后,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鬧事者,陳獨秀等人隨后回國避風頭。
1903年,沙俄背約,拒絕撤軍,企圖長期霸占東三省。消息傳出后,上海、東京出現了拒俄運動。這一年,許多新式青年轉向了民族主義立場,接受“排滿革命”的思想。陳天華的《猛回頭》和《警世鐘》、鄒容的《革命軍》、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開始熱銷。
回故鄉后,陳獨秀與幾個新派學生組成“青年勵志會”,發起安徽首次拒俄大會。在藏書閣,陳獨秀當眾發表愛國演說,抨擊清政府與俄簽訂辱國密約。
兩江總督端方密令安徽巡撫緝拿“首要分子”。陳獨秀逃亡上海。此時,因“蘇報案”入獄的章士釗已獲自由,隨后創辦更為激進的《國民日日報》,邀請陳獨秀參與編輯事務,日日宣傳“排滿”。
《國民日日報》停刊后,陳獨秀再次回到家鄉,與留日學生房秩五和吳守一共同創辦了《安徽俗話報》。這是皖省第一份白話報紙。
陳獨秀寄居在科學社小樓上,日夜夢想著革命大業,臭蟲爬滿了衣服和被褥,也感覺不到。他以“三愛”為筆名撰寫了許多政論,觀點激進,吸引了大量讀者。
在“排滿”情緒的推動下,立意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黨團體開始以“鼓吹、起義和暗殺”為手段,蔡元培、章士釗都曾卷入其中。當時,黃興回國組織華興會,謀劃在慈禧壽辰時起義。在章士釗的邀請下,陳獨秀從蕪湖到上海,正式參與暗殺活動,天天和楊篤生等人實驗炸彈。
1905春,楊篤生又組織了北方暗殺團,派吳樾狙擊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吳樾回鄉安排家事,路經蕪湖,與陳獨秀在科學社小樓上密謀。同年10月24日,吳樾在北京火車站實施暗殺行動,因火車起動時猛烈震動,炸彈自行爆炸,殉難。
暗殺“五大臣”事件后,陳獨秀對這種革命方式產生了懷疑。他不再參加暗殺活動,而是聯合蕪湖安徽公學和安慶武備軍的革命力量,與柏文蔚、常恒芳等人秘密組建了革命團體——岳王會,出任會長,從此投身“科學的革命運動”。岳王會后來與同盟會建立了聯系。
多年后,陳獨秀談到暗殺,說那“只是一種個人浪漫的奇跡,不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科學的革命運動必須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又說:“暗殺所得之結果,不但不能建設社會的善、階級的善,去掉社會的惡、階級的惡。而且引導群眾心理,以為個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會的善、階級的善,可以去掉社會的惡、階級的惡,此種個人的傾向,足以使群眾的社會觀念、階級覺悟日就湮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孫毓筠拍電報,邀請陳獨秀擔任都督府秘書長。
12月,陳獨秀攜妻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慶,第二年1月正式就任。孫毓筠比陳獨秀大10歲,原為清廷舊官僚,好佛學,還有抽大煙的愛好,許多政事都落到陳獨秀肩上。他大刀闊斧搞革新,常與同事發生口角。
1912年,孫毓筠進京改任袁世凱高級顧問。皖省都督一職由柏文蔚接任。陳獨秀和柏文蔚是當年創辦“青年勵志會”的同道,他協助柏做了許多工作,被贊譽為“治皖有功”。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開始,皖督柏文蔚宣布安徽獨立,并出任皖省討袁總司令。陳獨秀隨柏回到安慶,協助討袁,并起草“安徽獨立宣言”。
二次革命失敗。陳獨秀被袁任命的皖督通緝,逃到上海,開始了流亡生活。安慶的老家被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聞訊脫逃,親侄永年被抓。
1914年,在章士釗的邀請下,陳獨秀第五次赴日參與政論性雜志《甲寅》。雖然過著“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的生活”,他的精神卻再次振奮起來了。他結識了李大釗,開始用“獨秀”這一筆名撰寫政論文。
在引起巨大反響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中,他認為:中國人把國家和社稷、忠君等同,無絲毫自由權利與幸福。國家目的是在保障國民權利,共謀幸福。救國之道在于提高“國民之智力”,把中國人的思想引入現代化。
從“救亡”思想出發,這位“康黨”、“亂黨”的組織者和宣傳家開始“轉向”,走向文化啟蒙運動。
新文化運動統帥
仲甫為天生領袖,一決定事,不能動搖。
——章士釗
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來后就著手籌辦《青年雜志》。他明確指出:中國要進行政治革命,必須從“思想革命開始”,“要改變思想,須創辦雜志”。
9月15日,《青年雜志》正式出版。為了與基督教上海青年會主辦的雜志《上海青年》區別開來,從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
關于為何辦《新青年》,陳獨秀認為:當時的中國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腦子里不裝著帝制時代舊思想的,能有幾人?”,“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里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干凈不可”。他還提出20年不談政治,要在此時間里造成鞏固共和的“國民總意”。
創刊號上,他撰寫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這篇后來被人視為新文化運動宣言書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由此拉開新文化運動的大幕。
《新青年》以猛烈的炮火抨擊封建專制主義、舊思想和舊道德。陳獨秀與當時尚在美國留學的胡適通信,在他的誘導下,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開啟了“文學革命”。
陳獨秀身邊聚集起了一批有著新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撰稿人:李大釗、胡適、吳稚暉、馬君武、蘇曼殊、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筆名“二十八畫生”的毛澤東。
《新青年》迅速成為全國思想文化界關注的焦點,陳獨秀也成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領袖,全國出現許多效法《新青年》的雜志和社團。中共早期領袖周恩來、劉少奇、惲代英、鄧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響。
當時還是湖南省第一師范學生的毛澤東也是《新青年》的粉絲,他給雜志投稿,并組織“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后到北京專門拜訪陳獨秀。他說:“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