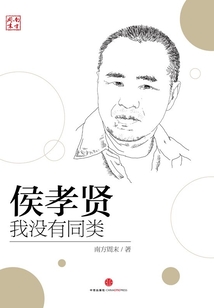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7章 當俠客,很辛苦——侯孝賢說武俠(2)
- 第6章 當俠客,很辛苦——侯孝賢說武俠(1)
- 第5章 第七次上戛納,侯孝賢得了最佳導演獎
- 第4章 創作本來就是有限制(2)
- 第3章 創作本來就是有限制(1)
- 第2章 思考的路,面對市場的電影是走不了的
第1章 侯孝賢是誰?
他是臺灣新電影最重要的代表。
1947年生于廣東梅縣,出生不久即隨父移居臺灣,1972年畢業于臺灣“國立藝專”影劇科。
1980年首導《就是溜溜的她》、《風兒踢踏踩》(1981)成名。
1983年與萬仁、曾壯祥聯合執導的《兒子的大玩偶》獲西德曼海姆影展佳作獎,并引領臺灣電影新浪潮的開端。
《風柜來的人》獲1984年法國南特大三洲電影節最佳作品獎。
《冬冬的假期》獲1985年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作品獎、第三十屆亞太影展最佳導演獎。
1985年執導《童年往事》,獲第二十二屆臺灣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第三十七屆西柏林電影節國際影評人獎,及鹿特丹電影節、夏威夷電影節、亞太影展作品獎。
1986年執導《戀戀風塵》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攝影音樂獎、葡萄牙特利亞國際影展最佳導演獎。
《尼羅河的女兒》獲1987年意大利都靈電影節第五屆國際青年影展影評人特別獎。
1989年執導《悲情城市》獲第二十六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臺灣中時晚報最佳作品獎、導演特別獎,第四十六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1993年執導《戲夢人生》獲臺灣中時晚報電影獎最優秀作品獎,1993年戛納電影節評委會獎。
其后作品有《好男好女》(1995年)、《南國再見,南國》(1996年)、《海上花》(1998年)、《千禧曼波》(2001年)、《咖啡時光》(2004年)、《最好的時光》(2005年)等。
侯孝賢自述:
有人說我后來拍的電影結局都非常悲傷,有時候是一種時間與空間的蒼涼感。為什么會這樣?我個性熱情,跟人非常容易相處,面對世界的眼光似乎不可能是悲傷或蒼涼的。
其實在童年,在成長過程里,你已經不自覺地對這個世界形成蒼涼的眼光了,那是逃不掉的,只是你當時說不清楚,也沒有人告訴你,那段時間就會在心底藏起來。
什么是根?除了實際的電影經驗,就是你成型時期的人文素養,你成長的背景。
《童年往事》說得非常清楚,1947年,我父親是廣東梅縣的教育局長。因為參加審議會,碰到他同學,他同學要來臺灣當臺中市長。他邀我父親當主任秘書,我父親就實實在在來臺灣了。過來以后寫信回去,就把我們全家都接來了,我那時候才4個月。
然后,1949年就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影響到我家里。影響比較嚴重是我母親。突然回不去,她的后援就沒了,親戚朋友全都沒了。我父親得了肺病,心臟也不好。臺北潮濕,會引起氣喘,他就長期住療養院,然后不得不遷到南部。我母親常常兩邊往返,然后帶著一堆小孩。從小就很艱苦,這是我的一個感受。
我奶奶一直要帶我回大陸,她說過了梅江橋就要回去了,因為她太老了,已經沒意識了,她感覺是在真實地回家。你不知道生活有多少荒謬,所謂黑色,是從真實和荒謬來的。
我是4月生人,我的星座是白羊座。星座可能有一定道理,我的性格是總想逃避,就是不想呆在家里,總往外跑。
我們在鳳山的時候,住在城隍廟附近,縣衙旁邊。這個地方是一個古老的小鎮,我們那個城隍廟是臺灣南部七縣市戲劇比賽的地方,每次比賽都要一兩個月。有地方戲劇,就是歌仔戲;有布袋戲,我們叫掌中戲;還有就是皮影戲。這三個是最重要的。小時候我經常在榕樹下跳來跳去,爬到頂上去看人家怎么打。
遇到電影,我就去拉人家的衣袖:叔叔,叔叔,你帶我進去。這樣三次,總有一次可以進去。稍微大一點就不好意思了,就爬墻、剪鐵絲網。
我們還做假票。人們進入戲院后就會把票扔掉,我們就去撿來用。我那時候那么小,可非常清楚,撕票的人絕對不會仔細看的。
我看的電影非常多,所以就養成了一種習慣,到一個地方,比如去北京,一定先看電影,然后看中央電視臺,經常一起床就看。
差不多初中時,我們家住在縣政府宿舍里。我中午吃了飯就溜出來,爬上墻,旁邊就是芒果樹,我就偷摘芒果。我不會偷了就趕快溜,不是,我是先吃,吃完了再帶,帶完了再走。
吃的時候很專注,因為你怕被人家抓,你會注意到底下有沒有人出來,那時候還是農業社會,午休時路上偶爾會有一個人騎單車嘎吱嘎吱過去。你一邊吃,一邊注意細節,因為非常專注的原因,你會感覺到樹在搖,你感覺到風的存在,聽到蟬聲,因為你那么專注,所以那一刻周圍就凝結了——凝結就是瞬間情感的放大。其實電影里面的時間凝結就是把情感放大了,電影中的各種情緒也是如此,有點像慢動作的意思。
我把這段經歷拷貝到了《冬冬的假期》里。這是我對片斷的理解,我常年寫劇本,寫的時候,就想好怎么拍了。
我當導演,可能跟我小時候在城隍廟長大有關,你從小就跟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很自然就有分工:有的人談判,有的人打架。無形中我就養成了領導才能。
我們年齡差不多的孩子形成了一個幫派,內部打,打完之后就跟外面打。我念初三時,我們那一幫差不多十幾二十個人吧,跟南門那邊的人打,他們的外號叫“二十四男嬰”,我們這邊叫“城隍廟”。有一天曠野黑漆漆的,我們到南門那邊打架,我跟另外一個孩子一人帶一把刀,一點都不夸張,先去探。過了橋,到了那邊的小學,一探,沒發現人。回來我們就說沒看到。沒想到他們早就埋伏在橋底下,“哇”一下就圍上來了。
天很黑,刀和刀碰在一起濺出火花,我們退到馬路上,我們一些個頭小的就去撿石頭、磚頭,噼里啪啦地打。
受傷會有,出人命不太可能——因為人多,又在街上。但那很刺激的。那種場面,現在的年輕人很少見到了。
高中時,我們把陸軍士官俱樂部砸了,被抓入獄。在少年斗毆的過程里,當你做得比較大時,比如把士官俱樂部砸了,回到學校里面,你會感覺別人的眼光不一樣,對你突然會有一種尊敬,讓你有一點膨脹。
有同學受了欺負來告訴我,同學說,報你的名沒用,還是被打。我找到那些人就打——以前大家會對打,現在你打他,他不會還手。這些都是經驗。
像我這種玩法,高中畢業是考不上大學的。考不上大學就要去當兵的那一刻,我自己就非常自覺地轉變了。
拍電影是一個團隊,在我們那個年代,每個電影都是跌跌撞撞,沒有一部電影不打的,工作人員遇到問題就打。有時候我在那邊吃便當,看到他們打起來了。“噼噼啪啪”打了一頓之后,我就把他們拉開:好了,不要打了。我知道他們不常打的,挨了打都不知道誰打的。一直打到我導演的第一部片子,我那個制片人跟攝助(攝影助理)打起來了,追著攝助打,他們兩個人一追,我也就不自覺地跑起來,跟著要去打,跑了一半,我想不行:我今天開始當導演了。
這些經驗是你跟人相處、觀察人蠻重要的一個階段。這些經歷讓你有足夠的領導力,不然的話很困難。你不要以為拍電影很容易,有時候一桌人會碰到一撥別的導演競爭,他當場給我難堪,我不必多說,就一句“到外面去”,屢試不爽,很簡單。
現在臺灣男生都比較“娘”了。但你看韓國的電影還是有這種(力量),有這種男人的勁兒。
(作者侯孝賢口述王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