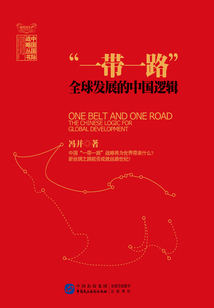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67章 后記
- 第66章 主要參考文獻
- 第65章 初戰告捷“一帶一路”戰略初見成效(13)
- 第64章 初戰告捷“一帶一路”戰略初見成效(12)
- 第63章 初戰告捷“一帶一路”戰略初見成效(11)
- 第62章 初戰告捷“一帶一路”戰略初見成效(10)
第1章 序言
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在西北地區工作了較長的時間,對絲綢之路的各種信息比較關注,工作之余,對古絲綢之路的歷史信息和現實狀況都有興趣獵涉和觀察。盡管那時身居大漠中古絲路上的一個小小的城鎮,考察和吸取信息的半徑很小,但也還是盡力收集有關的資料。
記得在80年代中期,新疆與陜西、甘肅的出版部門分別組織了有關絲路的研究叢書,陜西、甘肅多著眼于漢唐絲路研究,新疆則全方位地從西北的草原文化和西南的石文化與圖騰文化角度,推出許多學術著作。與此同時,他們也出版了西方早期“探險家”的系列記述作品,如斯文·赫定發現樓蘭和他在羌塘探險的自述,等等。這些書籍過去都被視為西方“探險家”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種記錄,能在中國再次翻譯出版,是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分不開的。當時西部的交通是十分不便利的,人們只能從間接得來的信息中認識西部輝煌的過去和夢想著西部新的復興。后來我從事經濟類新聞工作,范長江的經典新聞通訊集《中國的西北角》也就成為必讀之書。
閱讀這些考察論文和寫實作品,你可以感知一個世紀前的羅布泊的真實存在和那時的生態環境,也能夠感知古絲綢之路的壯闊,而不完全是被人視為畏途的難以想象的艱難跋涉。這應當是改革開放后對絲綢之路的研究和引起關注的一次高潮,又或是人們從歷史上關注絲路的一次認識沖動,但總的概念還停留在對歷史文化的認識上,尚未脫離文化考察和歷史考察的階段。絲綢之路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進入了新的階段,也即現實經濟活動階段,而這種現實經濟活動的聚焦點就是西部大開發。而在西部大開發拉開大幕之前,則是對“第二座歐亞大陸橋”的研究。
人們對西部的關注,必然要伴隨著對絲綢之路的關注,從而關注與絲綢之路有著必然聯系的“第二座歐亞大陸橋”。西部大開發與“第二座歐亞大陸橋”的延伸,為人們打開了絲綢之路研究的更為開闊的歷史視野和現實視野。人們不再是只從二十四史和傳世的文獻資料里鉤沉一些盡人皆知的史實,或在歷史文化的領域里兜圈子,或在歷史風情中緬懷中華民族輝煌的過去,而是開始了區域發展中文化因素的各種分析和探尋,或者把絲路文化作為一種經濟資源,推動西部經濟發展。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成為那段時間里絲路研究比較常見的形式。至于古代絲綢之路作為一種曾經在昔日世界里長時間大范圍跨地域廣泛發生,并對世界文明發生根本影響的超地緣經濟技術與文化交流現象,蘊含著什么樣的歷史能量,對中國的未來和對世界的未來還會產生怎樣深遠巨大的影響?誰也沒曾想過,也很難想到。
或許可以這樣說,僅就學界,對于絲綢之路的研究和認識大體已經經過了兩個階段。
一是古代絲路的歷史學階段。較早著有《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蘇州大學教授沈福偉在其《絲綢之路與絲路學研究》一文中概括:“絲路學是20世紀才問世的新學問,也是涵蓋了文化、歷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學科,以及地理、氣象、地質、生物等自然科學的,匯聚了眾多學科、綜合研究多元化的學問。”這種研究最早起源于國際,很快影響到絲綢之路的東方故鄉,出現了持續不斷的高潮。絲綢之路研究中,過去更多地偏重人文和歷史,偏重于歷史的經濟和現實的旅游經濟,是無可厚非的。沒有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既不能達成國內、國際上的人文共識,也難以談到絲綢之路復興的地緣基礎和文明交流傳統。但這只能找回對輝煌歷史的自信,而非對現在與未來的共同發展走勢的牢牢把握。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現代鐵路交通與物流專家提出了“歐亞大陸橋”運輸問題,開始跳出純學術研究和純文化研究的范圍,進入“大陸橋”運輸與物流研究階段。這個階段始于1990年9月12日中國北疆鐵路與蘇聯土西鐵路的接軌。中國北疆鐵路與蘇聯土西鐵路的接軌被稱為“新亞歐大陸橋”貫通,也被稱為“第二亞歐大陸橋”。一些學者提出“開創陸橋經濟新時代”和“第三亞歐大陸橋和亞歐合作”的論點,絲路經濟便以“大陸橋”的陸上運輸形態開始進入區域經濟學家和物流專家的視野。
所謂“大陸橋”,原是地理地貌概念,泛指連接大陸的海中島嶼與地理走廊。用“大陸橋”來描述跨洲和跨洋鐵路則是在20世紀50年代之后,因為那時出現了橫貫北美大陸的跨洋鐵路和60年代末蘇聯修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第二條歐亞大陸橋”和陸橋經濟觸及了跨國物流產業發展合作的研究半徑,甚至也成為西部大開發最初的一種呼聲。那時我在經濟日報社擔任評論部主任,先后寫過關于東南沿海開放的系列解釋性新聞述評《大戰略》和《大陸橋》,算是關注西部開發的開始。但那時對西部開發還停留在產業梯度轉移的老舊理論上,認識和研究并不能直擊到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經濟共同發展的歷史要求與本質,更不能直擊到基于地緣經濟規律基礎上的絲路發展。對絲綢之路有關材料的閱讀,只當作是一種文化背景,對大陸橋的思考也只能說是絲路重新進入現代國際經濟生活的一個朦朧的、零碎的甚至是幻想式的模糊感知。
絲綢之路,一個在世界經濟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永遠閃亮的名字,究竟是輝煌的過去還是未來的繁榮?的確,絲綢之路曾經是一個歷史概念,因此引起大量中外學者的探尋與研究,并由此形成了熱極一時的“絲路學”。就陸上絲綢之路來講,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起伏,榮辱更替,過去曾是無可替代的歐亞大陸間的經濟、技術、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是當時世界夢想的中心舞臺,承載起數之不盡的歷史內容和信息。研究絲路的歷史,你可以說它是絲綢之路,也可以說它是彩陶之路、瓷器之路、青銅紅銅冶煉技術之路、鐵器之路、茶馬與車騎之路、火藥紙張印刷術科技傳播之路、農牧業產品基因交匯之路、文化和不同國家民族的文明理念交流之路,還可以說他是民族遷徙、民族融合和亞歐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之路。在中國的歷史上,絲綢、瓷器、茶和馬匹是流通其間的四種大規模交易產品。交易鏈最長的是絲綢,處于價值鏈頂端的也是絲綢,這就是李希霍芬將其命名為絲綢之路的根本原因。說到底,絲綢是一個重要的貿易符號,而且是有生命的貿易符號。它代表著很長時期亞歐貿易的繁盛與繁榮,也會代表未來亞歐與世界貿易的進一步繁盛與繁榮,在新的生命周期里再次復興。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他在阿斯塔納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時,從古絲綢之路留下的寶貴啟示里第一次明確指出,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的絲綢之路,完全可以成為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共享和平、共同發展的新的絲綢之路。他闡明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基本特質: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緊接著他又在上海合作組織領導人會議上提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正在協商的交通便利化協定,將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道。中國愿同各方積極探討完善跨境交通基礎設施,逐步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絡。為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造福沿線人民。時隔一個月后,他又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時進一步提出了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發展構想作為一個極其重大的現實活體發展戰略,作為一個來自世界文明發展源頭深處并將對中國、對世界、對當前世界經濟一體化和未來世界和平發展、共同發展產生重大歷史影響的戰略思想,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一帶一路”發展構想的提出不僅標志著絲路發展再次復興,絲綢之路再次成為連接亞、歐、非和東西方經濟文化聯動發展的紐帶,也充分體現了東方發展的戰略智慧。“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構想提出短短一年多時間里就引起世界沿線國家的廣泛共鳴,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發展、共同發展理念不脛而走,沿線五十多個國家響應參與,并與他們各自的發展戰略積極對接,成為一種共同的戰略取向,形成一種活潑的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實踐,這是空前和罕見的。“一帶一路”發展構想甫一問世,就成為當前世界最具影響力、最有操作前景的發展戰略理論,成為中國和沿線國家地區共同發展的共同地緣經濟財富和推動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的重大理論創新,同樣是空前和罕見的。
這不僅是因為絲綢之路承載著文明發展的市場傳統,也基于地緣經濟規律的一種永恒,這種永恒并不會因為“地球村”的出現就會發生改變,相反地進一步拉近了互動的距離,拉近了人們審視過去,面向未來的視野。在這條歷史悠長的絲路上印滿的,不僅是對中西經濟、文化和文明交流的記憶,還會印滿具有巨大可逆性的現實經濟發展的印轍。當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入了新的關鍵階段,中國的發展也進入經濟轉型的新常態,習近平主席“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舉重若輕,熔鑄古今,面向未來,對中國與世界的可持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戰略貢獻。
中國有句諺語說:“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亞洲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誰也不可能“單打獨斗”“獨善其身”,也不會是“零和博弈”,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深度合作,才能產生“一加一等于二的疊加效應”,甚或“二乘二等于四的乘數效應”。在這里,地緣問題其實是“地利”,而“地利”之利,不僅在于認知,更在于蓄勢待發中的通盤謀劃。在人們的常識里,大多都知曉地球上曾經存在過一條影響到人類文明發展的絲綢之路,但未必想得到,這條絲綢之路在未來還要深刻地影響到世界的發展軌跡,影響到世界經濟技術文明的繼續提升。從歷史認知到現實實踐,是思維與思想的區別。一個經歷過“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首次出現了一個全面完整和成熟的經濟發展戰略,看似“橫空出世”,其實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必然結果。這是認知與實踐的“常青樹”上結出的果實,樸實無華,帶著昔日泥土的芳香,卻又像戈壁灘上千年不倒的胡楊樹,根深葉茂,更像是西亞與歐洲花園里的“無花果”,在平實的思維枝干的尖端上凝結出一種跨時空的東方智慧。
“一帶一路”發展構想不只是一個理論,而且具有深厚的內容與內涵。平等互利、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其靈魂,共商、共建、共享是其追求,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人心相通這五個通則是其方法論。因此,具有明白如話的可操作性。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從經濟合作布局到建立不同形式、不同合作程度的經濟伙伴關系,從自貿談判到項目合作,從貿易到投資,從金融合作到新的國際金融機構的籌備,成果巨大,尤其在第22次APEC領導人會議在北京舉行期間,中國啟動了亞太自貿區路線圖,這其實也是“一帶一路”發展的新的進展,顯示了“一帶一路”發展的影響力和巨大的能量。
“一帶一路”發展構想也使“絲路學”進入現實的跨大區域經濟發展實踐與地緣經濟戰略學階段。圍繞“一帶一路”,中國全新全視角的絲路發展戰略學開始出現,并成為多種國內國際發展戰略中的核心戰略。這個核心戰略扎根在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樹冠與枝葉伸向世界,視野開闊,澤被全球,打破了近代西方戰略學,特別是形形色色的地緣政治學說話語系統“霸權”的一統天下,是奠定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發展話語權的重要基石。“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具有三個明顯繼承性的傳統特征,即和平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也具有三個新的特征,即通透、開放與軟硬實力渾然一體、緊密結合。這些特征貫穿了發展的硬道理,統領多種戰略研究,形成更明確、更具戰略自信和更具普世價值的發展戰略體系。
對絲綢之路的戰略理論研究,目前是理論滯后于實踐,有些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需要系統開展。筆者研究水平有限,對“一帶一路”構想學習理解尚淺,能借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組織出版“中國國際戰略叢書”的機會拿出來與讀者交流,多少有些不揣淺陋,一些觀點也難免會有偏頗之處,希望能夠拋磚引玉,也歡迎批評指正。是為序。
感謝中國出版集團李巖先生,感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劉海濤先生、趙卜慧女士、石松先生、劉姝宏女士,更感謝叢書主編鄭必堅先生,沒有他們的幫助,本書不可能很快面世。在此一并致謝。
馮并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