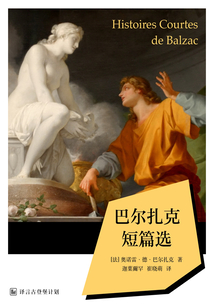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17章 《認不出的杰作》和《巴黎的一條街道和它的居民》譯后記
- 第16章 《薩哈西妠》翻譯說明及詞表(4)
- 第15章 《薩哈西妠》翻譯說明及詞表(3)
- 第14章 《薩哈西妠》翻譯說明及詞表(2)
- 第13章 《薩哈西妠》翻譯說明及詞表(1)
- 第12章 巴黎的一條街道和它的居民(2)
第1章 薩哈西妠(1)
致夏爾·德·貝爾納·杜·格亥伊先生
我沉入了幻夢,那種在最最鬧騰的聚會上,將所有人,即便是輕薄浮躁之輩,都牢牢攝住的濃深幻夢。午夜剛剛叩響波旁–愛麗舍宮[1]的大鐘。我坐在窗洞[2]中,藏身于閃光幃幔的波瀾之下,便可以從容凝視這座宅邸的林園,消磨今晚的時光。那些樹,雪衣襤褸,在構成云天的灰茫底色中勉強現形,幾乎不為月光洗映。在這奇幻的氣氛里看去,它們冥冥中像是些尸布零落的鬼魂,著名的/死亡之舞/的巨人景象。接著,我轉向另一側,又可以欣賞生活之舞!一座華麗燦爛的客廳,金墻銀壁,明燈高懸,燭光耀眼。在那里,成群結隊、蜂涌攢動、蝶舞翩翩的,全都是巴黎最漂亮的女人,最最富有,最是尊貴,光鮮亮麗,榮華軒昂,陣陣眩目的鉆石光芒!臉上貼著花,胸前別著花,發間戴著花,裙擺撒著花,連腳上都系著花環。歡愉的悸動,撩人的步態,她們嬌柔的腰肢間,蕾絲、紗綾與綢羅隨之繚轉婆娑。一些活潑過頭的明眸四處放電,蓋過燈的光明和鉆石的火焰,把那些本就炙情過盛的心神煽動得火旺焰高。還可撞見的是,送向情人的秋波,真真切切,面對丈夫的態度,卻是拒之千里。每一次擲出意外的色子,玩家們嗓門的爆破、金子叮當的回響,都與音樂和竊竊私語混為一談;這群人已被世上包羅萬象的誘惑弄得飄飄如仙,而香水的蒸薰和全場的熱昏仍在鞭策脫韁的心馬,直要來一個醉死夢生。如此這般,我的右側,死亡陰郁靜漠的景象;我的左側,生命合情合理的縱歡;這邊,是冷卻的自然,凄清死寂,身披喪服;那邊,是歡樂的人類,盡享今宵。而我呢,我位于這兩幅格格不入的畫面的邊界上——它們以形形色色的方式重演了千萬遍,使巴黎成為世上最讓人歡樂、也最令人深思的城市——我便成了一張精神拼盤,一半是歡愉,一半是悲悼。用左腳,我踩著節拍,我以為我的另一只腳踏進了棺材。其實,這條腿只是被那種溜進來的風給吹凍了,這種風會把您的半邊身子都吹僵,而您的另半邊還正感受著客廳里的濕潤熱情——舞會上相當常見的小意外。
“德·朗蒂先生得了這宅子才沒多久吧?”
“哪里。卡里格利亞諾元帥賣給他都快有十年了……”
“哦!”
“這些人一定錢多得都數不清了吧?”
“那可不!”
“真是場盛會吶!奢侈得過份。”
“您認為,他們會富得像德·努辛根先生和德·恭德維爾先生那樣嗎?”
“怎么,您竟然不知道?……”
我探出頭去,認出這兩位談話人,是那種好打聽之流,在巴黎,這伙人專門忙著琢磨那些個/為什么?怎么樣?他是哪兒來的?他們是誰?出了什么事?她干了什么?/他們壓低了嗓門,退避到某張孤寂的沙發上,以便聊得更加暢快。在奧秘勘探家們面前,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哪座更為豐饒的礦藏呢。沒人知道德·朗蒂一家是從什么地方來的,也沒人知道,他們做的是哪門子生意、如何地巧取豪奪、怎樣地海上劫掠、還是從誰哪里繼承了遺產,才得來這么一筆估計有好幾百萬的財產。這一家子,人人都會說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英語和德語,還說得相當完美,不由得讓人揣測他們與這些個民族肯定都處過很久。莫非他們是波西米亞人?莫非他們是安的列斯海盜?
“就算是魔鬼又怎樣!”幾位青年政要說道,”他們招待起客人來,可真是好得神奇。”
“哪怕德·朗蒂伯爵搶劫過什么/北非王宮/,我也照樣樂意娶他的女兒!”一位哲人嚷道。
又有誰會不樂意娶瑪利婭妮娜呢?十六歲的少女,她的美麗,使東方詩人心中縹緲的幻境成了真。就像/阿拉丁神燈/中蘇丹的女兒,她真該永遠都蒙著面紗。她的歌聲,令瑪利卜杭、桑塔格、弗多茲那些不完善的才華黯然失色,這些人身上總有某種突出的特質妨害了整體的完美;而瑪利婭妮娜卻能將音色的純凈、感受性、拍子與音調的精準、靈魂和技巧、規范和情感,恰如其份地融為一體。這姑娘是那神秘詩學的原型,一切藝術的同心之結,人們尋覓慕求,卻總是臨之則逝。甜美而端莊,敎優且靈慧,沒人能蓋過她的光芒,除了她的母親。
您可曾見過這樣的女人,她們的驚魂之美傲逸歲月的摧折,年至三十六,卻比其在十五年前更令人渴求?她們的臉就是激情澎湃的靈魂,光芒萬丈;眉宇間處處閃耀著精明強干;毛孔中全都蘊藏著非凡的光華,尤其是在燈光之下。她們攝人的雙目,或在勾人心魂,或是拒人千里,或在若有所語,或是緘口不言;她們的步調章法老練,卻又天真自然;她們的嗓子施展出最為嬌媚、最是親甜的聲調中才具有的歌音瑰寶。她們給予別人的贊揚,立于比較,有憑有據,最怕癢的自尊心聽了,也不由心悅臣服。她們眉頭一動,眼色一變,嘴唇一抿,都會在那些性命和幸福都懸于她們一身的人們心上刻下一道道驚悚慞惶。初嘗愛情、輕信言表的少女可能會受人迷惑;可對于這種女人,男人必須學會,就像德·舒绔先生那樣,藏在壁櫥里被女仆開門夾碎兩根手指之時,都能夠不動聲色。去愛這種強大的塞壬[3],這不是在玩火自焚嗎?可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愛她們愛得如火如荼!德·朗蒂伯爵夫人正是這樣的女人。
菲利波,瑪利婭妮娜的兄弟,和他姐姐一樣,也秉承了伯爵夫人的神奇之美。一言蔽之,這少年就是安提諾烏斯[4]的活畫像,只是身形更削瘦些。不過,這清瘦嬌弱的身材與青春朝氣水乳交融,而那橄欖色的臉龐、強勁的眉棱和溫淳目光中的星火,又預示著未來雄渾的激情和寬宏的思想!如果說,菲利波會以白馬王子的形象留在少女們心中,那么,他同樣會作為法國最佳女婿的人選駐進所有母親的記憶。
這兩個孩子的美貌、幸運、聰明和優雅,全都得自他們的母親。德·朗蒂伯爵既矮又丑,還一臉麻子;陰郁如西班牙人,無趣如銀行家。別人卻以為他是位深不可測的政要人物,或許是因為他難得一笑吧,還老是引用德·梅特涅[5]或威靈頓[6]先生的話。
拜倫勛爵有一首詩,對于其難點,社交界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讀,而這個神秘家庭有著與這詩完全一致的魅力:一首越唱越撲朔迷離、越唱越高風勁節的歌。德·朗蒂先生和夫人對其出身、往昔、與四分天下的那些個國家的聯系諱莫如深,這在巴黎,作為一個轟動話題,本不該持續多久。恐怕再沒有別的地方,能比這里更好地理解韋斯巴薌的那句格言[7]了。在這里,埃居[8]上即使沾滿了血跡汚穢,也不會露馬腳,埃居就代表一切。這個上流社會只要了解了您的財產數目,就會把您劃歸到與您的金額相應的級別中去;沒人要看您的羊皮紙[9],誰都知道那玩意兒才值幾個錢。在一個社交問題是用代數方程式來解答的城市里,冒險家們可真稱得上是奉天承運了。這個家庭就算是出身于波希米亞,可他們如此富有,如此引人入勝,有那么點小秘密,上流社會本來也沒什么不能諒解的。可不巧的是,朗蒂一家的歷史謎團,貢獻著一個滔滔不竭的興趣源泉,頗有幾分安妮·拉德克里夫小說里的味道。
觀察家們,就是那種連您家的大燭臺是在哪家店買的都要打聽清楚,或是發覺您的公寓不錯便要詢問房租多少的人,已經注意到,在伯爵夫人舉辦的聚會、音樂會、舞會以及交際會上,時不時會出現一個奇異人物的身影。是個男的。他在這宅邸的初次露面是在一場音樂會上,似乎是被瑪利亞妮娜那令人著迷的歌聲所吸引,走入客廳里來的。
“我這會兒覺得有點冷。”門那邊一位女士對她身旁的人說。
那陌生人恰在這女人附近,他走了開去。
“這可真是奇了怪了!我又覺得熱了。”怪人一走,那女人就說。”您也許會罵我瘋了,可我還是忍不住覺得,我旁邊的那位,剛走開的那個穿黒衣服的先生,就是他讓我感到冷的。”
很快,天性夸張的上流社會便為這個神秘人物炮制、匯編出了一大套令人捧腹的見解、刁鉆古怪的段子和荒誕不經的傳聞。雖然他未必就是吸血鬼、食尸鬼、人造人、某種浮士德或羅賓漢,但根據奇幻愛好者的說法,所有這些類人物種的特性他身上全部具備。多多少少總有些德國人還能把巴黎人這種別出心裁的惡毒玩笑當了真。這怪人只不過是個/老頭/罷了。好些個習慣于每天一大清早用幾句高雅辭藻來決斷歐洲前途的年青人,硬是看出了這陌生人是某個重大罪犯,身上錢財無數。小說家們便描繪起這老頭的生平,為您和盤托出他在給邁索爾邦王子效力時所犯下暴行之千奇百怪又千真萬確的詳細內幕。銀行家們,這些更講究實際的人,也擬定了一份頗為迷惑人的奇談:
“噢!”他們突發一陣惻隱,聳聳雄厚的肩膀,”這小老頭可是個/熱那亞頭/啊!”
“先生,若不冒犯的話,請不吝賜敎,您說的熱那亞頭是什么意思?”
“先生,這個人啊,他身上堆著的財富可多得去了,他的身體好壞,毫無疑問,左右著這一家人的收入。我記得曾在德·艾斯巴赫夫人家,聽一個磁氣療法師用極為迷惑人的歷史推理法證明,這老頭,放到玻璃棺里看,就是那個著名的巴爾薩摩,人稱卡格里奧斯托[10]。據那位現代煉金術士說,這位西西里冒險家已經煉就了長生不死,只是自得其樂地為他的孫輩們制造黃金。不過,弗海特的大法官宣稱他已經確認,這個詭異人物就是德·圣日爾曼伯爵[11]。”
這些個胡言亂語,說得如此詼諧風趣,說得簡直眉飛色舞,展現了當今這個信仰缺失的社會之特征,也使得對德·朗蒂府上的曖昧揣測經久不息。不過,這也是由于情況特殊,機緣湊巧——一家子成員對待老頭總是那么神神秘秘,而他的生活狀況,無論如何調查,又總是不露蹤跡——世人對此心存猜疑,也就并不為過了。
這個人物應該是呆在德·朗蒂宅邸中他自己的套房里的,要是他一跨出套房的門檻,就會如顯靈一般把全家上下驚得一片大呼小叫。別人還會以為出了多大的事兒呢。唯獨菲利波、瑪利婭妮娜、德·朗蒂夫人和一個老仆人才享有服侍這陌生人起坐行走的特權。每個人都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看起來他仿佛是個會吟咒的人,大家的幸福、生活、財產,全都仰賴于他呢。這是出于畏懼,還是摯愛?社交界找不出任何能解開這個疑團的線索。這位家神,在某座不為人知的神廟深處藏匿了足足幾個月之后,會突然從里面走出來,神不知鬼不覺,出人意料地現身于客廳之中,就如往昔的那些女妖,從飛舞的悍龍背上一躍而下,來攪擾未曾邀請她們的慶典。此時,只有最老道的觀察家,才能猜出府上主子們的焦慮,因為他們掩飾情緒的本領非凡。可有時,就在跳四對舞時,太過單純的瑪利婭妮娜,身在舞池,卻仍留意著老頭,會驚恐地向他投去一瞥。又或是菲利波,奔跑著鉆過人群,沖到他那邊,守在他身旁,既親熱又警惕,仿佛別人輕輕碰一下,或是微微吹口氣,這個古怪的生靈就會裂成碎片。伯爵夫人在竭力朝他那邊靠過去,但看上去又沒有要和他待在一起的意思;過了一會兒,她才跟他說上兩三句話,態度神情既卑微又親熱、既溫順又專橫,卻幾乎總能將老頭擺平,于是,他便消失了,被她帶走了,更確切地說,被她搶走了。若是德·朗蒂夫人不在,伯爵就得用上千方百計才能走到他跟前;可他似乎很難使他聽話,就像母親慣著寵壞的孩子,由著他任性,又怕他無法無天。有幾個不識相的,竟冒冒失失去跟德·朗蒂伯爵打聽,而這個冷漠拘謹的人,好像從來就沒聽懂過這些好打聽們的問題。這樣的嘗試總是無功而返,因為所有的家庭成員都非常謹愼,一個機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便沒人還會想要去鉆探了。圈子里的包打聽、無事忙、政要團們,遂生厭戰之心,也就不再為此謎團浪費時間了。
不過,這會兒,在這些光鮮亮麗的客廳里,或許還有幾位哲人,吃著冰淇淋或凍果冰,或是喝完潘趣酒,把杯子往壁臺上一放,討論道:
“要說這伙人真的是賊,我也不至于吃驚。那老頭一直深藏遠遁的,只有到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才露一下面,照我看,他就是個殺手……”
“要不就是個破產詐騙犯……”
“這差不多是一回事。把人家的財產弄掉,有時候,比把人弄掉還慘呢。”
“先生,我賭了二十金路易,我該拿四十的。”
“天吶!先生,桌上只剩三十……”
“唉!您看看這伙人有多亂。沒法玩了。”
“可不是么。不過,我們快有六個月沒見過那個鬼了吧。您覺得他是活的嗎?”
“嘿!嘿!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