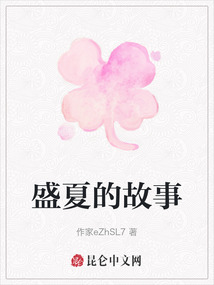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梧桐葉落在便簽上時
舊書里的橙紅信箋
十月的風把梧桐葉吹成深焦糖色時,「清淮書社」的木門上貼了張淺米色海報——上官清淮要辦一場“舊書換故事”的市集,用家里藏的老書,換客人們帶的舊物故事,海報邊緣畫著圈小小的銀杏葉,是李嘉崢用淡金色顏料描的。
冀家祺來幫忙時,書店里已經堆了半屋子舊書。上官清淮正蹲在書架前,把書按年份排開,米白色針織衫袖口沾了點灰,他卻不在意,指尖拂過書脊時,像在摸老朋友的手。“這些都是爺爺留下的,”他拿起本藍布封皮的書,封面上燙金的字已經磨得模糊,“有些夾著信,有些夾著車票,每本都是故事。”
李嘉崢在角落里修書脊,手里捏著支細針,正把斷開的線重新縫回去。他穿了件淺灰色的薄毛衣,腕間的木質珠串隨著動作輕輕晃,陽光從玻璃窗照進來,落在他膝頭的麂皮布上,把散落的棉線照成了金絲狀。“家祺,幫我遞下那邊的白膠?”他抬頭時,眼里映著書架上的干花,是淺橘色的小雛菊。
冀家祺剛遞過膠水瓶,就聽見上官清淮“呀”了一聲。他從本1987年版的《邊城》里,抽出了張折得整齊的信箋,紙邊已經泛黃發脆,上面是用橙紅色鋼筆寫的字,字跡娟秀,像春天的藤蔓:“阿明,銀杏黃時我就回來,帶你去看河邊的白楊樹。”
三個人圍著小桌坐下,上官清淮輕輕展開信箋,橙紅色的字跡在暖光里泛著柔潤的光,信尾沒有署名,只有個小小的銀杏葉符號。“應該是很多年前,有人夾在書里的。”他指尖碰了碰信箋邊緣,像怕碰碎了時光,“說不定,她后來真的和‘阿明’去看了白楊樹。”
李嘉崢從帆布包里掏出個小小的透明塑封袋,把信箋小心裝進去:“可以貼在留言本里,說不定有人會認出這個字跡。”冀家祺看著塑封袋里的橙紅信箋,忽然想起外婆相機里的老照片,那些沒說出口的話,或許都藏在舊物的褶皺里,等著被人輕輕翻開。
整理到傍晚時,書店里飄起了肉桂香。上官清淮在柜臺后煮熱紅酒,鍋里的橙片、蘋果塊和丁香在冒泡,甜香混著舊書的墨香,漫得滿屋子都是。他倒了三杯,杯口插著干橙片,遞過來時,杯壁上的水珠滴在桌布上,暈出小小的圓:“暖一暖,等會兒去巷口看銀杏。”
巷口的兩株銀杏樹已經黃透了,葉子像撒了滿樹的金箔,風一吹就簌簌落,鋪在青石板路上,像條金色的毯子。李嘉崢掏出拍立得,對著漫天飛舞的銀杏葉按下快門,“咔嚓”一聲,把冀家祺伸手接葉子的樣子拍了下來。照片顯影時,她看見自己掌心托著片銀杏,背景里的金葉像在發光,上官清淮站在遠處,正低頭撿著什么,影子被夕陽拉得很長。
“看這個。”上官清淮走過來,手里舉著片邊緣帶淺紅的銀杏葉,葉脈像用金線繡的,“這種‘紅邊銀杏’很少見,夾在書里能存很久。”他把葉子遞給冀家祺,又從口袋里掏出兩片,分給李嘉崢:“夾在我們的留言本里,湊成三枚,像我們三個的小標記。”
相機里的銀杏與月光
市集當天,書店里擠滿了人。每個攤位前都擺著舊書,客人們帶著自己的舊物——有泛黃的日記本,有掉漆的鋼筆,還有個老奶奶帶來了臺老收音機,說里面還能放出幾十年前的戲曲。冀家祺負責登記故事,桌上放著本新的牛皮紙本子,每記下一個故事,就貼一片銀杏葉。
李嘉崢在角落擺了個“舊相機展覽”,把自己修過的相機都擺了出來,其中最顯眼的就是那臺柯尼卡C35,旁邊放著洗出來的海邊照片,還有那張夾著橙紅信箋的《邊城》。有個小女孩指著相機問:“叔叔,這個能拍月亮嗎?”他蹲下來,笑著說:“能啊,等晚上,我們就用它拍月亮。”
上官清淮在柜臺后煮熱紅酒,客人們喝完就坐在書架旁,有的讀舊書,有的聊故事。有個穿藍色外套的男生,用一本1990年的《小王子》,換走了那本夾信的《邊城》,他說:“我爺爺叫阿明,我想把這封信帶回去,給奶奶看看。”上官清淮遞過書時,眼里的光很軟:“說不定,這就是信里的‘阿明’呢。”
傍晚客人們走后,三個人坐在滿地銀杏葉的書店里,收拾著攤位。冀家祺翻著新的故事本,里面記滿了細碎的溫暖——有情侶的定情信物,有朋友的畢業紀念,還有老人對老伴的思念。李嘉崢把相機收進帆布包時,忽然說:“今晚月亮很圓,去河邊拍月亮吧?用柯尼卡。”
河邊的風比巷子里涼,卻帶著點銀杏的甜香。冀家祺舉著柯尼卡,對著天上的圓月調焦距,李嘉崢站在旁邊,指尖輕輕幫她穩住相機:“慢一點,月亮會更清晰。”上官清淮坐在河邊的長椅上,手里拿著那本《小王子》,輕聲念著:“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記得。”
“咔嚓”一聲,相機拍下了月亮。冀家祺看著取景框,里面的圓月像塊白玉,落在淡藍色的夜空里,河邊的白楊樹影映在水里,像水墨畫。李嘉崢掏出手機,對著月亮拍了張,遞給她看:“等膠卷洗出來,我們把月亮照片貼在留言本里,和銀杏葉放在一起。”
回去的路上,銀杏葉還在落,月光把葉子照成了半透明的金。冀家祺手里攥著那片紅邊銀杏,口袋里裝著拍立得照片,心里像被暖光填得滿滿當當。上官清淮走在最前面,哼著首老曲子,調子輕輕的,和腳步聲、落葉聲混在一起,像首溫柔的夜曲。
“下次,我們去看雪吧?”李嘉崢忽然說,聲音被月光裹得很軟,“我知道山里有個木屋,冬天會下雪,能拍雪景,還能烤紅薯。”上官清淮回頭笑:“好啊,我帶本雪夜讀的詩,家祺帶柯尼卡,我們把冬天也裝進相機里。”
冀家祺點頭時,看見巷口的銅鈴鐺在月光下泛著淡光,風一吹就“叮”地響,像在應和他們的約定。她忽然覺得,這些日子的時光,就像舊書里的橙紅信箋,像相機里的銀杏與月光,像身邊這兩個人的笑臉,都被小心地藏在時光里,輕輕一碰,就滿是溫柔。
雪夜里的暖爐與詩
十二月的雪來得比預想早。冀家祺裹著米色羽絨服,站在巷口等李嘉崢和上官清淮時,雪花已經把梧桐枝染成了白色,像開了滿樹的銀花。李嘉崢背著個大帆布包,里面裝著柯尼卡相機、拍立得和烤紅薯的工具,上官清淮提著個保溫桶,里面裝著熱湯,兩人的頭發上都沾了點雪,像撒了把碎糖。
“車在前面。”李嘉崢拉著她的手腕往巷外走,指尖的溫度透過手套傳過來,暖得像揣了個小暖爐。上官清淮跟在后面,笑著說:“山里的雪更大,木屋前的銀杏樹,現在肯定是滿樹銀白。”
車開了一個小時,才到山里的木屋。木屋是深棕色的,屋頂積著厚厚的雪,門口掛著串玉米和紅辣椒,像幅民俗畫。推開門時,暖爐里的火正旺,把屋子照得暖橘色,木桌上放著本翻開的詩冊,是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書頁間夾著片干銀杏。
“這是我爺爺的木屋。”李嘉崢蹲在暖爐旁添柴,火苗映在他臉上,像跳動的金,“小時候冬天常來,清淮哥總帶著詩來讀。”上官清淮把保溫桶里的熱湯倒出來,是蘿卜排骨湯,香氣漫開來,混著暖爐的木柴香,讓人心里發暖。
吃完熱湯,雪下得更大了。冀家祺舉著柯尼卡,對著窗外的雪景按下快門。雪花落在銀杏枝上,像給樹枝裹了層白絨,遠處的山林變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只有幾棵松樹露出深綠色的尖頂,像水墨畫里的留白。李嘉崢站在她身邊,幫她拍掉肩上的雪:“別凍著,里面有暖寶寶,我給你拿。”
上官清淮在木桌旁煮熱紅酒,這次加了肉桂和八角,甜香更濃了。他翻開詩冊,輕聲念道:“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聲音混著窗外的雪聲,像把整個雪夜都裹成了柔軟的棉花。冀家祺坐在暖爐旁,看著跳動的火苗,忽然覺得,這樣的夜晚,就像夢里的場景——暖爐、熱紅酒、詩,還有身邊的兩個人,都讓人不想醒來。
傍晚的時候,雪停了。夕陽透過窗戶照進來,把雪染成了淡粉色,像撒了層桃花粉。李嘉崢掏出拍立得,對著暖爐旁的兩人按下快門——冀家祺手里捧著熱紅酒杯,上官清淮翻著詩冊,背景里的火苗像在發光。照片顯影時,他們看見彼此的臉上都帶著笑,暖爐的光把影子投在墻上,像兩個靠在一起的小太陽。
“烤紅薯好了!”李嘉崢從暖爐里掏出個錫紙包,打開時,甜香撲鼻。紅薯烤得焦甜,咬一口,燙得直哈氣,卻暖得從舌尖甜到心里。上官清淮遞過張紙巾,笑著說:“慢點吃,沒人跟你搶。”冀家祺擦了擦嘴角的糖汁,忽然想起第一次在舊物市集遇見李嘉崢時,他遞過來的那顆薄荷糖,也是這樣的甜。
晚上,他們躺在木屋的小床上,看著窗外的月亮。月亮被雪映得更亮了,像掛在天上的銀盤。李嘉崢說:“明天早上,我們去拍日出,雪后的日出會是橘紅色的,特別好看。”上官清淮輕聲說:“我還帶了星星燈,明天可以掛在銀杏樹上,拍出來像星星落在樹上。”
冀家祺閉上眼睛時,聽見暖爐里的木柴偶爾“噼啪”響,聽見身邊兩人輕輕的呼吸聲,心里像被填滿了暖光。她忽然覺得,相遇這件事,真的很神奇——從舊物市集的銅齒輪,到書店的薄荷茶,從海邊的夕陽,到雪夜的暖爐,每一個瞬間,都像時光精心安排的禮物,輕輕拆開,就滿是溫柔。
第二天早上,日出果然是橘紅色的。他們在銀杏樹上掛了星星燈,冀家祺用柯尼卡拍下了橘紅的日出、掛著星星燈的銀杏樹、雪地里的腳印,還有李嘉崢和上官清淮笑著的臉。膠卷里的每一張,都是這個冬天最溫暖的故事。
回去的時候,冀家祺把洗出來的照片貼在了書店的留言本里,旁邊貼了片雪地里撿的銀杏葉,葉子上還沾著點雪的痕跡。上官清淮在照片旁邊寫了行字,用的還是淡藍色墨水:“雪會化,葉會落,但我們的故事,會一直留在時光里。”李嘉崢畫了個小小的暖爐,旁邊畫著三個人的影子,冀家祺則貼了顆薄荷糖的糖紙,透明的糖紙在陽光下晃著,像顆小小的星星。
風從書店的玻璃窗吹進來,帶著巷口銀杏的香,留言本被吹得輕輕晃,照片里的日出、雪景、笑臉,還有那片銀杏葉,都像在輕輕呼吸。冀家祺看著身邊的兩個人,忽然明白,有些陪伴,就像舊書里的故事,像相機里的光影,像雪夜里的暖爐,不用多說,就滿是溫柔——而這樣的溫柔,會一直陪著他們,走過一個又一個春夏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