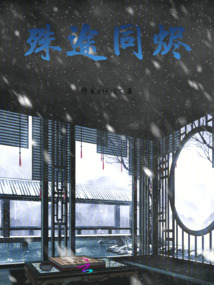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殿試驚鴻
永熙十二年,春闈剛過,金殿之上,新科進士們垂首屏息,等待著最終命運的宣判。
殿內金碧輝煌,蟠龍柱高聳,支撐著繪有祥云仙鶴的藻井。御香裊裊,來自西域的沉水香清冷馥郁,卻壓不住空氣中彌漫的緊張。十位經過層層選拔、脫穎而出的青年才俊,身著嶄新的青色進士袍,按名次肅立。他們低垂著頭,目光緊盯著腳下光可鑒人的金磚,連呼吸都刻意放輕,生怕一絲聲響會驚擾御座上的天子,斷送大好前程。
龍椅上的皇帝已過知天命之年,眉宇間帶著難以掩飾的疲態,連日來的春闈瑣事和朝政紛擾顯然耗損了他的精神。然而,那雙略顯渾濁的眼睛此刻卻銳利如鷹,緩緩掃過殿下站立的年輕人,評估著帝國的未來棟梁。他的目光在排在首位的青年身上多停留了一瞬,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扶手上的白玉螭龍。
“沈墨。”
內侍尖細卻清晰的唱名聲打破了殿內的沉寂。
“學生在。”
清越如玉石相擊的聲音響起,不卑不亢。位列一甲的青袍青年應聲出列,躬身行禮。動作流暢而標準,帶著一種經年累月修煉出的優雅。即便低著頭,那挺直如松的背脊和從容不迫的氣度,也讓他在這群佼佼者中顯得格外不同。
“朕觀汝策論,”皇帝的聲音平穩,聽不出喜怒,卻在空曠的大殿中激起隱隱回音,“所言‘漕運之弊,在官不在民,在權不在法’,甚是新奇。詳細道來。”
“遵旨。”
沈墨微微抬首,臉上那副精致的銀絲面具在燭光下泛著冷冽的光澤,遮住了鼻梁以上的面容,只露出線條清晰的下頜、略顯蒼白的唇瓣和一雙沉靜如古井寒潭的眼。那目光清澈、穩定,沒有絲毫閃躲。
她并未急于表現圣前對策的純熟,而是稍作沉吟,仿佛在腦中再次梳理脈絡,方才開口,聲音清晰而平穩,每一個字都清晰地送入殿內每一個人的耳中:
“漕運之弊,積重難返,朝野俱知。然學生以為,究其根本,非運河運力不足,亦非河道年久失修、不暢所致,其核心在于——利益盤根錯節,各級官吏借漕糧征收、轉運、入庫之機,層層克扣,以權謀私,結黨營私,以致國帑流失,民怨沸騰……”
她侃侃而談,從漕糧征收的“淋尖踢斛”到運輸途中的“水火耗損”,從倉場看守的刻意刁難到戶部稽核的官官相護,剖析深入肌理,引用的數據、案例詳實得令人心驚。所提出的對策更是既犀利尖銳,又頗具可行性,并非空中樓閣。
殿內鴉雀無聲,落針可聞。唯有她清朗平穩的聲音在梁柱間回蕩。幾位須發皆白的老臣微微頷首,交換著眼神,目中流露出難以掩飾的贊賞。此子不僅文采斐然,竟對實務也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實屬難得。
殿柱投下的濃重陰影里,一架玄木輪椅無聲地停駐。輪椅上的人一襲玄色繡金蟒袍,身形隱在昏暗光線下,看不真切面容,只余一雙眼睛,深不見底,如同寒夜星空,此刻正精準地鎖在殿中那抹卓然而立的青色身影之上。
蕭玦的指尖有一下沒一下地輕輕敲擊著光滑的輪椅扶手,無聲地訴說著主人正在進行的思忖。
沈墨。寒門學子,籍貫江南,師從不詳。科考一路走來,縣試、鄉試、會試,直至殿試,文章篇篇錦繡,見解每每獨到,幾乎毫無瑕疵。策論、詩賦、經義,無一不精。太過完美,反而讓人……生疑。
尤其是那篇關于西北邊關軍屯改革的策論,其中幾點關于地形利用、戍卒輪換、糧草補給線的見解,角度刁鉆,思慮周詳,絕非尋常埋頭詩書的文人所能有,倒像是……親身經歷過戰陣烽火、深諳軍旅之事的人。
而且,從此人幾篇涉及朝政的文章來看,他似乎對京城各方勢力的微妙平衡,乃至一些官場深藏的隱秘都知之甚詳。這些消息,一個遠離權力中心的江南學子,從何得知?
蕭玦的目光掠過沈墨臉上那副遮住了上半張臉的銀絲面具。禮部報上來的說法是,幼時家中失火,面容遭火燎灼傷,故而畏見風,亦畏人目光。倒是個……很好的遮掩。
此時,沈墨的話語正到最關鍵處:“……故學生以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非良策。當設漕運督察使,直屬中樞,繞過地方藩籬,另辟相對獨立之新道,專司緊急軍糧及重要物資輸送,如此方可打破僵局,以點破面……”
“荒謬!”
一位隸屬三皇子派系的糧道老臣終于忍不住,出列沉聲駁斥,聲音洪亮,帶著久居上位的威嚴:“另辟新道?談何容易!開鑿河道,征發民夫,耗費幾何?工期幾許?此乃勞民傷財之舉!再者,中樞何來如許多精通漕務、又能即刻任事之人?此真乃書生之見,紙上談兵!”
突如其來的發難并未讓沈墨有絲毫慌亂。她只是微微側身,面向發難者,姿態依舊從容:“李尚書老成謀國,所言切中要害,學生受教。”
先肯定對方,緩和氣氛,隨即話鋒一轉:“然學生所言新道,并非全然耗費巨萬、興師動眾新開河道,乃是優先整合利用現有支流、廢棄堰埭,加以局部疏通修繕,如此可事半功倍。至于李尚書所憂人選之困……”
她話音刻意一頓,目光似無意般,極快地掃過殿柱陰影的方向,旋即收回,快得仿佛只是錯覺,聲音卻提高了些許,足以讓整個大殿聽清:
“學生聞聽,攝政王統領大理寺以來,雷厲風行,偵辦漕運積案數十起,積累卷宗浩繁,其間亦收押不少涉案之漕運官吏、賬房、乃至資深漕工。其中不乏多年浸淫此道、精通業務卻一時糊涂、行差踏錯者。若能量才選用,許其戴罪立功,豈非比培訓全然不知漕務為何物的新人,更快上手,更能解燃眉之急?”
此言一出,滿殿皆靜。
好一招“借力打力”、“釜底抽薪”!不僅輕巧化解了“勞民傷財”、“無人可用”的質疑,更四兩撥千斤,將難題和視線,隱隱引向了那一直沉默于陰影之中、卻無人敢忽視的——掌管大理寺的那位!
無數道目光,或明或暗,下意識地瞟向柱影處的輪椅。
御座上的皇帝,眼中閃過一絲極淡的笑意,他目光轉向那片陰影,聲音平穩無波:“攝政王以為如何?”輪椅緩緩自陰影中駛出,碾過光潔如鏡的金磚,發出幾不可聞的輕微聲響,卻仿佛碾在每個人的心頭上。
燭光終于照亮了來人的面容。
那是一張極其俊美卻過分蒼白的臉,仿佛久不見天日,棱角分明如冰雕雪鑄。眉飛入鬢,本應顯得英氣逼人,卻因眉宇間那化不開的陰郁與冷厲而帶上了幾分煞氣。薄唇緊抿,唇色極淡,唯有一雙眼睛,深不見底,此刻正如同盯住獵物的鷹隼,精準地落在殿中那抹青影之上。
蕭玦并未先回應皇帝的詢問,他的目光如有實質,沉甸甸地壓向沈墨。
沈墨只覺得一股無形的、冰冷徹骨的壓力驟然籠罩下來,周圍的空氣似乎都變得粘稠凝滯,幾乎讓人窒息。那目光銳利得仿佛能剝開她層層的官袍與偽裝,直刺內里。她強迫自己站穩,脊背挺得愈發筆直,藏在寬大袖袍中的手微微握緊,指尖抵住掌心,利用那一點微弱的刺痛感維持著絕對的清醒與鎮定,不避不閃地迎上那探究的視線。
四目相對,一坐一立,一玄一青,在莊嚴肅穆的金殿之上,無聲地對峙著。
片刻,蕭玦才開口,聲音低沉緩滯,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嘲諷,像是冰棱相互輕擦:“沈進士……”他頓了頓,似乎是在品味這個名字,“倒是頗為關心本王的差事。”
他操控輪椅,又向前移動了半分,拉近了距離,語氣依舊平淡,卻字字如淬了冰的刀鋒,直指核心:“大理寺卷宗浩如煙海,涉案人員錯綜復雜,其內情縱是朝中諸公亦未必全然知曉。沈進士遠在江南苦讀,兩耳不聞窗外事,對此等瑣碎繁雜之事,竟也能如數家珍,實在令人……驚訝。”
“驚訝”二字,他說得極輕,尾音微微拖長,其中的質疑與審視不言而喻——你一介書生,如何得知這些?消息來源何在?目的為何?
殿內氣氛瞬間繃緊到了極點。先前發難的李尚書嘴角幾不可察地露出一絲冷笑。所有人都聽出了攝政王話語中的機鋒。
沈墨心中凜然,知道這是最關鍵的考驗。她再次躬身,姿態放得更低,語氣卻依舊平穩,聽不出絲毫波瀾:“王爺謬贊,學生愧不敢當。學生乃一介布衣,寒窗十載,只知圣賢書,豈敢窺探大理寺機密重務。”
她略微抬首,目光誠懇地看向蕭玦,又迅速垂下,繼續道:“不過是此次進京赴試途中,于運河渡口,偶遇幾位正被押解入京的漕犯。聽其歇腳時抱怨路途艱辛,又談及往日于漕運之上‘風光’,言談間提及諸多關節名目、人員往來,學生一時好奇,便多聽了幾耳,心生感慨,方才于殿試策論中有所聯想。今日陛下垂詢,學生惶恐,據實以答,班門弄斧,讓王爺與諸位大人見笑了。”
理由依舊牽強,甚至有些刻意,將一切推脫于“偶然聽聞”,但卻巧妙地堵住了進一步追問細節的可能——難道攝政王要當著陛下的面,去追究幾個已落網漕犯在押解路上說了什么閑話嗎?
蕭玦盯著她,目光在她面具邊緣和纖細的脖頸上停留了一瞬,半晌,那過于蒼白的臉上,嘴角勾起一抹極淡、極冷的弧度,似笑非笑。
“原來如此。”他緩緩道,聲音里聽不出是信還是不信,“耳聰目明,心思縝密,觀察入微,更能學以致用。沈進士不僅才學過人,這份‘機緣’,更是難得。”
他終于轉向御座上的皇帝,微微頷首:“陛下,”聲音恢復了一貫的沉冷,“臣以為,此子……確是大才。”
“大才”二字,他咬得清晰而緩慢,回蕩在寂靜的大殿中。是由衷的贊賞,還是別有用意的標記?無人能從他毫無波瀾的語氣中分辨。
皇帝深邃的目光在蕭玦和沈墨之間流轉一瞬,沉吟片刻,終于緩緩點頭,一錘定音:“策論第一,見解非凡,臨辯不亂。沈墨,即日起,入翰林院,授修撰。”
“臣,謝主隆恩!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沈墨深深叩首下去,額頭觸及冰冷的地面。
塵埃,終于落定。
退出金殿時,春日的陽光撲面而來,有些刺眼。沈墨微微瞇了瞇眼,深吸了一口帶著暖意的空氣,強行壓下胸腔中翻涌激蕩的情緒。
成功了。第一步,也是最難的一步。她終于踏入了這座權力的核心殿堂。
然而,那股如芒在背的冰冷注視感,并未隨著她離開金殿而消失。她能清晰地感覺到,有一道目光,如影隨形,穿透厚重的殿門,落在她的背上。冰冷,銳利,探究,仿佛能穿透她的官袍,看破她層層偽裝下的真實。
蕭玦。
權傾朝野的攝政王,皇帝亦要讓其三分的人物。掌管大理寺,手握詔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京城里人人畏懼的“活閻王”,“九千歲”。
她未來路上,最大也最危險的……敵人。
或許,冥冥之中,也是這世上唯一能窺破她、理解她的……知己。
沈墨斂去眼中所有波瀾,將所有情緒深深壓入心底。她挺直脊背,一步步,穩穩地走下漢白玉階。陽光將她的影子拉得很長,官袍的袖口里,指尖悄然掐入掌心,留下幾個月牙形的淺痕。
棋局,已布下第一子。
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