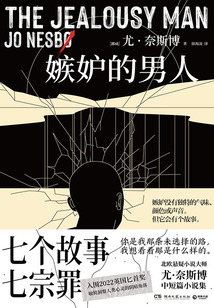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倫敦
我不怕坐飛機。對經常乘坐飛機出行的旅客來說,死于飛機墜毀的概率是一千一百萬分之一。換言之,你在同一架飛機的座椅上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的概率,比死于墜毀的概率還要高八倍。
等到飛機平飛后,我把身體靠向一邊,用我希望的那種讓人放心的低沉聲音,把這組數據告訴了窗邊那位低聲啜泣、全身發抖的女士。
“不過確實,在你害怕的時候,數據也幫不上什么忙,”我隨后補充道,“我說這個是因為我非常了解你的感受。”
你——到現在為止依然直直望向窗外——緩緩轉過身來看向我,就好像你此刻才意識到你身邊還坐了其他人。商務艙的特點就是座椅之間多了幾厘米的距離,它讓人只需稍稍集中注意力,就能相信自己是獨自一人。商務艙乘客也擁有一種共識,即不應打破這種幻想,彼此之間的交流應該被限定在簡單的寒暄和不得不討論的實際問題(“我能拉下遮光板嗎?”)之內。而且因為身前空間足夠大,去衛生間也不需要其他人起身相讓,加上儲物倉就在頭頂,一切都無需他人的協作,的確,就算是持續半天的飛行,你仍有可能完全忽略掉身邊的人。
從你臉上的表情不難看出,你對我打破商務艙的首要原則有些驚訝。你的著裝有種毫不費力的優雅——那條褲子和毛衣的顏色乍看并不協調,穿在你身上卻十分和諧。這一切都告訴我,距離你上一次不得已乘坐經濟艙(如果你真的坐過的話),已經過去很久了。但你在哭泣,難道不是你打破了那堵無形的墻嗎?另一方面,你哭泣的時候是背對著我的。顯然,你并不想和同你一起坐飛機的人分享這種情緒。
嗯,但如果不說些安慰的話,那也太冷漠了,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我面臨的困境。
你的臉色蒼白,臉上還掛著淚水,但仍有種靈動而出眾的美。或許正是那淚痕和蒼白的臉色才讓你顯得那么美麗?我向來對脆弱和敏感的事物毫無抵抗力。我將起飛前空姐墊在我們水杯下的紙巾遞給了你。
“謝謝。”你接過紙巾,說道。你勉強擠出一個微笑,將紙巾壓在一只眼睛旁淌下的睫毛膏上。“但我不相信。”你說著,轉過身去,將前額抵在機艙窗戶的有機玻璃上,仿佛想要把自己藏起來,啜泣再一次讓你的身體搖晃起來。你不相信什么?不相信我了解你的感受?隨便吧,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當然,從現在起,我就應該讓你獨處了。我打算看半部電影,然后睡會兒,盡管我估計自己睡著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小時。不管要飛多久,我都很少能在飛行中入睡,尤其是當我知道我需要睡眠的時候。我只會在倫敦待六個小時,接著就要回紐約去。
安全帶的指示燈熄滅,一位空乘人員走了過來,將我們之間那個寬大、牢靠的扶手上的空杯子重新加滿。起飛前,機長告知我們,今晚這趟從紐約到倫敦的航班將飛行五小時十分鐘。我們身邊有些人已經放下了椅背,用毯子裹住自己;其他人坐著,臉被前面的屏幕照亮,正在等待餐食送到。起飛前,當空姐送來菜單時,我和身旁這位女士都說了“不用,謝謝”。在“經典電影單元”,我很高興地找到了《火車怪客》,正準備戴上耳機開始看,我聽見了你的聲音:
“是我丈夫的事。”
仍抓著耳機的我轉過身去。
睫毛膏凝固在眼周,像是夸張的舞臺妝。“他出軌了,對象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識到仍將那人說成你最好的朋友很奇怪,但我看不出我有任何必要向你指出這一點。
“我很抱歉,”我轉而說,“我不是有意刺探……”
“不必道歉,有人關心是好事。很少有人真的這么關心他人,我們都害怕那些令人不安和悲傷的事情。”
“確實。”我說道,不確定應該把耳機放下,還是繼續拿在手里。
“我猜他們倆這會兒正躺在床上呢,”你接著往下說,“羅伯特總是很饑渴,梅利莎也是。這會兒他們一定正在我的絲綢床單上做愛。”
我的大腦立即想象出一對年過三十的夫妻。他負責賺錢養家,收入可觀,而你負責挑選床上用品。我們的大腦是形成刻板印象的專家。有時候,這些印象符合事實,有時候則不然。
“這一定很糟糕。”我希望自己的聲音聽上去不要太夸張。
“我只想死,”你說,“所以關于飛機的事你弄錯了。我倒希望它真的墜毀。”
“但我還有需要做的事情。”我露出憂心忡忡的神情。
這一刻你盯著我。也許這是個糟糕的笑話,或是開在了糟糕的時機,而且在此刻,說這些似乎太輕佻了。畢竟,你才說完你想死,甚至給了我一個可信的理由。這個笑話可能被認為不合時宜且毫無同理心,也可能給這個無可否認的凄涼時刻稍稍提供了喘息之機。喜劇性緩解,至少在它奏效的時候,人們都這么稱呼它。無論如何,我都后悔這么說了,并屏住了自己的呼吸。接著你笑了。盡管只是泥坑中的小小漣漪,稍縱即逝,但我總算能夠呼吸了。
“放輕松,”你平靜地說,“我是唯一會死的人。”
我疑惑地看向你,但你避開了我的視線,望向我身后的機艙。
“在第二排有個嬰兒,”你說,“商務艙的嬰兒可能會哭一整晚,你怎么想這事?”
“什么叫怎么想?”
“你可以說,嬰兒的父母應該理解,商務艙的乘客額外付費就是為了睡會兒。也許乘客們下了飛機就要去工作,或者第二天早晨就有會議。”
“嗯,也許吧。但只要航空公司不禁止嬰兒進入商務艙,那么你就不能指望父母不帶小孩進來。”
“那么航空公司就應該為欺騙我們而受到懲罰,”你小心地擦拭另一只眼睛下面,手里已不再是我遞給你的紙巾,而是你自己的舒潔面巾紙。“商務艙的廣告里都是乘客安然入睡的景象。”
“從長期來看,航空公司會承擔相應的后果。我們并不喜歡為沒得到的東西付錢。”
“但他們為什么這么做?”
“你是說父母還是航空公司?”
“我理解父母的行為,他們的錢比他們的羞恥感更多。但商務艙的服務這樣降級,航空公司將來肯定會損失收入吧?”
“但如果航司對小孩不友好,也會讓公眾不滿,公司的聲譽一樣會受損。”
“小孩才不在乎是在商務艙還是經濟艙里哭鬧呢。”
“你是對的。我指的是對嬰幼兒的父母不友好,”我笑了,“航空公司可能擔心那樣看起來像是種族隔離。當然,這個問題也好解決,航司可以立下規定,誰在商務艙哭泣,誰就得把座位讓給一位微笑著、好相處的經濟艙乘客。”
你的笑聲輕柔且迷人,這一次你的眼睛似乎也在笑著。很難不去想——我也這么想了——誰會對這么漂亮的女人不忠。但事情就是如此:無關外在美,也無關內在美。
“你從事什么工作?”你問道。
“我是個心理醫生,也做研究。”
“你研究什么?”
“人。”
“那是自然。有什么發現嗎?”
“弗洛伊德是對的。”
“哪一方面?”
“人,除了少數例外,都毫無價值。”
你笑了。“確實呀,這位……”
“叫我肖恩。”
“瑪麗亞。但你不是真的相信這個說法吧,肖恩?”
“除了少數人,其他人都沒價值。為什么我不該相信這個?”
“你有同情心,真正厭惡人類的人不會有同情心。”
“我明白了,所以為什么我要撒謊呢?”
“同樣的原因,因為你是個有同情心的人。你小心翼翼地討好我,說你和我一樣,也害怕坐飛機。當我說自己遭遇背叛時,你安慰我說這世界上到處都是壞人。”
“哇哦,我以為我才是心理醫生來著。”
“你看,甚至你的職業選擇也暴露了你。你還是承認吧,對你的主張來說,你自己就是最佳反例。你是有價值的人。”
“我真希望如此,瑪麗亞,但恐怕我表面的同情心不過是英式資產階級教養的結果,而且對我之外的人而言,我并沒有什么價值。”
你以幾乎不可察覺的幅度向我這邊靠近了一些。“那么是你的教育賦予了你價值,肖恩。但那又如何呢?是你做的事情,而不是你的思考或者感受,讓你有價值。”
“我想你夸張了。我的教育只是讓我遵從規則,做人們認為可以接受的行為,我并沒有做出任何真正的犧牲。我適應這些,并避免不愉快。”
“嗯,至少作為心理醫生,你是有價值的。”
“恐怕在職業道路上我也讓人失望。我不夠聰明,也不夠勤奮,從來沒有發現精神分裂癥的解藥。如果飛機此刻墜毀,這世界不過多損失一篇發表在科學刊物上的無聊文章,談論著一些業已存在的偏見,僅僅幾位心理學家會讀到。僅此而已。”
“你不好意思了嗎?”
“是的,這是我的另一種惡習。”
這會兒你笑得更燦爛了。“如果你消失了,連你的妻子和小孩都不會想念你嗎?”
“不會。”我回答得斬釘截鐵。因為我坐在過道一側,所以無法通過轉向窗戶,假裝在午夜時刻的大西洋上看見了什么有趣的東西來結束這場對話。而選擇抽出身前座椅袋子里的雜志,又顯得過于刻意了。
“對不起。”你小聲說。
“沒事,”我說,“你說你將會死,是什么意思?”
我們的眼神相觸,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彼此。盡管這可能是后見之明,但我想我們都在這一瞥之內抓到了什么,它甚至在這時就告訴我們,這是一場可能會改變一切的相遇。事實上,它已經改變了一切。也許你也是這么想的,但很快你就分心了。當你越過扶手向我靠過來時,你發現我繃緊了身體。
你身上香水的味道讓我想起了她。這是她的味道,她回來了。你靠回自己的座椅,看著我。
“我準備自殺。”你低語道。
你又往回坐了坐,端詳著我。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樣的表情,但我知道你沒有說謊。
“你打算怎么做?”這是我唯一想到的問題。
“要我告訴你嗎?”你帶著一種猜不透的,大抵是被逗樂的笑容問我。
我想了一下。我想知道嗎?
“不過這樣說并不準確,”你說,“首先,我不是準備自殺,我已經做到了。其次,不是我殺了我自己,而是他們。”
“他們?”
“是的,我簽了協議……”你看了眼手表,是卡地亞的。我猜這是羅伯特送你的禮物。是在他不忠之前還是之后送的?之后,梅利莎不是他第一個情人,從一開始他就在出軌。“……就在四個小時前。”
“他們?”我重復問道。
“自殺機構。”
“你是說……像在瑞士那樣?協助自殺?”
“是的,不過協助的部分更多。區別在于,他們會殺死你,而且讓你看起來不像是自殺。”
“真的嗎?”
“你看起來并不相信我。”
“我……我相信。我只是很意外。”
“我理解。這件事只能我們兩個知道,協議里頭有保密的條款,實際上我是不能跟任何人提起這個的,但我就是……”你笑了,眼眶里有淚珠在打轉,“……感到孤獨。你是個陌生人。一個心理醫生。你承諾會保密吧?”
我咳了一聲,說:“面對患者的時候,是這樣的。”
“那么,我就是你的患者。我看得出來,你此刻沒有預約的病人。醫生,你收費如何?”
“恐怕我們不能這樣做,瑪麗亞。”
“當然了,這有違你們職業的原則。但你可以就以個人身份聽一聽吧?”
“你必須理解,對心理醫生來說,這是倫理問題。如果有人向我表達自殺的傾向,我是不能袖手旁觀的。”
“你不懂,現在做什么都遲了,我已經死了。”
“死了?”
“這個協議不允許反悔,三周內我就會被殺死。他們一開始就告訴我,一旦簽署了協議,就沒有撤回的按鍵,否則,事后可能會產生各式各樣的法律糾紛。你現在坐在一具尸體旁邊,肖恩,”她笑了,但笑聲刺耳、苦澀。“你現在可以和我喝一杯,聽我說一會兒嗎?”你抬起修長、纖細的手臂,按下服務燈按鈕,它的鈴聲穿過黑暗的客艙。
“很公平,”我說,“但我不會給你任何建議。”
“好的,你能保證之后都不要提起這件事嗎?甚至在我死后。”
“我保證,”我說,“盡管我看不出這對你來說有什么區別。”
“噢,有區別的。如果我違反了保密條款,他們就可以起訴我,要求我賠償一大筆錢,這樣我的錢就無法留給我資助的那個機構了。”
“有什么我可以為您效勞的?”無聲出現在我們之間的空姐問道。你側身越過我,為我們點了金湯力。你的套頭衫向下滑了少許,我看見你裸露的蒼白皮膚,意識到你身上沒有她的氣味。你聞上去有淡淡的甜味和芳香,像是汽油。對,汽油。還有一種我想不起名字的樹的味道。你聞上去幾乎像是個男人。
空姐摁滅服務燈,離開了。隨后,你踢掉鞋子,伸出一對被絲襪包裹著的苗條腳踝,讓我想起了芭蕾舞。
“自殺機構開在曼哈頓的辦公室讓人印象深刻,”你說道,“那是一間律所,他們宣稱這一切都是合法且公開的,我并不懷疑這點。舉例來說,他們不會殺死有精神障礙的人。在簽署協議前,你必須完成全面的精神疾病檢查。你還需要撤銷一切保單,這樣他們就不會被保險公司起訴。剩下還有很多條款,但最重要的是保密這部分。在美國,兩個成年人自愿達成的協議中的權利可以比其他國家更進一步,但如果他們的行為被人知道,尤其是被公眾知曉,機構擔心,人們的反應會讓那些政治家制止他們。他們并不給自己的服務打廣告,只服務于那些經過口口相傳,才得以知曉他們存在的有錢人。”
“也是,我能明白為什么他們要保持低調。”
“他們的客戶也需要守口如瓶;自殺有點像墮胎,總會讓人感到羞愧。負責墮胎的診所并不是非法經營的,但他們也不會在大門口大張旗鼓地宣傳自己的業務。”
“確實如此。”
“當然了,守口如瓶和羞恥感是整個商業概念的基礎。他們的客戶花大價錢,就是為了在身心都很愉悅,且沒有任何預期的時候,告別人世。但最重要的是,讓這場自殺在他們的家人、朋友乃至全世界面前都不會被懷疑為自殺。”
“他們是怎么做到的?”
“當然,沒人會告訴我們。我們只知道有很多種辦法,而且這場死亡一定會發生在協議簽署后的三周內。我們也不知道之前的案例是怎么做的,這樣我們就不會在有意或無意的情況下,避開一些特定的場景,從而產生不必要的恐懼。我們唯一被告知的是,死亡不會有任何痛苦,我們也不會知道它何時到來。”
“我能理解對有些人而言,隱瞞自殺的真相很重要。但你是為了什么?這不正是一種復仇的方式嗎?”
“你是說對羅伯特和梅利莎復仇?”
“如果你明顯是自殺,那就不僅僅與羞恥感相關了。羅伯特和梅利莎會責怪自己,還會不自覺地責怪對方。這是我們時常見到的情況。舉個例子,你有沒有關注過有孩子自殺的家庭中父母的離婚率?或是父母自己隨孩子自殺的概率?”
你只是靜靜看著我。
“我很抱歉,”我感到自己臉變紅了,“我把復仇的欲望強加給你了,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在你的處境中,會想做這樣的事。”
“肖恩,你認為你讓自己難堪了。”
“是的。”
你猛地笑了一聲。“你也沒說錯,因為我的確想要復仇。但你不了解羅伯特和梅利莎。如果我自殺了,留下控訴羅伯特不忠的遺書,他只會否認一切。他會說我是抑郁而亡,此前也因此接受過治療,當然,這是真的,而且到生命的最后,是我變得疑神疑鬼了。他們倆行事隱秘,也許其他人根本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奸情。我猜我葬禮過后的六個月中,她明面上會和羅伯特的金融圈子里的其他人約會。他們都為她癡狂,但梅利莎總能脫身離開,只調情,不上床。六個月后,她和羅伯特就會宣布他們都因為我的死而悲傷,因而走到了一起。”
“嗯,你可能比我更痛恨人類。”
“我不懷疑這一點。更令人作嘔的是,在羅伯特的內心深處,他可能會感到驕傲。”
“驕傲?”
“一個女人如果不能完全擁有他就活不下去,他會這么看待整件事。梅利莎也會這么看。我的自殺會讓他覺得自己更有分量,到頭來也會讓他們更開心。”
“你相信會是這樣?”
“當然。你難道不熟悉勒內·基拉爾的摹仿欲望理論嗎?”
“不清楚。”
“基拉爾的理論是,在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我們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們會模仿周圍的人,我們珍惜他們珍惜的東西。如果你身邊認為米克·賈格爾性感的人足夠多,你也會希望得到他,哪怕一開始你認為他長得很惡心。如果羅伯特的分量因我的自殺而變重,梅利莎就會更想得到他,他們在一起時也就會更快樂。”
“我明白了。如果你看上去像是死于意外或者其他形式的自然死亡呢?”
“效果截然不同。我就是被命運或霉運帶走的人。羅伯特看待我和我的死的方式也不同。雖然緩慢,但我最終會有神圣的光環。當有一天梅利莎惹羅伯特不開心時——她當然會這樣——他就會想起我的好,想起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兩天前,我給他寫了封信,告訴他我將離開他去尋找自由。”
“這意味著在羅伯特看來,你并不知道他們的事情?”
“我看過羅伯特手機里他們所有的短信,但在和你說之前,我從沒跟任何人提起過。”
“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一開始,羅伯特肯定會如釋重負,因為他不必做那個離開的人了。不必因為離婚付出一大筆錢。而且哪怕他很快就和梅利莎搞在一起了,他的形象也不會受損。但不久后,信里埋下的種子就會發芽。我讓他自由,但那是因為我堅信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人。在我離開前,可能就已經存在這樣一個人了。一個渴望著我的人。而只要羅伯特這么想……”
“……你就是那個被摹仿欲望所渴求的人了。這就是你去找自殺機構的原因。”
你聳了聳肩。“所以孩子自殺,父母的離婚率是多少?”
“什么?”
“是父親還是母親會選擇自殺?我猜是母親。”
“嗯,你說呢?”我說著,把視線投向前方座椅的靠背。但我能感覺到你投向我的目光,你想要更具體的答案。
這時,兩杯酒變魔術般地從黑暗中出現,落在我們中間的扶手上,拯救了我。
我咳嗽起來。“你每天早晨醒來都會想,今天是不是我被殺死的日子。等待的時間這么長,是不是很難忍受?”
你猶豫了。你不想這么輕易地放過我。但最后你還是放手了,回答道:“如果那個念頭是‘今天也許我不會被殺’,感覺更糟。即使我們有時會自然而然地被對死亡的恐懼壓倒,產生我們從未要求過的求生本能,對死亡的恐懼也并不比對活著的恐懼更強烈。這是你這樣的心理醫生很熟悉的事情。”你微微加重了“心理醫生”這個詞。
“的確如此,”我說,“有人曾經做過有關巴拉圭的游牧部落的研究,在那里,部落會議可以決定人的生死。當他們認為一個人太老、太虛弱,只是部落的負擔時,他們會殺死他。當事人不知道他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被殺,但他能接受整件事情。畢竟,這個部落需要在缺乏食物的環境中進行漫長、艱苦的游牧。他們之所以能生存下來,正是靠著犧牲弱者,從而確保整個部落的健康。也許在年輕的時候,那個被判死刑的人也不得不在某個黑夜在小屋外揮舞棍棒,打碎某個虛弱的老姑婆的頭。然而,研究表明,這種不確定性對部落成員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這可能也是整個部落預期壽命很短的原因之一。”
“壓力當然存在,”你說道,打了個哈欠,穿著絲襪的腳觸碰到了我的膝蓋。“我也希望等待時間不要有三周這么長,但我猜他們要找到最好、最安全的方式,就需要這么久。比如說,死亡既要看上去像是意外,又要無痛,那么可能需要非常精心的策劃。”
“如果飛機現在墜毀,你的錢能拿回來嗎?”我啜飲了一口金湯力,問道。
“不會。他們說,因為他們在每位顧客身上都花了很多錢,而這些顧客本身又有自殺傾向,所以他們必須確保,顧客在有意或是無意對自己動手前,有在好好活著。”
“嗯,所以,你最多還有二十一天可活。”
“很快就是二十天半了。”
“那你想要怎么度過呢?”
“做我之前沒做過的事。和陌生人聊天、喝酒。”
你一口飲盡了杯中酒。我的心開始劇烈跳動,仿佛預知到隨后會發生什么。你放下杯子,將手覆在我的手臂上:“我想和你做愛。”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
“我現在去洗手間,”你說,“如果你在兩分鐘內跟上,我還會在里頭。”
事情正在發生。不只是欲望,那種內在的喜悅感染了我的整個身體,一種許久未有的重生之感,老實說,我估計這種感覺以后也不會再有。你將手掌按在扶手上,準備離開座椅,但沒有站起來。
“我想我沒有那么堅強,”你嘆氣道,“我需要知道你會不會來。”
我又喝了口酒,緩了緩。她看向我的杯子,等待著。
“如果我已經有對象了呢?”我說道,自己都能聽出聲音的嘶啞。
“但你沒有。”
“如果我覺得你沒有吸引力呢?如果我是同性戀呢?”
“你害怕了嗎?”
“是的,主動提出性需求的女人讓我害怕。”
你端詳著我的臉,似乎在找什么。“好吧,”你說,“我信了。不好意思,這不是我一貫的風格。但我沒時間猶豫了。我們接下來該怎么做?”
我感到自己漸漸平靜了下來。我的心仍跳得很快,但恐慌和想要逃開的本能都已消失不見。我轉著手上的杯子,說:“你到倫敦后,還要接著飛嗎?”
你點點頭:“我還要飛去雷克雅未克。在我們降落后一小時,那趟航班就會起飛。你在想什么?”
“在倫敦找家酒店。”
“哪一家?”
“蘭登。”
“蘭登很好。你在那里逗留超過二十四小時,職員們就會知道你是誰。除非他們懷疑你是來偷情的,否則他們好像記不住任何事情。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不會在那里待超過二十四小時。”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重新訂明天飛雷克雅未克的航班。”
“你確定?”
“是的,這回你滿意了?”
我想了想,并不開心。“但如果……”我開口,又停下了。
“你是不是擔心他們可能會在我們相處的時候動手?”你問道,開心地與我碰了碰杯,“害怕醒來時發現身邊躺著一具尸體?”
“不,”我笑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相愛了怎么辦?你已經簽署想要死去的協議,還是不可撤回的。”
“太晚了。”你說著,把你的手放在扶手上,覆在我的手臂上。
“是呀,這正是我想說的。”
“不,我是說其他事情已經太晚了。我們已經愛上了彼此。”
“有嗎?”
“就一點點,但已經足夠了。”你捏了捏我的手,站起身,說你一會兒回來。“足夠我為還擁有三周時間感到開心。”
在你去廁所的時候,空姐過來取走我們的杯子,我向她多要了兩個枕頭。
你回來時,臉上帶著新的妝。
“這不是為你化的,”你說,明顯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更喜歡我之前臟兮兮的樣子,不是嗎?”
“我都喜歡,”我說,“那你是為誰化的妝呢?”
“你覺得是為誰?”
“為他們?”我問道,向機艙方向點點頭。
你搖了搖頭。“我最近完成了一項調查,大多數受訪女性都說,她們化妝就是為了讓自己感覺好。但她們所說的‘好’是什么意思呢?僅僅是‘不會感到不適’嗎?那種對自己真實容貌的不適?難道化妝只是我們給自己加的另一件罩袍?”
“化妝不是用于隱藏和強調的嗎?”我問道。
“強調,就是對其他事物的隱藏。所有的編輯——在闡明的同時——也涉及掩蓋。一個化了妝的女人希望吸引人們關注她可愛的眼睛,這樣就不會有人留意到她的鼻子太大了。”
“但這是罩袍嗎?我們不都想被看見嗎?”
“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沒人希望暴露出自己真實的樣子。順便提一句,你知道在韓國和以色列等國家,一位女性一生中花在化妝上的時間和男人服兵役的時間一樣多嗎?”
“不知道,但這聽起來似乎是隨手拿了兩個數據進行比較。”
“聽上去是如此,但這個比較并不是隨機的。”
“哦,不是嗎?”
“這個比較,一方面以我自己為例子,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可靠的觀測。假新聞并不一定意味著假事實,可能只是經過了刻意編輯。這個比較會讓你怎么看待我在性別上的態度呢?我是不是在說,男人們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為國效力的時候,女人卻選擇讓自己變美?也許是這樣。但說法只需稍稍變化,這個比較便可以表示,女人害怕真實的自己被看見,就像一個國家害怕被敵人擊潰一樣。”
“你是記者嗎?”我問道。
“我給不值得被印出來的雜志做編輯。”
“女性雜志?”
“是的,還是最糟糕的那種。你有什么行李嗎?”
我猶豫了一下。
“我是在問,我們落地之后,可以直接打車離開嗎?”
“我只有手提行李,”我說,“你還是沒有告訴我,你為什么重新化妝。”
她抬起手臂,用食指輕撫我的臉頰,撫摸著眼睛正下方的皮膚,就好像剛才我也哭過一樣。
“我再跟你說一個有關隨機事實的比較,”她說道,“每年死于自殺的人要多于戰爭、恐怖主義、激情犯罪,以及其他類型謀殺的受害者的總和。毋庸置疑,你是最有可能殺掉你自己的人。這就是我重新化妝的原因。我看向鏡子里那個準備殺死我的人,受不了她那張裸露的臉。我化妝,并不是因為現在我戀愛了。”
我們看向彼此。在我準備握住她的手時,她先牽起了我的手。我們的手指交錯在一起。
“我們對此無能為力了嗎?”我低語道,突然感到奔跑時的那種呼吸困難,“我們不能買斷你這份協議嗎?”
她歪過頭,像是想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我。“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我們說不定就不會墜入愛河了,”她說,“我們不能長久在一起的事實,是彼此吸引的重要原因,你不也是這么想的嗎?她也死了嗎?”
“什么?”
“那個人。那個當我問起你妻子和小孩的時候,你不愿提起的人。也是那個當我問你有沒有行李的時候,你猶豫的理由。失去她,讓你害怕再愛上一個你注定會失去的人。你想談談這件事嗎?”
我看著你。我想談嗎?
“你確定你想……”
“是的,我想聽。”你說。
“你給這個故事多長時間?”
“哈哈。”
我們又點了一輪酒。我開始講我的故事。
當我結束的時候,窗外的天已經漸漸亮了,飛機向著太陽、向著新的一天飛去。
你的眼眶再次濕潤了。“這太讓人難過了。”你說,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
“是啊。”我說。
“你回想起來還是會心痛嗎?”
“已經不是每次都會。我告訴自己,既然她不想再活下去,那么這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你真的這么覺得嗎?”
“你不是也這么想嗎?”
“也許吧,”你說道,“但我并不確定。我像是哈姆雷特,一個猶豫不決的人。也許死亡的國度會比塵世更糟。”
“和我說說你自己吧。”
“你想知道什么?”
“一切。開始吧,如果有什么我想知道得更詳細的地方,我會問你的。”
“好的。”
你講起了你的故事。那個女孩的形象逐漸清晰,甚至比此刻手放在我手邊,側身靠向我的人更清晰。有一會兒,飛機飛進湍流區,那感覺像是連續跨過一連串小而陡峭的浪。湍流給你的聲音加上了一種動畫片般的顫音,我們都笑了起來。
“我們可以逃走。”等你說完你的故事,我說道。
你看向我:“怎么做?”
“你先在蘭登訂一間房。今天晚上,你到前臺給酒店經理留一張字條,告訴他你準備去泰晤士河投河自盡。晚上你就到那邊去,找個沒人能看見的角落,把鞋子脫下來,留在堤岸上。然后我租輛車來接你。我們開去法國,從巴黎搭飛機去開普敦。”
“那護照呢?”你問道。
“這個我可以安排好。”
“你可以嗎?”你繼續盯著我,“你究竟是哪門子的心理醫生?”
“我不是心理醫生。”
“你不是?”
“對。”
“那你是什么?”
“你覺得呢?”
“你是那個要殺我的男人。”你說。
“對。”
“你在我去紐約簽合同之前就訂好了我旁邊的這個座位。”
“對。”
“你真的愛上我了?”
“對。”
你緩慢地點點頭,緊緊抓住我的手臂,好像害怕自己摔下去似的。
“你本來打算怎么做?”
“在排隊過海關的時候,用一根針。毒藥的活性成分會在一小時內完全消失,或溶入血液中。尸檢報告只會顯示你死于尋常的心臟病發作。在你的家族中,這是最常見的死因,我們做的相關檢測也表明你有心臟病突發猝死的風險。”
你點點頭。“如果我們逃了,他們會不會連你一起追殺?”
“是的,這涉及很多錢,以及多方勢力,包括我們這些執行任務的人。他們也要求我們簽署一份合同,期限也是三周。”
“一份自殺合同?”
“合同允許他們在沒有法律風險的情況下殺死我們。如果我們不忠于自己的任務,這個條款就會生效。”
“他們不會在開普敦找到我們嗎?”
“他們可是追蹤專家,他們會發現我們的蹤跡,然后被引到開普敦。但我們不會在那里。”
“那我們會在哪兒?”
“我能遲一些再告訴你嗎?我保證那是個好地方。有陽光,有雨水,不太冷,也不太熱。大部分居民都懂英語。”
“你為什么要這么做?”
“和你的理由一樣。”
“但你不想自殺。完成工作可能會讓你掙一大筆錢,但你現在這樣做,是在拿你自己的生活冒險呀。”
我嘗試微笑,說:“什么生活?”
你環顧四周,靠過來,吻我的唇。“如果你不享受我們的性生活怎么辦?”
“那我就把你沉進泰晤士河。”我說。
你笑了起來,再次吻我。時間比上次稍長,嘴也張得更大。
“你會享受的。”你在我耳邊低語。
“是的,恐怕會的。”我說。
你在此刻睡去,頭枕著我的肩膀。我把你的座椅向后調,給你蓋好了毯子。接著我調整好自己的座椅,關掉頭頂的燈,嘗試入睡。
當我們到倫敦時,我將你的座椅調直,幫你系好了安全帶。你看起來像是一個在平安夜睡著的孩子,嘴角還掛著淺淺的微笑。空姐走了過來,收走了從肯尼迪國際機場起飛時就在我們共用扶手上的水杯,那時你在啜泣,而我們仍彼此陌生。
站在6號窗口的海關官員面前時,我看見有人推著擔架跑進門內,他們穿著顯眼的馬甲,上面印有紅色十字圖案。我看了眼自己的表。在我們從肯尼迪機場起飛前,放進你杯子里的粉末生效很慢,但很可靠。你已死去快兩小時了,尸檢報告表明是心臟病發作,其他什么也沒有。與之前每次完成任務后一樣,我想哭。同時我感到快樂。這是有意義的工作。我不會忘記你的,你是那么特別。
“請看攝像頭。”海關官員對我說。
我得先把眼淚眨下去才行。
“歡迎來到倫敦。”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