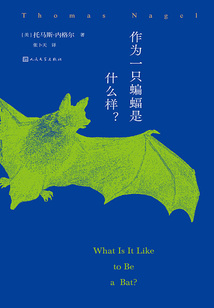
作為一只蝙蝠是什么樣?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50年前,《作為一只蝙蝠是什么樣?》發表在《哲學評論》(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74年10月)上。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表明,意識的不可還原的主觀性是心身問題的諸多解決方案的障礙。自那以后,意識逐漸成為哲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討論的一個核心話題,其獨特性所引出的特殊問題也受到了廣泛關注。關于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目前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一些人認為,可將意識納入一種唯物論的世界觀;而包括我在內的另一些人則認為,意識的實在性意味著物理科學對自然秩序的描述是不完整的;還有一些人認為,如果我們日常的意識概念與唯物論不相容,那么就不得不拋棄或修改它。
也許是因為通過一個特別生動的例子提出了這個問題,這篇文章已經成為許多這類爭論及由此產生的理論的標準參考文獻。20世紀70年代初,我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有一所房子,蝙蝠在其木建部分筑巢。黃昏時分,它們會出來覓食,但偶爾會有一只迷路,最終進入房子,給我一種與陌生生物親密接觸的驚恐體驗。我想蝙蝠也有同樣的感覺。
對蝙蝠的思考成為我持續反思心身問題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提供一種新的方式來引出問題。通過指出某種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關于蝙蝠經驗的東西——即對于蝙蝠來說是什么樣——即使我們可以確信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是真實的,我也希望人們認識到,蝙蝠的心靈并不只是我們通過觀察原則可以獲得的那種生理描述或行為描述所能把握的東西。通過解釋為什么我們無法理解蝙蝠經驗這一特征,我希望明確說明其關鍵的、本質上主觀的特征。[1]
這篇文章被認為有助于對心身問題的討論,而關于蝙蝠的觀點只是主要結論(即意識的主觀性阻礙了將心理還原為身體)論證過程中的一個輔助步驟。但蝙蝠開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并成為同一時期逐漸顯著的另一個討論領域——動物意識——的標準參考物。碰巧的是,我可能以另一種方式幫助這個話題在科學上受到了尊重。1973年至1974年,我訪問了洛克菲勒大學,其中一位杰出人物是發現蝙蝠回聲定位的動物學家唐納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他欣然同意與我會面,我們不僅討論了蝙蝠,而且討論了一般的動物意識,還討論了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不愿談論這一點,甚至連承認這一點都不情不愿。他開始相信這是一個重要且被忽視的主題,于是寫了《動物意識問題》(The Question of Animal Awareness)一書[2],對人們認真對待這一主題產生了重要影響。如今,該領域已經發展到不僅對哺乳動物和鳥類,而且對魚類、軟體動物和昆蟲的意識和認知進行廣泛研究的程度。
我的文章有時會遭到誤解,人們認為它是在聲稱,由于意識的主觀性超出了客觀物理科學的范圍,所以完全超出了科學理解的范圍。恰恰相反,我認為它表明,不應把科學理解局限于那種基于共同觀察的客觀外部實在理論,這是物理科學的典型特征。意識的實在性要求擴展我們的科學思想,以容納不符合物理客觀性概念的東西。
我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這一點,并且建議了一種客觀現象學,但在文章發表后的若干年里,我繼續思考心身問題,試圖設想如果認真對待意識的主觀性,那么正面的解決方案會是什么樣子。對于那些可能感興趣的讀者,我在本書中加入了一篇這樣的論述作為第二篇文章,它是我在意識科學研究協會2023年年會上的講演。這一想法在一篇更長的文章《心理物理關聯》(The Psychophysical Nexus)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闡述,該文可見于我的《隱藏與暴露及其他論文》(Concealment and Exposure and Other Essays,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3]一書。雖然必定是試探性和極具思辨性的,但它表達了一種我仍然認為有希望的立場。
《蝙蝠》一文的歷久彌新和持續的突出地位促使我將它放在這本小書中重新出版。它所引出的問題仍然存在。
注釋
[1]兩項致謝:1971年,蒂莫西·斯普里格(Timothy Sprigge)在其論文《目的因》("Final Cause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suppl.vol.45)中提出,作為意識的基本條件,必定存在作為相關生物“是什么樣的感覺”。法雷爾(B.A.Farrell)則在他的論文《經驗》("Experience",Mind,1950)中提出了“作為一只蝙蝠是什么樣?”這個問題,盡管他沒有理會唯物論的困難。當我寫那篇論文的時候,我沒有讀過斯普里格的文章,也忘記了法雷爾的文章。
[2]Rockefeller University Press,1976.
[3]它最早發表于Paul Boghossian and Christopher Peacocke,eds.,New Essays on the A Prior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