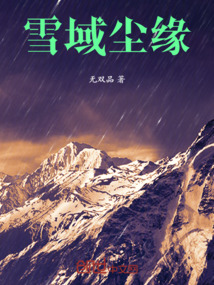
雪域塵緣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1-8章
★雪域塵緣★
弧桑
???????????
★第一章避亂桃源
???????????
光緒三十二年,我(沈玉鍪)從湖南武備學(xué)堂畢業(yè)。
這所學(xué)堂由時任湖南巡撫的陳右銘一手創(chuàng)辦,校址位于長沙城小吳門外,是當(dāng)時湖南培養(yǎng)新式軍事人才的重鎮(zhèn)。
學(xué)堂的學(xué)生由各州縣選送,年齡在十八至二十歲之間,不僅要身體健壯、文理清暢,還要求家世清白、品行端正,經(jīng)層層考試合格后方能入學(xué),學(xué)制為三年。
課程設(shè)置兼顧中西,涵蓋漢文、日文、算學(xué)、倫理學(xué)等基礎(chǔ)學(xué)科,以及軍制學(xué)、戰(zhàn)術(shù)學(xué)、城壘學(xué)、地形學(xué)等軍事專業(yè)知識,力求培養(yǎng)文武兼?zhèn)涞男率杰姽佟?
學(xué)堂實(shí)行獨(dú)特的分段教學(xué)制,學(xué)生先在學(xué)堂系統(tǒng)學(xué)習(xí)一年理論,隨后派赴部隊(duì)實(shí)習(xí)半年,在實(shí)戰(zhàn)中鍛煉技能,這種理論與實(shí)踐結(jié)合的方式,讓學(xué)生能更快適應(yīng)軍隊(duì)的節(jié)奏。
當(dāng)時朝廷正著力大規(guī)模改造舊軍、編練新軍,急需各類軍事人才。
為此,湖南武備學(xué)堂又在長沙陸續(xù)附設(shè)了將弁、兵目、陸軍速成三個學(xué)堂。
其中,將弁學(xué)堂專門從軍營中挑選年富力強(qiáng)的軍官,培訓(xùn)一年后派往舊軍擔(dān)任改造骨干。
兵目學(xué)堂則從各營選拔目兵,經(jīng)一年培訓(xùn)后作為新軍的基層力量。
陸軍速成學(xué)堂則挑選目兵進(jìn)行一年半的強(qiáng)化訓(xùn)練,為新軍輸送初級軍官。這幾所學(xué)堂合力為湖南新軍培養(yǎng)了一大批可用之才。
我畢業(yè)后被任命為湖南新軍第七十九標(biāo)隊(duì)官。
當(dāng)時新軍隊(duì)伍里,多數(shù)士兵愚昧無知,將校也大多是行伍出身,唯獨(dú)我所在的隊(duì)伍,士兵是新近從家鄉(xiāng)招募的青年學(xué)子,其中不乏秀才、廩生,素質(zhì)遠(yuǎn)勝其他部隊(duì)。
其時清廷政局混亂,內(nèi)憂外患不斷,我看在眼里,心中也曾對革命心生向往,我部的青年士兵大半都秘密加入了革命組織。
次年,同學(xué)林浴凡專程約我從老家湖南鳳凰縣城動身前往湖北,拜見湖北總督趙公讓。
趙公讓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向來以開明著稱,他早年擔(dān)任湖南巡撫時,大力推行興學(xué)練兵,我們這些青年學(xué)子都深受其革新思想的影響。
趙公讓的親弟趙季和,科舉之路不順,只得通過納捐進(jìn)入仕途,因才干得到山西巡撫錫某的賞識。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錫某調(diào)任四川總督,趙季和隨他入川,之后相繼擔(dān)任永寧道臺、建昌道臺。
期間,他奉命招募兵勇,平定了地方土司的叛亂,從此與川邊事務(wù)結(jié)下不解之緣。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朝廷任命趙公讓為四川總督,趙季和則出任四川邊務(wù)大臣,他在打箭爐駐軍,并將“打箭爐”改名為“康定府”。
內(nèi)務(wù)府正白旗人連豫也正在川邊推行過大規(guī)模改革。
我雖已決意隨軍西征,但家中的境況卻讓我百般牽掛,侄兒正患重病,妻子年紀(jì)尚輕,一家人寓居他鄉(xiāng),本就凄涼孤獨(dú)、形影相吊,聽說我要西行出塞,更是痛哭不止,拉著我的衣襟苦苦挽留。
此情此景,讓我不免有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之感。
可轉(zhuǎn)念一想,協(xié)統(tǒng)鐘新待我向來真誠,再者革命潮流勢不可擋,內(nèi)地早晚難免動蕩,將來這茫茫神州,又何處是安身立命的樂土?
況且我在軍中本無貳心,四川當(dāng)局卻仍懷疑我是革命黨人,而且長年客居他鄉(xiāng),終究不是長久之計(jì)。
青海地處偏僻,風(fēng)俗淳樸,或許能借這次從軍的機(jī)會,效仿秦人避亂桃源,也算是明哲保身的辦法。
于是我強(qiáng)打精神,千方百計(jì)安慰家眷,忍痛拋下家事,揮淚告別。
我清楚記得出發(fā)那天是宣統(tǒng)元年秋七月十六日。
恰逢鐘新奉旨援川,我不免技癢,呈上自己撰寫的《西征計(jì)劃書》,對進(jìn)軍路線的規(guī)劃頗為詳盡。
鐘新看后大加贊賞,當(dāng)即召我返回成都,委任我為一標(biāo)三營督隊(duì)官。
可我妻子當(dāng)時寓居長沙,若留下則無依無靠,想返鄉(xiāng)又缺乏路費(fèi),更無人可以托付,因此極力推辭。
后來管帶林浴凡反復(fù)勸說,鐘新又特意饋贈禮金,并承諾從優(yōu)發(fā)放月薪,盛情難卻,我才最終決定啟行。
鐘新是正黃旗人,他父親迎娶了同治皇帝的親妹,官至盛京副都統(tǒng),后來因?yàn)楦胶土x和團(tuán)得罪朝廷,流放至川邊軍營。
他走到成都,假托生病,經(jīng)川督錫良奏請,留下養(yǎng)病,其實(shí)是慈禧太后的密旨。
鐘新是同治皇帝的表兄弟,自然得到西太后的寵愛。
同治帝上頒布密詔,命鐘新借協(xié)統(tǒng)軍銜訓(xùn)練新軍,當(dāng)時鐘鼓明僅十八歲。
新軍訓(xùn)練完成后,鐘新?lián)螀f(xié)統(tǒng),率領(lǐng)新軍進(jìn)入川西,當(dāng)時是宣統(tǒng)元年。
鐘新麾下有三名標(biāo)統(tǒng),陳慶是其中之一,而林浴凡當(dāng)時隸屬于陳慶標(biāo)下,擔(dān)任第三營管帶一職。
后來,我與林浴凡一同隨軍入川,一路輾轉(zhuǎn)抵達(dá)昌都。
林浴凡在昌都遭到趙季和解職,隨后便返回了內(nèi)地。
回到內(nèi)地后,他與石清陽等人積極為革命事業(yè)奔走效力,在廣東一帶頗有聲望。
???????????
★第二章★援軍出塞
???????????
我最初在林浴凡所在的營中擔(dān)任督隊(duì)官,他離職后,接替他出任了管帶。
后來回到內(nèi)地,林浴凡身處廣東,我則駐守湘西,兩人自此便斷了聯(lián)絡(luò),再無往來。
當(dāng)時,趙季和、連豫等人打算在川邊推行改土歸流政策,觸動了當(dāng)?shù)嘏f貴族的利益,引發(fā)了他們的強(qiáng)烈不滿,導(dǎo)致騷亂爆發(fā)。
慈禧太后接到連豫的求援后,下令四川總督派遣混成一協(xié)的兵力前往支援。
我那時正擔(dān)任陸軍六十五標(biāo)的隊(duì)官,也隨這支增援部隊(duì)一同進(jìn)入了四川。
援軍出師之前,經(jīng)過長達(dá)半年的籌備,糧草輜重一應(yīng)俱全,行軍路線反復(fù)推敲,可謂算無遺策。
不料大軍剛一出發(fā),便遭遇重重阻礙,原先精心設(shè)計(jì)的行軍計(jì)劃竟成紙上談兵。
夫役逃亡一事尤其令人頭痛。從成都開拔第三天,沿途征調(diào)的民夫便開始成群結(jié)隊(duì)地遁入山林。
軍隊(duì)每到一處,差役們便如餓虎撲食般四出搜捕,嚇得百姓聞風(fēng)喪膽,村落十室九空,竟至炊煙斷絕。
殿后的第三營尤為嚴(yán)峻,行至邛崍時,五百名夫役已逃去過半。輜重車輛橫七豎八地拋棄在路旁,裝軍餉的檀木箱裂開在泥濘中,縱使懸賞十兩白銀也無人應(yīng)募。
軍紀(jì)敗壞更甚于夫役逃亡,那些在內(nèi)地令行禁止的精兵,此刻竟成了禍害鄉(xiāng)里的匪類。
每當(dāng)宿營時,我總在油燈下翻閱《全唐詩》中的邊塞詩卷。
岑參“將軍金甲夜不脫”的豪言,王昌齡“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的壯語,此刻讀來格外動人。
那些被后世傳頌的名句,分明是蘸著戰(zhàn)士的血淚寫就。
七月初三抵達(dá)雅州,只見阡陌縱橫,竹林茅舍間炊煙裊裊。
西行二十里,天地驟然變色。二郎山如巨斧劈開蒼穹,茶馬古道在千仞絕壁間扭成羊腸。
與劍門關(guān)一夫當(dāng)關(guān)的險峻相比,此處的山勢更增添了幾分蠻荒之氣,偶而可看見藏族碉樓孤懸峭壁,宛如遠(yuǎn)古遺存的烽燧。
時值三伏天氣,官兵穿著夏布單衣,汗?jié)n在后背結(jié)出白霜。
翻過泥巴山埡口,凜冽山風(fēng)撲面而來,恍如墜入冰窖。
北風(fēng)卷著雪粒子抽打著面頰,眾人不得不解開輜重,將預(yù)備入藏的氆氌呢袍提前裹上。
有些體弱者寒顫不止,竟在八月艷陽下活活凍死。
最險處在飛越嶺九倒拐,馬幫的鈴鐺聲在云海里若隱若現(xiàn),腳下萬丈深淵吞沒了失足騾馬的嘶鳴。
我親眼看見三匹馱著彈藥箱的健騾遭突如其來的冰雹驚嚇,連人帶畜滾落山澗,慘叫聲在絕壁間回蕩良久。
當(dāng)隊(duì)伍蹣跚走到草鞋坪時,珙桐樹的白花正紛紛揚(yáng)揚(yáng)飄落,宛如祭奠亡魂的紙錢。
安靖的大相嶺茶馬古道,秦朝叫“旄牛道”,漢朝叫“靈關(guān)道”,唐朝叫“清溪道”。
明清時期,因?yàn)橐貌枞~換馬,故稱為“茶馬古道”。
這條路是從滎經(jīng)進(jìn)入沈黎邊境的必經(jīng)之路,后人便將這段路稱為“大相嶺茶馬古道”。
歷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南方絲綢之路、川藏茶馬古道,都得經(jīng)過這個山口,此處地方不大,卻是天下交通的命脈。
傳說諸葛亮南征時,為了方便軍隊(duì)通行,親自帶人鑿山開路。
當(dāng)?shù)匕傩崭心钏亩鞯拢桶堰@座山嶺叫作“大相嶺”,旁邊的小山也稱“相公山”,嶺上有一座小廟,雖然簡陋,卻香火不斷。
《一統(tǒng)志》記載:“大相公嶺在雅州榮經(jīng)縣西一百里,傳說是諸葛亮當(dāng)年征西南夷時經(jīng)過的地方,上面還有座諸葛廟”。
《太平寰宇記》也記載:“相公山,當(dāng)年蜀漢丞相諸葛亮常在這里駐兵”。
每年暮春時節(jié),山花盛開,好像丞相還手拿羽扇、頭戴綸巾站在那里。
到了秋季,樹葉紛紛落下,又好像千軍萬馬披著鎧甲,風(fēng)中都能聽到金鼓聲。
這條路極其險峻,最險惡的地方叫虎耳崖,右邊是刀削一樣的石壁,左邊是萬丈深谷,低頭看滎經(jīng)河,好像一條帶子,碧綠清澈,但水聲咆哮,嚇得人腿軟。
路不到三尺寬,全是亂石,長滿青苔,極易打滑。
我騎的馬是成都有名的快馬,平時跑起來像飛一樣,到了這里卻汗水直流,鼻子直噴白氣,怎么打都不肯走。
我只好手腳并用,抓著藤蘿往上爬,歇息了好幾回才爬到山頂,回頭一看,白云都在腳底下,像騰云駕霧上了天。
山頂北邊的石崖上,有一塊清朝果親王允禮題的摩崖碑。
石碑被雪蓋住了,只露出一小截。我用馬鞭掃開積雪,露出粗糲的石面,文字慢慢顯現(xiàn)出來,是一首詩:
“奉旨撫西戎,冬登丞相嶺。
古人名不朽,千載如此永”。
???????????
★第三章過渡定橋
???????????
題字是楷書,筆力遒勁,好像新刻的一樣。
落款是“果親王胤禮題,雍正十二年冬”。
詩的前兩句是敬仰諸葛亮,后兩句自夸奉命安撫邊疆的功勞。
碑背面還有幾行小字,記載著當(dāng)時同行的官員和士兵的姓名,字雖然小得像米粒,卻一筆一劃極其工整。
果親王愛新覺羅·胤禮是康熙帝的第十七子,雍正帝的異母弟,其生母為純裕勤妃。
雍正帝即位后,為避雍正帝的名諱改名“允禮”。
允禮從小聰明好學(xué),不貪名利,喜歡游山玩水,又精通佛經(jīng),曾將藏文的《丹珠爾》翻譯成漢文,編輯了《古文約選》給八旗子弟當(dāng)教材。
雍正元年,允禮被封為果毅郡王,雍正十二年奉命巡視四川、云南、西藏的邊防,這碑文就是那年進(jìn)四川時刻的。
史書上說他“性格溫和,識大體”,看這詩就知道不假。
從雅安、漢源往西南再走三十里,抬頭就能看見一座高聳入云的大山,山頂終年積雪,像刀削過一樣陡峭,當(dāng)?shù)厝私兴帮w越嶺”。
山南是漢源,山北是瀘定,一山分隔兩縣。
山腳有一塊大草甸,叫“化林坪”,坪上立著一塊石碑,碑面長滿青苔,但字跡還清楚,仍是果親王題的題詩:“泰寧城到化林營,峻嶺臨江鳥道行。無限化羌開此地,塞坦宜建最高坪”。
落款為“雍正乙卯(1735年)二月果親王題”。
兩百多年來,風(fēng)吹雨打,來往的漢藏商人路過此地,都要下馬瞻仰。
從飛越嶺行軍六天,遠(yuǎn)遠(yuǎn)就聽見山里頭轟隆隆作響,好像悶雷。
拐過一道彎,大渡河出現(xiàn)在眼前,河面七十多丈寬,水深得發(fā)黑,浪頭撞在石頭上,濺起十幾丈的白沫。
康熙以前,過河只能靠牛皮筏子或者溜索,得折騰半天,貨物在岸邊堆成小山。若遇到筏子翻了、溜索斷了,連人帶貨全部沖得無影無蹤。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九月,康熙帝指著地圖上的大渡河說:“蜀道再難,朕也要用人力開出一條路!”于是下旨修橋。
工匠們從各地趕來,鐵錘叮當(dāng)響了七個月,鐵鏈子一根根拉過河,再鋪上木板。
次年四月大橋修成,康熙帝親自書寫了“瀘定橋”三個大字,又在橋東頭立碑,橫批寫“一統(tǒng)山河”。
從此,成都到打箭爐一天就能到,西藏的貨物十天就能進(jìn)四川,后來又有瀘定縣。
過了瀘定橋再前行兩天,地勢拔高,喘氣就好像吞冰碴子。眼前忽然開闊,一座小城鑲嵌在峽谷里,這里就是打箭爐。
傳說諸葛亮南征時,派大將郭達(dá)在此地支爐子造箭,所以叫“打箭爐”。
藏語叫“達(dá)折渚”,意思是“兩條河匯合的臺地”。清末雖然改成康定府,但老百姓還是習(xí)慣叫打箭爐。
打箭爐三面環(huán)山,終年陰云濃霧,狂風(fēng)怒號,氣候異常寒冷。山頂?shù)姆e雪終年不化,三伏天也需要穿棉衣。
此地才高于海面三千六百米,比巴塘、雅江、甘孜、道孚等地較低。只因四圍雪山環(huán)抱,陰濕多風(fēng),反而比巴塘、雅江、甘孜、道孚等地寒冷。
當(dāng)?shù)睾0稳Я倜祝拿嫜┥絿荒甑筋^陰云大風(fēng),三伏天也得穿棉襖。
我們到了以后,皮襖、氈衣、毯子一層層往身上裹,還是冷得打哆嗦。
我開玩笑說:“內(nèi)地的寒冷是從外往里鉆,瘧疾的寒冷是從里往外冒,這里的寒冷是直接從骨頭縫里生出來,躲都沒處躲”。
城里滿街都是穿紅袍、黃袍的僧人,本地人說,常住喇嘛有兩千多人,加上云游掛單的,常有三千多人。
原本有八座大寺廟,現(xiàn)在還剩下七座,安雀寺、南摩寺是黃教大廟,金頂閃閃發(fā)光。奪吉村寺是紅教祖庭,念經(jīng)聲如雷貫耳。其余四座小廟,每廟十來人,星星點(diǎn)點(diǎn)散落在城中。
當(dāng)?shù)丶抑兄灰腥齻€男孩,必定送兩個去當(dāng)喇嘛。喇嘛的地位高過內(nèi)地的舉人,家里還能免除差役、分到田地,所以人人都爭著把孩子往廟里送。
大喇嘛廟有的高達(dá)九層、十層,金頂經(jīng)幡,風(fēng)中嘩啦啦響。
百姓的房子圍著寺廟蓋,紅墻白窗,遠(yuǎn)遠(yuǎn)看去就像星星環(huán)繞著月亮。
當(dāng)?shù)靥鞖鈬?yán)寒,只能種青稞和小麥,無論百姓還是喇嘛,一天三頓都吃糌粑,糌粑是將青稞炒糊了磨成粉,用熱酥油茶攪拌,捏成團(tuán)就能吃。
酥油茶的制做是先將茶熬得發(fā)黑,倒進(jìn)竹筒里,加上酥油、鹽,用圓棍子杵上千下,令油、茶、鹽混和為一體,再倒進(jìn)銅壺里用小火煨。當(dāng)?shù)厝嗣刻於己冗@種茶,一盞接一盞,能喝十幾碗。
我第一次聞到,腥臭得差點(diǎn)嘔了。同伴們打賭,誰喝不下就罰錢,我勉強(qiáng)抿了一口,立刻惡心得不行,便交錢認(rèn)罰,再也不敢碰了。
集市上熱鬧非凡,四川人售賣臘肉辣椒,云南人售賣普洱白藥,陜西人馱來布匹鐵器,還有黃頭發(fā)、藍(lán)眼睛的外國傳教士,身穿黑袍,行色匆匆。
藏族男人寬袍大袖,腰扎彩帶,頭戴呢子高帽。
女人穿長衫長裙,腰系絲帶,脖子上掛著幾十串珊瑚、蜜蠟,走一步就嘩啦啦響。
???????????
★第四章 雪域行軍
???????????
高等僧人穿紅黃緞子,靴子是由紅牦牛皮做的,手里捻象牙佛珠,低級僧人只能披粗呢片,赤著腳化緣。
老百姓的房子大多是三層碉樓,底層養(yǎng)牛馬,中層住人,頂層曬糧食。
屋內(nèi)墻上畫著《格薩爾》的故事,五顏六色,一年到頭不褪色。
我們還在瀘定橋時,探子就飛馬來報(bào),番王已下令噶倫調(diào)一萬民兵,把守雀兒山、折多山各個山口,阻撓我軍入塞。
當(dāng)時,川邊大臣趙季和親自率領(lǐng)八營邊軍向北疾進(jìn),平定白仁青之亂,同時推進(jìn)改土歸流的新政。
得知鐘新統(tǒng)領(lǐng)的川軍即將入藏時,恐怕與沿途的番兵正面沖突,無異于驅(qū)羊入虎口,傳令到打箭爐:“貴部不必循南線硬碰番兵,改由北道出關(guān),與我會師昌都!”
這道命令是趙季和對新軍的體恤,北路雖然繞道很遠(yuǎn),卻是清廷經(jīng)營多年的驛傳大道,沿途驛站、人戶較多,既能避開番軍主力,又便于補(bǔ)充給養(yǎng),對初次入川的陸軍而言,無疑是一條比較穩(wěn)妥的道路。
我軍在打箭爐待命七天,第八天午后,鐘統(tǒng)領(lǐng)的旌旗終于在折多山口出現(xiàn),其麾下人馬也疲憊不堪。
又經(jīng)過三天整頓,才重新開發(fā)。
北路雖然號稱官道,實(shí)則是一代代驛卒踩著牦牛踏出的痕跡,在荒山中硬生生走出的一條小道。
大部分路段仍舊砂礫遍地,時而攀援絕壁,時而俯臨深谷,馬蹄踏在碎石上,發(fā)出“咯吱”的異響,好像是在抱怨這趟苦差。
每營一千二百人的編制,卻需要配備兩千多頭牛馬。
彈藥箱需要防潮,軍米袋需要密封,帳篷、鍋灶、醫(yī)藥箱、柴炭捆,乃至軍官們的藤轎、皮箱,都得靠烏拉馱運(yùn)。
每天消耗的軍糧,就得裝滿十頭牦牛的馱筐,而那些防潮的油布、取暖的皮襖,更是占去了一大半烏拉的運(yùn)力。
高原的牦牛是天生的負(fù)重者,但也有極限,連續(xù)負(fù)重兩天后便會萎靡不振,必須兩三天一換,否則便會倒斃途中。
若前方的烏拉隊(duì)銜接不上,士兵們就得自己背槍扛糧。
有一次在折多山北段,因暴風(fēng)雪延誤了換班,我們背著二十斤重的米袋行軍,腳下是冰坡,肩上是重?fù)?dān),走三步滑一步,傍晚抵達(dá)營地時,都累得倒地不起。
內(nèi)地調(diào)來的川馬,平日能日行百里,一進(jìn)高原,就口鼻噴出白沫,四條腿軟得像面條,連站都站不穩(wěn)。
沿途藏民的犏牛、矮馬成了真正的主力,它們個頭不高,卻能在雪地里健步如飛,馱著彈藥箱爬坡時,蹄子蹬得冰碴四濺,那股勁頭,令士兵們嘖嘖稱奇。
出發(fā)那天,打箭爐下起了雨夾雪,寒風(fēng)像無數(shù)把小刀,刮過臉頰,鉆進(jìn)衣領(lǐng),凍得人直打哆嗦。士兵們裹著濕冷的棉衣,背著沉重的槍支,在泥濘中深一腳淺一腳地挪動。
牛馬似乎也受了天氣影響,牦牛甩著尾巴不肯前行,馬群則焦躁地刨著蹄子,整個隊(duì)伍亂成一團(tuán),吆喝聲、斥罵聲、牛馬的嘶鳴聲混在一起,在風(fēng)雪中格外刺耳。
午后抵達(dá)折多塘?xí)r,天色已黑,士兵們頂著濕透的棉衣,肚子餓得前胸貼后背,三三兩兩地摸索著往營地挪。
我與向?qū)ё咴谇懊妫仡^望去,身后的隊(duì)伍像一條散了架的長蛇,斷斷續(xù)續(xù)地在黑暗中蠕動。
營地扎在山谷里,篝火升起時,才看清周圍的景象,低矮的石頭房子?xùn)|倒西歪,地上的積雪被踩成了爛泥,牦牛和馬被隨意拴在枯樹上,嘴里嚼著干硬的草料。
山谷中回蕩著牛鈴和馬嘶,偶爾夾雜著士兵的咳嗽聲,叫喊聲一直鬧到深夜。
次日清晨,風(fēng)雪驟停,雪線以上的山峰被陽光照得刺眼。
沿著山腰小道行進(jìn),左邊是深不見底的峽谷,右邊是刀削般的絕壁,而腳下的積雪在陽光下閃爍,好像一條白色的綢帶,纏繞在山間。
藏族兒童騎著馬,揮著牛毛鞭子從我們身邊呼嘯而過,臉頰曬得通紅。
我身為督隊(duì)官,每天天未亮就得帶著向?qū)Ш捅O(jiān)營官騎馬先行探路。
經(jīng)過道孚附近,見一群藏民正在賽馬,我一時興起,揮鞭追了上去。
可我的騎術(shù)本來不精,那匹藏地矮馬又性子暴烈,在草地上顛得我上下起伏,差點(diǎn)被甩下馬背。
最后總算狼狽地追上隊(duì)伍,回營時腰酸得像灌了鉛,連吃飯都抬不起胳膊,惹得同伴們大笑。
抵達(dá)道孚時天色尚早,我和幾個同伴到近郊散步。
十來所房子散落在疏林之間,草色一直鋪到天邊,像塊巨大的綠絨毯。
樹林外有一道小溪,寬約四五尺,碧水清淺,能看見水底的鵝卵石,溪里的魚又多又大,往來游動,時不時躍出水面,濺起一串水花。
我們頓時來了興致,卷起褲腿就想下去抓幾條來加餐,可又頓生疑惑:“這里居民不少,怎么會有這么多魚沒人捕撈?”
隨行的通司說,當(dāng)?shù)亓?xí)俗,僧侶死后用火葬,普通人多用天葬,將尸骸剁碎,供雕鳥食用,而罪人與貧民死后,則直接扔到河里,任憑魚鱉分食,這便是水葬。
第七天傍晚,我們終于抵達(dá)霍爾章谷。這里已完成改土歸流,清廷設(shè)置了理事官,街上甚至有了漢人開設(shè)的店鋪,這是我們出關(guān)以來第一次見到如此多的漢人面孔。
士兵們湊錢買了一口肥豬、十幾斤干魷魚,找了口大鐵鍋,就在營地里支起了灶臺。
將豬肉和魷魚切成小塊,用豆豉、干辣椒爆炒,香氣四溢,裝在兩只木桶內(nèi),沿途食用。
霍爾章谷是烏拉轉(zhuǎn)運(yùn)站,按計(jì)劃要在這里更換新的烏拉隊(duì)。
可前一天傍晚,本該到齊的牦牛,因暴風(fēng)雪堵在山口,只來了七成。
???????????
5
第五章★冰天雪地
???????????
過了甘孜,山勢開闊,峽谷深隧,空氣稀薄,士兵們走路越來越慢,每走幾步就要停下來喘氣,嘴唇干裂得像樹皮,有些人開始流鼻血,用布條塞著鼻孔繼續(xù)走。
崗?fù)写迨沁M(jìn)藏最后一站,瀾滄江在這里拐了個大彎,江水奔騰咆哮,如同千軍萬馬。
站在崗?fù)械纳郊股希瑯O目遠(yuǎn)眺,能看見遠(yuǎn)方昌都的紅墻金瓦,以及趙季和邊軍的狼煙臺。
從打箭爐到昌都,經(jīng)歷二十三天,跋涉了六百里。
夜半時分,忽然聽到喧呼之聲,起身一看,原來是番人送烏拉牛馬來了,漫山遍野,不下數(shù)千條。
我正擔(dān)心明天清晨掉換烏拉,馱裝捆載行李,不知要費(fèi)幾個小時。
等到次日清晨起床,只見番人輕車熟路,不到一個小時,兩千多馱糧食彈藥已捆載完畢,番人身手之敏捷,漢人簡直望塵所及。
我們見番人個個體力強(qiáng)健,不覺艷羨不已。難怪唐朝安史之亂后,吐蕃屢次犯邊,朝廷不敢言戰(zhàn),被迫與吐蕃和親。
每天宿營時,牛馬擁擠在草坪中,藏人卸裝行動迅速,馱牛兩千多頭,不到一個小時便卸裝完畢。藏民呼嘯一聲,馱牛便四散走動,漫山遍野,到處啃草。
到了黃昏前后,藏人又呼嘯一聲,但見山上群牛攢動,爭先恐后,匆匆歸來,根本不需要驅(qū)趕。
藏人在地上打樁,系上長繩,排列為若干行,長繩中又系有無數(shù)短繩,拴在牛蹄上,牦牛或站或臥,秩序井然。
記得有一天深夜,我起床方便,放眼望去,白雪皚皚,一頭牦牛也沒看見,不禁大吃一驚。
我慌忙詢問衛(wèi)兵,才知道牦牛就躺臥在雪中,大雪遮蓋住牛身,看上去好象無數(shù)個雪堆,隱約立地地上,若不是轉(zhuǎn)身抖落厚厚的雪花,哪里知道是牦牛?
甘孜、曾科(今四川甘孜白玉縣贈科鄉(xiāng))、麥削(今四川甘孜德格縣麥宿鎮(zhèn))、崗?fù)希ń癫冀_(dá)縣崗?fù)墟?zhèn))一帶,峰巒疊嶂,冰雪滿山。
從山腰經(jīng)過,經(jīng)常可看見山水瀉冰,形成寬十多丈的河道。人馬通過,必須先鋪上沙土,才能免于傾覆。
谷底的溪流凝結(jié)成冰,牛馬數(shù)千條踏冰而過,冰面破碎之聲數(shù)里之外也能聽到。
當(dāng)時已是暮秋,天氣日益寒冷,大雪紛飛,北風(fēng)怒號,人馬牲畜,如同披上銀裝。
我有一句詩云:“冰敲馬蹄鈴聲細(xì),雪壓槍頭劍氣寒,”絕非夸張,純屬寫實(shí)。
麥削以西,河深流急,無舟船,無橋梁,故我軍渡河,都用皮船。
皮船用野藤與牛皮制成,呈橢圓形,如同半個西瓜。
皮船輕捷似飛燕,好似一片樹葉起伏于驚濤駭浪之中,遠(yuǎn)遠(yuǎn)望去,看似時刻會傾覆,實(shí)則穩(wěn)如泰山。
皮船大的可載重四百斤,小的也可載二百余斤。小船用一張牛皮制成,大船則用兩張。
軍隊(duì)渡河時,先渡行裝,再渡官兵。由于船太小,每次渡河都需要好幾天。
僅我所在的全營士兵,渡河就耗費(fèi)了三天。而沿途河流又特別多,所以行軍速度極慢。
藏地的牛馬都能泅水,每當(dāng)渡河時,先驅(qū)一頭牛過河,其他馬牛便自己入水,不必驅(qū)趕,都向?qū)Π队稳ァ?
我軍渡崗?fù)虾訒r,在江邊歇宿了幾天,見山中的貝母雞(注:即綠尾虹雉,因喜歡取食貝母的球莖,土名叫“貝母雞”)成群結(jié)隊(duì)。
聽說這種野雞味道特別好,我就約了同伴攜槍上山射擊,每天可獵到好幾只。
到河邊剝?nèi)テす牵瑢⑷馇谐尚K,拌上胡豆醬炒吃,味道特別鮮美,遠(yuǎn)非家禽所能比。
高原行軍,最苦的不是行路難,而是苦于起床太早,睡眠不足。
過了甘孜以后,沿途居民漸漸稀少,趙季和所定的路程,每天都在一百二十里以上,若不整天趲行,就會錯過宿站。
沒有宿站,就沒有藏官預(yù)備的燃料,不能燒火作飯,所以不得不起早床。
而且行軍都自帶帳幕,到了目的地后架設(shè),出發(fā)前又要收拾。
當(dāng)?shù)貛缀鯖]有一天不下雪,一到半夜,大雪鋪滿帳幕。
次日清晨早起,必須先將帳幕用火烘干,才能馱遠(yuǎn)。
最痛苦的是天還未亮,帳幕已經(jīng)撤了,風(fēng)如刀割,站在曠野中,等候烘干帳幕的這段時間。
直到裝上馱牛,大約需要一個半小時之久,眾人一個個手足凍僵,渾身戰(zhàn)栗,呻吟不止,這種痛苦實(shí)在非語言所能形容。
行軍五十余天,才到達(dá)昌都。
昌都又名察木多,是打箭爐至拉薩的樞紐之地。
昌都城內(nèi)有居民六七百戶,大小喇嘛寺很多,漢人居住在此地者不少,朝廷設(shè)有軍糧府作為治理機(jī)構(gòu)。
我軍來到昌都,已疲憊不堪。
當(dāng)時,趙季和駐軍更慶(四川甘孜德格縣更慶鎮(zhèn)),邀請鐘新由甘孜來會面,鐘新不敢去,趙季和便命我軍暫時集中于昌都,偵探番兵情形,等待后命。
???????????
6
第六章★臘左歷險
???????????
鐘新來到昌都后,號令全軍,選擇四人前去偵察,幾天都無人響應(yīng)。
當(dāng)時趙季和常說西征士兵都是些書生,不曉得什么軍事,我引以為恥,所以挺身請求前去。
林浴凡也極力慫恿我,向軍糧府請求發(fā)給馬牌。清朝官員外出辦理公務(wù),所到驛站更換馬匹的憑證稱馬牌。
我便輕裝出發(fā),攜向?qū)埞γ髑巴?
張功明五十多歲年紀(jì),四川人,流寓川邊多年,經(jīng)營商業(yè),熟悉川邊情勢。
當(dāng)天由昌都出發(fā),過了橋,前行三里多路,只見一大群烏鴉遮天蔽日而來,飛鳴聲響徹云霄。
張功明的馬受驚,他竟跌落馬下,我只得下馬步行,驅(qū)散烏鴉,牽馬而行。
起初我以為當(dāng)?shù)囟酁貘f,沒有什么征兆不妙的念頭。
前行三十里來到俄洛橋,有一哨(注:約五十人)邊防軍駐扎于此。
哨官姓鄧,四川人,武備生未畢業(yè),招待極其殷勤。
當(dāng)時已經(jīng)是黃昏時分,鄧哨官待飯留宿,我也想向他詢問前方情況,便歇宿于軍營。飯后,共談川邊形勢,很是融洽。
他說番兵駐扎于恩達(dá),先頭部隊(duì)已抵達(dá)林多壩,巡邏騎兵出沒于距此處三十里的臘左塘,勸我不要冒險前去。
我雖然很感激他的好意,然而由于任務(wù)在身,不肯中途而廢。
次日清晨出發(fā),沿途并無居民,也全無人跡。策馬行走三十里,來到臘左塘,就是臘左附近的山寨。
此地有一所塘房,設(shè)塘兵四人,我抵達(dá)時,塘兵已經(jīng)捆載好行李,即將返回昌都,形色很是倉皇。
塘兵見我到來,大吃一驚,說番騎夜夜來此,力請我一同返回。
張功明也說不能再前進(jìn)了,我奮然說:“縱使不去臘左,也應(yīng)登山望一望,”于是決然上山。
山高十余里,迂回而上,冰雪滿路,人馬多次跌倒。
我只得牽馬步行,也屢次跌倒,將到山頂,遙望白霧迷蒙,疑心是番騎的煙塵。
爬到山頂,狂風(fēng)怒號,卷起雪花,寒風(fēng)刺骨,人馬氣喘,幾乎不能呼吸,二人當(dāng)即昏倒在地。
幸好我神志尚清醒,不久便醒來,強(qiáng)行起身牽馬,再扶起張功明。
張功明埋怨道:“不聽老人言,自尋苦惱,看到什么沒有?”
我說:“您老人家莫見怪,既然來了,必須去臘左看看,”于是打起精神下山。
張功明不得已,只好跟著我走,沿途多次跌落,幾乎被馬踩傷。
走了大約八九里路,才下到平地,天已經(jīng)快黑了。
幸好有雪光掩映,尚能分辨道路,我們沿著小溪前行兩三里,來到臘左。
隱約見有二十多戶民舍,散布在兩岸,家家關(guān)門,悄無人聲,用木棍敲門,無一戶人家答應(yīng)。
后來來到一家樓下,一名老人出來,我們詢問他,他說:“番兵離這里只有十余里,邏騎夜夜來這里,居民都已逃避,我因病走不動,所以留在家。”
張功明問我怎么辦,我指著對岸一間靠山的房屋說去那邊投宿,于是牽馬涉過溪河。
我們登上樓,推門進(jìn)去。樓只有一人高,把馬系在樓下,我選擇樓上較寬的一個房間下榻,點(diǎn)燃洋燭,略略烤烤帶來的燒餅。
張功明勸我不要點(diǎn)蠟燭,我就將蠟燭移到角落,取一塊木板覆蓋住,推開窗子,但見月色明朗,照耀冰雪世界,不勝清寒。
我想稍作休息,就登山眺望,以防番騎來偷襲,正在閉目思索,忽然聽見鈴聲從遠(yuǎn)處傳來。
我知道番騎到了,急忙下樓,反穿白羊裘,埋伏在后山一塊巨石后面。
不久,只見番騎數(shù)十人,從容進(jìn)入對岸的民房,挨戶用馬鞭敲門,操著番語,問有沒有漢奸,不得藏匿。
番騎沒有涉過溪流,便向臘左山去了。大約一個小時后又返回,再次敲門查問,隨即離去。
我以為從此無事了,便入室休息。張功明跟了進(jìn)來,皺著眉說:“好險!差點(diǎn)完蛋了。”
我笑道:“還沒完蛋,明天帶你去前方一探究竟”。
話音未落,突然聽見鈴聲急促,我慌忙熄滅蠟燭,推開窗戶向外看,只見番騎一百余人,從兩翼飛馳而來。
距對岸大約一百步,都下馬拔刀,跳躍而來。我已來不及逃遁,只聽喊殺聲、馬嘶聲響成一片,聲震山谷。
我急忙走出房間,見旁邊有一間小屋,便躲了進(jìn)去,暗中摸索,摸到磚石,似乎是廚房,墻上有小洞。
我從小洞向外窺看,只見番兵持刀蜂擁而來,刀有四五尺長,映著月光雪色,森嚴(yán)恐怖。
???????????
7
第七章★死里逃生
???????????
我急忙關(guān)上門,推來石塊撐住,再向外窺探,見番兵僅相距僅十多步了。
我轉(zhuǎn)念一想,門既然從里面關(guān)上,怎么可能沒人?這如同是告訴敵人自己藏身于此,不如索性打開門等待。
門剛打開,番兵已來到樓下,我想自己藏身暗室,倘若番兵持刀亂斬,就完了,不如出門大喊大叫,或許可以幸免。
于是我挺身而出,剛出門,番兵已經(jīng)登上樓。
我厲聲喝叱,先上樓的那人沖向我狠狠斫來,幸好房屋矮,刀太長,被房檐擱住,沒砍中我。
番兵蜂擁而來,我只覺背部一陣劇痛,頓時拳腳交加,有人喊“殺”,有人喊“活捉”,番兵用刀柄打中我的右額,頓時眼冒金星,倒地昏迷。
昏迷中感覺有人將我拖到樓梯口,向樓下拋擲,于是不醒人事。
我昏迷后被番兵捆在馬背上前行,顛簸中又蘇醒過來了,乘著月色行走十余里,經(jīng)過一座長橋。
一百多名番騎擦肩而過,馬蹄聲交織,將我吵醒,知道已被番人俘虜,頭、腰、手都受了重傷,但已經(jīng)麻木,尚不覺得太痛楚。
途中駐扎有數(shù)百名番兵,見我被捉獲,無不拍掌歡呼。
再沿河道前進(jìn),兩面都有番兵警戒,只見番兵左手敲鑼,右手擊鼓,絡(luò)繹不絕。
又走了十余里,來到林多壩,已是深夜。
番兵將我牽到樓上,樓上有幾名男女在燒火熬茶。番兵將我綁在梁柱上,我倚柱而坐,只覺頭和腰痛不可忍。
張功明也被牽來,早已嚇得面無人色。
不久,有個貌似番兵頭目的人走來,手持馬鞭審問我。
我說自己奉趙大臣之命而來。頭目不相信,掄起馬鞭便打,我再次昏厥過去。
又過了許久,又來了一人,裝束仿佛番官,細(xì)細(xì)盤問了一番,他的臉色才稍稍好轉(zhuǎn)。
我仍堅(jiān)持說奉趙大臣之命來此,他問我文書在哪里,我說:“文書放在馬鞍中。”
番官下樓許久,回來說:“馬鞍中并無文書,莫非是誑騙我么?”
我知道番人素來畏懼趙氏如天神,便一本正經(jīng)地說:“行李文書,你們都搶去了。
既然懷疑我沒有文書,何妨去往昌都趙大臣行轅詢問?”
番官問道:“趙大臣已到昌都了么?”
我詐稱道:“趙大臣率邊兵八營,比我提前一天到達(dá)昌都,你們還不知道么?”
番官沉思良久,復(fù)問:“趙大臣遣你來這里,是何用意?”
我說:“見了你們堪布就知道了,你不必多問。”
番官又檢查我的傷勢,與頭目低聲說了許久。又問我的官秩,我詐稱是三品官,番官便與頭目下樓。
不久,兩個番兵來為我松綁,繩索剛剛解開,只覺兩手痛徹肺腑,又昏倒在地。
番兵背我下樓,進(jìn)入一間臥室,頗為清潔,似乎是番官的住所。
番兵拿來酥油茶,我正好口渴冒火,飲下酥油茶,竟覺得異常甘甜,神思也逐漸清醒,靠墻睡去。
我聽到雞鳴犬吠鳥叫聲才驚醒,仰視窗外,天已經(jīng)黎明。
不久,只聽室外人馬聲嘈雜,番官進(jìn)來對我說:“堪布有令,約君去恩達(dá)一會,請立即起行,”我矍然起身。
番兵扶我上馬,行走特別緩慢,只覺腰間創(chuàng)口迸裂,血流不止,痛苦不堪。
途中每當(dāng)經(jīng)過溪流,或登臨山坡,前后簸動,痛楚尤為厲害。
當(dāng)時晨風(fēng)凜冽,寒冷徹骨,觸目所及,盡是荒野,不覺黯然神傷。
偶而想到妻子、侄兒浮寓長沙,離家千里,不知他們?nèi)绾畏掂l(xiāng),不禁悲從中來。
然而轉(zhuǎn)念一想,男兒志在報(bào)國,要死就死,又何必對妻兒牽腸掛肚呢?想到此處,又不覺神清氣爽。
走了二十余里,抵達(dá)恩達(dá),已是上午十點(diǎn)。
恩達(dá)汛官葉蒙氏,身穿朝服出迎,非常恭敬,引導(dǎo)我來到堪布的營地。
堪布也出營迎接,極其謙遜。落坐后,獻(xiàn)上茶點(diǎn),堪布極稱未得趙大臣告知,以致產(chǎn)生誤會,致謙不已。
我答道:“趙大臣恐怕大軍逼近,玉石俱焚,特遣在下前來曉諭,限即日撤兵退回。
如今新軍已經(jīng)從北路出拉里,西川邊軍集中于昌都,之所以不立即進(jìn)軍,不過憐憫番民無知,不忍急于用兵罷了。”
又詳細(xì)說明我在臘左的經(jīng)歷,堪布惶恐謝過,獻(xiàn)上面食果餅,極其殷勤,說道:
“我原本是僧官,番王督責(zé)極嚴(yán),不得已統(tǒng)兵阻止。
如今駐軍恩達(dá),也是等待趙大臣前來,豈敢輕舉妄動?”
堪布又具文呈報(bào)趙季和,請我即日返回昌都,向趙大臣復(fù)命,承諾三日內(nèi)撤退番兵。
???????????
8
第八章★因禍得福
???????????
我因創(chuàng)痛嚴(yán)重,不肯立即動身,堪布力請不已,我才應(yīng)允。
堪布又為我施符咒、吃藥餌,并贈送良馬、佛像、捻珠、奶餅,派士兵四人送我回臘左塘,
于是收拾起身,堪布等人送到山下才返回。
鐘新率標(biāo)統(tǒng)、管帶來到欽差大臣行轅參謁,黃昏才回。
軍官張青隨林浴凡前去拜謁,不久便馳回,告訴我說:“欽帥因你貪功失機(jī),罪當(dāng)斬首!怎么得了?”
我問:“管帶如何對答?”
張青說:“管帶默然不語。”我很是詫異。
等林浴凡歸來,又向他詢問,林浴凡只說欽帥明天早晨傳見我,然后一言不發(fā)。
此時我才預(yù)感到林浴凡別有用心,我想自己奉命而去,不顧安危,九死一生,為國盡忠,有何罪過?
次日清晨去見欽帥,才剛出門,便有趙季和的衛(wèi)兵持大帥令傳召我。
我很是驚訝,便隨他走,到了行轅,見鐘新與軍糧府劉紹站在門外。
衛(wèi)兵帶我進(jìn)去,趙季和滿面怒容站在帳中,怒斥我貪功冒險、損威辱師之罪,要將我繩之以法。
鐘新、劉紹二人急忙趨入,極力說情,趙季和仍怒火難息。
我至此境地,也不能為林浴凡隱諱了,于是慷慨陳辭道:“奴才罪該萬死,但是銜命而往,雖然被俘虜,番人還能以禮送回。
而且奴才宣示欽帥德威,番兵望風(fēng)撤退,有功有罪不敢自我評定,惟欽帥深察。”
鐘新又極力勸解,趙季和的怒氣才稍稍平息,便詳細(xì)詢問事情始末。
趙季和又問“林管帶果真事先知道你去嗎?”
我如實(shí)回答,并說軍糧府尚有林管帶的咨文可作憑證,趙季和索取咨文查驗(yàn)完畢,便轉(zhuǎn)而詢問林浴凡,林浴凡無言以對。
趙季和大怒,當(dāng)即扯下他的朝服、佩刀,就在桌案上親手書寫朱諭,撤去林浴凡職務(wù),由我代任管帶,我也不敢發(fā)言,叩謝而出。
清朝欽差大臣有權(quán)代皇帝下“朱筆諭旨”,簡稱“朱諭”。
后來我回到內(nèi)地才知道,趙季和曾致電川督(即其兄趙公讓)稱:“頃接察稟,番人將沈玉鍪放回,可恥可恨!請速電飭正法。川軍弟不便擅專。鐘守(即鐘新)毫無營規(guī),非此不足以肅軍紀(jì)也”。
讀了此電,我不禁汗流浹背。
鐘新雖然年少不夠老練,但他是皇上的表兄弟,特邀西太后恩寵,趙季和不敢對軍機(jī)處斥責(zé)鐘新,但是可以告訴其親兄弟。
古人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我因此事轉(zhuǎn)禍為福,但還有更離奇的事。
有個安徽人張紅升,為人陰險狡詐,起初在趙季和手下任邊軍管帶,后因事被撤職,回到四川投靠鐘新。
鐘新西征,委任張紅升為工程營管帶,其實(shí)是個有名無實(shí)的職務(wù),張紅升整天鉆營,想升任為步標(biāo)管帶,苦于沒有機(jī)會。
正值我在臘左被俘虜,兇耗傳到昌都,趙季和的隨員與張紅升友善,對張紅升說,他奉欽帥之命,就沈玉鍪之事詢問林浴凡,林浴凡一言不發(fā),只不過哀聲嘆氣而已。
張紅升便慫恿林浴凡道:“欽帥的性情暴躁如烈火,倘若他親自問你沈玉鍪之事,你不如謊稱不知道此事。
欽帥幕僚中,有個人是我的摯友,他會袒護(hù)你,你不必?fù)?dān)心”,林浴凡信以為真。
等趙季和到來,恨我擅自行動,有損國威,林浴凡沉默不語,趙季和更加憤怒。
張紅升求見趙季和的親信文案傅華豐,為我極力辯護(hù),痛罵林浴凡無恥,其意在取林浴凡而代之,并非愛我而恨林浴凡。
傅華豐是張紅升的好友,便在趙季和面前極力詆毀林浴凡。
所以趙季和赦免我貪功冒險之罪,將林浴凡褫職,張紅升還沒來得鉆營,趙帥一紙朱諭,迅如閃電。
張紅升固然垂頭喪氣,我則死里逃生,轉(zhuǎn)禍為福,用心險惡之報(bào),既可笑也可憐。
張紅升之弟也隨軍擔(dān)任隊(duì)官,隨鐘新西征,后來隨鐘新投奔錢西賓。
張紅升與鐘新、錢西賓從印度返國后,倪世沖將張紅升舉薦給張功勛,張紅升與鐘新部下的標(biāo)統(tǒng)陳慶同任張功勛的營長。
鐘新被逮后,張紅升命其弟率領(lǐng)六人赴京申辯,七人到達(dá)天津,被羅長依的黨羽殺死。
張紅升聽說其弟慘死,又親自赴京為鐘新辯冤,到京后鐘新已經(jīng)被清廷處死,張紅升萬念俱灰,便出家遁入空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