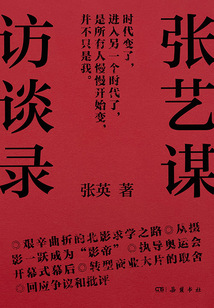
張藝謀訪談錄
最新章節
- 第18章 張藝謀奧運訪談錄 所有人的努力是最偉大的
- 第17章 張藝謀奧運訪談錄 意見與調整
- 第16章 張藝謀奧運訪談錄 運氣與責任感
- 第15章 張藝謀奧運訪談錄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 第14章 張藝謀奧運訪談錄 “我們是一家人”
- 第13章 張藝謀奧運訪談錄 曲折的創意過程
第1章 序章 張藝謀小傳(1)
一封信改變的命運
“我是比較低調、執著和堅持的人,不被干擾,一直堅持往前跑,機會給我撞上就成功了,再加上機遇,所有的機會撞上就成功。”張藝謀對筆者說。
張藝謀第一次改變自己的命運,是他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黃鎮寫了一封信,成功地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從而離開了咸陽市國棉八廠,成為一名大學生。
1950年4月出生的張藝謀,父親和母親都姓張,母親張孝友后來曾任西安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皮膚科大夫,父親張秉鈞是西安臨潼人,在陜西農林局工作。
從小時候起,張藝謀就因為家庭出身和政治問題,一直是社會邊緣人。張藝謀的爺爺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后來當過民國時期陜西柞水縣縣長。爺爺剿匪不成,還被土匪燒了自家大院,逃到西安避難。這段經歷刺激了爺爺,后來他把三個兒子送到黃埔軍校讀書。
“張藝謀大伯是黃埔九期,二伯是黃埔十五期。張藝謀的父親排行老三。”[1]他們從黃埔畢業后,上前線帶兵打仗,張藝謀奶奶想留一個兒子在身邊,于是小兒子進了國民黨軍隊,當后勤軍需官。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后,張秉鈞和母親留在大陸。張藝謀大伯去了臺灣,二伯在胡宗南手下,在準備起義投奔去延安時,被軍統逮捕后失蹤。西安解放前,張藝謀父親離開軍界,去了陜西省財政廳工作。
根據解放初期的肅反政策,國民黨的軍需、軍醫等技術人員可以留用。新中國成立后,政府給張秉鈞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去省農林局下轄的一所學校工作。張藝謀母親從西安醫科大學畢業后,留在學校第二附屬醫院皮膚科工作。
張藝謀是家里第一個孩子,他的名字是爺爺取的:張詒謀。外公對“詒”字的理解是“詒者,勛也”,是期望他在未來建立功勛,光宗耀祖。后來,張藝謀又添了兩個弟弟——張偉謀和張啟謀。
“文革”時期,張藝謀的父親被定為“歷史反革命”,被打倒,在牛棚勞動改造十幾年;失蹤的二伯被定為“潛伏特務”;大伯當時在臺灣,原來是國民黨軍人。
“我當時是‘狗崽子’,是‘黑五類’。”張藝謀對筆者回憶說。
母親出于對三個孩子前途的考慮,也迫于當時的政治壓力,一度打算和父親離婚,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環境。盡管父母最終并未離婚,可這件事給當時的張藝謀以巨大的打擊,留下深深的陰影。
“我實際上是被人從門縫兒里看著長大的。從小自卑,心理和性格就壓抑、扭曲,一直收縮性地做人,從小養成這樣性格,即使后來家庭問題平了反,個人的路走得比較順,但仍舊活得很累。”[2]
1968年,張藝謀中學畢業,作為問題家庭的孩子,他是當時第一批到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我們被認為是沒有出路的,戶口什么都轉了,一刀切全部下去當農民。我們班也有女生嫁給當地農村青年的,在完全絕望、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城里人才嫁給農村人,她嫁的時候也哭。”
那個年代離開農村,“知識青年”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文體特長。
插隊時,張藝謀帶了畫筆、顏料和油漆。在下鄉的楊漢鄉北倪村,他花了幾天,給村里所有的門全畫上主席像。“現在想來,那時候確實有政治激情,尤其要通過這種方式顯示自己的忠誠,加上自己的出身不好,‘黑五類’,我就要把主席像畫得比別人更大、更鮮艷,紅彤彤。”
張藝謀籃球打得不錯,遠距離投籃很準,加上擅長寫美術字、刷大標語、畫主席像,這些文體特長讓他邁過了政治出身問題,成為咸陽國棉八廠的車間輔助工人。
“我好像從來都這樣,想做個什么事,先不聲張,悄悄做準備。”[3]張藝謀說。進工廠后,他干過電工、搬運工。張藝謀總值夜班,黑白顛倒,很辛苦。他不懂攝影,就跟愛拍照的表哥借書,跟同學借書,有一些書是同學從圖書館偷出來的。為了學會攝影技巧,他把借來的書,幾十萬字從頭到尾抄一遍。
張藝謀學攝影,是想開個照相館謀生。他靠著出板報、畫宣傳畫、拍照片的特長,從一名生產車間干體力活兒的工人到被調入工會,成為辦公室里的文職人員,負責宣傳工作。
1978年5月,北京電影學院恢復招生,招收“文革”后第一批本科生,其中有攝影專業。28歲的張藝謀把這當成改變命運的機會,準備報名。但當時電影學院規定攝影專業只招22歲以下的學生。
張藝謀不甘放棄,挑選了一批攝影作品,利用一次出差進京的機會,跑到電影學院報名。負責招生的老師對他的作品贊嘆不已,但得知他超齡時,只能表示遺憾:“你先回西安,我們會向學院反映你的情況。”
正道不通,張藝謀決心挖地道。他再次跑到北京,托親戚找到了畫家秦龍,進而認識了電影學院攝影系教授趙鳳璽。趙鳳璽將張藝謀推薦到西安電影制片廠,制片廠的領導欣賞他的才華,同意接收。不過,咸陽國棉八廠雖然同意他考學,但不同意他調離。
張藝謀沒有放棄,他再次托親友輾轉找到黃永玉和電影學院副院長吳印咸,并通過他們將自己的攝影作品和求學信轉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黃鎮。
黃鎮在批復中說:“我看了實在高興,他的作品很有水平,應加緊培養,可以作為特殊問題,以進修生或其他適當名義,允他入學深造。”[4]同時,黃鎮還在電影學院呈送文化部的草擬文件上批示:“根據他的優異成績,特殊處理。”
從6月1日到7月20日,從文化部到電影學院,各級領導就張藝謀入學問題,前后有不下十個重要批示。接到文化部函件后,電影學院仍不愿違背招生原則;文化部再次發函,請電影學院立即招收張藝謀。
最終的結果是,張藝謀如愿以償,被破格錄取,進入攝影系78班,學習兩年。
“在電影學院我是屬于那種埋頭讀書的類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縮,不張揚,也緊張,自己害怕,總是覺得有危機感,因為年齡、家庭出身、長期養成的習慣。在生活中,我從來不做太過分的事,盡量不去張揚自己,盡量低調……”[5]
曾任北京電影學院院長的張會軍回憶說,當時的史料顯示,電影學院當時并未讓張藝謀報名,也沒對他進行任何考試;只是同意其旁聽兩年,而后自謀職業。此外,學校不承諾發放文憑。
“當時我已經被折騰暈了。雖是破格錄取,但不知是正式生、旁聽生還是進修生。我也不敢問,怕把事兒給攪黃了。”[6]張藝謀回憶說。
學習滿兩年時,學院領導突然找張藝謀談話,商討其未來去向。張藝謀回憶說:“我當時沒心理準備,一聽這口氣,覺得繼續學習是沒啥希望了。”[7]準備離校前,張藝謀茶飯不思、坐臥不安,他對導演系的田壯壯說:“我這一走,以后永遠也見不著你們了。”[8]
張會軍是當時攝影系的班長,他把張藝謀學習刻苦、成績優秀的情況寫進報告,提交學校領導。后來,北京電影學院給張藝謀補辦正式的大學入學手續,就張藝謀繼續學習的問題再次請示上級。
后來文化部明確回復:“同意張藝謀繼續學習。”張藝謀終于獲得了繼續學習的機會,也拿到了他念念不忘的大學文憑。
從攝影、“影帝”到導演
大學畢業分配,張藝謀分配到廣西電影制片廠工作,還分到了房子。
1983年,張軍釗導演拍了《一個和八個》,張藝謀擔任攝影。這是張藝謀的第一部作品。《一個和八個》是“第五代導演”的第一槍。因為這部電影,張藝謀獲第一屆中國電影節優秀攝影獎。
《一個和八個》原為著名詩人郭小川的長詩,講述了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一位特殊的共產黨員的故事。這部電影與以往的主流電影不同,主人公不是單一的形象,“八個”和“一個”共同塑造了這部戲的靈魂。
《一個和八個》拍完,送到文化部審查時,剛好碰上當時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文藝界大批“人性論”,北京召開全國故事片廠長會議,《一個和八個》被當成“精神污染”重點批判。
時任廣西電影制片廠廠長的魏必達在會議上為電影辯護:“對于這批有事業心又勇于創新的青年人,應該關心和愛護,肯定他們的成績,有缺點和不足不要過多地指責,如有錯誤應當由廠領導承擔,由我作為廠長的來負責。”
十一個月后,1984年10月16日,《一個和八個》終于獲得通過。
魏必達在廠長會議上的發言,被西安電影制片廠的編劇張子良錄了音。張藝謀、何群和陳凱歌在西影的招待所,準備去延安拍攝《深谷回聲》(后改名為《黃土地》)。張子良把錄音帶放給他們聽,三人非常感動,給魏必達寫了感謝信。
在《黃土地》里,張藝謀通過攝影機展現了深邃遼闊的黃土地、奔騰洶涌的黃河、高高的天空,整部影片體現出來的壓抑自始至終緊緊地壓在觀眾心頭。作為攝影的張藝謀在這部片子里大展才華,也通過這部片子獲得了贊譽。
《黃土地》是陳凱歌和張藝謀第一次合作。陳凱歌導演、張藝謀攝影,這部電影一口氣獲了四項大獎:法國第七屆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獎、美國夏威夷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獎、瑞士第三十八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銀豹獎”、第五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攝影獎。
“在電影創作的過程中,我對天空的處理、對地平線的處理、對黃土的表達、對土地的描述,我覺得有一定的思想內涵。這是我們每一個去陜北的人都會有的體會,也是我在影片的攝影構圖中所要表達的主要感受。”
拍《大閱兵》時,張藝謀和陳凱歌經常發生爭執。張藝謀不想把自己的思維加入劇本,強勢的陳凱歌難以接受,兩個人不接受對方的想法,經常在攝影棚里爭執。《大閱兵》拍完,張藝謀和陳凱歌選擇分手,各自發展。
在《黃土地》采景時,張藝謀認識了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導演吳天明。當時,吳天明在米脂縣拍《人生》,張藝謀、陳凱歌、何群拄著拐棍到《人生》的外景地借錢。兩年后,吳天明要拍《老井》,請張藝謀當攝影。
吳天明想找一個真正的農民,演《老井》男主角孫旺泉,找來找去不滿意,就想到了張藝謀。張藝謀不敢演,最后吳天明再三游說,他才勉強同意:“是你讓我來的,我不想演戲,因為咱這戲沒人演了,所以我來,那演砸了我不負責任。”
張藝謀演《老井》,片酬五百元。
誰也沒有想到,《老井》大獲成功。張藝謀成為第二屆東京電影節、第八屆金雞獎和第十二屆百花獎的影帝。《老井》拍完,吳天明想把張藝謀調到西安電影制片廠,廣西電影制片廠不同意。吳天明把張藝謀妻子調到西安電影制片廠圖書館工作,還給他們分了兩室一廳的房子。張藝謀從此在西安有家了。
“在拍《老井》的過程中,張藝謀就給我看莫言的小說,他說他想拍電影,將來就叫《紅高粱》。”[9]吳天明回憶說。張藝謀在朋友推薦下看到了莫言的《紅高粱》,看中的就是高粱地里“這些男人女人,豪爽開朗,曠達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渾身的熱氣和活力,隨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快樂”[10]。
張藝謀把拍電影的想法和故事大概說了下,吳天明同意西安電影制片廠拍。《老井》做后期時,張藝謀就去了莫言老家,跑到山東轉了一圈,回來就要了四萬塊錢種高粱。
張藝謀抓住了第一次當導演的機會,一炮走紅。
《紅高粱》榮獲第三十八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還拿到了當年的金雞獎、百花獎、香港金像獎,一舉確立了張藝謀的導演地位,讓他成為第五代導演的核心代表。
張藝謀回憶說:“《紅高粱》在籌拍階段,就有人指責‘張藝謀在《一個和八個》里就歌頌土匪抗日,這個本子又是些土匪加妓女,色情加暴力’。”[11]等《紅高粱》拍完上映,又有人指責“《紅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渾渾噩噩,生命缺乏崇高感”。此前,還有人批評他和陳凱歌合作的《黃土地》“沒有跟上火熱的時代步伐,沒有正面表達沸騰的生活,而是展示了中國蒙昧落后的一面”[12]。
針對這些批評,張藝謀回應說:“電影首先是電影,拍電影要多想怎么拍得好看,不要先講哲學,搞那么多社會意識。我總覺得現在電影創作中‘文以載道’的傾向太嚴重,如果所有的電影都是關于民族命運、民族文化的思考,那無論是拍電影的還是看電影的,都要累壞了。”[13]
十年藝術片時期
因為《紅高粱》,張藝謀和妻子離婚,和鞏俐走到了一起,兩人開啟了長達十年的合作。《紅高粱》之后,張藝謀拍了槍戰類型片《代號美洲豹》。
“《紅高粱》拍的是農村,我就想拍一部城市題材的影片。”《代號美洲豹》很少被評論家提及,張藝謀自己也不愿意提:“那是個失敗的作品,我根本就不想拍,但最后還是拍了。這部電影確實拍得不好,完全是因為我不想拍,還不是我沒有發揮好的問題,它準備到一半我就想放棄,我找不到感覺。但那時候已經花了投資人九萬,不拍了怎么交代?然后我就硬著頭皮拍下去,劇本也是投資方給我找來的,我也沒用心拍,二十七天就拍完了,所以真的很差。”
有了這個教訓,張藝謀又掉頭拍農村。《紅高粱》還在后期剪輯當中,張藝謀就看中了劉恒發表在《北京文學》雜志上的《伏羲伏羲》,理由是《伏羲伏羲》的主題完全與《紅高粱》相反——《紅高粱》寫的是人性的活力和張揚,《伏羲伏羲》寫的卻是人性的扭曲和壓抑。
“如果說《紅高粱》表現的是沒規矩、沒王法,那么《伏羲伏羲》(《菊豆》)則寫那規矩把人逼到墻角,置人于死地。《伏羲伏羲》感動我的是劉恒原作中對中國人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對中國人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畫。”[14]張藝謀回憶說。
因為國內找的錢不夠,除了在“中影”拿的一百二十萬人民幣投資,張藝謀接受了日本電影制作人德間康快的一百萬美元的投資。當時的電影劇本叫《黑暗中的呻吟》,日本人覺得名字不好,電影拍完的時候,張藝謀才想好片名《菊豆》。
那時候拍電影基本上賺不了什么錢,從張藝謀到鞏俐、李保田,一天都只有十塊錢補助。拍了幾個月的戲,鞏俐掙的片酬都交給了中央戲劇學院的戲劇研究所,然后領每月一百多塊的工資。
《菊豆》讓張藝謀從攝影師成功轉型成導演。“《菊豆》對我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此之前,我還一直站在攝影師的角度,不太重視調動演員,不太重視挖掘人物內心,更注重電影的整體風格、造型和視覺沖擊力。”[15]
《菊豆》拿到了香港電影金像獎十大華語片和戛納電影節首屆路易斯·布努埃爾特別獎、西班牙巴利亞多利德國際電影節金穗獎和觀眾評選最佳影片獎,以及美國芝加哥國際電影節金雨果獎。
《菊豆》成為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第一部中國電影,一些批評者認為它刻意迎合西方觀眾的獵奇心理:“丟了中國人的丑、誣蔑了中國人的形象,張藝謀是想以此取悅外國影評人,想在國際影展中獲個什么獎。”
也因為這些爭議,《菊豆》雖然可以在國外發行上映,在國內反而未能全國發行放映。盡管電影在開頭標注著“中國二十年代某山村”,但依然未能避免張藝謀電影人生里遭遇到的第一個打擊。
現實是個陷阱,張藝謀于是把目光投向了歷史背景更模糊的蘇童的中篇小說《妻妾成群》。
這是個“新瓶裝老酒”的故事,描述封建社會里大戶人家一夫多妻的日常家庭生活。張藝謀看中的是蘇童與眾不同的歷史視角:“蘇童作品中有價值的是寫出了人與人之間與生俱來的那種敵意、仇視,那種有意無意的自相損害和相互摧殘。”[16]
因為用的是臺灣的年代集團的資金,侯孝賢成了這部電影的制作人之一。《妻妾成群》后來變成了《大紅燈籠高高掛》,在保留蘇童故事原貌的同時,張藝謀在電影中大量運用了紅燈籠這一象征性道具,它既成為男性威權的象征,也成為電影敘事的有效手段,讓幾個女性的命運和故事彼此有了聯系。
“我在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表現那種高墻大瓦,一成不變、堅固的東西對人造成的壓力和桎梏。點燈、封燈、吹燈、滅燈,我們加了很多的儀式。我覺得我們生活中有很多的東西,就像儀式一樣每天在重復,包括我們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這些形式感構成了一種象征性。可以說,這種象征隱含了我在那個年代的一種憂患意識。當時審查時,給我的電影下的一個結論是‘沉渣泛起’。”[17]張藝謀回憶說。
《大紅燈籠高高掛》再次獲得了奧斯卡外語片提名,并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十大華語片,還獲得了意大利第四十八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提名。
1994年,在《新民晚報》上發表的一篇名為《文學馱著電影走》的短文里,張藝謀很感激文學界對自己的幫助:“無數出色的影片和電視劇莫不是從小說改編而來,電影金字塔的最底下,那最闊大厚實的一層就是我們的文學了。文學馱著電影,走出了國門,走向了世界,讓世界了解了我們中國。”
《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還有《秋菊打官司》和后來的《活著》,這幾部電影分別是根據劉恒、蘇童、陳源斌、余華的小說改編的。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張藝謀還有許多買下電影改編版權,但最終沒有開拍的小說,比如格非的《迷舟》、賈平凹的《美穴地》和劉震云的《一地雞毛》。
1992年,張藝謀一改自己的風格,開拍一部與中國社會現實很近的電影《秋菊打官司》。“這個電影是我對自己的補課,以前的電影缺少對人物命運的關注,這次我要把精力和目標集中在人物的刻畫上。”[18]在張藝謀原來的構想中,由香港銀都機構投資的《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徹底的生活喜劇。但在開拍前,張藝謀把它改編成了一部紀實風格強烈的電影。原因是“秋菊一次次進城打官司,按照常規方法拍只是一個傳統故事,沒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和效果”[19]。后來,張藝謀決定用紀錄片的手法拍這部電影。
鞏俐出演的女主角秋菊挺著大肚子,扮演一個因丈夫挨村長的打罵而不服、層層上訪的農婦,操一口陜西方言,一邊吃飯一邊用袖子擦嘴巴和鼻子。《秋菊打官司》獲得了當年的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農婦秋菊”也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
電影局為張藝謀、鞏俐舉行了一個慶功會,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對該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電影中的“上級(法院)”給了秋菊一個說法,電影局也給了張藝謀一個說法,張藝謀此前被禁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也開禁公映,和《秋菊打官司》同年上映,形成1993年的張藝謀電影熱。
從此開始,“活著”就好
按照張藝謀的工作計劃,《秋菊打官司》之后,應該開拍王朔的《我是你爸爸》。當時定的主角是鞏俐和姜文。因為姜文準備拍《陽光燦爛的日子》,沒有空當,張藝謀放棄了這個電影。兩人這次合作未成,倒是為后來的《有話好好說》埋下了伏筆。
張藝謀最后開拍的是《活著》。
余華對筆者說,張藝謀最早看中的是他發表在《收獲》雜志上的《河邊的錯誤》。那是一個迷宮式的推理小說,張藝謀想把它改編成一個偵探電影。在余華家里,張藝謀想了解余華的其他作品,包括《收獲》給余華的《活著》的清樣。
第二天,張藝謀打來電話,說他改拍《活著》會更有把握。余華回答:“如果我來改編《活著》,會比改《河邊的錯誤》更容易。”
“張藝謀對我說過,一部影片只要有三場好戲就行了,而《活著》中有三十場好戲,電影受長度限制,當然就得割舍。這篇小說通俗易懂,敘述都是大白話,小學生也能讀。后來張藝謀說,他拍《活著》,要拍得就連民工也喜歡看。”余華回憶說。
“我不想拍一部政治電影,小說里中國人身上那種默默承受、那種韌性和頑強求生的精神讓我很激動”。在《活著》里,張藝謀放棄了以往電影的重造型、求氣勢,轉而追求樸實的藝術風格,請來了葛優和鞏俐主演“福貴”和“家珍”。
“福貴在大的時代變遷和大的政治動蕩中無能為力,當苦難屢屢降臨到他的頭上,他活下來唯一的信念就是讓自己活得更好。我覺得,在幾十年前的中國,在所有家庭的潛意識中,就是‘活著’兩個字。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都有這樣的精神經歷,就是活著,沒有任何想法——聽領導的,聽中央的,聽毛主席說的話,說什么都照做,不作他想。”張藝謀這樣談《活著》的創作。
《活著》在北京電影學院試映,看過電影的學者、評論家、影評人意見不一,有人稱“《活著》真正走出第五代導演自筑的巢穴,是張藝謀的一次自我突破”;也有人認為《活著》的敘事方式和電影表現手法有點回歸傳統,變成了謝晉,沒有期待中的進步。評論界對此有針鋒相對的觀點。
一直與張藝謀合作的文學策劃王斌目睹了《活著》的全部拍攝過程,他在《張藝謀這個人》一書中回憶說:“關于《活著》的主題,藝謀說,就是活著的還活著,死去的死了,說得再通俗點,就是‘好死不如賴活’。”
《活著》赴戛納參賽,獲得戛納評委會大獎及最佳男主角獎。因為電影背景的設定,《活著》最終未能在國內放映。張藝謀遭到兩年之內停止與境外投資方合作的處罰。
很多批評者都感嘆,假如沿著《活著》的路子繼續走下去,張藝謀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導演。但《活著》的遭禁,使張藝謀的電影選擇發生了改變。“張藝謀選擇了謝晉的團團作揖,為了他的電影事業能夠繼續活著。這既是他本人的選擇,也是被迫的選擇。”李劼說。
“我不是一個能勇敢地站起來和別人斗爭的人。我們這個國家很大,事情很多,也不是你一個人斗爭得過來的。惹不起總躲得起吧,我只能采取躲的態度。這也不是誰跟誰妥協的問題,我知道我必須接受某種現狀。在我現在的處境之下,我不能再找一個敏感的題材。”[20]
張藝謀意識到,如果不做出調整和選擇,他就只能從此沉寂。
“《活著》一直沒上映,我想短期內也不會上映。作為一個導演,如果你的作品中國人長期看不到,我相信是很失落的,我不能接受這情況。”[21]張藝謀做出的調整是拍巴金兒子李曉的小說《幫規》。“這個題材跟政治無關,離現代社會距離也很遠,它寫的是人的故事。”[22]《幫規》后來改名為《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是一個徹底的黑幫類型片。崔衛平說:“在某種意義上,這部影片的確體現了制作者經歷了挫折之后的某種收斂——盡管是有關‘黑社會’題材,但最后卻要‘漂白’它,將它表現為一個‘人的故事’。”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是張藝謀的第一部商業片,張藝謀后來對它的評價是“不及格”。因張藝謀對上海文化的陌生,這部黑幫片并沒有獲得商業上的成功,鞏俐在片中飾演的小金寶也未得到觀眾的認可。這回媒體不批評他展現陰暗面了,轉而批評他“把舊上海的浮華演變為黑幫的廝殺,在偷情和活埋之間,隱藏著權力爭奪和人性的陰暗”。
“我不能接受電影被人看不到”
“時代變了,進入另一個時代了,是所有人慢慢開始(變),并不只是我。”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拍完,張藝謀和鞏俐分手,和張偉平成立了新畫面公司,合作了十年。
1990年的春節,張偉平和張藝謀在一個朋友張羅的飯局上認識了。當時張偉平做的是“藥品代理、航空食品配送,偶爾也投資點房地產”。那次的聚會完畢,因為順路,張偉平開夏利把張藝謀送回了家。
一路上兩人聊得很投機,分手時又各自留了電話。過了十天,鞏俐給張藝謀打來電話,張偉平順便請鞏俐和張藝謀來家里吃飯,就這樣開始你來我往,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1995年,張藝謀準備拍《有話好好說》,不料投資出現問題。有一天,張藝謀見一個投資商,看見面時間早了點,他便去了張偉平家。張偉平見張藝謀悶悶不樂,寬慰著說“實在不行就我投吧”。張藝謀眼睛一亮,問:“真的?”張偉平點頭說:“再過一個禮拜,如果投資還沒有到位我就投。”兩個星期以后,張藝謀資金還是沒找到,只好給張偉平打了電話。
張偉平停掉了手上做的地產項目,劇本也沒看,就打了兩千六百萬到張藝謀指定的賬號上。“當時藝謀還跟我說電影跟你的房地產不太一樣,這個要是投砸了就剩拷貝了。”張偉平聽了也沒往心里去。
今天來看,兩千六百萬不是一個大數目,但在1995年的電影圈,那絕對是一個大制作。《有話好好說》的主要投入花在演員片酬上,無論是姜文、李保田,還是李雪健、葛優、趙本山,都是當時的一線明星。
電影拍完了,張藝謀找到張偉平,說電影開始剪片了,得想發行的事了。對電影一竅不通的張偉平不知道電影怎么賣,找了幾個發行商,幾個回合下來,國內外的版權都賣給了保利的董平——國內版權賣了八百萬,國外版權兩百七十萬美金。
滑稽的是,《有話好好說》上映時,張偉平在電影院里看到,電影屏幕上在制片人后面寫的是張衛平。張偉平不想賺錢,只想把兩千六百萬的投資拿回來。結果《有話好好說》國內票房達三千多萬,是那一年的票房冠軍,但國外版權在董平手上放了半年多,卻一直沒有賣掉,最后還給了張偉平,砸在了手里,放到了現在。
《有話好好說》讓張偉平賠了一千八百萬,也弄清了電影是怎么回事。張藝謀很內疚,覺得自己連累了朋友。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來,兩人討論來討論去,覺得應該把命運放在自己手上,干脆成立了專拍電影的新畫面公司。
1997年,一心想給張偉平挽回損失的張藝謀,一口氣拍了《一個都不能少》和《我的父親母親》。這兩個電影沒有用大牌明星,卻分別拿到了柏林電影節的銀熊獎和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
沒想到戛納電影節參賽名單公布以后,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布公開表示,非常喜歡《我的父親母親》,不喜歡《一個都不能少》,認為張藝謀“替政府做宣傳”。
1999年4月18日,張藝謀通過媒體公開了他寫給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布的信,信中說,他準備撤下已經送去的兩部參賽影片《一個都不能少》與《我的父親母親》。“一部電影的好與壞,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對于中國電影,西方長期以來似乎只有一種‘政治化’的讀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類,就列入‘替政府宣傳’一類。以這種簡單的概念去判斷一部電影,其幼稚和片面是顯而易見的。”
張藝謀再次成為國內媒體的熱點,他的公開信成了新聞,上了中央電視臺,《北京青年報》刊發評論說:“此次曾屢獲國際大獎的張藝謀對戛納說‘不’,是中國電影人公開對某些西方人‘意識形態偏執’的公開挑戰和明確回應。”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則把這起事件看作是“張藝謀的退場秀”:“雅各布讀不懂那封信,那主要是寫給中國人看的,張藝謀要用這封信把自己的罵名和惡名聲洗刷干凈——顯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態度。”
事隔多年,張偉平揭開了風波后的內幕:“當我們聽說雅各布對《一個都不能少》的意見后,我們曾努力做過工作,張藝謀致函說明情況并沒有消除雅各布對影片的政治評價。另一部影片《我的父親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才再次參評。”結果,雅各布個人表示“非常喜歡《我的父親母親》”,并希望張藝謀撤出《一個都不能少》,以《我的父親母親》來替代。后來,“張藝謀非常氣憤,這才公開正式聲明將兩部影片同時撤出”。
為打擊盜版,當時國家版權局還為《一個都不能少》下發了版權保護通知,這是中國第一次對國產影片的版權實行“紅頭”保護。
張藝謀后來把兩部影片送去另外兩個電影節,《一個都不能少》拿到了當年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我的父親母親》拿到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
當《一個都不能少》在威尼斯電影節上獲獎時,張藝謀站在大廳里接受記者采訪時很感慨:“在中國拍電影難免會有各式各樣的政治原因,外國人選擇從政治角度看中國電影,這是文化的偏差。我把電影從戛納撤回這事很正常,我用一種比較公開的方法表達我自己的觀點,電影允許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一個都不能少》投了一千兩百萬,后來九百萬賣給中影,加上國外收回來三百多萬;《我的父親母親》投資一千萬,國內票房八百萬,我們收回來三百多萬,加上國外收回了五百多萬,略虧;《幸福時光》投了一千萬,電影既不文藝,也不商業,票房很不理想。”張偉平對筆者回憶說。
[1]引自方希《張藝謀的作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33頁。
[2]引自黃曉陽《印象中國:張藝謀傳》(華夏出版社,2008年),第35頁。
[3]引自《張藝謀的作業》,第17頁。
[4]引自張會軍回憶文章《張藝謀1978年被破格錄取始末:文化部部長親作批示》。
[5]引自《印象中國:張藝謀傳》,第35頁。
[6]引自《張藝謀1978年被破格錄取始末》。
[7]同上。
[8]引自《張藝謀1978年被破格錄取始末》。
[9]引自吳天明口述《吳天明:開掘中國新電影成長沃土》。
[10]這是張藝謀對選擇拍《紅高粱》的解釋,轉引自張小虹《〈紅高粱〉中的女人與性》。
[11]引自羅雪瑩對張藝謀的采訪,《〈紅高粱〉導演訪談錄》。
[12]引自郝建評論文章《〈黃土地〉:打起紅色腰鼓,第五代出場》。
[13]引自羅雪瑩《贊頌生命,崇尚創造——張藝謀談〈紅高粱〉創作體會》,《論張藝謀》(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年),第169頁。
[14]引自李爾葳《張藝謀說》(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7頁。
[15]引自魏龍、柯北《謀天下》(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年),第78頁。
[16]引自《張藝謀說》,第23頁。
[17]引自王世軍評論文章《總結“對張藝謀的罵”:究竟誰是“文化怪物”?》。
[18]引自《張藝謀說》,第49頁。
[19]引自《張藝謀說》,第36頁。
[20]引自《張藝謀說》,第121頁。
[21]引自《張藝謀:電影導演工作與電影制作》,張會軍采訪。
[22]引自《張藝謀說》,第12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