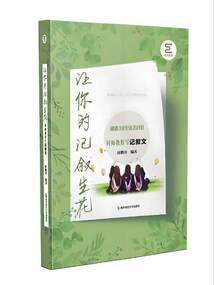
讓你的記敘生花:時師教你記敘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技法篇 1.文體特征
第1章 技法篇 1.寫什么就應該是什么
——文體特征
《2019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說明》的“寫作”部分沿襲了近年的一些說法,仍然把作文考試的要求分為基礎等級和發展等級——雖然近年很多省市的高考作文評分已經不再按照這兩個等級給作文分別判分了。
在“基礎等級”的六條要求中,“體現文體特征”赫然在列。
隨著作文閱卷時確定一個“基準分”的通行做法(比如江蘇,很多年內,總分70分的作文往往會在50分上下確定一個分數,作為某次作文閱卷的“基準分”)的廢止,作文判分實行了“六類”“五類”“四類”判分法。
比如江蘇,把70分的作文切分為“六類”(63分以上為一類卷,56分以上為二類卷,49分以上為三類卷,42分以上為四類卷,28分以上為五類卷,27分以下為六類卷)。
比如上海,把70分的作文切分為“五類”(63分以上為一類卷,52分以上為二類卷,40分以上為三類卷,21分以上為四類卷,20分以下為五類卷)。
比如河南,雖然采用的是“全國卷1”,但是把60分的作文切分為“四類”(49分以上為一類卷,36分以上為二類卷,25分以上為三類卷,25分以下為四類卷)。
在這種“六類”“五類”“四類”判分法風行的背景下,“體現文體特征”顯得尤為重要。說得明確些,就是“基準分”判分法下,閱卷人會圍繞“基準分”適度上浮或下調賦分,不會輕易給極低分;而新的判分法明確了“類”,閱卷人會把你的文章歸到“六類卷”(“五類卷”“四類卷”)而很少會有心理障礙。
就是一些按照“基礎等級”(分為“內容”和“表達”二維,各20分)和“發展等級”(“特征”,20分)判分的省市,“表達”的20分中,有文體、結構、語言、字跡四個考量的維度,“一等”“二等”都要求“符合文體要求”,而且列在第一位。
足見,“文體特征”(“文體要求”)在寫作中的重要性。
那么,記敘文這種文體有哪些“特征”呢,或者說,寫作記敘文這種文體需要滿足哪些“要求”呢?
這是一個宏大命題。
但是,我們可以簡而言之。
所謂記敘文,可以概括為三句話:一是講故事。二是藝術地講故事。三是講有意義的故事。
講故事,強調的是記敘文的情節性。
初中階段寫的是簡單的記敘文;對高中生而言,應該在初中階段寫簡單記敘文的基礎上升格,寫比較復雜的記敘文。簡單還是復雜,情節是主要的決定因素。
記敘文真正的中心是人,“只有把人放到動態發展的人生中去,放到人的歷史性展開的過程中,才能展示人的豐富生動的性格”。這,和議論文中用二三事的例證法寫人是不同的。在議論文中作為例證的敘事片斷,只要交代人物做過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文字必須盡量簡省,定向敘述,不枝不蔓;而記敘文中不但要寫出人物做了什么,更需要表現人物如何去做,要寫出過程,寫出動態。要寫出“我”看到了什么(動態),看到的東西在“我”心里引起了什么反應(動態),“我”的行為又引起了別人的什么反應(動態)。
一言以蔽之,很多的記敘文都是“現在進行時”。當然,進行的方式最好是有別于“直線式”的那種“波浪式”,曲徑通幽,回環蘊藉。“文似看山不喜平”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情節性可以表現為縱向的歷時性,比如,《私家車詠嘆調》(見本書“佳作篇”之“高考篇”之“佳作”18;此后一律簡化為:“佳作”XX),讀者諸君可以閱讀以加深認識。
也可以表現為某個節點的即時性,比如,《握住我的手》(“佳作”53)。
還可以表現為類似于影視的閃回法,比如,《拜謁貝多芬》(“佳作”10)。
藝術地講故事,強調的是記敘文的技巧性。
古代的說書藝人總是善于在故事的推進過程中“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做到張中有弛;總是善于在故事推進到最關鍵處以“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戛然而止:這就是有技巧。
我們講故事的技巧有很多方面可以講究。
比如全篇結構上的倒敘。先把高潮部分呈現給讀者,把結果推到讀者面前,然后再娓娓道來。
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堪稱經典:先寫祥林嫂之死,然后才是對祥林嫂一到魯鎮、二到魯鎮的經歷的敘寫。
本書的《突圍》(“佳作”60)也是以倒敘開篇的:
“啪——”一個巴掌再一次打在了我的臉上,一個讀高三的女孩子的臉上!我與父親之間的那堵隔墻再一次被加固,固得不可動搖。
比如敘事視角上的“非人化”。下筆的時候,不一定都從定勢思維出發,用人的視角敘寫事情的前后過程,其實還可以用動物視角、植物視角、礦物視角、器物視角等來敘事。
高考佳作中,運用此類技巧的比比皆是:
2004年江蘇高考“山的沉穩,水的靈動”(“典題”40)推出的佳作《我的自述》就是以“我叫歡歡,是張局長家的狗”開篇的;2007年江蘇高考“懷想天空”(“典題”39)推出的佳作之一就是以“我是一只豬”開篇的;2017年全國卷2“中華名句”(“典題”8)推出的《如你在遠方》(“佳作”11)就是以“我是一只羊,終日無所事事、平平淡淡地生活著”開篇的;2018年北京高考“綠水青山圖”(“典題”6)推出的佳作之一就是以“我是一條小魚”開篇的。
2008年江蘇高考“好奇心”(“典題”36)推出的佳作之一《好奇心》(“佳作46”)就是以“我是當年武則天立下的那塊無字碑”開篇的;2017年江蘇高考“車來車往”(“典題”12)推出的佳作之一《綠皮火車的成長道路》(“佳作16”)就是以“我,是一輛綠皮火車”開篇的;2019年天津高考“三位名人說愛國情懷”(“典題”3)推出的佳作《我是一棵麥子》(“佳作”5)就是以“我是一棵麥子,一棵不起眼的,生長于清朝末年的麥子”開篇的。
“日常篇”中的《前行的“宸輿”》(“佳作”58)就是以“我是一只輪胎,曾經屬于一部農用大車,而今孤零零地蜷縮在屋子的一角”開始敘寫的。
比如過渡的技巧。一直非常欣賞著名作家吳伯簫的側重寫人的名篇《獵戶》中的過渡性文字。開篇交代了行文線索:“正是大好的打獵季節。我們到紅石崖去訪問打豹英雄董昆。”再看看隨后的這些句子吧:
“我想:董昆是什么樣子呢?可像家鄉的尚二叔?”
“咱們先繞道去望望‘百中’老人吧。”
“場長說:‘走吧,老人跟董老大最熟,說不定到紅石崖去了呢。’”
“可是又不巧,踏上紅石崖,不但‘百中’老人沒有來,就連董昆也到縣城領火藥去了。”
“這時候倒真巧了,我們在林牧場木柵欄門跟前,頂頭遇到一位彪形大漢。我們幾個人不約而同,都冒叫了一聲:‘你是董昆同志吧?’寬肩膀,高身材,手粗腳大,力氣壯得能抱得起碾滾子,——貌相跟傳說中的打豹英雄這樣相似,不是他該是誰呢?”
就在這樣的文字里面,你幾乎可以把全篇的內容都串起來。
比如伏筆、照應的技巧。還是說《獵戶》吧。文章第二節有這樣的文字:“深秋的太陽沒遮攔地照在身上,煦暖得像陽春三月。”最后一節如此這般:“天晴了。很好的太陽。”
至于講有意義的故事,強調的是記敘文的思想性。
都知道“文以載道”的道理,雖然不同時期的“道”內涵不一甚至迥異,但是對“道”的意識與表達是每一個作者心中所念。而今有個時髦的詞匯:“正能量。”在我們的寫作中,我們也希望同學們能夠通過你的筆傳遞出“正能量”。
當然,如何表達你想表達的“意義”,還是有講究的。如果是從考場作文的角度來看,著者以為不宜含蓄,可以在行文過程中有所流露,也可以在即將結束的時候直道其詳。畢竟,快速閱卷的機制決定了我們不能像作家們的文學創作一樣追求藝術性,追求含蓄;因為這可能會讓我們的匠心被閱卷者疏漏掉,而且這樣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