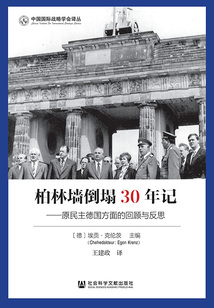
柏林墻倒塌30年記:原民主德國方面的回顧與反思
最新章節
- 第17章 漢斯·莫德羅:起點與終點[1]
- 第16章 埃貢·克倫茨:民主德國的淪亡是蘇聯崩潰的分[1]
- 第15章 亨寧·施萊夫:對民主德國鄉鎮體制的反思
- 第14章 弗里德里希·沃爾夫:時代轉折與階級斗爭
- 第13章 埃克哈德·利貝拉姆:一個發達工業國的社會主義起跑
- 第12章 赫伯特·格拉夫:對民主德國從成立到被摧毀的內部和外部原因之反思
第1章 譯者序
2019年11月9日是柏林墻倒塌30周年。
本文集的編選者是原東德統一社會黨最后一任總書記克倫茨。
本文集的15位作者大都是東德黨政軍領導同志,平均年齡為85歲。其中年齡最長者是曾經為昂納克總書記、莫德羅總理、施特雷利茨總參謀長等領導人擔任過辯護律師的97歲的沃爾夫大律師;最年輕的原東德羅斯托克專區第一書記佩克也已經71歲了。他們留下的反思文章,彌足珍貴。
本文集緣起于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2017年9月,克倫茨總書記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與佩克同志一起訪華,出席第八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恰逢中共十九大召開。訪問期間,所到新鄉、寧波、金華、義烏、溫州、重慶等地,克倫茨一路上非常認真地學習和品味中共十九大報告,非常仔細地考察和體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變化,并且不無痛苦地聯系當年東德社會主義失敗的教訓,每天用隨身攜帶的平板電腦記錄了很多數據和感想(回國后寫下了《我看中國新時代》一書,2019年8月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在陪同訪問期間,我們在交談中逐步形成一個共識,即利用2019年11月9日柏林墻開放(東德老同志忌諱“倒塌”這個詞)30周年的難得契機,動員仍然健在的東德黨政軍老同志寫一些反思文章,翻譯出版一本中文版紀念與反思文集。
克倫茨回到柏林后,很快向14位黨政軍老同志發出群發信件,請各位原政治局委員、黨中央和政府部委領導以及專區(相當于省一級)黨委領導同志從各自的觀察角度,每人寫一篇5~15頁的反思文章。2018年上半年,各位老同志紛紛發來了稿件。
克倫茨總書記曾經寫過很多反思東德社會主義失敗的文章,此次因為忙于撰寫關于蘇聯與東德關系的新書而沒有另外撰文,于是委托我幫他編選。我特意把他為《89年的秋天》一書2009年再版時所寫的“前言”選出來,作為本文集的“代前言”,還選入了他2016年出席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世界社會主義論壇時的主旨發言稿《民主德國的淪亡是蘇聯崩潰的一部分》。
由于某些原因,克倫茨總書記約稿時沒有邀請東德最后一任統一社會黨籍總理莫德羅。為了求得本文集的觀點平衡,我在征求克倫茨同意之后,選入了莫德羅總理《起點與終點》一書的節選稿。莫德羅當年是黨內的“改革派”,曾經被昂納克總書記長年排擠在政治局外。此書是他在兩德統一后撰寫的第一部政治回憶錄,出版于1991年。《起點與終點》一書中多處點名批評克倫茨在關鍵時刻軟弱寡斷,觀點十分尖銳。我將該書的主要內容約五萬字選編出來,列在本文集末尾,幫助讀者全面審視1989~1990年驚心動魄的歷史演變歷程。
在翻譯反思文集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這些政治老人的觀點對我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有著重要的、現實的借鑒作用。
感謝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文集得以在兩德統一30年之后不久面世。
在翻譯和編輯本文集時,有兩個措辭需要做出解釋:(1)原東德的老同志一般不使用“東德”(Ostdeutschland)這個詞,而是堅持使用“民主德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DR),簡稱“民德”;(2)老同志們不愿意使用“柏林墻倒塌”(Mauerfall)這個概念,而是堅持使用“打開邊境”或“開放邊境”的說法。本文集在翻譯過程中尊重老同志的選擇,一律照譯。但我在“譯者序”中采取超脫的做法,并不忌諱“東德”和“柏林墻倒塌”等習慣用法。
還有一點要特別指出:我的多年好友、82歲的原國防部部長霍夫曼海軍上將,克服癌癥病痛堅持寫下將近9000字的稿件,交稿不久便于2018年11月溘然長逝。另一位好友、82歲的東德最后一任駐華大使羅爾夫·貝希托爾德,則在稿件完成之前就因癌癥晚期亦于2018年11月病逝。在本文集付梓之際,特意向他們的在天之靈遙寄感激之情。
王建政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
2019年6月5日 于上海崇明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