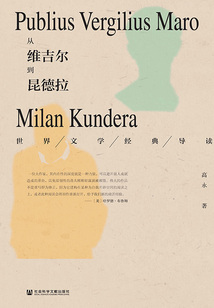
從維吉爾到昆德拉:世界文學經典導讀
最新章節
- 第12章 對存在的詩性沉思——昆德拉的小說創作
- 第11章 孤獨還是內心的狂歡——井上靖的《獵槍》
- 第10章 “徒勞”:作為一種生命狀態
- 第9章 書寫生命的詩行——葉賽寧的詩歌世界
- 第8章 用同情的眼光審視世界——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 第7章 文學作為一種精神自傳——契訶夫與他的《牽小狗的女人》
第1章 緒論 透過文學的望鏡探索精神世界——以哈羅德·布魯姆的經典閱讀論為中心
數年前,在天津某高校舉辦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高峰論壇”上,一位教授的一句話——“文學是用來拯救世界的”——在與會學者中引起的不只有贊同的掌聲,還有一些不易察覺的不屑和嘲笑。這是當前文學的價值和經典的意義正在遭受質疑的一種表現。在一些人眼中,文學之用只在于利益的獲得,而文學研究僅是一些人的“稻粱謀”罷了。
尼古拉·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Despreaux)說,寫作或者說文學創作是最危險的一行。這一行不相信平庸,“平庸就是惡劣,分不出半斤八兩”,所謂“無味的作家就是可憎的作者”,“一個瘋子倒還能逗我們發笑消愁,一個無味的作家除討厭一無是處”。[1]這樣說,并不意味著要讓所有的作家都成為一流作家,或要求所有作家都能成為莎士比亞、歌德、卡夫卡、曹雪芹、魯迅,而是說文學創作者該有一種創新的意識與沖動,努力使自己的個性得到彰顯。可能受個人天分、才力,以至客觀條件等原因的限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可以揚名立萬,成為大作家、名作家,但作家應有一種內在的充盈,并借此對抗個人條件的有限和現實的束縛。無論是努力使自己成為一位個性作家(體現在創作和思想中,不是生活中),還是面對現實處境保持獨立的品格,都需要一種精神的充盈,需要保持對人性深入探索的熱情與耐心。
文學關注人的精神世界,關注人的靈魂或內宇宙,文學創作就是要去探索人類最深層的需要,探索人類的內在精神,這是文學最大的價值和最重要的意義:“不錯,文學不會令你賺百萬!文學本來就是無用的,但是一個人的生命中沒有文學的話,總會覺得少了點東西,特別是在你成年就業,當了大經理或賺了一百萬以后。文學可以不作為專業,但它是大學人文教育必備的一環,一個大學如果沒有人文教育也決不會是一所好大學。”[2]這是深諳文學之本質的洞明之見。讀到李歐梵的這段話時,我們不得不把欽佩之情獻給這位“狐貍”型學者。“精神”“生命”這樣的字眼是多么不合時宜,多么不與時俱進——與功利盛行的當今社會多么不合拍,正因如此才更能說明文學的不可或缺與文學經典價值的不容否定。
一 文學何用與經典的價值
2011年,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出版力作《影響的解剖》,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文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所標示的那樣,布魯姆一生堅持他的“文學之愛”。對他而言,“莎士比亞就是律法,彌爾頓就是教義,布萊克和惠特曼就是先知”[3]。也就是說,文學在布魯姆那里已然上升到了宗教的高度,是與人之內在精神世界直接相關的存在。但就是這個布魯姆在寫作《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書時,先為文學經典唱了一曲悲歌,最后又給全書加上了一個“哀傷的結語”:“我在一所頂尖大學教了一輩子的文學以后,反而對文學教育能否渡過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4]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文學經典正處于怎樣的歷史環境之中。
眾所周知,隨著現代傳媒方式的發展,視覺盛宴沖擊著人們的眼球,快餐文化成為大眾的精神食糧,嚴肅文學早已失去了其在19世紀的強力。像布魯姆那樣的知識人越來越多,他們哀悼文學之失落,進而為文學家的邊緣化鳴不平,時時發出不平之聲。他們內心不平是可以理解的:文學的被邊緣化已成為關涉文學發展前途,甚至是關系其生死存亡的大事。懷疑甚至否認文學價值的聲音不是正甚囂塵上嗎?文學經典的意義不是正經受前所未有的考驗嗎?
據說文學已經死了,那么我們對此應抱有什么樣的態度呢?布魯姆在這個問題上不經意間陷進了一個自己設置的陷阱:他堅持認為應該排除一切從社會文化學角度對經典進行解讀的方式,應堅持審美化的閱讀與闡釋,使文學回歸文學自己的領地。但誰又能否認,這種文學的回歸帶來的必然結果就是文學失去其以往的輝煌與強力(那份輝煌與強力,不正源于文學承載了太多它不應承載的東西嗎),退到人們視界的邊緣呢?這不正是文學本身應該得到的待遇,也是最好的待遇嗎?這不正是布魯姆本人一再追求的嗎?那么,“經典的悲歌”又悲從何來呢?
從事文學研究和在大學中教授文學的教師遇到“文學有什么用”這樣的問題,再正常不過了。正確的回答也許應該是:當你問這樣的問題時,你已經錯了,因為你沒有弄明白文學作為人文學科的特性。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本就不應用功利的眼光去看待,用功利的標準去衡量。布魯姆在他的《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書中曾說過:“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荷馬或但丁,喬叟或拉伯雷,閱讀他們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進內在自我的成長。深入研讀經典不會使人變好或變壞,也不會使公民變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靈的自我對話本質上不是一種社會現實,西方經典的全部意義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獨,這一孤獨的最終形式是一個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5]閱讀文學經典并非為了使人變好或變壞等功利目的,文學經典關注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一種社會現實,即與現實功利無關。事實也的確如此,相對于自然科學而言,文學不會直接創造價值,因為文學從根本上關注的是人之精神世界。如果非要賦予文學一個功利化的目的,以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話,那么,關注精神就是它的最終目的。“文學無用,文學有大用”,這句看似矛盾的話,實際上就是文學存在的最大意義:文學讓我們看清人性最深層的東西,讓我們看清人的本質,讓我們看清人之存在的狀態。西方文學自基督教產生以來,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一種基督教文學或反基督教文學。人與神的關系問題,對信仰的關注不正是對人本身的關注嗎?而信仰問題,不正是人之存在的一個本質性問題嗎?諾曼·N.霍蘭德(Norman N.Holland)曾言:不存在神的視野,我們永遠不能遷出自身之外。如果人不能遷出自身之外,人又如何自知呢?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樣說,并不是要大家都去信神,而是要讓大家明白,是文學,是人文學科幫助我們對信仰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認知,信仰問題無論如何都是大問題,全世界現在的地區沖突從根本上說不都是信仰的沖突嗎?
文學說到底是人學,對人的認知,就是它最大的意義。而那些所謂直接創造價值的學科,如果失去了對人的觀照,那就不會有任何意義與價值,甚至會走向反人類的歧途。在當前這個科學理性(本質上是“工具理性”)統攝一切、實用功利思想甚囂塵上的時代,文學等人文學科的價值就顯得更為突出了。多年前,有一部成龍主演的電影《神話》,這部影片雖然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有抄襲《古今大戰秦俑情》(張藝謀主演)的嫌疑,但它仍值得我們去欣賞,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表現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沖突,看到了自然科學如果失去人文精神的觀照,便有走向歧途的可能。
文學與精神相關,文學創作說到底是一種精神書寫。那么作為創作主體,作家和文學研究者的精神現狀如何呢?他們又應抱有什么樣的精神旨趣呢?
二 智識精英的當下處境
現化性的陰謀之一:讓每個人的生活都變得面積很大,而高度很低,扁平而不是豐滿。于是一切深入靈魂的探索都不再顯得必要,智識精英的最大價值——深入認知、不斷反省自身以至整個人類的精神世界——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智識精英不再是英雄,他們被體制化地排擠到了社會邊緣。
在平等、民主、人權的大旗下,精英主義在當今社會廣受詬病。事實上,平等、民主、人權并不是反對精英的理由,這并不是一道單項選擇題,正如英國學者巴特摩爾(Tom Battomore)——雖然他是某種意義上的反精英主義者——指出的那樣: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恰當地處理公眾與精英之間的關系。真正的民主是“使大多數公民,即使不是全體,能夠參與社會問題決策的條件”,并“最大限度地縮小精英與群眾間的差別”[6],而不是置這種差別的客觀性于不顧。真正的平等“是指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全面發展他作為個人在與他人無拘無束的交往中所具有的聰明才智”[7],而不是以喪失或降低標準為代價,換取虛假的平等。此外,我們還應該清醒地看到,在向精英主義發起的諸多進攻中,大眾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而只是某些“權力”的工具,精英只是“權力”為獲取公眾支持而找到的標靶。
有兩種左右社會思想主潮的思想傾向,正合力排擠精英與智識。其一是打著平民主義的旗號反對精英、反對智識。將精英視作反民主、反人權、反平等的洪水猛獸,推崇智識、抱有偉大理想、為社會與個人設定高標準則被貶為“不合時宜”;其二是不遺余力地制造另一種“精英”,用物質財富代替智識的中心地位。當今,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物質財富的代名詞,于是暴發戶成為受尊重的對象;依靠各種非正常手段(所有的手段都包括,只是不包括個人的智識和精神意志)搏取出位的娛樂人物成為“英雄”。無論其身份與地位是靠什么換來的,只要能將寶馬車的方向盤握在手中,就可以成為“寧可坐在寶馬車里哭泣的女孩”的白馬王子,哪怕這“馬”上坐的不是王子。當然,智識精英身處尷尬境地的情況不是今天才出現的。
當年,梅列日柯夫斯基(Dmitri Sergeevich Merezhkovsky)以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的經歷為例,向我們證明,俄國知識分子的處境從來就處于兩種壓迫之間:一方面是專制政體,一方面是黎民百姓。劉小楓就此指出,“處于兩種壓迫之間,與其說是俄羅斯知識人、毋寧說是知識人這號人的普遍命運:在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夾縫中生存”[8]。這樣的判斷基于一個簡單的前提:專制政體(推而廣之是國家)與人民大眾之間的二元對立。知識人處于二者之間,無論是獻身于拯救民族(國家)的事業,還是獻身于人民,其實都是對自己本位的拋棄。劉小楓進而認為,在專制政體下,有教養的人雖然被夾在統治與被統治的兩極中間,但因為兩極之間的差序格局空間還相對寬敞,“有教養的人也還有自己精神生存的回旋余地”[9]。而在現代社會,民主政治的興起使這種回旋余地幾近喪失。在這樣的境況下,梅列日柯夫斯基認為,知識人就會變成“未來的無賴”。“未來的無賴”在俄羅斯會因階層不同,形成不同的三張面孔:即將替代傳統君王專政的實證主義專制、繼續“向神授的君主報恩的東正教”和“三張面孔中最可怕的一張面孔”——“流氓階層、流浪者、刁民”。針對“未來的無賴”的三張面孔,梅列日柯夫斯基提出用“精神高貴”的三要素——身體、靈魂、精神——與之對抗。其對抗策略是:“活生生的肉體對抗大地和人民、活生生的靈魂對抗社會、活生生的精神對抗知識分子。”[10]
劉小楓認為,梅列日柯夫斯基依持圣靈降臨抵制現代性的實證形而上學庸眾和民主主義的價值顛覆,從而“擺脫了現代的種種‘主義’、擺脫了糾纏俄羅斯知識人近兩百年的西化—斯拉夫化的對立,看到知識人作為精神守護者面臨的真正生存抉擇:高貴抑或低劣甚至下流”[11]。
梅列日柯夫斯基的宗教—政治批判當然與當時俄羅斯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有關,也與梅列日柯夫斯基本人特異的個人精神追求有關,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為面對現代性擠壓的現代知識人提供了一條至少是可供選擇的道路——退歸內在世界,做精神的守護者。
事實上,我們當前面臨的文化與精神危機,并不比梅列日柯夫斯基當初面對的危機更樂觀。如果我們還承認,除了現世的功利訴求,人還需要一種超越性的內在豐盈,以安慰人之虛無宿命帶給我們的無力感的話,那么,這樣的安慰在今天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種末日的危機感正籠罩著我們,這樣的末日預言與其說是一種可能的現實,不如說是一個“心靈寓言”——人類無時無刻不對前途充滿質疑、焦慮與恐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為《2012》那樣的電影叫好。它最大的成功也許就是利用了這種“心靈寓言”,洞悉了人們內心深處最脆弱的東西。如果說人類精神史中時有發生的末日恐懼還主要是一種宗教情緒的話,那么我們今天對末日的恐懼,與其說是來自我們對世界終點的憂慮,不如說是源于我們對當下人類現實處境與精神狀態的憂慮。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緊張、人與人之間情感的淡漠、個人對自我存在價值的質疑以至否定,這一切使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或如行尸走肉,沉溺于物欲或情欲的死水中無從逃脫,雖生猶死;或沉浸于絕望的黑暗之海,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光亮,悲觀主宰著一切;或被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所掌控,為某種意識形態式的狂熱而歡呼。所有這一切都可以歸結到整個社會的物欲橫流。
秉持精英主義文學立場的表現形式很多:審美性、天才論、競比性等。但這樣的立場在文化多元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早已成為眾矢之的。文化多元主義者去精英化的一個重要表征是否認文學的審美自主性,他們要做的就是將原本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學趕下神壇,這是一個“文學祛魅、經典祛魅、崇高祛魅”的過程。文學淪為文化研究的工具,淪為意識形態、政治、道德宣傳的手段,此時的文學還是文學嗎?經典還是經典嗎?
在這樣的背景下,布魯姆不僅秉持精英主義文學立場,大張旗鼓地為其辯護,還向文化多元主義者奮力拋出自己的匕首投槍。這份勇氣,足以令人驚嘆,這樣的批評個性足以令我們肅然起敬,畢竟個性是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生命,是其得以探索精神之海的航船。如果我們還對文學抱有一絲敬意,如我們堅信文學具有使人認識到此生有超乎想象的意義和價值,如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所認為的那樣:“我認為文學作品有啟迪價值。我的意思是,這些作品使人認識到此生有超乎想像的意義。”[12]那么,布魯姆的堅守就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晚年布魯姆所指出的那樣,文學與生命是同構的。文化研究關注的是身份、立場、差異,在這種研究中,文學的生命本質、審美屬性被綁架、遮蔽了。失去根本的文學研究,必有回歸本位的時候。文化多元主義研究或許能為文學研究提供更多的視角,但絕不是反對文學獨立性、審美自主性的理由。一首詩應該首先被當作一首詩去對待,而不是當成社會文獻,更不是意識形態、政治傾向的記錄,從這個角度來說,布魯姆的精英主義立場對維護文學的合法地位具有積極意義。
精英主義文學立場的另一個意義在于為文學經典樹立了嚴格的準入標準。只有那些在與前驅的較量中,突破“事實性”之重的強力詩人才可能打開傳統之門,使其作品進入經典行列。布魯姆秉持一種開放的經典觀,如他所說,“一切經典,包括時下流行的反經典,都屬精英之作,世俗經典從未封閉過,這使‘破解經典’之舉實屬多余”[13]。從這個意義上說,布魯姆的精英觀同樣是開放的。當然,我們必須認識到,作為美國文化的認同者,布魯姆的精英主義文學觀,服務于他重構美國傳統文化的目標。在布魯姆看來,美國的文化多元主義研究傷害了愛默生開創的美國傳統文化。理查德·羅蒂曾指出,布魯姆就是要通過他對文學經典的守護,在“浪漫的空想中構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14],那是美國需要的未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認為布魯姆對普遍人性的大聲疾呼、對不屈不撓的意志的信念,“就如同櫻桃餡餅一樣完全是美國式的,只不過他把這一點誤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15]。也就是說,在伊格爾頓看來,布魯姆的精英主義立場實際上是典型的美國立場。考慮到布魯姆深刻的“愛默生情結”,我們就會明白,伊格爾頓洞見了布魯姆精英主義立場的本質。但是,這不正是布魯姆的價值所在嗎?我們難以想象一個失去民族根基的文學批評家能最大限度地體現其價值。
此外,精英從來不是一個過時的概念,精英階層也從來不是一個可以完全被否定或被抹殺的存在,只要“精英”還不是“封閉”“僵死”的同義詞。事實上,文化多元主義者,在批評布魯姆的精英主義立場時,又何嘗不是在塑造另一種精英呢?意大利精英主義理論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以法國的德雷福斯案[16]為例向我們清楚地證明,舊精英的衰落往往伴隨著新精英的興起。文化多元主義者主觀上也許是在為劣勢群體爭取權益,也許他們確實是站在少數派的立場上,但他們或許沒明白,只要存在利益(什么時候不存在呢?),利己主義就不會消失,那么,“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在幫助新精英的利己主義取得勝利”,多元文化主義者再次上演著帕累托所說的“主觀現象與客觀現象的背離”[17]一幕。更可怕的是,如果說布魯姆強調的精英標準還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崇高意味的話,那么文化多元主義者追求所謂的平等則很容易導致事實上標準的喪失。
如此看來,布魯姆對精英主義立場的堅守體現出其對某種標準的追求,而這標準又不失其超越性、崇高性,可以說,布魯姆的堅守之于我們思考中國文學批評與文化建構問題的啟示意義不容小覷。就文學本身而言,中國當下文學界盛行相對主義,其造成的混亂有目共睹。曹文軒說,“從批評到創作,都沉浸在相對主義的氛圍中”,“相對主義的寬容、大度的姿態,還導致了我們對文學史的無原則的原諒”。[18]這一切都因為“文學性”這個本不應有爭議的標準,卻在這個混亂的時代被不斷解構。于是,標準不再,文學失范。
如果說標準的喪失,還有“標準多元化”這塊遮羞布的話,那么,獨尊物質財富為標準則是赤裸裸的。所有的創造、所有的偉大思想、所有的遠見卓識、所有的貢獻與付出都無法與金錢相比,在金錢的光輝中,一切卓越與崇高都變得孱弱且沒有說服力,甚至成為嘲笑的對象。知識與思想只有在金錢的烘托下才顯得重要,此時,知識與思想已無立錐之地,至少失去了其獨立性。一個否定智識、喪失標準或使金錢成為單一標準的社會,豈止是可怕那么簡單?利益第一的短視似乎成了理所當然,我們無從判斷,這是否與“人生苦短”有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社會良知的缺失、個人精神的虛空罪責難逃。
面對這樣的現實與精神文化處境,反思或退歸內在世界也許是我們獲取拯救之途的不二法門。智識精英只要堅守住這最后的堡壘,其價值就永遠不可被忽視,并將不斷為這個社會提供精神血液。
我們強調精神的力量,擺明智識精英的尷尬處境,并不是想為智識精英鳴不平,我們堅信智識終有一天會回歸,從來不相信一個排斥智識精英的社會能良性發展;也不是想為嚴肅文學唱悲歌,因為文學本就不應該占據中心位置,但也絕不相信“文學已死”的謠言。只要我們還承認文學本身的意義,還承認文學研究的價值,那么我們就應該承認:關注精神世界、關注人的生存狀態是文學與文學研究發揮其意義與價值的重要表現。
三 經典閱讀的意義與現狀
可以說,創新是文學的生命。正如布魯姆指出的:“自主和創新才是強力閱讀的目標,如同它們也是強力寫作的目標一樣。”[19]文學也許是最不承認沿襲與重復的領域,但所有事物的發展都必然以繼承為基礎,文學也同樣如此,其發展是繼承與創新的辯證。
我們不能為了創新而創新。從文學發展史來看,文學的創新性遠無法與繼承性相比。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有言:“如果我們不抱這種先入的成見去研究某位詩人,我們反而往往會發現不僅他的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個性的部分,很可能正是已故詩人們,也就是他的先輩們,最有力地表現了他們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我說的不是這個詩人易受別人影響的青春時期,而是他的完全成熟了的階段。”[20]這一方面說明,棄絕傳統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說明,希圖創新何其艱難。
對于我們來說,讀書也許是實現繼承的關鍵。讀書即批評,沒有思考與情感投入的閱讀是虛假的閱讀,是生命的浪費。但問題是讀什么書?怎么讀?為什么讀?又如何在閱讀中實現文學的繼承?
首先,只有對文學懷有赤誠之心的讀者、作家和批評者,才可能寫出最好的文學作品,做出最具說服力的批評,才可能叩問文學中最深層的精神存在,進而透過文學的望鏡窺見自己的心靈世界。但就是這樣最簡單的道理,卻被眾多批評實踐棄置了,閱讀成了一種功利活動。我們看到諸多以文學為工具而非本體存在的批評,于是批評成為謀求利益的資本,成為換取身價的籌碼,成為人情往來的“禮盒”。文字不再從心靈流出,既無勃勃生氣,又缺少作者的生命律動,這樣的文字當然無法打動讀者。讀者不再為了心靈的愉悅與內在精神的豐盈而讀書。“強力批評家和強力讀者知道,假如我們懷疑真正的寫作者和讀者的文學之愛,我們就不能理解文學。偉大的文學,崇高的文學,需要的是感情投入而非經濟投入”[21],這意味著,有關文學的“真正”書寫也必然發乎真心,以解釋人的心靈世界、精神存在為指歸,這是批評的生命力所在。福柯(Michel Foucault)說:“我忍不住夢想一種批評,這種批評不會努力去評判,而是給一部作品、一本書、一個句子、一種思想帶來生命;它把火點燃,觀察青草的生長,聆聽風的聲音,在微風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號,而不是去評判;它召喚這些存在的符號,把它們從沉睡中喚醒。也許有時候它也把它們創造出來——那樣會更好。下判決的那種批評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歡批評能迸發出想象的火花。它不應該是穿著紅袍的君主。它應該挾著風暴和閃電。”[22]福柯的意思是說,批評并不依靠“權利”,而是依靠批評家強大的生命力獲得力量,唯有具有生命力的批評才可能迸發出想象的火花。從這一角度來看,布魯姆的文學批評,無疑具有這樣的品質。這也啟示我們,文學閱讀或文學批評需要主體的情感,甚至是生命的投入。
其次,只有相信內在性的深度是一種力量,才可能在閱讀中敞開自我,擁抱文學中的精神世界,也才可能洞穿文學中的精神城堡,進而與偉大作家的內在精神相契合。“一位大作家,其內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種力量,可以避開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負,以免原創性的苗頭剛剛嶄露就被摧毀。偉大的作品不是重寫即為修正,因為它建構在某種為自我開辟空間的閱讀之上,或者此種閱讀會將舊作重新打開,給予我們新的痛苦經驗。”[23]這就意味著,所有的創作,無論是文學寫作,還是批評寫作,都必須建立在“某種為自我開辟空間的閱讀之上”,只有這樣的強力閱讀才可能與前人強大的內在性相對抗。
但是,關注精神性、內在性強力,并不意味著必然遮蔽文學的審美屬性,相反,通過發現文本的敘述策略有助于深入精神的世界,并進而與人的存在狀態相溝通,洞悉作家的身份認同。布魯姆對卡夫卡(Franz Kafka)的“經典性忍耐”和“不可摧毀性”的分析頗能說明這一點。卡夫卡有意地用“嚴厲冷酷”的敘述抵制情感的狂歡;他努力拒斥一切心靈的表面化探尋,這是通過其作品中冷漠的基調及書寫人物沒完沒了的“無意義”的語言和行動來實現的,因為他真正要表現的是一種沒有任何希望可言的人的生存處境——“不可摧毀的存在”。在卡夫卡那里,所有的希望都是能被摧毀的意識,只有人們內心深處隱秘的存在,即深層自我是不可摧毀的。對深層自我不可摧毀性的發現,與布魯姆的猶太人身份是分不開的,是其猶太人身份與處境的理論展現。布魯姆這樣論說卡夫卡的經典性:“卡夫卡作為本世紀最經典的作家,是因為我們都把存在和意識的分裂視為他的真正主題,他把這一主題等同于猶太人身份,或者至少是特別等同于流亡猶太人的身份。”[24]存在與意識的分裂,這正是流亡猶太人的生存現狀。在意識中他們眷戀著曾經的榮光,即作為上帝選民的神賜榮光。雖然這份榮光屬于過去,但并未隨著他們不得已的流亡而消逝,反倒隨歲月流逝更加清晰了。但現實的存在狀態是不可回避的,于是他們回歸了內心最深處的自我,這是一種生存意志的體現。在這樣的生存現狀中,只有忍耐是通往真知,即不可摧毀性的可行途徑,“忍耐與其說是卡夫卡心目中的首要美德,不如說是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就像猶太人的經典性忍耐一樣”[25]。這樣布魯姆就找到了解讀卡夫卡的一把鑰匙——雖然不是唯一的,卻是有效的。“經典性忍耐”確實是解讀卡夫卡思考和概括猶太人生存狀態,甚至是整個人類生存狀態的一個關鍵詞:“人類有兩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惡均和其有關,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經心。由于缺乏耐心,他們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經心,他們無法回去。也許只有一個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們被驅逐;由于缺乏耐心,他們回不去。”[26]
布魯姆對經典文本的闡釋,是以審美為武器進行的文本解剖,他重視作品,特別是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生命力和精神屬性。在莎士比亞戲劇中的諸多人物形象中,布魯姆最欣賞哈姆萊特和福斯塔夫,對其分析得也最為充分。在布魯姆看來,在莎士比亞塑造的所有人物中,這兩個人物所表現出的心智是最全面的:“莎劇迷們喜歡福斯塔夫和哈姆萊特遠甚于其他人物,我們也是這樣,因為胖杰克和丹麥王子清楚地展現了在文學中的最全面的意識,這種意識要比圣經作者的耶和華、馬可福音中的耶穌、但丁和喬叟的圣徒、唐吉訶德、艾瑟·薩默森、普魯斯特的故事敘述者和利奧波德·布盧姆要廣大的多。”正是在這意義上,布魯姆覺得,“也許正是福斯塔夫和哈姆萊特,而不是莎士比亞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俗上帝,可能是他們最偉大的心智和智慧使他們的創造者被神圣化了”[27],因為這兩個人物體現了生命的博大,體現了人性的豐富,依靠閱讀這些人物形象,我們得以更全面、更深刻地認知人本身。
在哈姆萊特和福斯塔夫身上,布魯姆看到了一種將自我傾聽(或自言自語)發揮到極致的力量,也就是一種自由反思的內省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布魯姆說:“哈姆萊特心靈上每時每刻都在上演一出戲中戲,因為他比莎劇中任何其他人物都更是一位自由的自我藝術家。他的得意與痛苦同樣植根于對自我形象的不斷沉思之中。”[28]布魯姆對哈姆雷特的這一洞見建立在他對莎士比亞人物心靈世界準確把握的基礎上,在他看來,莎士比亞創造的戲劇人物都是典型的自我傾聽者,正因如此他們體現出心理的復雜性與多變性。布魯姆甚至認為這是莎士比亞之所以成為經典核心的關鍵。借此,布魯姆又將以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為代表的這一品質與文學的精神性聯系到了一起:“我們每一個人現在都會不停地自我傾訴與傾聽,然后才進行思考并依照已知情況行事。這并不全是心靈與自己的對話,或內在心理斗爭的反映,這更是生命對文學必然產生的結果的一種反應。”[29]也就是說,生命只要進入文學書寫的范疇,必然表現為一種自我傾訴與傾聽,由此文學或想象性寫作就發展成了一種表現“如何對自我言說”的藝術。
其實,與作品中人物心靈的對話過程,也就是閱讀者發現作家心靈世界的過程。我們常常從布魯姆的文學閱讀中發現其洞悉作家豐富精神世界的精妙。雖然我們對莎士比亞的生平與內心生活所知甚少,也難以從他的創作中發現莎士比亞本人的影子,但布魯姆發現,通過多年鍥而不舍地閱讀莎士比亞,至少可以逐步了解他不是什么。通過分析莎士比亞不是什么,布魯姆暗示我們:莎士比亞的內心世界是絕對自由的,這是一種四下彌漫而又不可限制的精神,正是這種脫離了教條和簡單化道德的自由精神使莎士比亞的戲劇具有了一種自然的恢宏,其塑造的人物及其個性具有了一種難以企及的變化多端的特點。
更為重要的是,布魯姆強調將作家置于文學傳統的關系鏈中。從強力作家間的競比關系入手,布魯姆發現,所有的強力詩人都是通過對抗先驅使自己獲得存在可能性的。這是一個影響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絕非理想式的善意傳承過程,而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搏殺過程。后輩詩人只有通過搏殺,踏前驅于腳下,才能使自己逃脫被壓抑窒息的命運。因此,“每一位詩人的發軔點(無論他多么‘無意識’)乃是一種較之普通人更為強烈的對‘死亡的必然性’的反抗意識”[30]。如此,布魯姆就深入到了作家意識與精神世界的最深層——死亡意識或反抗死亡的意識。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與作品中的人物和作家本人心靈的對話過程,或洞悉其內在世界的過程,也就是閱讀者回歸自我的過程。在布魯姆看來,真正的閱讀說到底,都是一個向孤獨的心靈回歸、叩問深層自我的過程。所謂真正的閱讀,就是以一種以審美為出發點,也以其為落腳點的閱讀,而非從哲學或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或以其為最終目的。這種閱讀使我們得以回到文學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獨的心靈中去,于是讀者不再是社會的一員,而是作為深層的自我,作為我們終極的內在性”[31]。如此,文學的閱讀過程也就成了閱讀者心靈的展示過程,閱讀者與文學中存在的心靈世界的對話過程:“我們之所以閱讀……是為了鍛煉自我,認識自我真正的興趣。……閱讀的樂趣的確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是有益于社會公益。”“文學評論若說還有功能的話,那便是為給這些自了讀者看,他們是為了自己而讀,而不是為了自身之外的好處而讀。”[32]也就是說,在布魯姆那里,閱讀就成了一種純粹的內在行為,是自我修習精進的過程。
由是觀之,布魯姆與“存在”哲學家海德格爾之間的距離并沒有他本人想象得那樣遠,只是布魯姆對存在的關注,更傾向于其精神層面,并且這種關注從未試圖拋棄文學的望鏡。
中國學者陳平原有一段話,充分說明了閱讀與精神生活之間的聯系:“你半夜醒來發現自己已經好長時間沒讀書,而且沒有任何負罪感的時候,你就必須知道,你已經墮落了。不是說書本本身特了不起,而是讀書這個行為意味著你沒有完全認同于這個現世和現實,你還有追求,還在奮斗,你還有不滿,你還在尋找另一種可能性,另一種生活方式。說到底,讀書是一種精神生活。”[33]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我們的閱讀現狀堪憂。
首先是不讀書。數年前,有消息稱有關部門正試圖通過立法來使全民閱讀。無論消息真假,大家對此持何種看法,但這至少說明我們的閱讀狀況已墮落到何種程度,甚至需要用法律手段來補救。一個與法律無涉的事,卻不得不訴諸法律的權威。不只是社會中人不讀書,連本該讀書的大學中人的閱讀現狀也不容樂觀。首先,高校教師的閱讀正在被“文獻檢索取代”,在閱讀中體味人生、體驗活潑潑的人性,從而不斷提升自我修養的閱讀狀態,正與我們漸行漸遠。不讀書在大學中造成的一個直接結果是課堂教學中我們看到的是過多重復陳舊的知識。教材當然重要,但教材往往和前沿研究成果相距甚遠。更為重要的是,對于人文學科而言,讀書是科研工作的重要保證。一個不讀書、不搞科研、沒有學術素養的教師如何成為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換句話說,他能教給學生什么是值得懷疑的。更為重要的是,不讀書還意味著精神的干枯,我們又如何指望一個精神干枯的教師能培養出精神充盈的學生。
我們處在閱讀史上最糟糕的年代,這一定程度上是現代性的代價(或陰謀)之一。早在多年以前,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就曾警示我們要小心現代社會“簡化”(縮減)的力量:“伴隨著地球歷史的一體化過程——上帝不懷好意地讓人實現了這一人文主義的夢想——的是一種令人暈眩的簡化過程。應當承認,簡化的蛀蟲一直以來就在啃噬著人類的生活:即使最偉大的愛情最后也會被簡化為一個由淡淡的回憶組成的骨架。……人類處于一個真正的簡化的旋渦之中,其中,胡塞爾所說的‘生活世界’徹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終落入遺忘之中。”[34]這樣的“簡化”(縮減)同樣發生在閱讀領域,特別是文學閱讀領域。“我們的個性化的、豐富的閱讀”,“被變成了‘壓縮’式的閱讀。過去的經典文字閱讀被‘讀圖’取代,進入了選刊時代。什么叫‘選刊時代’?就是把流行、時尚的讀物進行‘壓縮’,進行刪減,作為‘快餐文化’推向讀者。尼采說,這種閱讀是一種讀書趣味危機,就是生命不復處于整體之中,‘整體根本不復存在,它被人為地堆積和累計起來,成了一種人工制品’。最終,在這種閱讀文化生活中,‘生命、同等的活力、生命的蓬勃興旺被壓縮在最小的單位中,生命剩下了可憐的零頭’”,而隨著現代科技的發現,一種新的“壓縮”出現了,打著復興國學與傳統的大旗,于是“我們有了‘時尚讀史’,有了‘新明星學者’給我們經過‘壓縮’和‘速成’的歷史,有了被人‘混嚼’出來的叫做歷史的東西,有了很像速成教材的歷史速成著作,可那歷史的本來面目不知在這種‘壓縮’中失去了幾多真實”[35]。文學的豐富與歷史的恢宏就這樣被一種現代化的扁平與縮約代替了,而我們深陷于這種所謂的“閱讀”之中無法自拔。今天,隨著“抖音”“快手”“喜馬拉雅”“懶人聽書”等視聽平臺的大熱,傳統閱讀似乎已被當作需要拋棄的東西,逐漸從大多數人的生活中被剔除了。
其次是過于強調閱讀的功利性。讀書有目的性當然沒錯,但不能過分強調這一點,更不應該因為強調功利閱讀而忽視了一種超越性的閱讀。出于某種目的,如備課、寫論文等當然可以,但也許更重要的是一種自由的、憑興趣進行的閱讀,超越性的閱讀。有人將閱讀的快樂區分為目的性快樂和過程性快樂。功利性閱讀指向的是目的性快樂;超越性閱讀則指向過程性快樂。超越性閱讀往往可以在閱讀的過程中得到快樂,那種快樂是一種不期而遇式的驚喜,但時間久了則會對專業工作與學習帶來有益影響,進而與目的性快樂合而為一。隨著新儒學的興起,一些新儒學理論家強調儒家思想具有宗教性,筆者對此一直不以為然:一般意義上說,宗教的第一特性是超越性,即認為有超越此生的存在,即一種“神”性的存在,或一個彼岸的世界。孔子說:“不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彼岸世界的存在,否定了神之拯救的可能性,因此也就失去了“超越”現世的可能,最終儒家思想成了一種純粹的有關社會倫理的思想。后來在無意中讀到一本書,其中包括杜維明的一篇文章。他指出,儒家思想確實注重道德倫理規范,“儒家思想的鮮明特點就在于它對社會倫理的關切”,但這并非儒家思想的全部,我們必須“綜合地去理解儒家的思想體系”,“某些跡象可能表明,其社會準則一方面來源于所謂的儒學深層心理,另一方面又必需延伸到儒家的宗教信仰領域”。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用諸如社會調節之類概念是很難解釋其全部內涵的。我們還必須使用諸如個體整合、自我實現和終極追求等概念”[36]。這就啟發了我:也許過去對“超越性”的理解過于狹隘了,這不啻是受西方思想影響的結果,忽視了對中國文化的考察。“超越性”即可以憑借外力——神——去完成,亦可通過“精神修煉”實現,最后達到“內在超越”的境界。事實上,西方宗教也經歷了一個從外在超越(或者說“外在拯救”更合適)向內在超越轉化的過程。基督教思想的轉變——從“靈魂被基督拯救”到“基督拯救和人自身拯救的統一”——便是明證。在儒家思想那里,外在拯救被有限度地否定了:“不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卻為內在超越留下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間。如果我們強調宗教性與信仰的關系,那么儒家思想中就不乏宗教因素。從這個角度看,過于武斷地否定儒家的宗教性便有欠妥之處了。但也許只強調超越性閱讀還不夠,我們要做到的是把閱讀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之所以如此強調非功利的閱讀,還出于以下考慮:我們的專業分得太細了,細到使我們除了懂得自己的專業外,對其他專業幾乎一無所知。更可悲的是,我們很多人抱著專業主義的腿不放,自以為是專家、學者,其實這其中的一些人不過是“有專業無智慧、有知識無見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識小販。他們的全部本錢就是那一點點專業知識,把它說成是了不起的獨家擅長,不過是想奇貨可居而已”[37]。鑒于專業細分帶來的弊端,有學者開始批判專業主義,強調“業余者”身份。強調“業余”并非反對專業主義,也不是不要專業,而是要在專業主義之外另有作為。徐賁以薩義德(Edward Said)個案來說明這一問題,強調文學研究應該告別文學研究的“室內游戲”。非專業化的閱讀,或者如我們前面所說,非功利性的閱讀,可能有助于我們規避將文學研究,甚至是文學教育局限在“室內游戲”的范圍。
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是對的,他認為我們應該“把一部分空間讓給意外之書和偶然發現之書”[38]。當我們把閱讀作為一種生存方式,而非功利手段的時候,閱讀往往就會變一個“赴未約之會”的過程,在那時我們會發現一種功利閱讀無法體會到的美好。
再次是過于依賴網絡閱讀和電子閱讀。我們不應該一味地反對網絡閱讀和電子閱讀,但至少在現階段,電子閱讀還無法替代傳統閱讀,其弊病非常明顯。第一,電子閱讀針對性過強,無法有讀紙質書時的“不期而遇”之感。相信大家都有過這樣的經歷,電子書或數據庫閱讀,往往是在我們查閱資料時使用,目的性明顯,直指結果;紙質書則不同,我們往往在查閱某一問題時,另一問題卻與我們不期而遇。第二,閱讀本應是一個自由的、愉快的過程,但在電子閱讀的過程中很難有這種閱讀體驗。自由的、隨性的閱讀,或坐、或臥的愉快閱讀,電子書怕還做不到。第三,網絡上的大量信息,其可信度是可疑的。在網絡信息泛濫的情況下,也許信息的甄別能力遠比信息的獲取量更重要。這也許就是布魯姆冒天下之大不韙,預言“大量投資電子書籍的出版商們會遇到經濟災難”[39]的原因吧!
四 走進文學的精神世界
那么,我們該從哪些方面做準備,以待通過文學經典閱讀實現與繆斯的“不期而遇”呢?
第一,要祛除閱讀經典的世俗功利之心,堅信文學經典在精神超越方面的價值與意義。
布魯姆的批評先導,也是他心目中的批評英雄——約翰遜博士(Dr.Samuel Johnson)曾說:只有傻瓜,才為了錢之外的事寫作。布魯姆對約翰遜的這一座右銘欣然贊同,但至耄耋之年,布魯姆說,錢或者說經濟利益現在只是他的第二動機,他之所以還在堅持閱讀、堅持講課、堅持寫作,是因為“我們內部的那個偉大的聲音,它響起,作為對沃爾特·惠特曼的聲音和莎士比亞所創造的千百種聲音的回應”[40]。文學閱讀與寫作最終是指向內部世界的,是指向精神存在的。這種“聲音”是對自我的充分肯定,是對自我內在精神強力的認可。這也許就是我們破解文學繆斯之所以在當下傷痕累累這一謎團的金鑰,也是引領文學批評走出尷尬境地的明燈。
事實上,文學從根本上是排除功利性的。在一個功利主義盛行的時代,文學非功利性的價值尤為突出。古羅馬詩歌理論家賀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指出:當銅銹和貪得的欲望腐蝕了人的心靈之后,我們怎樣才有使詩歌還值得涂上杉脂,值得保存在光潔的柏木匣里呢?賀拉斯開出的良方是作家要增強內在修養。[41]事實上,歷代作家和理論家都非常強調作家的修養,古典主義哲學家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Despreaux)也曾說:“一個有德的作家,具有無邪的詩品,能使人耳怡目悅而絕不腐蝕人心:他的熱情絕不會引起欲火的災殃。因此你要愛道德,使靈魂得到修養。”[42]
將自己的個體生命體驗融入文學書寫中,成為作品的靈魂,是所有偉大作品必備的品質。如果說偉大的作品都只有一個主人公的話,那這個主人公一定是作者本人,準確地說是作者本人的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其實任何一部偉大作品都在某種意義上是作者的精神自傳。“得有一個多么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才支撐得起一首詩的寥寥數語!”[43]我們無法想象,一個缺乏個人修養的作家能真的寫出富有精神超越性的作品;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個性喪失的詩人能寫出穿越時空,與未來讀者產生共鳴的偉大詩歌;我們也無法想象,一個內在世界干癟,沒有能力感受生活的作家能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當然,我們更無法想象,一個生命力枯萎、對精神超越不屑一顧、被世俗功利之心占據了靈魂的讀者能與豐饒的文學精神世界真正建立聯系。
第二,要處理好“歷史的探尋”與“美學的沉思”之間的關系。艾金伯勒(Etiemble)針對文學研究提出了“歷史的探索”與“美學的沉思”這兩個概念,[44]但在具體研究實踐中,“美學的沉思”常被我們忽視,而“歷史的探索”則被過分彰顯,于是,文學被賦予了太多非文學的責任。面對文化研究大潮對文學理論的沖擊,布魯姆一再強調文學的審美屬性,不惜冒“政治不正確”之風險,將所有文化研究者冠以“憎恨學派”之名。布魯姆顯然更強調“美學的沉思”,但絕非要否認“歷史的探尋”,只是在處理二者關系時,他認為強調后者不應成為傷害前者的理由:“一首詩無法單獨存在,但審美領域里卻存在一些固定的價值。這些不可全然忽視的價值經由藝術家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而建立起來。這些影響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會的因素,但其核心還是審美的。”[45]因此,布魯姆批評那些變成了“業余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46]的文學研究者。文學對歷史的書寫,絕非是簡單地記錄過往,而是要對歷史、當下與未來進行一種整體的、全面的人文觀照,從中發現其中的血肉聯系。這是文學價值的體現,也是文學存在合理性的憑依。昆德拉在《小說藝術》一書中通過分析布洛赫(Hermann Broch)[47]的《夢游者》向我們指出:小說寫作應建立起歷史、當下與未來的血肉聯系,如此才可能多角度、深層次地觀照歷史、現實和未來之間的聯系。[48]如果反思歷史到反思止,缺乏對現實的觀照,那么這樣的反思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書寫現實到記錄止,缺乏對未來的指涉,那么這種書寫的價值也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書寫未來到空想終,那樣的未來書寫也就失去了指導作用。文學寫作應建立起歷史、當下與未來的血肉聯系,文學批評也同樣如此。文學批評若試圖實現“歷史的探尋”的意圖,就必須充分尊重文學自身的性質與功用,認識到“美學的沉思”不可或缺,最終以人文精神觀照與統攝歷史的探尋,而不是將文學視作一種工具性存在。
優秀的文學作品自有其文化反思、歷史反思之維。文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去探索存在于歷史、現實與未來這一巨大張力結構中的人之生活的各種可能性。所有具有創造性的書寫都必然是以書寫者的內在精神強力為基礎的。文學經典的閱讀者必須明白,“歷史的探尋”與“美學的沉思”在文學經典中缺一不可,他們共同體現了作者“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
第三,要從“形而上的思索”與“形而下的關懷”兩個層面觀照文學經典。任何文學作品如果失去形而上叩問,即失去對人之存在的關注,哪怕它再流行,都會成為文學歷史中的過眼煙云,最終消逝在人們的視野之外;同理,如果一部文學作品失去了對現實的關注,無論它多么充滿哲理,都只會被束之高閣,成為收藏癖們的獨享。有鑒于此,我們在閱讀與批評文學經典時,應該結合形而上和形而下兩個層面,整體認知一部文學經典的價值。
文學創作是一種相信作家靈性的活動,但這并不是否定作家需要“用功”的理由:對政策的研讀、對社會問題的調查、對現實生活的了解等,是作家創作得以立足大地的保證。然而,文學家能讓自己的創作超越形而下之維,在立足大地的同時指向天空,發現文學才能發現的世界,才是其真正的價值所在。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這位“在追求他故鄉憂郁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沖突和交錯的新象征”[49]的土耳其作家,在他的小說中,“一方面將本土神秘主義的失落以反語出之,生動表征了土耳其民族身份在歷史變遷中的迷失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呼愁’,另一方面又在其中體悟出了本民族走出身份尷尬與精神困惑的途徑”[50]。由此看來,精神的向度和思想的深度是一位作家能否越超自己的生活,進入一種洞察世事的澄明的形而上之境的關鍵。唯有思想之矛方能戳穿思想的鎧甲,唯有精神之刃才能切開精神的堅殼。我們無法相信一個精神與思想的貧血癥患者,能洞悉文學精神,破解繆斯之謎,進而成為卓越的文學批評家或合格的經典閱讀者。
布魯姆之所以將文學經典置于神壇之上并頂禮膜拜,就是因為他相信,閱讀文學可以實現內在自我的擴展,經典之于人類具有精神拯救的功效。理查德·羅蒂不無洞見地指出:“對布魯姆這樣的功能主義者來說,文學經典的標準‘規定了一生的閱讀范圍’,而制定標準的主要目的是告訴年輕人去哪里尋找激情和希望。”[51]在羅蒂看來,這也正是布魯姆不同于福柯的地方:“福柯拒絕沉湎于空想不是出于遠見和洞察,而是因為他看不到人類獲得幸福的希望,進而也就不把美看成是幸福的前奏。這實在令人遺憾。福柯的追隨者努力模仿他。他們看不起布萊克和惠特曼之類的詩人,看不起受這些詩人啟發的人……當代美國福柯式的學院左派正是寡頭政治夢想中的左派:這個左派只顧揭露現實的本質而無暇討論還需要通過什么法令才能使未來更加美好。”[52]在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中都存在兩種傾向:或執著于現實或失之于空懸。寡頭政治的“聰明”就在于鼓勵一種執著于現實的“左派”。雖然布魯姆本人也是一個悲觀論者、一個虛無論者,與“看不到人類獲得幸福的希望”的福柯一樣,但是他相信文學可以重鑄人之內在精神,使想象的力量得到延伸,從而最終使每一個人身上的內在力量化合為一股希望之光,照亮人類黑暗的前方之路,使“屬靈”世界在光輝中再次顯現。這是一種身陷絕境后奮起反抗、面對死亡時執著抗爭的勇氣。從人的內在世界中獲取堅持的力量,使我們無從判定這是一種空想,還是真正的遠見和洞察。但無論如何,布魯姆讓我們看到了文學經典與精神拯救之間的密切關聯,讓我們得以在一個意義缺失的時代重拾文學經典的價值。
破除“左派”迷陣的另一個途徑是在文學書寫與文學批評中強調文學中的“偶然性”因素,這與文學中的理想主義緊密相關。很多作家執著于俯身大地的敘述狀態,卻忽視了對形而上問題的叩問。一些作者關注人物的命運,寫出了他們生命的歷程,看到了時代風云對人物命運的影響,也道出了性格在人物生命歷程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卻很少關注在人物經歷背后,掌控人物生命歷程的其他力量。這些力量至少還包括人物身上隱藏的文化精神,包括人的生命中不可逆轉的多種發展趨向。人是文化的產物,人物的命運是文化影響的結果;人之存在有太多自身無法掌控的因素,這些因素或隱或顯地左右著我們的生命歷程,業已成為人的宿命。除了性格與時代的因素,還有什么左右著他們?特殊的民族文化精神在他們每個人身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否有宿命的東西在其中起了作用,而人物卻不自知?優秀的作品往往通過表現人之存在中的“偶然性”因素,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或予以回答。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使《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故事始終與現實保持著一定距離,這部作品中的很多故事與其說是現實規律的產物,不如說是世界之偶然性的結果。有鑒于此,喬叟雖然被稱作英國現實主義詩歌之父,但他更是一位浪漫主義文學家,一個骨子里的理想主義者。在浪漫情懷被幽禁、理想主義漸行漸遠的今天,希望我們在文學中感受其深厚現實基礎的同時,也能從中得到一些——如喬叟給予我們的——精神、理想與浪漫情懷方面的慰藉。
第四,處理好文學的快感與有用性之間的關系。文學理論家奧斯汀·沃倫(Austin Warren)曾指出:“當某一文學作品成功發揮其作用時,快感和有用性這兩個‘基調’不應該簡單地共存,而應該交匯在一起。文學給人的快感,并非從一系列可能使人快意的事物中隨意選擇出來的一種,而是一種‘高級的快感’,是從一種高級活動、即無所希求的冥思默想中取得的快感。而文學的有用性——嚴肅性和教育意義——則是令人愉悅的嚴肅性,而不是那種必須履行職責或必須記取教訓的嚴肅性;我們也可以把那種給人快感的嚴肅性稱為審美嚴肅性(aesthetic seriousness),即知覺的嚴肅性(seriousness of perception)。”[53]在平庸的文學中,我們讀到了太多的“有用性”——這種有用性一定程度上是作者自覺賦予的——而很難在閱讀中感到那種只有在“無所希求的冥思默想”中才能獲得的“高級的快感”。有鑒于此,文學既要關注文學與眼前之物的關聯性,也應對文學與遠方風景的關系有所揭示。不妨仍以奧罕·帕慕克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無論如何都是一位嚴肅作家,但他的作品與一般當代文學家的作品“叫好不叫座”的情況不同。帕慕克的作品不僅頻頻得獎,而且每部都會成為暢銷一時的書籍。他的《新人生》一書,是土耳其歷史上銷售最快的書。帕慕克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受讀者喜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采用了通俗小說的表現技巧。如他的代表作之一《我的名字叫紅》的主體故事,就是再俗套不過的探案推理故事加愛情故事的模式。這樣的故事使小說具有了大眾文學的特點,有人因此指責他有嘩眾取寵之嫌,并認為他的小說帶有很強的“媚俗”性;甚至有人認為,2005年帕慕克最終沒有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就是他的小說太好看、太流行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小說的思辨性。但是,正如諾獎委員會頒獎詞所說的那樣:帕慕克的小說“在追求他故鄉憂郁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的沖突和交錯的新象征”[54]。這也許正是眾多文學評論家把他和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托馬斯·曼(Thomas Mann)、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等大師相提并論的原因吧!帕慕克無疑是處理文學的快感和有用性之間關系的典范。
能否將自己的創作置于整個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是以歷史和現實為觀照對象的文學創作能否成功的關鍵。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c)曾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我們不妨將這個“秘史”理解成暗藏民族文化精髓的歷史,它可能與史書的記載不盡相同,但卻與民族性緊密相關。如果能將自己的小說與民族文化緊密結合,并以人性為核心去揭示民族文化之精髓的話,那么無論小說內容帶有多強的“地方性”,都會具有“世界性”的品質。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需要對本民族文化的本質與內涵有非常深入的所握,對其精神內涵有深刻的洞悉。文學批評,乃至整個文藝批評就應關注批評對象與民族文化之間的密切關聯。
李歐梵曾經分析過三部以“竹林”為打斗背景的武俠電影:胡金銓的《俠女》、李安的《臥虎藏龍》和張藝謀的《十面埋伏》。在李歐梵看來,香港老導演胡金銓《俠女》的“竹林之戰是一種創舉”[55],雖由于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畫面并不那么美,但卻是胡金銓從中國古典文化,特別是禪意美學中悟出來的“全境美學”的體現。[56]在李安的《臥虎藏龍》中,周潤發和章子怡在竹林頂上打斗的那場戲,令觀眾驚嘆。在李歐梵看來,李安“為的是向胡金銓致敬”[57]。李安理解胡金銓鏡頭背后的文化含義,因此“也在意境上下功夫,在竹子上面駕輕功飛來飛去,而不入林中”[58]。張藝謀導演的《十面埋伏》中的竹林戲,在李歐梵看來完全沒有明白竹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美學與精神指向,在竹林中追殺完全與竹林禪意美學背道而馳,“《俠女》的竹林保持了中國文化的原汁原味,《十面埋伏》的竹林卻‘埋伏’了太多的機關與科技”[59]。在一次演講中李歐梵說:“張藝謀是個電影巨匠,這個匠是工匠的意思,不可否認他的鏡頭感很強,拍出來的畫面很美,可鏡頭背后的意境,張藝謀完全不能理解,他是在做電影,美麗的鏡頭背后,竹林蘊含的文化意境被他破壞得鮮血淋漓。”[60]造成《十面埋伏》竹林打斗場面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創作者對中國傳統竹文化內涵缺乏起碼的了解。
閱讀需要有所選擇,但網絡的普及,特別商業炒作行為對文學領域的滲透,使閱讀對象的選擇成了一個大問題。選擇的標準有很多,這里只提一點:閱讀經典而不是暢銷書。歌德說,好的鑒賞力是靠讀那些最優秀的作品獲得的。對我們來說,優秀的作品就是那些經典著作。當然并不是說所有的暢銷書都不值一讀,這需要我們自己具有一定的判斷力。客觀來講,一些暢銷書是書商炒作、各種文化力量引導的結果,這樣的案例有很多。前幾年流行過一本名為《狼圖騰》的文學著作,一些學者從生態文學、民族精神等多種角度對之進行解讀,并對之大加頌揚,但也有一些學者如李建軍、諾獎評委馬悅然(Goran Malmqvist)和德國學者顧彬(Wolfgang Kubin)不遺余力地批判過此書。據說《狼圖騰》英文版由權威的企鵝出版社出版,由著名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譯,在美國打算銷售到200萬冊,但這仍改變不了這部小說的暢銷只是一個炒作的結果。更重要的是,《狼圖騰》的精神內核——極權與暴力——與現代文明相去甚遠。作者辯護說自己這本書是“中國的故事,西方的精神”,表現的是西方游牧文化的源頭精神。如果說本書里面有西方文化,正如李建軍所指出的那樣,也是一種沒落的西方文化。[61]如果作者知道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是如何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他就知道西方文化的中心是什么了——是人,是人的精神的張揚。這本書在國內如此流行的原因之一,就是適應了當今社會在商品大潮背景下推崇“叢林法則”的現實。但我們需明白,這個法則本身有悖于現代文明標準,畢竟對待弱者的態度,是衡量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尺,而“美妙的自然法則之所以絕妙,也許就在于最軟弱的人得以幸存”[62]。
注釋
[1]〔法〕布瓦洛:《詩的藝術》,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第207~208頁。
[2]李歐梵:《我的哈佛歲月》,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第132頁。
[3]Harold Bloom,The Anatomy of Influence: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24.
[4]〔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409頁。
[5]〔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21頁。
[6]〔英〕湯姆·巴特摩爾:《平等還是精英》,尤衛軍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100頁。
[7]〔英〕湯姆·巴特摩爾:《平等還是精英》,尤衛軍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117頁。
[8]劉小楓:《圣靈降臨的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208頁。
[9]劉小楓:《圣靈降臨的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209頁。
[10]劉小楓:《圣靈降臨的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212頁。
[11]劉小楓:《圣靈降臨的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213頁。
[12]〔美〕理查德·羅蒂:《附錄二:文學經典的啟迪價值》,《筑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黃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第98頁。
[13]〔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26頁。
[14]〔美〕理查德·羅蒂:《附錄二:文學經典的啟迪價值》,《筑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黃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第103頁。
[15]轉引自劉峰《伊格爾頓評布魯姆的新著〈如何閱讀和為什么〉》,《國外文學》2001年第2期。
[16]德雷福斯案:1894年,法國猶太裔上尉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控出賣法國軍事情報給德國,軍事法庭裁定其叛國罪名成立,判處終身服苦役并流放魔鬼島。事后證明這是一樁純粹因誣告造成的冤案,但軍事法庭因德雷福斯的猶太人身份而拒絕改判,這引起了以左拉(Emile Zola)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的抗議。法國社會因為這一案件分裂成兩派,相互攻詰,反映了法國社會思想分化、各種力量相互沖突的復雜現實。這一事件留給人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從事德雷福斯案研究的著名學者,美國人邁克爾·伯恩斯(Michael Burns)曾指出:“德雷福斯事件中存在著多種形式的對抗,個人與國家、文人政府與軍事當局、議會政治與群眾政治、對一般人性的信念(無論是宗教的或俗世的)與現代種族主義。”(〔美〕邁克爾·伯恩斯:《法國與德雷福斯事件》,鄭約宜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第2頁)可以說,德雷福斯事件不僅是我們透視那一時期法國社會的一面鏡子,也是我們借以思考現代社會的一個經典案例。
[17]〔意〕維爾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興衰》,劉北成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3頁。
[18]曹文軒:《混亂時代的文學選擇》,《粵海風》2006年第3期。
[19]Harold Bloom,Agon: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8.
[20]〔英〕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學論文集》,李賦寧譯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第2頁。
[21]Harold Bloom,The Anatomy of Influence: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17.
[22]包亞明主編《權利的眼睛——福柯訪談錄》,嚴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04頁。
[23]〔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8頁。
[24]〔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360頁。
[25]〔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365頁。
[26]〔奧〕卡夫卡:《卡夫卡散文》,葉廷芳、黎奇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第1頁。
[27]Harold Bloom,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New York:Riverhead Books,1998,p.4.
[28]〔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53頁。
[29]〔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35頁。
[30]〔美〕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增訂版),徐文博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第10頁。
[31]〔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8頁。
[32]〔美〕哈洛·卜倫:《盡得其妙》,余君偉、傅士珍、李永平、郭強生、蘇榕譯,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第9~10頁。
[33]吳越:《當閱讀被檢索取代,修養是最大的輸家——陳平原談數字時代的人文困境》,《文匯報》2012年7月13日。
[34]〔法〕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第22~23頁。
[35]許民彤:《被“壓縮”了的閱讀》,《工人日報》2007年8月31日。
[36]〔美〕A.馬塞勒等著《文化與自我——東西方人的透視》,任鷹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44頁。
[37]楊瀟:《更專業?更業余?——專訪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徐賁》,《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29期。
[38]〔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黃燦然、李桂蜜譯,譯林出版社,2012,第10頁。
[39]〔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中文版序言”,第35頁。
[40]Harold Bloom,The Anatomy of Influence: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18.
[41]〔古羅馬〕賀拉斯:《詩藝》,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第108頁。
[42]〔法〕布瓦洛:《詩的藝術》,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第211頁。
[43]楊煉:《什么是詩歌精神?——阿多尼斯詩選中譯本序》,〔敘利亞〕阿多尼斯《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阿多尼斯詩選》,薛慶國選譯,譯林出版社,2009,第4頁。
[44]〔法〕艾金伯勒:《比較文學的目的、方法、規劃》,干永昌、廖鴻鈞、倪蕊琴編選《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第116頁。
[45]〔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17頁。
[46]〔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第412頁。
[47]赫爾曼·布洛赫(1886~1951),奧地利著名作家,代表作《夢游者》《維吉爾之死》等。
[48]〔奧〕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第70頁。
[49]轉引自沈志興《奧爾罕·帕慕克:發現文明沖突和交錯的新象征》,《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
[50]張虎:《“沒有人永遠是自己”——解讀帕慕克的小說〈黑書〉》,《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2期。
[51]〔美〕理查德·羅蒂:《附錄二:文學經典的啟迪價值》,《筑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黃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第100頁。
[52]〔美〕理查德·羅蒂:《附錄二:文學經典的啟迪價值》,《筑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黃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第102~103頁。
[53]〔美〕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第20~21頁。
[54]轉引自沈志興《奧爾罕·帕慕克:發現文明沖突和交錯的新象征》,《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
[55]李歐梵:《看電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第38頁。
[56]李歐梵:《看電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第38~39頁。
[57]李歐梵:《看電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第27頁。
[58]李歐梵:《看電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第34頁。
[59]李歐梵:《看電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第115頁。
[60]
[61]李建軍發表了一系批判《狼圖騰》的文章,其中包括《是珍珠,還是豌豆?——評〈狼圖騰〉》(《文藝爭鳴》2005年第2期)、《假言敘事與修辭病象——三評〈狼圖騰〉》(《小說評論》2005年第2期)、《狼到底是誰的圖騰——讀圣童〈《狼圖騰》批判〉》(《黃河文學》2007年第4期)等。
[62]〔美〕弗·納博科夫:《論契訶夫》,薛鴻時譯,《世界文學》198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