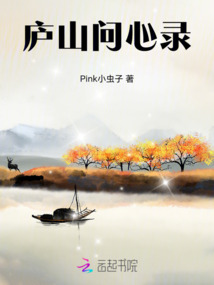
廬山問心錄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潯陽歸客踏江來
飛機開始下降時,程云修猛然從淺眠中驚醒。舷窗外突如其來的陽光如利劍般刺入瞳孔,他條件反射地抬手遮擋,指節撞到了前排座椅靠背,發出一聲悶響。鄰座的中年婦女不滿地瞥了他一眼,繼續低頭織那件似乎永遠織不完的紅色毛衣。毛線針在她粗糙的手指間靈活地穿梭,發出細微的“咔嗒”聲,那團紅毛線在座椅扶手上微微顫動,像一只被困住的小動物。
“抱歉。”程云修低聲道歉,聲音因睡眠干澀而沙啞。他揉了揉太陽穴,透過指縫看見云層如破碎的棉絮般散開,露出下方蜿蜒如銀練的長江和星羅棋布的湖泊。陽光在水面上跳躍,形成無數細碎的光斑,像是撒落的金箔。水網交織的鄱陽湖平原在五月陽光下泛著翡翠般的光澤,而遠處,那片蒼翠的山脈如同蟄伏的巨龍——那是廬山,他闊別十年的故鄉之山。山頂的云霧繚繞,宛如一條輕盈的白紗巾,那是廬山特有的“瀑布云”奇觀。
“各位乘客,我們的飛機即將降落在九江廬山機場,當地氣溫23攝氏度,天氣晴朗...”空乘溫柔的播報聲在機艙內響起。程云修看了眼腕表,這是一塊老式的精工機械表,表盤邊緣已經有了幾道細小的劃痕。下午四點二十分。這趟從LS經停重慶的航班延誤了近兩小時,讓他疲憊不堪。在XZ為期兩個月的采訪讓他曬黑了不少,顴骨處還留著高原陽光灼傷的痕跡,皮膚粗糙得像砂紙一樣。他的指甲縫里還殘留著些許難以洗凈的酥油茶漬,那是他在日喀則偏遠牧區采訪時留下的印記。
機艙里響起此起彼落的手機開機聲。程云修從背包側袋摸出自己那部老款華為手機,指尖觸到采訪筆記粗糙的封面——那是他在XZ的成果,關于雪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專題報道。筆記本的皮質封面已經磨損,邊角處露出了里面的硬紙板。筆記扉頁上沾著酥油茶的褐色痕跡,散發著淡淡的松木香,是他在日喀則一家藏餐館采訪時不小心打翻茶碗留下的。那家餐館的老板娘卓瑪當時慌忙用圍裙擦拭,卻讓茶漬滲得更深了。筆記邊緣已經卷曲,內頁貼滿了彩色便簽,記錄著他在海拔四千米的草原上采訪唐卡畫師、在風雪中記錄格薩爾王史詩傳唱的見聞。有一頁特別皺,那是他在納木錯湖邊寫稿時被突如其來的雨淋濕的。
飛機輪子接觸跑道時的劇烈震動將他徹底拉回現實。透過舷窗,他看見機場跑道旁“九江廬山機場”六個紅色大字,漆面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下方是英文“JIUJIANG LUSHAN AIRPORT”。航站樓造型像展開的書卷,側面裝飾著精美的白鹿浮雕——這顯然是近年新建的,他離開九江時機場還在使用老舊的軍民兩用設施。記憶中的舊航站樓墻上還留著“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標語,每次經過都讓他有種穿越時空的錯覺。新航站樓的玻璃幕墻反射著陽光,像一塊巨大的水晶,倒映著遠處廬山的輪廓。
取行李時,手機在口袋里震動起來。屏幕上“王主編”三個字讓程云修條件反射般挺直了腰背。這位《華夏文化》雜志的副主編以雷厲風行著稱,手下的記者沒少挨訓。程云修還記得去年在云南采訪時,因為一篇稿子改了七遍還被罵得狗血淋頭的經歷。
“云修啊,落地了吧?”電話那頭傳來王主編標志性的大嗓門,背景音里夾雜著編輯部特有的嘈雜聲和鍵盤敲擊聲,“你那組藏文化保護的報道反響很好,社里決定開個‘傳統文化現代傳承’系列專題,第一期就做你老家九江。白鹿洞書院、東林寺、潯陽樓,都是文化富礦啊!”王主編說話時總是帶著濃重的山東口音,把“文化”說成“溫化”。
程云修張了張嘴,還沒來得及回應,王主編又連珠炮似地補充:“知道你剛回來辛苦,放你三天假。但下周一我要看到選題方案,要深入挖掘地方特色,體現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對了,記得多拍些照片,社里準備做圖文專題。”電話干脆利落地掛斷了,留下程云修站在行李轉盤前苦笑。他太熟悉王主編的風格了——從不給人拒絕的機會,布置任務像發射連珠箭一樣密集。
他拖著行李箱走向出口,忽然注意到轉盤旁站著一位穿藏袍的老人,正焦急地比劃著什么。老人臉上的皺紋像干涸的河床一樣深邃,藏袍的袖口已經磨得發亮。程云修在XZ學了點基礎藏語,上前詢問才知道老人找不到接機的親人。他幫老人聯系上對方后,老人從懷里掏出一條哈達非要送給他。這條潔白如雪的哈達此刻正安靜地躺在他背包的夾層里,散發著淡淡的酥油香氣,和他記憶中祖父書架上那本《XZ風物志》里夾著的干枯雪蓮花的味道有些相似。
走出機場大廳,五月的陽光毫無保留地傾瀉而下。程云修瞇起眼睛,看見停車場里整齊排列的出租車,司機們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抽煙聊天。香煙的藍色煙霧在陽光下呈現出半透明的質感,緩緩升騰然后消散。遠處,廬山輪廓如黛,山頂還殘留著最后一抹冬雪,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像戴了一頂銀色的王冠。山腰處的云霧緩緩流動,宛如一條游動的白龍。
九江五月的空氣帶著特有的濕潤,混雜著鄱陽湖的水汽、廬山植被的清香,還有遠處飄來的淡淡茶香——那是廬山云霧茶特有的蘭花香,他童年最熟悉的味道之一。十年前離開時也是這個季節,只是那時的空氣里還彌漫著梧桐絮,惹得他鼻炎發作,噴嚏連連。現在街邊的梧桐樹少了許多,取而代之的是香樟和銀杏,空氣中少了那種惱人的絮狀物。
幾個出租車司機操著濃重的九江口音圍上來:“老師傅去哪滴?市區走啵?”“到潯陽路只要五十塊!”他們的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T恤領口處露出金項鏈的閃光。程云修擺擺手,拖著行李箱走向公交站臺。站牌上“機場-市區”的線路圖顯示會經過長虹大道、潯陽路,終點是煙水亭。這些地名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他記憶的閘門。站臺的金屬座椅被太陽曬得發燙,他剛坐下又立刻站了起來。
長虹大道旁原來有家“德福居”茶樓,祖父常帶他去吃蘿卜餅和糯米雞。那家店的蘿卜餅外酥里嫩,咬開金黃酥脆的外皮,里面是清甜的白蘿卜絲和鮮香的臘肉丁,每次他都吃得滿嘴油光。老板是個胖乎乎的中年人,總愛用沾滿面粉的手摸他的頭,說“小程老師又帶孫子來改善生活啦”。茶樓的八仙桌總是擦得锃亮,上面擺著青花瓷的茶壺,壺嘴處有個小缺口,是某次祖父激動地拍桌子時碰壞的。
潯陽路上曾經遍布古玩店,他總愛溜進去翻看那些泛黃的舊書。有一家叫“汲古齋”的店里,老板收藏了一套民國版的《水滸傳》連環畫,每次他去都能免費看上一兩冊。那家店的門檻特別高,小時候他要費很大勁才能跨過去。店里永遠彌漫著樟腦丸和舊紙張混合的氣味,柜臺上的玻璃罐里泡著各種奇怪的藥材。后來那條街拆遷時,老板特意把那套書送給了他,現在還在BJ公寓的書架上,書頁已經發黃變脆,翻動時會發出輕微的碎裂聲。
而煙水亭...那是李白筆下“登高壯觀天地間”的地方,也是他和同學們逃課去江邊玩耍的老據點。初三那年,他和幾個男生在這里偷偷抽煙,被巡邏的警察逮個正著。他們躲在一個廢棄的漁船里,卻被煙味暴露了位置。祖父來派出所領人時,那失望的眼神他至今難忘。老人什么也沒說,只是默默地走在前面,背影在路燈下顯得格外佝僂。
公交車緩緩駛入城區,窗外的景象卻讓程云修感到陌生。記憶中的低矮房屋被林立的高樓取代,玻璃幕墻反射著刺眼的陽光。狹窄的街道拓寬成了雙向六車道,黑色的瀝青路面平整得像鏡面一樣。連曾經熱鬧的碼頭區也變得規整冷清,只剩下幾艘觀光游輪停泊在新建的躉船旁。只有偶爾掠過的老建筑——那座哥特式風格的天主教堂,尖頂上的十字架依然閃耀;那棟民國時期的銀行大樓,羅馬柱上的雕花依舊精美——還能喚起他的鄉愁。
“下一站,四碼頭,請準備下車的乘客...”機械女聲報站打斷了程云修的思緒。他看見窗外閃過“信華廣場”的巨型LED廣告牌,正在播放某款手機的廣告。記憶中那里原是一片老式居民區,巷子里有家做豆參煮魚頭的小館子。老板姓胡,是個退伍軍人,左腿有點跛,據說是對越自衛反擊戰受的傷。他總愛給常客多添一勺自釀的米酒,那酒裝在舊軍用水壺里,喝起來有股特別的金屬味。程云修十五歲那年第一次喝醉就是在那里,回家吐了一路,被祖父罰抄《醉翁亭記》十遍。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跡至今還留在他中學的作業本上。
車過龍開河時,程云修注意到河岸砌起了整齊的石欄,花崗巖的表面打磨得十分光滑。兩岸建成了步行景觀帶,鋪著紅色的塑膠跑道。幾株新栽的櫻花樹已經開過花了,地上還殘留著些許粉色的花瓣。他想起高中時這里還是條臭水溝,夏天蚊蠅滋生,居民們都不敢開窗。如今卻成了市民休閑的好去處。幾個老人正在河邊的涼亭里下象棋,棋子落在木棋盤上發出清脆的響聲;穿漢服的姑娘舉著油紙傘在石橋上拍照,裙擺隨風輕輕擺動;年輕母親推著嬰兒車在櫻花樹下散步,嬰兒的小手在空中抓握著陽光。城市變遷的魔力令人唏噓。
在煙水亭站下車后,程云修沿著濱江路漫步。夕陽將長江染成金紅色,波光粼粼的水面像鋪了一層碎金。對岸湖北黃梅縣的輪廓在暮靄中若隱若現,幾艘漁船的黑影在水天交界處緩緩移動。江堤上,三三兩兩的市民在散步:白發老人打著舒緩的太極拳,動作如行云流水,衣袂飄飄;年輕父母推著嬰兒車,不時停下來逗弄孩子,笑聲清脆;幾個穿校服的中學生追逐打鬧,書包在背后一跳一跳,拉鏈上的掛飾閃閃發亮。遠處,一艘貨輪拉響汽笛,低沉的聲音在江面上回蕩,緩緩駛向下游的上海。
他找了一處花崗巖長凳坐下,石面還殘留著白天的余溫。打開手機備忘錄開始構思選題,手機殼上貼著他在LS買的轉經筒貼紙,已經有些褪色了。屏幕上的光標閃爍了許久,他卻只打出“九江傳統文化”幾個字。十年記者生涯練就的職業敏感告訴他,這個題目太大太空,需要找到一個獨特的切入點。他想起在XZ采訪時,那個老唐卡畫師說的話:“真正的傳統不在博物館里,而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江風拂過程云修的短發,帶來一絲涼意,也帶來了遠處烤魚的香氣。他抬頭望向西邊的天空,落日余暉為云層鍍上金邊,宛如一幅水墨丹青。忽然,他注意到江堤欄桿上刻著的詩句:“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這是白居易《琵琶行》的開篇,當年祖父要求他背誦全文時,他可是叫苦連天。那些詩句現在讀來,卻有了不同的感受。
琵琶亭就在不遠處,新修的仿古建筑在夕陽下熠熠生輝,琉璃瓦反射著橘紅色的光芒。程云修記得那里原是一處破舊的涼亭,油漆剝落,木柱上刻滿了“到此一游”的字跡。他和同學們常在那里吃冰棍、看江景,把腳懸在欄桿外晃蕩。如今修葺一新,成了旅游景點,門口還立著白居易的雕像。雕像前的簡介牌上寫著:“公元816年,白居易在此送客,寫下千古名篇《琵琶行》。”銅像的表面已經被游客摸得發亮,尤其是那只撫琴的手。
程云修走近細看,發現雕像基座上刻著《琵琶行》全文。他的目光停留在最后幾句:“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當年背誦時只覺得拗口難記,如今讀來卻莫名心酸。祖父曾說,讀詩要知人論世,四十五歲的白居易被貶江州(今九江),正是在這里寫下了這首飽含人生況味的詩篇。那時的江州,對白居易而言就像現在的LS之于程云修——都是遠離權力中心的邊緣之地,卻也因此看到了不一樣的風景。
天色漸暗,江邊的路燈次第亮起,暖黃色的燈光在暮色中顯得格外溫馨。程云修決定先找地方住下。他打開手機搜索附近的酒店,忽然聽到一陣熟悉的旋律——是《春江花月夜》的古箏曲調,從琵琶亭方向傳來。循聲望去,只見一位穿漢服的少女正在亭中撫琴,周圍聚集了不少游客。少女的手指在琴弦上靈活地跳動,指甲上繪著精致的花紋。
琴聲如流水,在暮色中格外清越。程云修不自覺地走近,站在人群外圍靜靜聆聽。少女彈到“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時,琴音陡然轉急,如珠落玉盤。這一刻,他忽然理解了祖父常說的“音樂通神”是什么意思。琴聲停止時,周圍響起熱烈的掌聲,有人往琴盒里放錢。程云修摸了摸口袋,發現自己最小的面額是五十元,猶豫了一下還是放了進去。少女驚訝地抬頭看了他一眼,那眼神讓他想起納木錯湖水的清澈。
“程云修?真的是你?”
一個清亮的女聲從身后傳來,帶著幾分遲疑和驚喜。程云修轉身,看見一位穿著淡青色亞麻連衣裙的年輕女子正驚訝地望著他。女子約莫二十七八歲,皮膚白皙,眉眼如畫,烏黑的長發松松地挽在腦后,幾縷碎發垂在頰邊,襯得她溫婉中帶著幾分書卷氣。她懷里抱著幾本厚重的線裝書,手腕上一串檀木佛珠隨著動作輕輕晃動,散發出淡淡的檀香。她的眼睛在暮色中依然明亮,像是盛著星光。
“許清嘉?”程云修遲疑地叫出這個名字。記憶中那個總愛和他爭論古詩釋義的語文課代表,與眼前這位氣質古典的女子漸漸重合。高中時代的許清嘉總是扎著馬尾辮,穿著寬大的校服,眼鏡后面是一雙充滿求知欲的大眼睛。她課桌上永遠堆著課外書,從《紅樓夢》到《西方美學史》,課間總能看到她埋頭閱讀的身影。有一次她看書太入迷,上課鈴響了都沒聽見,還是程云修用橡皮砸她才回過神來的。
“天哪,得有十年沒見了吧?”許清嘉在他旁邊坐下,懷里的書散發出一股淡淡的樟木香,“聽說你成了大記者,跑遍全國各地?連高中同學群都很少露面。去年聚會時張老師還問起你呢。”她的聲音比記憶中低沉了一些,但依然清脆悅耳,像風鈴在微風中輕響。
程云修笑了笑,注意到她左手無名指上沒有戒指:“什么大記者,就是個到處跑腿的文字民工。”他指了指自己磨破的背包和沾滿灰塵的運動鞋,“剛從XZ回來,那邊條件比較艱苦。”鞋面上的灰塵是LS街頭特有的紅色塵土,怎么拍也拍不干凈。
“XZ?”許清嘉眼睛一亮,瞳孔在暮色中擴大,“是去做那個非遺保護的專題嗎?我在《華夏文化》上看到你的署名文章了,關于唐卡技藝傳承的那篇寫得真好。特別是描述老畫師用金粉繪制佛像眼睛那段,說那是‘將靈魂注入畫布的神圣時刻’,這個比喻太傳神了。”她的手指不自覺地模仿著畫師的動作,在空中劃出優美的弧線。
程云修有些驚訝:“你還在看《華夏文化》?”
“當然,每期都看。”許清嘉輕輕撫平書頁的卷角,這個動作讓程云修想起她高中時整理筆記的樣子,“我現在在九江學院文學院教書,主講古典文學。偶爾也幫白鹿洞書院整理古籍。”她拍了拍懷里的線裝書,書頁發出沙沙的響聲,“這不,下周書院要舉辦‘傳統文化與現代教育’國際論壇,我去幫忙做些文獻準備工作。”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齊,沒有涂任何指甲油,透著健康的粉紅色。
白鹿洞書院?程云修眼睛一亮。這不正是王主編要他做的選題嗎?作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首,白鹿洞書院始建于南唐,朱熹曾在此講學并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堪稱中國傳統教育的活化石。他記得祖父書房里就掛著一幅白鹿洞書院的木刻版畫,老人常常對著它出神。
“論壇對外開放嗎?我是說,我可以去采訪嗎?”程云修不自覺地前傾身體,聲音里帶著記者特有的敏銳。他能聞到許清嘉身上淡淡的墨水香氣,混合著一絲若有若無的茉莉花香。
許清嘉眨了眨眼,睫毛在夕陽下投下細碎的陰影:“當然可以,我還能幫你弄個媒體證。”她忽然笑起來,露出兩個淺淺的酒窩,“怎么,大記者對傳統文化感興趣了?我記得高中時你可是最討厭文言文的,每次默寫《滕王閣序》都要偷看小抄。”她的笑聲像一串銀鈴,在暮色中格外清脆。
“人總會變的。”程云修望向遠處的廬山輪廓,暮色中群山如黛,“特別是在XZ看到那些瀕臨失傳的唐卡技藝、格薩爾王史詩后,才發現傳統文化就像...”他停頓了一下,尋找合適的比喻,“就像長江水,表面上看不斷流逝,實際上一直在滋養著兩岸的土地。”江面上,一艘漁船的燈火倒映在水中,被波浪拉長成金色的絲帶。
許清嘉眼中閃過一絲驚訝,隨即轉為欣賞:“這個比喻很好。其實九江的文化底蘊比你想象的還要深厚。”她如數家珍般說道,手指在空中輕輕比劃,“除了白鹿洞書院,還有東林寺的凈土宗文化、能仁寺的禪茶一味、周瑜點將臺的三國遺跡,更不用說廬山本身——李白、白居易、蘇軾、朱熹...多少文人墨客在這里留下足跡。”她的聲音里帶著掩飾不住的自豪,眼睛在提到這些名字時閃閃發光。
兩人聊起高中同學的近況。班長張毅去了美國硅谷,成了人工智能專家,朋友圈里全是高科技產品的照片;體育委員陳剛繼承家里的茶葉生意,現在是有名的“廬山云霧茶”經銷商,茶葉罐上印著他的大幅照片;當年總考倒數第一的劉胖子居然考上了公務員,在市政府文化局工作,去年同學聚會時已經胖得認不出來了...
“你還記得教語文的張老師嗎?”許清嘉問道,手指無意識地轉動著腕上的佛珠,“他退休后在東林寺旁開了家書院,專門教孩子們誦讀經典。去年查出肺癌晚期,卻堅持不肯住院,說要在有生之年多教幾堂課。”佛珠碰撞發出輕微的聲響,像是時間的腳步聲。
程云修心頭一緊:“張老師...他怎么樣了?”他想起那位總是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的老教師。張老師講課有個習慣,講到激動處會不自覺地扯自己的領帶,以至于那條藍條紋領帶總是歪歪扭扭的。
“上個月走了。”許清嘉聲音低了下來,像是怕驚擾了什么,“葬禮上來了好多他教過的學生,大家輪流朗誦《論語》篇章送他最后一程。他臨終前說,能一輩子與圣賢書為伴,此生無憾。”她的眼眶微微發紅,但很快控制住了情緒。遠處江面上,一艘渡輪拉響汽笛,聲音悠長而哀傷。
暮色漸濃,江風轉涼。程云修想起張老師當年講解《岳陽樓記》時激情澎湃的樣子,粉筆在黑板上敲出一個個白點;想起他因為自己沒背出《滕王閣序》而罰抄課文的情景。那些曾經覺得枯燥乏味的古文,如今想來卻字字珠璣。他記得最后一次見到張老師是在高考結束后的謝師宴上,老人拍著他的肩膀說:“云修啊,你文筆不錯,就是太浮躁,要多讀經典。”當時他只當是老人的嘮叨,現在想來卻是金玉良言。
“對了,”許清嘉從包里取出一張燙金請柬,信封上印著白鹿洞書院的徽記,“這是論壇的邀請函,后天上午九點,白鹿洞書院正門。“她猶豫了一下,又補充道,“我可以提前半小時到,帶你參觀一下書院。這些年修復了不少古跡,還新建了國學體驗館。”她的指尖在請柬上輕輕劃過,留下一道幾乎看不見的痕跡。
程云修接過請柬,觸感細膩的宣紙上印著書院欞星門的燙金圖案,下方是端莊的顏體字:“傳承千年文脈,弘揚圣賢之道”。請柬邊緣裝飾著細小的白鹿紋樣,在燈光下若隱若現。他能感覺到許清嘉的手指在交接請柬時微微顫抖,不知是因為江風太涼還是別的什么原因。
“謝謝,我一定準時到。”他將請柬小心地放進采訪本夾層,忽然想起什么,“對了,你還在研究李商隱的詩嗎?高中時你寫的《錦瑟》解析可是被張老師當范文全班傳閱。”那篇文章他至今記得,許清嘉把“莊生曉夢迷蝴蝶”解釋為對現實與虛幻的哲學思考,讓張老師贊不絕口。
許清嘉眼睛一亮:“當然!去年還在《文學遺產》上發了篇關于《錦瑟》新解的文章。”她看了看手表,表面在暮色中泛著柔和的藍光,輕呼一聲,“啊,這么晚了!我得趕最后一班回濂溪區的公交。”她匆匆起身,又回頭道,“后天見!記得帶相機,書院的晨曦很美。還有...”她頓了頓,嘴角浮現出一抹溫柔的笑意,“歡迎回家,程云修。”她的背影很快消失在人群中,只有那股淡淡的墨香還留在原地。
程云修在攜程上訂了信華建國酒店,這是九江老牌的五星級酒店,離煙水亭只有十分鐘步行距離。前臺小姐用帶著九江口音的普通話熱情地介紹著酒店設施,還特意給他安排了高層江景房。前臺的大理石臺面擦得锃亮,倒映著水晶吊燈的光芒。
“先生是來旅游的嗎?”前臺一邊辦理入住一邊搭話,胸前的名牌顯示她姓李,“最近廬山杜鵑花開得正旺,好多攝影愛好者都上山了。”她的指甲涂著淡粉色的指甲油,在鍵盤上敲擊時像十只小蝴蝶在飛舞。
“算是工作吧。”程云修遞過身份證,證件邊緣已經有些磨損,“我是記者,來做文化專題采訪。”他注意到前臺電腦旁擺著一盆小小的多肉植物,葉片肥厚飽滿,在燈光下呈現出半透明的翠綠色。
“哦!那您一定要去白鹿洞書院看看。”前臺眼睛一亮,耳垂上的珍珠耳環隨之晃動,“最近在辦國際論壇,來了好多外國學者呢。我們酒店還專門推出了‘書院文化主題房’。”她遞過來的房卡裝在印有書院圖案的信封里,散發著淡淡的檀香味。
電梯上升時,程云修透過玻璃幕墻俯瞰九江夜景。長江大橋如一條光帶橫跨江面,車流在上面緩緩移動,像一串發光的珍珠。遠處廬山的輪廓在月光下顯得神秘而莊嚴,山腳下的燈光如同散落的星辰。這座他出生、成長卻十年未歸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電梯里的背景音樂是古箏版的《春江花月夜》,與他在琵琶亭聽到的是同一首曲子。
房間寬敞明亮,落地窗外是璀璨的九江夜景。程云修沖了個熱水澡,溫熱的水流沖走了旅途的疲憊。他換上舒適的棉T恤,布料柔軟得像第二層皮膚。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搜索白鹿洞書院的資料,鍵盤在他指尖下發出輕微的咔嗒聲。網頁上的圖片喚起了他塵封的記憶——欞星門前那對威嚴的石獅,朱子親手栽種的古桂樹,碑廊里那些被歲月磨平了棱角的石刻...最難忘的是書院后山那條小溪,他和祖父常在那里野餐,聽老人講朱熹“問渠那得清如許”的故事。溪水清澈見底,能看見小魚在鵝卵石間穿梭。
祖父程硯秋是九江有名的語文老師,癡迷中國古典文化,尤其崇拜朱熹。退休后,他幾乎每周都要去白鹿洞書院,有時做義務講解員,有時只是坐在明倫堂前的石階上發呆。年幼的程云修常常被迫同行,那時的他對那些晦澀的文言文毫無興趣,總是趁祖父不注意溜去溪邊捉魚蝦,或者爬到樹上掏鳥窩。有一次他捉到一只知了,放在祖父正在閱讀的《四書章句集注》上,把老人嚇了一跳。
直到初二那年,祖父帶他去看了書院珍藏的一部宋版《論語》。當老人顫抖的手指輕撫那些歷經八百余年依然清晰的文字時,程云修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種超越時間的震撼。那些泛黃的紙頁上,先賢的智慧穿越時空直抵心靈。那天回家的路上,祖父對他說:“云修啊,廬山不只是風景山,更是人文圣山。這里的每一塊石頭都浸透了文化的汁液,每一寸土地都沉淀著先賢的智慧。”老人的眼睛在夕陽下閃閃發光,像是含著淚水。
可惜那時的程云修正沉迷于金庸的武俠小說,對祖父的諄諄教誨左耳進右耳出。后來他去BJ上大學,祖父病重時也沒能趕回來見最后一面。這個遺憾像一根刺,一直扎在他心里。此刻,窗外的九江燈火通明,而祖父卻再也看不到這座城市的變遷了。
電腦屏幕的光在黑暗中顯得格外刺眼。程云修關上電腦,走到落地窗前。夜色中的九江燈火輝煌,與記憶中九十年代那個安靜的小城判若兩地。只有遠處廬山的輪廓依舊,沉默地見證著這座城市的變遷。山腳下的燈光如同一條璀璨的項鏈,環繞著這座沉睡的巨人。
明天他要去給祖父掃墓,然后好好準備后天的采訪。不知為何,他對這次白鹿洞書院之行有種奇怪的預感,仿佛那不僅僅是一次普通的采訪任務,而是某種等待已久的召喚。窗外,一彎新月懸在廬山之上,清冷的月光灑在江面上,碎成萬千銀鱗。程云修想起祖父常吟誦的一句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今十年漂泊歸來,他是否能夠看清這座“人文圣山”的真面目?
床頭柜上的請柬在月光下泛著微光,欞星門上的白鹿圖案似乎眨了眨眼。程云修伸手觸碰那個圖案,指尖傳來微微的涼意。恍惚間,他仿佛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耳邊輕語:“回來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