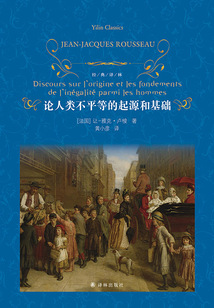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讀
段德敏
作為一本小冊子,《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是盧梭最早的政治著作,它包含了盧梭整體政治思想的主要要素。可以說,這本小冊子打開了盧梭政治思考的大門。理解盧梭的政治思想最好從本書開始。
盧梭的思想通常以激進著稱,但這種激進在他早年或許與他對一鳴驚人的渴望有一定關系。1750年,法國第戎科學院以“科學和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利于敦風化俗”為題征文,盧梭以《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利于敦風化俗》一文應征,斷然給征文題目以否定的答案,結果獲得了第一名,名聲大噪。1754年,第戎科學院再次征文,題目是“什么是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它是否為自然法所許可?”盧梭又以否定的答案提交了論文。盧梭的百科全書派的朋友狄德羅曾記載,最初是他建議盧梭以否定的角度應征科學院的征文,以“顯得更具原創性,從而贏得大獎”。有論者推測,盧梭當時應該是接受了狄德羅的建議,但當他開始沿著這個方向思考時,發現這正是他自己所相信的。當然,這篇論文并沒有像前一篇那樣獲得大獎。盧梭自己對此也有所預料,他在后來的《懺悔錄》中寫道:“這篇東西,在全歐洲恐怕只能找到很少數的讀者能夠理解,而這些讀者中恐怕更沒有一個人愿意談論它。……我早就料到一定得不了獎,因為我深知科學院的獎金絕不是為我這樣的文章而設立的。”對這篇文章的反對聲或許以盧梭在思想上的宿敵伏爾泰發表的觀點最為典型。伏爾泰挖苦道:“從沒有人用過這么大的智慧企圖把我們變成畜牲。讀了你的書,真的令人渴望用四只腳走路了。”顯然,伏爾泰是在諷刺盧梭對自然狀態的褒揚和對文明社會的貶抑。
盡管伏爾泰的嘲諷帶有明顯的個人色彩,但它仍戲劇化地反映了盧梭和當時圍繞在王公貴族身邊的那批啟蒙學者之間的極大距離。后者相信理性和人類文明的進步帶來人的自由和平等;而前者則正好相反,認為人類文明的進步恰恰伴隨著純樸感情的消失和道德的墮落。更為重要的是,人變得越來越不平等,越來越違反人的自然本性。也許我們可以從與孟德斯鳩的對比中窺出盧梭思想激進色彩之一斑。孟德斯鳩出生的時間比盧梭略早,他們的個人背景也有著巨大的差別:前者是具有很高地位的貴族,而后者則是出身底層的平民。但在政治思想上,二者同樣都訴諸“自由”。孟德斯鳩認為歐洲君主國家的貴族傳統是其能保持自由的關鍵原因,貴族的“榮譽”實際上是對君主權力的規范,貴族的獨立地位保證了權力之間的分立和制衡,從而也保證了君主國的自由和法治。可以說,在孟德斯鳩看來,貴族傳統才是歐洲國家自由的源泉,也是歐洲溫和的君主國區別于東方專制國家的最主要因素。
然而,在盧梭那里,這一切都極其荒謬。盧梭拒絕將貴族制與自由聯系在一起。在盧梭的筆下,孟德斯鳩式的貴族的“榮譽”和令人尊敬的獨立性都是“不平等”的表現,都是人類虛妄、驕奢、淫逸、道德墮落的象征。在盧梭看來,難以想象,當一部分人依賴另一部分人,當人人都渴望攀附權貴從而有機會統治別人時,還有什么自由可言。正如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結尾所說:“不管我們如何對不平等進行定義,以下這些顯然是違背自然法則的:孩子命令老人,傻瓜領導智者,一小撮人富得冒油,而大眾則因缺乏生活必需品忍饑挨餓。”盧梭明確地表明孟德斯鳩所贊揚的“榮譽”是違反自然的,或是“不自然的”(unnatural)。這一極具批判性的視角始終左右著盧梭的政治思考。
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政治思想家大都離不開對自然法和自然狀態的描述。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自然狀態是一種不完備的狀態,都需要人類運用理性建立政府來補足這種不完備性。而在盧梭這里,則完全相反。自然狀態是一種理想狀態,歷史上的人類社會則是從自然狀態的墮落。但我們必須知道的是,盧梭對自然狀態的描述與基督教中上帝的伊甸園相差甚遠。盧梭是在用一種類似人類學的方法描述人類心靈的進化史,用研究盧梭的專家茱迪斯·斯珂拉(Judith N.Shklar)的話說,他是在為每一個人立傳,每一個人自然地應該是什么樣子,而他們事實上和現在卻是什么樣子。霍布斯說自然狀態中每個人與每個人為敵,追求對別人的統治是所有人本能的沖動,但對盧梭來說,這卻是社會狀態中的人的典型特征。在自然狀態中,人們絕不會有支配他人的沖動,人們有自我保護的需要,在必要的時候需要用武力保護自身的存在,但支配別人的欲望卻是從社會中發展而來。
當然,盧梭對自然狀態的描述是為了引出他對不平等的理解。盧梭的自然狀態中的人大致處在野蠻人或者野獸的狀態,但他把它當作社會狀態中的人的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在文明進步的過程中實際上放棄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自然狀態中的人是平等的,這種平等并不是生理意義上的平等,因為有人天生更強壯、更聰明。而盧梭所要說的不平等主要指的是“精神和政治意義的不平等”。在自然狀態中人們如野獸一般老死不相往來,至多在異性之間的交媾和照顧幼兒方面有一些交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是幾乎沒有交往的。盧梭說,“難以想象在原始狀態中,一個人需要另一個人,甚于一只猴子或一匹狼需要它們的同類”。既然人們之間幾乎沒有交往,便也不會形成“意見”(opinion)。在自然狀態中,人們頂多有看到同類遭受痛苦時所天然具有的同情心,但他們絕不會產生誰比誰更漂亮、誰比誰更有風度這樣的“意見”。以公眾評價為內容的“意見”只有在社會狀態中、在人與人之間的不斷交往以及互相需要中產生。
在盧梭看來,正是在人類文明的進化過程中產生的人與人之間互相品評的“意見”奠定了社會狀態中不平等的基礎。在盧梭的自然狀態里,人們本能的“自愛”僅限于自我保存,它并不涉及與他人的關系,也與別人的意見無關。然而,人之所以區別于動物,在于其具有完善自己的能力,人不可能永遠如野獸一般生活。當人們結成一定的群體,開始某種交往時,一種新的“自愛”便在人們的腦海中產生了。前一種“自愛”(amour de soi)是一種簡單的生理意義的自我關愛,而后一種“自愛”(amour propre)則涉及精神和政治,它是一種希望得到別人的承認、贊美和尊重的自愛。盧梭說:“人們一開始相互品評,尊重的觀念一在他們心靈中形成,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有被尊重的權利。”每個人都試圖高別人一等,盧梭認為這是人們在進入社會狀態中發展出的心性。也正是這種發展導致了人類一步步走向了不平等的深淵,因為既然每個人都希望被尊重,那么人們必然需要某種穩定的秩序、某種道德觀念來分配被尊重的權利,從而進一步使不平等固定化。
在這個過程中,私有制的產生是關鍵的一環。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對私有制大加撻伐,但他并不像馬克思那樣從階級分析的角度批判私有制的剝削本質。對盧梭來說,私有制的存在為政治統治準備了條件。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上,在誰應該統治、誰應該被統治的爭執中,財富始終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在盧梭的人類文明進化史中,也正是財富以最具說服力的方式確定了誰更值得被尊重,與更漂亮、更聰明、更有力相比,更有錢往往更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自然狀態中的人往往滿足口腹之欲便可,而社會狀態中的人則奮力追求遠超出自己需求的財富,最終不過是為了使自己高人一等。從而,在財富多寡的分殊中產生了人類社會最大的不平等之一。盧梭說:
誰第一個將土地圈起來,膽敢說“這是我的”,并且能夠找到一些十分天真的人相信他,誰就是文明社會真正的奠基者。假如這時有人拔掉木樁,填平溝壑,并且向他的同類大聲呼吁:“不要聽信這個騙子的話,如果你們忘記果實為大家所有,而土地不屬于任何人,你們就全完了!”那么,人類可以避免多少罪惡、戰爭、謀殺、苦難和暴行啊!
“窮人”和“富人”實際上是帶有品評性質的意見。在自然狀態中,人們根本沒有窮和富的觀念,即使某人恰好擁有比別人多得多的食物,這也絲毫不會改變他和別人之間的關系。而在社會狀態中,人們卻熱衷于用這窮和富的分化來判斷一個人應該受到多大程度的尊重。在文明社會中,人們急切地想知道他們在別人心目中的地位,財富則提供了一個相對可靠和安全的標準。
然而,財富遠遠不能確定穩定的秩序。很快,盧梭說:“在最強者的權利和先占權之間產生了無休止的沖突,最終只能以戰斗和殺戮收場。”人類文明在這里才走到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狀態。每個人都想統治、支配別人。也正是在這里,盧梭所要討論的不平等的含義才顯現出來。盧梭說,在自然狀態下,“一個人很可能奪走另一個人采摘的果實,將他殺死的獵物或居住的洞穴據為己有;但是,如何能做到讓一個人服從于他人呢?在一無所有的人們之間,能產生什么樣的奴役關系?”不平等正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從屬關系。對盧梭來說,這實際上是人們接受一個主人的過程。戰爭的狀態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需要一個評判是非的人,需要一個道德體系和法律制度來使人們服從。然而,人們接受的道德標準和法律實質上是富人用來進行統治的工具,那些動聽的格言、高雅的藝術和繁縟的禮節不過是套在人們身上的鎖鏈上的花環。
盧梭在這里要描述的并不是階級的壓迫,而是普遍的人心的墮落。人們從自然狀態中走出來,獲取了更多的能力,文明和藝術獲得進步,但人們失去了原初的純真和平等。在社會狀態中,人們卻愿意擁有一個主人,“所有的人都奔跑著迎向枷鎖,認為這樣可以確保他們的自由”。《社會契約論》中的名句“人生來自由,卻無處不身同奴隸”,并不是對有產者的控訴,而主要是對人心的失望。在這種社會狀態之下,打破枷鎖的人不過是為了回過頭來把枷鎖套在別人頭上,這個枷鎖并不是套在被剝削階級、被壓迫階級頭上,而是套在“每一個人”頭上。事實上,有趣的是,盡管盧梭不遺余力地描述不平等的產生,但他對下層階級的反抗事實上并不感興趣。其原因主要在于,在盧梭看來,反抗的結果很可能是為社會確立一個新的主人。盧梭所要追求的是一個沒有主人或者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的社會。顯然,這一社會是以自然狀態為參照的。
需要指出的是,盧梭也并不是要人們回到自然狀態。盧梭并沒有貶低人完善自己的能力,他批評的是人在完善自己的過程中失去本來具有的純樸感情,成為別人的意見的奴隸。事實上,人們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回到自然狀態。盧梭時刻以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做對比,主要是在用自然狀態的鏡子照出文明社會的諸般丑惡和不堪。他在告訴人們,那些看起來牢不可破的傳統和等級都是與自然相悖的產物,它們“并沒有任何真正的天然基礎”。人心的變化是一個微妙的過程,人們本應可以保持自己那份純真,從而也可以維持他們之間的平等關系,但在文明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他們卻微笑著迎接他們的枷鎖。
在《愛彌兒》中,盧梭以兒童教育的視角探討如何保持人自然的獨立性和純樸感情,而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則以一個共和國為例,討論在政治社會中如何維持人的自由和平等。顯然,這些討論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都能找到它們的雛形。“將人們從自然狀態引向社會狀態的道路已經被遺忘和迷失”,盧梭要尋找的是如何在社會狀態中維持人的“精神和政治”上的平等。寫于1762年的《社會契約論》無疑是這一探討過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以這樣的評論結束:“不管我們如何對不平等進行定義,以下這些顯然是違背自然法則的:孩子命令老人,傻瓜領導智者,一小撮人富得冒油,而大眾則因缺乏生活必需品忍饑挨餓。”而《社會契約論》則以這樣的宣示開頭:“當一國人民被迫服從并且服從的時候,挺好;一旦他能夠擺脫桎梏并且那么做了,那就更好。”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是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的核心訴求。不能回到自然狀態做自己的主人,則努力在政治社會中成為自己的主人。
在人們通過契約建立的共和國中,每個人都將自身置于公意的指導之下,而“每個人既然是向全體獻出自己,他就并沒有向任何人奉獻出自己”。在公意的指導下,沒有人是別人的主人或奴隸,“精神的和政治的”平等是衡量人們是否自由的標準。盧梭以古典時代的斯巴達和當代的日內瓦共和國為藍本,將它們理想化,從而構想在社會狀態中實現這種平等的可能性。公意既不是神意也不是具體個人的意志,它是全體公民相結合而構成的意志。公意的抽象性保證了參與到公意中的人們之間的平等性,只要是公意在統治,那么就不是某個具體的人在統治,從而人與人間的從屬關系也就不存在。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盧梭所分析的不平等,既不是指經濟或階級關系上的不平等,也與底層人民起來反抗的所謂“民主”相去甚遠。盧梭的思想所循的是一條西方共和主義的線索。本書開宗明義所給出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主要指的是權力上的依賴關系。自然狀態中的野蠻人并不依賴于任何人,他們是完全獨立的,因而也就是平等的。而在社會狀態中,人們難以擺脫的正是這種依賴關系,總會有富人和窮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主人和奴隸的區別。在盧梭看來,雖然困難,社會狀態中的人們并不是沒有擺脫不平等噩夢的可能。盡管相對于自然狀態來說,文明的進步與人類不平等的發展直接相關,但文明本身并不一定是人類的詛咒。人類可以而且應該在社會狀態中追求平等,人類社會不一定只有一個不平等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