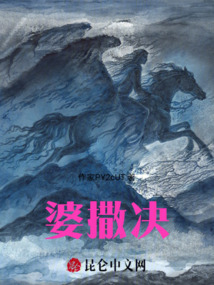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何者當因
霞光流溢,映照得佛寺熠熠生輝。
廊下搖椅之上,一位老和尚悠然躺著,喃喃自語:“佛曰不可說!”
鄭岑芳將茶斟滿杯,終是按捺不住,啟唇問道:“大師,他在里面嗎?”
“在或不在!在于不在,皆取決于你。”
鄭岑芳凝視著寺院四周,若有所思。她一路艱辛打聽,終是尋至此處,可惜,在此居住月余,卻未曾見他一面。
三年前于江夏分別,原以為再無相見之機,抑或會是仇人相見。可時至今日,她竟主動尋他,只為求得一個說法,或是再聽他說一次大話,亦或是讓他再摸一次頭。
老和尚轉過頭來:“五年前,他就來了。”言罷,轉身又睡了過去。
鄭岑芳猛地一愣,心中思忖,五年前,絕無可能,三年前才在江夏見過他,倘若他未曾出寺,那三年前自己見到的又是何人。
鄭岑芳再也坐不住了:“老東西,別睡了,再不告訴我他在何處,定要拆了你這破廟。”
“呵!五年前,李施主初來此地,也說過此般話語,李施主總道大殿破舊需得翻新,故而拆舊蓋新。”
“大師,我只是想見他一面,過分嗎?”
“佛曰:不可說。”
這是鄭岑芳來到這里聽聞最多的一句話,究竟有何不可說?她不停追問,卻無人應答。寺里的每一位和尚見了她,都避之不及,只因她是女子。“女施主,阿彌陀佛。”每次聽到這話,她便不再為難他們。原本佛門清凈之地,不讓她留宿,可寺里的大師傅卻破例讓她住在后山的小屋。“后山本是寺里的菜園,以前有一位看園子的老師傅,老師傅圓寂后,小屋一直空著,女施主若不嫌棄,可暫住于此。至于女施主所問,老衲無法回答,佛曰不可說。女施主若有閑暇,可來寺里多聽聽講經,說不定能自行悟得答案。”自那日起,她除了午膳、晚膳,便是欺負偶遇的和尚。“小和尚,你拿的是經書嗎?可否借我一閱?”
“師傅不好了,經書……女施主拿經書往香爐里扔。”“唉——”
“師傅,女施主……”
“老和尚,你找我?”她就那般趴在桌上,以手抵頭,望著大和尚。
“施主,老衲乃出家人。”
“嘿!這大光頭,怎的不反光呢。”說著,她便伸手去摸那光頭。
“阿彌陀佛!”
自那以后,所有和尚望風而逃,轉身離去,被抓到的也都設法快跑。
約莫五年前,他來了。清晨,師弟去開山門,見他醉倒在門口。佛家之地,實難容他這等世俗之人,可師弟怎么都喚不醒他。我聽聞師弟呼喊,出門瞧了一眼,也不知為何,總覺得似曾相識,許這便是因果業報。我在廟里住了近二十年,他終究還是找來了。
“后來呢?”鄭岑芳吃著素面,聽他講述著他的故事,這怕是她頭一回從他人之口了解他,每一個細節她都想聽。“再來一碗。”
我讓師弟扶他進來,畢竟那天下著大雪,放任他在外,恐會凍餓而亡。可他渾身酒氣,又怕驚擾了菩薩,便將他安置在后山。
“便是我住的那間小屋。”
他睡了兩日,醒來頭一件事,便是將院子里的菜全都拔光。他言自己不白吃他人之飯,既然留他過夜吃飯,他就干點活抵飯錢,便幫我們把院里的菜都拔光了。望著光禿禿的院子,他忽地笑了,他說這樣的院子才配我們的發型。
“大師,不如我也幫你們干點活吧,您告訴我他在何處?”
“廟不大,女施主何不自己找找看。”
鄭岑芳倒是想過,可即便找到他又能如何?說些什么?該問他何事?他決定之事,從未有過更改的可能。三年前,他近乎癲狂地狂笑了一夜,喝遍了三條街。她知曉他定是遭遇了事,次日話都未說,人便消失無蹤。她只是隱約憶起他曾提及的這個地方,他常言自己信佛,可惜六根不凈,守不住清規戒律,貪杯好飲,佛門不收他。后來方知,并非因清規戒律,而是因其出身道門,祖父乃是當今正一的當家祖師,按理說他日后可是要接任天師的。又怎會讓他入佛門,所以,他發狂的那一夜定是窺破了天機,至于這天機究竟為何,她想要知曉。
“您可曾聽他提及過什么?諸如他的身世,他的命數?”
大和尚坐起身子:“佛曰不可說。”
“那便是知曉了,他總言自己活不過五十,四九當是終數,究竟為何?”言罷,一指寒風掠過和尚眼前,遠處的銅鐘正兒八經地被隔空敲響,凜冽的劍氣擊在十米開外的銅鐘上,她已失了耐心。
大和尚亦瞧出了,這一指夾雜著千萬人的冤魂,乃是白骨堆積而成。
“女施主究竟從何而來?”
“呵!從來處來啊!”那玩世不恭的態度,加之和尚們的禪機妙語,竟說得如此順口。
“唉,那口鐘已然二十多年未曾響過了,二十多年前有一位屠戮萬人的將軍來到此處,只求和尚們能救一救他的愛人。這一生殺人無數,活著于他而言毫無意義,所有人都將他視作惡魔、怪物。唯有一人把他當成了人,為他煮了一碗素面。她說,她的家鄉自幼便遭屠城,她一路討飯至此,是廟里的和尚救了她。因她是女子,不能留在廟里,她便到山下賣素面為生。見到他時,她已病入膏肓,多年積勞成疾,回天無力。他帶著她回到廟里,廟里的師傅言只要他能讓三千銅鐘不絕而響,便可救她。他不停地拼命敲,就用那把砍過無數人的刀不停砍著銅鐘,可不論他如何敲,至多也只能將十幾口銅鐘一同敲響。最后,她還是走了,她未等到三千銅鐘的絕響,他便在廟里住了二十多年,一直苦思如何讓三千銅鐘絕響。女施主,同樣的問題,老衲想問問您。”
鄭岑芳頭一次站在大殿的筑基之上,她對逛廟毫無興致,從未發覺,寺里竟有如此多的銅鐘。“老和尚,你挺有錢的嘛,將這些銅鐘拆了變賣一番,半輩子足夠了吧。”
和尚終是坐不住了,即刻從搖椅上起身:“女施主,莫要動手,這些銅鐘皆是善信捐助的,據說皆有百年以上,在下來此二十多年,從未想過……阿彌陀佛,老衲懇請女施主收手吧。”他怕了,上一個欲拆他的大殿,他未加理會,次日,大殿的門窗便沒了,留下的立柱上寫了兩個字:通透。今日又遇一個要拆他銅鐘的,倘若他不開口,估摸明日這些銅鐘也只能剩下空架子了。估計還會留下兩個字:清凈。和尚怕了,從未見過這般人物,這是第二個。“女施主,是否欲知他為何會來此?”
“不想,我要知曉他在何處?”
“女施主不是剛言從來處來,欲知他在何處,便要知曉他如何而來。”
“有道理。”
轉身翻下大殿的筑基,坐在搖椅上瞇著眼,喝了口茶:“舒服,難怪你整日都躺在這,老和尚挺會享受的嘛,說吧,我聽聽。”
五年前,他醉倒在山門口……
“停,停,停,聽過了,換一換。”
身后的小和尚抬頭開了口:“師傅講述的確實是李施主進山門的過程,可……師傅不知,是我為李施主換的衣裳,換衣裳時李施主說了一句……”
“唉~”
“何話?”
小和尚面帶苦色,看看師傅,又瞅瞅鄭岑芳:“李施主說:該走了,該走了。”
“何意?”
“小和尚不知,李施主似是有備而來,彼寺在穹山后峰,平日里鮮少有施主前來,那日還下著大雪,李施主應當就是沖著本寺而來。”
老和尚轉身在樹下的臺階上坐下:“是沖我來的,該來的總會來,該走的也無法挽留,該走了!”
“究竟何意?”
老和尚搓動念珠:“事情大約是三十年前。”
鄭岑芳突然后仰:“越說越亂,你們這些和尚是不是總喜歡說一半留一半,所有事都讓人去猜,猜不到呢,又跟你講一堆道理以證一句話的意義,美其名曰叫悟,滿口什么禪機已到,對了,他也常說此句,太累,就不能簡單些,好懂又好記。”
“佛家講因果,老衲便是那個因,至于果,李施主不愿承擔的那個結局,我們稱為業報。”
鄭岑芳喝著茶聽他講述,還是莫要打斷他了,繼續說吧。
老和尚搓了好一會兒念珠:“三十年前,貧僧尚未出家,當時天下大亂,諸多地方皆在鬧饑荒,家里的大哥率先餓死了,緊接著是小妹。實在沒法子了,我與三弟出門討飯,走了好些天都未討到一口吃食,遍地皆是餓死之人。不知走了多少日,終是走到一個村子。進村不遠的一戶人家,家里僅有一個女人帶著個孩子。三弟實在餓急了,便翻了進去搶了些吃食,女人拿著柴刀追了出來。我也急了,一把拉過三弟,女人不知何故突然倒地,柴刀恰好砍進了她的脖頸。我們只是想要一口吃食,不想餓死,卻失手殺了人。我讓三弟快走,我就那般坐在院子里等著村里的人去報官。那個時候,哪里還有官,無非就是鄉紳大戶說了算。我被村里自稱是里長的人抓起來吊在了谷場上,本以為一切都結束了,終于不用餓著肚子活著了……”
鄭岑芳險些睡著,這個因著實漫長……出家人,南無阿彌陀佛。“大師,您能快些嗎?”
“唉,往事如夢已如幻。我仍記得那日是個正午,太陽甚大,我又餓又困,迷迷糊糊中,遠處走來一人,是個道士,背著個布包坐在不遠的石臺上,一來便打聽為何將我吊在此處。待我醒來時,已然被放了下來,還有吃食。里長言語譏諷,說是道長用他布袋里的藥換了我一條命。我吃飽之后,立刻去谷場上見他。他坐在石臺上為村里人治病,我走過去跪下謝他的救命之恩。他扶起我說我不該死在此處,這便是機緣。他言我或可改變這天下,亦或是讓天下所有人都有飯吃,他今日救我一命可為日后天下格局做一個因,這方為道。倘若我真如他所想讓天下得以改變,便是成全了他的大道。”
鄭岑芳差點把杯子扔地上:“大師,這與他有何關系?三十年前他還……他才剛出生而已。”
老和尚搖頭:“那個救我的便是他爺爺李在山。”
鄭岑芳終于聽到了些感興趣的,頓時來了精神:“繼續,繼續,后來呢?”
“后來,我與他在村里住了好一段時日。平素我就在村里當佃戶打工換兩頓飽飯,晚上便與李在山住在村后的土地廟里。他與我講了許多,還教我本事,日后遇到強盜土匪還能防身。我也終于知曉了,他所謂的大道是何。按他所言,這天下紛爭不斷,人們本可以不變應萬變,可一人變,天下變。他欲憑借自身本事結束這天下紛爭,可一人之力遠遠不夠,他就……據李在山講,他們家祖上留下了三本奇書,家祖有言如若天下需要,可打開其中一本逆勢而為,如若太平盛世,李家后人不可為。”
鄭岑芳終于聽到了重點,如今想來,他應當也動了那三本書,他那脾氣會聽祖訓?鬼才信。“如此說來,他偷看了那三本書?”
老和尚搖頭:“何止偷看,他把三本書全燒了,如今他便是那三本書……這也是我見到他之后才知曉的。”
鄭岑芳突然不想找他了,反倒對那個三十年前的故事興致盎然:“那三本書寫了什么?”
“無人知曉寫了什么。三十年前,聽李在山說過些許。本來此種事皆是祖上密事,不會對外人言。李在山說我與三本書有機緣,可因是祖上之物,故而不能給我參讀,只是與我講了些書里的秘法。李在山講他也只翻看了一本而已,便得了窺天之力,而這開天眼的本事也不過是書里簡單易懂的部分。李在山修習二十年,從推演術數,到五行奇門,終于得以開了天眼,只一眼便看到了因果。據他所說,此書為逆世之法,修習者先要舍棄自己本心大道才可修習,然后再以第二本順勢道法歸于本心,成就不世大道基業。可李在山只修習了一本便無回天之力,他怕自己走火入魔,禍及天下,所以第二本從未翻開過,一生行醫濟世,只為贖罪,可最后……”
鄭岑芳突然坐起:“李家人倘若每幾年便尋一個修習三本秘法,是否就能獨步天下了?”
“獨幽晃晃六百年,修習秘法者一千多人,到李在山這僅有四人窺了天道。”
“那他呢?”
老和尚起身走向大殿:“晚課到了,女施主若想聽,明日老衲再與你講。”
鄭岑芳猛地一愣:“什么嘛,干嘛,沒講完呢,我連夜拆了你的廟你信不信,回來老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