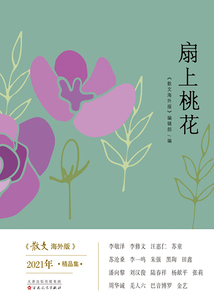
扇上桃花:《散文海外版》2021年精品集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雜言三則
李敬澤
一盞歷史之茶
熱帶很熱,太陽垂直地吊在頂上,人的腦袋就不免昏昏沉沉的,想睡覺。高更的畫兒里,塔希提島的人、植物和石頭不是正睡著,就是剛醒來或將睡去。高更厭棄現代文明,不遠萬里去尋一個盡情睡覺之地。反過來說,所謂“文明”,就是盡可能少的睡眠和盡可能清醒的頭腦。
所以,一位新加坡政治家認為,空調的發明具有偉大歷史意義,它使新加坡或者塔希提與巴黎或紐約有同樣涼爽的室內環境,熱帶地區的人民由此可以振作精神,把更多睡眠時間用于工作、思想和創造。
——這很好。但我要談的是茶,飲茶是中國人的偉大發明,據說公元五〇〇年左右飲茶的習俗開始廣為傳播,那是南北朝時代;到了唐代,陸羽著《茶經》,對飲茶進行了最初的文化闡釋: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澀、四肢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
看看這些癥狀吧:又熱又渴,心里發悶腦袋疼,渾身倦怠睜不開眼,總之是無精打采昏昏欲睡,這時就應該喝茶。
沒有發明飲茶之前,比較上進的中國人是很痛苦的,“頭懸梁、錐刺股”,我們的老祖宗與人要睡覺這一自然節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后來有了茶,每天喝上幾壺,大家都成了“精行儉德之人”,人人朝氣蓬勃,想睡也睡不著,于是能以更多的時間、更高的效率去做更多的事,比如批公文或者織布,比如畫畫兒或者寫詩。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文明史上的關鍵時期,宗教、繪畫、書法、詩歌,各種精微的精神形式如鮮花盛放,中國人的眼睛好像一下子亮了,心像絲綢一樣敏感,文明由簡樸、粗豪變得華麗、繁復。原因何在呢?當然是飲茶。茶除了讓人少睡覺還讓人心明眼亮,茶是提神的,所“提”之“神”是“精神”。
同樣,咖啡在十七世紀初傳入歐洲,所謂“啟蒙”“理性”“現代”,所謂“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大概都是受了咖啡因的刺激。茶不僅提升了我們的精神,我認為它還極大地改善了全民族的腸胃功能,因為茶可解酒,有助消化之功效,而這一點對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尤其緊要。那些馬上的好漢,天天喝酒吃肉,千萬年來備受消化不良之苦;終于,南方的農夫們發現了這種神奇的樹葉,它消食化瘀,令人上下通暢,于是草原上馬更快,刀更亮,成吉思汗的大軍喝著開胃的奶茶席卷南宋,鯨吞大半個世界。
但農夫們有更精明的算計,他們用另一種方式征服世界。在歷史的疾風猛雨之下,茶一直穩定地、源源不斷地將白銀吸向中國。自唐代起,茶葉就是我們文明的基本物質因素,它和陶瓷、絲綢一樣,在漫長的時間里壟斷世界市場。北方的游牧民族要喝茶,后來英國人也離不開茶,那么好吧,拿銀子來!那時咱們多牛啊,僅憑著茶葉就能維持絕對、長久的貿易順差。
這種傲慢到了鴉片戰爭依然拖著長長的影子,那時有聰明人目光如炬,一眼看出英國人的色厲內荏:只要咱不賣茶葉,那些鬼子還不得大便干燥,活活憋死?
這倒不失為“釜底抽薪”之計,但問題是老先生們不知道,英國人那時已經在印度大規模種茶,而最初的種苗恰恰是由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從中國帶往印度的。
此事發生在一七九四年,馬戛爾尼在咱們“圣明”的乾隆皇帝那兒碰了一鼻子灰,離京南下澳門。途經江浙一帶時,“弄”了幾株優質茶苗——這事就發生在天朝陪同官員的眼皮底下,他們樂于對沒見過世面的洋人表現居高臨下的慷慨大方。
但就在那一刻,茶的歷史光輝悄然消散。茶不再是文明的榮耀,不再是神奇的財富,它只是茶,一種日常飲料。
——此時,手邊是一盞陳茶,作為抵抗睡眠、反對沒精神兒的武器,我覺得它不如咖啡;如果我吃撐了,更有效的辦法是服用胃動力藥;作為一個無所用心的飲者,我可以喝中國的龍井、烏龍、普洱,利普頓紅茶我也喝得,當然,天要熱了,室內須有空調。
我喜歡的島嶼
威爾基·柯林斯是我最早知道的英國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讀了他的《月亮寶石》,印度王冠上的寶石帶著詛咒流落英國,誰擁有了寶石,誰將遭遇災禍。故事的具體情節我記不清了,但我記得那三個纏頭的印度人,他們好像吹著笛子,好像還玩著蛇,他們是寶石的守護者,是命運的使者,他們追隨寶石,直到天邊。
現在我會告訴你,這個故事是殖民心理的例證:他們對“東方”的占有欲,對“東方”的恐懼,以及潛意識中的罪孽感。但二十幾年前,在“月亮寶石”中我只看到了“英國”,那遙遠、神秘的島嶼。
后來,一個人長大了,上中學、上大學、工作,經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像同時代的中國讀書人一樣,我也在歐亞大陸上從東到西地漫游: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蒼茫的莫斯科,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宏偉的圣彼得堡;布拉格彎曲縱橫的街巷,卡夫卡和昆德拉像鼴鼠一樣溜過去;還有柏林、維也納,那是尼采、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和弗洛伊德的城市;當然條條大路通巴黎,穿著睡衣的盧梭、矮小的薩特、禿頭的福科、筋疲力盡的羅伯·格里耶和瑪格麗特·杜拉斯……一大群法國人等待著我們。
通往西方的路有兩條:一條陸上,一條海上。由于某種神秘的原因,當代中國讀書人的求知之旅通常都是搭乘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但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從海上西去,搭一艘十九世紀的船,最終在海平面上看見島嶼浮起,海浪拍打荒涼的礁石。
——那是不列顛群島。從地圖上看,它像歐亞大陸掛在胸脯上的一枚墜飾,幾百年來,它一直猶豫不定:是歸入大陸的懷抱,還是轉過身去,獨自漂向茫茫的海洋?它驕傲、世故、頑強,它眺望大陸上的風起云涌、樓起樓塌,骨子里是不動心的,就像一張紳士的臉,心藏在灰色的眼睛后面。
我喜歡英國,喜歡福爾摩斯,他的瘦臉,他的黑披風,他冰冷、堅韌的理性;還有狄更斯,我認為他比巴爾扎克至少高明1.5倍,他筆下霧氣沉沉的倫敦是人類想象的奇觀;還有羅素,又老又無恥的羅素,他鎮定自若地解說這個世界;還有披頭士,穿學生制服的天使般的搖滾,我覺得他們和王爾德一樣瘋狂卻又優雅。我甚至喜歡黑方、紅方,它比較重,還有Burberry的雨衣和格子圍巾,那是自然、考究的趣味,相比之下,巴黎的時裝像馬戲團的行頭。當然,我還喜歡費雯·麗、戴安娜……
對我來說,這個島嶼是一種銀灰色的精神現象,低調、華貴、堅硬牢靠。英國人培育和發展了經驗主義的思想傳統,他們相信,理性解決不了的事發瘋更解決不了,這種傳統下的哲學家通常“不好看”,他們保守、冷靜、負責任,不直奔“終極”,不把哲學、歷史想象成詩,你不能設想在英國會有海德格爾或盧梭,就像不能設想英國人會把一切砸爛從頭再來。
英國的文學也有同樣的氣質。我讀過格雷厄姆·格林的所有中譯本,我奇怪為什么中國作家很少提到他,我認為他是現代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他的尺度感、他對人性的精細觀察、他內在的深厚和藝術姿態的平衡都是中國小說家所缺乏的。
但格林下盤太穩,太講內功,他在中國遭到冷遇也許是因為他不像英吉利海峽對面的同行們那樣凌空蹈虛、花拳繡腿,他大概從來就沒想過怎么破壞小說,他只愿把小說寫好。
很多人不喜歡英國文化,但我喜歡。如果讓我講道理,我希望我是羅素,假設我寫小說,我希望我是格林。我愿意想象:很早以前我已經坐上船,向著那個島嶼出發,威爾基·柯林斯,這個十九世紀的三流小說家、這個陰郁的老家伙就是我的船長。
反游記
我一向認為寫游記在這個時代是一件無聊而可疑的事。在這個時代,無數人飛來飛去,旅游已成大規模工業,駕著汽車的先生小姐們探遍窮鄉僻壤,攝像機和數碼相機把世界的每一個羞處打開。“游記”的生活前提和文化前提幾乎不復成立。
所有的“游記”都在說一件事:“我”在“現場”。游記作者秉持愷撒式的氣概:我來、我看、我寫。
而我想加上一條:我疑。我懷疑我的眼睛和頭腦,我認為我們大驚小怪地宣稱看到并寫出的,通常都是我們頭腦里已有的,所謂“現場”、所謂“風景”,不過是境由心生,是一場眾所周知的戲。
盡力穿越幻覺,對“我”、對“現場”保持警覺,在“我”和“現場”之間留下“客氣”的余地,這即是我所謂的“反游記”——如果一定要寫的話。
人生如逆旅,此身原是客,既是客,就該客氣、有禮,游記是不客氣的文體,正如照相機是不客氣的機器,它們都不信這山河這人世自有不可犯的隱私,它們自負地把逢場作戲當成了隱私——套用一句流行的格言,旅游就是觀看“光明磊落的隱私”,而寫游記和拍照片則是想著對方,自己亂動。所以,我不寫游記,我寫“反游記”。但是,我仍然喜“游”,獨在異鄉為異客,那是生命的本質所在。所以,我現在的理想是:寫一本暢銷書,賺一筆大錢,買一只質地上好的皮箱,裝上書和衣服,然后,到很多地方去,住在飯店里,在陌生人中,做陌生的客人,一直如此,到死。當然,據我所知,這件事難度甚大,只有納博科夫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