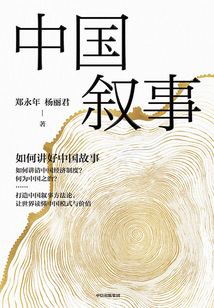
中國敘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最新章節(jié)
- 第23章 附錄2 講好中國故事,世界性和中國性不可分割[1]
- 第22章 附錄1 講好中國故事,需要構建中國原創(chuàng)性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1]
- 第21章 中國的應對
- 第20章 美國的對華認同政治戰(zhàn)
- 第19章 《中國如何應對中美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當代認同政治惡化著各國內政和外交
- 第18章 中國:共產(chǎn)黨的制度創(chuàng)新與中國之治
第1章 自序 中國敘事:從讀懂中國到主動解釋中國
“中國為何?”已經(jīng)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重大問題,甚至是最主要的一個問題。盡管我們內部這些年也在討論“何為中國”的問題,但這只是一個層面的問題,即中國的內部認同問題和“中國”形成過程中那些恒定的因素與變化的因素。而國際層面的討論似乎更具哲學和理論意義,即要為中國定性——中國代表的是一整套什么樣的價值系統(tǒng)。美國總統(tǒng)拜登在2021年12月召開所謂的“世界民主峰會”就是要實現(xiàn)其世界“兩極化”的目標,“兩極”即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一極和以中國為代表的一極。拜登執(zhí)政之后,一直把中美關系簡單地定義為“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之爭。人們普遍認為,拜登組織的“世界民主峰會”實際上是美國對華意識形態(tài)冷戰(zhàn)的“宣言”。美國的這種行為并不難理解。自登上世界舞臺以來,美國的一項重要使命甚至可以說是宗教式的使命,便是把美國所代表的西方價值觀帶向世界其他地方,或者讓世界其他地方接受美國的價值觀。
就知識追求而言,意識形態(tài)之爭毫無意義。如果從意識形態(tài)出發(fā),知識就非黑即白,但真實的世界并非如此。在真實世界中,人們都可以找到幾種主義共存的現(xiàn)象。正如經(jīng)濟學家熊彼特在其大作《經(jīng)濟分析史》中所詳細討論的,在資本主義成為西方主導性生產(chǎn)方式之前的封建社會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幾乎所有要素。從經(jīng)驗來看,簡單地用“主義”來分析歷史的進展并不科學,因為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tài)中,都可以找到被人們稱為各種“主義”的因素;同樣,人們所宣布的用一種“主義”替代或者消滅另一種“主義”的情況也沒有發(fā)生。現(xiàn)實如此復雜,人們并不能用一種“主義”來概括之。
但是,人們絕對不能低估以“主義”為代表的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性。如果忽視了各種“主義”之間競爭和斗爭的歷史,人們很難理解迄今為止的歷史是如何造就的。就大歷史而言,近代以來已經(jīng)發(fā)生了兩波世界范圍內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第一波是歐洲國家內部資本對馬克思主義的圍堵。西方經(jīng)濟史上,從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到二戰(zhàn)以后以芝加哥學派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聚焦的是如何創(chuàng)造財富。而以盧梭和馬克思的理論為代表的經(jīng)濟學探討的則是如何實現(xiàn)社會公平。前者代表資本的利益,后者代表勞動者的利益。馬克思主義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基礎,自然就遭遇了資本的圍堵和扼殺。資本對馬克思主義的圍堵盡管主要發(fā)生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內部,但也是很血腥的。兩者之間的對立直接促成了資本主義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第二波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lián)的圍堵。十月革命之后的蘇聯(lián)把馬克思主義現(xiàn)實化,消滅了私有制和市場,強化國家在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這和西方資本主義形成了直接的對立。蘇聯(lián)處于西方的外部,美蘇冷戰(zhàn)持續(xù)了半個世紀,最終以蘇聯(lián)的解體宣告結束。
今天,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轉向對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進行圍堵。對此,我們應當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希望中國成為另一個“西方”國家。盡管西方向中國開放是基于利益考量,但美國的這種“希望”構成了其向中國開放的政治算計。美國一旦認為中國不僅不可能變成它所希望的國家,還對它構成了挑戰(zhàn),就轉而把中國歸入“另類”,圍堵和遏制中國。今天美國對中國所做的一切,和美蘇冷戰(zhàn)期間美國對蘇聯(lián)所做的并沒有多大的區(qū)別。當然,美國是否有能力像圍堵蘇聯(lián)那樣來圍堵中國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在這個國際大背景下,人們不難理解近年來我們一直所從事的“讀懂中國”事業(yè)的重大意義。因為中國的崛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往何處去有很多不確定性。一些西方國家更是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邏輯強加在中國身上。所以,我們要逆轉這個局面,幫助國際社會讀懂中國,不要讓西方把對中國的理解強加到我們身上。和西方不同,我們有中華文明自身的邏輯。盡管我們是在開放狀態(tài)下成長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也向西方學了很多經(jīng)驗,但我們不僅不會變成西方國家,反而越來越“中國”。這些年,我們提倡“文化自信”(或者“文明自信”)就是中國文明復興的理論表述。
就我們自身而言,如果“讀懂中國”主要是幫助世界讀懂中國,那么我們首先需要自己讀懂中國。但這個問題恰恰是人們所忽視的,因為很多人假設我們是懂中國的。這些年來,我們在“講中國故事”領域花費了不少人財物力,但效果似乎不是那么理想。如果我們越講,人家越不懂,那么就表明我們講故事的內容或者方式是有問題的。固然不管我們如何講故事,外在世界的少數(shù)人,尤其是那些堅定的反華人物,總是“不懂”,但這一解釋并不適用于大多數(shù)人。如果我們講的故事為外在世界的大多數(shù)人所聽懂和接受,那么這些少數(shù)人的“不懂”也就不重要了。故事沒有講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講故事者本身沒有“讀懂中國”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近代之初,中國實際上是從“讀懂西方”開始的。那個時代,因為封閉、落后,中國被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打開了國門。我們挨打,所以我們邁開開放的第一步就是讀懂西方。就是說,盡管近代以來的第一波開放是被迫的,但就我們自己而言,這一波開放就是從讀懂西方開始的。第二波開放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鄧小平所開啟的改革開放。這一波開放是主動的開放,但實際上也是從讀懂外在世界開始的。在80年代,那些近代以來幫助我們讀懂西方的作品,無論是翻譯過來的西方作品還是中國學者自己寫的介紹西方的作品,一版再版,就是一種具體表現(xiàn)。在改革開放40多年之后,中國已經(jīng)融入世界。照理說,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擁有了優(yōu)越的條件來同時讀懂世界和讀懂自己。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無論是讀懂世界還是讀懂中國,我們都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就如何讓世界讀懂中國來說,我們自己讀懂中國必須被置于最高議程。很顯然,如果我們自己都不能讀懂中國,那么如何幫助外在世界來讀懂中國呢?
也就是說,我們更需要幫助自己讀懂中國。不難發(fā)現(xiàn),有些人,尤其是年輕人對我們中國本身的理解還是有欠缺的地方。近代以來的主流是西方文化,一開始我們用了大量西方的概念和理論做中國研究。這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往往失去了自己的東西、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文化。西方敘事反映的是西方的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而這些都是建立在西方的實踐經(jīng)驗之上的。簡單地用西方敘事的概念和理論來研究中國,很難把中國故事講好。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今天的西方依然掌握著話語權,控制著世界輿論場。如果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這樣的做法顯然是不可持續(xù)的。
這里便涉及一個重要的核心問題,那就是在讀懂中國之前,我們必須首先解釋中國。如果說現(xiàn)在讀懂中國的效果還不夠好的話,那么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把中國解釋好。在筆者看來,讀懂中國的核心目標其實是確立以中國實踐經(jīng)驗為基礎的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西方的強大,核心不僅僅是經(jīng)濟總量大、經(jīng)濟技術強,而且在于他們創(chuàng)造了一套建立在自己實踐經(jīng)驗基礎上的知識體系。因為這套知識體系能夠解釋西方是如何發(fā)展和強大起來的,西方人所講的西方故事就很容易被非西方讀者接受。近代以來,最有效的社會科學理論便是“知行合一”理論,就是所有理論都有堅實的經(jīng)驗基礎,是可以驗證的。中國如果要強大起來,那么隨著經(jīng)濟的強大,也必須建立起一套能夠解釋自身行為的知識體系,而這套知識體系是幫助外在世界讀懂中國的終極工具。在早期,很多學者往往簡單地搬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現(xiàn)象。但現(xiàn)在情況不一樣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發(fā)現(xiàn)和指出西方的概念和理論解釋不了中國現(xiàn)象,因此學界不乏批評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努力,更有學者一直在提倡和呼吁要建立中國學派。然而,迄今確立“中國學派”依然是一種理想,除了“解構”西方社會科學的努力,人們少見“建構”中國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的努力。
一句話,“解釋中國”是構建基于中國實踐經(jīng)驗之上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最有效方法,而“解釋中國”于我們來說還任重道遠。根據(jù)法國社會學家杜爾凱姆的說法,社會科學研究就是對“社會事物”的研究,包括對實踐、政策等社會現(xiàn)象的研究。從這個角度而言,人類的實踐就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學術是對過去實踐經(jīng)驗研究的積累。學術的核心是概念、理論和原理。但在社會科學中,尤其是近代以來的實證社會科學中,幾乎所有的概念和理論都是對實踐(包括政策)的提煉。我們可以舉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為例。這是一本最為經(jīng)典的政治學作品,但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知道,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基礎就是古希臘各個城邦所實行的不同的政體或者政治制度,他經(jīng)過比較分析,構建出一套理論。西方整個政治學體系都是建立在不同的政策或者制度實踐之上的。霍布斯的《利維坦》是英國當時國家形式的反映,洛克的《政府論》也是。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抽象的概念和理論。從經(jīng)驗來看,實踐(包括政策)總是先于概念和理論而存在。黑格爾說,“存在的就是有其理由的”,這句話道出了概念和理論的真諦。社會科學的本質就是對“社會事物”的解釋。
對自然界各種存在的解釋構成了科學或者純理論。在這方面,中國和西方表現(xiàn)不同。傳統(tǒng)上,中國所發(fā)現(xiàn)的自然現(xiàn)象也不少,但我們少有解釋這些現(xiàn)象的純理論,因此我們沒有產(chǎn)生像西方那樣的純科學。我們的文化強調實用和應用,但對與實用和應用無關的純理論不那么感興趣。西方則不同,西方文化不會停留在發(fā)現(xiàn)自然現(xiàn)象,而是還要追究自然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理由,這導向了西方的純科學。這里以火藥為例。火藥是中國發(fā)明的,英國近代思想家培根就說過,中國的三大發(fā)明(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塑造了近代世界。但在發(fā)明火藥之后,中國盡管有各種應用,卻對火藥本身的研究缺乏興趣。也就是說,中國有火藥技術,卻沒有火藥科學。人們可以說,火藥科學助力西方的崛起,但中國卻被自己發(fā)明的火藥打敗了。
在社會科學上更是如此。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的文明,中國的每一朝代都有詳細的歷史記載。正因為如此,中國產(chǎn)生了大量的史學家。但在讀二十四史和其他偉大歷史著作的時候,人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有那么豐富的歷史記載和材料,卻沒有產(chǎn)生類似西方的經(jīng)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呢?中國方方面面的實踐實在太豐富了,但這些實踐并沒有被提升為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理論。
但是,社會科學家光解釋“社會事物”還不夠。社會科學家不僅僅是分析社會事物的工具,還有其自己的價值觀,根據(jù)其價值觀去塑造社會。因此,馬克思認為,哲學家的兩大任務便是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
正因為這樣,一不當心,社會科學家就會構建出各種不同的“烏托邦”,希望能夠在人間實現(xiàn)符合其理想的社會。所謂的“烏托邦”就是沒有現(xiàn)實可行性的。人是一個道德個體,充滿情感和知識想象,構建烏托邦是一種自然的現(xiàn)象。盡管烏托邦在一些時候助力人類的進步,但人類社會上大的烏托邦運動則對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例如,自由主義批評馬克思主義是烏托邦,但發(fā)展到今天,新自由主義本身又變成了另一個極端的烏托邦。
如何避免烏托邦?我們可以引入馬克斯·韋伯的“價值中立”概念。人是社會性動物,人有立場和觀點受制于文明、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因此人很難做到完全的“價值中立”。但是在解釋“社會事物”的時候,必須盡最大努力來實現(xiàn)“價值中立”,否則就如我們平常所說,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總會出現(xiàn)很多問題。
我們可以把社會科學家和其所生活的社會與世界的關系比喻為醫(y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系。醫(yī)生根據(jù)其所學到的知識和積累的經(jīng)驗給病人看病。醫(yī)生的道德底線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把病人醫(yī)死。如果病看好了,表明醫(yī)生的知識是對的,經(jīng)驗足夠。但如果醫(yī)生醫(yī)不好病,那么醫(yī)生只能說自己所學的知識不夠甚至不對,或者自己經(jīng)驗不足。沒有醫(yī)生會說,醫(yī)不好病是因為病人的病生錯了。
但今天的一些社會科學家卻認為“病生錯了”是存在的。社會科學家根據(jù)自己所學的知識來解釋社會現(xiàn)象,解釋得通的時候,可以說其掌握的知識是有效的,解釋不通的時候,則不能說社會現(xiàn)象是不對的,只能說其所學的知識不夠用了,需要新的知識。但很可惜,一些社會科學家在解釋不通社會現(xiàn)象時,往往認為是社會現(xiàn)象本身出了問題,而自己的知識沒有問題。
這絕對不是說社會科學家只解釋“社會事物”,承認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存在有其理由,但有理由并不意味著合理。社會科學家是社會人,是道德體,他們診斷社會問題(例如自殺和他殺問題、一項政策對不同社會群體的影響、巨大政府工程對社會的影響等等),需要找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就像醫(yī)生要把病人的病醫(yī)好那樣。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社會科學是近代歐洲的產(chǎn)物。從社會科學的建構來說,有兩點是相當清楚的。第一,基于“價值中立”之上的分析是社會科學的基礎。所有有效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是對“社會事物”的分析。近代以來流行各種“主義”,但它們一開始都是基于實證之上的研究,而非“主義”。一旦成為“主義”,那么就成了意識形態(tài)。第二,“社會事物”是變化的,對“社會事物”的解釋也需要變化,解釋、再解釋構成了社會科學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的巨大動力。
不管怎樣,我們自己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也必須建立在我們自己的實踐經(jīng)驗之上。中國的崛起必須伴有自己的一套能解釋自己的知識體系,沒有這樣一套知識體系,不僅自己不能讀懂中國,更難幫助外在世界讀懂中國。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讀懂中國都是一項偉大的事業(yè)。
基于“解釋中國”是讀懂中國的基礎這一信念,這些年來,筆者試圖在解釋中國方面做一些努力,涉足政黨、政治體和政治經(jīng)濟系統(tǒng)等各個方面。《中國敘事》就是對這些研究基礎的“非學術”表述,意在讓讀者意識到,只要我們有意識,解釋中國不僅必須,也是可能的。希望《中國敘事》這本小書能夠為讀懂中國這項事業(yè)做出一點小小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