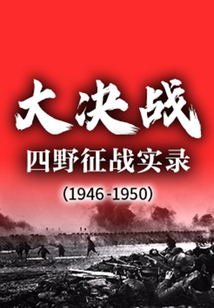
大決戰:四野征戰實錄(1946—1950)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決戰錦州》:黃金般的黑土地
毛澤東說: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朝氣蓬勃的共產黨人,要將這片豐饒的黑土地收入囊中。
為了拿下東北,東北野戰軍實行大練兵,忙著磨刀擦槍。整整6個月,黑土地陷入大戰前的沉寂。
1.只要有了東北
1945年春,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說:“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清一色黑鈣土的松遼平原,是中國最大的糧食產地。大豆、小麥、高粱、水稻,或以數量居全國之首,或因質量名聞遐邇。大豆和柞蠶更是飲譽中外。大小興安嶺和長白山系綿延千里的群山,森林覆蓋面積超過內地總和。在大山和黑鈣土下面,是閃耀著各種瑰麗色彩的數十種礦藏。其儲量之豐富,有的為中國之最,有的為世界之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時,這里的重工業占全國的90%。新中國成立后的“鋼都”(鞍山)、“煤都”(撫順)、“電都”(小豐滿),都在東北。而據1943年統計,東北生鐵產量占全國87.7%,鋼材占93%,煤炭占49.5%,發電量占78.2%,水泥占66%,鐵路、公路長度分別占全國的一半以上和將近一半。沈陽還有中國最大的兵工廠。東北素有“糧倉”之稱,其中大豆產量占全世界的60%以上。大小興安嶺和長白山,木材蓄量占全國的1/3。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日本投降不久,蔣介石就不惜血本,調遣其精銳的遠征軍,不遠萬里來搶奪東北了。3年之后的1948年,朝氣蓬勃的共產黨人,馬上就要把這片豐饒的黑土地收入囊中了。
河北省平山縣,緊靠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嶺上,有個不到百戶人家的小山村,叫“西柏坡”。
西柏坡因柏坡嶺上的古柏而得名,因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而名聞天下。
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就是在國共兩黨的決戰時期,在這里指揮了震驚世界的遼沈、淮海、平津戰役。
東流的滹沱河水,世世代代唱著那支古老的歌。掩映在農舍樹叢中的天線下的電臺,曰曰夜夜唱著共產黨人的《勝利進行曲》。
4月22日,彭(德懷)張(宗遜)[1]野戰軍奪回延安。
5月17日,徐(向前)周(士第)兵團攻占臨汾。
6月11日,許(世友)譚(震林)兵團收復曲阜。
6月22日,陳(毅)粟(裕)野戰軍攻克開封。
7月6日,陳粟野戰軍睢(縣)杞(縣)大捷,活捉國民黨7兵團司令區壽年[2]。
7月16日,劉(伯承)鄧(小平)野戰軍政克襄陽,活捉國民黨15“綏靖”區司令長官康澤[3]。
經過兩年的浴血奮戰,共產黨已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取得了全國戰場上的主動權。國民黨軍隊已由戰爭開始時的430萬人,減到365萬,能夠用于前方作戰的只有170萬,作戰方針也由“全面防御”、“分區防御”,變為以北平、西安、漢口、徐州、沈陽五大戰略據點為支柱的“重點防御”。共產黨軍隊則由120萬人發展到280萬,所占面積為全國的1/4,人口達到1/3以上。
比這些數字更令人振奮的,是難以用數字表示的人心與士氣的對比。
黑土地的形勢更為看好了。
到1948年3月冬季攻勢結束,國民黨軍隊已被殲滅57萬人。此時,尚有14個軍,44個師,加上地方武裝共55萬人,但已被壓縮在長春、沈陽、錦州三塊互不相聯系的地區。人心浮動,士氣低下,供應困難,恨不能像冷兵器時代那樣,掛出一塊“免戰牌”。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占共產黨軍隊1/3以上的105萬東北野戰軍和地方部隊,占領地區為黑土地的97%,人口為86%。
一方孤城困軍,把希望寄托在不知何日才能到來的援軍,甚至是至今也未爆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上。一方大軍踴躍,實力就像大地一樣實在而又堅厚,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當初,日本投降后,毛澤東是亦喜亦懼。喜不必說了,那懼不僅是憂懼內戰行將爆發,對內戰前途也不能說沒有憂懼。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從未把自己當成神。戰爭畢竟是實力的對抗。當時的中國革命前景實在不容樂觀。
“八一五”后的蔣介石,擁有中國4億人口中的3億人以上的地區,控制著所有大城市和絕大部分的鐵路。他接收了100萬侵華日軍的裝備,有430萬軍隊。這樣一支龐大的軍隊,不僅在中國,就是在亞洲也是首屈一指的。作為這支軍隊的統帥,沒有比在軍旅中起家的蔣委員長更懂得它意味著什么了。
更重要、更意味深長,也是更具有威懾力的,是這支軍隊有39個旅是美械裝備。在當時,美械裝備就是“現代化”、“勝利”的代名詞;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和美國站在一起就是和勝利站在一起。有一個“39個旅”,就意味著會再有一個、幾個“39個旅”,就意味著美援會源源而來。
比之總是干凈利落,穿一套質地考究的軍服,既有軍人的威儀,又有學者般儒雅的蔣介石,身材略高點的毛澤東,就“相形見絀”了。這不僅因為他就像他指揮的那支質樸的軍隊一樣,總是穿著那種又肥又大,有時還打著補丁的粗劣的衣服,還因為這個從信仰到性格都和蔣氏格格不入的人,確實不怎么修邊幅。
然而,即使是天天都在詛咒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中國的第一個偉男子和天才。
毛澤東的天才和風度,表現在他站在歷史峰巔上“一覽眾山小”的恢宏氣度,和勇立時代潮頭駕馭歷史縱橫自如的瀟灑。此前,他曾將坎坷艱難的共產黨引向坦途,并使之充滿朝氣和活力。此后,僅用3年時間,就把那個被朋友和敵人都視為中國最強有力的人物,流放般地趕到了那個雖然美麗,卻無論如何也盛不下那顆心、咽不下那口氣的海島上。
可是,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脫掉那身灰布衣服,換上一套藍布制服,再戴上一頂那個年代好像挺時髦,卻讓人覺得有點不倫不類的盔式帽時(以后好像再沒見他戴過),他的心情可實在不敢輕松。
他不是怕去重慶打那種冠冕堂皇的嘴巴子宮司。有一手風流倜儻好書法,寫一手才氣橫溢好詩詞和政論的毛澤東,在這方面對付蔣委員長游刃有余。可嘴巴子、筆桿子再厲害也不行,嘴巴子和筆桿子里面出不了政權。
當時的毛澤東已不像在江西時那樣“寒酸”了,但他所統帥的部隊力量仍然薄弱。蔣介石的軍隊接近他的4倍。如果裝備和訓練程度也可以用數字表示,還不止這個數。力量對比當然不僅僅是數量的多少,可沒有數量也談不上力量。
講求實際的共產黨人,即使想打內戰也應該再等上幾年,待雙方實力相當,或是比對手強大時,再動手。
由不得共產黨。
和平是力量的均勢、平衡,或者是由于不平衡而屈辱的臣服。“八一五”后的中國,沒有這種平衡。毛澤東的字典里,也沒有“臣服”這兩個字。
但到了1948年,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中國革命已具備了勝利的可能性。不過,國民黨還控制著相當強大的戰略集團,還有很大的戰爭能力。真正解決勝負,還得通過最后的戰略決戰。
在毛澤東的視野里,西北、中原、華東,華北和東北五大戰場,1948年秋天,“稻浪”金黃,豐收在望。而豐饒的黑土地,則是塊秋色濃,來得早,熟得快,應該開鐮收割的第一塊高產田。
“只要有了東北!”毛澤東下定決心,現在就要拿下東北——只要拿下東北,這天下遲早就是共產黨的了。
2.大練兵
墻上刷著“練好兵,打長春”;會上講著“練好兵,打長春”;請戰書和決心書上寫著“練好兵,打長春”——從1948年3月開始的歷時近半年的大練兵,刀鋒直指長春。
這是黑土地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練兵活動。以往基本就是在戰場上真刀真槍地練了,這次就是訓練、演練。練什么?主要是練攻堅。當然也離不開林彪的“六個戰術原則”,即“一點兩面”,“三三制”,“三猛戰術”,“三種情況三種打法”,“四快一慢”,“四組一隊”。
各級指揮員所練各有側重。連隊主要是練“四組一隊”,練爆破,練土工作業,練攻城,練巷戰。
當時東北野戰軍的訓練方針是:“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
離休前為某軍副軍長的黃達宣老人,當時是2縱6師1團1連3排長,在練兵中立過一大功、三小功。老人說,練兵時的陣地和工事,都是按長春布防情況設置的,反復演練了三四個月。白天練射擊、刺殺、投彈、中鋒、翻院墻、爬城,晚上是夜行軍和村落、街道攻防戰斗。村頭到處都挖了掩體、交通壕,人人練捆炸藥包、安雷管、接導火索。破土地廟、爛房子、坡坎什么的,都成了“地堡[4]”,爆炸聲白天晚上響。怎樣穿墻打洞,土墻怎么炸,石墻怎么炸,反復研究、演練。怎么過外壕,壕那邊有地堡,壕下有地雷,怎樣把炸藥包扔過去炸……那兵練得呀,全連戰士都是第一次經歷。
1946年9月15日,毛澤東致電林彪,問“你們所說的一點兩面的戰法是什么意思”。9月19日,林彪在復電中說:
所謂一點,就是說要集中優勢兵力于主要的攻擊點上,反對在各點上平分兵力的辦法。所謂兩面,就是說必須采取勇敢包圍辦法,防止敵之突圍逃走。兩面是指至少兩面,兵力多時也可以是三面四面。一點的精神在于保證一定打垮敵人,整個的精神在于使打垮的敵人不致跑掉。大意就是如此。是針對我們干部不肯徹底集中兵力和不敢進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規定的。
“一點兩面”的戰斗部署,“三三制”的戰斗隊形,“三猛”的戰斗動作,“三種情況三種打法”,“四快一慢”的攻擊原則,“四組一隊”的戰斗編組。就這樣把理性的、概念的,也是枯燥乏味的,對那時的基層官兵尤顯探奧的戰術理論,概括成“六個戰術原則”,簡單明了,通俗易記,連沒有文化的大老粗也能搞懂。
為了便于學習、運用,有的部隊將“六個戰術原則”編成順口溜,有的編成歌曲傳唱。有的老人還記得開頭一句是“‘一點兩面’要牢記”,然后解說“一點”是什么,“兩面”是什么,接下來就是其他的五個戰術原則,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5]似的。
拿破侖說:“進行戰爭的原則也和實施圍攻的原則一樣,火力必須集中在一個點上(一個地段上),而且必須打開一個缺口。一旦敵人的穩定被破壞,爾后的任務就是把它徹底擊潰。”
“一點兩面”注重的,正是包圍、突破后的全殲。
集中主要兵力突擊主要方向,從孫子到勞克塞維茨,從馬克思到毛澤爾,都是這個原則。
三三制戰術組織形式,是一個班內由三至四人劃分三或四組。正副班長為當然小組長。另在班內挑選政治較好、戰斗勇敢,或有經驗的戰士充當組長。在戰斗時各組以班長為核心,在班長指揮下,率領本小組根據敵情地形,散開距離間隔進行作戰,不超過班長口令指揮范圍以外。在平時使三三制編制要與日常生活管理教育公差勤務等一切活動相結合,在戰斗中求得靈活運用發揮其效能。
1944年10月18日,林彪在陜甘寧邊區部隊高干會議上的講話中,就講到了這個問題:
我們部隊作戰時愛成群地涌來涌去,勇氣很好,但是缺乏有智術的動作。
“在近代的用火力的戰爭條件之下,用集團的沖鋒目標大大,如果被人家的大炮和機關槍射擊的時候,損失就太大了,因此現在我們要教育戰斗員三五成群的戰斗,一個兩個的去戰斗。”
“六個戰術原則”都是在黑土地上提出來的,其中“一點兩面”和“三三制”提出得最早。
秀水河子戰斗[6]前,林彪在秀水河子小學校給1師、7旅營以上干部講話。在講了戰爭不可避免后,主要就是講解“一點兩面”、“三三制”說在錦州西部打的幾仗,敵人火力密集,我軍隊形密集,傷亡大,說現在不同于抗戰打日本,敵人是美械裝備,火力猛,又是精銳,不能像過去那樣一打一沖,人海戰術。當時大家第一次聽到“一點兩面”、“三三制”,覺得新鮮,一時又弄不懂。有的老人還記得林彪邊講邊在黑板上寫、畫,說明“一點兩面”和“三三制”的要領、意義。
“三猛戰術”就比較簡單、直白了:
對于所選定的主攻點上,應將各種機關槍各種炮秘密地盡量接近敵人,適當的配備起來,以便統能向主攻目標射擊,并于同時猛然開火,這就是我們所謂“猛打”。這種火力用法,他是反對零零碎碎打的,反對把火力到處分散使用的。
在主攻點上,火力猛然開始射擊后,我突出部隊應乘此際敵人發呆、發慌時一時拿不出主意和來不及調兵時猛烈沖鋒,躍然奮進,以刺刀、手榴彈向前沖去,以刺刀刺殺敵人,不敢以刺刀刺敵的不算最勇敢的部隊與戰士,我軍必須建立刺刀血戰的威風和隨手榴彈的飛出爆炸而猛進的勇氛,這就是我們所謂“猛沖”。
對于已被沖動和潰亂的敵人,應實行猛烈追擊,要一直壓下去,這就是我們所謂“猛追”。
“三種情況三種打法”是:
一種是敵人守,一種是敵人要退不退,一種是敵人退,為了不至于亂用,提出三種基本不同的情況。如果敵人守,就要經過正式的準備,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后再攻擊;如果敵人要退不退,我們準備好了再打,敵人會跑掉,不準備就打,又會被碰下來,這時應先將敵人圍起來,圍而不攻,或圍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們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脫,然后準備好再打;如果敵人退,就要猛追,這時不要等命令,不準備就是合乎戰術,準備了反而不合乎戰術,不要怕部隊少,也不要怕情況不靖楚,追就是了,當然,戰役指揮員是應該組織有計劃的追擊。
有老人告訴筆者,“三種情況三種打法”,蘇軍條例上就有,但比較抽象。林彪用比較通俗的語言,把它形象了,具體了,明確了。
當時沒有條件辦正規院校,軍政大學和各種參謀集訓隊,也都是速成性質。戰爭環境,沒有機會長篇大套上大課,而且干部戰士文化很低,講多了,講深了,也不懂,記不住。于是,林彪就用“一點兩面”、“三三制[7]”、“三猛”、“三種情況三種打法”這些詞匯、短語,把諸多戰術理論歸納起來,通俗易懂好記。
林彪講得較多的,是“四快一慢”:
向敵前進要快:譬如打某個地方,怕敵人跑了,前進時要快。……
抓住敵人后進行準備要快:看地形,選突破口,構筑工事,捆炸藥,動員,調動兵力,布置火力等等,忙個滿頭大汗才好,這要快。
突破后擴張戰果要快。
敵人整個潰退了,離開了陣地。我們追擊時要快,這時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
慢是指什么時候,什么事情上慢呢?是指總攻發起時機這一下要慢(但總攻開始后就要快)。在這問題上要沉住氣,上級催罵,派通信員左催右催,這就要沉著,反正我要準備好再打。
“四快一慢”和“四組一隊”,都是四平攻堅戰后提出來的。
“四組一隊”,據說是劉亞樓總結出來的。
四組即火力組、突擊組、爆破組、支持組。……提出四組一隊主要是提醒大家:突擊連隊要分工,小組互相掩護,互相配合。至于實際運用,應根據具體目標,同志們提出三個組,五個組,也有將機槍組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戰斗班的,我想今后也可能不一樣的。
老人都說,在打錦州和天津時,“四組一隊”起了很大作用。
林彪的六個戰術原則,矛盾,有像“一點兩面”有“點”有“面”一樣,每個階段都有一種主要傾向,抓住這種傾向歸納出一點,大講特講。一個問題講得差不多了,另一個階段又開始了。比如,由游擊戰轉變為正規戰時,大講特講“一點兩面”、“三三制”。準備反攻了,就大講特講“四快一慢”和“四組一隊”。林彪把各個時期需要的戰術和能體現出這種戰術的各種新名詞,灌輸給他的將軍和士兵。
很多老人都談到,那時一仗下來,各級指揮員都要到陣地或突破口去開現場會,根據實戰情況總結經驗教訓。打下錦州后就奔遼西,殲滅了廖耀湘兵團后,有的部隊還特意回到錦州,補上這一課。
黑龍江軍區原副政委張多樹,當時是9縱25師73團政委。老人說,9縱還沒升級為主力時,在冀東沒練過“一點兩面”、“三三制”這些戰術,后來就從頭練,趕緊練。1947年夏季攻勢打四平失利后,上邊是真下了狠心,下邊也真練。不練不行。過去盡打野戰,野戰變攻堅,是門新功課。“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句話可不是掛在嘴皮子上的。
每個老人對這場大練兵印象都很深刻,都說那幾個月的汗水沒白流。那戰術動作、機靈勁兒和精神頭兒,都和過去大不一樣。
筆者采訪到的老人,幾乎眾口一詞:這些戰術原則,當年別說師團干部,就是連排干部,甚至班長、老兵、骨干,都懂,會用。這是打勝仗的原則。林彪那人話語金貴,在這上頭卻不惜話語,有個“小婆婆嘴”,有機會就給你叨叨,就怕你不懂,不按他的來。
遼沈戰役前,林彪還挺“婆婆嘴”的,不時會指點幾句,強調一番。遼沈戰役后進關,就算不得“婆婆嘴”了。待到四野南下后,關于六個戰術原則,林彪只是偶爾提提了。直到抗美援朝跨過鴨綠江,四野官兵還是這么打的,拿著在美國人眼里簡直就是破銅爛鐵似的家什,文化水平也比人家差一大截子,但戰術卻是一流的。
黑土地上的共產黨人就這樣由小到大,由弱變強,越打越精明。
據說,毛澤東當年對林彪這些戰術是肯定的,有的還很欣賞。
3.“我為誰人扛起槍”
1947年9月28日,東北民主聯軍[8]總政治部將《遼東3縱學習土地政策經驗(訴苦)介紹之二》,電報軍委總政,毛澤東逐字逐句作了批改(文字66處,標點符號48處),轉發全軍,推廣3縱訴苦教育經驗。
遼沈戰役前的大練兵,練軍事,也練政治,練思想。其中最主要的、也最見功效的,是開展憶苦運動。
憶苦運動通常以連為單位,選個苦大仇深的典型,進行宣傳教育。那時這樣的典型很多。只要實話實說家里幾口人,動產不動產都有些什么,病死的,餓死的,被地主逼債逼死的,送人的,賣給人家的,被國民黨抓壯丁沒了音信的……把具體怎么回事說清楚就行。
訴苦教育,一般分為五個階段。一是典型引路;二是“聽了別人的苦,你有什么苦”,進入訴苦階段,又叫“倒苦水”;三是“苦從何來”,也叫“擦亮眼睛挖苦根”階段;四是“你有什么對不起自己的苦的地方”,檢查忘本思想,進行坦白階段,自我教育的同時,也教育大家;五是“有苦有仇怎么辦”,進入練兵磨刀、殺敵立功階段。
開展憶苦活動后,戰前政治動員的內容,主要就是講明為誰當兵,為誰打仗。有時干脆就搞一場憶苦報告,苦水一倒,戰士們就咬牙切齒地向敵人沖去了。
1947年夏季攻勢前,有些部隊還搞起靈前宣誓。通常以連為單位,找個空曠的地方,搭起個席棚子,把全連官兵被地主老財或國民黨軍隊逼死、殺害的親人的姓名,寫在一塊木板上,供上點燃香。各連的席棚里,都供著十幾個牌位,就在那靈前訴苦、宣誓。有呼爹叫娘的,有叫著爺爺奶奶兄弟姐妹的,都說這回就要上戰場了,一定多消滅幾個敵人,為你們報仇。
過去為配合戰前的動員,縱隊和師里宣傳隊會下來演出節目,像《白毛女》、《血淚仇》一類的話劇。但這種方式受局限,覆蓋面也小。訴苦則可隨時隨地進行,幾近人人參與,且是主動的自我教育、激勵、提高的過程。
另外靈前宣誓的時候,一些圍觀的老鄉參與進來,有的當場要求參軍,有的報名參加擔架隊,擴大了我軍的力量。
據《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統計,3年中,黑土地有1445907名農民參加了共產黨軍隊。還不算我們經常在銀幕和熒光屏上看到的肩頭背著槍,手中拿著鋤頭,正在田間勞動的那種民兵。
翻身不忘恩,好漢去當兵!
保田保家保鄉去!
勝利反攻,人人有份!
……
在農民分得土地后,這樣的口號,幾乎寫遍黑土地每個村莊每條街道的每堵墻壁。
到1947年初,東北有400萬窮苦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到1948年上半年,土改基本結束。農民有了土地,再給他們一支槍去保衛土地,這實在是太順理成章的事了。
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集團,敢于像共產黨這樣武裝人民。因為人民武裝起來后,就要用槍桿子解決自己的痛苦了。
殺富濟貧,開倉放糧,然后率領憤怒的饑民撲向另一座城池。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幾乎無一不在重復這樣的畫面。但是,沒有任何階級和政黨能像共產黨那樣成功,那樣徹底,那樣更具歷史的主動性和創造力。
從這疙瘩到那疙瘩舌頭緊靠著牙,
民主聯軍和老百姓守住東北守住家,
東北是我們家鄉拼命保住它!
眼淚里長著苗鮮血中開著花,
打敗那敵人保住我們的家!
……
唱著這支《從這疙瘩到那疙瘩》,黑土地上的農民,一批批走上前線。
訴苦教育,最早是在3縱7師20團9連搞起來的。
9連是“八一五”光復后,由本溪和撫順暴動的“特殊工人”組成的,大都是中條山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官兵。那時連老百姓都“想中央,盼中央”,這些人能不想、不盼?沙嶺戰斗是3縱組建后第一次比較大的戰斗,9連兩個排埋伏在一片墳地里,距敵100多米,都是老兵,軍事技術蠻好,卻只聽槍響,不見人倒——那槍大都是朝天上放的。國民黨打國民黨,是有點下不了手。
而1946年9月23日,《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關于部隊坦白運動與訴苦運動的經驗》中,有這樣一段:
從一個連的材料觀察,大部分參加過偽滿時的警察,國兵,公安隊,棒子隊,土匪,及受過敵偽各種洲練,并且說明了任職與訓練的年月。做的壞事有:殺人,勒大脖廣(即敲詐勒索一一筆者),槍劫,嫖賭,強奸,抽大煙,扎嗎啡,加入三番子,溜大號(不經請假允許,就跑回家去,叫溜大號)。多報家庭人口達到多領優待糧,以及重復過去的一些行為。在參軍動機上,為掙錢吃飯,不愿做莊稼活,認為扛活太累或當兵不累,以及光復后沒有生路,即純粹為著生計問題,從好吃懶做思想出發的,占54%。
要讓這樣一些人舍生忘死投身革命,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辦到的。
四平保衛戰后。3縱在柳河進行整頓,7師布置擁政愛民教育,出了17道題。有道題是:有人說窮人養活富人,有人說富人養活窮人,你認為哪個對?
當時任20團9連指導員的趙緒珍老人說,那時人沒文化,腸子不拐彎兒,講課搞教育得直來直去講實的。講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現在的指導員會馬克思怎么說,列寧怎么說,大三條,小三條,左三條,右三條,念上十幾頁稿紙。那時候指導員沒有這“水平”,就講共產主義是個沒有剝削。壓迫的社會,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地種,有書讀。其實這還是個階級教育。只是這樣搞缺乏形象,對不上號,不著邊際“誰養活誰”這個問題就不一樣了,再沒文化,再笨,也能說幾句。
有的說富人什么活不干,卻吃香的喝辣的,是窮人養活富人。有的說富人不租給你地種,你喝西北風?有人說他闖關東要凍死了,一個財主把他架到家里熱炕上,給飯吃,又給活干,這不是富人救了窮人又養活窮人嗎?有的說土地自盤古開天地就有,憑什么就成了地主的,就得租他的地?這不公平。有的說窮人和富人是互相養活,誰也離不開誰。有的說窮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有錢人是有能耐,墳埋得好……總之是各說各的理,誰也不服誰,爭論得熱火朝天。
當天晚上點名唱了支歌,叫《誰養活誰》:
誰養活誰呀?大家來看一看,
沒有咱勞動,糧食不會往外鉆。
耕種鋤割全是咱們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糧食一滴汗,
地主不勞動,糧食堆成山。
誰養活誰呀,大家來瞧一瞧,
沒有咱勞動,棉花不會結成桃。
紡線織布沒有咱們呀干不了,
新衣服,大棉襖,全是咱們血汗造,
地主不勞動,新衣穿成套。
誰養活誰呀,大家來說一說,
沒有咱勞動,哪里會有瓦和磚。
打墻蓋房全是咱們出力干,
自己房,二三間,還有一半露著天,
地主不勞動,房子高又寬。
這首歌大家原來就會唱,不知是不是唱多了不新鮮了,反正唱的人沒覺出什么,倒是一些旁邊看熱鬧的老鄉聽出滋味兒了,七嘴八舌道:這歌唱到咱心里去了。就這樣,一個深刻的階級問題就在這首記錄生活真實的歌曲中找到了答案。
有一天上課,搞政治教育,大家挺奇怪:指導員抱件破棉襖,一領破席頭,一個討飯瓢,旁邊還站著個老大爺。這是干什么呀?
老人的苦,把100多條漢子的苦水引發了,一個個哭成了淚人。
沙嶺戰斗中,在戰壕中抱槍不動的房天靜,成了憶苦典型:俺16歲叫小鬼子騙到本溪下煤窯,俺娘從山東來看俺,斷了盤纏,把三弟賣了25元錢。到本溪俺娘就病了,就那么眼睜睜看著俺娘死了。俺哭啊,哭有什么用?窮人沒有錢,富人誰管咱?俺這窮小子卻壞了良心忘了本,打仗不向階級敵人反動派開槍,真是個混蛋呀!
不服從命令還打副連長的王福民,跺著腳哭:俺也是個窮小子呀,卻盼蔣介石來,要干“正牌”。蔣介石來了還有窮人的好呀!俺過去瞎了眼,現在心里亮堂了。俺王福民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
后來房天靜成了戰斗英雄。王福民五次負傷(兩次重傷)不下火線,三保臨江大北岔戰斗犧牲前,抓著趙緒珍的手要求入黨。這位當初被列為“危險分子”的兵痞,被追認為共產黨員。
有錢人家出身的也哭:過去吃香的喝辣的,以為那是憑本事掙的,原來喝的都是窮人血汗呀!
筆者采訪的幾位當年是解放戰士的老人都說,一場訴苦會下來,一個個抽抽搭搭的,人還未解放,那心已經是共產黨的了。怪不得解放軍這么不要命,官死了兵領著沖,像中了什么邪似的,敢情人家是為了自己打仗呀!有時候訴著訴著,家有“200畝地”的也跑上臺去了。問他你有什么苦水可倒的,他說我家哪有一壟地一片瓦呀。國民黨那邊是越富越露臉,窮人受白眼,都報家有幾十畝地。不懂共產黨規矩,還捧著老皇歷瞎吹牛。
一仗接一仗,傷亡大,俘虜沒法送,就隨抓隨補。聽口音是老鄉,就說你到我們班吧。老鄉見老鄉,首先嘮家鄉。你家幾口人呀?都干什么呀?村里有沒有地主呀?地主下地干活嗎?手上有繭子嗎?地主吃的穿的住的什么樣子?你家吃的穿的住的什么樣子?一天行軍沒到頭,一個人差不多就“赤化”了。
遼沈戰役解放沈陽后,林彪、羅榮桓和劉亞樓看望主力中的主力2縱5師,和師政委石瑛有這樣一段對話:
羅榮桓:談談傷亡情況。
石瑛:團以上干部傷亡11個,有的團營,連排干部傷亡比編制還多,全師傷亡7800多人。
羅榮桓:還有多少人?
石瑛:南下時足1.6萬人,現在1.7萬人。
劉亞樓:這不都是俘虜嗎?
黑土地上最能打的王牌師,此刻簡直就是個“解放師”了!
《遼東3縱隊的訴苦教育情況專題綜合報告》中,有這樣一段:
據7師1947年10月冬季攻勢前統計,全師9568人中就有解放戰士3254人,占全師總人數的34%,到遼沈戰役結束時,一般連隊解放成分都占54%左右,有的連隊甚至達到60%。許多解放戰士已經成了戰斗骨干,有些還入了黨,當了干部。……通過訴苦,把蔣介石軍隊的士兵,變成為蔣介石自己的“掘墓人”,使蔣介石不但在作戰物資和武器裝備上,而且在人力上也成了我軍的“運輸大隊長”。
我為誰人來打仗?為誰來打仗?
我為誰人扛起槍?為誰扛起槍?
為革命,為祖國,
我為自己來打仗,
為了你,為了他,
我為人民扛起槍。
……
在那不打仗的日子像節日一樣少的年月里,從1948年3月15日冬季攻勢結束,到發起震驚世界的遼沈戰役,整整6個月時間,黑土地一反常態地沉寂著。
這是大戰前的沉寂。
運籌帷幄,磨刀擦槍。
親歷者的回憶
韓先楚
(時任東北野戰軍第3縱隊司令員)
……冬季攻勢后,進行了出關以來第一次近半年的大練兵,部隊的軍事素質和政治素質,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以“大兵團、攻堅戰、正規化”為指導方針的軍事大練兵,提高了使用技術裝備的能力,提高了使用炮兵、工兵和坦克兵協同作戰的能力,攻城、爆破、巷戰、射擊等項目訓練,也都取得了良好成績。
政治大練兵,本著毛主席以訴苦、三查方法進行新式整軍運動的指示精神,開展“五整一查”,提高階級覺悟,加強團結,加強政策紀律,也收到了良好效果。
整個部隊,陣營雄壯,士氣高漲,求戰心切……
——摘自:韓先楚《東北戰場與遼沈戰役》
杜聿明
(時任國民黨徐州“剿總”副總司令)
1948年3月9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永吉和號稱電都的小豐滿;13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四平街,殲守軍1.9萬余人。
至此人民解放軍在東北發動的冬季攻勢已告一段落,共殲國民黨軍15萬余人。
這時在東北的國民黨軍,只剩下長春、沈陽、撫順、本溪、錦州、葫蘆島等幾個孤立據點。沈陽、長春軍民補給全靠飛機運輸。
而中航公司,自3月8日起決定每日只有4架飛機運輸物資接濟。
同時,衛(立煌)打算趕快將向東北增調的部隊及補充兵員運到葫蘆島登陸,另在錦州以及沈陽附近抓捕大批青年壯丁將部隊補充齊全,加緊訓練,以期長期固守沈陽。
——摘自:杜聿明《遼沈戰役概述》
注釋
[1]張宗遜:陜西渭南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工農革命軍第36師師長、軍長、紅五軍團第14師師長、紅軍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紅軍中央縱隊參謀長、紅三軍團第4師師長、紅四方面軍第4軍參謀長、軍委一局局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358旅旅長,呂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第1縱隊司令員、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等職。
[2]國民黨第7兵團司令區壽年:廣東羅定人。國民黨陸軍中將。北伐戰爭時期,任國民革命軍第11軍10師28團團長。1929年任國民黨軍第11軍60師120旅旅長,1931年任第19軍第78師師長。抗日戰爭爆發后,任第176師師長,第48軍軍長,第26集團軍副司令等職。抗日戰爭結束后,任第六“綏靖”區副司令,第7兵團司令等職。1948年7月在豫東戰役中被人民解放軍所俘。
[3]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康澤:四川安岳人。國民黨陸軍中將。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曾留學蘇聯中山大學。1931年經蔣介石批準成立南昌行營別動總隊,康澤任總隊長。1932年后,擔任過中華復興社中央干事與書記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深受蔣介石的器重,即成為“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任廬山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主任。抗戰勝利后,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在襄樊戰役中被人民解放軍俘虜。
[4]地堡:供步槍、機槍射擊用的有掩體的低矮工事,由一個或數個射擊室、人員休息室和出入口組成。用土、木、磚、石、鋼鐵或鋼筋混凝土等材料構筑;建在橋梁、渡口、街巷、道路等交通要道旁。主要用于掩護橋梁、渡口或封鎖街巷、道路和開闊地,也可以與其他工事相結合構成支撐點。
[5]《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國人民軍隊統一的革命紀律和基本要求。原為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制定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1947年統一規定,重新頒布。內容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6]秀水河子戰斗:東北民主聯軍在遼寧法庫秀水河子地區,對國民黨軍隊進行的一次殲滅戰。1946年2月上旬,國民黨軍隊向東北解放區的遼中、法庫進犯,企圖驅逐東北民主聯軍,維持北寧路的鐵路運輸。2月11日,國民黨第13軍89師一個團又一個營進至法庫西邊的秀水河子時,被東北民主聯軍以7個團的優勢兵力包圍。13日黃昏,東北民主聯軍發起總攻。經過一夜激戰,全殲守敵1600余人,繳獲大批作戰物資。
[7]三三制:所采取的分配政策。原則是:共產黨員(代表工人階級和貧農)、“左派”進步分子(代表小權)中,人員分配比例可作某種變動,以防豪紳地主把持政權。目的在于保證中國共產黨對政權的領導,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對漢奸和反動派實行專政。
[8]東北民主聯軍:1945年10月31日,進入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各一部及東北抗日聯軍統一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年1月,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到10月止,編組了第1、第2、第3、第4、第6等5個縱隊另4個獨立師(旅),并建立了10個炮兵團及戰車、高射炮兵大隊等特種兵。到1947年9月,又編成了第7、第8、第9、第10縱隊,并成立了南滿、冀察熱遼兩個軍區前方指揮所。1948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