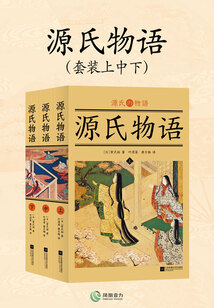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源氏物語(上)》:前言
《源氏物語》(約1007或1008)是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學名著,對于日本文學的發展產生過并繼續產生著巨大的影響,被譽為日本物語文學的高峰之作。作者紫式部,本姓藤原,原名不詳,一說為香子。因其父藤原為時曾先后任過式部丞和式部大丞官職,故以其父的官職取名藤式部,這是當時宮中女官的一種時尚,以示其身份。后來稱紫式部的由來,一說她由于寫成《源氏物語》,書中女主人公紫姬為世人傳頌;一說是因為她住在紫野云林院附近,因而改為紫姓。前一說似更可信,多取此說。女作家生歿年月,歷來有種種考證,都無法精確立論。一般根據其《紫式部日記》記載寬弘五年(1008)十一月二十日在宮中清涼殿舉行“五節”(正月七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上巳、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九月九日的重陽)時稱自己是“年未過三十”的青春年華,以此溯上類推她生于天元元年(978)。一說根據《平兼盛集》載,式部逝世時,其父仍在任地,認為其父于長和三年(1014)辭官返京,與此有關,因而推測她歿于此年。另一說則根據《榮華物語》長元四年(1031)九月二十五日上東門院舉辦地供奉儀式出現其女賢子的名字卻未提及她,故推斷她歿于這一年之前。
紫式部出身中層貴族。先祖除作為《后撰和歌集》主要歌人之一的曾祖父藤原兼輔曾任中納言外,均屬受領大夫階層,是書香世家,與中央權勢無緣。其父藤原為時于花山朝才受重用,任式部丞,并常蒙宣旨入宮參加親王主持的詩會。其后只保留其階位,長期失去官職。于長德二年(996)轉任越前守、越后守等地方官,懷才不遇,中途辭職,落發為僧。為時也兼長漢詩與和歌,對中國古典文學頗有研究。式部在《紫式部日記》《紫式部集》中多言及其父,很少提到其母,一般推斷她幼年喪母,與父相依為命,其兄惟規隨父學習漢籍,她旁聽卻比其兄先領會,她受家庭的熏陶,博覽其父收藏的漢籍,特別是白居易的詩文,很有漢學的素養,對佛學和音樂、美術、服飾也多有研究,學藝造詣頗深,青春年華已顯露其才學的端倪。其父也為她的才華而感到吃驚。但當時男尊女卑,為學的目的是從仕,也只有男人為之。因而其父時常嘆息她生不為男子,不然仕途無量。也許正因為她不是男子,才安于求學之道,造就了她向文學發展的機運。
紫式部青春時代,家道已中落,時任筑前守的藤原宣孝向她求婚,然宣孝已有妻妾多人,其長子的年齡也與式部相差無幾。式部面對這個歲數足以當自己父親的男子,決然隨調任越前守的父親離開京城,逃避她無法接受的這一現實。不料宣孝窮追不舍,于長德三年(997)親赴越前再次表達情愛的愿望,甚至在戀文上涂了紅色,以示“此乃吾思汝之淚色”。這打動了式部的芳心,翌年遂離開其父,回京嫁給比自己年長二十六歲的宣孝,婚后生育了一女賢子。結婚未滿三年,丈夫因染流行疫病而逝世。從此芳年守寡,過著孤苦的孀居生活。她對自己人生的不幸深感悲哀,曾作歌多首,吐露了自己力不從心的痛苦、哀傷和絕望。
其時一條天皇冊立太政大臣藤原道長的長女彰子為中宮,道長將名門的才女都召入宮做女官,奉侍中宮彰子。紫式部也在被召之列。時年是寬弘二年或三年(1005或1006)。入宮后,她作為中宮的侍講,給彰子講解《日本書紀》和白居易的詩文,有機會顯示她的才華,博得一條天皇和中宮彰子的賞識,天皇賜予她“日本紀的御局”的美稱,獲得很優厚的禮遇,如中宮還駕乘車順序,她的座車繼中宮和皇太子之后位居第三,而先于弁內侍、左衛門內侍。因而她受到中宮女官們的妒忌,甚至收到某些女官匿名的揶揄的贈物。同時有一說,她隨彰子赴鄉間分娩期間,與藤原道長發生了關系,不到半年又遭道長遺棄。她常悲嘆人生的遭際,感到悲哀、悔恨、不安與孤獨。
不過,紫式部在宮中有更多機會觀覽宮中藏書和藝術精品,直接接觸宮廷的內部生活。當時攝政關白藤原道隆辭世,其子伊周、隆家兄弟被藤原道長以對一條天皇“不敬”罪流放,道長權傾一時,宮中權力斗爭白熱化。紫式部對藤原道隆家的繁榮與衰敗,對藤原道長的橫暴和宮中爭權的內幕,對婦女的不幸有了全面的觀察和深入的了解,對貴族社會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衰落的發展趨向也有較深的感受。她屈于道長的威權,不得不奉侍彰子,只有不時作歌抒發自己無奈的苦悶的胸臆。《紫式部日記》里,也不時表現了她雖身在宮里,卻不能融合在其中的不安與苦惱。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紫式部長期在宮廷的生活體驗,以及經歷了同時代婦女的精神煉獄,孕育了她的文學胚胎,厚積了她的第一手資料,為她創作《源氏物語》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源氏物語》作品成書年份,至今未有精確的定論,一般認為是作者紫式部于長保三年(1001)其夫宣孝逝世后,孀居生活孤寂,至寬弘二年(1005)入宮任侍講前這段時間開筆,入宮后續寫,于寬弘四年或五年(1007或1008)完成。在《紫式部日記》寬弘五年十一月多日的日記里,也記載了這段時間《源氏物語》的創作過程以及聽聞相關的種種議論,并暗示有了草稿本。而且該月中旬的日記這樣寫道:
奉命行將進宮,不斷忙于準備,心情難以平靜。為貴人制作小冊子,天亮就奉侍中宮,選備各種紙張、各類物語書,記下要求,日夜謄抄,整理成書。中宮贈我雁皮紙、筆墨,連硯臺也送來了。這不免令人微詞紛紛,有指責說:“伺候深宮還寫什么書?”盡管如此,中宮繼續贈我筆墨。
這段日記,說明紫式部入宮前開始書寫《源氏物語》,初入宮就已謄抄。日記還記錄了她在一條天皇和中宮彰子面前誦讀,天皇驚喜她精通漢籍及《日本書紀》,對她的才華甚為贊賞,因而宮中男子也傳閱并給予好評。中宮彰子之父藤原道長動員能筆多人,助她書寫手抄本。這是可以作為《源氏物語》上述成書年代可信的資料,此外別無其他文獻可以佐證。其后菅原孝標女的《更級日記》也記有治安元年(1021)已耽讀“《源氏物語》五十余回”,并在許多地方展開對《源氏物語》某些章回的議論,將這五十余回“收藏在柜中”,從而旁證了該小說的手抄本早已廣為流布。可以說《源氏物語》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寫實小說,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源氏物語》的誕生,是在和歌、物語文學發展走向成熟的過程中,此時已有和歌集《萬葉集》《古今和歌集》《古今和歌六帖》《拾遺和歌集》《后撰和歌集》,古代歌謠神樂歌、催馬樂;物語集《竹取物語》《宇津保物語》《落洼物語》等虛構物語和《伊勢物語》《大和物語》等歌物語。虛構物語完全沒有生活基礎,純屬虛構,具有濃厚的神奇色彩;歌物語,雖有生活內容,但大多是屬于敘事,或者是歷史的記述。而且這些物語文學作品幾乎都是脫胎于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是向獨立故事過渡的一種文學形式,散文與和歌不協調,結構松散,缺乏內在的統一性和藝術的完整性。紫式部首先學習和借鑒了這些先行的物語文學的經驗,揚長避短,第一次整合這兩個系列,使散文與韻文、內容和形式達到完美的統一。
紫式部在創作《源氏物語》中借鑒了先行的典故乃至借用某些創作手法,作為其創作思考的基礎,乃至活用在具體的創作中。比如《古事記》中的海幸山幸神話故事(《明石》)、三山相爭的傳說故事(《夕顏》)、《萬葉集》中的真間手兒女的故事(《浮舟》)。《竹取物語》輝夜姬的形象借用在紫姬身上《,伊勢物語》的故事與和歌對《小紫》《紅葉賀》《花宴》《楊桐》等諸回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源氏物語》描寫源氏與眾多女子的愛情,和《伊勢物語》男主人公好色的特征——追求極致愛情的描寫,更是有相傳相承的類似性,打上了《伊勢物語》的濃重的烙印。
紫式部同時學習和汲取藤原道綱母的《蜉蝣日記》完全擺脫了此前物語文學的神奇的非現實性格,成功地將日常生活體驗直接加以形象化,并且擴大了心理描寫,更深層次挖掘人物的內面生活,出色地描寫當時女性的內心世界的創作經驗,還繼承和融會了《蜉蝣日記》所表現的“哀”“空寂”的審美理念。同時,也運用清少納言的冷靜知性觀察事物的方法,參照她的《枕草子》以攝政的藤原家族盛衰的歷史為背景,描寫平安王朝的時代、京城、自然、貴族、女性,和自己的個性交錯相連,以反映社會世相的寫實創作經驗。也就是說,《源氏物語》的出世,與包括物語文學、日記文學、隨筆文學在內的先行散文文學有著血脈的聯系,它們對于這部日本古代長篇小說的品格的提升,都直接或間接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紫式部對傳統文學的繼承和創新,以及她的觀書閱世的經歷,都為她創作《源氏物語》提供了對人生、社會、歷史更大的思索空間,更廣闊的藝術構思的天地和更堅實的生活基礎。可以說,紫式部以其對前人精神的不斷學習、造詣頗深的學問、人生坎坷的體驗、宮廷生活的豐富閱歷,以及對社會和歷史的仔細觀察與深沉的思考,并充分發揮文學的想象力,厚積薄發,才成就了她作為女作家留下這一名垂千古的巨作《源氏物語》。
紫式部在《源氏物語》以及《紫式部日記》和《紫式部集》里,表現了內面和外部、真實與虛構的兩面,相互映照和生輝,這也使紫式部這個名字,不僅永載于日本文學史冊,而且在196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年度表彰的世界偉人之一,享譽世界文壇。
《源氏物語》在藝術上也是一部有很大成就的作品,它開辟了日本物語文學的新道路,將日本古典寫實主義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全書共五十四回,近百萬字。故事涉及三代,經歷七十余年,出場人物有名可查者四百余人,主要角色也有二三十人,其中多為上層貴族,也有中下層貴族,乃至宮廷侍女、平民百姓。作者對人物描寫得細致入微,使其各具鮮明個性,說明作者深入探索了不同人物豐富多彩的性格特色和曲折復雜的內心世界,因而寫出來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富有藝術感染力。小說的結構也很有特色。前半部四十四回以源氏和藤壺、紫姬等為主人公,其中后三回是描寫源氏之外孫丹穗皇子和源氏之妃三公主與柏木私通所生之子薰君的成長,具有過渡的性質;后半部十回以丹穗皇子、薰君和浮舟為主人公,鋪陳復雜的糾葛和紛繁的事件。它既是一部統一的完整的長篇,也可以成相對獨立的故事。全書以幾個重大事件作為故事發展的關鍵和轉折,有條不紊地通過各種小事件,使故事的發展和高潮的涌現彼此融會,逐步深入揭開貴族社會生活的內幕。
在創作方法上,作者摒棄了先行物語只重神話傳說或史實,缺乏心理描寫的缺陷,認為物語不同于歷史文學只記述表面粗糙的事實,其真實價值和任務在于描寫人物內心世界。在審美觀念上,則繼承和發展了古代日本文學的“真實”“哀”“空寂”的審美傳統,因而對物語文學的創作進行了探索和創新,完成了小說的虛構性、現實性和批判性三個基本要素,構建了一個有機的統一體。
在文體方面,采取散文、韻文結合的形式,植入八百首和歌,使歌與文完全融為一體,成為整部長篇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散文敘事,和歌抒情和狀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文字記述了二百處和漢音樂,并有意識地以音樂深化主題。這樣文、歌、樂三者交匯,不僅使行文典雅,而且對于豐富故事內容、推動情節發展、傳達人物感情,以及折射人物心理的機微,都起到了良好的輔助作用。以音樂舉例來說,描寫弦樂,由于自然氣候差異,音色有變化,在春天時寫呂樂顯其明朗,秋天時寫律樂露其哀愁,以展露出場人物的不同心境。《源氏物語》主要貫穿“哀”與“物哀”的審美情趣,音樂也以律樂為主體,開辟了文學創作手段的新途徑。
在語言方面,作者根據宮廷內人物眾多、身份差異甚大的特點,在使用敬語和選擇語匯方面都十分注意分寸,充分發揮作為日語一種特殊語言現象的敬語的作用。在對話上使用敬語更是十分嚴格,以符合不同人物的尊卑地位和貴賤身份。即使同一個人物,比如源氏,年輕時代和晚年時代所使用的語言也有微妙的差別,以精確地把握他不同年齡段上的性格變化。同時在小說中還使用了許多擬聲語,根據人物身份,或優美,或鄙俗,以輔助人物的造型。這樣作者就不斷擴展自己的語言空間,并由此也開闊了文學藝術的空間。
紫式部主張文學應該寫真實,《源氏物語》正體現了她的這種寫實的“真實”文學觀。它的表現內容以真實性為中心,如實地描繪了作者所親自接觸到的宮廷生活的現實。也就是說,描寫的素材始終是真實的,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紫式部以較多的筆墨留下了這方面準確的記述,《源氏物語》的故事是有事實依據的,是近于現實的。比如它是以藤原時代盛極而衰的歷史事實作為背景,反映了當時政界的傾軋和爭斗的現實。比如書中描寫朱雀天皇時代以源氏及左大臣為代表的皇室一派與以弘徽殿及右大臣為代表的外戚一派的政治爭斗中,弘徽殿一派掌握政權,源氏一派衰落;相反,冷泉天皇時代,兩者倒置了。這是作者耳聞目睹道隆派與道長派交替興衰的史實,并將這一史實藝術地概括出來的典型。就其人物來說,比如源氏雖然不是現實生活中原原本本的人物,而是經過藝術塑造,并且理想化了,但如果將這個人物分解的話,也不完全是虛構的。紫式部本人在日記中談及的源氏的史實,與道長以及伊周、賴通等人的性格、容姿、言行、境遇十分相似,起碼是將這些人物的史實作為重要的輔助素材來加以運用的。
根據日本學者考證,源氏被流放須磨實際上就是以道隆之長子伊周的左遷作為素材的。概言之,《源氏物語》精細如實地描繪了那個時代的世相[1]。無論是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還是故事內容和人物,都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宮廷生活和貴族社會的實相。《源氏物語》的記述,可以說是珍貴的文化史料,包括社會史料、掌政史料乃至政治史料。日本文學評論家暉峻康隆認為紫式部是日本最偉大的寫實小說家,《源氏物語》是運用“史眼”來觀察社會現象,與虛構的要素結合構成的,它開拓了描寫現實的新天地。《源氏物語》是日本文學史上的寫實主義傾向的三個高峰之一[2]。島津久基也認為作者紫式部無論在文學主張上還是在作品實踐中都確實是一位卓越的寫實主義作家,《源氏物語》是日本屈指可數的寫實主義文學之一[3]。
紫式部在《源氏物語》中,以“真實”為根底,將“哀”發展為“物哀”,將簡單的感嘆發展到復雜的感動,從而深化了主體感情,并由理智支配其文學素材,使“物哀”的內容更為豐富和充實,含贊賞、親愛、共鳴、同情、可憐、悲傷的廣泛含義,而且其感動的對象超出人和物,擴大為社會世相,感動具有觀照性。
《源氏物語》完成了以“真實”“物哀”為主體的審美體系,在日本由“漢風時代”向“和風時代”的過渡中,完全使七世紀以來“漢風化”的古代日本文學實現了日本化,這是不朽的偉大歷史功績。可以認為《源氏物語》的誕生,標志著日本文學發展史和美學發展史的重大轉折。
《源氏物語》一方面接受了中國佛教文化思想的滲透,并以日本本土的神道文化思想作為根基加以吸收、消化與融合;借用中國古籍中的史實和典故,尤其是白居易的詩文精神,并把它們結合在故事情節之中;繼承日本漢文學的遺產。另一方面以日本文化、文學的傳統為根基吸收消化,從而創造了日本民族文學的輝煌。
《源氏物語》是在日本文化“漢風化”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中國文化、文學滋潤了它誕生的根。可以說,沒有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影響,就沒有現在這般模樣的《源氏物語》。但它更多的是傳承、活用本土的古典文化、文學。據日本學者根據現存的日本平安時代后期藤原伊行的《源氏物語》最早注釋書《源氏釋》統計:引用和漢典籍全部共計488項,其中和歌360項、漢詩文49項、故事19項、佛典13項。就以活用《古今和歌集》與白居易詩來比較,前者比后者的引用活用量大得多。實際上,《源氏物語》無論采用外來的中國古典文學素材與本土的傳統文學理念的結合,還是汲取外來的中國古典文學理念與本土的固有文學素材的結合,都不是簡單的嫁接,而是復雜的化合。是以日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為主體,以中國文化為催化劑,在彼此化合的過程中促其變形變質,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日本化”。它達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我為主”的天衣無縫的融合境地。因而它吸收中國文化,是按照日本式的思考方法,更多地開拓傳統的藝術表現的空間。如果說,菅原道真總結學習中國文化、文學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在理論上提出了“和魂漢才”,那么紫式部則在《源氏物語》的創作實踐上成功地實現了“和魂漢才”。
紫式部在廣闊的中日文化空間,高度洗練地創造了《源氏物語》的世界。它是日本文化、文學走向“和風化”的重要轉折之一。這是歷史的必然造成的。《源氏物語》超越時空,乃至日本以外的國家和地域,影響至今。這一段日本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文學的發展首先是立足于本民族、本地域的文化傳統,這是民族文學之美的根源。離開這一點,就很難確立民族文學的價值。然而,本民族、本地域的文學,又存在與他民族、他地域的文學的交叉關系,它是與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文學交流匯合而創造出來的,自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力。也就是說,優秀的文學不僅在本民族和本地域內生成和發展,而且往往還要吸收世界其他的民族和地域的文學的精華,在兩者的互相交錯中碰撞和融合才能呈現出異彩。
葉渭渠
2004年寫于團結湖寒士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