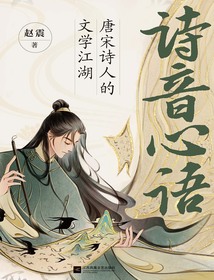
詩音心語:唐宋詩人的文學江湖
最新章節
- 第15章 參考文獻
- 第14章 浮生若夢
- 第13章 《番外篇》:曼殊沙華
- 第12章 江湖心姜夔——平生最識江湖味
- 第11章 癡心晏幾道——北宋版賈寶玉 現實版落難貴公子
- 第10章 苦心柳永——你是心中的白月光
第1章 《唐代篇》:詩心李白——并不針對誰,但我才是真正的詩壇神話
有一個人,如果沒有他——
幾位唐代大詩人會偷著樂:杜甫將是絕頂,沒有惱人的“之一”后綴;李商隱不必委委屈屈地被稱為“小李”;王昌齡可以從“七絕圣手”升級為“七絕無雙”。
但也有人會不高興:
《英雄》的導演張藝謀一定無法為片中李連杰的絕招想出“十步一殺”這樣冷酷的名字。
《慶余年》中范閑“祈年殿醉酒吟百詩”的名場面也將大打折扣。
冰心將無法為她的小說起名《斯人獨憔悴》。
郭沫若的書只能寫一半。
聞一多將惋惜地刪去這段精彩文字:“我們該當品三通畫角,發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因為我們四千年的歷史里,除了孔子見老子(假如他們是見過面的),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紀念的。我們再逼緊我們的想象,譬如說,青天里太陽和月亮走碰了頭,那么,塵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遙拜……”
余光中將缺少一首名詩:“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金庸的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將缺少一個合適的下聯。
我們詩歌想象力天花板的高度會斷崖式下跌。
我們的漢語言將失去一大批至美的表達。
至于成語,那就損失更為慘重了:青梅竹馬、一擲千金、魚目混珠、摧眉折腰、鐘鼓饌玉、仙風道骨、揚眉吐氣、九天攬月、大塊文章、秉燭夜游、粲花之論、暮云春樹、停云落月、東風馬耳、笑而不答、星離云散、浮生若夢……這些統統都會不見。
更為重要的是——
誰來告訴我“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誰來告訴我“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誰又來告訴我“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這些詩句,是力,是美,更是信念。
這個人,當然就是李白。
你要寫李白,就不能只寫李白。
要寫江城落梅,關山云海。
寫霜花拂劍,邊月弓影。
寫縱橫,寫漫游,
寫孤帆遠影下的悵然與離愁。
要寫大塊文章平生意,吳姬壓酒。
寫大道青天,寫賜金放還,
寫一場浮沉如夢的人間貶謫,
寫一場轟轟烈烈的凡人修仙。
我欲因之而夢,仙人驚鴻照影,
然后陡然折筆,
向暮春風,云游雨散,
原來屬于他的世界,就在凡間。
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篤信與期盼
今天寫李白的自媒體們,文案大多是這樣的:《李白: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李白:古代流行語大師、文案大神,繡口一吐便是爆款刷屏》《李白:瘋子、狂人以及唐代自媒體人》《詩仙李白:沒機會高考,北漂做自媒體成了唐朝第一網紅》……
他們以為這樣已經足夠博眼球的了,卻不知道,李白其實有著更潮更引流的行為——比如“修仙”。
很多人都說李白像神仙。
他媽媽說生他的時候夢見長庚星入懷,于是起名為李白。這里的潛臺詞就是——我兒李白乃太白金星下凡。問題是,官方正史還正式記載了這種說法: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新唐書》)
也就是說,李白的前世曾去花果山招安過孫悟空……
一個劉姓的縣尉和他一起喝酒,說他是唐朝的東方朔。而東方朔這個人能識怪哉之蟲,據說是木星轉世。李白寫詩《留別西河劉少府》(節選)記錄道:
閑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
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
他說他其實是“來自星星的你”,只不過東方朔來自木星,而他李白來自金星。
而與李白齊名,在經歷了《冬日有懷李白》《春日憶李白》《天末懷李白》,以至于常常《夢李白》的杜甫同學則說他是天子呼來也不上船的酒中仙。
賀知章就更不用說了,修道煉丹,和神仙走得很近,一見李白就驚呼:這不是“天上”的那誰嗎?怎么跑到人間來了?
而李白自己怎么看呢?他晚年寫過一篇名為《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的序言,他說:“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賀知章那老頭兒說我是天上貶謫下來的仙人,其實不過是實話實說而已,這老賀,也不知道要低調點兒。
不會吧不會吧,難道李白真的相信有神仙?
是的,李白崇信道教,相信神仙,并期待著與仙人相遇又或是重逢,他在《懷仙歌》中高唱: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
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
堯舜之事不足驚,自余囂囂直可輕。
巨鰲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
我看見一只白鶴飛過茫茫滄海,那是否是仙人的坐騎?任憑我的心神遨游天外,最終要去哪里停放?我看見仙境中的仙人們正在放聲高歌,期盼著我的到來。長久的等待使他們有所疲憊,于是就攀扶著瓊樹玉枝休息一下。人間沒有什么新鮮的事情,堯舜禪讓天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海中的巨鰲啊,你不要把蓬萊仙島馱到別處去了,因為我正要去蓬萊山頂走一走呢。
仙境如同故地,仙人皆是舊友,相遇不過重逢。
劉全白在《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中寫道:
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
古人行文喜歡用省略句,現代語法定義的句子三大主干成分主謂賓,在古人眼中那都不叫事兒。為了行文簡潔,生動有氣韻,謂語偶爾可以省略,賓語常常被省略,主語當然也不能搞特殊,省省更簡潔。
主語當然是李白,他崇尚道家的種種術法,相信人終究可以達到神仙之境。
世上真的有神仙嗎?這個話題就和世上是否真的有龍一樣令人著迷。
學道術、求長生,這難道不是修仙小說主人公才會做的事情?李白這樣聰明絕頂的人物,真的會信這個嗎?
事實上李白不止信,而且深信。
要知道,唐代本就信道成風,天子、公卿、公主都曾參與其中,這是一種文化風尚。至于說到求仙與長生——
君不見,秦始皇,遣人入海求仙方;君不見,漢武帝,亦信神仙終可期。
雄才大略的秦皇漢武都相信神仙的存在,李白相信,又有什么可驚訝的呢?
心動不如行動,或者說,正因為心動了,才會行動。李白為得道,做了許多事。
讀道書
李白幾歲起就開始接觸道家典籍了呢?五歲。
“五歲誦六甲。”《六甲》一般認為是道教的入門級著作,道術能調動鬼神:“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神仙傳》)不過估計李白沒學明白,也幸好他沒學明白,不然此刻我就該寫“大唐陰陽師”傳奇了(笑)。
雖然不能役使鬼神,但后來的他學會了御鳥術,且看他的《上安州裴長史書》:
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因舉二人以有道,并不起。
李白和一位號為東巖子的道士隱居在四川岷山,修心向道。他們在居住的山林里飼養了許多奇禽異鳥。這些美麗而馴良的鳥兒,好像能聽懂人的語言,一聲呼喚,便從四處飛落階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點都不害怕。這件事被當作奇聞在當地廣傳,后來連廣漢太守也親自到山中觀看鳥兒們的就食情況。太守認為他們有道術,便想推薦二人去參加道科的考試,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絕了。
“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風,泛瑟窺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煉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闕。”李白(《感興八首》)還是少年時的李白,就已經懂得煉丹的相關事情了,“煉金骨”即是煉丹。
開元六年(718年),李白十八九歲時,隱居匡山讀書,在戴天山的大明寺,潛心研讀道經。
長大后的李白,依舊不忘學習道家典籍:“我閉南樓著道書,幽簾清寂若仙居”。也曾虔誠地親自抄寫道經:“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經。”(李白《游泰山六首》)遠行時更是道書不離身:“是日也,東出桐門,將駕于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獨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
結仙友
白哥的好友列表中如果有星標朋友,那多半不是杜甫、孟浩然,而是下面這兩位:
愿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
這是李白《寄王屋山人孟大融》中的名句,其中的夫子名為司馬承禎,能令心高氣傲的李白甘心追隨,當然非同凡響。他是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師,身為道士,卻是帝王師。開元九年(721年),奉詔進京,被唐玄宗留于內宮,問以養生延年之事。第二年,玄宗幸洛陽,命司馬承禎隨駕東行。開元十一年(723年),年近八旬的司馬承禎厭倦了長安的喧囂,要求回轉浙江天臺山。
開元十三年(725年),李白慕名去拜訪司馬承禎,二人在江陵相見。
司馬承禎不僅道行深厚,而且文采飛揚,出口成章。至于李白,那是閑談也能做粲花之論的人。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粲花之論》中寫道:
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
所以二人一見,傾蓋如故。再看過李白的詩文之后,司馬承禎稱贊他“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李白《大鵬賦》)認為李白有“仙根”。
這一評價可以說對李白影響極大,讓他的修仙之心愈發堅決。這就好像你寫了篇小說,同學看到,說哎呦不錯哦,你內心毫無波瀾;媽媽看到,說還行,你淡淡笑了笑;語文老師看到,說有點意思,勉之。你開始有幾分得意。然后魯迅先生看到了,說后生可畏,以后打敗黑暗,拯救光明的使命就交給你了,你什么反應?當然是一拳砸碎玻璃,然后狂熱地搞創作去。那可是魯迅啊,他說我有前途,沒前途我都造個出來給你看!
一心向道的李白就是如此,得到道家宗師的激賞,心情十分興奮,回來后就寫下了名篇《大鵬賦》:“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乎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網。以恍惚為巢,以虛無為場。我呼爾游,爾同我翔。”這是李白的第一篇成名大作。從此,李白與司馬承禎結為忘年交,互有詩賦往來,司馬承禎還把李白列為他所結識的詩歌朋友圈“仙宗十友”司馬承禎、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盧藏用、王適、畢構、宋之問、陳子昂之一。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
這是李白《將進酒》中的名句,其中的丹丘生,名叫元丹丘,是與李白保持了終生友誼的道友。在李白眼中,這個朋友已經得道,能跨海飛天:“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峰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游心無窮。”(《元丹丘歌》)并且長生不死:“云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西岳云臺歌送丹丘子》)
這固然是夸張了,但兩個人的關系絕不夸張:“吾將元夫子,異姓為天倫。”(《穎陽別元丹丘之淮陽》),我們是姓氏不同的親兄弟。
他們一起訪師學道:“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冬夜于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一起談玄悟道:“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郎悟前后際,始知金仙妙。”(《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一起隱居在嵩山尋仙煉丹:“提攜訪神仙,從此煉金藥。”(《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
而李白第一次入長安時,能夠見到唐玄宗,也是因為元丹丘向玉真公主引薦李白,玉真公主再向玄宗引薦,再加上賀知章等人的推薦,事情才得以成功的。
訪名山
世間若有神仙,他們會住在哪里呢?先不急著說答案,我們來講個奇遇的故事。
劉晨、阮肇兩個人上天臺山采藥,結果迷了路。不過按故事展開的套路,這往往是好運的前兆。
他們饑渴交加,突然看到山上某處有桃樹,果實已經成熟,兩個人趕忙攀爬到那里,吃了幾顆大桃子,然后就感覺肚子不餓了,頭也不昏了,腿腳也靈便了,精神頭也足了。細心的讀者當體會,這不是普通的桃子,這是伏筆啊!
他們吃飽后想下山,就順著水走,結果見到溪流中流過一只杯子,杯子里盛有胡麻飯,二人互相看看,明白這是靠近人煙了,很高興。然后就在溪邊遇見二個女子,容貌姣好,還沒想好如何搭訕,人家女子倒先說話了:“劉、阮二郎為何來晚也?”
不僅知道他們的名字,還好像舊日相識一樣。這是前世姻緣嗎?
兩個女子邀請他們做客,酒飯款待,宴席結束后,幾個侍女捧著桃子,笑著說:“二位貴婿隨我來。”注意稱呼,貴婿,這真是天上掉下個神仙姐姐!再然后,他們就與兩個女子結為夫妻,好花月圓了。這樣過了十天,劉、阮要求回鄉(這說明故事就是故事,如果是真的,誰會想回去啊),仙女不同意,苦苦挽留下,又過了半年。
又是一度子規春啼,劉、阮二人思鄉心切,兩位仙女終于允許他們回去,并指點了回去的路途。等他們回到家鄉后,卻找不到舊址,四處打聽下,結果在一個小孩子(他們的第七代孫子)口中聽到,長輩傳說祖翁入山采藥,之后便消失了沒有音信。原來,他們在山上過了半年,山下竟已經過了幾百年。二人見狀,只得返回采藥處尋妻子,結果卻怎么也找不到,他們就在溪邊踱來踱去,徘徊不已。后來該溪因此得名惆悵溪,溪上的橋得名惆悵橋。
這是一個記載于《搜神記》上的遇仙故事,那兩個女子,就是桃花仙子。
神仙在哪里?其實仙這個字已經透露了玄機,人在山,則仙;人在谷,則俗。所以要遇仙,得訪山。李白在《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就曾寫道:
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
早在四川的時候,李白就走訪過不少道教名山:
在峨眉山,他有過羽化飛升的遐想。
在紫云山,他觀看齋醮的儀式。
在戴天山,他寫下一首《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山中春色,溪流潺潺,犬吠隱隱,溪邊桃樹上的桃花開得正好,幽深的樹林中偶爾會看到梅花鹿一閃而過。他沿著溪流的方向信步而行,這條路已走過很多次,熟悉的景色如同老友。可是可惜啊,他要尋訪的道人并不在家,問了很多人,沒人知道他的去向,倚靠在門前的松樹上等了許久,道士仍然未歸,不覺有些惆悵。
詩歌意境清幽,其中一句,更是引領潮流許多年,點染出一句流行文案,至今仍在流行:
林深時見鹿,海藍時見鯨,夢醒時見你。
后來在漫游天下時,他也曾去過嵩山,不過又經歷了一次失望。這一次他想拜訪的人是女道士焦煉師,李白說她:“嵩山有神人焦煉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于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谷,居少室廬,游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人東海,登蓬萊,竟莫能測其往也。”(《贈嵩山焦煉師》)行走如飛,瞬間萬里,果然不是普通人,李白希望成為她的弟子,可惜“盡登三十六峰”,卻終未能謀面,于是留詩一首,悄然離開。
受道箓
讀書人拜師要先給老師送一份束脩之禮,佛門弟子入佛門要剃度,而道家,則是受道箓(道教教的典冊、簿籍)。
天寶三載(744年),李白離開長安,來到山東紫極宮,道士高如貴為李白親授道箓,至此,李白正式成為道門中人。
受道箓后,他心存感激。不久,高如貴要北行,李白設宴款待,并作《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箓畢歸北海》一詩留念:
道隱不可見,靈書藏洞天。
吾師四萬劫,歷世遞相傳。
別杖留青竹,行歌躡紫煙。
離心無遠近,長在玉京懸。
高如貴道士來歷、行蹤沒有很多史料記載,他為李白傳道箓后隨即歸北海仙游而去。但從詩中“吾師四萬劫,歷世遞相傳”看,其修行來歷絕非一般。
此后不久,李白訪道北上,到達德州安陵,遇道士蓋寰,后者為他書寫真箓,對修道人來說這可是件不容小覷之事,故李白寫詩為記:“學道北海仙,傳書蕊珠宮。丹田了玉闕,白日思云空。為我草真箓(道教的秘文秘錄),天人慚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輝星虹。”(《訪道安陵遇蓋寰為予造真箓臨別留贈》)
這可能是一個級別更高的道箓,但有沒有舉行過授箓儀式,就不得而知了。
至此我們可以說,李白篤信道家,期盼長生,那么道家的仙風道骨又為李白帶來了些什么呢?
霓為衣兮風為馬,云之君兮紛紛而來下:簡傲與超然
任華在《寄李白》中寫道:
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為客,未嘗一日低顏色。
其實李白的志向、理想是可測的,或者說根本不需要推測,他自己說得明明白白,他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寫道:
將欲倚劍天外,掛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
他有兩個理想,一個是求仙,一個是做官,而且是做大官,立功業,然后功成身退。
他可以求仙,但他不能做官,因為當時的皇帝唐玄宗召人編纂了一部行政法典《唐六典》,對官制,包括科舉做了詳細規定:“刑家之子,工商殊類不預。”規定罪犯、商人的孩子不能參加科舉。
李白的祖先曾經被流放碎葉,他父親李客又是位商人,兩條他全中。
所以縱使你天縱奇才,也無緣科舉。那怎么辦?還有一條路,依靠那些達官貴人的推薦,也可以獲得官職。所以李白要去干謁,也就是拜訪各種有權力、有名望的人,把詩文呈獻給他們看,希望獲得他們的推薦。也就是說,你要去求人。
求人就要低頭,但李白偏偏不可能低頭,因為道家的瀟灑出塵賦予他如仙人一般的貴潔,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詩文中,從來無需仰視仙人仙境,自己是和他們一樣的存在,仙人是他的朋友,仙境是他的家,他們在等待著他的回歸。
高潔瀟灑、絕對自由的天人,又如何能向人間的平凡與庸俗低頭?
我們喜歡的,不也正是他視王侯如糞土、不畏權貴的高傲嗎?
他去拜訪李邕,希望對方可以提攜一下自己,因為“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但他們之間的第一次見面并不愉快,李白離開后就留了首《上李邕》回懟對方: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世人見我恒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不得不說,有才就是好,寫首詩跟玩兒一樣,隨隨便便的句子就驚艷后世你我一千年。
那時李白二十歲左右,正是意氣風發的時候,低眉順目地求人豈是天人姿態?他求韓朝宗舉薦自己,可你看他寫的《與韓荊州書》: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愿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云耶?
文采飛揚,氣勢縱橫,哪里有半點低聲下氣之態?要知道,在此之前,李白曾求見駙馬張垍,希望見到玉真公主,結果被安排在終南山住了一個多月,受盡冷遇,卻無果而終。
求人如吞三尺劍,靠人如上九重天。可李白,人要求,事要做,但就是不肯低顏色。可想而知,他求人的結果會如何。不過上天還是給了他一次異常難得的機會,在真正的朋友元丹丘、賀知章等人的幫助下,他終于見到了玄宗皇帝,并成為翰林待詔,這是李白一生中最閃耀的時刻。《新唐書·李白傳》中記載:
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
他終于來到了皇帝的身邊,終于來到了政治舞臺,他的行政才能如何?他會改變嗎?《新唐書·李白傳》記載了這期間發生的兩件事:
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
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脩。
這就是后世津津樂道的力士脫靴的故事。
快意嗎?快意啊!李白嗎?很李白啊!
可這樣的疏狂舉止,卻恰恰是為官的大忌,是政治素養極其不成熟的表現。李白希望自己可以做宰相,宰相要具有怎樣的能力?
《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記載: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多么復雜艱巨,可李白連身邊最基本的人際矛盾都無法處理,又如何勝任宰相之位呢?無他,性格決定命運,率性坦蕩、喜怒分明,灑脫自由的李白,根本就無法在復雜的政治舞臺上立足,又遑論表演呢?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懇求還山。結果,“帝賜金放還”。(《新唐書·李白傳》)
這大約是長安之行的最好結局。
一顆仙心,未能給他仕途的坦蕩,卻給了他詩途的璀璨。最神奇渺遠的仙人仙境與最瑰麗的文字語言、最浪漫無拘的想象相遇后,云行雨施,天造草昧,會孕育出怎樣一片燦爛壯美的星河?
此前從未有人,此后也不可能再有人,寫出過他筆下那般煙雨迷離、龍變虎躍,氣勢恢宏壯麗的境界。
我喜歡酒,美酒,我喜歡詩,好詩。除了這些,我還相信神仙,喜歡名山大川。其實它們本是一體,山中有詩,詩需美酒,美酒當和神仙共飲。
人們說起海外的仙島,飄渺不定,難以見到。但人間的天姥山,在云霞掩映間可以見到。傳說那座山上有神仙歌唱過。其實天姥山的美名,早在魏晉時期就已流傳,謝靈運,對,我只佩服過他,他就寫過“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還期那可尋?”(《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哪可尋?那就是不可尋,可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有機會去一趟天姥山啊!要是還能遇到山中的神仙,那真是此生無憾了。
算了,再來一杯酒吧,一夢千年。
月光下,眼前的景色都仿若籠罩在一層薄紗之中,迷離夢幻。這里的山峰重巒疊嶂,主峰高聳入云,湖光月影伴著我輕盈的身姿,亦真亦幻之間,飛至九曲剡溪。啊,謝靈運當年登臨天姥山的投宿之地仍在,春水微皺,猿猴輕啼,他當年吟誦“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的詩句如在耳畔,他遇到山中的神仙了沒有?我穿上謝公為登山而創制的一種木鞋——謝公屐,去攀爬直入云霄的天梯。半山腰處,回首可見紅日從東海升起,聽到傳說中住在東海桃都山頂一棵大樹上的天雞破空一啼。
山路仿若迷宮,幽巖絕壑,奇花異草,這不像是人間所有啊!
我正沉浸其中之時,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大霧迷蒙,然后就聽到野獸般的叫喊聲,像是龍的吟嘯,又像是熊的狂呼。突然間,閃電破空,霹靂驚天!山巒崩塌,轟隆一聲巨響過后,仙府石門洞開!
我看見無數的仙人穿著霓虹羽衣,坐在鸞鳳彩車上,蒼龍在前引路,白虎在旁作衛。仙人密密麻麻、熙熙攘攘,猝不及防,我被擠下云彩。
突然下落的感覺讓我猛地一驚,一睜眼卻發現剛才不過是夢。一聲長嘆,入夢前的枕席依舊安放在一旁,夢中仙境里的煙霧云霧全都消失不見。
我悵然若失。
這真是一場長長的夢,我為何會做這樣的夢?
這個夢境像極了我剛剛進入長安時的景象——那高高聳起的天姥山,不就是我心目中帝京長安的模樣嗎?那一夜的飛度,扶搖直上,與當年奉詔入京,成為翰林待詔何其相似。那山中莫測的云雨,豈非君心難測的寫照?那熙熙攘攘的仙人,未嘗不是長安城中的達官顯貴;跌下云端,賜金放還。
說不失意,不合人情,其實我一直郁結于心。然而剛剛的這一刻,我忘記了所有,我身非我,物我渾然,種種不如意,輕若鴻毛,微不足道!三年的待詔翰林,也無非黃粱一夢,夢醒皆空,我何必這樣耿耿于懷不能放下?
來來,且更進一杯酒,騎上白鹿,去名山尋仙訪道,人生貴在適意,怎么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呢!
幾天后,朋友們來拜訪我,我便將這個使我解脫的奇異夢境寫成詩,贈給了他們: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云霞明滅或可睹。
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天臺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
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腳著謝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
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衣兮風為馬,云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
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朋友問我,為何明明沒有去過天姥山,卻能將天姥山的景象寫得如此恍恍惚惚,奇奇幻幻呢?
我大笑,神游天地,物我交融,那一刻我就是神仙,安有其不能耶?
這首《夢游天姥吟留別》,首尾清醒,物我相對,是現實。中間夢中神游,徹底忘卻現實中的一切紛擾煩惱,盡情體會那些從未體驗過的奇異感覺,這種體驗盡管非常短暫,卻是完整而物我相融的生命體驗,生命在這短暫的神游中產生了永恒的意義。
心理學家馬斯洛把這種感受稱為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
馬斯洛在調查一批有相當成就的人士時,發現他們常常提到生命中曾有過的一種特殊經歷:“感受到一種發自心靈深處的顫栗、欣快、滿足、超然的情緒體驗”。由此而獲得的心靈自由,照亮了他們的一生。
道教所賦予李白仙風道骨的氣質,融進了他的詩歌里,讓他的詩歌變得超塵拔俗。在那里,李白自己的世界里,大江大浪化為仙人,時空變幻顛倒古今都尋常不過,這些無邊無際的想象及仙氣都來自道教,他喜歡別人叫他“謫仙”,道教是他的精神支柱,卻也是他的障礙。
他渴求如神仙般自由,卻也渴望能仕途通順,建功立業,這兩者是如此的矛盾。
他對兩個理想的追求,讓他非常分裂和孤獨。
其實,他在創作的時候,在寫詩的時候,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的時候,想入非非,自由自在,筆下的世界里他就是神,這種超然無我的高峰體驗,不就是神仙境界嗎?
屬于他的,應該是詩。
挹君去,長相思,云游雨散從此辭:失落與清醒
如果不是“安史之亂”,如果不是永王李璘,李白的第二個夢或許還不會醒。
“安史之亂”發生后,唐玄宗李隆基一行人逃往四川。史書記載說明皇幸蜀,不得不說,皇帝駕臨某地曰幸這個表述發明得實在不錯,無論事實上有多狼狽,至少在史書記述中依然體面。
在馬嵬驛,老將陳玄禮協同太子李亨發動兵諫,楊國忠和楊玉環因之而死。之后陳玄禮向李隆基請罪,而李亨與李隆基父子之間的嫌隙已生,遂分道揚鑣:李隆基繼續往四川成都走,永王李璘(他是李隆基的第十六子)隨行,而李亨則北上去了靈武。
到了靈武后,李亨在身邊眾臣勸說下登基稱帝,是為唐肅宗,尊李隆基為太上皇。此時的李隆基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太上皇”了。他發布詔令,封李亨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封其他幾個王分別為節度使,共同討伐安史叛軍,其中永王李璘所封的勢力范圍最為富庶。
這個詔令在發布前,高適(著名邊塞詩人,但此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眼光卓越)曾建議不可,認為這樣可能會導致他們擁兵自重,對抗朝廷,但唐玄宗并沒有聽,或許是聽了也沒用,已經別無他法。
于是李璘就去赴任,他所統領的地域最為富有,且沒有受到北方戰亂影響,十分容易發展,他的下屬諸將建議他可以割據一方,以觀局勢變化,但他并沒有回應。
那么請問就目前這個局勢,李白你怎么看?
如果是諸葛孔明、賈詡、田豐這些三國時期的一流謀士,他們又會怎么看呢?
天下同時有兩個皇帝,這是不可想象的。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為了皇權,一切皆可不惜。唐玄宗曾經一日殺三子,馬嵬事變中又犧牲了楊玉環,他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帝位嗎?此時他手中用以對抗李亨最好的力量是什么?恰是永王李璘。所以他會對李璘有進一步的部署和要求。
而在肅宗李亨的眼中,他這個兄弟的威脅遠遠大于安史叛軍,若李璘割據南方自立為王,自己就算剿滅了北方的叛軍,也是一個南北朝的局面,他的地位不會穩固,所以他也一定會對李璘采取措施。
此時李璘的下一步行動就十分重要。擇主的話,要么選擇實力相對強大的李亨,比如高適(此時的他已經離開玄宗,跑到了李亨身邊為其出謀劃策,真是有遠見);要么選擇老皇帝玄宗,賭他可以翻盤;要么觀望,看李璘會如何反應。
李璘亦在這時征召了隱居于廬山的李白,如果你是李白,你會去嗎?
當然是不去為佳,局勢正撲朔迷離,學習過縱橫術的李白怎么能在這個時候去呢?連他的妻子都勸他不要去。他的妻子宗氏出身官宦世家,祖父宗楚客政治經驗豐富,卻仍然死于權力斗爭,在她看來李白的政治經驗為零,去了必然兇多吉少。
李白卻認為,這是實現他政治抱負的絕佳機會。
他不愿求人,而這次是李璘派人前來請他;他渴望被賞識,此次李璘正是禮賢下士;他的理想是使寰區大定,而此去正是為剿滅叛軍。這樣的機會以后還會有嗎?所以他去得義無反顧。
然后李璘行動了,無視李亨的詔令,開始東巡,李白隨行并寫詩作贊。東巡途中遇到吳郡太守李希言寫信質問其意圖,結果永王李璘立刻派兵攻打吳郡,同時派遣大將攻打廣陵。這就再也說不清楚了,叛軍未滅,卻先打起了自己人,這難道不是謀逆?最后李亨出兵,李璘兵敗被殺,審判同黨,李白被判長流夜郎。
經此一事,李白終于清醒了,他根本沒有經綸天下的才能,他不是張良,不是魯仲連,不是范蠡,他盡可以在詩的世界中盡情書寫他們,卻不能在現實中期待自己成為他們。
他的仕途之夢醒了,那么求仙呢?仙人是否眷顧了李白?
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盧敖游太清。——和神仙一起約好了接他和朋友走。
終當遇安期,于此煉金液。——如果能碰見安期生,我就和他一起好好煉仙丹。
紫書倘可傳,銘骨誓相學。——如果能把成仙的書留給我,我一定刻骨銘心地學習。
仙人如愛我,舉手來相招。——仙人如果愛我,就趕快揮手招我過去。
但這些都是他的想象,他終究沒有遇見神仙,等待他的是一個又一個失望。他煉制的丹藥,也沒有令他成仙,反而損害了他原本健康的身體。他不再那么篤定了,仙境真的存在嗎?人真的能夠成仙嗎?
寶應元年(762年,李白在這一年逝世)的春天,他似乎預感到了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于是前往當涂的橫望山看望自己的舊友吳筠道士,或者是一次訣別。然后,他寫下了一首長詩《下途歸石門舊居》(節選),詩中,他以一種超脫出來的眼光看待曾經學道的往事:
余嘗學道窮冥筌,夢中往往游仙山。
何當脫屣謝時去,壺中別有日月天。
我也曾為學道而鉆研道經與學仙,往往夢中都在仙山上游行。總盼著有一天會得道解脫而玉,進入那壺中別有日月的仙境。
學道對于自己,已經是過去時了,從前的自己,是那樣的渴望另一個神仙世界。
數人不知幾甲子,昨來猶帶冰霜顏。
我離雖則歲物改,如今了然識所在。
那里一些人已長壽得說不清自己的年齡,一個個肌膚猶如冰雪般潔白。自從我離開那里,一年年地發生了變化,如今,我終于明白了關于仙境的所在。
依然和以往一樣,描繪了神仙所在的仙境,但這一次,他說自己了然了。他從沒有像這般清醒過,他知道神仙其實也是虛幻,或許他早就知道了吧,只是一直不愿承認。
挹君去,長相思,云游雨散從此辭。
欲知悵別心易苦,向暮春風楊柳絲。
“云游雨散從此辭。”我想這是李白寫的最動人的一句詩。
雖然此刻他仍然在描寫著神仙的世界,但我們能感受到,他在告別,他終于回到了人間。之前大半生他都相信自己是謫仙人,一心想要離開人間,離開這紛紛擾擾的紅塵。然而這一刻他才明白,人間才是他唯一的家。唯有人間,才有那些恨他、想他、念他、傾慕他、欣賞他、排擠他、幫助他的親人、朋友、愛人、敵人。唯有這一切,才是生命的真實。
他不屬于天上,也不屬于政治,他屬于詩。
若說有遺憾,大約會后悔為什么不盡情地傾瀉自己的才華好好寫詩,可真的需要遺憾嗎?如果沒有那些求仙訪道、官場周旋的經歷,又如何會有那些多姿多彩的詩作呢?
是啊,不需要遺憾,他是李白,用筆墨和詩歌塑造了自己的神話,在詩歌的仙境中,在他揮筆創造的那一刻,他就是神。
他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中寫道: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宛若做了一個長長的夢,從太上忘情的期盼到漫游山海的傲岸,又到物我兩忘的超然,直至不能忘情的清醒。
他終于醒了,天上的事都放下了,人間的富貴功名還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他不同于蘇子,蘇子先有得,得到后又失去,在得失之間,在起落浮沉之中徹悟,然后活在當下,隨遇而安。李白終其一生,都沒有真正得到過。或言李白一生灑脫,其實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李白一生都在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中糾纏。
現在,放下了,心就安寧了,放下了執著,得到了自在,不就已然成仙了?
其實屬于自己的,只是一支詩筆啊!
李白,他找到了自己的那顆心——詩心。
詩心永在,浪漫不死,李白萬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