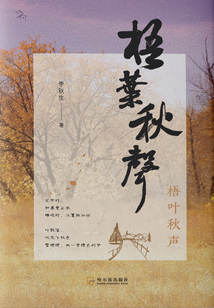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老家印象·藍花嗉子東井水
奶奶管茶壺叫“嗉子”。
一把老嗉子,白底藍花,盤口般上下一樣粗細,身上爬滿細碎的裂紋,兩根細銅條提把兒——它可是奶奶的寶貝。
每天早飯后,洗把手,奶奶便在方桌右手邊紫黑色的椅子上坐定,干瘦的手從方桌靠墻的茶盤里摸過嗉子,再從抽屜里的鐵盒子里抓一把茶葉沫子慢慢撒進去。母親早已把灌滿開水的竹篾皮暖瓶放到方桌腿邊上。奶奶彎腰提起暖瓶,拔下瓶塞,將開水嘩嘩地倒進嗉子里,熱氣一縷縷冒出,茶的香便裊裊地彌散開來。這時你看奶奶,一臉的幸福。
于是一上午的光陰就全裝在這把嗉子里了——從釅到濃,從濃到淡,直到茶水像頭頂那白亮亮的太陽,沒有了一點顏色。
沏茶的水是從東井挑來的。奶奶說:“東井通著龍宮,水旺,甘甜。”
東井在村子的東頭,西向沖著中心大街。井就在大街的東延長線端,像棧橋。只不過,這“棧橋”是伸進碧綠的莊稼地里的。全村李蔣司張汪齊諸姓氏四百多口子人,沿大街南北聚族而居,遠的近的全都喝著東井里的水。
清晨公雞的打鳴聲拉開村子沸騰的一天的序幕,光亮就慢慢暈染在窗欞發烏的“貓頭紙”(麻紙)上,屋里的黑影漸漸向犄角旮旯處躲藏,門后的大水缸便顯出輪廓,方桌上的嗉子也藍白分明起來。“吱呀——哐當”,左鄰右舍的街門陸續打開。不多時,街上便有“吱嚀吱嚀”空桶搖擺的聲音從西向東響過來。
“挑水啊?”
“挑水。”
“大叔早啊!”
“早!早!”
一會兒,熟悉的寒暄聲伴著“嘎吱嘎吱”扁擔負重的低啞聲和“咚咚咚”沉重的腳步聲從東向西響過去……來來回回,你呼我應中,天空現出道道紅霞,早起挑水人家的水缸里便一漾一漾地泛上清清冽冽的光。
上午喝足了茶水,起晌后,奶奶精神頭十足,拿把撐子坐在胡同口西屋山的陰涼里,靜靜地看風景:街北慶利家墻外的柴火垛根,一群黃的黑的花的母雞正在認真地低頭刨食,不時咕咕咕地叫幾聲;穎穎家的那只黑狗,總是會在半下午時,跑到八子家門口的那棵洋槐樹根下撒泡尿,然后顛顛地向西找順成家小花狗玩兒去。奔跑玩耍的孩子、拎著衣物青菜的媳婦們,東來的,西去的,知道奶奶耳背,老遠就高聲招呼,奶奶也揚起胳膊大聲地回應著……
太陽西斜,屋山角的影子在街上越拉越長,直到把昏黃的陽光趕上對面的土墻頭……下地的人們陸續回來,一天里挑水的另一番場景便開始了。
在奶奶眼里,論挑水的功夫,西頭柳子是最好的。柳子二十一二歲,長得也像柳樹樁子般壯。挑水不用手不說,還能換肩。他用右肩挑水走著走著,到人多的地方,猛地將腰一挺,肩膀把扁擔往上一送,順勢一弓腰,頭和身子向右一閃,扁擔便穩穩地落在左肩上。大伙還沒明白過來,他已經挺直身子,挓挲著手,大步流星地去了。奶奶——豎大拇指:“好小子!”
二叔家的棗花兒,個不高,十八歲。常常挽著褲腿腳兒,露著一截兒雪白壯實的小腿,兩條又黑又粗的大辮子。她挑著水一走起來,腰就扭;腰扭,辮子就扭;辮子扭,桶也跟著扭。奶奶見了嘬一下嘴:“真俊,這閨女!一定找個好主兒!”
奶奶一看見小祥出來就嘆氣:“苦孩子啊!”小祥個小,瘦,虛歲十四。兩只大桶剛能拖離地兒。挑水時,得雙手用力向上撐著扁擔,步子總是踩不到點上,慌慌亂亂的。人晃,桶晃,水也晃。小祥爹前兩年得病沒了,母親拉扯著他們三兄妹。他老大,水就得他挑。
一來二去中,天色便發青、發暗。這時才出門的一定是明儒。五十出頭,走路有點瘸——年輕時苫屋,不留心從屋頂上摔下,右腿落下了毛病。這么多年,他從來不急,都是等人家挑完了才慢悠悠地出門。他往東井走的時候,正好母親隔墻喊奶奶吃飯,奶奶朝明儒擺擺手,便拾起撐子往家走。不多時,夜幕從遠處籠過來,不急不躁地跟在明儒蹣跚的身后,罩過東井,罩上大街,隨著明儒家大門“哐當”一聲響,被關在門外大街上。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東井里的水總是清清亮亮的。它就像一面大鏡子,倒映著明晃晃的藍天,映照出打水人生動的剪影,折射出鄉親們百態的生活。
一擔擔井水,從井沿兒濕黑的青磚開始,在街中心滴成一溜溜黑線,然后散進街南街北的胡同、大門里。于是,家家戶戶就有了茶香,有了粥甜,有了夏面的涼爽;有了雖舊但干凈的衣衫,有了大姑娘小媳婦們俊俏的臉龐;有了雞鳴鴨叫,有了嬰兒們咯咯的歡笑聲;還有那墻里墻外一畦畦的生菜、芫荽、一架架的扁豆、絲瓜……
孩子們永遠是忙碌的,他們連等一碗熱水變涼的耐心都沒有。無論冬夏,躥得滿頭大汗、敞懷露胸的孩子,跑回家一頭扎進飯屋,一瓢涼水一揚脖兒,一口氣咕咚咕咚就下了肚。抹一把嘴,捋一捋圓鼓鼓的小肚子,一溜煙地又飛上了大街。東井水養出來的孩子沒病沒痞,個個皮實得很。
南鄰的維俊大爺,犯癆病,隔著三間宅子都咳得人睡不著,獨生閨女更是被他咳到去大姑家住。在赤腳醫生那里不知道吃過多少藥丸子,后來,他干脆不吃了。睡前,就讓老伴兒舀一碗涼水蹲在炕頭,晚上咳得厲害,他就端過來喝上兩口。清涼的水順著干痛的喉嚨下去,滋心潤肺,反而把咳嗽壓住了。于是,白里夜里維俊大爺總裝瓶涼水帶在身邊,一咳就喝。時間一長,咳得輕了,人也精神了,好些年不能下地的他居然也扛上鐵锨了。有人好奇問他,他就拍拍瓶子:“咱有神水!”
那次新春家失火該是夏天的一個十五前后。記得那晚的月亮很圓,月光如同在院子里灑下的一地水銀。乘涼到很晚的人們剛剛進入夢鄉,忽然大街上傳來急促的“救火”聲。男人們匆忙披上衣服提桶端盆往外跑,忽明忽暗的火光照著街上紛亂的腳步。新春家離東井不遠,很快火被撲滅了。火是從飯屋煙囪處著起的,新春娘見好在沒蔓上大屋,自是千恩萬謝。第二天天一亮,她就來到東井,在井臺上點燃一炷香,跪在井臺下的泥濘里,重重地磕了三個響頭。
第二年春天出奇的旱。年前一冬不見雪,過了年到清明也沒記得下一滴雨,眼見地瓜秧子都沒水栽。鄰村的井干了,吃水也成了困難。只有東井安然無恙,依然是明晃晃的半井筒子水。奶奶說:“東井通著龍宮呢。”北邊村里幾個姑娘就隔三岔五地來東井推水,調皮的大娃子就鬧她們:“推水,是要收費的。”姑娘們也不說話,只顧低頭忙活。三年后,那“被收費的”里面最俊的姑娘就做了大娃子的媳婦兒。據說,洞房夜,大娃子問新娘子相中他啥,新娘子臉一紅:“你村水甜。”
天旱也罷澇也罷,東井里有水,奶奶的白底藍花嗉子就永遠是溫熱的。有時奶奶和后鄰的大奶奶(個高,腳大)喝足茶拉完呱,就踱到院子里看花兒——奶奶喜歡花兒,院子邊角旮旯里種上步步高、光光花、臭芙蓉、馬榨菜。靠西墻根有一個很大的石頭槽子,足足能盛下三擔水。我和弟弟每天或挑或抬,把它灌得滿滿的。奶奶就拿個水瓢,澆澆這,澆澆那。高的矮的,大的小的,紅的黃的花兒,倒也開得活潑鮮艷,兩個奶奶堆滿皺紋的臉上掛滿笑意。
東井滋養著一村人,人們自然把它看得比眼珠子都重要。
每年人們都將井臺四周培土夯實,把井臺上的碎磚換掉、坑洼填平。井臺周圍的雜草秸稈都清得干干凈凈,以免被大風或雨水帶到井里。
“不能往井里扔雜七雜八”也成了約定俗成的規矩。那年,月鳴家小山子往井里撒了一泡尿。他爺爺聽說后,把他狠揍一頓。盡管大伙都勸說“童子尿,不騷”,可他爺爺硬是雇人用“195”(抽水機)把井水抽干、把泥淘凈,徹底清洗一遍才完事。
老川媳婦跳井是當年一起很轟動的事件。
老川媳婦三十五六歲,人老實,少言語。那天傍晚,她餾好干糧、做好湯,一小鐵鍋白菜粉條燉到六七成熟。她起身去拿鹽,腳蹚到了燒火棍,燒火棍別倒了支鍋的磚,小鐵鍋一歪,白菜就全扣在火堆上。正不知所措,老川下地回來,一步跨進屋門,見此情景,不等媳婦解釋,劈頭蓋臉地罵起來。媳婦嗚嗚地哭,老川一頭攮到炕上生悶氣。
等老川迷迷糊糊醒來,屋里漆黑一團,沒一點動靜。他喊幾聲,無人應,便起身來到父母家。只有兩個孩子在,不見媳婦,便氣呼呼地到大街上喊,依然沒有回應。他就有些慌,便張羅本家兄弟子侄十幾號人出村四下里去找。老川幾個人來到東井,手電筒照見井口邊有一只方口藍條絨鞋。老川一看,大叫不好,急忙趴在井口向下照著看。卻見井水平靜如鏡,沒一絲波動。竹竿扛來,綁上抓鉤,插到井底,貼幫靠沿來來回回地撈,卻無一點礙擋。老川的汗和眼淚就一起下來了。嘴角一咧,正待號啕,突然北邊遠處玉米地里傳來吆喝聲:“找著啦——找著啦——”多虧鄰村的那口土井水不深,老川媳婦兒頭部只是一點擦傷,歇息數日后也就好了。
后來年輕媳婦們聚到一塊就當玩笑地逗老川媳婦:“你那時玩的是聲東擊西的戰術吧?”老川媳婦低著頭笑著說:“俺是怕染了東井里的水。”
到晚年,奶奶有些懶得動,上街就少了。于是大奶奶和鄰居的幾個老人就常聚到家來,喝茶抽煙,扯東道西,說古聊今。
一次,茶喝得正酣,蔣家胡同的矬二奶奶就說起一件蹊蹺事,前日,村東頭建林家媳婦晚飯后去三嫂家借籮,路上聽見“咕啊——咕啊”的叫聲。她停下來仔細聽,是從東井方向傳過來的,像嬰兒夢里斷續地哭,很細很遠。她頓覺頭皮發麻,便快步回家,告訴建林。建林拿個手電來到東井,四下里照照,沒發現什么。往井里照照,也沒有動靜。那“咕啊——咕啊”的聲音,白天沒有,一到天擦黑安靜的時候就有,嚇得孩子和媳婦們不敢從那走呢。
“號貓子!”大奶奶笑笑,茶碗一蹾,肯定地說。
“不會是蛤蟆吧?”大伯母提著嗉子邊續水邊疑惑地問。
一直側耳聽著的奶奶吐口煙,幽幽地說:“怕是龍王哭呢!”
“噢。”大家便不再搭話。繼續喝著水,換個話題,聊起學堂家養的老母豬下了十一個小豬仔的事兒……
“東井是該淘了!”村會計老齊的父親齊老掐著手指頭算著。齊老是村里的宿儒,熟讀孔孟,能寫會算,通事明理。說話時,眼睛就從花鏡框上邊看著你。
土井每隔三四年是需要淘一次的。近段時間,人們確實感覺東井的水靠下了,打水時井繩得多續下半庹;水的回漲也沒原來快了,半天上不了一磚;打上的水也不似先前清亮……
淘井是老齊帶著四個男勞力干的。那時玉米剛剛竄出穗子,放眼望去,村外一片綠色的海洋。他們先用地排車將“195”(抽水機)拉過來在井口旁架好,把井里的水排進四周的玉米地里。井水抽干,將兩個梯子首尾相接捆到一塊,放到井底。兩個年齡稍大、辦事細致的青年,就輪流換上水鞋沿木梯下到井底清理淤泥雜物;另外兩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就在井口把盛了淤泥雜物的水桶拔上來倒掉。
井底的淤泥雜物并不多,每次也就小半桶:
第一桶上來,紫黑的淤泥里有一小截井繩頭;
第二桶上來,紫黑的淤泥里有兩塊磚頭、三塊瓦片;
第三桶上來,紫黑的淤泥里有一個擔杖鉤(大艷兒家的)和一個桶提把(鳳來家的);
……
“哎,一個活的,小心!”忽然,粗重的聲音從井底冒上來。
上面的人一聽,麻大利地往上拔。水桶輕飄飄的,兩把三把提上來。定睛一看,是一只蛤蟆,趴在桶底,頭尾四爪緊卡著桶壁,跟淤泥一個顏色,只有兩只眼睛亮亮的一眨一眨。老齊提過桶,瞅一瞅:“這就是東井的神啊!”邊說邊撩起井臺邊凹處還沒滲掉的清水,將蛤蟆清洗兩遍,然后小心地倒進玉米地里。“哇,這么大!”蛤蟆眨巴眨巴眼睛,在周圍孩子們的驚叫聲里緩緩地爬進玉米棵子里。
淤泥清理完,用清水沖刷井底時,還在泉眼處的磚縫里,意外地找到了司大嬸三年前掉進去的那枚銅簪子。
——這是東井的最后一次淘洗。
淘洗過后,東井并沒有太大變化。泉眼似乎沒有了以前汩汩的氣勢,細細弱弱的。淺淺的井水隱隱約約地能看見井底的磚。再后來,井水發渾不說,好像還有了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東井的水有味兒呢。”奶奶抿一口茶皺著眉說。
“東井的水有味兒呢。”齊老從眼鏡框上邊瞪著眼疑惑地說。
“東井的水有味兒呢。”棗花甩一甩大辮子說。
“東井的水有味兒呢!”一街人紛紛說。
……
第一個從“三號站”(給輸油管道加溫的)往家帶水的,是在化工廠上班的八子。每天一下班,他脫下工裝,換上干凈衣衫,騎上新“永久”自行車就去“三號站”。車后座一邊一個白塑料桶在鐵架子里“咚咚”地跳著,就像兩面歡快的鼓。不消兩刻鐘,“丁零丁零”一陣清脆的車鈴聲,八子滿載而歸,沉甸甸的兩桶水把自行車后座都墜得吱嘎吱嘎響。
漸漸地,村里的青壯年都像八子一樣去“三號站”倒騰水了。有自行車的用自行車,沒自行車的用小推車。用水多的人家干脆用地排車拉個大鐵桶,雖然慢,卻以一頂三、頂四,甚至五六。
早早晚晚,男男女女,大小車輛,來來回回,外出弄水吃倒也成了一道風景。
但風景再大,總也有罩不住的人。像明儒、維俊,他們去不了“三號站”,就繼續上東井。明儒也不再分早晚,跛著腳,擔著水,一路晃一路嘆息。維俊則走一段,就放下扁擔,歇歇腳,喘喘氣,然后罵一句:“王八蛋!”罵誰呢?不知道。
村長柳子決定異址打井,是在環保局來人從東井取走了兩瓶水之后一個多月時。西鄉來的打井隊在村西頭扎下盤子,機器一開,鉆桿呼呼地轉,僅三天,一口深水井就躥出清涼的水。井打成,上面蓋上水樓,井里下水泵,一推電把子,水便呼呼地跑進水樓里。水樓下邊靠路一面安著水龍頭,定時放水。負責放水的是柳子的老丈人維俊。
從此,人們不再去“三號站”,村西的水樓子便熱鬧起來,而東井則漸漸荒蕪在一片雜草中。可時間一長,村里人都說“水樓子的水不如東井的甜”。
這時候,奶奶已經去世快五年了。那把藍花嗉子一直靜靜地擺在方桌靠墻處,再沒動過。
——這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