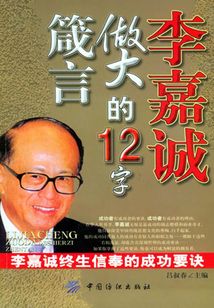
李嘉誠(chéng)做大的12字箴言
最新章節(jié)
- 第36章 “義”字箴言:仁義兩字值千金(5)
- 第35章 “義”字箴言:仁義兩字值千金(4)
- 第34章 “義”字箴言:仁義兩字值千金(3)
- 第33章 “義”字箴言:仁義兩字值千金(2)
- 第32章 “義”字箴言:仁義兩字值千金(1)
- 第31章 “合”字箴言:百人擊掌聲震天(4)
第1章 “韌”字箴言:在挫折中磨練自己(1)
李嘉誠(chéng)出生在書(shū)香世家,但他童年卻是不幸的:父親在其14歲時(shí)去世了,他只能退學(xué)打工掙錢,承擔(dān)起家庭的重?fù)?dān)——照顧母親撫養(yǎng)弟妹。正是年少的苦難磨練出他堅(jiān)強(qiáng)的意志,為他以后在商場(chǎng)上如魚(yú)得水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商場(chǎng)如戰(zhàn)場(chǎng)。創(chuàng)業(yè)后,李嘉誠(chéng)在市場(chǎng)激烈的競(jìng)爭(zhēng)壓力下,充分發(fā)揮“韌”勁,遇危難不倒,遇強(qiáng)手競(jìng)爭(zhēng)不弱,在商戰(zhàn)中屢戰(zhàn)屢勝。
1.苦難的年代,立志存高遠(yuǎn)
在中國(guó),人們歷來(lái)重視家傳,很多家庭都有“耕讀傳家”的訓(xùn)條。家庭對(duì)一個(gè)人的成功與否,舉足輕重。因?yàn)榧彝ゲ粌H給你生命,而且還給你做人的準(zhǔn)則。
李嘉誠(chéng)出生于一個(gè)書(shū)香世家,他從小就受到很好的家教和家傳熏陶。據(jù)李氏族譜載,明末清初,一世祖李明山,為避戰(zhàn)亂,舉家由福建莆田遷至潮州府海陽(yáng)縣(今潮州市)。家史再往前溯,李氏家族的祖先在中原。從一世祖李明山定居潮州,傳至李嘉誠(chéng)這一輩,正好第10世。
廣東潮汕地區(qū)的韓江之水碧波蕩漾,原來(lái)這就是李氏家族的祖屋。1928年7月29日(農(nóng)歷6月13日),李嘉誠(chéng)就出生于這座古宅里。
李氏家族乃書(shū)香世家,李嘉誠(chéng)的曾祖父李鵬萬(wàn),是清朝甄選的文官八貢之一。在李家門前還有一座3米高的碑臺(tái),上插貢旗,以記其事。李氏家族,世代教學(xué)治學(xué),聞名鄉(xiāng)里,深得四野鄉(xiāng)村人崇敬。
李嘉誠(chéng)的祖父李曉帆是清末秀才,也是飽學(xué)之士,無(wú)奈未能求得功名,只好在村中做一個(gè)教書(shū)先生。20世紀(jì)初,懦弱無(wú)能的清政府飽受西方列強(qiáng)欺凌,人民痛苦不堪。同時(shí),西方的先進(jìn)文明成果也逐漸滲透進(jìn)來(lái)。飽讀四書(shū)五經(jīng)的李曉帆夢(mèng)想教育救國(guó),他毅然送兒子李云章、李云梯東渡扶桑留學(xué),一個(gè)學(xué)商科,一個(gè)念師范,他們學(xué)成回國(guó)后,分別在潮州、汕頭從事教育工作。
李嘉誠(chéng)的父親李云經(jīng)排行老三,他秉承家訓(xùn),走的也是治學(xué)執(zhí)教之路。李云經(jīng)從小聰穎好學(xué),1912年(15歲)以優(yōu)異成績(jī)考入省立金山中學(xué),1917年畢業(yè)時(shí)成績(jī)名列全校第十名。無(wú)奈家境貧寒,無(wú)緣繼續(xù)求學(xué),中學(xué)畢業(yè)后,他便受蓮陽(yáng)懋德學(xué)校之聘,開(kāi)始了執(zhí)教生涯。
李云經(jīng)學(xué)識(shí)淵博,教學(xué)有方,深得上司的賞識(shí)及當(dāng)?shù)厝罕姷暮迷u(píng),在鄉(xiāng)鄰四野頗受尊重。1935年春,他被聘請(qǐng)為庵埠宏安小學(xué)校長(zhǎng)。李嘉誠(chéng)來(lái)到人世時(shí),世界已不太平。盡管此時(shí)北伐已取得輝煌的勝利,而中國(guó)依舊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huì)。世界經(jīng)濟(jì)經(jīng)歷長(zhǎng)久繁榮后,接踵而來(lái)的是世界性的經(jīng)濟(jì)大蕭條。
潮州偏安一隅,受時(shí)局的影響微乎其微。這使得李云經(jīng)得以在教書(shū)之余攜長(zhǎng)子嘉誠(chéng),流連于青山綠水間,享受安祥寧?kù)o的自然生活,生活清苦,卻也樂(lè)得逍遙自在。李云經(jīng)心底也不時(shí)泛起憂國(guó)憂民之心,他對(duì)兒子的最大期望,就是學(xué)有所成,報(bào)效國(guó)家和家鄉(xiāng)。
李嘉誠(chéng)不負(fù)乃父厚望,他聰穎好學(xué)。3歲就能詠《三字經(jīng)》,《千家詩(shī)》等。詠詩(shī)誦文,是李嘉誠(chéng)童稚時(shí)代的最佳娛樂(lè)。“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xí)相遠(yuǎn)。”李嘉誠(chéng)正是在這些童蒙讀物中,最早接受了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
深厚的家學(xué)培養(yǎng)了李嘉誠(chéng)許多優(yōu)秀品德。不可否認(rèn),這些優(yōu)秀品德對(duì)他后來(lái)的發(fā)展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少年時(shí)代所受的教育如何,有時(shí)的確能影響一個(gè)人的一生。
李嘉誠(chéng)的父親重義輕利,安貧樂(lè)道,熱衷于教育事業(yè),視教育為強(qiáng)國(guó)利民之本。
李嘉誠(chéng)也深受父親的熏陶,一言一行皆按父親要求的去做,更重要的是他酷愛(ài)讀書(shū)很有上進(jìn)心,深得李云經(jīng)的喜愛(ài)。
那時(shí)候,李嘉誠(chéng)的童年夢(mèng)想是像父親一樣,做一名桃李滿天下博學(xué)多識(shí)的教師。
李嘉誠(chéng)5歲那年在父親的引導(dǎo)下,祭拜孔圣人,進(jìn)了潮州北門街觀海寺小學(xué)念書(shū)。學(xué)堂是觀海寺的廟堂,誦經(jīng)聲與讀書(shū)聲此起彼伏。此時(shí),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已經(jīng)歷10多年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正在經(jīng)受工業(yè)革命的洗禮。而這里學(xué)堂的讀書(shū)聲與寺廟的誦經(jīng)聲一樣亙古不變,“之乎者也”構(gòu)成授課的主要內(nèi)容,時(shí)光恍然凝固。
課堂的墻壁上,貼著一副醒目的對(duì)聯(lián):
“風(fēng)聲雨聲讀書(shū)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guó)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
李嘉誠(chéng)對(duì)先生教授的詩(shī)文,自幼在家里早已爛熟于胸,他有著極強(qiáng)的求知欲,早已不滿足于老師講授的那些東西。他對(duì)陌生的詩(shī)文抱有濃厚的興趣。尤其對(duì)那些千古流傳的愛(ài)國(guó)詩(shī)篇,他雖然似懂非懂,竟也能沉醉其中。
李氏家族的古宅,有一間珍藏圖書(shū)的藏書(shū)閣。每日放學(xué)回家,李嘉誠(chéng)便泡在藏書(shū)閣,孜孜不倦地閱讀詩(shī)文。他涉獵甚廣,《詩(shī)經(jīng)》、《論語(yǔ)》、《離騷》、唐詩(shī)、宋詞、元曲……他尤其喜歡文天祥、陸游、岳飛、辛棄疾等人的詩(shī)詞,漸漸地,他也能體味出其間的豪情與憂憤。
在書(shū)房的小小天地里,李嘉誠(chéng)常做著狀元及第、衣錦還鄉(xiāng)的美夢(mèng),他對(duì)那些精忠報(bào)國(guó)之士尤其敬佩不已。
年少的李嘉誠(chéng),將父親奉為自己的楷模。他夢(mèng)想著自己能夠擁有父親那樣廣博的學(xué)識(shí),也像父親那樣受人尊敬。因而,他讀書(shū)非常刻苦自覺(jué),經(jīng)常在書(shū)房里點(diǎn)煤油燈讀書(shū),很晚很晚都不睡覺(jué)。
待父親回家來(lái),他便纏著父親給他講解不懂的詩(shī)文,歷史背景、人文故事等。李嘉誠(chéng)讀書(shū)的悟性與勤勉,深得父親的嘉許。1934年,李云經(jīng)受聘擔(dān)任宏安小學(xué)校長(zhǎng)不久,李嘉誠(chéng)便轉(zhuǎn)入宏安小學(xué)就讀,從此父子倆有機(jī)會(huì)天天相聚。
父親時(shí)常向他講起日本侵占東三省的暴行。隨著父親娓娓的話語(yǔ)和憂郁的神色,李嘉誠(chéng)仿佛看到憂國(guó)憂民的屈原,仰天吟唱“路漫漫其修遠(yuǎn)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壯懷激烈的岳飛,仰天長(zhǎng)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還有位卑不敢忘憂國(guó)的杜甫,在寒冷的秋夜,對(duì)著自家的破茅屋,高歌“安得廣廈千萬(wàn)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李嘉誠(chéng)似懂非懂,但有一個(gè)理念卻分外清晰:勤勉苦讀,出人頭地,報(bào)國(guó)為民。
時(shí)局動(dòng)蕩,生活清貧,未能建功立業(yè)的李云經(jīng),眼見(jiàn)兒子如此懂事聰穎,便把厚望寄托于兒子身上。李嘉誠(chéng)優(yōu)異的學(xué)業(yè),是郁郁不得志的父親最大的慰藉。
少年時(shí)代接受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為李嘉誠(chéng)后來(lái)的發(fā)展與輝煌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他后來(lái)雖然沒(méi)有遵循兒時(shí)的志向,走求學(xué)治學(xué)之路,但小時(shí)候所受國(guó)學(xué)家傳的熏陶,卻培育了李嘉誠(chéng)“達(dá)則兼濟(jì)天下,窮則獨(dú)善其身”的大志向。在以后的歲月中,李嘉誠(chéng)雖歷經(jīng)坷坎,飽嘗貧窮之苦,但他自強(qiáng)不息,不甘沉淪,可以說(shuō)完全得益于他早年立下的志向。在人的一生中,堅(jiān)定的志向是最重要的,這等于為自己定下了一個(gè)前進(jìn)的方向。如果沒(méi)有方向,走哪算哪,很難到達(dá)理想境界。而且,立志宜高遠(yuǎn),這樣,在任何時(shí)候都能保持自尊自愛(ài):即使身處貧賤也不會(huì)自輕自賤,而力求改善不利處境,以獲得受人承認(rèn)的成就和受人尊重的地位。如此有意識(shí)地、持之不懈的努力,怎么會(huì)沒(méi)有作為呢?
2.寄人籬下,接受生活的挑戰(zhàn)
如果一個(gè)人一帆風(fēng)順的話,很可能會(huì)碌碌無(wú)為,相反,如果一個(gè)人遭遇苦難,往往會(huì)激發(fā)出他的斗志,然后選擇勇往直前。
李嘉誠(chéng)年少時(shí)痛離失所,寄人籬下,生活的苦難磨礪了他的思想,更磨練出了他鋼鐵般的意志。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fā),中日戰(zhàn)爭(zhēng)全面開(kāi)始,日軍迅速侵占了中國(guó)的半壁河山。
1939年6月,潮汕淪陷,日寇橫行,寧?kù)o而美麗的潮州城變成了一片廢墟。縣教育科宣布所有學(xué)校停課。李云經(jīng)失業(yè),教育救國(guó)的愿望遭到沉重打擊。
太陽(yáng)旗在潮洲城頭四處飄揚(yáng),四散逃難的人絡(luò)繹不絕。
素有愛(ài)國(guó)之心的李云經(jīng)經(jīng)常與城里的知識(shí)分子相聚在一起,密謀抗日大計(jì),其間也有不少青年志士前往抗戰(zhàn)前線或加入了敵后游擊隊(duì)。
李云經(jīng)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兒女,終于未能邁出這一步。他常常在心中自責(zé),感到萬(wàn)分愧疚。
1940年初,李云經(jīng)攜妻帶子逃到澄海縣隆都松坑鄉(xiāng),寄住在姨親家。不久,又輾轉(zhuǎn)逃靠在后溝小學(xué)任教的胞弟李奕家。兄弟見(jiàn)面,抱頭痛哭。李云經(jīng)痛心的說(shuō):“我逃荒失業(yè),一家人生活無(wú)著落,加上染瘧疾,沒(méi)醫(yī)沒(méi)藥,禍不單行,苦不堪言。”
這一年,李嘉誠(chéng)的祖母因受驚嚇貧病而離開(kāi)了人世。李嘉誠(chéng)的伯父?jìng)兌荚谒l(xiāng)執(zhí)教,潮汕淪陷,日寇橫行,他們沒(méi)有能趕回來(lái)奔喪。只有李云經(jīng)、李奕兩兄弟全力草草為母親辦了葬禮。
李云經(jīng)失業(yè)一年后,仍未找到教職。他不會(huì)體力勞動(dòng),也不會(huì)做生意,除了感嘆“百無(wú)一用是書(shū)生”外,毫無(wú)辦法。胞弟李奕薪水微薄,李云經(jīng)不忍心長(zhǎng)期受其接濟(jì),不禁心焦如焚。李云經(jīng)與妻子莊碧琴商議多日,決定前往香港投靠妻弟莊靜庵。莊靜庵是香港的富商。此時(shí),內(nèi)地戰(zhàn)火紛飛,兵荒馬亂,香港卻是太平盛世,一派祥和,成為戰(zhàn)時(shí)內(nèi)地人所向往的避難所。
李奕贊同胞兄的計(jì)劃,臨行的前一天,兄弟倆帶家小到山崗祭奠老母。當(dāng)晚,兄弟倆伴著昏黃的油燈小酌。談到目前時(shí)局的艱難和未來(lái)前途的不測(cè),兄弟倆長(zhǎng)吁短嘆,愴然涕下。
小小年紀(jì)的李嘉誠(chéng),雖然常從書(shū)中讀到有關(guān)國(guó)破家亡的描述,但沒(méi)想到此種凄慘景象這么快就降臨到了自己的頭上。
美好的童年生活徹底結(jié)束了。他默默地看著父母愁苦哀傷的面容,心中充滿了困惑與茫然。
這一刻,永遠(yuǎn)印在了他的腦海里。
1940年冬天,李嘉誠(chéng)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隨父母踏上艱難的旅程。
李氏一家冒著隨時(shí)可能被殺的危險(xiǎn),躲著不時(shí)而來(lái)的流彈,爬過(guò)道道封鎖線,步行十幾天,一路風(fēng)餐露宿,歷經(jīng)千辛萬(wàn)苦,終于來(lái)到目的地香港。
李云經(jīng)的妻弟莊靜庵,幼年在潮州鄉(xiāng)間讀私塾,小學(xué)畢業(yè)后,像眾多的潮州人一樣離家外出闖蕩。1935年,27歲的莊靜庵來(lái)香港涉足鐘表業(yè),從最簡(jiǎn)單的布質(zhì)、皮質(zhì)表帶做起,步步做大。他的產(chǎn)品質(zhì)優(yōu)價(jià)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費(fèi)者歡迎。后來(lái)開(kāi)始兼營(yíng)鐘表貿(mào)易,購(gòu)入瑞士鐘表,再銷往東南亞各國(guó)。
李嘉誠(chéng)一家到來(lái)時(shí),莊靜庵已被潮人視為成功人士。他騰出房間讓李氏一家住下,設(shè)家宴為他們洗塵。席間,他仔細(xì)詢問(wèn)了家鄉(xiāng)的近況,然后為姐夫介紹了香港現(xiàn)狀,勸李云經(jīng)不要著急,先安心休息,逛逛港街,再慢慢找工作。
莊靜庵未提起讓姐夫李云經(jīng)上他的公司做職員,這是李云經(jīng)夫婦始料不及的。這也許是莊靜庵在商言商,絕不把公司人事與親戚關(guān)系攪和在一起的緣故吧。
李云經(jīng)長(zhǎng)期生活在傳統(tǒng)倫理氛圍中,雖然明白這是有頭腦的商家通常的做法,但在感情上卻不容易接受。莊碧琴想去質(zhì)問(wèn)弟弟,但被李云經(jīng)制止。他不想給妻弟添太多的麻煩,來(lái)香港投靠妻弟,已是萬(wàn)不得已。而且,他畢竟是讀書(shū)人,有著傳統(tǒng)儒士慣有的清高,不愿輕易“為五斗米折腰”。
莊靜庵并不滿足于眼下的業(yè)績(jī),他要不斷地?cái)U(kuò)大經(jīng)營(yíng)規(guī)模,資金分外緊張,家庭生活僅屬小康。姐姐一家的到來(lái)無(wú)疑會(huì)成為莊家的負(fù)擔(dān)。
他在事業(yè)上更是異常忙碌,沒(méi)日沒(méi)夜,每天都要工作10多個(gè)小時(shí)。初時(shí),他還經(jīng)常來(lái)看望姐夫一家人,問(wèn)寒問(wèn)暖。后來(lái),他來(lái)的次數(shù)愈來(lái)愈少,有時(shí),幾天都不見(jiàn)他的人影。
莊靜庵對(duì)自己家人也是如此,他沒(méi)時(shí)間也沒(méi)有閑情逸致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lè)。
所謂“商人重利輕別離”乃時(shí)勢(shì)必然,并非本性如此。是商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沖淡了家庭氣氛及人際關(guān)系。李嘉誠(chéng)稍大時(shí),莊靜庵深有感觸道:“香港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激烈,不敢松懈懶怠半分,若不如此,即便是萬(wàn)貫家財(cái),也會(huì)輸?shù)靡回毴缦础!鼻f靜庵如果講情,對(duì)李家照顧得無(wú)微不至的話,日后李嘉誠(chéng)必然產(chǎn)生依賴思想,從而缺乏奮斗精神,因?yàn)槿耸且环N好逸惡勞的動(dòng)物,在很多情況下,奮斗是因?yàn)榄h(huán)境所迫,只有很少情況下是因?qū)κ聵I(yè)真心熱愛(ài)所致。所以,從結(jié)果來(lái)看,莊靜庵的“冷漠”,反倒成全了李嘉誠(chéng)的一生。
講人情并非壞事,但人情也有副作用,用得地方不當(dāng),不但對(duì)受者無(wú)益,反而有害。因此,濫施人情肯定是一種缺點(diǎn),就像醫(yī)生濫開(kāi)補(bǔ)藥一樣,不值得提倡。
好在除莊靜庵這門至親,李云經(jīng)夫婦在香港還有不少親友同鄉(xiāng)。他們也曾來(lái)看望李家一兩次,此后便杏無(wú)音信。潮人在異國(guó)他鄉(xiāng),以團(tuán)結(jié)互助而著稱,但這主要是在商場(chǎng)合作上。純粹的人情方面的“幫襯”是有限的,潮籍富翁,無(wú)一不是靠自己的勤儉毅力搏命搏出來(lái)的。
李嘉誠(chéng)回首往事,如是描繪他少年時(shí)的心態(tài):
“小時(shí)候,我的家境雖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文化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讀書(shū)人。抗日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我隨先父來(lái)到香港,舉目看到的都是世態(tài)炎涼、人情冷暖,就感到這個(gè)世界原來(lái)是這樣的。因此在我的心里產(chǎn)生了很多感想,就這樣,童年時(shí)五彩繽紛的夢(mèng)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其實(shí),少年李嘉誠(chéng),尊敬并崇拜舅父莊靜庵。舅父不像他的先父和叔伯,總是引經(jīng)據(jù)典地大談倫理道德,舅父是個(gè)實(shí)用主義者,是個(gè)不愛(ài)清談的搏命猛人。
舅父白手起家的創(chuàng)業(yè)經(jīng)歷,也給李嘉誠(chéng)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覺(jué)得這種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極有挑戰(zhàn)性,值得學(xué)習(xí)。于是堅(jiān)定了李嘉誠(chéng)日后創(chuàng)業(yè)的志向和決心。
3.適應(yīng)環(huán)境,堅(jiān)定信念,學(xué)做港人
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能力是成大事者必備的能力。處在新環(huán)境中無(wú)所適從的人是難有作為,因?yàn)闀r(shí)勢(shì)多變遷,計(jì)劃不如變化快,只有適應(yīng)新的環(huán)境才能征服新的世界。在人生中,只有善于適應(yīng)環(huán)境并能營(yíng)造新環(huán)境的人,才是真正的偉人。
李嘉誠(chéng)的父親李云經(jīng)是個(gè)很堅(jiān)強(qiáng)的人,不愿仰賴他人生活,因此,他跟莊靜庵談了想出去找工作的打算。
莊靜庵極表贊成說(shuō):“香港時(shí)時(shí)處處都有發(fā)財(cái)機(jī)會(huì),就怕人懶眼花,錯(cuò)過(guò)機(jī)會(huì)。潮州人最能吃苦,做生意個(gè)個(gè)都不錯(cuò)。我認(rèn)識(shí)好些目不識(shí)丁的從潮州鄉(xiāng)下來(lái)的種田佬,幾年后,都發(fā)達(dá)了起來(lái)。”
李云經(jīng)第二天就出去找工作,然而卻四處碰壁。他心中不禁泛起一股失落感。在家鄉(xiāng),他是受人尊敬的小學(xué)校長(zhǎng),他的淵博學(xué)識(shí),使那么多的財(cái)主富商黯然失色。
來(lái)到香港這個(gè)商業(yè)社會(huì)后,一切都顛倒了過(guò)來(lái),拜金主義盛行,錢財(cái)成為衡量人生價(jià)值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
這里再也沒(méi)有人向李云經(jīng)請(qǐng)教古書(shū)上的問(wèn)題,更沒(méi)有人夸獎(jiǎng)兒子李嘉誠(chéng)吟誦詩(shī)文的出眾稟賦。不惑之年的李云經(jīng),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李云經(jīng)雖與香港的商業(yè)文化格格不入,但在環(huán)境的逼迫下,他也不得不努力使自己與環(huán)境融合。
李云經(jīng)終于找到了工作,是在一家潮商開(kāi)的公司做小職員。其時(shí),抗日戰(zhàn)爭(zhēng)進(jìn)入最艱苦階段,香港商會(huì)號(hào)召商人市民募捐,用以購(gòu)置飛機(jī)武器支援中國(guó)軍隊(duì)。李云經(jīng)捐出了積攢多日的數(shù)枚港幣,而那些富商們,捐出的卻是數(shù)千上萬(wàn)港元。見(jiàn)此情景,喊了半輩子教育救國(guó)的李云經(jīng),對(duì)友人感嘆道:“實(shí)業(yè)亦可救國(gu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