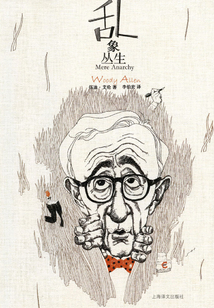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犯錯(cuò)是人之常情,升空是神之法力
氣喘吁吁之中,我的生活,像書中的花邊插圖,連成惆悵的一串,從眼前閃過。幾個(gè)月前,我發(fā)現(xiàn),自己快給海嘯般的垃圾郵件淹沒了。每天早上,吃完熏魚,這些信就從門上的信孔里傾瀉而入。多虧我們的清潔女工、有瓦格納歌劇味道的格倫黛,聽到一大堆畫展邀請(qǐng)函、慈善催命信,還有我贏的各類大獎(jiǎng)通知底下傳來低沉的嗓音,才借助我們的吸蟲器,把我解救出來。我正在認(rèn)認(rèn)真真按照字母順序,把新來的郵件送進(jìn)碎紙機(jī),忽見到,在兜售喂鳥籠子,每月訂購干果蜜餞的林林總總商品目錄中,有一本不請(qǐng)自到的小雜志,名字醒目,叫“魔力組合”,顯然是面向新時(shí)代市場的。里面文章講的,從水晶的法力,到全身心理療,到通靈震顫法,五花八門,還介紹養(yǎng)蓄靈氣的方法、愛情與壓力的關(guān)系,以及前往何處,填寫哪些表格,才能重獲新生的詳盡資料。這些廣告,看上去措辭謹(jǐn)慎,并不像打假偵緝隊(duì)抓獲的騙子編造的那樣不合情理,里邊賣的有“充鐵理療器”、“水旋加能器”,另有一種產(chǎn)品叫“草藥豐胸”,專門為了讓富態(tài)婦人的兩枚香瓜更加豐滿。其中,還充斥了不少算命師的忠言,像“通靈”算命師,她頗有遠(yuǎn)見,可還要同稱作“七星合一的天使群落”反復(fù)核實(shí);或者赤裸全身、接受洗禮的女孩“莎琳娜”,她能夠“理順你的能量,喚醒你的DNA,招財(cái)進(jìn)寶”。當(dāng)然,靈魂深處的探訪之旅結(jié)束時(shí),付上一小筆報(bào)酬,貼補(bǔ)郵票費(fèi)用,或是,這些師傅在另一維度生命中可能支出的其他花銷,也不為過。然而,這里最讓人吃驚的人物,要算是哈氏地球人升天運(yùn)動(dòng)創(chuàng)始人和神圣領(lǐng)袖。這位自封的女神,眾信徒叫她佳布麗·哈瑟,廣告寫手稱她“以人的形體,顯現(xiàn)神靈的全能”。這位偶像來自西岸,她告訴我們:“因果報(bào)應(yīng)正在加速實(shí)現(xiàn)……地球進(jìn)入了精神上的冬季,將持續(xù)四十二萬六千個(gè)地球年。”考慮到漫長的冬天有多么難挨,哈女士創(chuàng)辦了一個(gè)運(yùn)動(dòng),引導(dǎo)人們升上“更高的頻率層次”,我估摸著,到了那個(gè)層次,人們可以多出出門,打打高爾夫球了。
“升到半空、瞬間易位、全知全能、隱形逍遁等,都會(huì)成為人們?nèi)粘>邆涞哪芰Α保@位生意人大夸海口,招攬說,“升上高頻率層次,可望見低頻率的人;而低頻率的人,卻瞧不見高層次的人。”
某位叫作“星月神女”的佳人,給予了熱情推薦。不過,要是上手術(shù)臺(tái)之前告訴我,我的大腦手術(shù)醫(yī)生叫此姓名;或是登機(jī)之前告訴我,飛機(jī)駕駛員叫這個(gè)名字,我會(huì)驚愕得沒完。若做哈女士運(yùn)動(dòng)的追隨者,就必須經(jīng)歷“令人羞辱的過程”,這是每日化解自我、調(diào)高頻率的活動(dòng)中的一項(xiàng)。拿現(xiàn)金付費(fèi),令人不屑。不過,要是表現(xiàn)得謙卑忠孝,做點(diǎn)有益的活計(jì),便可以賺得一張床位,一盤有機(jī)綠豆,與此同時(shí),也增加些意識(shí),或是失去些意識(shí)。
我之所以提到所有這些,是因?yàn)楫?dāng)天稍后,我在哈馬歇爾·施勒默爾直銷產(chǎn)品專門店里猶猶豫豫,浪費(fèi)時(shí)光,不知是買鴨汁壓榨機(jī),還是買世界上最精致的手提式斷頭臺(tái);出來時(shí),正像泰坦尼克號(hào)碰上老冰山一樣,碰上了大學(xué)里認(rèn)識(shí)的馬克斯·恩多菲恩。他已經(jīng)中年發(fā)福,眼睛如同鱈魚,禿頂上的假發(fā)擺弄得中間鼓起,足能以假亂真,看似高背頭式樣。他使勁握著我的手,開始講述最近遇到的好運(yùn)氣。
“怎么說呢?小伙子,我發(fā)了。我聯(lián)系上了內(nèi)心深處的精神自我。從此以后,我肥了。”
“愿聞其詳,”我說道,第一次注意到他一身定做的漂亮行頭,還有小拇指上像瘤子一樣大的戒指。
“我想,我真不應(yīng)該同一個(gè)低頻率上的人嘮叨,但既然我們老早時(shí)候就——”
“頻率?”
“我是說層次。我們?cè)诟咭綦A上的人接受了訓(xùn)導(dǎo),不要在你這等凡俗的類人猿身上浪費(fèi)健康的離子——你別介意。不是說我們不研究,不了解低等形態(tài)——這得多虧列文虎克[1],你懂我的意思嗎?”突然,恩多菲恩露出老鷹抓獵物般的本能,扭頭盯上一位兩腿修長、穿著超級(jí)超短裙、正滿世界找出租車的金發(fā)美女。
“神靈顯現(xiàn),可卻撅著小嘴,”他說,口水如泉涌。
“一準(zhǔn)是個(gè)雜志中間插頁上的美女,”我叫了起來,忽然有中暑的感覺,“看她那透明的襯衣。”
“看著,”恩多菲恩說著,深吸了一口氣,開始上升,在哈馬歇爾·施勒默爾店前,升離地面一尺。我和那位七月最佳小姐很是驚訝。這位甜甜的美眉一面四處找電線,一面把香軀湊了過來。
“嘿,你怎么升起來的?”她嬌甜地問。
“拿著,這是我的地址。”恩多菲恩說,“今晚八點(diǎn)以后我在家。來串個(gè)門。我馬上就能讓你升離地面。”
“我?guī)考t酒來。”她輕柔地說,把他們相會(huì)的資料塞進(jìn)乳溝,搖擺身姿走開了。恩多菲恩也慢慢降回地面。
“怎么回事,”我說,“你成了烏丹尼[2]?”
“噢,”他嘆口氣,擺出一副好心腸,“既然我屈尊在跟一個(gè)小蟲子說話,那就把實(shí)話告訴你吧。咱們先到大舞臺(tái)食品店,消滅些點(diǎn)心,我來接受你的覲見。”說著,他就呼的一聲,不見了。我就像基什姐妹[3]一樣,倒抽氣,張大口,用手捂住嘴。過了幾秒鐘,他又出現(xiàn)了,有點(diǎn)悔悟。
“對(duì)不起,我忘了,你們低層人不會(huì)隱身,不會(huì)易位。是我不對(duì)。咱們走。”我不知是醒是夢(mèng),還在掐著自己時(shí),恩多菲恩已經(jīng)講上了。
“好吧,”他說,“鏡頭回放到六個(gè)月前。恩多菲恩夫人的小子馬克斯,因?yàn)橐贿B串的艱辛磨難,情緒波動(dòng),要是再加上我把貝雷帽放錯(cuò)了地方,情況簡直比約伯還要苦難深重。先說臺(tái)灣來的那個(gè)好運(yùn)餅干,我教其解剖水力學(xué),他卻為了個(gè)餡餅店的學(xué)徒拋棄了我。然后,我因?yàn)榘盐业慕荼惯M(jìn)了基督教科學(xué)派[4]閱覽室,就聽著許多總統(tǒng)安葬時(shí)奏的曲子,吃上了官司。這還沒完,我前次婚姻慘劇留下的一個(gè)兒子,放棄賺錢的法律行業(yè),成了一名口技演員。所以,我心灰意冷,在城里竄來竄去,想找到活著的理由,找個(gè)精神支柱。這不,忽然間,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我在最新一期的《顫動(dòng)畫報(bào)》上看到一則廣告。一個(gè)類似水療館的地方,能把你的晦氣吸走,把你提升到高頻率,讓你終于能像浮士德一樣,掌控大自然。通常,我都很精明老到,不會(huì)給這類招數(shù)騙了。可我探明白了,那里的首席執(zhí)政官,確實(shí)是個(gè)肉身顯現(xiàn)的女神。我估摸著,這有什么不好呢?而且,還不收費(fèi)。他們不要現(xiàn)錢。他們的做法基本是某種奴隸制的變體,但作為回報(bào),你能得到這些水晶,能獲得法力,還有,你能捎帶上所有的圣約翰草[5]。噢,我還沒說,她會(huì)羞辱你。可這是療程的一部分。所以,她的奴仆們會(huì)把我的床弄亂,趁我不注意,把一條驢尾巴粘在我褲子后面。確實(shí),有一段時(shí)間,我成了笑料。但是,跟你說吧,我的自我意識(shí)化解了。忽然間,我明白過來,我回到了前世。先是個(gè)簡簡單單的鎮(zhèn)長,后是老盧卡斯·克拉納赫[6]……噢,我忘了,也許是小盧卡斯。不管他,再往后,我醒來時(shí),正躺在硬木板上,我的頻率上了高層。我后腦勺上罩上了光環(huán)。我成了全知全能。我是說,我馬上就在貝爾蒙賽馬場連贏兩次;沒出一個(gè)星期,我在拉斯維加斯的貝拉吉奧大賭場一出現(xiàn),就吸引一大堆人。要是拿不定哪匹賽馬,或是打撲克牌吃不準(zhǔn)是進(jìn)牌還是持牌不動(dòng),就有那么一群天使給我出主意。我是說,并不是誰長了翅膀,由神秘物質(zhì)組成,就不能賭馬使詐。數(shù)數(shù)這一沓。”
恩多菲恩從每個(gè)口袋里都掏出好幾沓千元面值的鈔票。
“噢,噢,抱歉,”他說,忙著尋找他掏出大把綠票子時(shí),從衣兜里掉出來的一些紅寶石。
“這些服務(wù),她不要任何報(bào)酬嗎?”我問,心里就像老鷹長了翅膀。
“呵,你呀,塵世凡人都這么問。人家是大派頭。”
那天夜里,盡管家中女人胡亂詛咒,還給施萊克父子律師所打電話,查詢我們的婚前協(xié)議是否包括了突然患上早發(fā)型癡呆,但我還是朝著西邊,飛往“莊嚴(yán)升天寺”,在那里,安居著一個(gè)圣靈,好萊塢弗雷德里克內(nèi)衣專賣店里一個(gè)叫“熱浪星系”的夢(mèng)幻佳人。她把我迎進(jìn)圣殿。這座圣殿占據(jù)了她好大的地方,周圍是荒棄的農(nóng)場,怪怪的,有點(diǎn)像曼森[7]一伙的斯班牧場。她放下磨指甲的小銼,坐到沙發(fā)上。
“歇一會(huì)兒,親愛的,”她對(duì)我說。那口氣,不大像瑪莎·格雷厄姆[8],倒像艾里斯·阿德里安[9]。“就是說,你想跟靈魂深處搭上線。”
“是。我想讓我的頻率調(diào)高點(diǎn),能升高,易位,隱形,還想全知全能,足以事先測到紐約州毫無規(guī)律的彩票中獎(jiǎng)號(hào)碼。”
“你是做什么事的?”她詢問。對(duì)她這樣有君王之風(fēng)的神明來說,這可問得無知無能,有點(diǎn)奇怪。
“在蠟像館守夜,”我回答,“但不像說的那樣有充實(shí)感。”
她轉(zhuǎn)向圍在身邊、手持棕櫚葉蒲扇、給她扇涼的努比亞人[10],朝其中一個(gè)說:“你說呢,小伙子?看起來,他做個(gè)勤雜還不錯(cuò)。也許負(fù)責(zé)糞池吧。”
“謝謝,”我一邊說,一邊跪下來,臉貼著地面,十分謙卑。
“好啦,”她拍拍手。她的忠實(shí)奴仆們從簾子后面,排成隊(duì)形,急匆匆走出來。“給他一個(gè)盛米飯的碗,把頭剃了。要是沒有空床,就讓他跟雞群睡在一起。”
“悉聽尊命,”我細(xì)聲細(xì)語地說,不敢直視,生怕看中暑小姐一眼,就會(huì)打擾她剛剛開始的填字游戲。就這樣,我給人匆忙帶走了,隱隱擔(dān)心身上會(huì)不會(huì)給烙鐵烙上印記。
隨后的日子里,就我所見,大院里充斥了各色各樣的落魄鬼:膽小如鼠的家伙、喜歡裸體的家伙、舉手投足都要模仿某顆行星的女演員、肥胖的家伙、參與某種動(dòng)物標(biāo)本丑事的人、拒不認(rèn)命的侏儒等等。這些人,都爭著上升到高檔次,同時(shí)整日勞作,好似大腦給切除了的樣子,對(duì)高高在上的女神服帖極了。有時(shí),能看到她在大院里跳舞,像是伊莎多拉·鄧肯[11],或抽著長長的煙袋,笑得像那匹賽馬海洋餅干[12]。大院的薩滿酋長曾做過保安,我覺得,在某部關(guān)于《梅甘法》[13]的紀(jì)錄影片中看到過他。為了得到他的恩準(zhǔn),喘上幾口氣,信徒們每天要干十二到十六個(gè)小時(shí)的活兒,收獲水果和蔬菜,供工作人員享用;或是制作各種商品,如春宮撲克、掛在汽車后視鏡上的塑膠小骰子,以及餐館清理桌面的小刮板。我除了負(fù)責(zé)下水道之外,作為勤雜,還要撿拾地上扔棄的長條甜餅包裝紙以及遍地的煙頭。每天的飲食,主要是苜蓿菜籽、豆面和離子水,有點(diǎn)難于適應(yīng);但是,一個(gè)不大虔誠的僧人得了十元錢,他有個(gè)兄弟在附近開飯館,所以,不時(shí)能吃點(diǎn)魚肉泥。這里面,紀(jì)律松散,卻期待人們要負(fù)起責(zé)任,雖然不守日常飲食規(guī)定,干活偷懶,可能招致鞭打,或是給綁到外面的電話柱子上。在消除自我的每日禮數(shù)中,一個(gè)羞辱接著一個(gè)羞辱。最后,傳來了旨令,要我同一個(gè)酷似比爾·帕塞[14]的印度教女祭司上床。我于是決定,該顛兒了。漆黑的夜色中,我匍匐在地上,爬過鐵絲網(wǎng),招呼上了最后一班前往紐約上西城的747飛機(jī)。
“原來如此,”我太太說,擺出對(duì)早衰患者的雍容大度,“你是隱形易位回到這兒的?我看到你衣領(lǐng)上還吊著大陸航空公司的餐巾?”
“我待的時(shí)間不夠長,”我搪塞過去,對(duì)她拐彎抹角的挖苦憤憤然,“不過,我付出了一定的辛苦,學(xué)得了這種絕技。”說著,我就升離地面六寸,在半空晃著,而她的嘴,張得就如同電影《大白鯊》中的鯊魚嘴。
“你們這些低頻率的萬事通,根本不懂。”我沖她說,沒有掩飾自己的得意,但也原諒了她。女人發(fā)出一聲尖叫,好像是敵機(jī)要來空襲,讓孩子們趕緊躲開這場噩夢(mèng)般的巫術(shù)表演。此時(shí),我才開始明白,我不會(huì)降下來。無論怎么費(fèi)勁,就是不成。屋里如同《歌劇院之夜》中的那個(gè)大廳,成了一個(gè)魔窟,孩子們狂呼亂叫,鄰居們以為是出了血案,跑過來救人。這當(dāng)兒,我使盡力氣要落下來,擠出笑容,四肢亂舞,頗似啞劇。最后,賢內(nèi)助奮起行動(dòng),僅用普通物理學(xué)原理,就掌控了亂局:她從鄰居那里拿了個(gè)滑雪板,朝我頭頂使勁砸將下來,把我狠狠地打回地面。
后來聽說,恩多菲恩隱遁了,再也沒有重現(xiàn)。至于“熱浪星系”和她的“莊嚴(yán)升天寺”,人們傳聞,讓財(cái)政部的警員給關(guān)了,都轉(zhuǎn)世或是轉(zhuǎn)進(jìn)監(jiān)獄了。至于我嘛,再也沒能升離地面,或猜中賽馬場上哪怕一匹跑進(jìn)前五名的賽馬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