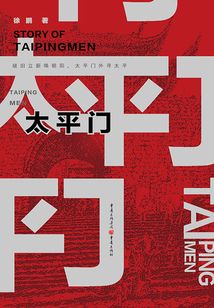
太平門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破廟相逢
亂世偶遇
“起來起來,老叫花子挪挪地兒!”
“老叫花子?”這個聲音對于辛佑國而言,就像是從另外一個世界隔空傳過來的,空曠而縹緲。他很想起身離開,但是卻只是困難地扭了扭頭,瞟了一眼。
他囁嚅著,終究沒有說出話來。因為他已經躺在這座破廟里至少有三天沒吃任何東西了,已餓得前胸貼著后背。
靠著一絲余光,辛佑國看到踢他的是個精瘦的年輕人,衣服雖舊但還算干凈,渾身的肌肉緊繃著,像是隨時都能跟別人干一架。這個年輕人正想繼續沖著地上的辛佑國發火,卻被旁邊的中年男子伸手攔住:“大虎!莫要生事,不要管他,快去撿柴。”
渾身沒有力氣的辛佑國懶得挪動地方,只能繼續裝睡,不大一會兒,他聞到了一股食物的香味,他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發現一個長相清秀的小男孩蹲在他面前,他手里拿著一個鍋盔遞給他。鍋盔顯然是剛剛烤過的,外皮焦脆,內里松香,對于好久沒進食的辛佑國而言,這簡直是天大的美味。他趕忙起身接過,恨不得一口吃下去喂飽身體里饑餓的巨獸,但是嘴巴和舌頭卻不聽使喚,有幾次甚至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
看到這一幕,剛才制止大虎的中年人遞給他一個壺。小男孩剛要阻止,誰知辛佑國接過根本沒看,仰頭就喝,一大口進肚后才發現是酒。
那酒還帶著沒過濾掉的雜質,粗咧咧的就順著喉嚨奔涌進肚,帶來了一股回涌的灼熱感。他也只是皺了下眉頭,發出了響亮的咂嘴聲。
肚子里暖了后,他開始回憶上一頓吃的是什么。好像是跟著上一個逃難戲班趕到這個破廟的時候,有人在后山打到了幾只野兔,戲班中有會做的人把兔子懸著剝了皮,斬丁加了辣子花椒炒熟,連兔頭都沒浪費。這個戲班沒有京班那么正式,等級也沒有那么森嚴,都是一個人操持著許多角色。就連辛佑國都干過打門簾這樣的工作。等到辣子兔丁做成了,辛佑國自然也分了幾塊,久不吃肉的人們吃起肉來像是忘了該怎樣張嘴、咀嚼與吞咽。很多人吃第一口的時候一不小心就吸進了肚子里,壓根沒來得及用牙齒細細咀嚼。還有人一心急咬破了嘴唇。那是一群饑餓鬼的搶食像,也是一群窮苦人的求生群像。
也許是很久沒吃肉,也許是辣椒的作用,那晚辛佑國跑了幾次茅房,折騰了大半夜都沒入睡,以至于后半夜戲班那一句“土匪來了”也并沒有把他驚醒。等到他再一次醒來,已經日上三竿,搭伙的戲班已經連夜往前趕路去了。他索性就等在這里,等著下一個能把他帶往下一個地方的戲班或者其他隊伍。
吃完鍋盔的他現在開始試圖回味那帶著炙熱的溫度一下子滑入咽喉的兔丁。那溫度甚至一度燙到了他的胃里,帶來了瞬時的百爪撓心的感覺。這是人在闊綽的時候感受不到的。那只兔子被抓住并快速地打整干凈,迅速地洗凈并斬成了丁。辛佑國還記得那塊臨時被充當案板的牌匾上,依稀寫著“蘭若”兩個字。
“在寺廟里吃肉”,一想到這里,他就想到了《水滸傳》中的花和尚魯智深。走南闖北這么些年,他感覺這是少有的老老少少都喜歡的故事。每每看到衣不蔽體的聽眾眼睛里透出的對梁山好漢的敬仰和向往,就知道他們的喜好和他是一樣的,也同樣掙扎在死亡線上。
以前每次挨餓的時候,他也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被自己狼吞虎咽吃下去的食物。碰上好點的年景,每逢春天,稀薄的土地澆透了雨水,就會自然而然地冒出各種帶著清香可供食用的嫩芽。薺菜總是最好的果腹食物,車前草、稀繁菇、牛哈水也都是不錯的。村里的人總是會在農忙之后撅著屁股漫山遍野地尋找這些食物,像極了在覓食的牲口,組成了一把一遍一遍梳理著大地的密齒梳子。
在辛佑國的記憶中,從小到大,吃飽飯都是一種奢侈,挨餓倒成了家常便飯。
說到挨餓,還真的不是什么大事。辛佑國的祖輩幾代人都有人餓死。翻開二十四史,每個王朝末期都充斥著大量的“人食樹皮”“立人市鬻子女”“父子相食”“人相食”。就算康乾盛世,幾乎也是一年一次大饑荒,更何況當下這個世道。
皇帝的奏折里當然是看不到餓殍遍地,只知道海晏河清,歌舞升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辛佑國清楚地記得那一年,不是因為朝廷甲午海戰輸給了日本,更不是割讓臺灣島和賠款兩萬萬兩白銀,而是父母雙雙餓死在了那慶祝慈禧太后六十壽誕而搭建的碩大戲臺下。
據說人和人在饑餓面前是迥然不同的。年輕人扛餓,餓久了就像是原野上的狼。老年人怕餓,餓久了就像是癱在床上的羊。但不管是什么人,挨了餓總會先瘦后胖。水腫得像是吹起來的氣球,又像是沒發好的面團,一按一個窩窩。只要是挨過餓的人,都會對餓形成天然的記憶,會不顧一切地囤積糧食,以防災年。
正當他胡思亂想的時候,中年男子看他一直發呆,使勁地用手掌拍著他的背,笑道:“這位兄弟伙耿直,一口酒就喝曠(方言,意為呆傻)了!”
醒過神來的辛佑國被拍得直擺手:“這位兄弟見笑了,別拍了別拍了,再拍老骨頭要散架了。”
大虎在一旁突然很驚奇地叫了起來:“老叫花子原來會說話嗦,我還以為是個啞巴。你這不是許仙的雞冠兒嗎?”
其他的人都跟著笑了起來,辛佑國聽不懂這些人口中的川話,但又猜得到多半不是什么好話,就跟著笑了笑,說:“拿人手短、吃人嘴軟。我也剛好是靠嘴吃飯的,你說到許仙,那我就給你們說一段許仙,抵作飯食錢。”
話音剛落,這群陌生人的叫好聲就跟著起來了。不管是太平盛世還是亂世災年,上到皇親國戚下到販夫走卒,聽書看戲是大家最喜聞樂見的。只見辛佑國又喝了一口酒,恢復了中氣,才慢慢地講起來。他說的與其說是書,其實更像是戲文夾雜在彈詞里。他在這十幾年的顛沛生涯中,跟過不少戲班,《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義妖傳》早就爛熟于心,京戲《白蛇傳》更是聽了幾百場。東拼西湊下講的故事雖然有東有西,卻有著別樣的風采。他還特別在開場白中加上了這段傳說的來龍去脈。
辛佑國說道,這許仙和白娘子的故事本是起于北宋年間,源于河南淇縣和湯陰縣的黑山淇河一帶,當地有一個百丈懸崖青巖絕,青巖絕上有一白蛇洞,洞中有一白蛇仙女。在黑山主峰西側不遠,有一許家溝村,許家溝村的一位許姓老人,從一只黑鷹口中救過白蛇仙女的性命。白蛇仙女為報恩,嫁給了許家后人牧童許仙。婚后,白蛇仙女經常用草藥為村民治病,這使得黑山上金山寺的香火變得冷清起來。
黑鷹轉世的金山寺長老“法海”大為惱火,決心置“白娘子”于死地。就有了后來的法海扣許仙、水漫金山寺,白蛇仙女生下許仕林以后被鎮壓在雷峰塔下。等到許仕林狀元及第后,便是三拜雷峰塔,雷峰塔轟然倒下的故事了。
后來靖康年間金兵南下,東京開封城破,徽欽二帝被俘北上,康王趙構南渡。隨著趙構南遷的文人武夫中,自然是河南人居多。大名鼎鼎的岳飛本就是湯陰人,部下之中有不少黑山淇河附近的人。岳家軍南征北戰隨宋室南遷后,把家鄉的傳說帶到江南蘇杭之地,再也沒有回歸故土,傳說故事經過幾百年的口口相傳,裹在南遷遺民淚里的家鄉傳說就這樣變成了西湖邊的人蛇戀情。
辛佑國引經據典加上吃飽飯之后的精氣神讓這幾個目不識丁的趕路人大開眼界,聽得進去、聽得明白。簡單介紹了過場之后,辛佑國單刀直入講起水漫金山。他多年練就的語調語氣,加上旁若無人的自在之境,講得眾人仿佛都成了金山寺的佛僧信眾,目瞪口呆。
“只見那法海向空中拋去一根銀杖,頃刻變作一條氣勢洶洶的銀龍,白娘子豈甘示弱,隨手從發間拔下一支金釵,扔向空中,頓成一條通身焦黃搖頭擺尾的金龍……”講到這里辛佑國想喝口酒,卻被眾人催促著抓緊往下繼續講。在這荒郊野外的小小破廟之中,一身破舊長衫的年長說書人在此刻反而成了最光彩奪目的人物。
這一段書辛佑國也是說得酣暢淋漓,在飽受饑寒之苦后,又釋放了多日來孤苦一人的寂寞,更讓一幫趕路人刮目相看。
書剛說罷,中年男子就帶頭鼓掌叫好。大虎巴掌都拍紅了。辛佑國也在眾人夸張的肢體和表情下看到了他們衣服下藏著的匕首和坐在屁股底下包得嚴嚴實實的槍。
這些顯然不是戲班或者商隊該有的東西。從體型上看,這幾個人雖然黑瘦精干,但瞧著也不是土匪的身型。還沒等他想明白這到底是一幫什么人的時候,中年男子就已經率先從興奮中安靜了下來,開始指揮眾人準備休息。
“老六,今晚你守夜,把劉老板的貨看好,這趟萬不能出婁子。大虎,把明火滅了。省寨,把馬喂好拴牢。明兒一早繼續趕路。”
他指揮完就彎腰抱起了一床鋪蓋,丟給了辛佑國,說:“你這個兄弟伙我認了,明兒跟我走吧,高低有口飯吃,比躺在這強得多。”說完不等回話,躺下便睡,一會兒就鼾聲如雷。
辛佑國也不知道這些人是好是壞,現在肚子不餓的感覺讓他很是滿足,恍惚如在夢中。
看見中年男人睡著,旁邊小男孩好奇地問他:“您來自哪里?”
或許是因為那個鍋盔讓他想起了漂母對韓信的一飯之恩,辛佑國似乎對這個小男孩一見如故,便告訴小男孩,他來自遙遠的北方,庚子國難的時候,八國聯軍打破北京城,整個北方亂成一鍋粥,隨著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西逃的人們攪動了帝國首都周邊省份那一個個偏遠山村的寧靜。
很多原本一輩子拴在土地和荒原上的人們像是被一竿子打下來的棗,有些落地爛了,有些落地熟了,還有些落地滾遠了、生了根。而他從家鄉逃難出來的時候已經四十出頭,在這沒黑沒白的日子里,他從大字不識到能冒充說書先生,都是靠著這些“下九流”里的“不入流”人的幫忙,他也只不過是這洪流中的一粒微沙,流向哪兒,得看上天的意思。
說到這里,他不由得拽緊了一套像破棉絮的黝黑物件,如今自己已經年近五旬,卻還在顛沛流離,恐怕這輩子也難回故土了,這戲袍似乎成了他魂魄的歸宿。
辛佑國告訴小男孩,這是他跟著上上個戲班的時候,死去的王老頭留給他的。王老頭在戲班里管戲服。那個戲班是京城來的,也是被庚子國難那個浪花推過來的,是個在內務府堂郎中報了花名冊、演出劇目的正經戲班。聽戲班總管事人說還曾給官府交過甘結。
但就是這樣的戲班也在不斷的南下、西進、東出中散了形。先是頭等角兒去了天津,二路角兒留在了西安,等快到了四川,就只剩了龍套和武行。靠著武行倒也能撐持下去。王老頭看著辛佑國這個說書的就像個叫花子,找了半天給了他一個據說是原來京城名角穿過的戲袍。那個袍子的面料是辛佑國之前從未見過的,摸起來很滑,不像地里的麥子那么扎手。所以他格外珍惜這個袍子,穿上了它,他才覺得活得有意義。
“那你們怎么又走散了呢?”小男孩好奇地問。
當然,辛佑國并沒有告訴小男孩,因王老頭出城去找暗娼,不知道是被哪路土匪給剁了腦袋,赤條條地扔在了外邊的官道上。聞訊而來的戲班人等也都嚇破了膽,承班人索性就地散伙,分了家財。辛佑國也分得了一個銀圓和幾個鑼鼓。除了王老頭送的那身戲服,他把物什變賣換了現錢,統統寄回了老家,然后加入下一個逃難的戲班,繼續南行。
交談中,小男孩告訴他,自己叫華咸聲,為首的那個中年人叫徐春風,是男孩的師父,也是這個隊伍的頭兒。
聽到這個名字,他不禁打量著小男孩,咸聲二字應該取“咸與維新,聲聞于天”的首字,看起來他應該出身于詩書之家,否則也不會取出個這么文雅而有寓意的名字來,只不過他怎么和這幫子拿槍的土匪在一起呢?
當然他不敢問,于是他好奇地問華咸聲:“咸聲,好名字哇!你是哪里人?”
咸聲搖搖頭:“我是廣安人。”
“廣安,那可是個好地方啊!”
“你也知道廣安?”華咸聲聽到這句話也驚奇不已。
辛佑國頷首道:“當然知道,話說北宋開寶二年(969年),宋太祖趙匡胤應西川轉運使劉仁燧之請,御筆點渠江縣境秀屏山下的濃洄鎮置軍,取‘廣土安輯’之意,命名廣安軍,隸屬梓州路,領渠州之渠江、合州之新明、果州之岳池三縣,廣安一名,由此始。”還有詩曰:
欲說賓城好,先夸方物妍。
金羹收稻后,紅臘落梅前。
照座梨偏紫,堆盤荔更鮮。
清州如斗大,盛事數從前。
崖日神留傳,山高子得仙。
何詩春夢草,張諫力回天。
人物宜旌表,蟲魚不足箋。
華咸聲聽完頓時對他露出了欽佩的目光,他不知道眼前這個叫花子般的老頭居然有此番學識。
“我們廣安還流行這么一首民謠。”華咸聲接著辛佑國的詩吟誦起來,“金廣安,黃白瑩瑩然,桑麻榆棗豐,沃野無閑田。金廣安,庶民百姓,忠介質樸,不畏水旱,抗拒兇頑,名冠天府,點染好家園。”
“是吶,天府雖好,可終究還是他鄉。”辛佑國聽到這里,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你們呢?是做什么的,我看這幾個人還帶著刀槍,帶著你這么個小朋友出來,也不像土匪。”憋了半天,辛佑國忍不住問華咸聲。
華咸聲指了指馬車前面那面三角旗幟一努嘴:“你看,上面寫著呢。”
辛佑國借著篝火,看到紅色旗幟上用黑線繡著一個“洪”字,下面用金絲繡著一只猛虎。辛佑國瞬間明白了,這都是洪門的人。
洪門起源于明末清初,滿人入關后強迫天下漢人剃發易服,為保留漢家文化,南明東寧總制使陳近南先生以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號為名,秘密創立洪門反清復明。
洪門成立后便分散到五湖四海,有道是,廟堂之高皆進士,江湖之遠盡洪門,凡有江湖之處,便有洪門子弟。從康熙到光緒年間,洪門一直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庚子國難后,慈禧西太后帶著光緒狼狽逃出京城,天下大亂,革命黨風起云涌,朝廷威信一落千丈,這鄉野碼頭便再也無力掌控,洪門也從地下轉為地上。
雖然天下洪門是一家,各地南北風俗不同,旗子也有區別,北方愛用藍底,南方多用紅底,北方多繡熊,南方多繡虎,都是圖個威猛吉祥之意。能用金絲繡旗,代表這是大的堂口,水陸都能吃得開,辛佑國見他們不是土匪,懸起的那顆心也就落下了大半。
“那你準備去哪兒啊?”華咸聲好奇地問道。
辛佑國沉默了,出來這些年,他也不知道何去何從,這時候他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話“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月,人的命運有時候真的不是自己能把握的。
“死活存亡,聽天由命去罷。”辛佑國自言自語道。
華咸聲本來還想多問他戲班的趣事,結果辛佑國酒勁兒上來了,詞不達意了幾句后便心事重重地睡著了。
拜師開蒙
等到辛佑國再次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天光大亮。眾人沒有生火做飯,而是直接收拾了東西上馬趕路。辛佑國分到了一匹沒人騎的灰白雜毛馬,那馬很溫順,不用趕就會順著路往前走。他趁著趕路中間停馬歇息的空當問了下華咸聲口中那位領頭大哥徐春風:“徐大哥,咱們這是要去哪兒?”徐春風頭也不抬地說了兩個字:“成都。”
成都,這個熟悉的名字,讓辛佑國這個說書人心里多了幾絲遐想。這是個古老而傳奇的城市,古人說“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寫下《子虛賦》的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在那里相遇,劉玄德拿下益州后在此地稱帝,袁天罡算出了《推背圖》,杜甫在這里設下了草堂,還寫下那句:“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為博愛妃花蕊夫人一笑,在這里種滿芙蓉花,所以成都還有一個蓉城的別稱,更有人言“少不入川,老不出蜀”,他以五旬的年齡入蜀,難不成也會再不出川?
其實他之所以一直在路邊徘徊而遲遲不入城,也有這份擔憂。畢竟人人都想落葉歸根,成都再好,也不是他的故鄉,他不想落著一個客死他鄉的結局。但他現在不得不做出抉擇,如果不跟隨徐春風的隊伍走,那么他可能真的就餓死在這破廟之中了。
正在他猶豫不決的時候,看到華咸聲那企盼的眼神,也許是肚子又餓了,也許是鬼使神差,瞬間沒有了糾結。
在混合著馬糞牛屎、臟水臭泥氣味的道路上搖晃了十幾天后,他們終于趕到了成都城外,徐春風他們卻不急于進城,先在城外的一家小書局落了腳。只留下大虎陪著辛佑國,其他人則謎一樣地帶著那幾車貨消失了。在這三四天的光景里,書局老板郝壽臨倒是經常有一搭沒一搭地跟他聊天,興致來了還會翻箱倒柜地找典籍給辛佑國糾正典故遣詞。他們也會在書局門口支起一個小桌子,邊喝茶邊下棋。
辛佑國現在過的是穿著郝壽臨的舊衣服,跟著大虎他們搭伙吃飯的日子。雖然不再擔心餓肚子,但他自己也說不上這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他甚至連徐春風這些人給誰運貨,運的是什么貨也不知道。書局里其他年輕人也不會跟他說話,郝壽臨顯然是唯一的突破口,但每次一聊到這個話題,郝又總是顧左右而言他。
有些時候,辛佑國甚至懷疑郝壽臨也不過像自己一樣,是被半路上撿回來的,他們既沒想讓他們這兩個老家伙入伙,也沒想讓他們再度去討飯。或許就是單純的需要人看看家財、吃吃剩飯。
等到第五天的時候,辛佑國一大早就被馬車的車軸聲吵醒了。徐春風他們幾人趕著三輛大車到了。等到馬車停穩,徐春風就跳了下來。一個年輕人從書局里疾步迎上去,叫了一聲“徐大哥”。
“少昌,你來了。”
排好手下人將馬卸下來拉到后院去后,華咸聲看到年輕人后,便怯怯地叫了聲:“爸,你來了。”
辛佑國聽到這句,心道原來這位叫少昌的年輕人就是華咸聲的父親。
卻沒承想,華少昌帶著咸聲直接走到了自己的面前:“來,咸聲,快叫師父。”
華少昌這一舉動讓辛佑國措手不及,他連連擺手:“使不得使不得,我就是一個說書人,當不成師父。”
徐春風拉著辛佑國的袖子從中勸道:“沒得啥子。娃兒還沒開蒙,辛大哥剛剛好。我雖然也是孩子的師父,但洪門子弟多是武夫,只會打打殺殺,教不了什么文化,少昌是我的兄弟,這個貨棧是我們一起開的,他平時也沒空管著兒子,還望辛大哥不要推辭。”
“辛大哥,我是華少昌,我是貨棧東家,徐大哥是洪門堂主,這兒的兄弟既是貨棧的力哥,也是洪門的子弟,都是自己人,我們一直尋思著給孩子物色個開蒙的師父,還望辛大哥莫要推辭。”
聽到這里,徐春風拍手道:“對極了,我等相逢便是緣啊。你來之后,我們一文一武來教習咸聲,將來一定會將他培養成文武全才。”
華咸聲在父親和徐春風的催促之下,怯怯地叫了一聲師父,便跑得無影無蹤了。徐春風也不去追,只是跟辛佑國說:“今天晚上我們就進城,到時候我找個住處給先生,先生可以一邊教咸聲,一邊說書。錢的事,不用費心。我定期找人送來。”
辛佑國心懷感激地推辭道:“我本來就是窮困潦倒,蒙徐先生不棄,已是大恩難報,今又如此厚愛,我心中過意不去。”
徐春風爽朗地笑了:“先生只要把咸聲帶上正路,就當得、受得。”
辛佑國還想再次推辭,大虎跑過來跟徐春風和華少昌咬了一陣耳朵,三人就匆忙走開了。
那一天剩下的日子顯得格外漫長。郝壽臨讓他隨便挑幾本書帶走,還說以后空了都可以來書局坐坐,但是“以后買書要收錢了”。當郝壽臨說這話的時候,兩個人相視一笑。
辛佑國挑來挑去挑了本《尚書》,一本《三俠五義》。郝壽臨左手一本右手一本地來回瞄著,思索著,說:“一本尚德,一本重義;一本廟堂之上,一本江湖恩怨。你啊,看得出來,也是個神人。”
等到夜色完全籠罩了大地之后,大虎走進房間,辛佑國正在教華咸聲認字。大虎平淡地交代了下事情就出去了,由一個被稱作王孃孃的中年婦女拿著包袱皮打包行李。隨后幾人從書局后門潛入了夜色,沿著荒無人煙的鄉下小路向成都走去。
王孃孃一路上都在嘟囔,說的四川土話里夾雜著大量的臟話。辛佑國憑借著之前跟著戲班走南闖北時積攢下的經驗,零零碎碎地聽懂了一些。大概就是家里的兒媳婦還等著她回去替換好吃飯;家里的孫兒最近生濕疹,睡都睡不好,“焦心得很”;這么晚了才跟她說來接人,還不讓走大路;“那幾個錢連一雙娃娃的鞋子都做不了”。
這一路的嘮叨讓華咸聲半路上就睡著了。等到辛佑國背著他到達成都廣成貨棧的時候,后背已經被汗水浸濕。王孃孃帶著他們敲開了門,穿過天井走向偏房,開了鎖丟下東西就走了。辛佑國慢慢地放下咸聲,簡單收拾了一下,也安穩地睡下了。
翌日凌晨,下起了雨,馬蹄踩踏在石板路上和車輪碾過發出的聲音尤好辨別。開門的聲音雖然很輕,但依然驚醒了辛佑國。他雖然沒有起身查看,但后面的時間卻再也睡不著了,就這么睜著眼候到了天亮。
天快亮的時候,徐春風就來敲門了。他依然還是初次見面時的裝扮,只是多了一頂帽子。他走進門來,將帽子放在桌上,掏出火折子把油燈點上。黃豆般大小的燈火將他魁梧的身影投射到墻壁上,顯得更加英武逼人。
他拿起桌上的竹簽慢慢地將燈芯挑起,好讓燈光更亮一些。燈油燃燒后散發的香味和燈芯燃燒時噼里啪啦細碎的響聲,聞起來聽起來都讓人感覺心生安寧。
辛佑國很快披上大衣,下了床。徐春風點了一鍋煙剛嘬出火來,辛佑國就已經坐到了他的面前。
“辛師傅,這一單生意做完了還沒開春,暫時有些空閑。華少昌你已經見過了,今兒我先帶你認識一下隔壁茶館的張老頭。以后啊,你就跟著貨棧的伙計們吃住,茶館那邊呢,照應一下,得閑了就在這兒說說書掙點閑散銀子零花。”
辛佑國聽完,心里感到溫暖極了。他從來沒想到會有一天結束自己漂泊流浪的生涯,找到一個能夠固定落腳的地方。他總是覺得自己這把老骨頭始終是走到哪兒撂到哪兒的命,甚至興許死了都只是被好心人就地一埋,說不定什么時候風吹雨沖地就又曬了太陽。
他的嘴唇顫抖著,一只手撐著桌子,想順勢就這么跪下去,叩個首,但激動的身體卻不聽使喚。徐春風看出了他的舉動,伸手扶住了他:“您也別客氣。再說這些也不是白給您的。”
徐春風回頭看了眼還在熟睡的咸聲,繼續說道:“這孩子聰明,又有點淘氣。我和少昌都無暇管教他,以后不能讓他再跟我們一樣跑江湖了。以后,這孩子就跟著你,該開蒙開蒙,該棍棒棍棒。”
辛佑國兩手抱拳,說道:“我本來也是鄉野間的村夫,逃難路上才學了點皮毛。您是我的救命恩公,只要您放心把咸聲交給我,我一定悉心教導。”
徐春風開心地笑了:“那就好,那就好。辛先生,我還有一個要求。那就是您這說書的營生,要大張旗鼓地搞起來。”
辛佑國對于這個要求卻是充滿了疑惑。他想拒絕,但話到嘴邊,還是變成了點頭應承下來。
興隆茶館
雞鳴了三遍以后,就有伙計過來請他們去吃飯了。廣成貨棧是一個獨門獨院,由大堂、四個偏房還有賬房、伙房、門房組成。屋子都已經有些年頭了,是華少昌從當地人手里租下來的。
說是貨棧,實際上要護送的貨并不在這里集散。這也是成都城里大多數貨棧的慣常做法。實際上很多貨物的上岸、運輸、交割,在碼頭就已經完成了,貨棧只是供力哥、客商、鄉親們暫時歇腳的地方。這飯自然也就是隨做隨吃的大鍋飯。飯做好了在天井中間支張桌子,自盛自取。
吃罷早飯,徐春風帶著華少昌等人來到辛佑國住的偏房,介紹說:“正式給辛師傅介紹下,我這位貨棧東家華兄弟義薄云天,在我們洪門里都是能排得上號的。”
聽到這里,華少昌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撓著腦袋說:“這都是洪門里的兄弟們抬舉。”
徐春風爽朗地笑了:“少昌,你這個意思是我們這些老家伙不得行,把你們這些小兄弟給推到前頭去了喲?”
華少昌這下倒不知道該說什么好了,于是大家都跟著笑了。
在背海堂的這段時間,辛佑國慢慢知道了洪門子弟不只遍布大江南北,還包括海外,有華人之處便有洪門,甚至官府兵營里都有堂口。各省綠營兵和曾國藩的湘軍之中,下層兵勇幾乎都是洪門出身。
特別是湘軍,里面基本奉行的都是洪門的幫規會律,各營均有龍頭、堂主、刑堂、巡風等各級頭目,有時候為了控制手下兵丁,各級軍官也不得不加入洪門,白天的軍官可能晚上要給比自己級別高的士兵堂主叩首,所以有“白天為朝廷官軍,晚上做洪門兄弟”一說,縱橫天下的曾國藩也無可奈何。
讓大半個中國天翻地覆的太平天國更是有過之無不及,太平軍從廣西到南京,所到之處,各地洪門群雄并起,有的開山設堂,有的占山為王,有的直接投了太平軍,等到南京被湘軍攻破,太平天國敗亡之時,全國人口死掉了四分之一,但洪門卻徹底一統了民間江湖,不管農民商販、船夫纖夫、木匠鐵匠,還是教書先生、官兵鄉紳,三教九流、販夫走卒幾乎都成為了洪門中人。
聽到這里,辛佑國不禁驚嘆道:“雖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這反清復明四個大字何以有如此魔力,竟可在民間綿延百年而不絕?”
見辛佑國如此驚訝,徐春風哈哈大笑:“你真是個老學究,江湖上哪有那些多胸懷大志的兄弟,廟堂之高,江湖之遠,誰做皇帝關我們這些老百姓何事,哪個皇帝來了還不是要納糧交租,自秦漢以來朝廷就管不到郊野碼頭,你們北方可有皇命不下縣一說?”
“這個說法倒是有。”辛佑國點頭道,“朝廷任命的官員就到縣令為止,再往下就沒有官府了,我們北方農村皆是族長鄉紳一言九鼎,鄉村之中若有爭斗,哪怕出了人命也不會送官,而是押到祠堂任憑族長發落。”
徐春風點頭道:“你們天子腳下尚且如此,何況南方天高皇帝遠,又是大山隔絕,更是如此。很多人一輩子都沒進過官府,更沒見過縣令,一旦遇到紛爭,自然是靠拳頭打天下。別說不同地方,就是不同宗族,甚至不同字輩之間,一言不合就能械斗,打起來自然人多的一方占上風,所以大家入洪門多是圖個依靠,出門有個保障而已。”
在徐春風的侃侃而談中,辛佑國了解到四川山多水多,道路多在群山之中,所以貨棧生意繁盛。貨棧分水路和陸路,水路走船,陸路靠走馬。廣成貨棧便是走的水路,水路靠碼頭,船夫纖夫和力哥盡是洪門兄弟,華少昌才入行時沒有堂口罩著,自然備受欺負。后來遇到徐春風出手相助,便一起共了事。二人性格互補,外面的事交給徐春風,華少昌專心運營加管賬。
洪門子弟雖然大部分各自出身不同,偶爾搶地盤時也會有爭斗,但還都是會講究“五倫八德”:五倫乃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君臣有義、朋友有信;八德乃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會規中還有三十六條誓言和十條戒律,總之以義氣為重,所以像徐春風這種經歷豐富,尚武崇德又好打抱不平,見慣了大風大浪槍法又高超之人,自然受到眾人擁護。
后來在徐春風的建議下,廣成貨棧明面上運米面糧油,實際上販賣鹽茶,于是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徐春風也在協興碼頭開山立堂,坐上了這背海堂的頭把交椅。
隨后徐春風又帶著辛佑國去了隔壁的興隆茶館,說是茶館,實際上就是一堆破桌子爛板凳外加一個燒熱水捏茶葉的老劉頭。
老劉頭是個羅鍋,左眼還看不見東西。他負責燒水、打掃衛生、摻茶和收錢。之前興隆茶館還賣瓜子炒貨,但是老劉頭總覺得自己是“一抓準”,從來不上秤給顧客稱東西。加上他又是獨眼,經常瞎抓、缺斤短兩,導致人們都給他起了個名號叫“一爪沒”。后來來這兒喝茶的就開始自帶瓜子零食了。老劉頭勸不住,就定了個規矩:除了茶葉和熱水不能帶,其他愛帶啥都行。
后來興隆茶館慢慢熱鬧起來了,有帶麻將的,還有人來斗蛐蛐斗雞斗狗的,有一年本地幫會的擺茶碗陣都是在興隆茶館搞的。興隆茶館之前也請過人說書,還有唱小曲、唱戲的,不過都要么跟老劉頭不對付,要么是嫌掙錢少,都先后不干了。
聽說辛佑國要來說書的時候,老劉頭拿右手比了個九:“你是第九個來說書的,估計也說不長的個。”說完老劉頭就去照看自己的爐火去了。他這一天要源源不斷地燒水,好供茶客們飲用。興隆茶館的老主顧都是些底層人士,喜好喝碎茶、磚茶還有老鷹茶,還都要一抓一大把,必須得多加水、加熱水,才能沖得出香味、泡得出滋味。
辛佑國回到貨棧,找來了一塊木板和筆墨,在茶館門口仔細地擦干凈那塊木板,等待表面干燥后,在上面寫起了字來。
他寫字的時候一點兒也不像個落魄人,倒更像一位書生。花白的胡須更讓他看起來像飽讀詩書的老學士。他用枯瘦的手指握著毛筆一筆一畫地寫字時,華咸聲就在旁邊跪在長凳上認真地看著。爺孫倆親熱又專注的樣子讓走來過往的人都忍不住駐足觀看。老劉頭更是嘖嘖稱贊,在他寫好后伸出了一個大拇指:“這個字寫得精神。哪天給我這茶館也題個牌匾。”
辛佑國還沒來得及推辭,旁邊就有人遞過來了紙。辛佑國想了想,寫下了興隆茶館四個字。圍觀的人無不叫好。掌聲剛落,就有人發現了問題:“唉,這個隆字怎么少了一筆?”
辛佑國還沒說話,華少昌就在邊上說:“辛師傅這是說未來興隆茶館興隆無邊吶。”
大家這才醒悟過來,頓時爆發出了更熱烈的掌聲。老劉頭當寶貝一樣地把字收起來,連忙說改天就請個師傅來換個牌匾。等到熱鬧的人群散了,辛佑國這才發現徐春風他們又不知所蹤了。
辛佑國后半天的時間都在思考第一場書該如何說好。連教華咸聲寫字都走神了幾回。巴蜀地區除了盛行川劇,評書流派也有很多種。受坊間追捧的有盛春秋,是專講春秋故事的;還有徐老道,愛講封神榜;石爛龍是講聊齋的。他自己擅長的東西,要是歸總了,也夠說一個月的。但是要說全本,他心里一點兒也沒底。好在他在郝壽臨那里拿了套《三俠五義》能夠救急。
他早上正是在木板上寫了出“設陰謀臨產換太子,奮俠義替死救皇娘”。他又怕一出不夠講的,思來想去還是在教華咸聲認完字后再準備一出。他從來沒有感受到這么充實而有奔頭的日子。
記憶中,他這輩子總是在為吃口飽飯而忙碌,但又總是徘徊在即將死去和能夠茍活之間。他那個媒妁之言的妻子,也總是蠟黃蠟黃的臉,骨瘦如柴的手臂,餓得厲害的時候連眼眶都是深陷進去的。
等到他決定要逃荒的時候,她卻死活也不愿意走,讓本來打算跟他一起走的父母也猶豫了。即使等到他父母都餓死了之后,她也沒改變過主意。辛佑國走的頭一天晚上,她說了很多話。辛佑國也是第一次詳細知道了她的過往,她那個沒落了的秀才爹和不言不語的娘。
她從小家道殷實,但因為自己父親寫字忘了避皇上諱缺筆而死在牢里,從此家庭衰敗。她說她小時候長大的村莊,那個時候怎么也不覺得會挨餓。她說后悔沒給他生個一兒半女。說到后面辛佑國都很驚訝平時沉默寡言的妻子居然內心藏了這么多東西。
她到最后都沒哭出來。辛佑國現在想想,她應該在他走后哭了很久。只是當著他的面時,她努力做出跟他短暫告別的樣子。
他一路往南,中間也托人帶過幾次錢回家。前一兩次還能收到她托人帶來的褲襪。但后面他越來越居無定所,就再也沒了她的音信。
現在他可以不用考慮填肚子的事兒了,甚至可以干點自己喜歡的事兒。興許這件事兒做好了他還能讓自己的妻子不再挨餓。
等到晚上,興隆茶館挑上燈的時候,辛佑國開始了屬于自己的評書表演。他先吟誦了一段定場詩:“蕭條市井上燈初,取次停門顧客疏,生意數它茶館好,滿堂人來聽評書!”驚堂木清脆的聲音加這一段半文半白的定場詩,立即引來臺下叫好聲一片,也讓辛佑國更有了底氣,講得更加順暢自然。
辛佑國在說書的時候,也不由自主地打量著下面坐著的人。很多人有著明顯的特征,比如倚靠著一根棒棒的,就是力哥;穿著馬褂布鞋的,很有可能是過路的商人;穿著僧佛道袍的,可能是在家的居士;面露精光,渾身都是肌肉的,肯定是貨棧的武行。辛佑國用目光掃過眾人的時候,驚訝地發現徐春風也在,他正在跟另外一個辛佑國沒見過的彪形大漢講話。他們邊嗑著瓜子邊聊天,看上去十分愜意。當他與辛佑國四目相接的時候,二人就像不認識一樣,短暫接觸了便錯過了。
一回講完,臺下的觀眾紛紛叫好,還要求再講一段。老劉頭這個時候端著個臟兮兮的盒子四處討賞,不一會兒就收了半盒子的銅錢。等到辛佑國按照眾人要求開始講第二回的時候,卻用余光發現徐春風和那個男子已經不見了。
這一晚上的說書結束后,華咸聲已經在邊上睡著了。辛佑國收拾著東西,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下他的肩膀。他嚇了一跳,一回頭,正是徐春風。
徐春風哈哈一笑:“嚇到你了?我可不是故意的。”他也開始搭手幫忙收拾東西。邊收拾邊說:“先生餓不餓?一會兒跟到我去整點夜宵。”
聽他這么一說,辛佑國才發現自己餓了,于是點點頭。跟著徐春風順著堤壩在月色映照下向江邊走去。
兩人走了一陣兒,終于到了離碼頭不遠的幾艘漁船旁。這幾艘船都燈火通明,徐春風帶頭走進了第二艘船。辛佑國這時才發現除了那個他不認識的大漢,大虎和華少昌都在。
“來來來,坐坐坐。”徐春風招呼他像大家一樣圍著一口熱氣騰騰的鍋坐下來,“這個是咱們川渝碼頭上的人最喜歡的東西,叫火鍋。雖然都是些下水,但是好吃得很。”
辛佑國接過碗筷,夾了一筷子菜道:“這火鍋可是大有來頭的。”眾人驚訝地道:“你這個北方人,也知道火鍋來歷?”
辛佑國放下筷子,對眾人說道:“明代永樂年間,重慶的朝天門碼頭很多屠夫宰殺豬牛,把不吃的下水都扔掉,碼頭的力哥們都是窮苦之人,吃不起肉,便把沒人要的下水收集起來,加上花椒辣椒以及牛油一起燉煮,發現味道奇香,因為鍋在火上,于是取名火鍋,又因為便宜,便迅速流傳到巴蜀各地了。”
看眾人聽得津津有味,辛佑國繼續講道:“北方也有一種類似的吃食,名叫鹵煮,跟火鍋差不多,也是把剩菜、下水、燒餅放在一個大鍋里熬,只不過不放辣椒,放的是八角桂皮香葉。一文錢便能吃一碗,熱氣騰騰,餅上沾滿了汁水,運氣好了還能吃到塊肉呢。自古以來,這些個好吃的,那都是窮人發明的。”說完這句,辛佑國在眾人的注目下把燙熟的毛肚吃了下去,卻忘記了蘸油碟,瞬間被又麻又辣的味道給嗆到了,連連咳嗽。
大家都笑了,華少昌遞給他一杯酒,順了一下才緩過氣來。但這一口麻辣一口酒的獨特方式卻讓辛佑國再也無法忘記。
吃了一陣之后,徐春風也不介紹,就當辛佑國也是他們的一員,開始旁若無人地與那個大漢交流起來:“老二,這次拉肥豬打算好久擺地攤?”
大漢說:“說不好。城守營的弟兄們還沒給我信。”
徐春風又問:“重慶那些槍什么時候到學堂?”
大漢說:“已經到了,但現在還沒發給學生,等學生拿到了我們就能拿到。”
徐春風說:“好。等那些槍發到了,我們這邊就換些鳥銃過去,替換一下。”
徐春風那邊說得熱絡,辛佑國也聽不懂這些黑話,就埋頭只顧吃。華少昌看出了他的尷尬,于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跟他解釋兩句。他這才明白,徐春風既是洪門背海堂的老大,也是這廣成貨棧名義上大當家的。那個彪形大漢叫做冉慶,和大虎等人都是他的手下。
這次到重慶去,是趁著重慶新式學堂的學生做實槍操練,順便找人多搞了幾把槍藏了起來,準備找機會帶回成都,不同的是,冉慶雖然是徐春風的手下,但二人是拜了把子的,所以要叫一句二當家的或者二爺。華少昌是貨棧的東家,平時管著整個貨棧的賬簿,但在背海堂坐的則是第三把交椅。
后面辛佑國也差不多搞清楚了徐春風們所說的“抓肥豬”其實就是劫富濟貧,如今這世道,洪門的子弟也會偶爾搞點這種副業。只不過現在他們有了更加迫切的需求,那就是——洋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