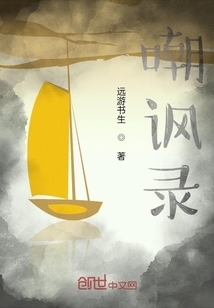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序言
序言
從語言的角度,嘲諷是一種高級的說話技巧,可以是指桑罵槐,可以是聲東擊西,也可以是不露痕跡地反映一些難以啟齒的腌臟,而不只是揶揄挖苦,更不是輕蔑嫉妒、火上澆油。
如此一般的代表人物有委婉點出君王脫離民眾、寵幸讒臣、迷戀酒色的鄒忌,有如手術刀般精準剖析黑暗動蕩年代落后國民麻木不仁、蒙昧無知的國民先生魯迅,還有許多極具文化修養、德高望重的讀書人。他們大多不是巧舌如簧的無知小人,也并非是逢迎諂媚之徒,更不是沒有真才實學、不接地氣的所謂文人。他們只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多少端著幾分文化人架子,故而罵得不直接、不粗俗,不失風度,以便和民風淳樸剽悍的刁民區別開來,以便和整日生活在污言穢語中的底層人區別開來,或許他們從未意識到這一點,即他們并沒有在身份上看不起別人,只不過對于不符合自己喜好的動作行為反應會激烈些。故而民國的報紙上多見一個個聲名斐然的文人大家相互挖苦,甚至直接寫文對罵,那便是文人吵架的架勢,也是民國文壇一樁為人樂道的趣事。魯迅先生是一股清流,因為他雖然經常會攜帶個人情緒去嘲諷一下個別無病呻吟的作者,或個別他不喜的人物,但他的雜文和小說從來不會因為個人的情緒而有失偏頗,所以他筆下的鞭子才會一下一下地抽到當時時代之痛處。鄒忌諷齊王納諫,則更多是一種官場的說話藝術。在那個帝王掌管世人生死大權、降黜拔擢的時代,在那個與人交際如履薄冰的時代,鄒忌的諷諫方式可謂是極其聰明的,故而側面說明情商的重要性。
近現代以來,嘲諷藝術再找不出如魯迅先生那樣簡單直白又立竿見影的標志之作,倒不是因為文字環境太過于拘束,相反地,其實如今的話語自由權利是民國渴求不來的,只不過是少了一些如魯迅先生那樣有趣又簡單的人。這個時代的學者和文人多是專心致志搞學術研究之人,亦或者是一些努力營生糊口的人,大受現代相互尊重習性的影響,批評柔和得多,平靜得多,言簡意賅、鞭辟入里的文字很少看見了,故弄玄虛和綿軟無力的文字篇章倒是不少。這樣過于周正中庸的結果是文壇里大家隱士于鬧事俗塵潛心創作,小人物粉墨登場逗人捧腹,以至于傳統文學在中國發展得舉步維艱,這在網絡文學風靡無二的當下更是如此。當然,這個文人環境中還是會有難得的統一時刻的,至少有一個人常年活在文人的吐槽之中的,那便是青春文學代表人物——郭敬明。郭敬明是有文學才氣的,其文筆尚佳,講故事的本領也不差,只不過成名太早,后來也就不好好寫文字,轉向輸出符合年輕人趣味的文化產品去了。郭在年輕人群體里是極受歡迎的,因為其小說中恰如其分的感傷很能觸動青年人細微波動的神經,而故事主題又總是愛情啦友情啦,這些文學永恒不變的常青藤,情節又不拘于俗套,故而作為流行讀物而言,其實挑不出太多毛病。只不過流行就意味著其創作目的是為了迎合讀者喜好,是一種以市場為導向的文化創作,是可以量產的商品,套路是一樣的。先前可能還有人美滋滋地買賬,久而久之就會習慣,甚至于是厭倦,在諸多同質化的產品大潮中便也是被淹沒了。遭遇這般困境是所有作家最愛也是最怕的事情。一方面,很多初出茅廬的新手都需要找到一條路子走,都需要找一個受眾耳熟能詳的標簽來表率自己的特點;另一方面,當一個人在某個領域小有成就時,他如果不突破,不轉型就會被長久形成的標簽束縛住,也極有可能被新興的人取而代之。轉型意味著撕去標簽,也意味著巨大的風險,作為商人而言,多數人會選擇穩健地收割固定受眾,而不愿意轉型,而這樣的人的作品大多就是流水線上的產物,只能販賣所謂的故人情懷。遭遇如此困境的人有很多,常年陪跑諾貝爾文學獎的村上春樹就是如此;立志成為成功商人的唐家三少也是如此。文下題材、主題、文風都一如既往地偏向于青春愛情的村上春樹,在形成自己獨樹一幟的文學魅力之后,也離“授予為人類文學進步做出重大貢獻”的諾貝爾文學獎越發地遠了。長期苦心耕耘塑造的個人風格和不斷尋求主題上、內容上的突破的文學異質化,似乎是文學乃至于所有藝術領域的一個悖論,而恰巧是這個悖論,不斷推動著人類文學的不斷發展。
2021年的時候,我偶然看到一件有趣的帖子,議論的主角是賈平凹之女賈淺淺,內容是說她的詩作極其粗鄙不堪,竟然搬上臺面。我心想可能是詩作的確粗糙不堪,故而才會招致罵聲。于是我找出那首名為《朗朗》的詩,讀完,良久不語,一邊在品味,一邊在思考。
詩作的文筆水平不高,至少從審美情趣上來說,很不符合人們對詞語和文法的期待,我個人也這樣覺得。至于內容而言,表達很不同尋常,不能說很驚世駭俗,但還是很大膽,如果沒有最后一句,如果主角不是孩子,這首詩算不得什么可愛的作品。但是因為主角是孩子,因為最后一句的形容很有趣,故而還可以理解。讓我對這首詩印象如此深刻的,不是這首詩的內容,而是各種評論。有人說此詩開了什么什么的先河,極具藝術價值;有人說此詩污染了中國文壇,像賈淺淺之流應該從中國文壇除名;也有人深謀遠慮般覺得中國文壇長此以往危矣,更有甚者說賈淺淺能火都是依托父親的名氣,乃至于批判起了賈平凹的人品,各種各樣的言論似乎個個義憤填膺得巴不得寫個長篇出來斥罵。而主角本人也回應過為中國文學之前途而憂心忡忡的群眾,只不過在鼎沸的人聲中,不僅沒有說清楚問題之所在,反而激起了更洶涌的謾罵。這本是新聞媒體嘩眾取寵的噱頭,不知為何卻激起不小震蕩,可是在風頭褪去之后,那些咒罵譴責的人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了,那些對中國文壇愛之深責之切的仁人志士也不知又去哪里繼續唇槍舌戰了,只至于連個正兒八經的出來說話的人都沒有。這個時代的罵戰罵得群情激奮,罵得涕泗橫流,罵得別開生面,可不見罵得字字珠璣者,更不見為不平和落后而發聲的人。這便是這個時代的悲哀,明明是太平盛世,明明擁有著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豐饒的物質基礎,明明擁有著龐大的人口基數,卻是沒有形成一種屬于現代風格的中國文學。怪不得余秋雨先生曾在《中國文脈》中便感嘆道“中國文脈自民國之后,進步極少,而突破寥寥”。盡管他在字里行間流露出文人獨有的崇古貶今情絲,但是批評總體而言還是十分中肯的。
文人自古是憤世嫉俗的,無論是壯志難酬的風流才子,還是憂國憂民的樸實文章,故而諷刺在文學中極為常用,用法也多種多樣,精彩的文章更是多如牛毛。除去世杰上最經典的,如契訶夫、魯迅等大家的文章,其余出自小眾群體的尚佳的文章我也讀過不少,如《透明的屋頂》、《十字勛章》,還有一篇寫留守兒童的,不過忘了文章名字。黑色幽默的電影也不少,《驢歡水》、《尋夫記》、《我是余歡水》、《十一回》等是其中較為優秀的,演員的表演很精彩,劇本質量也經得起考磨,文學意義和審美價值尚佳,但是就商業性而言,不符合個人對于大場面、大事件、大制作的期待,所以始終不入流,沒有激起什么水花。偶爾跳出來幾個營銷號控訴“人民失去審美能力”、“好演員沒有前途”什么的,標題取得極為吸引眼球,但是分析卻極為片面,沒有談到核心問題,幾句牢騷過后便沒了后續。而這樣的帖子在熱度過去之后,便了無蹤跡。當然,喜劇方面,周星馳和開心麻花的作品也無時不刻地透露著一種反諷文學所有的辛愁之感。姜文、葛優的作品也常見諷刺,不過不是小家碧玉風格,粗獷一些,仍是不錯。喜劇和純粹的諷刺文學比起來,反諷要來得輕巧得多,形式上也更容易為人所接受,但是正是太過于春風化雨以至于人們常常被幽默的語言、形象和令人捧腹的情節所吸引,而忽略了劇作中意味深長的諷刺,也就是常說的領悟到第一層卻悟不到深層含義。多數人是前者,而接受過系統理論學習的人可能會在思考之后想得遠一些。而諷刺文學語言中迅疾的戾氣來得直白辛辣得多,以至于不那么討喜,甚至令人討厭。人們喜歡聽好話,喜歡看別人的笑話,就是不愿意聽別人對自己的批評。而很多寫作的人為了迎合讀者群眾的口味,一般也不會選擇諷刺,對于很多陰暗的東西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選擇明哲保身。以至于其實幾千年以來,留下來的諷刺代表作只堪堪有《儒林外史》和《聊齋志異》,而《西游記》,《水滸傳》由于暗喻太過,故只能算半部,這是傳統文學的一大憾事。如果這就是傳統文學最大的窘境,可能不會有人擔憂,不會有人感慨,因為遺憾大多都是精益求精的借口,而不是搖尾乞憐的慈悲,但現在的事實是中國傳統文學所面臨的問題不止如此。
多年前,一些傳統文化研究學者對于網絡文學嗤之以鼻。可現在,網絡文學蓬勃發展,欣欣向榮,已經在全世界引發熱潮。可反觀傳統文學,倒是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窘境,沒有什么瀲滟的起色,在中國高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時代,中國傳統文學卻愈發掙扎地被擠到邊緣,這才是時代真正的悲劇。不是文化發展的環境不好,只能說是做文化研究的人太多了,寫時代的人少了,寫真實的人少了,敢于指出這些問題的人也少了。一定程度上,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放聲的人,在這個光明的時代,寫一些真正的不堪的陰霾,以便讓人們能夠走得更為光明坦落。中國花了幾千年孕育出了一個孔孟,一個老莊,世界上幾千年也只有一個雨果,一個馬爾克斯,那是人類文明千年一遇的天才,是上帝在人間的遺珠,是每個人都應該崇敬的榜樣。但是我們不應該一直活在對他們的膜拜中,我們要一邊沿著他們走出的路途前行,一邊在他們從未經歷過的時代走出一條前無古人的路,為后來者留下些東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或許有人會說,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冰心文學獎等各種各樣的文學獎上每年都會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作者,都會產生許多優秀的作品,故而普通人大可以不必杞人憂天,自會有人來率領文壇走向更高一級的階段。事實的確如此,但是文學藝術從來都不會自發地進步,它只會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一點點地精進,一點點地脫變,一點點地煥新,物理化學如此,生命科學如此,人類社會發展如此。而我只不過是茫茫大潮中接踵而行的人之一,我只是希望他日有人肩挑大梁而行時,他不是獨身一人。
以上這些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可以稱之為理想追求,算是作為一種勉勵。這本書會是一本生活式的小說集,沒有天馬行空的想象,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生活之中,也沒有那么多的跌宕起伏,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故而極有可能開不出靚麗的花朵,更不可能達到歐亨利式的精妙。文章風格借鑒和模仿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和中國作家魯迅,以求用平淡的文字反映現實生活中的事情。同時借鑒了電影藝術作品中的黑色幽默和喜劇元素,力圖增加文章的可讀性。這是序言開篇時那句話的由來,也是書名的由來,至于效果如何,有待諸君檢驗,故而在此不妄下海口。
在我有限的閱歷中,見過夏目漱石幽默又辛辣的反諷,見過魯迅犀利鋒銳的口誅筆伐,見過季羨林不拘一格的破口大罵,也見過周星馳笑料中蘊藏的悲哀,見過諷刺漫畫作品中不著痕跡的隱喻語言的魅力就在于所有看似可有可無的搭配都能在不著意之處令人動容,所有雕刻和打磨都能在情感的共鳴中春風化雨。最為我喜歡的嘲諷風格還是美國新聞記者羅森塔爾的《奧斯維辛沒有什么新聞》中的幾句話,如文章開篇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布熱金卡,最可怕的事情是這里居然陽光明媚溫暖,一行行白楊樹婆娑起舞,在大門附近的草地上,還有兒童在追逐游戲。”,以及文章結尾的“這里天氣晴朗,綠樹成蔭,門前還有兒童在打鬧、嬉戲”;除此之外,那一句“雛菊花在怒放”也深受我的鐘愛。文章沒有花哨的刻意渲染,也沒有扭曲偏頗的個人感情,一切的力量都在平淡之中慢慢暈出,慢慢升華。在我看來,最好的文章莫過于如此。這是我所追求的,也是我正在寫下的。
嘲諷的目的不是奚落,不是打擊,只是為了用悲劇警醒讀者,如果可能的話警醒世人,為社會發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嘲諷也不是為了嘩眾取寵,更不會惡俗低庸;嘲諷,是以一種曲折回環卻又平易近人的方式,去揭露隱藏在華麗泡沫外衣下的隱痛,只為讓平白無實的雙眼把丑和惡看得真真切切。我力圖給讀者帶來一種既平易近人又不落俗套的作品,但因為個人審美情趣的不同,必然是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期待,故而諸君大可不必昧著本心吹捧,至于建議和批評是大有裨益的,筆者對此歡迎之至。
何為文學?我的一位老師曾問我這個問題。我當時的回答是“一些文字技巧,加上對生活的敏銳感受”,所以這本書也是我對這句話最生動的筆證,是我對生活最深切的體驗。
2021年6月于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