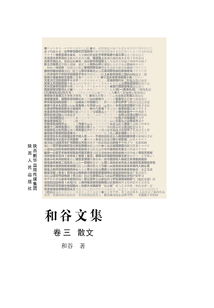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西麗湖筆記
獨居
一個人身只影單地走這么遠,住在這么一個偏僻的地方,時間又這么久,在我來說恐怕還是頭一次。盡管,在這幢高雅的別墅里同住有十來個人,大多則是五六十歲以上年紀的老人,何況只是頭一回打交道。大伙用餐前后聊聊天,我也極少言語,罷了,大多時間是一個人待在自己房間里。有兩張軟床,床頭裝飾分有男女的意思,卻只住著我一個人,一個男人,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我關上門,拉上窗簾,這個空間便獨我所有了。我看書,與卡夫卡、喬伊斯交談文學與禪,與眾多的散文大師談美學小品,與歷代雅士談古往的筆記體文學。更多的是自我交談,我同我的斑駁的記憶對話,然后寫一點文字,聊以自慰。我抽煙,喝茶,沖澡,大小便。我對著鏡子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都似乎認識又十分陌生。桌上有電話,可以打到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我卻一次未動它,怕它打擾我的寧靜。有汽車喇叭聲在庭院里響起,我不關心它。屋外有腳步聲,也不是在為我響動。倒是有人會敲我的門,那是服務員小姐中的某一位來送水或打掃房間,至于我,不過是這房間里的一位客人罷了。我看電視,想看哪一個頻道就擰哪一個頻道,這是獨居的長處。電視好看,好熱鬧,但他或她都不會從屏幕上走下來同我交往,他們只是影子。在這屋里,我想發現一個有生命的伴兒,竟是一只蚊子。它很漂亮,有很長的腿,也有要命的歌喉。我不忍心消滅它。我已發現雪白的墻上有它的同類的血和尸體。那血當是人血。是打死這只蚊子的那個人的血。血已經干了。我想,假如這只還在飛翔還在歌唱的蚊子敢吸我的血,我也只好這么干了。我憐憫它,但我不堪忍受被蚊子騷擾的精神痛苦,倒不是我舍不得一丁點養活一只蚊子的血肉。我時常一睜開眼,茫然地臥在床榻上,不知身在何處。我突然想起了陶淵明,想到了軟禁和流放這個字眼。我這是多么美麗而憂傷的流放。如果這是監獄,我當是最幸福的囚徒。這樣想著,我就不再感到恐懼和孤獨。抑或,比出家更合適,那么,這當是世界上最好的寺廟。我做我的功課,念我的經,修我的道,煉我的丹,爾后云游歸去。可我卻留戀塵世,渴望親情,渴望愛女人和得到女人的愛,不忍告別凡俗,這便是我的悲哀和注定不會成為超人的癥結。假如命運迫使我在這里永遠住下去呢?那也無妨,索性認了。我也有憎惡塵世的一面啊!
《新聞圖片報》 1989年3月14日
窟穴
南國麒麟山下的一個深夜,卡夫卡來找我,無意間談及窟穴。
他說:“我們在沙地上掘了一個窟穴,窩在里頭十分舒逸。夜里我們蜷縮在一塊兒,父親便把樹干架在穴頂,覆上枝葉,好像我們如此便可以避免暴風雨以及野獸的侵襲了。當天色暗了下來,就在枝葉底下,我們時常害怕地呼叫父親,但是父親并未馬上出現。”
“后來呢?”我真替他擔心。
“不久,我們才透過罅縫看到他的腿,他溜進來我們身邊,輕輕拍撫我們,他的手使我們安靜下來,于是我們便沉入了睡鄉。除了父親,還有五個男孩,三個女孩,這個洞穴對我們而言實在太湫窄了,但是,我們若不如此相互靠近,恐懼便會立刻爬上我們的心坎。”
他講完了,情緒似乎還沉浸在窟穴的境界里。
我說,我就是生在窟穴長在窟穴里的,老家人把它叫窯洞。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放羊歸來,遇到暴風雨,我和我的羊群便鉆入溝里一個窟穴里。其實也是不知哪個朝代的先人住過的窯洞,洞口積滿了泥土,長滿了雜草和洋槐樹。天色暗了下來,雨卻未住,我很害怕,很恐懼,和我的羊群依偎在一起。雨稍小一些,我才摸黑爬上溝坡,把羊群趕回村了。
記得那窟穴旁有口井,不知是水井還是炭井,那時間只是干枯著,扔一塊石頭下去像扔在溝底里。后來開荒地,父親和我冒雨填那口井,挖掉了一個小山頭,收獲過一料好麥子。
還有一回,我和祖父母從市里回來,半路遇雨,就躲進河邊一孔窟穴里。天黑下來,點燃一堆火,卻耐不住饑寒。尤其是頭上的壁虎令人恐懼,總共有十幾條。祖父曾養過幾箱洋蜂,放在菜花地邊,突然有一天發現蜜蜂沒一只了,箱子里養的是一條蝎子。這蝎子又怎么蜇了祖父的脖子,他就砸扁了它,用它的血肉貼在被蜇處拔毒氣。這壁虎總使人想到那蝎子。其實老家人就稱壁虎為蝎虎子的。
我偎在祖父懷里不敢動。面前的河水在漲著,說不定半夜要漲至這窟穴口。這么,我們就摸黑上路,走了四五里溝坡路,在雨中的一陣犬吠聲中找到了老姑家。那晚,在老姑家換了濕衣裳,偎在熱炕上吃了一頓米兒面,很稠,很燙,現在想起來也香。
卡夫卡聽我講著,不動聲色。他本來就很少微笑,內向得很沉郁。
我又講到華山上的洞穴,石的,是供佛住的,是石匠用鑿子鏨的。那年春天,我和我大學的男女同學們爬上華山,在黃昏里尋到這處宿營地。男的到山上撿柴火,女的打掃洞里的羊屎蛋。也是用樹干架在窟穴口上,以避免寒風和野獸的侵襲。火燃著,火上的水壺冒著熱氣,我們烤了前胸烤后背。唱歌,說笑話,惡作劇,耐不到天明就各自偎依著睡了。
半夜里,我醒過來,窟穴口灑進皎潔的月光,松濤如同大海在做驚天動地的深呼吸。不知怎么,我感到一陣心悸。天亮了,我們便爬上南天門,去看太陽如何從天邊跳動著誕生。
我與窟穴的緣分,使我做過無數次有關窟穴的夢。我在鉆窟窿,很黑,很湫窄,有時僅有碗口粗細,我就驚恐起來。我渴望一個好空間。
夢歸夢,多么恐懼,醒來依舊平安。但我上面講到的幾處窟穴,卻是記憶里的真實事。類似的例子,還可以從往事里找出許多來。
卡夫卡說他的窟穴是一個寓言。有一個寓言,正捏著生命的痛處。
堅韌地忍耐就是一種勝利。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不是一具軀體,而是一串成長的過程。生存,是需要勇氣的。
《人民文學》 1990年第1期
西麗湖筆記
江南雨
圣誕節過后的幾天,這里的太陽便躲在了云后邊。天色灰白,風微微涼爽,接著空中便織滿了銀絲。草綠得發青,樹也光澤十足,路上濕濕地發潮,于是才感覺下雨了。雨絲太透明太晶瑩了,以至難以辨認空氣里有液體的成分。而序曲之后,雨便由潛入變為闖蕩,嘩嘩啦啦,刷刷作響,直下個酣暢淋漓,久久不可抑止了。
在故土北方,此時的雪許是鋪天蓋地了吧?那才叫作冬天呢!北方的嚴峻,使雨凝結為白色的固體。空氣在濃縮,氣溫在跌落。在那種境界里,人,不是變得萎縮就是變得精神抖擻。四季分明,時令交替,以提示人對于流淌著的時間的珍重。
江南卻沒有冬天。雨能下在冬天嗎?鮮花常開的土地,且讓人飽嘗溫潤之春的永遠。含糊不清的時序,又使你感到自己永遠很年輕,不會有老去的時候。但這樣,是否會減少人的生理以至心理上對大自然變化的承受力,弄不好就要慵懶起來。江南是一個溫室,溫室是舒適的,溫室領略不到大自然的氣溫在推向或熱或涼極致時的生命感受。
窗外的雨里,紫色的牛蹄花和簕杜鵑在飄落著,直染紅了那條通往遠處的小徑。平時那位掃地的婦人總把落花掃到路旁的草叢里,讓它自行干枯。那婦人是誰?是林黛玉嗎?雨里,她不來掃花了,那落花就在雨地里浸泡著,被行人踩踏著,成了一地紅泥漿。江南雨啊,你總這般多情而失意。
有人敲門。我以為是服務員小姐來送水,打開來是一位陌生的女子。她是報社的記者,來拜訪一位老作家,敲門完全是投石問路。她被淋得濕濕的,索性就在這兒避雨。她笑得像小孩子,梳著頭,呷著茶水,剝著香蕉吃,談詩,說行旅觀感。我們似乎很熟。雨聲如注。
我不知道這雨能下多久。就這么下著,酣暢淋漓地下著,也挺好。我想起一幕小品,拉提琴的少女與失戀的小伙子還有賣蘋果的年輕人遇在了一角屋檐下,互不相干,卻也十分和諧。因為雨,使他們擁有了片刻的同一世界。雨住了,分手了,屋檐下也就空落起來。我不記得那是不是江南雨。
女記者是走了一段雨路趕到這兒來的。她說,下雨了,真霉氣,要是天晴著多好。她說這兒很幽靜,別有洞天,天晴著就好了。她說一個女孩子出門在外,過節時就想家。她說她的詩寫得很彷徨,不再談什么詩了。她說她在沒找到要找的東西之前,什么寄托也很無聊。
我隔窗看見她要找的那位老作家打著傘從外邊回來了,就把她引到那里去。記者是一種職業,而寫詩很難成為職業,何況成為職業就很沒意思了,她說。于是,她留給我一張名片,就去干她的職業了。我與她就此道別。
雨沒有住的意思。
我又復坐在窗下,想著這江南雨的語絲,在如何縈繞著一個北方人的客心與鄉愁。不是春雨,亦不是秋雨,是冬天的雨。在故土北方,冬天是不會下雨的。此刻,那雪花飄飄,已擁抱了我的古都。雨是響動的,雪是無語的。
我想,明天會晴嗎?我是擔心自己這回遠旅沒帶雨傘,怎么走到雨里去。我希望看見陽光下的江南風景。
房間
那個漆黑的夜晚,他一個人望著遠處豆粒般的燈光,默默地走過荒野。他很焦灼地尋找投宿處,也就是尋找房間。他踏入那間闊綽的房子了。讓四堵墻把自己圈起來,然后安然地進入夢鄉。翌日清晨,他便渴望房間外的世界,迫不及待地拉開窗簾,讓關在外邊的天地草木進來,還推開了窗戶讓空氣進來。他從一個叫作門的地方扳動開關,從洞天的地方走出去,站在草坪上的陽光里,讓房間空蕩蕩了。他又走出另一道門,擺脫四堵墻的院落,走到牛蹄花掩映的石徑上去。而外邊還有墻外的墻,局限是無窮盡的。常常,他又要回到那房間里去。
因為擁有了房間,他才厭惡起房間來。透過窗戶,景況依舊,紫色的簕杜鵑又凋落了幾枚花瓣,青綠的瀟湘竹又生發了一節新筍。偶爾有行人從小徑上走過,也不向這里瞥一眼。南國小姐又是在這個時間去倒垃圾,手提著紅色圓桶走到荒坡下去,又折向一旁的水龍頭處沖洗紅桶,再唱著流行歌曲走回來。日復一日,這情形周而復始,寧靜而單調。一旦他站在窗內時,不知怎么就覺得自己竟像是一個囚犯。
黃昏暗示長夜的來臨。他突然打開門,走到小徑上,又走到高高的荒丘上,走到低低的湖邊去。他想挽住時光嗎?湖心正燃燒燦爛的落霞,明麗輝煌。而四周的橙子園和荔枝林漸次墜入暗夜。路燈已亮在樹叢的小徑上,提示他回到房間里去。潮氣浸來,覺得臉上涼涼的了。他徘徊著,許久許久,終是朝著歸宿的方位,走過小徑,踏入庭院的門,又推開自己房間的門,回到自己剛才的位置。散一散心之后,房間又有了新的感覺,變得適意了。
房間是什么?
是把外界完全隔開的一個小小空間。那么,心,也居住在人的軀體所構造的房間里嗎?
暗香
當初一踏入這片異鄉的土地,就嗅出了一股奇異的氣味兒。尤其在夜間,從小石徑上走過,那濃郁的草木所散發的氣息便撲鼻而至。是牛蹄花嗎?不是。是簕杜鵑嗎?也不是。莫非是南國土地的呼吸?
從門庭的天井旁走過,又是那奇香浮動,刺激著敏感的鼻息。仔細捕捉,竟是那株毫不起眼的梔子花。它被剪成一個渾圓的冠,似乎枝干密匝匝的,葉很少也很小,那米粒般大小的小黃花就綴在枝葉間。
掐一朵湊到鼻翼下,猛地有一股能被熏昏的感覺。香得極致,竟是難以接受的苦艾一樣的澀味。
北方的梔子花多為盆景,株冠小巧,開不了這么繁的花,且很嬌貴。
后來才發覺這里滿路邊也凈是梔子花,如同北方的冬青樹一樣常見。
又是那浮動的暗香,誘惑一個旅人的感覺。它仍是梔子花香。這奇香被化開來,流動在空氣里,彌漫在夜色里,顯出這塊土地溫潤清馨的風范。
暗香,在空氣中均勻沖淡,恰如其分,且很中和。如同酒,假若濃為酒精便不可飲。又如同糖,假若濃為糖精也要化開來才是。
不去掐梔子花罷。
讓愛悄悄從梔子花的旁邊悄悄走過。花的靈魂將如同那芳香會不時叩問你的消息。冬天里的春天,梔子花在陽光下在夜色里開放著一片寧靜的時光。惆悵的旅人,便有了一個無欲的自在的夢。
時光
屋外的山包上有兩個小孩子正在玩耍。男的大約八歲,女的六歲,是隨奶奶從香港來這兒看望奶奶的舅舅的。我透過窗戶可以看見他們在那兒玩,一口粵語,我聽不清一句話。
這時候,孩子們的奶奶和奶奶的舅舅從湖邊散步回來,在小山包下的石徑上站住了。兩個老人,奶奶六十歲不到,奶奶的舅舅已七十有四了。
兩個老人與兩個孩子對望著。
只那么短暫的一瞥的相遇,卻可以跨越半個世紀的時光。
我想,我在二十年前的時候,也曾像這孩子這么大年齡,不過遠沒有他們闊綽,腳丫子從鞋子里戳出來,去山包上割草放牛。我和舅舅去礦上撿煤,抹得像黑孩子,一次被公家人抓住,筐被扔到溝里,挨了幾個耳光。
孩子的奶奶和奶奶的舅舅,在兒時這么個年齡里干什么呢?不知道,我只聽奶奶的舅舅對我說,他的外甥女年輕時候曾是上海之音的著名播音員,后來因故遷居去了香港。她兒子長大成人,變為富翁。我眼前的這兩個孩子便是她的孩子的孩子。
我眼前的孩子,不會對上海有任何印象。他們開始的是另一種人生。他們把這里叫作大陸。這里是他們的老家,是根。
兩個老人,兩個孩子。而我恰好站在中間。
眼前的情景又將很快成為記憶。
歷史就這么走動著。
空間
這里不是西安機場。這里是廣州車站。地球把你拋上一萬米高空,時速為一千公里,不及三個鐘頭,你便擁有了相距甚遠的這個新的空間。
你很小。你在空中對視于地面,那座城這座城也都小。同樣,飛機在天上飛,確也是一只銀色小鳥。
起點與終點,是此岸與彼岸,你越過了一千五百公里寬的江河。
你由熟識的空間挪到了一個陌生的空間。你正享受此岸的陌生。那雙惜別的淚眼,換作了路人的目光。
世界很蒼茫了。
從一個大都市來到另一個更熱鬧的大都市,從內陸到沿海,從古老到嶄新,其歷史年限約五千年。
你進入四號候車室,這里通往深圳。機票變成火車票,被檢票處的小姐咬一個M型的牙印。室內空蕩蕩的,你還是發現了比你先到的三個候車人,一個老頭兒,一個少婦和她的小女孩。老頭抱著拐杖,把光亮亮的禿頭顯給你。小女孩在座椅上搖搖晃晃走來走去,少婦在欣賞她的杰作。你坐在一角,抽著煙,望著這些情景。
難得有這么清靜的一隅。
你擺脫了一個喧囂的所在,在更喧囂的地方擁有了此刻的寧靜。
這空間真好。
你剝開一個從西安帶來的橘子,吃著便想,把石頭背到山里而山里的石頭更昂貴。
使你驚奇的是一只麻雀從窗戶破洞里撞進來,很快又消失了。你看清了是一只麻雀,很灰。此處竟有這類野鳥?
從白云機場剛剛起飛的飛機,正擦過窗外的天幕。是剛才乘坐的那一架飛機又折回西安去的嗎?
你是一個獨旅人,和那禿頭老人一樣的獨旅人。你是此岸,那老人便是彼岸,在歲月之河上。那少婦是什么呢?那小女孩是什么呢?她們母女在各自的一個時間流程里相依相伴。
很快,這塊空間屬于更多趕路人了。
迷津
車抵深圳。你走出車站,又尋找新的一段路,尋找車。
沒有站牌,沒有見到開往西麗湖的車子。你辨不出東西南北,不知道你最終的目的地距此有多遠。
一群小男人圍住你,請乘坐的士,少則四十元,多則九十元。你感到莫名其妙的厭惡。問誰話吧,人家都挺忙,懶得理你。你終于掏一元錢買了一張定價四毛的游覽圖,多出六毛錢也沒問清如何去西麗湖。你再問另一個女人路,她不搭話茬,總問你有無“鋼崽”(港幣)。你去打公用電話,一個閑人收了你兩毛紙幣卻不兌你硬幣而替你撥通電話,他不再肯喂電話,電話餓死了。他送你走不遠便十分便當地搭上了去南頭的的士,說到那兒可換乘去西麗湖。你感激得遞他抽了兩支煙。
你迷失了。
到了西麗湖,你仍未醒來。霓虹燈已醒了。
歸宿
目的地,其實正如啟程時的房間,是一個歸宿的抵達。
從西麗湖去西麗湖的創作之家,這最后一程路也同樣等待你的尋覓。走了一程,在交叉路口打問一位小姐,她說走錯了,甚至是方向性的錯誤。這又朝回走。再問商亭主人,說天黑了,路有二公里遠,出一塊錢坐順車吧,怕路上有壞人。你攔住一輛車子,它不去創作之家。
家,歸宿,在天黑之后的異地感到很暖。
你又一次打通了電話,你等車來接。
你靜靜等著,鼻息里有濃烈的花香。順便看立在路旁的西麗湖全景圖,終于看清了你所立足的位置,過松樹山莊,再沿水上樂園桑拿浴按摩中心翻過山梁就是療養院。你想到聯絡地點,丙三樓,心悅苑,創作之家。
這便等不耐煩,拎上行囊,何懼路途漆黑,心里極有把握地奔向目的地。
已經是夜里八九點鐘了,行人幾乎沒有蹤影。偶爾,有刺眼的車燈戳來,隆隆從身邊駛過去。
你走著,走入一團漆黑的沉寂之中,獨自聽著自己的腳步聲。這時,你聽見自己的腳步聲被另一個人的腳步聲碰撞得雜亂起來。有車燈遠遠掃過頭頂。
“你是陜西來的嗎?”
“是呀!你是——”
“我是小毛,你姓和吧?”
當他一把抓過我手里的行囊時,我覺得是到家了。
“前邊有燈處就是我們的小樓。”他親切地說。
遠岸
從大陸腹地出發,逾越一千五百公里,尋找岸。
向南,向南。地圖上位于南海岸邊的城市,仍然遠離海。去海岸邊,仍然有好些站的旅路。
原來,旅者還是處于這一塊近海陸地的中腹。
終于可以望見海了,卻又可望而不可即。海是冥冥的,夢幻般的,迷蒙的,云里霧里,看不清海的面孔。若去海灘上,仍有三幾里地的路要走。
而眼中的海只能是海峽,對岸又是朦朧的海岸。就是最浩瀚的海域,也還有岸在守候旅人。
行駛于海上的船只,也不過是岸的一部分,充其量是漂泊著的岸。它一旦脫離海岸,就意味著去尋找岸的母體。
岸,如果存在的話,它是在難以企及的遠方。
西麗湖
客舍離岸尚遠,只好去看近處的湖,西麗湖。被陸地緊緊圍攏住的一個小海。
湖水很綠,綠得起了苔蘚,如同湖的綠衣;綠得快要化為陸地了。但細察去,仍是透明的,平滑的,柔軟的,把星斗和燈光含在了它的多情眼眸里。
迂曲的長廊,通往一個幽靜而寂寥的所在。酒樓是詭秘的,如同那詭秘的霓虹燈,如同濃妝艷抹的旅境中的小女人。鬧中有靜,靜中欲動,動靜相宜,便是這個度假村的情調。
別墅是一幢幢石壘的房子,白得莊重而潔雅,被樹林子一遮一掩,就接近了大自然的原始意味。連路徑,也是原生的石頭鋪設的。
湖在低處,山在高處。西麗塔在高處的高處,成為這個湖的標志。它直指蒼穹,夜間也燈火通亮地構成一個錐形,顯示其不舍晝夜的存在。
畢竟因為人為的痕跡,湖水靜得似不再流動,凝固了似的蕩漾不起勃發生命的景觀。
西麗湖,一個尚嫌冷落的小女人。
蛇口
海與陸地,交錯成一個蛇口狀的蛇口。
蛇口的地域極小,去處卻有一個“海上世界”。是一只大船泊在岸邊,登舷可以遠眺香港,入艙可以看到民俗展覽,走入一個豐富而稀奇的陸上世界。
在視線內的海峽上,據說曾有無數來自陸地的人們企望前去對岸的另一塊陸地,或被惡浪吞沒,或被海獸傷害,或被槍彈擊沉,總是海把他們送回到剛剛離別的灘頭。海不可冒犯,它會把你歸還給岸。
一個曾經荒涼瘠貧的灘頭,卻在幾年光景里變成一座潔雅華美的小城。這里的碼頭通往海上的各個碼頭,世界的船只可以在這里找到靠岸的位置了。
去問林則徐,打聽蛇口的歷史。林則徐正站在高高的山巔,被銅鑄為塑像,手持古老的望遠鏡,在對視遠處的海面。頭頂是冬日里烘得頭皮發燙的艷陽,衣襟被海風兜起,遠處海面上船只在悠然移動。
炮聲啞了,如同左炮臺上生銹的塑像般的鐵炮。古炮已成為文物,綠樹和蘆葦叢遮住了炮的視野。
炮聲響了,那是開山的炮聲。
安寧而充滿活力的小城,在當代中國的所謂試管里生長著。這小城是適人意的,遠不是它的名字“蛇口”那么令人恐懼。
海與陸在此握手,親吻。
旋轉餐廳
早早起來,趕到國貿大廈去吃早茶。
“吃早茶”一說,只有在這里才說得那么在行。但與其說是去吃什么早茶,不如說去吃五十多層摩天大廈之巔的風景。
電梯是露天的,使你感到怎么漸漸離開地面而升上浩渺的高空。地面上的景物在緩緩縮小,愈小愈使人的視野覽盡闊大的東西。走在地上的人會發現,你貼著樓壁在滑落,墜向無底的深空,作垂直狀。
坐在窗前,山變得低矮,山外邊的異域的樓群探出了頭向這面眺望。俯視腳下,人比螞蟻還小,眼里只是樓房的頂端和斜壁,或是一切景物的頂部。
地球在腳下輕輕旋轉起來,把它的這一角落的每一個側面都顯示出來。
你以為自己在遠距離俯視這座城市,以至是超然于塵世,其實是一種錯覺。你還在地面之上。這是你的喜劇。
石巖湖
過白芒海關,去石巖湖。就是那個在深圳地圖上宛如一只小鹿的石巖湖嗎?
這里是溫泉度假村,不見溫泉,但見一個仰成一張弓的裸體少女抖動松軟的秀發。這尊塑像,使人領略到“溫泉水滑洗凝脂”的適意。但這不是故土上的華清池,這少女不是楊貴妃,她完全是一個開放型的現代女性。
去騎馬吧,這里有賽馬場,一處人造的草原。顛動于馬背上的人,有一種征服的快感。而觀賞大汗淋漓的十幾匹棗紅馬卸卻鞍子解脫籠頭在沙地上打滾的情形,實在令人抖擻。馬的自由、奔放、灑脫和剽悍,讓人的氣質為之遜然。
去租一只摩托艇來,代替你有限的雙腳,再化陸地為湖面,讓凝固的東西流動起來,你也贏得了頃刻間的快慰。兜風也好,宣泄也好,世界總是在你的視線里飛動起來。
異國情趣的情人島,更招惹旅人。房子的外形,不再是你看慣了的模樣,一反常態便有了個性的價值。湖邊蘆草簇擁,草浪里有一頭牛在那里靜靜修行。旅人便站在橋上,倚著欄桿,將奇特的房子和那頭牛作為背景,留一張影給記憶收藏。唯獨不遇情人。
草坪上的野炊的灶臺,原始而現代,只是空空蕩蕩的像片廢墟,不見煙火升騰。路旁一位占卜人,是用占卜乞討。他會為旅人編織幸運,而他看來永遠擺脫不了的是不幸的蛛網。
后來初識一位女詩人。她說她無法戰勝孤獨,純真可以演變,孤獨是無法演變的。她是從石巖湖來的。
是的,人們為了逃避喧囂與寂寞,才去游歷一處風景的。美的風景可以使人陶醉,而醒來之后你依然是一個匆匆過客。
圣地
近海的灘頭曾是一處墳地,近處的海也是黃湯淤泥。墳地上會開出紅的黃的美麗的花,也就會營造起高雅的殿堂。
這座大學,在丑陋的廢墟上建造起來,闊綽而典雅,美麗得如同宮殿。它當是嶄新的,一個圣潔的現代的維納斯。
在校門口的浮雕上我看到了這位美神。她又從浮雕上走下來,踏進階梯教室,坐在寧靜的圖書館里。她在露天式禮堂里講演,在水池邊嬉戲,在草地上仰臥著看流云。
我慶幸這里的驕子們。沒有專職行政人員,沒有專職的清潔工、圖書管理員和伙夫,除了老師和學生還是老師和學生。他們當主人又當仆人,這兒是知識的王國。
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的土地,也養育智慧之樹。
太陽下的傾斜的石座,呈圓形,將它的角度顯示給流動的日子。有子丑寅卯的刻度,軸心是一個圓柱,太陽便把陰影透過圓柱印在時辰的刻度之上。
這是新生命在對古老的一種膜拜。因為文化的根很深,深扎在五千年的時間的土壤里。古老卻不等同于陳腐。
她愈來愈神圣起來。
沙頭角
長不足里,寬不盈丈,一個遠近聞名的小街。以街心為界,東邊是中國管轄區,西邊則仍由港英管轄。只需一步,就跨越了一道無形的界墻。
既然是同一條街,就沒有了大的區別。房舍、商品、人的模樣,以及語言,看不出有什么懸殊來。
而交融和流通是悄悄進行的。如同血液,也如同這里的陽光、空氣。
被譽為“購物天堂”,卻也無物可購。金店是開給巨商豪富的,衣褲也動輒幾百上千元一件。大多觀光者在此慨嘆不已,實質上皆屬下等人、窮人一類,包括我自己。你去買點廉價的低檔貨吧,你的經濟人格在約束你不可奢望。
沙頭角,沒什么便宜可占。
一個富有誘惑力的令人失望的小街。
彼此在同化著,彼此在縮短距離,街這邊與街那邊,街里和街外。甚至于沿海與內陸。大循環的時代,使每一個人變成某種帶有同化元素的分子。
海風吹過來,滲入泥土。
沙頭角照樣有名氣,許多人談起它都那么眉飛色舞,煞有介事似的。
平安夜
客居別墅式的療養院,平和而安寧。卻在圣誕節的晚上,一個人怎么也坐不在房間里了。人類善于群居的本能,在撩撥獨居者去尋找熱鬧。這便沿著小路,去燈火通亮的度假村去湊興。
圣誕老人到處都可以碰到。他老人家返老還童似的在那里樂呵呵地微笑著。繁麗繽紛的彩帶縈繞著,輕歌曼舞在酒樓上醉著。唯獨他一個觀光者,默默徘徊于這異地的游樂場之外。
他找一塊草坪坐下,默默吸煙。草坪略帶潮意,很舒坦。對對戀人,從旁邊吻抱嬉鬧著走過去。爆竹聲,依稀如夢,時斷時續。
他去商場轉悠,買了一個剃須刀。他想到了獨居者不善儀表的雜亂的胡子。有靚女在窺視他,他倒先避開那銷魂的目光。
恰巧遇上友人,一起坐在酒樓。一個狗肉煲,一個包米羹,啤酒,火腿,花一百多元消受這平安夜。然后送朋友去巴士站,坐在冰冷的椅上候車,然后拜拜招手再見。
當他回到客舍,電視里也正過圣誕節的平安夜。他仍是旁觀者,與屏幕上的人兒不能交流。平,為安。客心則夜不成寐了。
水土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人的空間的遷移,無非是水土有別。不同的水,不同的土,養育不同的植物和動物,養育外在內在各異的人。這便有了地域之界,人際間有了鄉黨的稱謂。
我把舊有的生存環境丟在了1500公里外的西北方,獨獨地生活在這異域的土地上。腸胃沒有感到不服于水土,但情緒上總還不是味道。是的,房間極舒適。空調、熱水器淋浴、電視、電話、席夢思軟床,應有的都似乎有了。吃的是山珍海味,很可口。缺少什么呢?
缺少以往的水土。
水土是中國槐,走時已落盡霜葉,疏疏離離的了。這里仍一如春天,花繁葉茂,每一株草木都那么有汁氣,綠鮮得如同假飾似的。感覺上不是滋味的,是晚飯后聽南方人一一講解苑里花草樹木的名稱,什么牛蹄樹,什么三角梅,什么瀟湘竹。幾乎認不出幾種草木的我,記起了黃土高原上所熟識的每一種植物。
尤其是因水土而造成的人所發出的聲音的迥異,使我大為迷惑。這西麗湖,他們說成“賽萊屋”,幾乎每一單詞都同你的猜想相去甚遠,外語一樣需要翻譯。如入異國,我成了“老外”。回房間打開電視,中央臺竟奇跡般播放秦腔《卓文君》唱段,是戴春榮的拿手戲,隨后她又唱一曲陜北民歌《趕牲靈》。我擰大音量,覺得這是專門為我而唱的。
水土又不只是口音,甚至是一種心態。在我熟識的那座古都市,是不敢奢望較長時間有這般吃住條件的,但我有時痛感到這不是獎賞而是一種懲罰。我知道我的性情,平和沉穩的時候多,喜歡冒險的時候總是少一些。總說漂泊好,真正上了旅路就生出鄉愁的惆悵,尤其是獨旅。我也知道,這樣是保守的,是沒有出息的。
因為太留戀屬于自己的水土了。
香蕉園
香蕉園,在我想來是一個極妙的所在。
早餐罷,同伙的幾位老人說要去看香蕉園,就一路溜達著前往。先是寬寬的沙粒路,路邊的大坡被水沖刷為溝岔梁峁,酷似黃土高原的鳥瞰式地貌。
怎么,一聯想便是鄉土?
隨老人們的腳步走,路折入一條茅草間的小徑。小徑之小,僅僅可以容得一雙腳板。徑旁的草繡得實實的,高高的,呈蒼黃色。茅草又高了起來,直沒頭頂,白色的蘆絮在飄搖著歲月的白發。
然后是一個小石橋,跨過去又拐上了沙粒路。香蕉園,就藏在前面的凹地里。黃黃的寬大的葉子,碩肥的枝干,又似乎不是樹林子,而頂多是一片莊稼地。這印象,使“園”的感覺變得很通俗。
喚一聲小老板,香蕉園的主人卻在揚著縛有薄膜的長桿子在放鴨子。嘎嘎的一片叫聲,擊碎了池塘的平靜,也擊碎了香蕉園的雅致。小老板人小,年紀不過二十歲,著牛仔服,很機靈。他回屋棚子找了把小鋼鋸條,帶我們鉆入園子。
香蕉是倒掛在樹上的。這一點,使許多北方人為之驚異。園內有菜畦里的那種畦,泥干得板結了,低處是長毛的綠水。大伙瞅準一串子,小老板就使鋸條幾下子切斷牛角粗的蒂,斷處就滴下綠白的汁液來。我看著腳下一個發黑的有六七圈年輪的樹樁子,用腳一碰,斷處就噴泉似的冒水。
我獨自拐到一處,想摘下一串來,卻怎么也折不斷。最后將蒂撕裂了,弄兩手汁液,才使果子脫離母體。拿出屋棚一稱,有近二十斤,值八元錢。
拎在手里的香蕉可望而不可食,青黃青黃的。園主人說,放好幾天才能吃,最好多曬曬太陽。
割草
窗外的風聲在草木間流動,聽去是淅淅瀝瀝的雨在響。陽光把窗欞黑黑地畫在粉色的窗簾子上,怎么會疑風為雨呢?
有一種聲音,有節奏地忽輕忽重地出現在屋外。嚓、嚓、嚓。短暫,輕快而有力。是磨刀聲,不像。是敲擊聲,也不像。忽近忽遠,忽隱忽現,在簌簌的風聲里神秘地打著節拍,使流動的時間有一個類似秒針響動般的刻度。
打開窗簾,什么也沒有。坐下來,又是那聲音在誘惑你的心境。生活里常有一些小誘惑,使你有發現的渴望和醒悟。這便索性走出房間,站到庭院里捕捉這聲響的策源地。
聲音是從閣樓背后的小山包上傳來的。但還是看不到什么。扮一個捉蟋蟀或知了或螞蚱或蜻蜓的小頑童,躡手躡足地貼墻根繞到后山去。
先是看見了樹杈上掛的紅衣衫,繼而看清了制造神秘聲音的割草者。他傾著身子,雙手執一把彎刀。從背后看,他先將彎刀從右邊揮向背后,稍一停頓,然后迅猛地向左擂去,彎刀已停頓在左邊背后。那聲音,在這之間便完成了。
他在重復畫一個圓。一個圈便發出一個聲音。
他是國內的花匠嗎?割去茅草,栽起花木,需要草坪卻不需要茅草。要人為而不要野生。
在家鄉,用鐮割麥子也是這姿勢,坡地里撒谷種也是這姿勢。播種和收獲都在畫一個圓圈。這是輪回嗎?
似乎,輪回即一切。
回到屋里,仍被這割草聲纏繞著,只好與它且作冥冥的交談。
《海南日報》 1989年至1990年連載
客湖札記
重返是一種發現
我記憶中的諺語里有一句話說:“人一輩子,不走的路都要走三回。”當我又一次遠離故都南下至海南島謀事,又輾轉廣州至深圳欲求一個下榻之處時,想到的便是西麗湖。
又見西麗湖,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三年前曾在此寄居過一個月的時光,優美而孤寂,是消閑,也是自囚于斗室承受勞作之役。離開時卻是難耐的留戀,覺得此地已遺落了自己生命的一些日子,將在以后會不時想到這里。但不想奢望會有可能重返這里,完善人生樂園的祈望。
然而,時間之流水與空間之蒼茫多么奇妙,我又見西麗湖,在這夏日的陽光下。我的腳印如果有氣味的話,今與昔的腳步會重疊在一起,是在撿回自己的腳印,還是重訪往日的一草一木?人生會有多少機會,去沿著已經走過的路重新走一遭?緣分,是命運的同義詞。
想著這一層意思,西麗湖便熱切而惆悵起來。我像是重返家園,但因為不能永駐于此,就有了過客的感傷。因為重返的種種美麗的情景會成為記憶,就覺得正在享受的近似羅曼蒂克式的別墅生活亦真亦幻。難道這是夢的一段故事?
但這的確是真實的,腳步把石橋踩出響聲,綠湖上刮過的風舒暢地拂著臉面。西麗湖的雨,常是這么在朗朗晴日匆匆掠過,清新而酣美。而夜晚出奇地靜,除了林木間的風聲便是蟲鳴,仙境一樣令人神往。我明白了,重返不是重復,而是一種發現。
消閑的馬兒
我想,遠離深圳鬧市的西麗湖,該是一片靜謐安適的樂土。在沉寂與祥和的氛圍中,除了鳥的鳴唱,便是不時響起的馬蹄的達達聲。站到陽臺上去,發現馬蹄聲是從湖那邊的山林下傳來的。由于樹林和草叢的掩遮,僅可以看見攢動的馭手在貓腰前行,呈現波浪式起伏的身影。山路是彎曲的,穿過樹林與小橋,圍著湖水盤旋著。這使得閑適的山水間,多了傳奇似的神秘和美妙。
馬匹來自距這里三里地的馬場,那里是賽馬人的營地,是訓練騎術的課堂。有容納幾十匹馬的馬廄,有賽馬場,但幾乎沒有看臺。從現代都市來此度假的青春熱血男兒,也有善獵奇的女性,租一匹馬,就可以讓現代風度在馬背上在山水間疾馳。我不懂馬種,只知道馬匹個個高大剽悍,在我看來既駿烈又令人懼怕。
這西麗湖的風景同駿馬奔馳的情形一樣,已超越人類太功利的實際意義,完全變成一種消閑的享受。馬匹不再為重負而流汗,馭手也不是在履行生活的勞務,山也不只是為長木材,水也不僅為了澆地養魚。一切都變為詩畫和美學,由物質升華為精神的存在物。
當然,勞作并不可少,沒有勞作就沒有這一切。我多么想放下手頭的文字工作,擁有一匹心愛的馬,游歷于藍天白云與青山綠水之間。馬與我一樣平等,彼此給予生命活力的享受,彼此需要,彼此獲得存在的快樂。而別墅背后的麒麟山也是一匹馬,是我愛戀的山湖標識。
小葉桉林子
時別三年,我的桉樹林子還認識我嗎?曾經客居這里,不止一回探望過你,觸摸過你,以后的日子里惦記著你。每與他人提及樹木,我總記起你的模樣,你在我心中美麗地生長著,你是我所稱道的最美最出色的樹種。我想,你的潔白頎長的軀干認識我,新發的枝葉也會認識我,就連高枝上的鳥巢及巢中的精靈也會感知我的歸來。
黃昏,我從西麗湖邊走過,又來探訪你的處所。途經時我被你牽引住目光,總嫌過于匆匆。現在,我走近了你,你走進了我,我走入了你的叢中變成了你族類的一分子,你走入了我的體內。桉樹,小葉子如眉的桉樹,枝條柔軟修長的桉樹,尤其是軀干潔麗細膩的桉樹,如同一群裸身的少女聚在一起亭亭玉立,占盡風流。
我的掌心頓時感知到你的體溫,不熱也不涼,滑膩而又耐摸,似乎不是木質屬性,而是人類肌膚的質地。無枝杈無疤痕,就這么光潔地伸延到高處去。你已愈合了傷疤,把臺風折斷枝干的經歷包藏起來,留給人間的是無缺憾的完美。也會有石質的觸覺,是飽含生命的石,渾圓而健康,玉柱一樣挺拔。
如此風景,已超越樹族進入人體美學的空間。其中雜有的粗糙皮膚的桉樹的同類,是別的樹種,還是性別的原因,請恕我植物學的無知。我也不想深究桉樹的實用價值,木質如何,我只是贊嘆她美的形象。
我走遍了天涯海角,還未遇到過第二處類似的仙境。現在,桉樹就在我的四周簇擁著我,陶冶著我的性靈,我感覺極好。
星光槳聲及白椅
夜半,月亮沒有上來,滿天星斗掉進了湖里,湖水仍幽幽地沉郁。我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從客舍走出來,穿過蘆葦蕩邊的小石橋,站在這湖邊的碼頭上。寬闊的湖水在夜風的揉搓下,向我彌漫過來,像要接納了我融化了我。那樣,魚兒便是我嗎?
碼頭其實只是座亭子,亭邊泊了幾條龍形的小木舟。夜里有誰會來光顧,燈光這么燦燦地照亮著碼頭。不是去擺渡,這里既是此岸亦是彼岸,從這里啟程又會回到此地。但我還是駕動小木舟,劃起槳板,借了翅膀似的這邊劃幾槳那邊劃幾槳,我的龍舟便棄岸滑入湖心。我不再是處于陸地之上,我完全置身清涼的液體中了。郁結的心情一旦交付水汁,就不再干渴枯燥。
湖面一片銀灰色,很薄,很透明,但任你怎么也劃不透它。山影與樹叢使不遠處的湖水變得又黑又綠,使我恐懼,甚至不寒而栗。可我還是劃入了黑湖的領域,以為完全掉入了深洞,其實仍然在平滑的湖面上。即是如此,星星仍無處不在。我撈不上來它,它不斷碎在槳板與玉液之間。
我突然發現近處泊著一艘巨船,在漂搖著,朝我靠過來。船上的桅桿怎么長了枝葉,綠帆一樣拂動。原來是湖中的孤島。它也孤獨嗎?島上有一把雙人座的石椅,白天在陽光下非常醒目,因為周圍皆是綠草碧波。我繞島一周,未找見那把白椅。我想歸去,卻又丟失了碼頭,就這么信然漂流于夜湖上。月亮還沒有從湖底浮上來。
小石橋通往何處
腳下的拱形小石橋,看來只是供人視覺的一處風景,有山必有水,有水必有舟必有橋,這是園林藝術的正規思維。它并不通往什么地方,極少被納入路的范疇,最多也是游覽者駐足的一處景點。我踏上小石橋,也做一番倚欄遠眺或凝思的古詩詞里的好夢,觀遠天落霞片片,湖光樹影,低頭可見魚兒張了嘴巴在湖水中呼吸。橋頭另一端,一位老人也在扶欄觀魚。
走到小石橋一端,有藩籬織成網字,攔住去路。有側身可以穿過的縫隙,走進一片橘園里去。曾記得在橘園中吃過鮮橘,橘的顏色和形狀足可以燃燒美的欲望,且不說其味道如何甘甜了。現在是七月,不是橘熟季節,枝上空空的,是橘樹將青皮的橘果掩了起來,不忍將羞澀和生酸的感覺流露給人們。
橘園封閉著,是為了一年一度的成熟,是為了積蓄一次豐碩的開園典禮。那時,藩籬會拆除,小石橋一過就進了橘園,黃亮亮的橘子就會跨過小石橋走入市場,走入果盤,走入一個個暖暖的圓圓的微笑和愜意中去。空寂的橋頭,冷寞的石階,此刻顯出的是一片嶄新的歷史痕跡,其文化意味也十分的牽強。
湖面開始暗淡下來,小石橋的白色正被夜的風一縷縷剝蝕了去。那位老人沒有了蹤影,他獨自一人此刻又會在做什么?他孤寂嗎?他的魚兒也潛入了湖底,湖波皺紋縱橫,默無聲息。我駐足于老人剛才觀魚的位置,低下頭,脊背高高地拱起,感到了不再年輕的悲哀恰似浩浩湖水。
死蛇與逃命的蚯蚓
與友人漫步于長長的沿湖小道上,心情完全是閑適的。橘黃色的路燈已經亮了,像被高高擎著的燭臺,燭焰且包在橢圓的玻璃殼子里。典雅而悠然的情調,被腳下的一條蛇倏地趕跑了。
原來是條死蛇,準確地說是條奄奄一息的蛇。適才前邊飛馳過一輛小車,看來肇事者不會是別人。應該說是這條可憐的蛇倒了大霉,怎么會料到這個時分它會撞上致命的一擊呢?這許是所謂的命運。它早一點或晚一點穿過小道,也就不會發生這般的慘案。
太有自然歸屬的蛇,也會在現代旅游業的興盛中遇到麻煩,以至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喪生。許多事情的偶然性,往往帶著必然的成分,在人們驚嘆之余想起來也不過如此而已。蛇將它的斑紋印在輪胎上,也許不會有血,但用現代手段一定會查到肇事的車上有關這條蛇的氣味。但誰不是無辜的呢?
友人很想走近去看看蛇的慘狀,甚至想用樹枝去逗它,但終沒有走近前去。友人怕蛇,又從未見到過蛇,第一次見到蛇原來是這般死樣兒。可以看見蛇身挽成一個環兒,痛苦地掙扎著。它的肚子吃得很飽,比頭尾粗出好多。趁蛇之危,腹中的食物開始逃脫蛇的扼殺,在蠕動著爬出尾部。是些小的蚯蚓,慢慢離開現場。
一個生命包裹了另一些生命,蛇的臨死換取了蚯蚓類的再生。這種生命現象,簡直令人感嘆。第二天,友人突然提及去看那條蛇是死了還是活著跑掉了,那條蛇令人惦記也該幸福。盡管后來的肇事現場還保留著,死蛇的皮已干了薄了。殺死蛇的人,也許對此一無所知。
夢生榕樹下
三岔路口有一棵渾圓的榕樹,三角形的草坪僅僅擁有這一棵樹,巨大而精致,像是奇妙的盆景。三條白色石凳,長長的,相向而設,在這路口如同恬靜的驛站,供旅人小憩。
我與友人是在午飯后路過這里的,不約而同地從烈日下躲到這方陰涼里去。我們每人一條長石凳坐下,頓覺涼風習習,爽徹肌骨。我想,如果有三人行,每人坐一條石凳相向而視,是很和諧的一個圖案的形式。
在綠色的陰涼里,我們相視無語,然后目光投向頭頂的樹冠。這么,我索性躺在白色長條凳上,仰面朝上,臥成一個一字,把手掌交叉起來枕在頭下。我看見每一片葉子在瑟瑟顫動,有風兒在葉片間輕聲吟唱。一只無名的小鳥在枝葉間跳動,準確地說,是匆匆穿過,不知忙活什么。一只彩蝶也從烈日下飛來,浸入了陰涼里。
我發現面對的樹冠嚴嚴實實罩住了陽光,驀地有幾支銀針似的光線落下來。樹葉顯然正在換季,一邊長出新葉,一邊凋落舊葉,交替中有黃的成熟與綠的生鮮。不時有落葉飄忽而下,原來草坪已有薄薄一層落葉。正是夏日,這種現象已完全沒有了季節的概念。
好多年沒有這番閑情了,久違了的是故鄉夏日的柿樹或槐樹陰涼。而天空是沒有區別的。坐地日行八萬里,土地之上的空間豈能有故鄉與異鄉之別?我漸漸遁入夢境,一切均虛冥起來。等我醒來,落葉滿身,旁邊的石凳空著。友人不知何時離開樹蔭下,周遭一片寂靜。我渴望陽光,亦渴望一種庇護,是么?
路就是日子
從客舍的盒子里鉆出,熾烈的陽光令人有輝煌的畏懼。走過草坪,走過天鵝湖上的小石橋,走過長長的林蔭馬路,站在丁字路口等待代步的活物。有單騎摩托飛馳而過,見是戴盔的小伙子,只需“打的”一樣伸胳膊攔它,單騎會戛然而止,花三元錢便可以抵達巴士站。
如果趕巧了,半小時一趟的巴士會在最佳時間專門等你似的,抬腳就跨入一個冷氣庫。你被載著前行,變成會動的冰箱,不過是適溫的冰箱。它越過樹林山湖,在高速公路上加入滾動著的鋼鐵的隊伍。你閉目養神,等睜開眼已置身高樓大廈的峽谷。
這座年輕的城市,除了水泥鋼鐵的奇峰,就是人群和車輛。不過,這城市的人群亦很年輕,極少可以碰見老人。它的生命活力,似乎把自然規則帶給人類的衰老拋得很遠。它很優越,優越得使你感到自己已經老了,起碼不再年輕。另外,你是過客,很失意又很真誠。
你捉不住飛快的“的士”,你坐中巴或大巴,不知方位,勢必要走很多冤枉路。心理的盲目,使你所辦的事情所干的活兒拘謹而匆忙,有時也很狼狽。你匆匆趕路,直趕到離開這座城市的那天。這么,又依照慣例去火車站趕回程的巴士,機械而忙碌。
在天色漸漸向晚的變化中,你乘巴士回歸郊外的寓所。畢了,在鎮上排檔吃點東西果腹,再去找單騎摩托回你下榻的天鵝湖邊。這完全是一個程序,回想起來,這一天起碼有一半時間在趕路。因為,你是永遠的旅人,路,始終與你非常親近,沒路就沒有了你的日子。
新生命的明證
曾經是茫然地尋找西麗湖的方位,在深圳火車站扮演一個漂泊者的角色。那天傍晚,乘車至南頭,再換乘到西麗湖的車,末了還要走幾里路才抵達歸宿。而重返的心情是坦然的,不需問路,路在記憶里鋪設著,只需去丈量它,去體味它就行。當你去深入考察本來以為熟識了的事物時,便親情倍增。
這次是直接乘中巴到西麗湖的,西麗湖如果有情,會波光瀲滟著期待我的目光。景物如舊,這石鋪的山路,這店鋪,這塔影,這如黛的山麓,只是度假村的主要建筑拆了重蓋,一條寬闊的大道正在鋪設。石筑的小室在山湖間錯落有致,許是物是人非。有何人如我屬于夢中的重返者,西麗湖的故人呢?
強臺風在前幾天從近海的地方登陸,無情地襲擊過西麗湖。眼中的樹木斷枝損葉,甚至被攔腰折斷,風和陽光正在撫摸傷口。山間的泥沙曾順洪水而下,淤塞了潔凈的石鋪小道。此刻,陽光熾熱,我同第一次來此的友人在汗流浹背地趕路。在一棵菠蘿蜜樹下,我們躲避陽光,小憩于綠蓁蓁的陰涼里。歇腳的意味,真是情趣無窮。
我優越于心境上的訪舊,友人則獨享浪游的新鮮。我帶著友人走過我寄居過的心悅苑小樓,室內已換了多少主人?過小橋,走近創作之家樓舍,我把它當成家園。有人騎摩托過來,我們幾乎同時喚出對方的稱呼。他是小毛,當初在夜路上接我的小毛,我們已經三年未謀面了。他說,他的兒子已經兩歲多了。
一個新生命,正好是歲月的明證。
《美文》 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