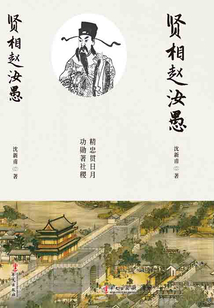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一
顏劍明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變,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隨后的宋室南渡開啟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人口大遷移、經濟大轉移、文化大融合。北方人口浩浩蕩蕩,數以十萬計地南遷,王公貴胄隨扈而來,士族百工紛紛擇地卜居,運河兩岸成為他們最佳的選擇之地,駙馬濮鳳善相風水,見幽湖遍地梧桐,聯想起“鳳凰非梧桐不棲”的古語,便決計定居下來,后來果然應驗,子孫繁衍,終成濮院巨鎮。施州刺史張子修、迪功郎張汝昌選擇了運河要沖石門灣,建東園、西園,日日流觴曲水,載酒吟詩,好不逍遙自在。伴駕的侍郎官顏歧也率子孫卜居于石門北面的白馬塘畔(今浙江省桐鄉市石門鎮民聯村蔣庵),為牢記自己是孔子大弟子顏回的后裔,繼承先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安貧樂道精神,將聚居的地方稱作“陋巷村”。
而宋朝宗室趙不求、趙善應父子則選擇了相對偏僻的水網地帶洲泉作為卜居之地。數十年后,趙善應之子趙汝愚科場奪魁,高中狀元郎(一說是探花郎),后又步步高升,位居右丞相,從此地以人而顯,洲泉的名聲扶搖直上。洲泉雅稱湘溪即源于此,湘溪原是寫作相溪的。
趙汝愚出生在洲泉,屬于南渡臣子的“官二代”。生賢里就是他出生的地方,這地名沿用至今。趙汝愚少有大志,曾說:“大丈夫留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考取狀元(一說探花)后,先后在秘書省和信州、臺州、福州、成都等地為官,宋孝宗對他頗為器重,謂其有文武之才。宋光宗即位后,對他也不薄,升他為敷文閣學士,后升任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1194),宮廷內發生了一件讓常人無法理解的事情,太上皇孝宗駕崩,身為兒子的當朝皇帝光宗因與父皇有隙,竟做出了有悖于封建禮教、有違于倫理綱常、讓滿朝文武驚訝不已的舉動來,居然稱病不出,死活不肯執喪禮祭奠。兩宮不相往來,大臣們屢次上奏,光宗就是不答復,遷延多日,朝野人心浮動,影響極壞。而此時的丞相留正,是個老滑頭,不想得罪人,竟稱病告老還鄉了,頓時朝中無人,群龍無首。身為吏部尚書的趙汝愚挺身而出,數次上奏太后,請求廢黜光宗,擁立其子嘉王趙擴繼承大統。嘉王自然是固辭不受,趙汝愚進言:“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嘉王于是登基,是為寧宗,改年號為慶元。
皇帝的廢與立,歷來是地動山搖的事,臣子一般退避三舍,是不肯去蹚這攤渾水的,因為風險實在太大,十有八九要背黑鍋,要冒殺頭的危險。但趙汝愚以國事為重,挺身而出,敢于擔當,不計個人安危得失,在關鍵時刻當機立斷,作出了明智的決斷。這是趙汝愚一生中最出彩的一筆,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績,是永留史冊的。他罷相后,朝野公憤,國子監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太府丞呂祖儉和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十多人聯名上書寧宗,替他打抱不平,說趙“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日月”。他死后,被謚以“忠定”二字,依據便是他擁立寧宗的功績。《謚法》云:“慮國忘家曰忠,大慮靜民曰定;善則推君曰忠,純行不爽曰定。”仔細推敲他這個驚人之舉,應該稱得上“忠定”二字的。
趙汝愚是一個值得后人細細研究的人,他是桐鄉歷史上唯一出生于桐鄉的狀元郎(一說探花郎),也是桐鄉歷史上唯一的丞相,科場上春風得意、獨占鰲頭,政壇上叱咤風云、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迄今為止,在桐鄉還沒有第二人,以后也恐難有人與他并駕齊驅。無論是作為讀書人,還是為官者,他都達到了巔峰,令后人望塵莫及。但就是這樣一個聲名顯赫的人,洲泉作為他的出生之地,桐鄉作為他的故里,800余年來,沒有人對他進行過較為詳細的研究,地方史志的記載簡而又簡,而且大同小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洲泉南郊鄉下,有位叫沈新甫的文化人,自幼喜愛文學,退休后仍筆耕不輟,對附近的歷史名人多有研究,前幾年《一代名醫金子久》已付梓,去年又寫了《賢相趙汝愚》,均是二十余萬字的長篇,堪稱填補空白之作。《賢相趙汝愚》系統完整地記錄了趙汝愚寵辱皆歷、大起大落的一生。
我與沈老師十余年前就認識,那時他還在永秀小學教書,我曾參與編撰《洲泉鎮志》,共同的愛好讓我們有機會聚談過幾次。這次他寫完《賢相趙汝愚》,即發來電子稿,我得以先睹為快。他又要我在書前寫幾句話,即所謂的序。現在似有一種風氣,序言好像都是由領導來寫的。我坦言以告,沈老師卻再三要我寫幾句,我于是又想,從前古人寫書,序一般由志同道合的朋友來寫。我與沈老師都喜愛鄉土文史,也算志同道合。這樣一想,也就覺得順理成章、心安理得了,是為序。
2018年1月
(作者系桐鄉市作家協會秘書長、《桐鄉文藝》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