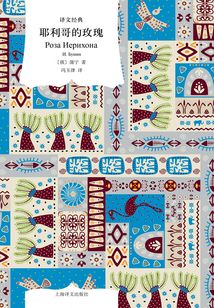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南游印象
“走哥薩克的路”
“啊,我的德聶伯河,
我的德聶伯·斯拉武季奇[1]!
你流經波洛韋次人[2]的土地,
你穿越重重石頭的山嶺!”
——《伊戈爾遠征記》[3]
一
我在海鷗號船上的一次航程使人終生難忘!這是我青年時代也是一生中的第一次旅行。后來,我曾經多次在世界各地漫游,卻沒有一次行程能夠像游覽俄羅斯南方這些短短的日子那樣,在我的心靈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對這次旅游,我早就開始醞釀。那時,我正在念中學,當然只有在夏天才有一點自由支配的時間。不過,為趕路所做的準備工作似乎早在一月份便開始了。我花了好幾個晚上來研究南方的地圖,確定旅行的路線,計算路上所需的費用,最后,還費了不少口舌,來說服母親讓我一個人出門。我的態度十分堅決、認真,終于迫使她同意了。當然,如果她事先知道我要去闖險灘的話,那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我走的!
不過,當時我對她說,我將沿著德聶伯河走一趟,到了險灘那兒就止步,這話也沒有騙她。此前,我讀過不少有關小俄羅斯、有關查波洛什人[4]營地的書,經常想象著德聶伯河上的險灘激流,以及“走哥薩克的路”、在旋渦中冒險穿行的情景,但我根本沒有指望在這年夏天會目睹這種場面。我在路上甚至忘掉了險灘。我的注意力完全被陌生的景色和不同類型的陌生人——小俄羅斯人所吸引了。在從庫爾斯克到基輔的火車車廂里,我或是連續幾個小時望著窗外,或是認真地聽著南方人那種溫柔的口音,觀察他們的臉龐。
打從第一眼起,我就喜歡上了烏克蘭人,并且一下便發現了大俄羅斯莊稼漢和烏克蘭人之間的巨大差別。我們的莊稼漢大都疲憊不堪,穿著滿是窟窿的厚呢上衣,腳上套著樹皮鞋,裹起包腳布,面容瘦削,頭發蓬亂。而烏克蘭人卻予人一種愉快的印象:身材高大,體魄健康結實,目光安詳而又溫柔,穿著干干凈凈的新衣服……而過了庫爾斯克,那地方的風光也是令人賞心悅目的:一大片平原延伸得好遠好遠,簡直讓我們中部和北部省份的居民無法想象。遠方點綴著座座瓦藍瓦藍的土岡,以及田莊中挺拔的白楊樹剪影。
由于被這些美麗景色所吸引,我在去基輔的路上耽擱了很久。過了普季夫利城,即那座當年雅羅斯拉芙娜于“早霞升起的時分”在城墻上為伊戈爾悲啼[5]的古老的普季夫利城,我就下火車,決定步行幾天。我把行李托運掉,把手槍留在身邊,只想毫無牽掛地實現自己的心愿。在那時,我萌生了一種只身一人留在草原上、徒步旅行的熱望。雖說那里離車站還不遠,以便能夠儲備食品,但畢竟是在廣袤平坦的草原上,一個人整日待在青天之下!
天氣,似乎有心助我似的,格外晴朗。每日天亮的時間越來越早。而在我的記憶中,這些日子就像一場明朗、溫暖的夢。當時適逢六月初,是一年中最舒適的季節。中午的時候,陽光從來沒有像在這個季節的那樣燦爛,大自然也從來沒有像在這個季節那樣充溢著幸福和歡樂的氣息;在熱氣騰騰的、塵土彌漫的路上邁步,在淹沒于紋絲不動的黑麥、燕麥和大麥中的田間土埂上穿行,我臉上感受到一股似乎來自篝火的熱氣,鼻子聞到一股草原植物——曬熱的花草散發出的芬芳,心里別提有多舒暢。而此刻,在頭頂上方回蕩著無數昆蟲用千百種聲調奏起的空中音樂,它們歌頌著六月中午的草原的歡樂生活,歌頌著沐浴在耀眼的陽光之中的無邊無際的遠方土地……
在離基輔約一百俄里的地方,我再次乘上火車。我記得,那時太陽已經偏西了,火車疾馳在德聶伯河邊的森林之中。突然,聞到空氣中有一股奇妙的清香,我朝窗外一望,心頭一陣喜悅,猛地顫動起來:在我的眼前展現出藍瑩瑩一片,那是森林、草地和遠處的山嶺——到了德聶伯河谷地啦!
“這是什么香氣啊?”我問坐在旁邊的人。
“噢!”他笑著說,“這是難得聞到的香氣!是德聶伯河春汛之后剛露出水面的小島上那些橡樹的綠蔭和柳樹枝散發出來的香氣。”
不知為什么,我在當時覺得他說的話挺有詩意。火車正在下坡,走得越來越快。站在窗前,溫煦的和風撲面而來,送來陣陣清香,令人陶醉。谷地披著金燦燦的夕陽余暉,越來越開闊地展現在眼前。然后,突然出現一片晶藍,這就是漲潮中的德聶伯河。在河那一頭的高山上,在火車的前方,基輔城里大小教堂的金十字架熠熠發亮。我們坐的列車正在穿越德聶伯河上的大橋,車廂下的輪子隆隆作響。橋拱的長廊那一根根梁柱從我的眼前飛閃而過,就在那一段時間里,火車好像在鐵籠子里奔馳。
“基輔!”我聽到周圍的人在說,“感謝上帝,我們總算平安到達!”
二
我的心愿終于實現了。我真的到了小俄羅斯,在德聶伯河上,而且站在海鷗號的甲板上,參加長途航行,這其間還要“走哥薩克的路”,去闖險灘!
我能搭乘上這條船完全是靠運氣,由于偶然碰到一位遠親,得到了他的幫助。他住在基輔,正在搜集有關小俄羅斯歷史的資料。
“既然您對德聶伯河那樣感興趣,”他對我說,“那我就安排您乘‘海鷗’去跑一次,一直到達亞歷山大羅夫斯克。您愿意嗎?”
“‘海鷗’是什么?”我好奇地反問。
這個瘦骨嶙峋的小老頭透過眼鏡狡黠地朝我斜視了一眼,輕聲笑了起來。
“那可不是鳥兒,”他帶著鼻音說,“那是運送木材的船。換句話說,那只是一條滿載木柴的平底貨船!”
說實話,我聽了挺失望。我想象中的海鷗號應該是艘漂漂亮亮的白輪船,扯著雪白的風帆。結果卻是一條裝木柴的平底貨船!
“是的,”這位年邁的學者再次肯定,“這是我認識的一位猶太人的貨船,是他給船取了個‘海鷗號’的名字。當然,這挺蠢,可是有什么辦法呢!您只好乘上它,慢慢地航行,不過您可以穿過險灘,倘若乘一般的輪船,闖險灘是辦不到的;你還可以親眼見到真正的查波洛什人的后代——那些引航員,他們能把海鷗號從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城一直領航到霍爾季察島,那個島過去也曾經是哥薩克的地盤。這樣,我想,您總可以在海鷗號上將就一下了……”
我趕快向他道謝,表示接受他的建議。說真的,后來我也沒有為此感到后悔,要知道我不僅在海鷗號上將就過去了,而且還對它產生了感情,離開它時真有點依依不舍。
我們的航行又安寧,又愉快!船上的乘員共計十一位,除了八名白俄羅斯槳手,還有猶太老頭本人、他的侄兒和我。白俄羅斯人幾乎整天站著,擺弄著長長的木槳。年輕的伊利亞·伊薩依奇躺在甲板上,大部分時間都在讀通俗小說,而伊薩依·馬爾科維奇,這個辦事非常認真的胖子,整日忙于算賬、祈禱和進餐,總是坐在他的船艙里。這樣,我便無拘無束,可以盡情地欣賞德聶伯河的壯麗景色了。
每當霞光初升,從寬闊的河面、從一望無際的河岸和藍瑩瑩的遠方總會吹來一陣陣令人精神抖擻的清風,送來一陣陣濕潤的芬芳——那是橡樹綠蔭所發出的濃郁的香氣,以至使人覺得每一次呼吸都會給人增添青春和活力。我們的船隨著潺潺的流水平穩地漂浮向前,滿潮的泱泱河水迎面而來,一個個長著綠色小樹林的島嶼從兩旁往后退去。河上處處漂著巨大的木排,沉甸甸的,人們正在上面忙碌著,發出一陣陣興奮的喊聲、說話聲和歌聲。早上的陽光已經十分燦爛,亮得耀眼,但我還是瞇起眼睛,注視著這條蜿蜒兩千俄里、奔騰在俄羅斯古老的土地上的滾滾巨流。我們那些槳手的模樣——長著藍眼睛的、溫順而又和藹的白俄羅斯人,腳套樹皮鞋,身穿骯臟的長襯衫,使我想起了德聶伯河的發源地,那是個貧窮的地方——斯摩棱斯克沼澤。那里,這條清淺的小溪奇妙地積聚起力量,流淌在波列西耶的密林中;那里,至今還出沒著野豬和野山羊,而海貍則在林中的河灣上筑巢;那里,這條小溪同人跡罕至、遮天蔽日的松林深處那些神秘的支流匯合起來,形成了一條浩浩洪流,奔瀉在這一片洋溢著農耕生活情趣的安恬和歡樂的烏克蘭美好的土地上。
我想到,這一片土地經歷過多少個世紀的流血征戰和紛爭,野蠻的佩切涅戈人[6]和波洛韋次人部落曾經踏遍了這一片草原,但她至今依然是那般美麗;我還想到,這一片土地盡管處在喧騰的新生活之中,卻依然久久地保存著遠古時代的痕跡……說來很可笑,我站在甲板上,還一次又一次地把目光投向岸邊的群山之中,搜尋達尼洛老爺[7]當年所住的那個白生生的小村子……
唉,天曉得這個達尼洛老爺住在什么地方!“可怕的復仇”的年代跟遙遠的波洛韋次人的年代一樣,早已消逝得無影無蹤。威嚴的先人已經不會使我們恐懼,只有洶涌澎湃、深邃無比的德聶伯河還在不時地向人們訴說當年生動的情景。兩岸的山岡依然酷似那些古墓……現在只能望見山上無數星羅棋布的風車的葉片,而在山岡的另一頭則展現出一望無際的曠野、草原,像大海一般廣闊,那里散落著一些石頭雕像,黑黢黢、藍森森的,是古人崇拜的偶像;一看到它們,心頭便會揪緊,思緒便會不由自主地飛向遠古蒙昧的時代……
三
我就在這樣的沉思中不知不覺地度過時光;海鷗號也就這樣平穩地、不知不覺地趕著路程。
白天依然那么晴朗而炎熱,此種天氣只有在南方才有。從上午十一點起,德聶伯河的整個畫面仿佛在凝滯的空氣中靜息了。空氣熱得如同滾燙的蒸汽一樣,這些蒸汽像燒熔的玻璃似的閃閃發亮,抖抖索索地飄浮在慢慢趕超我們的那些白色輪船的又粗又黑的煙囪上方。鋼藍色的德聶伯河紋絲不動,周圍的景色——遠處的小村落、白楊樹和低平開闊的草地后邊那些小山的淡藍色剪影也都顯得呆板凝固。一道道沙質淺灘耀眼地閃著光,看上去活像一片片已經成熟的黑麥田,黃澄澄的。海鷗號從淺灘旁邊駛過時放慢了速度,以至周圍的一切顯得格外寧靜。白俄羅斯人唱著憂郁的歌,并且隨著歌聲的節奏一起一落地蕩著槳。此刻,只有他們悠長的嗓音才打破了這死一般的沉寂。
松木板船艙被太陽曬得熱烘烘的,從河面反映上來的光影整天平穩地、難以覺察地在天花板上游移,打開的小窗透進涼風,送來一股水汽和魚腥味。而在船舷旁邊,德聶伯河透明的波浪整天喧騰著,拍擊著,起伏不停。盯著波濤看,不禁有點頭暈,產生了睡意……
在這種安寧、恬靜的環境影響下,我頭腦中那些同基輔地區緊密相關的古代往事的記憶漸漸變得黯淡,取而代之的是現今德聶伯河兩岸的新生活所留下的印象。我看到了喧闐的商務碼頭,那里擠滿了身穿小俄羅斯鮮艷服裝的人們;我看到了基輔城郊許多古老的村鎮,成百幢白色農舍掩映在花園的綠蔭之中,在它們的上方閃耀著鄉村教堂的十字架;最后,我也知道,在德聶伯河的左岸,在它的支流地帶和草原上,也有許多生氣勃勃、人口眾多的村莊隱沒在花木叢中;我期待看到一位詩人的長眠之處,他是多么熱愛這一切,他在詩歌中表達了自己飽經憂患的一生的痛苦,同時又描繪出了自己故鄉的全部的美。他有著一個普通農民的名字——塔拉斯·謝甫琴柯[8],這個名字永遠能為俄羅斯文學增光。
后來,我曾經尋訪過許多偉大人物的墓地,但是沒有一處能夠像烏克蘭人民歌手的墓地那樣給我留下這樣感人的印象。確實,誰的墓地能夠如此樸素,而又如此莊嚴和充滿詩意呢?在它的附近便是卡涅夫古城。“卡涅夫”是古代土耳其人所取的名稱,意為“流血之地”。那邊在古老的修道院墓地里,埋葬著古代的哥薩克英雄和祖國保衛者薩米洛·基什卡、沙赫和伊凡·皮德科瓦。而詩人自己的墳墓則坐落在風景如畫的高山上,在那里可以遠眺德聶伯河幽藍的谷地和數以百計的村落,遠眺為這位已故詩人所珍惜的一切。可是,它又是多么簡樸!小小的一個土丘,上面豎著一個白色的十字架,再加簡短的題銘……就這一些!躺在這墳墓中的人曾經向往著有一間自己的農舍,搭建在德聶伯河的河岸上,“使備受折磨的痛苦的心在德聶伯河邊的群山中找到安寧”。他甚至在去世之前不久還來到這群山上,把自己的宿愿感人地告訴他心愛的妹妹。可是,在飽受漂泊和思鄉之苦之后,他命定只有在墳墓中才找到歸宿!
一所粉白色小屋,周圍種著錦葵、罌粟花和向日葵,現在就矗立在他的墓地十字架旁邊。里面十分寬敞和整潔,但是它的主人卻已經永遠無法跨進門檻了。遺像中的他從小屋的墻上憂郁地俯視著擺放在桌上的那本詩集,似乎帶著責備的神情對參觀者說:“人們,你們對我干了些什么啊?我的一生為什么過得那樣悲慘和孤獨?我是多么熱愛這人世,熱愛我的祖國,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把我驅趕進墳墓呢?……”
四
我老是激動地回想起這一所小屋里的情景。我憂郁地目送著離我們遠去的卡涅夫群山。現在,偉大的人民詩人的故鄉在我的心目中變得更加美麗和親近了。
傍晚,在這樣的時候,燕子顯得特別興奮,它們一會兒自由自在地直沖晴空,一會兒在波平如鏡的河面上滑翔,用尖尖的翅膀掠起水花,然后又消失在明凈的天空中,傳來一陣莫名其妙的歡快的啁啾聲——在這樣的夜晚,處處充溢著絢麗和諧的色彩。
德聶伯河那靜止不動的水面,猶如大湖一般廣闊,倒映出了溫馨動人、五色斑斕的道道霞光:從銀灰到粉紅,從絳紫到金黃;湖面是多么平靜,宛如一幅畫,以至使人懷疑,我們是否真的是在河道航行……我們已經到了謝基爾納城郊,那里的右岸在山地之后綿延著寬廣低緩的平原,長與闊均有數俄里。那是一大片草地,雖是被水淹著的草地,卻不像我們大俄羅斯的草地那樣充滿荒涼的氣息。烏克蘭的草地,景色十分秀麗。時而草地中出現一叢青翠的小樹林,時而刈草場上孤零零地挺立著幾株枝葉繁茂的大樹,遠遠看去影影綽綽的,顯得格外迷人,簡直就像是風景畫中所見的樣子。也許,是夏日的傍晚,或者是我的情緒,即一個外鄉人的情緒,把這個地方美化了。不過,我總覺得,這個地方是真正的烏克蘭,是我從童年時代就開始想象的充滿詩意和令人神往的烏克蘭。
我遠眺這片漸漸落在暮色之中的漫著水的草地,想象出鄉間一條覆蓋著綠蔭的小徑,似乎聽到了白色農舍邊那些姑娘們的嗓音。她們的歌聲響徹晚霞初上的寧靜的天空,她們歌唱的正是偉大的烏克蘭詩人所頌揚的一切。我又回憶起那些古墓形狀的山岡,它們使我想起了昔日的傳說。我不知不覺地又把思路轉到對塔拉斯·謝甫琴柯一生的回顧,一面凝望著他的墓地。
遠方的卡涅夫群山還久久地停留在我們的后邊,猶如一堆暗紫色的烏云流連在金燦燦的西邊天空。整個傍晚,我們都能看到矗立在寬闊無比、平靜如鏡的德聶伯河那一頭的群山的剪影……
漸漸地,天色已黑,桅桿上掛起燈來,氣溫變低了,彌漫著輕霧。我往東、朝前邊望去,已經看不清河岸。藍瑩瑩的德聶伯河同黑沉沉的南方夜空融合在一片藍黑色霧靄之中。晚風吹起一大片漣漪,德聶伯河上銀波粼粼,使人覺得這個由大河和夜空組成的霧蒙蒙的藍色世界全都在翻滾流動,散發出遠方海洋冰涼的氣息……遠處有一艘我們看不分明的輪船在隱隱約約地閃耀著淡綠色的燈光……最后,連這燈光也沉沒在波浪的那一頭了……
我走進了船艙,大家都已經沉睡,但我卻躺在吊床上徹夜不眠。船艙里一團漆黑,簡直像在棺材里一樣。這一片昏暗,以及輕輕的顛簸使我產生一種感覺,我似乎身居墳墓中,又似乎整個地球都在輕輕地搖晃,而在我的床頭奔騰不息的德聶伯河波濤平穩單調的嘩嘩聲、持續不斷的拍擊聲和激蕩聲卻使我感到分外新奇,分外興奮……
那邊,在群山之巔,在憂郁的德聶伯河上方,在深夜的黑暗之中,有一座墳墓保持著永恒的緘默……
五
打這之后已經過去了好多年,但是我在德聶伯河上所獲得的感受卻永遠鐫刻在心。以前,我只是隨意地想去陌生的地方走走,現在,我明白了旅行意味著什么。我明白了,為了能使自己的生活充實起來,光是有學問,光是有書本知識和安寧的生活是不夠的。對我來說,正是在浪游生涯中發現了大自然的美,發現了藝術杰作同其創作者故鄉之間的深刻聯系,發現了研究民間風俗的引人入勝之處,發現了自由自在的生活的詩意……
“哎喲,哎喲!”伊薩依·馬爾科維奇搖著頭說,這時我們正駛近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城,“天氣變了,刮起了大風……我們到了險灘那里可怎么辦?這比去年的情況更糟啦……”
但是,即將面臨的危險反倒使我高興。盡管我們從洛茨緬斯卡亞-卡緬卡鎮(那兒的河面已經有險灘了)出發的那天風和日麗,我還是覺得,我們準會碰到什么非同尋常、可怕而又富有詩意的場面。
這種預感由于海鷗號上的人們不斷地談論險灘的情況,由于來自卡緬卡鎮的兩位引航員的樣子(根據法律,沒有他們的指引,任何船只不準駛過葉卡捷琳諾斯拉夫),也由于我們起航時那種鄭重其事的方式而得到了加強。我幾乎懷著崇拜的感情來看待這兩位引航員,這兩位查波洛什人的后裔。其中一人是個身材高大、表情嚴肅的哥薩克老頭,另一人長得矮胖敦實,態度和藹而又莊重,是個地地道道的“塔拉斯·布爾巴”[9]。高個子直率地自稱是“引航員”,而他的同伴則有個外號,叫“大叔”。
這樣,在船艙里接受了款待之后,“大叔”迅速地從座位上站起來,拿起帽子,捋了下胡子,便走到甲板上。
“喂,孩子們,”他摘下帽子,一本正經地大聲喊道,“讓我們向上帝作個禱告吧!”
接著,他第一個跪了下來,俯身鞠躬到地,激動得臉色發白。我們大家也跟著下跪,在一片肅穆之中熱誠地祈禱上帝保佑我們一路平安。然后起了錨,槳手們各就各位,海鷗號便緩慢地穿行在險灘之間。
按我在日記中的記載,那是在6月12日,星期二,而在13日的早晨我便永遠地離開了海鷗號。我們從基輔出發后一路上都在期待的一天終于來到了。這一整天都處在忙碌和驚惶之中,時間不知不覺地流逝。德聶伯河在這一帶水流湍急,我們的船行駛得很快。從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直到亞歷山大羅夫斯克,整條大河布滿了石頭“圍墻”和險灘。這些險灘和石墻實際上是一長列寬闊的花崗巖礁石,來自喀爾巴阡山的支脈,橫貫著德涅斯特河、布格河和德聶伯河。春天,礁石全部淹沒在水中,而在“中水”季節,也就是在我們航行的那個季節,這些巖石在許多地方都露出河面,德聶伯河的河水撞擊著這些石灘,發出陣陣轟鳴聲。石灘一共有十個,其中特別使人感到不安的只有二三個,而最危險的是涅納瑟捷茨灘。
我須重復一遍,不管眼前還是在德聶伯河石灘之間,海鷗號都行駛得很快。槳手們此刻正躺在甲板上休息。鋼藍色的河面亮閃閃的,河水沿著寬闊的河道奔流而去。可是,從遠處已經傳來轟隆轟隆的聲音……近了……更近了……不久,便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波浪和險灘的撞擊聲。引航員和“大叔”站在船尾的高處,目不轉睛地緊盯著河面;他們突然揮一下帽子,槳手們便趕快拿起木槳;需要給船加一把勁,讓它快一點從石灘之間沖過去。
“劃起來,劃起來,孩子們!”引航員喊道。于是,白俄羅斯人分成兩排,每排四人,一齊使勁壓住木槳,身子幾乎緊貼著甲板,海鷗號走得越來越快,眼看到了石灘跟前。
這種景象驚心動魄,叫我永生難忘。周圍是鋼藍色的河面,正平穩地往前滑行,而前邊卻橫著一道幾近黑色的大浪,從岸的這一頭直到那一頭,仿佛德聶伯河在這個地方給斫了一刀。從遠處望去,河面在此處折斷了,沿著斜坡飛瀉而下,黑色的波浪洶涌澎湃,浪峰泛著白色的泡沫。
“停!”“大叔”吸足了一口氣,突然喊了起來,“把——舵!”
白俄羅斯人當即丟下木槳,撲到在船尾上方隆起的那只巨大的木制舵輪上去,用盡全力去轉動它,不住地往左右擺著身子,而臉色發白的引航員則繼續使勁地叫喊:
“用力,用力!……用力,弟兄們,孩子們!”
這時,我們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想沖上去,不管怎樣要給海鷗號幫上一把——已經沖上險灘啦!周圍只見喧騰的波浪、飛濺的泡沫、令人頭暈目眩的漩渦,載著幾千普特[10]重木柴的海鷗號在大浪中不停地跳躍和晃動……
“沖過去啦!”最后,“大叔”如釋重負似的喊道,大家舒了一口氣,摘下帽子,眼望蒼天畫了個十字。此時,德聶伯河還沒有平靜,還在輕輕地搖動著船,而在后邊,險灘的轟鳴聲已漸漸遠去。
就這樣,我們沖過了卡達茨基灘、蘇爾斯基灘、洛漢斯基灘、茲沃涅茨基灘,以及最后的涅納瑟捷茨灘。引航員們把最后一個石灘稱為“老爺子”,那是一個最兇險的石灘,有九排巖石,還有“地獄”,那是指石灘下方的一個深潭,那里的漩渦包藏禍端。我們順利地繞過了“地獄”,此時可以完全放心了。現在,海鷗號走得慢了一點,一個個布滿樹林的島嶼、岸邊的山嶺、村落和遠處的平原從兩旁緩緩地往后退去。太陽漸漸西沉,夜幕降臨了。我們拋了錨,在一處空曠而又荒僻的地方歇宿。燃起了篝火,熬著粥,圍在鍋子邊久久地交談著,還聽兩位引航員講述他們驚險的經歷——他們的聲音很輕,頭頂著點點繁星和南方夜晚那藍黑色的天空……
第二天,我們又沖過了四個石灘,靈活地穿過了巖石崢嶸的高岸之間那條危險的峽谷,那是在離亞歷山大羅夫斯克不遠的地方,在德聶伯河折向東南的急轉彎處,過不久,我們便到了基奇卡斯城的碼頭。
在這里,我便同白俄羅斯人,同我親切殷勤的猶太船主,同引航員和海鷗號告別了。我要趕赴著名的“圣格奧爾基島”——霍爾季察島,在那里久久地徘徊,想尋找古老的哥薩克營地的某些遺跡。可是,島上卻是靜悄悄、空蕩蕩的……只有一些雜草叢生的土堤表明這里曾經有過軍營……
這里離草原已經不遠了。在霍爾季察島的那一頭便是德聶伯河的低岸地帶,在那里大河已經同許多一望無際的湖泊連成一片,遍布著幾千個小島,上面長著小樹林、柳條枝和蘆葦。那邊,靠近低岸地帶,在河的左岸,展現出了德聶伯河草地,那是一個由翠綠如茵的草原、沼澤和小河組成的王國——一個自古以來以其土壤肥沃、物產豐饒,并引起無數血腥爭奪而著稱的地方。再過去一點,過了低岸地帶和草原,便是蔚藍的大海,自由的風帆在遠方的海域閃著白光……
“往那邊去,往那邊去!……”我滿懷喜悅地想,“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誘人。只是應該明白,生活中最需要、最珍貴的是什么!”
(敖德薩,1898.9)
圣山[11]
一
通往頓涅茨河,通往古老的圣山修道院的路是朝東南方向的亞速夫草原那邊走的。
在復活節期間星期六的大清早,我已經趕到了斯拉維揚斯克城的郊外。不過,離圣山還有約二十俄里,得走快一點。我想在修道院里度過這一天。
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灰蒙蒙的空曠的田野。遠處有一個土丘,那是古代的邊界警衛崗,它似乎密切監視著平原的動靜。從清早起,草原上有一股春寒,還刮著風,風把壓在泥濘道路上的車轍吹干了,還把去年留存下來的雜草吹得窸窸窣窣地響個不停。在我的后面,在西邊的地平線上顯現出峰巒起伏的白堊巖山嶺,看上去挺美。它隱沒在朝霧之中,露出了一個個黑點,那黑點是一叢叢樹林,就像一塊古老的無光澤的白銀上出現的黑色斑紋。我頂著風行走,臉和雙手都已冰涼了,但是草原吸引著我,使我著迷,使我充滿了歡樂和朝氣。
土丘的后邊有一片圓形的凹地,漫著春水,亮晶晶的。我拐到那邊去歇息一會兒。在春天這些田野的小湖里總是有著某些純潔的、令人愉快的東西:鳳頭麥雞吱吱啾啾地在水面上方盤旋,灰白色的鹡鸰搖搖擺擺地踩著小步走過岸邊,在淤泥上留下了細細的、星狀的腳印,而在清淺的水中倒映著春天的碧空和白云。土丘周圍還是荒土,從來沒有給人犁過。土丘分成兩個小阜,上面覆蓋著去年的雜草,好像鋪著一塊已褪色的渾綠色絲絨桌布。斜坡上還有一些灰色的羽茅草,其實那是羽茅草可憐的殘莖,正隨風輕輕地擺動。我想,它們的時光是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它們在永恒的沉思之中只是模模糊糊地回憶得起遙遠的往事、昔日的草原和昔日的人們。那些人的心靈要比我們更能理解它們的絮絮細語,這種細語傳遍了自古便籠罩在沉寂之中的曠野,這種細語無聲地訴說著人世生活是多么渺小。
我躺在土丘上,休息了好一會兒。從田野那邊已經送來了溫暖的氣息,白云變得明亮了,漸漸消融在天際。在充溢著水汽和光華的空中,在草原的上方,幾只肉眼難以看清的云雀在歡樂地啼囀。風也變得溫煦、和暢起來。太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閉起眼睛,覺得自己渾身舒坦。在南方的草原上,每一個土丘似乎都是某一則充滿詩意的傳說的無言紀念碑。而漫游頓涅茨河一帶,探訪《伊戈爾遠征記》中所歌頌的小塔納伊斯城則是我的夙愿。頓涅茨河是伊戈爾大公征戰的見證,也許,圣山修道院也是一個見證。它有多少次遭到徹底的破壞,有多少次變成斷垣殘壁,一片廢墟!它矗立在韃靼人進攻的道路上,矗立在荒野的草原上,它的僧人便是戰士,抵御著金帳汗國[12]的大軍和結伙行劫的強人的長期圍攻,經歷了多少苦難!
傳來了大車的咯吱聲,車上坐著一個老頭兒。他把雙腿垂在車邊,腳上穿著一雙舊靴子。犍牛拖著重負,伸出頭頸,搖搖晃晃地慢步走在路上。這幅圖景驅散了我的思緒,我便加快了腳步。
遠處出現一片森林,灰蒙蒙、黑沉沉的。我定睛望去,心想,森林那一頭該是頓涅茨河和圣山之間的谷地了吧。這片森林又古老又荒涼。密林中的枯枝朽木,以及死一般的寂靜使我吃驚。我放慢了腳步,艱難地踩著枯枝雜草,跨過被狂風刮倒后浸在深坑泥漿中半已腐爛的樹木,穿行向前。樹林中聽不到一聲鳥鳴。有時,去路還被一大片春水淹沒了。周圍干枯的林木透著光,它們那些彎彎曲曲的樹枝投下了淡淡的陰影。
然而,過不久,在林中小路的空距間又可以望得見遠處開闊的原野了。草原上干燥的風刮得越來越大,驅散了春日晴空中的白云,使遠景變得漫無邊際。可是,卻找不到修道院的蹤影。
我走到一個烏克蘭人跟前去問路,這是一個身材魁梧的莊稼漢,腦袋很小,身穿一件像是用白楊樹皮縫制的短袍,不慌不忙地扶著犁。犁由四頭犍牛拖著,前邊還有一個小姑娘牽著牛。
“爹!”她對莊稼漢喊道,提醒他注意到我。
他停下步來。
“請問,這是到圣山去的路嗎?”我問道。
“您要上哪兒去?”[13]
“去修道院。”
“哪個修道院?”
“難道您從來沒有上過圣山?”
“是去農莊嗎?”
“不,不是去農莊,而是去修道院,上教堂。”
“上教堂?那我們自己村里就有教堂。”
“那么,去修道院呢?”
“去是去過的,不過那時我還是個小伙子。村里的牲口得了瘟病。有人說,那邊有個修士,知道怎樣消災。這樣,凡是家里牲口得病的人,都結伙上圣山去。當然,在那里做了禱告,還把那個修士請來。他在各家院子里轉啊轉的,灑了圣水,可是什么用處也沒有。”
“那么,這條路是通往那邊去的啰?”
“唔,是的……”
烏克蘭人甚至沒有再瞧我一眼,便又埋頭犁起地來。
我覺得有點累。滿沾塵土的滾燙的靴子里的雙腳,已經隱隱發痛。于是,我便數起步子來,這樣可以分散注意力。當我回過神來時,道路已經向左邊急轉彎,路面的白堊土耀眼地閃著光。在左前方遠處的地平線上,在一片小樹林的上方,露出了亮閃閃的教堂圓頂,像一顆金色的星星。我剛朝它望上一眼,便發現在我前邊原來延伸著一大片又寬又深的谷地,頓涅茨河就在這谷地里流淌。
我凝神屏息地站了好一會兒,望著這一片青郁郁的開闊的草地。它已經被水淹沒了——頓涅茨河正處在春汛期。鋼藍色的河水一道道地在深棕色的蘆葦叢和浸水的岸邊樹林里閃耀,而在南邊河水泛濫得更猛,茫茫一片,直到遠處白堊山山腳下。這些山是白晃晃的,望過去眼睛都迷糊了……然后,我趕上了一批朝圣者,有婦女,有少年,也有由于年邁和經受草原風吹而淚眼模糊的殘疾老人,心里一直想著古老的風尚,想著它所具有的神奇力量……這種力量從何而來,它意味著什么?
然而,修道院依然還沒有出現。天空變得灰暗起來,風從路面上刮起了陣陣灰塵,走在草原上感到有點寂寞。有個小伙子正從旁邊駕車而過,我便同他打個招呼,讓我搭乘上他的兩輪馬車。我們交談了起來,不知不覺地進入森林,往山下走去。
山路變得越來越陡峭、難走,路面很窄,有許多石頭,不過周圍的景色挺美。越是往下走,那些傲然挺立在雜樹之中,并把根株盤結在路邊山石之間的高大的百年古松將紅彤彤的樹干往上伸得越高,綠色的樹冠直沖碧空。我們頭頂上方的天空也似乎變得更加深邃和明朗了,一種像這天空一般清純的愉悅感充溢著我們的心靈。而在下方,透過青翠的林木叢,在幾株松樹之間,突然顯露出了一片似乎挺狹隘的谷地,還有金色的十字架、圓屋頂和在綠樹成蔭的山腳下幾間房子的白墻——由于距離很遠,這一切都顯得那么玲瓏,那么精巧。透過樹隙,還能望見像一條閃亮的狹長帶子一般的頓涅茨河,以及在河那一頭彌漫在密密層層的森林上方的一團灰藍的霧氣……
二
在圣山腳下,頓涅茨河的河道很窄,水流湍急。它的右岸高高地聳起,好像一堵陡直的墻壁,上面也長著茂密的樹木。正是在這山下邊,坐落著用石頭砌成的修道院,院子中間矗立著一座氣勢雄偉,但粉刷得稍顯粗糙的大教堂。在上方的半山腰里,有兩個白堊巖圓錐體——兩座灰白色山崖,山崖后面顯露出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教堂。再往高一點的地方,接近山脊,背襯著天空,聳立著另一座小教堂。
從南方飄來了一片烏云,因為是春天,傍晚依然那樣晴朗和溫暖。太陽緩緩地沉到山后,寬闊的山影漸漸鋪展到頓涅茨河上。我穿過修道院的石頭院子,繞過大教堂,朝通往山上的帶頂回廊走去。這個時刻,在這些不見盡頭的通道中空無一人。我越是往上走,便越是強烈地感受到修道院那種森嚴可畏的生活氣息。這種氣息來自描繪修士們用棺材取代睡榻的隱修院、僧房的壁畫,來自那些掛在墻頭的鉛印訓誡,甚至來自古老破損的每一級階梯。在這些通道的陰影中似乎出沒著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僧人們——那些嚴肅、沉默的苦行修士們的幽靈……
我急著想到白堊巖山崖那邊,去看看那個山洞,在那里曾住著一個最早來到這山里的人[14]。這是一個平凡而又心靈高尚的人,他以其偉大的胸懷熱愛小塔納伊斯城上方的山脊,并在勞動和祈禱中度過了一生。這位圣人初來之時的原始森林是多么荒涼和偏僻。郁郁蒼蒼的濃蔭壓在他的頭頂上方,密密層層的樹木遮掩了河岸,只有孤獨而又自由的河水在岸邊的懸崖下濺起冰冷的浪花,發出陣陣拍擊聲。周圍是一片寂靜!鳥兒的啼鳴,干樹枝在野山羊腳下的噼啪聲,布谷鳥那略帶嘶啞的“咕咕”聲,以及雕鸮在黃昏時的嘯叫聲都能在森林中引起久久的回音。夜里,一切都籠罩在肅穆的黑暗之中。僧人聽到一陣窸窣聲和河水的汩汩聲,他猜到有人在橫渡頓涅茨河。他們像魔鬼的大軍一般,悄悄地來到河這邊,穿過灌木叢,消失在陰影之中。山洞里的那個孤獨的人當時心里挺害怕,他的燭光徹夜不熄,他的祈禱聲一直響到天明。而到早晨,盡管經受了一夜的驚擾,盡管通宵未眠,他仍是容光煥發地去迎接白晝,去干活,他的心里又充溢著溫柔和寧靜……
在我下方深處,一切都已沉浸在溫暖的夜色之中,閃耀著燈火。那邊已經開始從容而又欣喜地為復活節晨禱作準備了。而在這里,在白堊巖山崖的后邊卻是靜悄悄的,還能見到微弱的霞光。棲居在山巖□和教堂屋檐下的小鳥在盤旋飛舞,像老風信雞那樣吱吱嘎嘎地叫著,一會兒直沖云天,一會兒又無聲地朝著黑暗的空間直落而下,不時撲打著柔軟的翅膀。南邊來的烏云遮住了整個天空,送來了一股帶有春天雷雨的清香氣息,并在一道道電光中微微顫抖。山崖上的松樹融成黑魆魆的一團,活像沉睡的野獸那弓起的后背……
我抓緊時間跑到了山頂,去了最上面的那個小教堂,腳步聲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靜。那里有個修士像幽靈一般站在一個裝著蠟燭的箱子邊,點著二三盞油燈,發出噼啪的響聲……我點起一支蠟燭,插上燭臺,用以紀念那位身體虛弱的老人,他在當年那些可怕的夜晚,修道院遭到圍攻、四周燃起篝火的時候,堅持留在這所小教堂里叩拜祈禱……
三
早晨充滿節日的氣氛,很熱,在頓涅茨河上方,在蔥蔥蘢蘢的群山之上,叮叮當當地響起了一片鐘聲,這聲音傳到山脊上的小教堂,直沖晴朗的天空。河面上人聲喧鬧,越來越多的人乘著大劃船來到修道院,華麗的小俄羅斯節日盛裝使周圍變得更加色彩絢麗。我雇了一條船,一位挺年輕的烏克蘭女人靈巧、快速地劃著船,沿著清澈透明的頓涅茨河逆流而上,穿行在岸邊綠蔭投下的陰影之中。在這個可愛的早晨,年輕姑娘的臉龐、太陽、樹叢,以及湍急的小河,一切都顯得那么美妙……
我在隱修院里稍作停留——那里十分寂靜,只有白樺樹嫩綠色的樹葉在竊竊私語,像是在墓地里一般。隨后,我便往山上走。
登山挺困難。腳老是深深地陷進苔蘚、朽木和軟綿綿的爛葉中去,不時會有一些蛇在腳下蜿蜒,又敏捷地爬開去。在松樹的濃蔭下,凝滯的空氣熱烘烘的,充溢著濃重的松脂香氣。而在我的眼前,展現出了多么開闊的遠景啊!從山頂上放眼看去,河谷有多么秀麗,遍布的森林就像蓋上一重深綠色天鵝絨,泛濫的頓涅茨河在陽光下金光閃閃的,周圍的一切都滲透著南方火熱生活的氣息!難怪當年有一位伊戈爾軍團的戰士,跨下打著響鼻的戰馬、登上這高山之巔,身處懸崖之上,俯視綿延而下的茂密松林,他的心因驚喜若狂而劇烈地跳動!
到黃昏時分,我已經漫步在草原上了。迎面吹來一陣陣和風,這風來自緘默無聲的土丘那邊。我坐在土丘上歇息,孤身一人流連于這片一望無際的曠野之中,又想起了古老的風尚,想起了長眠在草原的墳墓中、在灰白色羽茅草的絮絮細語中的先人……
(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