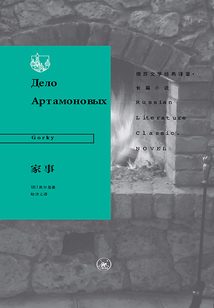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農奴解放令下后兩年,基督變容節那天彌撒祭時,尼古拉教堂的信徒們發現一個陌生的人——擠在人群里,不客氣地推搡著——勇武有力的男子,被鬢霜侵蝕得極多的圈形的大胡須,吉卜賽式的、微黑的、卷曲的頭發形成一只厚帽,巨大的鼻子,瞳仁像小鴿似的灰色的眼睛從濃厚的山丘形的眉毛底下大膽地望人。當他垂手時,人們看得見寬闊的手掌觸到膝蓋那里。
他走進一群知名士紳的行列,朝十字架膜拜,這尤其使他們不悅。彌撒祭告終時,特遼莫夫的知名人士聚在廊下交換對于這陌生人的意見。有些人說是販牛商人,有些人說是郡長,但是體弱、心善、性好和平的市董長葉夫賽意·巴意馬闊夫卻輕聲咳嗽,說道:“也許是家仆出身,獵師或是服務貴族娛樂方面的職業。”
布商博賣洛夫,綽號“守寡蟑螂”,是一個雜亂無章的登徒子,愛說尖刁話,滿面雀斑,十分丑陋,當時不懷好意地說道:“你們瞧——他的手巴掌多長?走起路來,好像鐘樓上的鐘全是為他撞響的。”
闊肩巨鼻的人在路中大踏步行走,好像走的是自己家里的土地。他穿著質地佳良的藏青呢外衣,好黑的軟皮長靴,手插在口袋里,肘緊壓腰際。市民們囑咐燒圣餅的女人葉爾唐司卡耶詳細打聽他是什么人,隨后在徹響的鐘聲里各自回家吃餡餅了。與此同時,他們還接受了到博賣洛夫的楊梅林里去喝晚茶的邀請。
飯后有些特遼莫夫人看見這不見經傳的人到河邊——牛舌灣——拉脫司基公爵的轄地。他在柳林里走來走去,用平正寬闊的步伐量著沙峽地,將手掌掩在眼上,瞭望城市,奧卡河像繩結般紛亂的支流,池沼狀的小溪瓦達拉克莎。特遼莫夫城里住的全是謹慎的人,誰也不敢喚他,問他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后來到底打發了巡捕棰子·瑪司卡前去。他是城里的小丑和酒鬼。當時當著眾人,也不避婦女,不知羞恥地脫下官家發的制服褲子,揉皺的軍帽還留在頭上,涉足渡過沉泥頗厚的瓦達拉克莎河,挺起醉鬼的大肚,舉著可笑的、鵝走的步伐,走到陌生人面前,為了增加勇氣,故意大聲問:“你是誰?”
沒有聽見陌生人怎樣回答,不過棰子立刻就回到自己的人那里,敘說道:
“他問我,你怎么這樣難看?他的眼睛惡毒得很,像強盜一般。”
晚上,在博賣洛夫的楊梅林里,燒圣餅的女人葉爾唐司卡耶,頸腺腫大的女人,著名的占卜者和先知者,凸出可怕的眼睛,向良善的人們報告道:
“他名叫伊里亞,姓阿爾達莫諾夫。他說他打算住在我們這里,經營一種事業,是什么事業,我沒有探出來。他順著伏爾哥洛特的大路來的,三點鐘后就從原路回去了。”
就這樣也沒有打聽出這人什么特別的來。這很不痛快,好像有人深夜叩窗,然后隱沒了,因此一言不發地預告災害的降臨。
過了三星期左右,市民們記憶里的創痕差不多磨平了,忽然這阿爾達莫諾夫在星期四那天親身到巴意馬闊夫家去,像劈斧似的說道:
“你瞧,葉夫賽意·米脫里奇,新的住戶到你的聰明的手里來了。請你幫幫忙,讓我在你的附近住下來,創立好的生活。”
他簡短而有頭緒地講述自己是拉脫司基公爵的人,原住勒提河庫爾司基封田。他曾充當戈渥爾基公爵的收租人,農奴解放令頒布后離開公爵,受了重賞,決定經營事業:開設布廠。他的妻子已過世,長子叫彼得,次子是駝背,名叫尼基大,第三子叫奧萊士卡,本是他侄兒,收做兒子。
“此地的鄉下人不大種麻的。”巴意馬闊夫在凝想中說。
“我們會讓他們多種。”
阿爾達莫諾夫的聲音濃重、粗魯,他說話好像大鼓,然而巴意馬闊夫一輩子在地上謹慎走路,輕聲說話,似乎怕驚醒一個可怕的人。他眨著悲哀的、丁香般的、和藹的眼睛,望著阿爾達莫諾夫的兒子。他們像石頭般站立在門外,長相不大相同的:老大像父親,寬闊的胸部,眉毛聚攏在一起,眼睛是小的,像熊眼;尼基大的眼睛是處女式的,大而發藍,像他的襯衣;奧萊士卡是頭發卷曲、臉色發紅的美男子,皮膚白皙,目光直而快樂。
“有孩子要當兵去嗎?”巴意馬闊夫問。
“不,我自己需要他們,有證書在手里。”
阿爾達莫諾夫向孩子們揮手,吩咐道:
“出去吧。”
在他們守著長幼輩分,魚貫地輕聲走出以后,他將重掌放在巴意馬闊夫膝上,說道:“葉夫賽意·米脫里奇,我想連在一起,向你求媒,把你的閨女嫁給我的大兒子。”
巴意馬闊夫竟大吃一驚,在長椅上跳了起來,搖手。
“你怎么啦!我初次和你見面,還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居然來這手!我只有一個閨女,出嫁還早,你也沒有看見過她,不知道她是怎么樣的人……你怎么啦?”
阿爾達莫諾夫從卷曲的胡須里發出冷笑,說道:“關于我,你可以問警官,他受過公爵的恩德,公爵寫信給他,叫他盡力為我幫忙。你不會聽到什么壞的傳言,圣像可以做保證。你的女兒我很了解,我私下到這城里來過四次,這里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全都打聽清楚了。我的大兒子也來過,見過你的女兒,請你安心吧!”
巴意馬闊夫感覺好像是一只狗熊撲到他身上來一般,求著客人道:
“你等一等……”
“稍等是可以的,如果久等——就等不及了。”固執的人嚴肅地說,并朝窗外院里喊道,“你們來呀,對主人鞠躬。”
他們辭別后,巴意馬闊夫懼怕地望著圣像,畫了三次十字,微語道:
“上帝保佑我!這是什么人?免去我的災難吧。”
他擊著手杖,踱進花園里去,妻子和女兒正在菩提樹下燒糖漿。肥胖、美麗的妻子問道:“那些在院里站著的年輕人是什么人?”
“不知道。娜泰里亞哪里去啦?”
“到廚房取糖去了。”
“取糖去了,”巴意馬闊夫陰郁地重復著,坐到草編的椅上,“人們說,農奴解放令下達后大家都很不安,這話很好。”
妻子盯了他一會兒,驚慌地問:“你說什么?又不痛快了嗎?”
“我的心痛起來了,心想這人是來接替我的。”
妻子開始安慰他。
“得了吧!現在人從鄉下到城里來的有的是呢。”
“就因為來的人多呢。我暫時不對你說,讓我想一想。”
過了五晝夜,巴意馬闊夫躺下床去,又過了十二晝夜便死了,而他的死投下了更深厚的黑影到阿爾達莫諾夫和他的兒子們的身上。在市董長病時,阿爾達莫諾夫來過兩次,他們兩個人面對面談了許多話。第二次巴意馬闊夫把妻子喚進來,兩手疲乏地合在胸前,說道:“你同她說吧。我大概在世也不久啦,讓我休息休息吧。”
“同我出去一會兒,烏里央娜·伊凡諾夫娜。”阿爾達莫諾夫命令著,也不瞧女主人是不是跟在后面,自己出屋去了。
“去吧,烏里央娜。大概這就是命運。”市董長看見妻子不敢跟客人出去,就輕聲勸她。她是聰明的女人,具有自己的性格,不會不假思索地去做任何事的,但是結果卻是這樣的:一小時后她回到丈夫身旁,美麗的長睫揮彈下淚珠,說道:“米脫里奇,顯然真是命運;你祝福你的女兒了吧。”
晚上她將服裝華麗的女兒領到丈夫床前,阿爾達莫諾夫把兒子推過來。男女兩人互不看視,拉住手,低頭跪了下來。巴意馬闊夫喘著氣,將鑲珠的祖傳的古神像蓋在他們頭上:
“為了圣父、圣子的名……上帝,愿時常賜恩惠給我的唯一的子息!”
又厲聲對阿爾達莫諾夫說道:
“記住,我將女兒托付給你,你應對上帝負責!”
阿爾達莫諾夫對他鞠躬,手觸著地板。
“知道的。”
沒有對未來的兒媳說一句和藹的話語,看也不看她和兒子,頭朝門外一指,阿爾達莫諾夫說道:
“出去吧。”
等被祝福的男女走出以后,他坐在病人床上,堅決地說道:“請放心吧。一切會進行順利的。我給我的公爵們當了三十七年的差,沒有一點兒差錯。人不是上帝,人不是慈悲的,很難博取他們的歡喜。親家母烏里央娜,你將來不會錯的。你代替做我的孩子們的母親,我已經吩咐他們要尊敬你老人家。”
巴意馬闊夫聽著,默默地望著屋隅的神像,哭泣了。烏里央娜也啜泣了。這人卻惱怒地說道:
“唉,葉夫賽意·米脫里奇,你回去太早,不肯保重自己。我真是需要你,太需要了!”
他用手將胡須梳得唰唰地響起來,大聲嘆氣。
“我知道你的事情。你誠實又極聰明,你同我再活上五年,事情會做得很好的,但這是上帝的意志。”
烏里央娜喊著,顯得可憐的樣子:
“你這烏鴉怎么盡呱呱地叫著,來嚇唬我們?也許會……”
但是阿爾達莫諾夫站起來,對巴意馬闊夫齊腰鞠躬,像拜死人似的:
“感謝你對我的信心。告辭吧,我要到奧卡河去,載著財產的小船到了。”
他走后,巴意馬闊夫女人生氣地痛哭起來:
“這鄉下野人,連一句和藹的話都沒有對他兒子的未婚妻說一下。”
丈夫阻止她:
“不許哭,不要吵我。”
想了一想,又說:
“你可以依靠他,這人也許比我們這里的人都好。”
巴意馬闊夫死后全城都來送殯致敬,五個教堂的牧師們全到了。阿爾達莫諾夫一家同死者妻女一起在靈后隨行:這使市民們感覺不快。駝子尼基大落在最后,聽見人群里嘟噥著說:
“不知道是什么樣人,居然一下子就鉆到頭位上去。”
博賣洛夫旋轉著橡實色的圓眼,微語道:“死者葉夫賽意和烏里央娜兩人全很謹慎,從不做亂七八糟的事,一定有什么秘密在里面,一定是這鳶鳥用什么方法誘惑了他們,否則他們會同他結成親戚嗎?”
“是的,這是黑暗的事情。”
“我說是黑暗的事情,一定是妖惑。要知道巴意馬闊夫生前真是圣人一樣呀。”
尼基大俯首聽著,駝背彎得低,似在期待打擊。那天有風,風追著人群吹刮,幾百條腿舉起的灰塵像云煙般在人后面飛揚,厚厚地拍貼在除下帽子的油光頭發上面。有人說:
“你瞧,灰塵把阿爾達莫諾夫撒得滿臉,發灰色氣了。這吉卜賽人……”
烏里央娜在丈夫葬后十天上就帶著女兒到修道院去住,把自己房子租給阿爾達莫諾夫。他和他兒子們像狂飆般旋轉著,從早到晚在眾人眼前閃過,在街上迅快地行走,匆忙地向教堂畫十字。父親好嚷鬧,愛怒;長子陰沉,不好說話,顯然是膽怯或害羞;美男子奧萊士卡同男人們好爭辭,看見女人就大膽地眨眼睛。尼基大從日出后就把尖駝背帶到河的對岸的牛舌灣去。在那里,木匠、石匠聚了一大堆,建筑一所長形的、磚制的工人宿舍,又在旁邊奧卡河邊用十二俄寸厚的木頭造了一所雙層大房,活像一所監獄。晚上,特遼莫夫的居民聚在瓦達拉克莎岸旁嗑南瓜子和向日葵子,傾聽鋸刀尖利的嘶聲、刨子的沙響、銳利斧頭甜蜜的裂聲,帶著嘲笑回憶建造巴比倫寶塔的無用。博賣洛夫還用安慰的口氣為這些陌生人預斷一切的不幸:
“春水會把這難看的建筑物淹沒的。也許會發生火災:木匠們盡抽煙,到處是刨屑。”
癆病樣的神父瓦西里應和著他:
“在沙上建筑的。”
“工人聚攏來,開始喝酒,偷東西,淫亂。”
身軀偉大、灌滿脂肪、滿身肥腫的磨坊主人兼酒店老板路加·巴司基用嘶啞的低音安慰大家:
“人多了,容易吃飯。不要緊的,讓他們工作吧。”
最使市民們可笑的是尼基大·阿爾達莫諾夫。他在一大方塊地皮上砍倒柳樹,掘去樹根,整天挖瓦達拉克莎河里的肥爛泥,切開池沼里的泥炭,駝背朝天,放在小車上運走,鋪到沙地上,烏黑的一堆堆地放著。
“想弄菜園呢,”市民們猜出來了,“這個傻子!沙子上加肥料有什么用?”
太陽落山后,阿爾達莫諾夫一家,父親在前,其他人隨著魚貫地渡越小河,身影落在碧綠的水上。博賣洛夫指著說:“瞧呀,瞧,這駝子的影兒!”
大家都瞧見第三個走著的尼基大的影子在異乎尋常地戰栗,似乎比他的弟兄們的長影還重些。有一次,大雨后河水漲了,駝子被河藻絆住腳,或是向坑里踏空,竟沒入水里去了。岸上的旁觀者全都高興得哈哈大笑,只有奧里貢卡·奧洛瓦,醉鬼鐘表匠的十三歲的女兒,憐憫地喊出:
“喔唷,喔唷,要沉死了!”
有人朝她的后腦擊了一下:
“不許瞎嚷嚷。”
走在最后的奧萊士卡鉆身入水,抓起他哥哥,讓他站住了身子。兩人全身濕淋淋,爛泥涂滿在衣裳上。登上岸后,奧萊士卡就一直朝著人群走去,使大家全退后讓開他。有人懼怕地說:
“你這小畜生……”
“他們不喜歡我們。”彼得說。父親一邊走,一邊朝他的臉望了一下:
“過些時候,他們會喜歡的。”
他又罵起尼基大來了:
“你這笨蛋,瞧著點腳,不要讓人家發笑。我們活著不是為受人家嘲笑的,木頭!”
阿爾達莫諾夫一家住在那里,同誰也不相識。一個肥胖的老婦替他們管理家務。她全身穿著玄色服裝,頭上扎著黑頭巾,頭巾的結兒凸出著,像是尖角,說的是一種揉壓的言語,說得不多,也不易了解,好像不是俄羅斯人。關于阿爾達莫諾夫家里的事情向她是打聽不出什么來的。
“假裝做和尚,這些強盜……”
有人打聽出父親和長子常到附近鄉村去勸農人種麻。有一次出行時伊里亞·阿爾達莫諾夫受了偷逃兵士的襲擊。他用縛在鞣皮帶上的兩磅重的鐵錘擲過去殺死了一個,把另一個的腦袋擊破了,第三個便逃走了。警官夸獎阿爾達莫諾夫,但是貧窮的伊里因教區的青年牧師卻為了這殺案決定作贖罪的苦行——站在教堂里誦經四十晝夜。
秋天的晚上,尼基大對父親和弟兄們朗誦圣賢生活記述、教堂長牧的遺訓,父親卻時常打斷他說:
“這些言辭很高深,不是我們的理性所可了解的。我們是粗人,不會想這些,我們生出來是做普通事情的。先公爵猶里讀了七千卷書,用思想用到連上帝也不信了。他走了許多地方,見過不少帝王,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但是造了一所布廠,沒有弄好。無論想做什么,都做不成,只有一輩子靠鄉下人的糧米過活。”
他說時把話語說得很親切,停下來想想,自己凝聽所說的話,重又教訓起孩子們來了:
“你們以后的生活很難過,你們自己就是律法和保障。我這一輩子過的日子不靠自己的意志,是聽人家吩咐的。看出來不應該這樣做,卻不能更改,不是我的事情,是主人的。不但不敢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連想都不敢想一想,就怕把自己的和主人的理性攪亂了。你聽見沒有,彼得?”
“聽見了。”
“對呀。你要明白,人活在世上,好像沒有他似的,自然責任小些,不用自己走路,有人驅使你。不負責任的生活容易過些,但是沒有什么意義。”
有時他說上一兩點鐘,老是問孩子們“聽見沒有”,坐在爐臺上面,腳懸空掛著,手指梳理胡須圈兒,不慌不忙地烙出一環環的話鏈。寬廣清潔的廚房里是溫暖的黑暗,窗外風雪呼嘯,在熨貼玻璃,像熨燙絲綢,或是霜凍在蔚藍的寒冷里破裂著。彼得坐在桌旁蠟燭前面,翻紙作響,輕聲地打算盤珠子;奧萊士卡幫助他;尼基大熟練地用樹枝編筐。
“現在皇上給我們自由了。這應該明了:這解放究意有什么計算?喂羊吃草也不是沒有計算的,現在卻是整個民族,好幾十萬人都被解放了。這意思就是皇上已經明白,在貴族們身上取不到什么,他們自己也要用的。戈渥爾基公爵在解放令以前已經猜到這層,對我說:‘強迫的工作并不合算。’這才信任我們,叫我們做自由的工作。現在當兵的不再背二十五年的槍,卻應該去工作。現在每人應該表現自己能做什么事。貴族制度已到了末途,現在你們自己就是貴族,聽見沒有?”
烏里央娜·巴意馬闊夫在修道院里住了差不多三個月,回家以后的第二天,阿爾達莫諾夫就問她:
“快辦喜事了吧?”
她惱怒了,生氣地瞥著眼睛。
“你怎么啦,醒醒吧!她父親過世還沒有半年,你就……你不知道罪孽嗎?”
阿爾達莫諾夫嚴肅地阻止她:
“親家母,我看不出有什么罪孽。貴族們做得還算少?可是上帝包庇著。我有需要;彼得需要一個女主人。”
隨后他問她有多少錢?她答道:“女兒的妝奩是五百塊錢,多一個也不能給!”
“你會多給的。”這個身材高大的農人盯著她,自信而且不經意地說。他們對坐桌旁,阿爾達莫諾夫靠在桌上,雙手的手指插進胡須的濃絨中,女人皺著眉頭,膽怯地挺直身子。她的年紀已在三十以外,但是她顯得十分年輕,在她的飽滿紅潤的臉上閃耀著淺灰色的、聰明的眼睛。阿爾達莫諾夫站起來,挺直身體。
“你很美麗,烏里央娜·伊凡諾夫娜。”
“還要說什么話?”她問,帶著生氣和嘲弄的神情。
“沒有什么話說了。”
他不高興地走出,沉重地倒退著兩腳。烏里央娜目送著,偶然在衣鏡般的冰面上瞥了一眼,憤憤地微語道:
“胡子鬼,黏上了……”
她感到在這人面前的危險,就走上樓找女兒,但是娜泰里亞不在那里。她向窗外望去,看見女兒在院里大門旁和彼得并立著。烏里央娜趕緊跑下樓梯,站在臺階上喊道:
“娜泰里亞,回家來!”
彼得對她鞠躬。
“年輕人,母親不在身邊,你同她女兒講話,太不合規矩了。以后不準這樣!”
“她是我的未婚妻。”彼得提醒她。
“一樣的,我們有自己的規矩。”烏里央娜說,但是同時又自問道:
“我生氣什么?年紀輕,還能不親熱親熱?有點不好,似乎是妒忌女兒。”
到屋里她狠狠地揪住女兒的辮子,到底禁止她同未婚夫私自講話。
“雖然他已和你定親,但是還沒有到時候,不定怎樣呢。”她嚴肅地說。
陰暗的驚慌攪亂她的思想。幾天以后她到葉爾唐司卡耶那里去問卜未來,全城婦女是常到這頸腺腫的、肥胖的、像一口鐘的魔術婦人那里去訴出自己的罪孽、恐懼和苦痛的。
“這沒有什么可問卦的,”葉爾唐司卡耶說,“我對你直說,你應該依靠這人。我的眼睛朝額角頭上躥不是沒有理由的,我知道人,我看透他們,像看透那副紙牌一樣。你瞧他的事情多么順利,像滾球一般,我們的人妒忌他,只好吞咽惡毒的唾沫。你無須怕他,他生活著不像狐貍,卻是像一只狗熊。”
“就因為是狗熊呀。”寡婦同意著,嘆了一口氣,對女卜者說道,“我害怕,從第一次他來求親的時候就害怕了,好像忽然從黑云里掉下一個誰也不熟識的人,硬來攀親。難道有這樣的事嗎?我記得他說著話,我看著他的傲慢的眼睛,他說的什么話我全答應,好比他掐住我的喉嚨管一般。”
“這就是說,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聰慧的燒圣餅的女人解釋著。
但這一切不能使烏里央娜安心,雖然女卜者從布滿草葉味的屋內送她出去的時候還贈言道:
“記住呀,唯有傻子是在故事里成功事業的……”
她很可疑地把阿爾達莫諾夫大夸一頓,夸得那樣厲害,好像被賄買似的。但是瑪德連娜·巴爾司卡耶,身大,膚黑,干癟得像一條咸鱸魚,卻說了另樣的話:
“全城都替你嘆氣,烏里央娜。你怎么不怕這些外來的人?你瞧!有一個小伙子是駝背,這不是偶然的,父母的罪孽不輕,才生出這樣的怪物來。”
烏里央娜心里難受,時常毆打女兒,同時又感到恨她是沒有理由的。她努力避見房客們,但是那些人卻時常橫梗在她面前,在她的生命上遮掩一層恐慌。
冬不經意地竄進,轟響的風雪,堅固的霜凍立刻侵襲過來,白糖般的雪山壓倒了市街和房屋,椋鳥窠和教堂的尖頂戴上棉帽,白鐵封住了河和池沼的黑水。奧卡河的冰上市民和附近村莊里農人開始了拳擊戲。奧萊士卡每逢節日出去參加拳擊,每次回家時總是挨了打,氣狠狠的。
“怎么啦,奧萊士卡?”阿爾達莫諾夫問,“顯然這里的戰士們比我們的熟練些。”
奧萊士卡用銅幣或冰塊磨擦傷處,陰郁地沉默著,瞥閃著鷹眼。彼得有一次卻說:
“奧萊士卡打得挺兇,只是自己的人——那些城里人——盡打他。”
伊里亞·阿爾達莫諾夫將拳按著桌子,問道:
“為什么?”
“不愛。”
“不愛他嗎?”
“不愛我們大家。”
父親用拳擊著桌子,蠟燭竟從蠟臺里跳出來,熄滅了。黑暗里傳出一陣吼聲:
“你為什么老對我講愛情,好像姑娘一樣?我不要聽這種話!”
尼基大一面點蠟燭,一面說:
“奧萊士卡可以不必去參加拳擊了吧。”
“這樣——為的是使人們笑我們阿爾達莫諾夫害怕了嗎?你住嘴,你這教堂撞鐘的!爛好人!”
這樣把大家都罵了。幾天后晚餐時阿爾達莫諾夫說著和藹、嘮叨的話:
“孩子們,你們最好去獵熊,是一樁好游戲。我同戈渥爾基公爵到略莊司基樹林去過,替他背獵槍,真有趣!”
他興奮地敘述幾樁打獵成功的事件,幾天后就同彼得和奧萊士卡到樹林里去打死一只龐大的老熊。后來弟兄幾人自行前去,追到了一只母熊。它把奧萊士卡的短筒皮襖撕破了,還抓傷了他的大腿,但是弟兄們到底把它打死了,將一對小熊帶回城里,把殺死的野獸留在樹林里,做狼的晚餐。
“阿爾達莫諾夫一家怎么樣?”市民們問烏里央娜。
“沒有什么,很好。”
“豬到了冬天總是安靜的。”博賣洛夫說。
寡婦有點不相信,開始感到從某個時候起人們對阿爾達莫諾夫一家人的仇恨態度會使她生氣,所流露的對于他們的不友善會使她也倒抽一股涼氣。她看見阿爾達莫諾夫一家人生活得清醒,友善,固執地經營自己的事業,看不出什么壞處來。她嚴密地留心女兒和彼得的行動,相信這矮胖、沉默的少年舉止十分嚴正,這與他的年齡不相稱。他并不想把娜泰里亞推到黑暗的屋隅里,搔她的癢癢,附耳說些羞人的話,像城里的那些未婚夫那樣。使她不安的是彼得對她女兒那份不易了解的,干燥的,卻又愛惜的,同時似乎又含著醋意的態度。
“他將是一個不失溫情的丈夫。”
有一天,她走下樓梯時,聽見下面外屋里女兒的聲音:
“你們又要去打熊嗎?”
“想去的。怎么樣?”
“危險得很,奧萊士卡被野獸抓傷了。”
“那是他自己的錯,不應該性急。這么說——你是想我嗎?”
“對于你,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咦,你這女浪人。”母親含笑地想,嘆了一下。
“然而他卻是個笨貨。”
阿爾達莫諾夫帶著越來越堅決的態度對她說:
“趕緊給他們成親吧,否則,他們自己會忙起來的。”
她看出來是應該忙了,姑娘夜間失眠,不能隱瞞肉體苦悶在壓逼著她。復活節時她又把她送到修道院去。過了一月回家后,她看見荒蕪的花園收拾得十分整齊,樹上的苔蘚業已除去,莓果樹全被剪齊,扎好;這全是熟練的手做成的。她順著小道到河邊去,看見駝子尼基大正在修被春水沖倒的籬笆。長及膝蓋的麻布襯衫里可憐地凸露出駝峰的骨架,差不多把包在齊直、光亮的頭發里的巨頭全遮掩住了;尼基大用榆樹枝包住頭發,不使它披露頭上。他的灰色的身形處在嫩綠的葉叢中,很像一個專意工作到自忘程度的老隱士。他揮搖陽光里發銀光的斧頭,熟練地劈砍一根木柱,輕聲淺唱,用女郎的、柔細的聲音,哼著一種教堂的歌調。薄綢樣子的水在籬外閃爍著綠光,陽光的金影在水中嬉戲,活像一群鯉魚。
“上帝幫助你。”女人帶著出乎自己意外的、溫柔的神情說。尼基大柔和的藍眼瞥看她一下,和藹地說道:“上帝保佑。”
“是你收拾的花園嗎?”
“是我。”
“收拾得很好。你愛花園嗎?”
他跪在那里,簡單地講述他從九歲起就被公爵送到花匠那里做學徒,現在他已經十九歲了。
“駝背,卻并不惡。”女人想。
晚上她同女兒在樓上喝茶的時候,尼基大站在門外,手持一束鮮花,不美麗、不愉快的、微黃的臉上含著微笑。
“請收下這一束花。”
“這為什么?”烏里央娜驚奇起來,可疑地審視那束選理得十分美麗的花和草。尼基大對她解釋說,他在貴族家里每天必須送花給公爵夫人。
“噢,原來這樣,”烏里央娜說,臉上帶點紅潤,驕傲地抬頭,“莫非我像公爵夫人嗎?她是不是一個美女?”
“你也是呀。”
烏里央娜又臉紅了。她想道:
“不是他父親教他的嗎?”
“謝謝你這樣尊敬我。”她說,但是并沒有請尼基大喝茶。在他走后,她想著就說出聲來了:
“他的眼睛很好,不像父親的,大概像母親的。”
她又嘆了一口氣:
“顯然,我們同他們住在一起是出于命運。”
等到丈夫去世一周年滿后,她不再勸阿爾達莫諾夫延到秋天再成親,卻堅決地對親家公聲明道:
“只有一樣,伊里亞·阿爾達莫諾夫,請你不要干涉這喜事,讓我照我們的老規矩來辦。這于你也有利的,你可以一下子和我們那些闊人們結交,顯得體面好看。”
“噢,”阿爾達莫諾夫驕傲地吼起來,“沒有這樣,人家也會遠遠地看見我的。”
她看見他這樣傲慢,有點氣,說道:
“這里的人們全不愛你。”
“會懼怕我的。”
他暗笑一聲,聳著肩:
“彼得也老是講什么愛不愛的。你們真是怪物……”
“但是這不愛顯然也落到我的身上。”
“親家母,你不必著急!”阿爾達莫諾夫舉起長手,指頭握緊成拳頭到紫紅的程度,“我會把人們擊碎的,誰也不能在我身邊跳得長久。沒有他們的愛我也過得去的……”
女人不說話了,帶著苦惱的驚慌想道:
“真是野獸。”
于是,她舒適的房屋里擠滿了女兒的女朋友們,城里好家庭的姑娘們。她們全穿上華麗的、古式的、錦織的長袍,帶著洋紗和薄布制成的、白水泡形的袖子,鑲緣邊和莫爾度式的刻花絲邊,手肘上圍著絲花邊,穿著山羊皮和摩洛哥皮的軟靴,長辮上戴著綢結。新娘穿著沉重的、銀色的錦袍,從領子到緣邊縫著一排金色的、細工刺繡的紐扣,肩上披著金錦織的外衣,披著白色和湖色的綢帶。她坐在前面屋隅,像冰人一般,用絲織手帕擦著流汗的臉,一面喘氣,一面響亮地唱詩:
“綠綠的草原上,
紺青的花朵上,
流滿了春水,
冰涼的、混濁的水……”
女郎怨訴的呻吟沉息下去了,女友們就親密地,大聲地接唱下去:
“送我這小姑娘,
送我到水里去,
赤著腳,不穿鞋兒,
光著身,不穿衣裳……”
奧萊士卡埋身在女郎們堆里,嘻嘻哈哈地笑,喊道:
“這支可笑的歌!把姑娘塞在錦織里面,好比火雞裝在洋鐵桶里,還嚷著‘光著身,不穿衣裳!’”
尼基大坐在新娘旁邊,一件藏青的新袍丑陋而可笑地從駝背峰那里擁到腦后,藍眼張得很大,向娜泰里亞很奇怪地望著,似乎懼怕姑娘立刻就要融化,消失似的。瑪德連娜·巴爾司卡耶站在門前,把整個門的空間都占滿了,旋轉眼珠,用深沉的低聲說道:
“你們唱得并不凄涼,姑娘們。”
她跨了一下寬闊的馬步,嚴聲教導她們,應該怎樣照古式唱歌,預備結婚時應帶著怎樣的戰栗。
“古話說:嫁丈夫好比跟從一面石墻。你們要知道墻是厚的,不容易撞破,是高的,不容易跳過。”
但是姑娘們不大聽她。屋里又擠又熱,她們推開老婦人,跑到院里和花園里去了。奧萊士卡穿著金色的綢襯衫、棉絨的馬褲,擠在姑娘們中間,像花叢的蝴蝶,嘻嘻哈哈地喧鬧著,像醉鬼似的快樂。
巴爾司卡耶翹起厚唇,瞪著眼睛,往前高抬錦緞裙子的邊緣,像一股濃煙的烏云般跑上樓去找烏里央娜,用先知者的口氣說道:
“你的女兒很快樂,這個不對,不合規矩。凡是快樂的開始必得到惡劣的終局。”
烏里央娜跪在一只包鐵的大木箱前面,在那里焦心地尋找什么。她身旁地板上,床上,擲滿了一塊塊的錦緞絹布、莫斯科紅綾布、毛絨圍巾、緞帶、繡花手巾之類,像開了一爿市集上的小鋪。寬長的目光靜臥在鮮艷的綢緞材料上面,使它們熠熾著各不相同的光,好像晚霞里的云乳。
“新郎沒有結婚以前就住在新娘的家里,這不合規矩。應該讓阿爾達莫諾夫一家人搬出去……”
“你早說,現在說這話晚了。”烏里央娜喃聲說,身軀俯到箱上,掩藏那副生氣的面孔。她又聽到了一陣低音的話語:
“大家說你是聰明人,所以我也不說了,心想你自己會想到的。于我有什么關系?我呢,只要拿實話說了出來,人家不采納,上帝會記下分數的。”
巴爾司卡耶站在那里,像一尊巨像,頭挺得動也不動,像端一個灌滿了智慧的瓶。她不等到回答,就鉆出門去。烏里央娜在花彩的、火燒的錦緞里跪著,帶著煩惱和恐怖微語道:
“上帝,保佑呀!不要叫我失去理智!”
門外又有衣裳擦響的聲音,她趕緊把頭埋入箱內,藏掩著眼淚。尼基大站在門前說:
“娜泰里亞打發我來問您要不要幫忙。”
“謝謝,親愛的……”
“奧里貢卡·奧洛瓦在廚房里被糖漿燙了一身。”
“啊呀,那怎么辦?很聰明的姑娘,可以做你的媳婦……”
“誰肯嫁我呢……”
園中菩提樹下,坐在圓桌上喝家釀啤酒的有伊里亞·阿爾達莫諾夫、笳佛里拉·巴爾司基——新娘的繼父、博賣洛夫、皮匠芮鐵意金——空虛的眼睛的人和專造大車的伏洛博諾夫。彼得靠在菩提樹上站著,黑發上涂了不少的油,頭好像是鐵制的。他恭敬地傾聽長輩們的談話。
“你們的風俗不同。”父親凝神地說。博賣洛夫吹起牛來了:“我們是基本民族,大俄羅斯!”
“我們也不是附屬的。”
“我們的風俗是古代傳來的……”
“許多莫爾特瓦人、丘瓦士人……”
姑娘們互相推搡著,隨著尖叫聲和嬉笑聲跑進園里,圍著桌子,許多長綢袍成了鮮艷的花圈。她們唱著頌歌:
“喂,偉大的親家公,
伊里亞·阿爾達莫諾夫,
跨一步——折斷一腳,
再跨一步——又折一腳,
跨了三步——腦袋離去。”
“怎么這樣歌頌!”阿爾達莫諾夫轉身向著兒子,驚異地喊了。彼得謹慎地冷笑一聲,望著姑娘們,揪了揪自己的耳朵。
“你再聽下去!”巴爾司基勸著,哈哈地笑了。
“這還不夠,我們的親家公,
姑娘的掠奪者……”
“還不夠嗎?”阿爾達莫諾夫興奮地喊著,顯然感到不安,手指擊著桌子。
姑娘們起勁地唱下去:
“應該和著歌聲讓你撞著犁耙,
從山上把你扔到石上,
好叫你不哄騙我們,
不盡信口夸獎,
那遼遠的異方,
無人跡踏到的荒村,
在那里播滿了憂愁,
撒滿了眼淚……”
“原來是這個意思!”阿爾達莫諾夫生氣地喊著,“姑娘們,我雖然不敢觸怒你們,可是自己的家鄉總是要夸獎的:我們的風俗溫和些,人們客氣些。我們還有一句諺語,司瓦帕和烏騷若流到賽姆河里。托上帝的福,沒有流到奧卡。”
“你等著,你還不大知道我們,”巴爾司基說,不知是夸口,還是恐嚇的意思,“應該賞點什么給姑娘們!”
“給多少?”
“愿給多少就多少。”
阿爾達莫諾夫給了姑娘們兩塊銀盧布。博賣洛夫生氣地說:
“你給得太多,干嗎耍闊!”
“你們是真難侍候呀!”阿爾達莫諾夫也發怒,喊起來了。巴爾司基哄笑了,皮匠芮鐵意金卻向空中撒布著細碎、尖銳的笑聲。
姑娘們的游戲到黎明時才完結。客人散了,屋里每人差不多全睡熟了。阿爾達莫諾夫同彼得和尼基大同坐園中,摸著胡子,低聲地說話,不時向園中看望,眼睛撫摸著玫瑰色的云:
“全是些尖刻的人,不和氣的人。彼得,你丈母娘叫你做什么,你全依著她做,哪怕是女人的無聊事情,也應該做!奧萊士卡去送女孩子們了嗎?女孩子們對他很要好,男孩子們卻正相反。巴爾司基的兒子惡狠狠地看他……尼基大,你應該和氣些,你是會的。你父親在那里做下了裂縫,你就當作封泥,替他擋住了吧。”
他用一只眼睛望著大火壺,繼續陰郁地說:
“大家都喝了酒,喝得像馬一樣。你想什么,彼得?”
彼得手里撫弄絲織的腰帶——新娘的贈物,小聲說道:
“鄉村里隨便些,住得比較安靜。”
“嗯……自然隨便些,即使天天睡覺……”
“他們把婚禮拉得太長了。”
“忍著點吧。”
于是到了彼得困難的大日子了。彼得坐在屋子前面的角落里,明知他的眉頭緊皺著,感到這不大好,使新娘瞧著不愉快,但是不能將眉毛放松一下,像被一根硬線縫住了。他蹙額望著客人們,搖著頭。蛇麻草撒到桌上,撒到娜泰里亞的面紗上。她也低著頭,疲乏地微閉眼睛,面色慘白,害怕得像小孩,由于害臊全身抖索著。
“酒苦呀!”一些通紅的、多毛的嘴臉,張著凸挺出的牙齒,轟吼起來,已經是第二十次了。
彼得轉身過去,像一只狼,不彎下脖頸,抬起面紗,用干燥的嘴唇、鼻子向面頰上撞去,感到她的皮膚上一種像摸到緞子似的涼意,肩頭近于恐懼的顫索。他很憐惜娜泰里亞,也覺得羞慚。但是擠坐成圈的酒客們又喊起來:
“新郎官不會呀!”
“往嘴唇上去!”
“叫我吻起來才好呢……”
酒醉的女人聲音尖響著:
“我來吻你!”
“酒苦呀!”巴爾司基喊了。
彼得咬緊牙齒,把嘴按到新娘的滋潤的唇上。唇抖索著,她全身白白的,似要融化的樣子,好像太陽下的云兒。他們兩人都餓了,從昨天起沒有吃東西。彼得由于心神的驚惶,蛇麻草濃烈的氣味,又喝了兩杯起沫的秦木良司基酒,感到自己醉了,又怕新娘覺察了出來。周圍的一切都動搖了。一群難看的嘴臉形成紅色的泡沫,一會兒見凝為色調斑駁的一堆,一會兒飄散到各處。兒子帶著哀求和生氣的神情看著父親。阿爾達莫諾夫頭發蓬亂,望著烏里央娜赧紅的臉,全身像冒火焰似的喊道:
“親家母,碰一下甜甜蜜蜜的杯!你身上全是蜜——甜得很……”
她伸出一只圓白的手,鑲翠石的金鐲在陽光里閃爍,項珠圈在高聳的胸部搖曳。她也喝了酒,灰色的眼睛里含著疲倦的微笑,微開的唇誘惑地動著。她碰了杯,喝完了酒,向親家公鞠躬。他呢,搖著毛發蓬松的頭,快樂地喊道:
“你的舉動真好,親家母!你真是有公爵夫人的舉動!”
彼得模糊地明了父親的行動有點不大對了。在客人們醉酒的吼鬧中,他微細地捉住博賣洛夫惡意的呼喊、巴爾司卡耶低音的責備話、芮鐵意金的細笑聲。
“不是喜事,卻是——審判所。”他想著,又聽見人家說:
“你瞧這狗怎樣望著烏里央娜。哈,哈!”
“還有一頓喜酒吃,只是沒有牧師……”
這類的話貼進他的耳朵里去,但他立刻就忘掉了,每逢娜泰里亞的膝蓋或手肘觸到他身上,引起他全身一種驚慌的疲倦的時候。他竭力不看她,頭挺直不動,但是眼睛不肯管事,老是向她直盯。
“這一切快完了嗎?”他微語。娜泰里亞答道:“不知道。”
“真叫人害臊……”
“是的。”他聽見她說,很喜歡新娘和他有相同的感覺。
奧萊士卡同女孩們在花園里喝酒;尼基大和長身的神父并坐著,神父滿是雀斑的臉上長著潮潤的胡須、黃色的銅眼。市民們從院里和街上朝敞開的窗里張望,幾十顆頭在蔚藍的空氣里搖動著,不時地互相替換;張開著的嘴微語著,發出嗤聲,呼喊著。窗戶好像是一只只的麻袋,這些喧鬧的頭顱立刻就要從那里像西瓜般滾進屋里。尼基大特別注意到浚河工人奇虹·瓦洛夫的臉,顴骨聳起,長滿赤紅的濃毛和斑點。初看過去沒有什么顏色的眼睛很奇怪地眨閃著,只是眼珠在耀光,睫毛毫不動搖;還有不動的是不大的嘴上柔細、緊閉的唇,四圍有卷曲的胡須微掩著;耳朵不合適地貼在頭蓋骨上。這人將胸部壓在窗臺上,人家想推開他的時候,不嚷,也不罵,只是默默地借著肩和肘輕微的行動抵抗著。他的肩膀圓得筆直,脖頸藏在里面,頭似是從胸部直接生出來的。他好像也是駝背,尼基大在他的臉上找出些易于接近的、善良之點。
一個跛腿少年忽然出其不意地敲響小鼓,手指在鼓皮上緊緊地彈著。小鼓咚咚地響起來。有人打嘯了一下,在膝上伸開兩行鍵的手風琴,立刻在屋的中央旋轉起來。司鐵巴薩·巴爾司基,圓臉、蓬發的男儐相,和著音樂的節拍喊起來了;
“喂,姑娘們——頑抗的女人們,
轉圈跳舞、好游戲的女人們,
我這里錢兒叮叮地響,
對著我,出來吧!”
他的父親挺直魁梧的身軀,大喊道:“司鐵巴薩!不要給城里人丟臉,給那些小雞們看看!”
阿爾達莫諾夫跳起身來,搖動著像掃帚般蓬亂的頭,臉上充滿了血,鼻子像燒煤似的紅,朝巴爾司基的臉上喊道:
“我們不是小雞,是老鷹!還不知誰能跳過誰呢!奧萊士卡!”
奧萊士卡滿臉堆著喜意,像涂上蠟油一般,微笑著審視特遼莫夫的舞客。忽然,他面色慘白,用不可捉摸的迅速的姿勢跑去跳舞,像女孩子那樣尖聲喊叫。
“連諺語都不知道!”特遼莫夫人們喊。阿爾達莫諾夫兇狠的吼聲立即發了出來:
“奧萊士卡——我揍死你!”
奧萊士卡不停歇下來,清脆地踏著鼓聲起落,徹響地呼嘯,大聲唱道:
“有一個靡開老爺,
用了五個仆人。
現在靡開老爺,
自己是一樣的仆人!”
“你們瞧!”阿爾達莫諾夫勝利地咆哮起來。
“嚇,嚇!”神父意義深長地喊著,舉起手指,搖著腦袋。
“奧萊士卡會賽過你們的人的。”彼得對娜泰里亞說。她膽怯地答道:
“身子輕些。”
父親們鼓煽著兒子們,像嗾使戰斗的雄雞。他們喝得半醉,并肩站在一起,一個身材魁梧,舉動笨拙,像一袋燕麥,眉毛底下紅而窄的縫里巨量地流出醉后歡樂的眼淚;另一個抬著整個身體,好像準備跳躍,搖動著長手,撫摸著大腿,眼睛差不多瘋狂的樣子。彼得看見父親顴骨上的須子在動彈著,猜想著:
“他在咬牙吧,立刻會打人的……”
“阿爾達莫諾夫一家跳得不好!”瑪德連娜·巴爾司卡耶發出喇叭管的聲音,“跳得沒有樣子!不強!”
阿爾達莫諾夫朝著她的圓似鐵鍋的臉兒,朝著她寬闊的鼻子哈哈地笑起來。奧萊士卡勝了,巴爾司基的兒子搖曳著身子,走出門外。阿爾達莫諾夫粗魯地把烏里央娜的手抓了一把,命令道:
“喂,親家母,出來跳呀!”
她臉色發白,揮搖著空著的手,含怒而慌張地后退著:
“你怎么啦?叫我同你跳?你怎么啦?”
賓客全不出聲了。博賣洛夫暗笑一聲,同巴爾司卡耶眨著眼,他的話語似油剪般發出咝咝的聲音:
“不要緊!烏里央娜,你讓我們快樂快樂,跳一跳,好不好?上帝會饒恕的……”
“有罪孽——到我身上去好了。”阿爾達莫諾夫喊。
他似乎清醒了,皺著眉頭,好像出場拳擊賽,非出于本意似的。有人把烏里央娜推到他的前面。薄醉的女人傾斜了一下身子,往后退了一步,隨即昂頭挺胸,旋轉起來。彼得聽出有人驚訝地微語著:
“唉,老天爺!丈夫躺在地底下還不到一年,她就把女兒嫁出去,自己跳起舞來!”
他不瞧妻子,卻明白她在替母親害臊,喃聲說:
“父親不該跳的。”
“母親也不該的。”她輕聲,憂郁地回答,站在長椅上,朝擁擠的人的頭上看望;身子搖動了一下,她的手抓住彼得的肩。
“小心!”他和藹地說,扶住她的手肘。
晚霞的薄光,通過觀眾的頭上,從敞開的窗里流了進來,一男一女在這微紅的暮光中像盲人一般的旋轉著。花園里、院里和街上,人們嘻嘻哈哈地笑著,悶熱的屋內越發靜寂了。繃得緊緊的鼓皮碰出一種深沉的聲音,手風琴啜泣著,在青年男女擁擠的一群人里,這一對還在狂熱地滾來滾去,像被燙傷了似的。姑娘們和年輕小伙子們默然望著他們跳舞,持著嚴正的神情,像看特別重視的事情。正經的人們一部分已走到院里,只剩下一些昏倒的、不動的醉鬼。
阿爾達莫諾夫跺了一下腳,停住了:
“你跳過我了,烏里央娜·伊凡諾夫娜!”
女人抖索了一下,也忽然站起身來,像站在墻前一樣,向大眾團轉地鞠躬,說道:
“請恕罪呀。”
她搖著手帕,立刻離開屋子。代替她出場的是巴爾司卡耶!
“引開新郎新娘!喂,彼得,跟我來。儐相們,扶著他!”
父親把儐相們推開,重重的長手擱在兒子的肩上:
“去吧,愿上帝給你幸福!讓我們擁抱一下。”
他推他一下,儐相扶著彼得。巴爾司卡耶在前面行走,一面向各處吐唾沫,一面喃聲說:
“嗤,嗤!無病,無災,無妒忌,無惡行!火呀,水呀,按著時間,免災得福!”
彼得跟著她走進娜泰里亞的房里,里面鋪上一張華麗的床。老婆婆沉重地坐在屋中椅上。
“聽著,別忘掉啦!”她鄭重地說,“給你兩個半塊錢的銀幣,你放在靴里腳趾下面。娜泰里亞進來,跪下來替你脫靴,你別讓她脫……”
“這是為什么?”彼得陰郁地問。
“不是你的事情。你三次不準她脫,第四次才許她,然后她吻你三次,你就把銀幣給她,對她說‘我送給你,我的奴隸,我的命運!’你記住啦!你脫了衣裳,躺下來,背朝著她,她會來請求你:讓我睡吧!你不要作聲,到第三次才向她伸手,明白了嗎?以后就……”
彼得驚訝地看這女教師黑暗寬闊的臉。她張開鼻孔,舔著嘴唇,用手帕擦肥胖的下頜,頭頸,威嚴而親切地說出一些粗魯的、無恥的話來,臨別時還重復著說道:
“呼喊——別相信,眼淚——別相信。”她搖曳著身子,鉆出屋去,留下一種酒醉的氣味。一陣憤怒占據了彼得全身。他脫下靴子,扔到床下,迅快脫衣,跳到床上,像上馬似的,咬緊著牙關,像是受了一種使他透不過氣來的大辱,怕要哭出來似的。
“一些池沼里的小鬼……”
鴨絨被褥的床上熱得很,他跳到地板上,走近窗前,打開窗框,一陣醉酒的哄笑聲,女孩的尖叫聲從園中朝他的臉上撲來。樹際蔚藍色的朦朧里蕩走著一些黑黑的人影。尼古拉鐘樓的細尖頂舉著銅指直觸到天上,沒有十字架,卸下來涂金了。奧卡河在屋頂后面悲戚地發光,圓塊的月亮融化了,無盡休的樹林躺在遠處,黑黑的堆在一起。他憶起另一塊田地——廣闊的田地、金黃的耕田,他抖索了。樓梯上一陣腳步聲,嘻嘻哈哈的笑語,他重又跳到床上。門開了,緞帶窸窣地發聲,皮靴吱吱地作響,有人輕聲啜泣了。放進鐵搭里的門環響了一下,彼得謹慎地抬頭,在朦朧中白色的人形站在門旁,有節拍地揮手,傴身及地。
“禱告呢。可是我沒有禱過告。”
然而又不想禱告。
“娜泰里亞,”他輕聲說,“你別怕。我自己也害怕。煩得要死呀!”
他兩手摸著頭發,揪了揪自己的耳朵,喃聲說:“這一切都用不著,脫靴的一切事情。愚傻事情!我的心痛得很,她還鬧玩笑呢。你不要哭!”
她側著身子,謹慎地走近窗前,輕聲說:
“還在游玩呢。”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