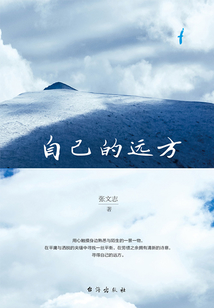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文志行旅
錢國丹
數年前我曾說過,再也不為人寫序或書評這類文字了。因為,把人家十幾、幾十萬字的篇章讀遍吃透,夠讓我費時傷眼了;其次,我不能保證我的禿筆,能否寫出夠格、精準的評價來。
但是張文志是個例外,她的身上,既有江南女子的委婉甜美,也有臺州山海文化鑄就的剛性和硬氣。她的為人和為文都是坦誠的、不矯作的,這讓我喜歡。
《臺州文學》的編輯工作,已經夠她忙的了,更難得的是她還是兩個男娃的媽媽。這雙重身份會讓許多女人叫苦不迭,但是張文志卻做得挺好,還能夠騰出一只手來寫出那么多散文。這實屬不易。
大概五六年前吧,我第一次接觸到文志的散文,不客氣地說,當時她的文字還比較稚嫩,讀來也有些別扭。可是一年之后,她拿給我《門前的風景》中的幾篇,就讓我覺得自然、真誠,字里行間透露的體恤之情,讓我刮目相看了。
志者,記也。斗室書房外的花草,天涯異域的風情,都能成為文志的良好題材。我讀她的文章,能讀出她敏感中的細膩,柔情中的剛性,身體里的脈動。她孜孜不倦地耕耘著散文的一畝三分地。每見風土人情,一有獨特感觸,便瀟灑走筆,以文志之。我忽然覺得,“文志”這名字起得真好。
現在,我面對著電腦屏幕,品讀她即將出版的《自己的遠方》。我比她年長許多,但她與我在文字之間沒有代溝。女性的視角,女兒的情懷,讓我們越來越近,共識陡增。我欣喜她傳達出來的典雅精神,更有一種對自然、對人生的真情實感,和對這個世界、對身邊親友的愛心。
這是一本很精致的散文集。目錄編排就很見創意,全書分三個板塊:《遠方的煙火》《門前的風景》《萬物的光輝》。這三塊是分列的,又是三位一體完美結合的。
善于捕捉細節,是文人一種不可或缺的潛質,它是與生俱來的,也是需要用一顆敏感的心為支撐的。同一次旅行,同幾個景點,有人走過路過,并沒有留住什么。高山的巍峨,草原的無垠,大海的遼闊,云空的深邃,花朵的芬芳,草木的葳蕤,風雨的蕭疏,鳥雀的歡歌,都能成為文志的記憶,留下獨特的雪泥鴻爪;更有那悠然生發出的縷縷情思,讓我觸摸到她的智慧與性靈,撩撥著我的心靈琴弦。
文志的行旅散文,是風景和情思的水乳交融,是人和景物的對話,是心靈的律動。她善于在他鄉迥異的風物中找到家園的元素,讓內心得到慰藉。在哈牡公路上,她看見“到處是莊稼,到處是豐收的氣息。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架勢的遼闊、廣袤,還有開天辟地的豪邁”;在新疆,她想象自己是武俠小說中的冰川天女,披蓑戴笠,雷厲風行;在俠客一樣以夢為馬海闊天空般的馳騁中,她領略到喀納斯湖水的韻味。她關注一閃而過的柳樹:“看著一株株膀大腰圓的大柳林,想起了左宗棠進疆時的悲壯,就問是不是左公柳?——當然不是,左公柳在平涼一帶。可是有什么不同嗎?我看著它們,江南如絲的楊柳,帶雨拂煙中,娉婷婀娜,嫁接不起眼前高大堅強的柳樹,三三兩兩,帶著西出陽關的惆悵,帶著壯士一去不復的決絕。臨水自照早已成為遙遠的絕響,面對沙土,狂風吹過,雖然有柔情,也無處訴說,站立成倔強。”她也寓情于石,因為石能通靈。我看到她寫云南石林的文字:“億萬年雨水流過,從上到下,嵌出了一條條淡淡的直線,又像被巨斧砍斫、撞擊后,石頭身上泛出的灰白的斫痕。而它們身上的橫紋,幾近整齊,深入巨石的內心,是被時光的弦勒出的裂痕。很多都勒得很有分寸,很有比例,看上去,它們如同無數披著各色灰袍的智者,袖著雙手,從容奔赴在時間蒼茫的長河里,從遠古長途跋涉到此,在寬廣的天地間,沉默如金。”
如此文字,收放自如,剛柔相濟,何其瀟灑!
而近處的風景,同樣能搖動她的心旌,激發她的靈感。在國清寺的陽光里,樹林和稻田、院墻和照壁、花葉和甬道,在安詳和莊嚴中,她回到生命最初的感覺。在寺后的佛隴叢林中,她聽到梵唄;在被譽為“東方釋迦”的智者大師肉身塔前,有在石墻下古道上行走的僧侶,她看到智慧感悟的光輝。
當然,文志也感受著許多離你最近的、卻容易讓人熟視無睹的生命,比如窗前的文竹:“從幾寸高的嫩枝,在我忽略的時光里長到兩尺有余,開枝散葉,蔥蘢蓬勃,在風里招搖。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何時長成這般,在我的窗前日夜舞蹈。但我詫異并歡喜它的舞蹈,它在我充滿油煙氣息的房子外添了一分清新。”她寫到兩只春天小鳥的鳴囀,它們的對話是歡樂的,是母子的關切,還是情侶的私語?一切都那么和美,鳥群歌唱者飛過樹林,或在長夜中停留在樹枝上的黑色精靈,如雕塑一樣,同樣給人一種美的悸動。
在這本書里,文志給我們展開很多畫面,無論是被她解救了的一棵受傷的樹,還是被掃帚驅趕著盲目亂撞的蝙蝠,我總能讀出她些許的內疚和無奈。尤其是那種養不活的麻雀,那聲聲的尖叫,那撞墻的慘烈,充滿震撼的力量,更有一種悲壯的美。
張文志在創作中曾經痛楚過:我是如此尋常、平庸的人,我需要那“五斗米”養家糊口,供房供車,贍老養幼。也坦陳:“我誠實地承認我是世俗的人,享受俗世的快樂,也承擔俗世的煩惱。但是我的內心又不甘心于世俗,總是渴望世俗之上的快樂,并能借其消除我俗世的煩惱。”
每個人的文字靈感,是與天地神通的。張文志從寫作中得到一種溫馨,一種慰藉。她曾說,我們向往遠方,到達遠方,“但我們也清楚,我們并不能融入遠方”。其實,處處青山處處家,詩和遠方,就在文志你的身邊。
《法華經》中說得好:“或以歡喜心,歌唄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在張文志的這些文字里,我們看到她的心靈澄澈之后的滿身清涼。
張文志還很年輕,她為人妻為人母,同時也為人女為人媳。她經營著安寧和溫馨,這是需要大智慧和大胸懷的。盡管環境曾經壓抑,生活仍然沉重,一日三餐柴米油鹽,小兒哭大兒鬧……但文志珍惜每一次難得的旅行,遼遠新疆、七彩云南、長白冰城、內蒙古草原,她的文章都讓我看到一個個移動的亮點,在文字營造的意境和氛圍里,她是瀟灑的,是逍遙的。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文志風華正茂,能將讀書、行路、寫作三者有機結合起來,雖然勞累,但她是精彩的。正如她這本集子中的美文,行文是流暢的,文字是旖旎的,品格是高尚的。人生如旅,生命如寄,文志,但愿你的散文能成為永恒,好運和幸福也將伴隨你終身。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