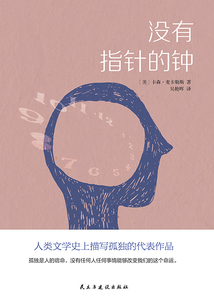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死沒有什么不同,但各有各的死法。托馬斯·詹姆斯·馬龍認(rèn)為死亡就像一件尋常事,悄無聲息地拉開了序幕,所以生命的終結(jié)如同一個(gè)季節(jié)的開始。他四十歲那年的冬天,這個(gè)南方的城鎮(zhèn)異常寒冷——白天冰天雪地、白光爍爍,夜晚冰光四射。1953年3月中旬,春天來勢(shì)洶洶,早花盛開,但風(fēng)刮得昏天黑地,馬龍渾身慵懶無力。他自己是一個(gè)藥劑師,所以他診斷自己是春困,于是給自己開了補(bǔ)肝和補(bǔ)鐵的藥。雖然他容易疲倦,但還是一如既往地生活。他走著去上班,他的藥房是主街區(qū)開門最早的店鋪,下午六點(diǎn)關(guān)門打烊。中午他在市中心的一家餐館吃飯,晚上則回家跟家人一起共進(jìn)晚餐。但他的胃口很挑剔,所以體重一直下降。他把冬裝換成淺色的春裝時(shí),褲子在他高挑而憔悴的身上顯得皺皺巴巴。他太陽(yáng)穴部位的肌肉凹陷了下去,所以咀嚼或吞咽時(shí),血管清晰可見,而喉結(jié)在瘦弱的脖子上費(fèi)力地上下移動(dòng)。但是馬龍感覺沒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他的春困病異常嚴(yán)重,于是他在補(bǔ)藥中加入了老式的硫黃和糖蜜——因?yàn)楸娙梭w驗(yàn)過后證明老藥方是最好的。想到這,他立刻備感欣慰,于是開始了一年一度的菜園打理。后來有一天,他正在配藥時(shí),身體一晃就暈倒了。之后他去看了醫(yī)生,接著在市醫(yī)院做了一些檢查。他還是沒有放在心上,總在抱怨春困和無力,但在溫暖的一天,他又暈倒了——一件平常,甚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馬龍從未想過自己會(huì)死,只是在某個(gè)黃昏,面對(duì)未知的未來,或在買人壽保險(xiǎn)時(shí)會(huì)想到死亡這個(gè)問題。他是一個(gè)普普通通、簡(jiǎn)簡(jiǎn)單單的人,他自己的死只是一個(gè)特別事件罷了。
肯尼斯·海登醫(yī)生是馬龍的優(yōu)質(zhì)顧客,也是他的朋友。他的診所就在藥房的樓上。那天馬龍的檢查報(bào)告出來了,下午兩點(diǎn)鐘馬龍去樓上查看報(bào)告。這次跟海登醫(yī)生單獨(dú)在一起,他第一次感到了難以名狀的恐懼。海登醫(yī)生并沒有直視他,所以海登醫(yī)生那蒼白而熟悉的面容似乎有些陌生。他一本正經(jīng)地跟馬龍打了招呼,接著一聲不響地坐在書桌前,手里拿著一把剪紙刀,不停地從一只手遞到另一只手,而眼睛卻緊盯著剪紙刀。
這種怪異的沉默讓馬龍心神不定,他忍無可忍,脫口而出:“報(bào)告出來了吧,我沒事,對(duì)嗎?”
海登醫(yī)生避開了馬龍悲傷而焦急的目光,眼睛不安地凝視著敞開的窗戶。最后,海登醫(yī)生輕柔而緩慢地說:“我們已經(jīng)仔細(xì)檢查過了,血液中好像有異常的東西。”
房間里干凈而沉悶,一只蒼蠅在嗡嗡地飛來飛去,空氣中彌漫著乙醚的氣味。此刻馬龍意識(shí)到自己身體出了什么嚴(yán)重的問題,但這種沉悶以及馬登醫(yī)生異樣的話音卻讓他無法忍受,于是他開始喋喋不休地辯解道:“我一直覺得你會(huì)查出我有點(diǎn)貧血。你知道我曾學(xué)過醫(yī)學(xué),我懷疑我的血細(xì)胞數(shù)量是否偏低。”
海登醫(yī)生看著自己正往桌子上放的剪紙刀,右眼皮抽搐了一下。
他壓低了嗓音,緊接著說:“既然這樣,我們就從醫(yī)學(xué)角度上談?wù)勥@個(gè)問題。紅細(xì)胞只有21.5萬個(gè),所以有可能存在一種并發(fā)性貧血,但這不是問題關(guān)鍵。如果白細(xì)胞異常增多——共有20.8萬個(gè)。”海登醫(yī)生停頓了一下,摸了摸抽搐的眼皮,接著說:“你可能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馬龍沒有反應(yīng)過來。他驚訝得不知所措,房間里似乎突然異常寒冷。他只知道,在這寒冷刺骨、搖搖欲墜的房間里,某件奇怪而可怕的事情降臨到了他的身上。海登醫(yī)生用粗短而干凈的手指轉(zhuǎn)動(dòng)著剪紙刀,馬龍看著那把旋轉(zhuǎn)的剪紙刀頓時(shí)失了神。雖然記憶模糊不清,但他在腦海里喚醒了一段塵封許久的記憶,讓他想起已被遺忘的羞恥。所以,此刻他同時(shí)飽受著雙重痛苦——海登醫(yī)生的話給他帶來的恐懼和緊張,以及神秘而無法忘懷的羞恥。海登醫(yī)生白皙的手上長(zhǎng)滿了汗毛,馬龍無法直視這樣的手在不停地玩弄剪紙刀,但卻一直鬼使神差地凝視著。
“我記不清了,”他無奈地說,“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沒能從醫(yī)學(xué)院畢業(yè)。”
海登醫(yī)生把剪紙刀放下,遞給他一個(gè)體溫計(jì),說道:“只要把這個(gè)放在舌頭下面就行了。”他瞥了一眼手表,雙手緊扣著背在身后,走到窗前,兩腳分開,站在那里往外看。
“據(jù)光片顯示是白細(xì)胞病理性增加,并伴有并發(fā)性貧血。不成熟的白細(xì)胞占了優(yōu)勢(shì)。簡(jiǎn)單地說——”醫(yī)生中斷了自己的話語,雙手重新握了握,然后踮起腳尖站了一會(huì)兒,“總之,據(jù)我們?cè)\斷就是白血病。”說完他突然轉(zhuǎn)過身,取下馬龍嘴里的溫度計(jì),迅速看完。
馬龍坐在那里,一條腿盤著另一條腿,喉結(jié)在虛弱的喉嚨里上下顫抖,緊張地等待著。他辯解說:“我感覺有點(diǎn)發(fā)燒,但我一直以為只是春困而已。”
“我想給你做一下檢查。愿意的話就脫下衣服,在治療臺(tái)上躺一會(huì)兒——”
馬龍脫掉衣服,躺在治療臺(tái)上,面色蒼白而憔悴,還有幾分不好意思。
“脾臟有些增大。之前身上有沒有長(zhǎng)過腫塊之類的東西?”
“從來沒長(zhǎng)過,”他回答說,“我想我對(duì)白血病有所了解。記得在報(bào)紙上看到有個(gè)小女孩,因?yàn)榈昧诉@種病將不久于人世,所以她的父母9月份就給她過圣誕節(jié)。”馬龍絕望地盯著石灰天花板上的裂縫。隔壁診室里傳來一個(gè)孩子的哭聲,聲音里透露出她的恐懼和掙扎,對(duì)馬龍而言,這哭聲似乎不是來自遠(yuǎn)處,而是源于他自身的痛苦。于是他問:“這個(gè)病——白血病會(huì)讓我送命嗎?”
盡管醫(yī)生沒有說話,但是馬龍心里已經(jīng)知道了答案。隔壁診室里那個(gè)孩子還在痛苦地尖叫著,叫聲持續(xù)了將近整整一分鐘。檢查結(jié)束后,馬龍顫抖著坐在治療臺(tái)的邊緣,對(duì)自己的軟弱和痛苦感到厭惡。他的腳兩側(cè)長(zhǎng)滿了老繭,這讓他深惡痛絕,所以他先把灰色襪子套在腳上。醫(yī)生在角落的洗臉盆里洗著手,不知為何這讓馬龍?zhí)貏e心煩。他穿好衣服,坐回到桌子旁邊的椅子上。他坐在那里用手撫摸著他那稀疏而粗糙的頭發(fā),長(zhǎng)長(zhǎng)的上唇小心地貼著顫抖的下唇,目光里充滿了不安和驚恐,看上去馬龍已經(jīng)是一個(gè)生無可戀的絕癥患者了。
醫(yī)生又開始玩弄起剪紙刀,馬龍又感到意亂神迷,痛苦若隱若現(xiàn);那只手玩弄剪紙刀的情景讓他想起了他的病痛,也讓他記起了那段模糊不清的羞恥。他咽了一口唾沫,鎮(zhèn)定地說:
“唉,醫(yī)生,我還能活多久?”
海登醫(yī)生第一次直視馬龍,并且盯著他看了一會(huì)兒;然后,把目光轉(zhuǎn)向了桌子上面朝他擺放的照片,照片上有他的妻子和兩個(gè)小男孩。“我們都是有家室的人,我是你的話,我明白自己要知道真相,然后把該做的事情安排好。”
馬龍幾乎說不出話來,但當(dāng)話語從他嘴里傳出來時(shí),是那么洪亮而刺耳:“還能活多久?”
蒼蠅的嗡鳴和街道上的喧鬧似乎使沉悶的房間更加寂靜、更加緊張。“我想可能還有一年或十五個(gè)月——難以準(zhǔn)確地估計(jì)。”海登醫(yī)生白皙的手上布滿了一縷縷黑色的長(zhǎng)絨毛,他用雙手不停地?cái)[弄著象牙色的剪紙刀,盡管馬龍有點(diǎn)害怕眼前的場(chǎng)景,但他卻無法轉(zhuǎn)移自己的注意力。他開始飛快地說起話來。
“真奇怪,今年冬天之前,我一直堅(jiān)持投最基本的人壽保險(xiǎn);但今年冬天,我把它改投了享有退休金的保險(xiǎn)——你肯定也注意到雜志上的廣告了。從六十五歲開始直到去世,每個(gè)月可以提取兩百美元。現(xiàn)在想想太可笑了。”他大聲笑了一會(huì)兒,然后接著說,“公司不得不給我轉(zhuǎn)回到原來的保險(xiǎn)——普通的人壽保險(xiǎn)。大都會(huì)保險(xiǎn)公司不錯(cuò),近二十年來我一直在它家投人壽保險(xiǎn)——經(jīng)濟(jì)蕭條時(shí)期投保額度稍有減少,但有能力的時(shí)候我都補(bǔ)全了。退休計(jì)劃的廣告上總有一對(duì)中年夫婦,背景是一個(gè)陽(yáng)光明媚的地方——佛羅里達(dá)州或者加利福尼亞州。但我和我妻子的想法有分歧。我們計(jì)劃去佛蒙特州或緬因州的一個(gè)小地方。一輩子待在這么偏遠(yuǎn)的南方小鎮(zhèn),肯定會(huì)厭倦陽(yáng)光和光亮——。”
話音戛然而止,面臨著厄運(yùn)馬龍無助地哭了起來。他用寬大的雙手捂住臉,竭力抑制著自己的抽泣,那雙手由于酸性物質(zhì)的腐蝕而顯得粗糙。
海登醫(yī)生看了看他妻子的照片,似乎在尋求引導(dǎo),然后輕輕地拍了拍馬龍的膝蓋:“現(xiàn)在這個(gè)時(shí)代,一切皆有可能。每個(gè)月科學(xué)上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一種對(duì)抗疾病的新療法。也許很快他們就會(huì)找到一種控制患病細(xì)胞的方法。同時(shí),我會(huì)盡一切可能延長(zhǎng)你的生命,讓你感到不那么難受。這種疾病有一個(gè)好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什么可以說是好的——那就是不會(huì)有太多的痛苦。我們會(huì)盡最大努力。我建議你盡快到市醫(yī)院辦理入住手續(xù),我們可以給你輸血并做X光檢查。這可能會(huì)讓你感覺好受一些。”
馬龍平靜了下來,用手帕拍了拍自己的臉;然后對(duì)著眼鏡哈了哈氣,擦了擦鏡片,又戴上了。“對(duì)不起,我想我太脆弱了,有點(diǎn)心煩意亂。一切聽您的安排,我隨時(shí)都可以去醫(yī)院。”
第二天一大早,馬龍就住進(jìn)了醫(yī)院,并且在那里待了三天。第一天晚上,他服用了鎮(zhèn)靜劑才睡著,他夢(mèng)見海登醫(yī)生的手和他在辦公桌旁玩弄的剪紙刀。醒來時(shí),他想起了前一天困擾他的那種塵封的羞恥,他明白自己為什么在海登醫(yī)生辦公室里會(huì)莫名地感到痛苦。他還意識(shí)到原來海登醫(yī)生是猶太人。想起那段記憶,他就非常痛苦,所以必須要忘記它。那是馬龍?jiān)卺t(yī)學(xué)院里的第二年,但他沒有通過考試。那是北方的一個(gè)醫(yī)學(xué)院,班上有很多猶太人。那些猶太人的成績(jī)都在平均成績(jī)之上,所以普普通通的學(xué)生沒有公平的競(jìng)爭(zhēng)機(jī)會(huì)。是猶太人把托馬斯·詹姆斯·馬龍擠出了醫(yī)學(xué)院,毀了他當(dāng)醫(yī)生的職業(yè)生涯,所以他只好轉(zhuǎn)行學(xué)了藥理。上學(xué)時(shí),馬龍對(duì)面有一個(gè)叫利維的猶太人,他倆中間就隔著一條過道,上課時(shí)利維總愛擺弄一把鋒利的刀,這讓馬龍無法集中精力聽課。一個(gè)成績(jī)A+的猶太學(xué)生每天晚上都在圖書館學(xué)習(xí),一直學(xué)到圖書館關(guān)門。馬龍感覺那個(gè)學(xué)生的眼皮偶爾也會(huì)抽搐一下。意識(shí)到海登醫(yī)生是猶太人似乎非常重要,因此馬龍納悶自己這些年來怎么沒有發(fā)現(xiàn)。海登是一個(gè)優(yōu)質(zhì)顧客,也算是一個(gè)朋友——他和馬龍?jiān)谕蛔髽抢锕ぷ鳎颐刻於家娒妗qR龍為什么沒發(fā)現(xiàn)海登醫(yī)生是猶太人呢?也許海登醫(yī)生的名字——肯尼斯·黑爾不像是猶太人的名字。馬龍覺得自己沒有偏見,但當(dāng)猶太人像他那樣使用了老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南方人名字時(shí),他感覺有些不妥。他記得海登家的孩子們都長(zhǎng)著鷹鉤鼻,他還記得曾在一個(gè)周六看到海登一家人去了猶太教堂。海登醫(yī)生來查房時(shí),馬龍憂心忡忡地看著他——盡管他是自己多年的朋友和顧客。與其說肯尼斯·黑爾·海登是個(gè)猶太人,不如說他是個(gè)活生生的人,而且會(huì)繼續(xù)活在這個(gè)世界上——而托馬斯·詹姆斯·馬龍卻得了不治之癥,一年或十五個(gè)月后就會(huì)從這個(gè)世界上消失了。一個(gè)人的時(shí)候,馬龍有時(shí)會(huì)暗自流淚。他還睡了不少覺,讀了很多偵探小說。他出院后,脾臟明顯萎縮,但是白細(xì)胞沒有多大變化。他難以預(yù)想幾個(gè)月后會(huì)怎樣,也無法想象死亡時(shí)的樣子。
后來,盡管他的日常生活沒有多大變化,但他卻深陷孤獨(dú)的囹圄。他沒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訴妻子,因?yàn)樗ε虏恍铱赡軙?huì)喚回他和妻子之間的溫情;但是對(duì)婚姻的激情早已隨著兒女的降生而煙消云散了。那一年,艾倫讀初中,湯米八歲了。瑪莎·馬龍精力充沛,但她的頭發(fā)已經(jīng)灰白了——她是一個(gè)好媽媽,也是家庭經(jīng)濟(jì)收入的貢獻(xiàn)者。大蕭條時(shí)期,她做糕點(diǎn)出售,那時(shí)馬龍覺得妻子的做法很合時(shí)宜。馬龍的藥房還清債務(wù)后,妻子繼續(xù)做蛋糕生意,甚至還為附近的一些雜貨店提供精裝三明治,包裝的絲帶上還印著她的名字。她賺了很多錢,也給孩子們帶來了很多福利——她甚至還買了一些可口可樂的股票。馬龍覺得這太過分了;他害怕別人會(huì)說他沒有盡到做丈夫的責(zé)任,這傷害了他的自尊。有一件事他堅(jiān)決反對(duì):他絕不會(huì)去送貨,也禁止自己的兒女和妻子去送貨。馬龍?zhí)_車去送貨,到達(dá)地點(diǎn)后他家的用人飛快地從車上把蛋糕或三明治卸下來。馬龍家的用人要么是年少的要么是年老的,所以他們的報(bào)酬低于現(xiàn)行工資水平。馬龍難以理解他妻子身上發(fā)生的變化。剛結(jié)婚時(shí),妻子是一個(gè)穿著雪紡綢裙的女孩,有一次,當(dāng)一只老鼠從她的鞋子上跑過時(shí),她都嚇暈了——不可思議的是,如今她成了一個(gè)滿頭灰發(fā)的家庭主婦,有了自己的生意,甚至還持有一些可口可樂的股票。現(xiàn)在他生活在一個(gè)怪異的封閉空間里,周圍環(huán)繞著家庭瑣事——中學(xué)的舞會(huì),湯米的小提琴獨(dú)奏會(huì),一個(gè)七層的結(jié)婚蛋糕——日常瑣事就像旋渦中心的枯葉一樣環(huán)繞著他轉(zhuǎn)個(gè)不停,而他卻莫名地?zé)o動(dòng)于衷。
盡管他很虛弱,但是馬龍還是閑不住。他經(jīng)常會(huì)漫無目的地在鎮(zhèn)上的街道上走來走去——穿過棉紡廠周圍雜亂無章、擁擠不堪的貧民窟,或者穿過黑人區(qū),或者穿過中產(chǎn)階級(jí)住宅區(qū)的街道,這些住宅坐落在精心布置的草坪上。他茫然地走著,像一個(gè)心不在焉的人在尋找什么,但卻已忘記了丟失了什么。他時(shí)常無緣無故地伸手隨意地觸摸一些物品;他會(huì)改變路線去觸摸燈柱,或者把手貼在磚墻上。然后他會(huì)愣愣地站著不動(dòng),魂不守舍。他又神情古怪地審視著一棵綠葉蔥郁的榆樹,就像他打量撿起的一片黑樹皮一樣。他雖然會(huì)死去,但是燈柱、墻壁和樹卻會(huì)依然存在,想到這馬龍心生怨恨。還讓他困惑不解的是——他無法接受自己快要死的事實(shí),內(nèi)心的矛盾讓他感到無處不在的虛幻。有時(shí),馬龍隱約感覺自己在一個(gè)混亂的世界里跌跌撞撞,那個(gè)世界顛三倒四、雜亂無章。
馬龍去教堂尋求安慰。當(dāng)虛幻的生與死折磨著自己時(shí),他意識(shí)到第一浸禮會(huì)教堂才是真實(shí)的。第一浸禮會(huì)教堂是鎮(zhèn)上最大的教堂,占了主街區(qū)周圍的半個(gè)市區(qū),估計(jì)市值約有二百萬美元。這樣的教堂肯定是真實(shí)的。該教堂的建造者是一些財(cái)力雄厚的頭面人物。例如布奇·亨德森,他是一位房地產(chǎn)經(jīng)紀(jì)人,也屬于鎮(zhèn)上最精明的商人階層。他擔(dān)任該教堂的執(zhí)事一職,一年到頭忠于職守——像布奇·亨德森這種人可能把時(shí)間和精力浪費(fèi)在虛幻的瑣事上嗎?其他的執(zhí)事如尼龍紡織廠的總裁、鐵路的理事、大百貨公司的老板,都是有責(zé)任心的精明商人,他們的判斷是萬無一失的。他們信任教會(huì),相信有來世。甚至連可口可樂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百萬富翁T.C.韋德威爾,也為教會(huì)捐贈(zèng)了五十萬美元建造教堂的右?guī)俊.C.韋德威爾富有不可思議的遠(yuǎn)見卓識(shí),他相信可口可樂的美好前景,同時(shí)他也信任教會(huì)和來世說,所以他將五十萬美元的遺產(chǎn)贈(zèng)給了教會(huì)。他從未投資失敗過,所以為來世投資也肯定是明智之舉。最后一位會(huì)員是福克斯·克萊恩。他是一位資深的法官,曾擔(dān)任過國(guó)會(huì)的議員——對(duì)于這個(gè)州甚至整個(gè)南方來說都是一種榮耀——他住在鎮(zhèn)上的時(shí)候經(jīng)常去教會(huì),當(dāng)他最喜歡的贊美詩(shī)唱起來的時(shí)候,他激動(dòng)得涕泗橫流。因?yàn)楦?怂埂た巳R恩是教會(huì)人士和忠實(shí)的信徒,所以不管在政治上還是在宗教信仰上馬龍都愿意以這位資深的法官為榜樣。因此,馬龍誠(chéng)心誠(chéng)意地去了教堂。
4月初的一個(gè)星期天,沃森博士做了一場(chǎng)布道,給馬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沃森博士是一位民間的傳教士,他經(jīng)常把自己比作商業(yè)界或體育界的精英。這個(gè)星期天的布道是救世之道,即如何看待死亡。他的聲音響徹了整個(gè)穹頂?shù)慕烫茫?yáng)光透過彩色玻璃窗灑在信徒的身上。馬龍筆直地坐在那里,全神貫注地傾聽著,希望隨時(shí)能得到可以拯救自己的信息。但是,盡管布道時(shí)間很長(zhǎng),他依然不知道什么是死亡,當(dāng)初滿懷希望而來,但當(dāng)離開教堂時(shí),他有種受騙的感覺。什么才是死亡?就像天空一樣一覽無余。馬龍?zhí)ь^仰望著蔚藍(lán)無云的天空,直到脖子酸痛。然后他匆匆地朝藥房跑去。
那天,馬龍經(jīng)歷了一次奇怪的遭遇,盡管表面上看似一件普通的事情。商業(yè)區(qū)空無一人,但他聽到身后有腳步聲,當(dāng)他轉(zhuǎn)過街角時(shí),腳步聲仍然跟在后面。當(dāng)他抄近路穿過一條沒鋪石子的小路時(shí),腳步聲消失了,但他感覺有人在跟蹤他,所以心里很不安。接著他瞥見了墻上的影子,他突然轉(zhuǎn)過身來,與跟蹤者撞在了一起。馬龍一看,這個(gè)跟蹤者是個(gè)黑人男孩,他散步時(shí)似乎經(jīng)常遇見這個(gè)孩子。或許僅僅是因?yàn)檫@個(gè)男孩與眾不同的外表,比較容易被他發(fā)現(xiàn)。這個(gè)男孩中等身材,身強(qiáng)力壯,面容憂郁。除了他的眼睛,他看起來跟其他黑人男孩沒有什么不同。但是他長(zhǎng)著一雙藍(lán)灰色的眼睛,在黑色臉龐的襯托下,顯得冷酷而粗暴。一旦看到這種眼睛,讓人覺得他身體的其他部分也顯得不尋常、不協(xié)調(diào)。他的雙臂太長(zhǎng),胸部太寬——表情時(shí)而多愁善感,時(shí)而故作陰郁。既然這個(gè)小男孩給馬龍留下了這種印象,馬龍就不單純地把他看作一個(gè)黑人男孩——他心里自然而然地用很刺耳的詞稱他為“可惡的黑鬼”,雖然他不認(rèn)識(shí)這個(gè)男孩,但通常他在這種事情上是寬宏大量的。當(dāng)馬龍轉(zhuǎn)過身時(shí),他們撞了個(gè)滿懷,黑鬼站穩(wěn)腳后,一動(dòng)不動(dòng)地站在那里,但是馬龍往后退了一步。他們站在狹窄的小巷里對(duì)視著。兩人的眼睛都是一樣的灰藍(lán)色,起初看起來像是一場(chǎng)瞪眼睛比賽。黑色臉龐上的一雙冰冷而炯炯有神的眼睛盯著馬龍——馬龍感覺他的目光顫動(dòng)了,接著變得堅(jiān)定而怪異,看似知道馬龍的處境。馬龍感覺這個(gè)男孩子知道他很快就要死了。這種感覺來得太快,讓馬龍感到很震驚,所以馬龍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轉(zhuǎn)過身去。他們相互對(duì)視了不超過一分鐘,也沒有造成任何明顯后果——但是馬龍覺得已經(jīng)完成了一件重大而可怕的任務(wù)。他搖搖晃晃地走到了小巷的盡頭,看到了一張張普通而友好的面孔,他才如釋重負(fù)。他輕輕松松地走出小巷,走進(jìn)了他那安全、普通而熟悉的藥房。
星期天晚餐之前,老法官經(jīng)常會(huì)到藥房里喝點(diǎn)東西。馬龍高興地看到他已經(jīng)在那里了,正對(duì)著冷飲柜前的一群好友侃侃而談。馬龍心不在焉地向顧客打完招呼,就走開了。天花板上的電風(fēng)扇嗡嗡地轉(zhuǎn)著,屋里彌漫著混合的味道——冷飲柜里散發(fā)出的糖漿味,摻雜著后面混合區(qū)散發(fā)出的藥味。
馬龍路過老法官去后屋時(shí),老法官停下了高談闊論,對(duì)他說:“馬上去找你,托馬斯·詹姆斯。”老法官人高馬大,面色緋紅,頭發(fā)黃白相間,十分蓬亂。他身穿一套皺巴巴的亞麻白西裝,里面套著一件淡紫色襯衫,打著一條裝飾著珍珠夾子的領(lǐng)帶,上面沾著咖啡漬。他的左手因中風(fēng)而不聽使喚了,所以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柜臺(tái)邊上。因?yàn)檫@只手不能用了,所以看上去很干凈,還有點(diǎn)浮腫——但他說話時(shí)經(jīng)常舉起的右手,指甲臟兮兮的,無名指上戴著一顆鑲著藍(lán)寶石的戒指。他手里拿著一根銀手柄的黑檀木拐杖。老法官結(jié)束了對(duì)聯(lián)邦政府的長(zhǎng)篇大論,到配藥室去找馬龍了。
這個(gè)房間很小,中間用一堵擺滿了藥瓶的墻隔開,一邊是藥房,另一邊是商店。藥房這邊只能放一把搖椅和一張開處方的桌子。馬龍拿出一瓶波旁威士忌,打開角落里的一把折疊椅。法官擠進(jìn)了房間,低著頭小心翼翼地坐到搖椅上,龐大的身體上散發(fā)出汗味與蓖麻油和消毒劑的混合氣味。馬龍倒酒時(shí),威士忌酒輕輕地流到了酒杯的底部。
“沒有什么比星期天早上第一杯波旁威士忌倒入酒杯的聲音更悅耳了。巴赫、舒伯特以及其他音樂大師都統(tǒng)統(tǒng)見鬼去吧,我孫子就彈他們的曲子……”老法官唱了起來:
“哦,威士忌就是男人的生命力——哦,威士忌!哦,喬尼!”
他慢慢地品著酒,每咽下一口后都要停頓一會(huì)兒,舌頭在嘴里舔舐著余香,然后再抿一點(diǎn)。馬龍喝得很快,酒好像到了他的肚子里才像玫瑰一樣散發(fā)出香味。
“托馬斯·詹姆斯,你有沒有想過,目前南方的這場(chǎng)革命風(fēng)暴和美國(guó)內(nèi)戰(zhàn)一樣恐怖?”馬龍未曾想過這個(gè)問題,但他把頭轉(zhuǎn)向一邊,嚴(yán)肅地點(diǎn)點(diǎn)頭,老法官繼續(xù)說,“革命風(fēng)暴愈演愈烈,足以摧毀南方的根基了。人頭稅很快就會(huì)被廢除,所有愚蠢的黑鬼都將享有投票權(quán)了。下一步就是平等的教育權(quán)利了。想象一下,將來為了學(xué)習(xí)讀書和寫字,一個(gè)嬌嫩的白種小女孩必須和煤黑般的黑人孩子同桌。高得離譜的最低工資法,將是南方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喪鐘,這可能會(huì)強(qiáng)加在我們身上。想想按小時(shí)支付一群干農(nóng)活的粗人,真是不值得。聯(lián)邦住宅項(xiàng)目已經(jīng)摧毀了房地產(chǎn)投資者。他們稱這是貧民窟大清理——但我想知道,貧民窟是誰造成的?難道是住在貧民窟里的那些目光短淺的人自己造成的?記住我的話,那些聯(lián)邦公寓樓——不管是現(xiàn)代的還是北歐風(fēng)格的——十年后也會(huì)變成貧民窟。”
馬龍虔誠(chéng)地傾聽著,就像在教堂里聆聽布道一樣。他和法官之間的友誼是他一個(gè)最大的驕傲。自從來到米蘭后,馬龍就認(rèn)識(shí)了法官;狩獵季節(jié)時(shí),他經(jīng)常去法官的獵場(chǎng)里打獵——法官的獨(dú)生子去世之前,馬龍每逢周六和周日都去那里打獵。盡管法官生病了,但是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依然很親密——當(dāng)時(shí)這位老議員的政治生涯似乎走到了盡頭。每逢星期天馬龍都會(huì)去拜訪法官,從自家的菜園里帶去一堆大頭菜,或是法官喜歡的水磨玉米粉。有時(shí)他們會(huì)玩撲克牌——但通常法官會(huì)高談闊論,馬龍只是傾聽者。只有這些時(shí)候馬龍才感覺自己離權(quán)力中心很近——似乎感覺自己也是一名國(guó)會(huì)議員。法官能起來四處走動(dòng)時(shí),他經(jīng)常在星期天去馬龍的藥房,一起在配藥室里暢飲一番。如果馬龍對(duì)老法官的想法有疑慮,老法官就會(huì)立即遮掩過去。他到底是為了誰而對(duì)議員吹毛求疵?如果連老法官都不正確,還有誰會(huì)是對(duì)的?現(xiàn)在老法官又說起了再次參加國(guó)會(huì)的競(jìng)選,馬龍覺得老法官應(yīng)該擔(dān)此重任,對(duì)此馬龍感到心滿意足。
喝到第二杯酒時(shí),法官拿出一盒雪茄,因?yàn)榉ü俚囊恢皇植混`活,所以馬龍也給他抽出一根。煙霧垂直飄到了低矮的天花板上,然后慢慢散開。沖著大街的門開著,一縷陽(yáng)光照射進(jìn)來,把煙霧變成了乳白色。
馬龍說:“我有一個(gè)嚴(yán)肅的請(qǐng)求,我想起草我的遺囑。”
“隨時(shí)愿意為您效勞,托馬斯·詹姆斯,你有什么特殊要求嗎?”
“哦,沒有,就是常見的那種遺囑——但我希望你能盡快擬好。”他平靜地補(bǔ)充道,“醫(yī)生說我的時(shí)日不多了。”
法官不再搖晃搖椅了,他放下杯子:“為什么?到底是怎么了?你怎么了,托馬斯·詹姆斯?”
馬龍第一次向人提起了自己的病情,說出來后似乎感覺如釋重負(fù):“我好像有血液病。”
“血液病!不可能,這太荒謬了——你身上流淌著這個(gè)州最好的血液。我非常清楚地記得你的父親,他在梅肯的十二號(hào)街和桑樹街的拐角開了一家藥材批發(fā)店。而且我也記得你的母親——她來自威爾瑞特家族。你的血管里流淌著最好的血液,托馬斯·詹姆斯,永遠(yuǎn)不要忘記這一點(diǎn)。”
馬龍感到了一絲快樂和驕傲,但這種感覺卻轉(zhuǎn)瞬即逝:“醫(yī)生——”
“噢,醫(yī)生——雖然我對(duì)醫(yī)生非常尊重,但我很少相信他們說的話。不要讓他們嚇到你。幾年前,我得了點(diǎn)小病,我的醫(yī)生——弗萊伍爾分院的塔圖姆醫(yī)生——開始向我灌輸一些危言聳聽的言論。禁止喝酒、禁止抽雪茄甚至是香煙。似乎我最好學(xué)著彈豎琴或去鏟煤。”法官用右手撥動(dòng)著想象中的琴弦,又?jǐn)[了一個(gè)鏟煤的姿勢(shì),“但是我和醫(yī)生談了談,就隨著自己的直覺去行事。直覺才是一個(gè)人唯一遵從的。現(xiàn)在,我身強(qiáng)力壯、精力充沛,這可能是同齡人夢(mèng)寐以求的狀態(tài)。可憐的醫(yī)生,頗為諷刺的是——在他的葬禮上是我給他抬的棺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醫(yī)生是一個(gè)絕對(duì)的禁酒者,他從不吸煙——但他偶爾喜歡嚼一下煙葉。他是一個(gè)了不起的人物,也是醫(yī)學(xué)界的驕傲,但是他跟他的同行一樣,診斷病情時(shí)大驚小怪,所以難免判斷失誤。別讓他們嚇到你,托馬斯·詹姆斯。”
馬龍備感欣慰,當(dāng)他開始再喝一杯時(shí),他開始懷疑海登醫(yī)生和其他醫(yī)生是否診斷失誤:“光片子顯示的是白血病,血細(xì)胞計(jì)數(shù)顯示白細(xì)胞數(shù)量明顯增多。”
“白細(xì)胞?”法官問道,“什么東西啊?”
“就是白血球。”
“從沒聽說過。”
“但是它們的確存在。”
法官撫摸著手杖的銀手柄,開口說:“如果是你的心臟、肝臟,甚至是腎臟出了問題,我能理解你的惶恐不安。但是由于白細(xì)胞過多而引起的無足輕重的紊亂,對(duì)我來說似乎有點(diǎn)無關(guān)痛癢。我怎么活了八十多年,卻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是否有白細(xì)胞這種東西?”法官的手指反射性地蜷曲了起來,他一邊重新伸直手指,一邊用藍(lán)眼睛疑惑地看著馬龍,“盡管如此,但是確實(shí)你最近看起來有些憔悴。肝臟有利于血液健康。你應(yīng)該吃點(diǎn)脆炸牛肝和洋蔥醬腌制的牛肝,既美味又是天然的良藥。陽(yáng)光是血液調(diào)節(jié)劑。我敢打賭,你沒有什么毛病,保持合理的生活方式,再曬曬米蘭夏天的陽(yáng)光,很快就會(huì)恢復(fù)健康。”法官舉起了杯子,“這是最好的滋補(bǔ)劑,刺激食欲,放松神經(jīng)。托馬斯·詹姆斯,你只是緊張和害怕而已。”
“克萊恩法官。”
格瑞恩·波伊走進(jìn)房間,站在那里等待著。他是黑人薇瑞莉的侄子,薇瑞莉是法官家的用人。這個(gè)男孩十六歲了,個(gè)頭高挑,體態(tài)肥胖,樣子傻傻的。他身上穿著一套淺藍(lán)色的西裝,衣服緊繃繃地捆在身上,腳上穿了一雙尺碼偏小的尖頭鞋子,所以走起路來躡手躡腳、一瘸一拐的。他感冒了,雖然胸口的口袋里有手帕,但他還是用手背擦了擦流出來的鼻涕。
“今天是星期天了。”他說。
法官把手伸進(jìn)口袋,拿出一枚硬幣給了他。
格瑞恩·波伊一邊迫不及待地、一瘸一拐地向冷飲柜走去,一邊回頭拖著甜甜的嗓音說:“萬分感謝,克萊恩法官。”
法官同情地向馬龍飛快地瞥了幾眼,但當(dāng)馬龍轉(zhuǎn)過身來時(shí),他避開了他的目光,又開始撫摸起他的手杖。
“每時(shí)每刻——每個(gè)活著的靈魂都在接近死亡——但我們會(huì)時(shí)常想起死亡嗎?我們坐在這里喝著威士忌,抽著雪茄,時(shí)時(shí)刻刻我們都在接近生命的終點(diǎn)。格瑞恩·波伊無憂無慮地吃著他的蛋筒冰激凌。現(xiàn)在我已是垂暮之年,死神曾與我爭(zhēng)斗過,結(jié)果雙方僵持著不分上下。在死神的古老戰(zhàn)場(chǎng)上,我是它的受害者。唉,自從我兒子死后,我等了十七年了。哦,死亡之神,現(xiàn)在你的勝利在何方?那個(gè)圣誕節(jié)的下午我兒子自殺后,死神就贏得了勝利。”
“我時(shí)常會(huì)想起他,”馬龍安慰說,“對(duì)此我感到很難過。”
“為什么——他為什么要這么做?一個(gè)相貌堂堂、前途無量的孩子——還不到二十五歲,大學(xué)的畢業(yè)成績(jī)非常優(yōu)秀。他已經(jīng)取得了法律學(xué)位,而且極有可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他娶了一個(gè)漂亮而年輕的妻子,還有一個(gè)即將出生的孩子。他的生活衣食無憂——甚至可以說是腰纏萬貫——這也是我運(yùn)氣的鼎盛時(shí)期。去年我花了四萬美元給他買了塞雷諾農(nóng)場(chǎng)作為畢業(yè)禮物——農(nóng)場(chǎng)里有將近一千英畝的頂級(jí)桃園。他出身于富貴之家,命運(yùn)的寵兒,諸事順利,才開始他的宏圖偉業(yè)。他可能會(huì)成為總統(tǒng)——他可能事事如愿以償。他為什么要死呢?”
馬龍小心翼翼地說:“可能是突發(fā)抑郁癥。”
“他出生的那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顆非常閃亮的流星。那是一個(gè)明亮的夜晚,那顆流星在一月的天空上畫出了一道弧線。米西小姐已經(jīng)分娩了八個(gè)小時(shí),我一直蹲在她的床前,一邊祈禱一邊流淚。然后塔特姆醫(yī)生把我拎起來,然后使勁把我拉到門口說:‘滾出去,你這個(gè)頑固的老東西——要么去廚房把自己灌醉,要么去院子里走走。’我走出院子,抬頭仰望天空時(shí),我看到了那顆流星劃出的弧線,就在那時(shí),我兒子約翰尼出生了。”
“毫無疑問,這是有先兆的。”馬龍說。
“后來,我沖進(jìn)廚房忙碌開了——已經(jīng)是四點(diǎn)鐘了——我給醫(yī)生炸了一對(duì)鵪鶉蛋,煮了一些玉米糊。我一直擅長(zhǎng)炸鵪鶉蛋。”法官停頓了一下,然后怯生生地說,“托馬斯·詹姆斯,你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不可思議的事情嗎?”
馬龍看著法官悲傷的面龐,什么也沒有說。
“那年圣誕節(jié)我們晚餐吃的是鵪鶉,而不是傳統(tǒng)的火雞。我兒子約翰尼圣誕節(jié)之前的星期天去打過獵。唉,生活的模式——無關(guān)大小。”
為了安慰法官,馬龍說:“也許那是個(gè)意外,也許約翰尼只想擦擦他的槍。”
“但那不是他的槍,那是我的手槍。”
“圣誕節(jié)前的那個(gè)星期天我去塞雷諾農(nóng)場(chǎng)打獵了。可能是因?yàn)樗查g的抑郁導(dǎo)致約翰尼的自殺。”
“有時(shí)我也這么想,”法官停了下來,因?yàn)槿绻俣嗾f一個(gè)字,他可能會(huì)哭,馬龍拍了拍他的胳膊,法官平靜了一下,然后又開始說起來,“有時(shí)候我覺得這是為了報(bào)復(fù)我。”
“哦,不!當(dāng)然不是這個(gè)樣子,先生。沒有人會(huì)想到,也沒有人能控制抑郁癥。”
“也許是這樣吧,”法官說,“但就在那天我們吵過一架。”
“那有什么?每個(gè)家庭都有吵架的時(shí)候。”
“我兒子想推翻一條公理。”
“公理?什么樣的公理?”
“是關(guān)于一些無關(guān)緊要的事情。牽扯到一件黑人的案子,我負(fù)責(zé)宣判的。”
馬龍說:“你沒有必要自責(zé)了。”
“我們坐在桌旁,喝著咖啡、抽著雪茄,品嘗著法國(guó)干邑白蘭地——女士們都在客廳里——約翰尼越來越激動(dòng),最后他沖我喊了些什么,然后沖上樓去了。幾分鐘后我們就聽到了槍聲。”
“他總是好沖動(dòng)。”
“如今,似乎年輕人都不愿意征求長(zhǎng)輩們的意見。我兒子一時(shí)興起,跳完一支舞后就決定結(jié)婚了。他叫醒了他媽媽和我,然后對(duì)我們說:‘我和米拉貝爾結(jié)婚了。’告訴你,他們偷偷跑到了治安官那里登記結(jié)婚了。這對(duì)他母親來說是一種沉重的打擊——不過后來倒是壞事變好事了。”
“你的孫子很像他的父親,”馬龍說。
“簡(jiǎn)直是一個(gè)模板刻出來的。你曾見過這么光彩照人的兩個(gè)男孩嗎?”
“這對(duì)你來說一定是一種極大的安慰。”
法官吸了口雪茄,然后回答道:“安慰——焦慮——這就是他留下的所有。”
“他打算學(xué)習(xí)法律,然后從政嗎?”
“絕對(duì)不可能!”法官粗暴地說,“我不想讓這個(gè)男孩從事法律或政治工作。”
馬龍說:“杰斯特不管干哪個(gè)行業(yè)都會(huì)成功的。”
“死亡,”老法官說,“是最大的背叛。托馬斯·詹姆斯,醫(yī)生認(rèn)為你得了不治之癥。我不這么認(rèn)為。雖然我很敬仰醫(yī)學(xué)界,但是連醫(yī)生都不知道什么是死亡——還有誰能知道呢?甚至塔特姆醫(yī)生都不懂。十五年來我這個(gè)老東西一直期望著死亡,但是死神太狡猾了。當(dāng)你靜候它,最后要面對(duì)它的時(shí)候,它卻永遠(yuǎn)銷聲匿跡了。它會(huì)跟你擦肩而過,降臨到蓄意等候者的身上,也會(huì)光顧那些將它置之腦后的人。哦,為什么,托馬斯·詹姆斯?我那光芒四射的兒子到底怎么了?”
“福克斯,”馬龍問,“你相信永恒的生命嗎?”
“我絕對(duì)相信生命的永恒。我知道我的兒子將永遠(yuǎn)活在我的身邊,我的孫子也將永遠(yuǎn)活在我和他的身邊。但是什么是永恒呢?”
“在教堂里,”馬龍說,“沃森博士做了一個(gè)關(guān)于救世的布道,即什么是死亡。”
“好動(dòng)聽的語言——真希望我已經(jīng)提到過。但根本沒有意義,”他最后補(bǔ)充道,“不,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來說,我不相信永恒之說。對(duì)我所知道的事情以及自己的子孫后代,我深信不疑。我也信任我的祖先。這能稱之為永恒嗎?”
馬龍突然問:“你見過那個(gè)藍(lán)眼睛的黑鬼嗎?”
“你是說一個(gè)長(zhǎng)著藍(lán)眼睛的黑人?”
馬龍說:“我說的不是那些眼睛是藍(lán)色的,但視力下降、上了年紀(jì)的黑鬼。我指的是一個(gè)年輕的黑人男孩,他長(zhǎng)著一雙灰藍(lán)色的眼睛。這個(gè)鎮(zhèn)上就有一個(gè)這樣的人,今天我被他嚇了一跳。”
法官的眼睛就像藍(lán)色的泡泡,他喝完了自己的酒,然后開口說起來:“我知道你說的那個(gè)黑鬼。”
“他是誰啊?”
“他只是鎮(zhèn)上的一個(gè)黑鬼,我對(duì)他不感興趣。他給人推拿按摩,賣點(diǎn)雜貨——一個(gè)萬事通。而且,他是一個(gè)職業(yè)歌手。”
馬龍說:“我在藥店后面的一條小巷里遇見的他,他嚇了我一大跳。”
法官加重了語氣,似乎當(dāng)時(shí)特意針對(duì)馬龍說:“那個(gè)黑鬼叫謝爾曼·皮爾,我對(duì)他不感興趣。不過,因?yàn)槿耸植粔颍艺紤]雇他當(dāng)用人。”
馬龍說:“我從沒見過這么奇怪的眼睛。”
“野生的小馬駒,”法官說,“床笫之事出了差錯(cuò)。他被遺棄在圣阿森松島教堂里。”
馬龍覺得法官隱瞞了一些秘密,但對(duì)于法官這樣的大人物,不適合跟他打探一些八卦的事情。
“杰斯特——說曹操,曹操就到——”
約翰·杰斯特·克萊恩站在房間里,陽(yáng)光灑在他的后背上。他十七歲了,體格有點(diǎn)柔弱,一頭紅褐色的頭發(fā),面色白皙,翹翹的鼻子上的雀斑就像灑在奶油上的肉桂。耀眼的陽(yáng)光使他的紅頭發(fā)閃閃發(fā)光,但他的臉上卻灰暗一片,他的酒褐色的眼睛躲開了刺眼的陽(yáng)光。他穿著一條藍(lán)色的牛仔褲和一件條紋運(yùn)動(dòng)衫,運(yùn)動(dòng)衫的袖子卷到了纖細(xì)的胳膊肘處。
“趴下,泰格。”杰斯特說。這只狗是一只布林德拳擊犬,也是鎮(zhèn)上獨(dú)一無二的一只。它是個(gè)兇猛的畜生,馬龍單獨(dú)在街上看見它時(shí),感到膽戰(zhàn)心驚。
“爺爺,我獨(dú)自去開飛機(jī)了。”杰斯特興奮地叫道,然后,看到馬龍,他禮貌地補(bǔ)充道,“嘿,馬龍先生,你今天過得怎么樣?”
法官那虛弱的眼睛里熱淚盈眶,淚水里夾雜著回憶、驕傲以及酒精的作用:“親愛的,你一個(gè)人開的飛機(jī)嗎?感覺如何?”
杰斯特想了一會(huì)兒,然后回答說:“感覺和我預(yù)想的不完全一樣,原本我以為會(huì)感到孤獨(dú)和驕傲,但感覺自己只是在看那些設(shè)備。我想我只是覺得——一種責(zé)任感。”
“想象一下,托馬斯·詹姆斯,”法官說,“幾個(gè)月前,這個(gè)臭小子剛向我宣布他正在機(jī)場(chǎng)里上飛行課。他自己攢了錢,已經(jīng)安排好了課程。但根本沒有跟我商量,就直接宣布:‘爺爺,我正在上飛行課。’”法官撫摸著杰斯特的大腿,“是不是這樣,乖寶貝?”
杰斯特兩腿交叉著站在那里,回答說:“這沒什么。每個(gè)人都應(yīng)該學(xué)會(huì)飛行。”
“是誰讓這些年輕人有權(quán)利做出這種聞所未聞的決定?在我和你的年代里,沒人會(huì)這么做,托馬斯·詹姆斯你現(xiàn)在該明白我為什么這么擔(dān)憂了吧?”
法官的聲音中透露著悲傷,杰斯特熟練地把杯子從他的手里拿下來,藏在角落的架子上。馬龍看到了這一幕,他替法官感到生氣。
“該吃飯了,爺爺。汽車就在路旁。”
法官扶著手杖艱難地站了起來,那條狗開始向門口走去。法官邊走邊說:“你說什么時(shí)候走就什么時(shí)候走,乖寶貝。”走到門口時(shí)他回頭對(duì)馬龍說:“別讓醫(yī)生嚇到你,托馬斯·詹姆斯,死神是一個(gè)很會(huì)耍花招的游戲玩家。我和你可能會(huì)在一個(gè)十二歲女孩的葬禮之后,共赴黃泉路。”他用臉頰貼了貼馬龍的臉,然后跨過門檻來到大街上。
馬龍來到藥店的前面去鎖正門,無意中聽到了祖孫倆的談話。聽到杰斯特說:“爺爺,有些話我不想說,但又不得不說,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在陌生人面前叫我乖寶貝或小寶貝了。”
那時(shí)馬龍覺得杰斯特很討厭。“陌生人”這個(gè)稱呼深深傷害了馬龍,雖然法官的話讓他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但此刻那束光芒卻又瞬間暗淡下來。過去,對(duì)每個(gè)人都熱情好客,真誠(chéng)地讓他們有歸屬感,即便是燒烤活動(dòng)時(shí)認(rèn)識(shí)的普通成員,也會(huì)讓他們感覺不孤獨(dú)。但如今,好客的真誠(chéng)已經(jīng)消失殆盡,只有孤立和隔閡。杰斯特才是個(gè)“陌生人”——他根本不像個(gè)在米蘭長(zhǎng)大的男孩子。他傲慢自大,卻又過于彬彬有禮。這個(gè)男孩自身以及他的柔弱背后隱藏著某種東西,他的活潑開朗似乎有點(diǎn)綿里藏針——他就好像是一把包在絲綢里的尖刀。
法官似乎沒有聽清他的話。“可憐的托馬斯·詹姆斯,”他一邊開車門,一邊說,“真是太難以置信了。”
馬龍很快鎖上了前門,回到了配藥室。
他獨(dú)自一人。他坐在搖椅上,手里拿著藥杵。藥杵是灰色的,表面因?yàn)殚L(zhǎng)期使用所以磨得很光滑了。二十年前開業(yè)時(shí),連同藥房的其他設(shè)備一起買下的。原本藥杵是格林洛夫先生的——上一次想起他是什么時(shí)候?——他死后,地產(chǎn)商變賣了他的所有財(cái)產(chǎn)。格林洛夫先生用這個(gè)藥杵用了多久?誰在他以前還用過它?……這個(gè)藥杵舊得不能再舊了,卻仍然堅(jiān)不可摧。馬龍想知道它是否是印第安人時(shí)代留下的遺物。雖然它是一件老古董了,但還能用多久呢?這塊石頭似乎在嘲笑馬龍。
他打了一個(gè)冷戰(zhàn)。就如一陣風(fēng)吹過,盡管他發(fā)現(xiàn)雪茄的煙霧沒有消散,但他卻冷得瑟瑟發(fā)抖。一想到老法官的話語,就像聽到了一曲挽歌,讓他不再那么害怕和恐懼。他記得約翰尼·克萊恩,也忘不了在塞雷諾農(nóng)場(chǎng)的往日時(shí)光。他對(duì)塞雷諾農(nóng)場(chǎng)并不陌生——狩獵季節(jié)他是塞雷諾農(nóng)場(chǎng)的常客,有一次他甚至在那里住了一晚。他和約翰尼一起睡在一張由四根柱子支撐的大床上,早上五點(diǎn)鐘他們就進(jìn)了廚房,他仍然記得魚子和熱餅干的味道,還有獵捕前他們吃早餐時(shí)狗身上潮濕的味道。是的,很多次他被邀請(qǐng)去塞雷諾農(nóng)場(chǎng),和約翰尼·克萊恩一起去打獵。圣誕節(jié)前的那個(gè)星期天,約翰尼死了,他當(dāng)時(shí)也在那里。雖然那里主要是用來充當(dāng)男孩和男人的獵場(chǎng),但是米西小姐有時(shí)也會(huì)去。法官一無所獲時(shí),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如此,他就會(huì)抱怨天空太大,鳥太少。即使那時(shí),塞雷諾農(nóng)場(chǎng)也一直是一個(gè)謎——但只是一個(gè)出身貧窮的男孩總會(huì)感覺到的一個(gè)奢侈的謎嗎?馬龍記起了往日的時(shí)光,還想到了現(xiàn)在的法官——他智慧超群、德高望重,內(nèi)心卻藏著無法愈合的傷口——他心里哼唱著愛之歌,就像教堂里的管風(fēng)琴音樂一樣莊嚴(yán)而憂郁。
當(dāng)馬龍凝視著藥杵的時(shí)候,他的眼睛因?yàn)榭駸岷涂謶侄W閃發(fā)光,眼神呆滯,所以他沒有注意到從藥店地下室傳來的敲擊聲。在這個(gè)春天之前,他一直恪守著生與死的基本節(jié)奏——《圣經(jīng)》說七十歲就進(jìn)入古稀之年。但現(xiàn)在他在苦苦探尋莫名其妙的死亡。他想到了孩子們,他們就像珠寶一樣精致而纖弱,躺在鋪著白綢緞的棺材里。還有那個(gè)漂亮的音樂老師,吃炸魚時(shí)喉嚨里卡了一根魚刺,不到一個(gè)小時(shí)就香消玉殞了。還有約翰尼·克萊恩,還有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中死去的那些米蘭的男孩。還會(huì)有多少人?怎么死的?為什么會(huì)死?他注意到了地下室的敲擊聲。是只老鼠——上周一有只老鼠打翻了一瓶阿薩菲達(dá),接連幾天都惡臭難聞,搬運(yùn)工都拒絕去地下室干活。死亡是沒有節(jié)奏可言的——只有老鼠敲擊的節(jié)奏和腐爛的惡臭。那位漂亮的音樂老師,滿頭金發(fā)的約翰尼·克萊恩的軀體——寶石般的孩子們——最終尸體都化成了水,棺材里臭氣熏天。他吃驚地看著藥杵,只有這塊石頭存活了下來。
傳來一陣踩踏門檻的腳步聲,馬龍突然緊張起來,所以藥杵掉了下去。藍(lán)眼睛的黑鬼站在他面前,手里拿著閃閃發(fā)光的東西。馬龍?jiān)僖淮文曋请p發(fā)亮的眼睛,從他那奇怪的表情里,馬龍?jiān)俅未_信這個(gè)男孩知道他的處境,他覺得那雙眼睛知道他將不久于人世。
“我在門外撿到的。”黑鬼說。
因?yàn)槭芰梭@嚇,所以馬龍的視力有點(diǎn)模糊不清,轉(zhuǎn)瞬間他以為那是海登醫(yī)生的剪紙刀——接著他發(fā)現(xiàn)那是掛在銀環(huán)上的一串鑰匙。
“不是我的。”馬龍說。
“我看到克萊恩法官和他的孫子來過這里,也許鑰匙是他們的。”黑鬼把鑰匙扔在桌子上,然后他撿起藥杵遞給了馬龍。
“非常感謝,”馬龍說,“我會(huì)打聽一下誰丟的鑰匙。”
男孩走了,馬龍看著他大搖大擺地穿過街道。馬龍心生厭惡和憎恨,所以感到渾身冰冷。
馬龍坐了下來,手里拿著藥杵,平靜地想自己剛才怎么會(huì)有那么沖動(dòng)的情緒,以前自己是那么溫和,這種矛盾的情緒變化讓他感到吃驚。愛和恨將他一分為二——但他還不清楚該愛什么和該恨什么。他第一次知道死亡近在咫尺。但是讓他感到窒息的恐懼不是因?yàn)樗懒俗约旱乃劳觥_@種恐懼源于正在上演的某個(gè)神秘劇——雖然馬龍并不清楚它的劇情。這種恐懼讓他想知道這幾個(gè)月里會(huì)發(fā)生什么事情——還能活多久?——讓他在屈指可數(shù)的日子里大放異彩。他就是鐘表的守望者,但那個(gè)鐘表卻沒有指針。
老鼠敲擊的聲響仍在繼續(xù)。“爸爸,爸爸,幫幫我。”馬龍大聲叫喊道,但是他父親已經(jīng)死了很多年了。這時(shí)電話鈴響了起來,馬龍第一次告訴妻子他生病了,讓她開車來藥房,帶他回家。放下電話后,他坐在那里,用手撫摸著藥杵,以此聊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