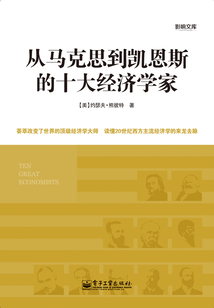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46章 附錄C拉地斯勞斯·方·鮑爾特凱維茲
- 第45章 附錄B弗雷德里克·方·維塞爾
- 第44章 附錄A喬治·弗雷德里克·克納普
- 第43章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5)
- 第42章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4)
- 第41章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3)
第1章 序言
本書所收錄的這些文章都寫作于1910—1950年這40年間,最早的3篇(瓦爾拉、龐巴維克、門格爾)是用德文寫的,而其余各篇都是用英文寫的。除了關于馬克思的那一篇外,其余的都是在一些雜志上刊載過的文章,有的是為某位經濟學家的去世而作,有的是為了某些重要事件的周年紀念而作,如紀念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發表50周年、紀念帕累托誕辰100周年等。因為這些文章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匆忙寫成的,熊彼特本人認為將它們匯編出版的價值不大,但有時又難免需要用到這些文章,而刊載它們的雜志又不易找到,所以在1950年1月,也就是熊彼特去世前幾個月,他還是同意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將它們整理出版。
這10篇主要的文章,除了關于馬克思的那篇之外,都是由熊彼特自己選定的。他本計劃收錄為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00周年而為《政治經濟學雜志》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的社會學與經濟學》(1949年6月)這篇文章,但是后來我們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的第一部分《馬克思的學說》取代了它,因為它更全面地論述了作為預言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對世界產生影響的馬克思。我非常感謝卡斯·坎菲爾德先生和哈培爾兄弟出版社,他們慷慨地答允了我的請求,這篇文章才得以收入本書中。在這里,我還要對《經濟學季刊》、《美國經濟評論》及《經濟學雜志》的編輯和出版商們表示感謝,是他們同意將原本刊登在自己雜志上的文章收入本書中。此外,還有一些文章刊登在《國民經濟》雜志上,不過該雜志已經停刊了。
根據哥特弗里德·哈伯勒教授的建議,我們將關于克納普、維塞爾和鮑爾特凱維茲的三篇短文收入附錄之中,他認為應該重新出版它們,并和其他傳記體的文章一起選入本書。這些文章分別是熊彼特作為駐奧地利通訊員(1920—1926年)和駐德國通訊員(1927—1932年)為《經濟學雜志》撰寫的。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里,熊彼特離開德國的波恩大學,轉到了美國哈佛大學工作。
作者和這些傳記文章的主人公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不僅是因為他欽佩他們的工作的關系,而且也因為他和他們中的一些人彼此熟悉,特別是和其中幾位還有著深厚的友誼。但馬克思是一個例外,馬克思于1883年去世,而熊彼特則和凱恩斯一樣,恰好在這一年出生,凱恩斯是十位經濟學家中最年輕的一位。熊彼特和馬克思有著一點相似之處——那就是對經濟過程有著相同的看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熊彼特試圖提出“一種關于經濟變化的純經濟理論,也就是說,這種變化不僅僅是建立在推動經濟體系從一種均衡過渡到另一種均衡的外部因素的基礎上的”。在這本書的日文版的序言里,熊彼特寫道:“開始時我不清楚,但對讀者來說很快就會看清,到底是什么思想、什么目標(熊彼特本人的)和構成馬克思的學說的這些思想與目標完全一致。實際上,他與同時代及過往的經濟學家的區別就在于對經濟過程的看法,即這種過程是否是由這個經濟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而在其他各方面,他只是引用李嘉圖的說法和觀點,但是把關于經濟發展的概念置于次要的黑格爾的背景中,卻是他自己的見解。這可能是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總是不斷地提起他的原因,盡管他們對這一概念也有很多不認同的地方。”在他的《經濟分析史》手稿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的思想框架中,發展不是那個時代的經濟學家所認為的經濟靜學的附屬物,而是該時期經濟的核心問題。他分析的重點落在了揭示經濟過程怎樣被自身邏輯決定,以及不斷變化的整體社會的結構上。”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推導出來的結果卻大不一樣:它使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社會,而使熊彼特成為資本主義的熱心的辯護人。
在熊彼特看來,經濟學是一門要借助于長遠眼光和純熟技術的學科。他推崇馬克思關于經濟過程的眼光,同時也推崇與他僅有一面之緣的瓦爾拉的純經濟理論。關于這點,他在《經濟分析史》里這樣說:“經濟學就好像是一輛大公共汽車,它搭載著許多興趣和能力不相稱的乘客。單就純經濟理論來說,我認為瓦爾拉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均衡體系把‘革命的’創造性和古典的綜合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這是唯一能和理論物理學的成就相提并論的經濟學家的作品。”
馬克思與瓦爾拉則完全不同,他們一個試圖給出經濟變化的邏輯解釋,另一個則給了我們一個“理論工具,它開創性地在我們的科學史上有效地使用了經濟數量之間互相依賴的純粹邏輯”。
熊彼特的特點是:對歷史的和純理論性的東西、計量經濟學和收集到的大量實際資料、社會學及統計學,他持肯定態度,認為它們有用。他如此廣泛的學術興趣也反映在這些傳記性的作品中。
在維也納學習期間,熊彼特就認識了門格爾、龐巴維克和維塞爾。門格爾和他的兩位弟子——龐巴維克和維塞爾可以算是奧地利學派的共同的創始人。那時門格爾已從大學退休,熊彼特也只和他見過一兩次,但是這些傳記還是翔實可信的,因為其作者是維塞爾和龐巴維克的研討班的積極參加者(1904—1906年)。后來,他和龐巴維克就利息率的問題展開了一次著名的論戰;1921年,在慶祝維塞爾誕辰70周年時,他是3位發言者之一。
雖然他很看重奧地利學派,而且在這個學派中受到了學術訓練,但實際上,他對提出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的另一個學派——洛桑學派更感興趣,這個學派就源于瓦爾拉的著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學派的創始人其實是帕累托。帕累托原來是瓦爾拉的學生,后來又接替瓦爾拉在洛桑大學擔任了政治經濟學教授一職。直到現在,對英國和美國的經濟學家來說,他們的著作也是過分“數學化”、過分“理論化”了。同時,英、美經濟學家也發現了一個問題,即閱讀用其他文字寫就的經濟學著作事實上是很困難的(也許是浪費時間)。但是洛桑學派在早期就有了兩位一流的美國信徒——歐文·費雪和H·L·穆爾。本書中的10篇文章中有3篇是獻給瓦爾拉、帕累托和費雪的。在關于帕累托的文章中,熊彼特特別描述了一次聚會,會上談論了許多經濟學家,而當時帕累托對歐文·費雪大加贊揚。熊彼特說:“在我聽到他(帕累托)高度評價(費雪的)《資本和收入的本質》時,不免感到意外。”
1906年,熊彼特在維也納獲得學位以后,又到英國生活了幾個月。在英國期間,他拜訪了幾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在1907年首次遇見了馬歇爾。熊彼特在1933年12月寫給《經濟學雜志》的有關凱恩斯的傳記文集《精英的聚會》(Essays in Biography)的書評的注釋中描述了這次會見。在評論凱恩斯寫作的關于馬歇爾的文章時,他寫道:“當我在1907年的某一天早餐時間隔著桌子看到他時,我告訴他(馬歇爾)說:‘教授,在我們談了關于我的科學計劃之后,我的確感到我就像一個莽撞冒失的戀愛者正在嘗試一個不可靠的婚姻一樣,而您就像一位慈祥的老者試著勸我放棄這個危險的念頭。’他回答道:‘事情本來就是如此,如果在這方面能有什么作為的話,老人的勸告就沒有用了。’”熊彼特在本書中表明了他對馬歇爾著作的態度,這篇論文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之后,他收到瑪麗·馬歇爾此處指瑪麗·佩利·馬歇爾,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夫人。——譯者注于1941年6月從英國劍橋寄來的一封短信。信里說:“剛收到這期的《美國經濟評論》,我正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你寫的關于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看得出你對他的著作評價很高,我很高興地看到你能借此機會如此熱烈地、恰當地表達這種評價。這篇論文的最后一段尤其使我感到欣喜。我也和你一樣欣賞凱恩斯寫的《紀念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一文。”
而在評價美國經濟學家(陶雪格、費雪、米切爾)時,熊彼特可能和他們剛剛認識。那是在1913—1914這一學年,我記得熊彼特好像是作為交流學者去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在此之前,他也曾閱讀過他們的著作,好像還和陶雪格通過信。陶雪格于1912年11月27日從劍橋寫了一封信給他,在這封信中,他對這位青年經濟學家的英文水平表示贊賞,然后討論了后者提出的一個理論問題。“我對于你的論證沒有什么異議,但我還是覺得應該以更現實的觀點來探討這些問題。”陶雪格還隨手附上了一些供給圖表,并說道:“我想把和資本、土地一樣的論證運用于勞動力,并發展一種‘租賃’勞動理論。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草擬出一個大綱。你可能也知道,我的朋友J·B·克拉克也進行過這種論證,而后來歐文·費雪也進行了更仔細的論證。但是這個論證到現在還沒有最后的結論。我并非是如此狂妄自大,以至于認為這個結論應該由我做出,但我確實希望能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貢獻。”雙方的友誼一直持續到1940年陶雪格逝世為止。實際上,在熊彼特到哈佛的頭幾年(1932—1937年),他和陶雪格一直住在斯考特街2號。
同樣地,他對歐文·費雪和韋斯利·克萊爾·米切爾也很欽佩,與他們也維系了一定的友好關系。他和費雪共同創辦了計量經濟學會。當熊彼特到費雪位于紐黑文的儉樸的家中做客時(那兒沒有煙、酒、咖啡,甚至連肉都沒有),咖啡是為這位“墮落的”客人特別準備的。阿爾及爾大學的G·H·布斯凱教授在1950年第3期的《政治經濟學評論》雜志上描述了這次在周末進行的交談。本書中紀念韋斯利·克萊爾·米切爾逝世的文章是熊彼特在逝世前一兩個星期完成的。米切爾和熊彼特有著共同的學術研究——研究商業循環,他們都相信,為了更好地分析這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現象,需要最廣泛的實證研究。熊彼特不辭辛勞地獨自收集資料,在此過程中幾乎沒有獲得來自他人的幫助,因為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但是他對那些能夠明智、有效地利用國家經濟部門的有關資料的人十分贊賞。
雖然凱恩斯曾經在很長的時間里擔任《經濟學雜志》的編輯,而熊彼特也從1920年起就擔任這個雜志在奧地利的通訊員職務,但雙方直到1927年才見了面。由于一些微妙的、很難解釋的緣由,他們兩人的關系無論是從個人角度還是從專業角度來說,都不十分密切。
對評述瓦爾拉、門格爾、龐巴維克的那3篇文章的翻譯曾遇到過麻煩。正如保羅·斯威齊在他的《帝國主義和社會階級》序言及哈伯勒早些時候在《經濟學季刊》中指出的那樣,由于應用德文寫作,所以熊彼特的文風特別難翻譯。哈伯勒說:“他的富于書卷氣的筆調,也許用‘奇異的風格’來形容最合適,這種風格恰好能表現他的復雜的思想結構。這種風格的特征表現在大量的長句子、大量的修飾短語、對修飾語的再修飾,以及對含義差別的辯解上。他的這些風格特征,正如人們所提到的,在他的德文著作里特別顯著,這是因為德語更適合于復雜的結構。”熊彼特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特別是關于龐巴維克的那篇文章。他認為那篇文章太冗長,應加以刪改,并為英語讀者而重寫。他著重指出,不那樣做是不行的。
關于龐巴維克的文章,本書中所收錄的相比原作已經刪去了一半。這項工作是由哈伯勒和文章的譯者赫伯特·查森豪斯教授一起進行的,而赫伯特·查森豪斯是熊彼特的學生。在這兒我要表達我對哈伯勒教授及3位譯者的感激之情,感謝他們慷慨的關心和幫助。我還要感謝保羅·斯威齊,他和我一起閱讀了全書,并在此過程中幫我潤色了英文及在多處澄清含義。出于某些考慮,我不得不對有些章節中的過于直譯和模糊不清之處做了一些修改,修改的重點就是那篇關于龐巴維克的文章,因此它的責任完全在我,由我一人負責。
其他的論文都是用英文寫的,這次也就保持不動了。除了一些小的印刷錯誤,以及為了保持格式的一致而做的一些小的改動——如大寫字母、標點符號、注釋的排列等之外,沒有再做其他改動或修訂。
伊麗莎白·布迪·熊彼特,熊彼特的第三任妻子。她也是哈佛大學的一名經濟學家,于1937年與熊彼特結婚。——譯者注
1951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