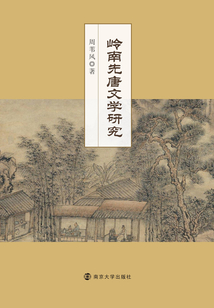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先秦嶺南文學(1)
南嶺是中國南部最大的山脈和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線,它西起云南的云嶺,東入貴州為苗嶺,再經兩廣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邊界而東達于海。南嶺是長江和珠江兩大流域的分水嶺。南嶺山地雨量豐沛,有不少著名江河發源于此。北坡除了瀟、湘兩江,還有資水上源夫夷水、湘江支流舂陵水和耒水,以及與貢水合成贛江的章水。南坡的河流更多,發源了桂江、賀江、武水、湞江,等等。“五嶺逶迤騰細浪”,南嶺的大小山嶺不計其數,尤以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五個山嶺最為著名,故又稱五嶺。嶺南指的是南嶺以南地區,相當于現在廣東、廣西以及海南全境,也包括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區。在歷史上,嶺南也包括曾經屬于中國皇朝統治的越南紅河三角洲一帶。嶺南是中國一個特定的環境區域,這些地區不僅地理環境相近,人民的生活習慣也有很多相同之處。
廣西位于全國地勢第二臺階中的云貴高原東南邊緣,地處兩廣丘陵西部,南臨北部灣海面。整個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傾斜,山嶺連綿、山體龐大、嶺谷相間,四周多被山地、高原環繞,呈盆地狀,有“廣西盆地”之稱。廣西周邊與廣東、湖南、貴州、云南等省接壤。東南與廣東省省界長約931公里,東北與湖南省省界長約970公里,北面與貴州省省界長約1177公里,西面與云南省省界長約632公里。西南與越南邊界線長約1020公里。大陸海岸線長約1959公里。東西最大跨距約771公里,南北最大跨距(南至斜陽島)約634公里。
廣東是中國大陸南端沿海的一個省份,位于南嶺以南,南海之濱,與香港、澳門、廣西、湖南、江西和福建接壤,與海南隔海相望。廣東是嶺南文化的重要傳承地,在語言、風俗、生活習慣、歷史文化等方面都有著獨特風格。距今約12.9萬年以前,嶺南就出現了早期古人——馬壩人。商周時期,廣東先民便與中原有了經濟文化往來。春秋戰國時期,嶺南與閩、吳、越、楚國關系密切,交往頻繁。公元前222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領五十萬大軍攻打嶺南。公元前214年,秦軍基本上占領嶺南,設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象郡轄今廣西西部和越南的中北部,今天的廣東省絕大部分屬于南海郡。
先秦時期,廣西為駱越國,居住著百越中的“駱越”、“西甌”、“蒼梧”人。駱越國是壯族祖先著名的方國,最早見于《逸周書·王會》,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云:“路音近駱,疑即駱越。”路即駱,此說中的。《逸周書》亦稱《周書》,乃先秦古籍,多數篇章出于戰國,其中所記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呂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駱之菌”,漢代高誘注:“越駱,國名。菌,竹筍。”越駱是漢語說法,意為越(山)谷或越鳥,越人語言倒裝為駱越。駱越與西甌構成了今天壯族的主要兩個支系,駱越方國創造的稻作文化、大石鏟文化、龍母文化,尤其是青銅文化中的銅鼓文化、花山文化,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駱越人和蒼梧人、西甌人一起,在我國最先發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為中華民族也為全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
嶺南文學源遠流長,從遠古以來,就有十分豐富的文學活動。春秋時期,有越人為楚國鄂君子皙擁楫而歌;著名的左江崖壁畫,證明自古以來廣西人民就能歌善舞。正是由于廣西先民對歌舞的鐘愛,才出現了后來名聞天下的有關劉三姐的傳說與山歌。“駱越”、“西甌”、“蒼梧”分別是嶺南百越族的一支,百越文化是嶺南文學的文化母體,“楚奏越吟”,古代嶺南文學在令人魂牽夢繞的越吟聲中揭開了帷幕。從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古代嶺南是一個獨具特色、自成體系而又相對封閉的地區。這一地區北有南嶺山脈,成為與中原地區交通的天然屏障;西北有云貴高原,阻隔了通往云貴川的道路;東南瀕臨浩瀚的南海,對外陸路至此而斷絕。在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和交通工具極其簡陋的狀況下,嶺南與外界的聯系和交往是非常困難的。盡管如此,這一地區與中原地區的聯系和交往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開始了。降及周代,嶺南與中原聯系更加緊密,西周的青銅器文化大規模地傳入嶺南地區。先秦時期中原文化在嶺南的傳播,影響了嶺南文學未來走向。春秋以后嶺南與中原地區的聯系,楚國應該是主要的媒介。春秋戰國時期,嶺南深受楚文化影響,楚文化成為嶺南文學與中原文學的重要紐帶。從出土文物來看,嶺南少數民族也曾有文字的萌芽,但在嶺南少數民族文字成熟之前,中原政權通過軍事手段將漢字輸入嶺南,土著文字的發展至秦代戛然而止。雖然有證據顯示,先秦時期漢字既已傳入嶺南,但尚沒能成為當地廣泛運用的交流工具,自然也不會產生純粹意義上的文學。因此,和中原上古文學一樣,先秦時期的嶺南文學主要有神話和詩歌。
第一節 先秦嶺南文學的母體——百越文化
在嶺南這片紅土地上,很早就有人類在此生息繁衍。1965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桂林文物管理委員會組成的普查組在桂林南郊獨山甑皮巖發現了一處內涵比較豐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后經發掘和年代測定,證明大約從距今12000年前甑皮巖就開始有人居住。[1]此外,在市內疊彩區的寶積巖[2]、西郊甲山鄉唐家村的轎子巖[3]、南郊雁山區李家塘村的廟巖[4]、臨桂縣二塘鄉太平村的大巖[5],也都發現了原始人類活動的遺跡。1980年在柳州市鯉魚嘴遺址發現6座屈肢葬[6],1986至1988年在高要縣(今肇慶市鼎湖區)廣利鎮蜆殼洲遺址發現24座屈肢葬和蹲踞葬[7],廣西南部邕江和左江沿岸地區,如橫縣西津和秋江、邕寧縣伶俐鎮長塘、南寧市青山、武鳴縣岜勛、扶綏縣江西岸和昌平鄉敢造[8]、崇左市和平鎮沖塘[9]等地也發現了大量蹲踞葬和屈肢葬。
春秋時,北方人將長江以南廣大地區的許多部落統稱為“百越”。“百越”一詞最早見于《呂氏春秋·恃君覽第八》:“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余靡之地,縛婁陽禺兜之國,多無君。”《漢書·地理志》說:“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皆粵分地。”顏師古注:“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后也。”百粵即百越。從地域上說,現在的云南西部及越南北部經廣西、廣東、湖南、江西、福建、浙江這樣一個弧形地帶都是百越集團的居住地。北起長江流域,南至紅河三角洲,東至濱海,西到四川,到處都有越人居住,統稱之為“百越”。“各有種姓”,說明百越集團雖然部落眾多,但由于地域廣闊,他們各自為政,從來沒有建立過統一的國家。越族的分布很廣。因為居住的地域不同,所以他們的名稱也有所不同。如居住在浙江省一帶的稱東甌越;居住在福建省境內的叫閩越;居住在廣東省一帶的叫南越;居住在西江流域一帶的叫西甌越;居住在四川、貴州一帶的叫夷越;居住在紅河下游一帶的叫雒越。關于雒越人,《水經注》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記》:“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緩。后蜀王子將兵3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安陽王。”雒越之雒,其來歷似與“山麓”、“雒田”有關。《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張守節《正義》云:“嶺南之人,多處山陸。”陸即今之山麓。“陸梁”為古越語“雒佬”之轉音,嶺南越人自稱。[10]嶺南多丘陵,其間谷地稱山麓。嶺南人多處于山麓間,墾食山麓之田,故謂之雒人。“雒”或作“駱”,《漢書·賈捐之傳》:“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駱越又稱甌駱。甌,據劉師培《古代南方建國考》云:“甌以區聲,區為崎嶇藏匿之所。從區之字,均有曲義,故凡山林險阻之地,均謂之甌。南方多林木,故古人謂之區,因名其人為甌入。”先秦廣西的一些原始居民被稱為“駱越”,屬于百越民族的一部分。
春秋戰國時期的越國,是越人在東南地區建立起來的一個國家。雖然它曾稱霸于中原,但僅僅是百越中的于越所建立的國家,并沒有統一整個百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發,被草萊而邑焉。后二十余世……勾踐立,是為越王。”《吳越春秋》也有記載:“少康……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無余始受封。”這些記載講述了越國的由來:越王勾踐祖先是夏禹王六世孫少康的庶子無余。夏禹王東巡,死于會稽,葬在稽山,距夏都甚遠。少康恐對禹的四時祭祀無人主持,于是把他的庶子無余封到這里來奉承香火,以免絕祀。無余到會稽后,不僅沒有改變土著越人的習俗,反而自己也文身斷發,披草萊,融合于土著民族。盡管如此,無余還是帶來了夏氏集團先進的經濟和文化,在這里建立起了城邑。勾踐既是夏后氏的子孫,當然不是越人的祖先了,因此顏師古特別強調越非禹后。越族不是華夏族后裔,只能說明浙江越人中有少數華夏人的血統。越國出越人而得名,并不是有了越王才有越國。越至立國到滅亡,經歷六世,據司馬遷《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公元前334年,楚威王攻越,殺死越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四散的越人有一部分進入兩廣,極大地促進和提高了當地的文化生產水平。所以羅香林《廣東通志民族略·族系篇》認為:“廣東一省原為苗民叢集之地,大約荊楚的三苗族……當嬴秦之時,已多徙入于云、資、桂、粵各地”,“楚人滅越,越人逃之南服,居址定后,遂抉其較高文化,部勒土著,自為君長,以是而百粵的苗蠻和擺夷始與越族人互相混化”。可見,先秦的嶺南居民,除了土著,還有后來遷徙來的越人。
百越是個龐雜的族群,具有共同的體質特征(南亞蒙古人種體質)和共同的文化特征(幾何印紋陶文化)。[11]百越文化,是源于我國東南沿海諸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兩大水系的原始文化。百越文化如同百越概念一樣,包含多種特性文化,形成于不同的時間序列,存在于遼闊的南方大地。百越文化的創作者古越土著,在與他族的交流過程中,一部分逐漸與漢族融合,一部分則逐漸成為近代壯、傣、布依、侗、水、仡佬、毛南、黎、苗、瑤、畬等民族,成為藏緬語族、孟高棉語族中部分民族的主要族源。后來,他們中的不少民族和外族,不斷地走出或走進百越地界。百越文化的傳統,也成為在整個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不斷發揚光大的跨國文化。
百越文化有著極為久遠的歷史,音樂更可以追溯至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七千年前的骨哨。1973年考古學家在浙江余姚河姆渡發掘出一百六十件骨哨,骨哨以鳥類肢骨制作,管身鑿一至三個音孔,吹奏時能發出酷似鳥鳴的簡單音調,是古越人模擬鳥鳴捕鳥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的骨哨中,有些腔內還插有細骨,吹管時抽動細骨,即可形成曲調,與今日杭州西湖隨處可見的“竹哨”極為相似。比較中推測,竹哨的前身是骨哨,可能就是古代樂器簫笛類的雛形。骨管音哨,當是竹管或蘆管樂器的先聲。當代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廣泛流傳的單管樂器(笛簫類)和編管樂器(蘆笙類),理應是百越文化創造者們對于中華文明的一大貢獻。產生在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骨哨已不僅僅作為勞動或狩獵的信號,由于產生了簡單的音調,因而已成為原始樂舞中草創的吹奏樂器了。從樂舞同源說推測,距今七千年河姆渡文化遺存之多孔骨哨應是古越這塊文化沃土上樂舞文化的最早實證。
遠古時代,各氏族均有自己的圖騰崇拜及其樂舞。例如,黃帝的《云門》、摯的《玄鳥》、堯的《咸池》、舜的《韶》等。其中,摯氏族的《玄鳥》,對后來百越文化的形成可能有一定的影響。音樂學家楊萌瀏(1899—1984)指出,這個氏族“以鳥為圖騰,把黑色的鳥(玄鳥)象征一年四季中春分、秋分等節氣。上述葛天氏《八闕》中的第二曲《玄鳥》就是崇拜這種圖騰的樂舞”[12]。摯,少皞氏,東夷部族首領。其后裔的一支與古越先民有關。《越絕書》和《吳越春秋》都有大禹為“大越海濱之民”治水及“使百鳥還為民用”的記載。《博物志·異鳥》和《吳越備史》甚至說:“鳥為越祝之祖”,“鳥主越人禍福,敬則福,慢則禍,于是民間悉圖其形以禱之”。說明居住大越海濱的越族先民,是鳥圖騰崇拜的民族之一。廣西境內曾廣泛流傳著一部創世史詩《布洛陀》,布洛陀,壯文記音為bouq loegh daeuz,意思是“鳥的首領”,可能是古越先民鳥圖騰氏族對其首領的稱謂。壯族還有一首著名的古歌《百鳥衣》,也可印證越人曾有過鳥圖騰的習俗。今人不妨以越歌與越人崇鳥習俗試著逆向考察,也許能找出音樂史上的《玄鳥》樂舞與百越文化的聯系。
遠古流傳至今的《擊壤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據音樂學家王光祈考證,此歌與現代閩浙一帶的畬族民歌在詞句結構上完全一樣,并進而推論,他們在旋律進行上也極其相似,音調也非常接近。[13]王充《論衡·藝增》說《擊壤歌》起于堯舜時代,堯舜相繼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父系氏族社會后期部落聯盟首領,其中舜“曾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南巡死于蒼梧之野”。以上所述之福建、浙江,蒼梧,均屬上古時代越人先民生息之地。雖然不能因此斷定《擊壤歌》源于越地,起碼說明《擊壤歌》曾在越地流傳。
百越民族向來能歌善舞,《河圖玉版》就記載了遠古時期越地同宗教儀式有關的民間樂舞,“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發而舞”。防風氏是古代越族的一支,《國語·魯語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一《浙江三·湖州府》武康縣封山下曰:“今縣境即古防風氏封守之地也。唐時改此為防風山。又禺山,在封山東南二里,相傳防風氏都此。”又提到“風渚湖”:“志云:湖即古防風氏所居之地。”《呂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見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這首古歌被音樂史學論著認為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南方民歌。這首古歌雖然只有一句,但反映了涂山女對禹質樸而強烈的思念之情,其中的兩個虛詞必然配合了婉轉起伏的旋律以抒發歌曲旖旎纏綿之情,說明旋律性己逐漸成為原始音樂的重要因素。聞一多先生《神話與詩》在談到無具體內容的兩個疊韻虛詞“兮猗”時認為,這種從心底發出的感嘆聲“便是音樂的萌芽……”。關于涂山地望,自古眾說紛紜。《楚辭·天問》洪興祖補注引蘇鶚《演義》云:“涂山有四:一者會稽(今浙江紹興),二者渝州(治今四川重慶),三者濠州(治今安徽鳳陽),四者《文字今義》云‘嵞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當涂縣也。”《說文》:“嵞山,會稽山也。”嵞即涂。《越絕書》卷八:“涂山者,禹所娶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認為涂山即今浙江紹興境內的會稽山。因此有人認為《候人歌》是遠古時越地涂山一帶的歌謠。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載范蠡進善射者陳音,勾踐詢以弓彈之理,陳音在應對中引用了一首相傳是黃帝時期的古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說它是黃帝時代的歌謠,固然沒有根據。但從內容和形式上看,無疑這是一首比較原始的獵歌。陳音為楚人。另外從彈弓的制造材料也可以推測,這首歌謠當產生在適合竹子生長的中國南方。因此有人認為,《彈歌》可能是古越先民的獵歌。
王粲《登樓賦》:“鐘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作為一個典故,“莊舄越吟”表達的是不忘故國家園、愛國懷鄉的思想感情。據《史記·張儀列傳》記載,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莊舄,戰國時期越國人,曾仕于楚,病時越吟,寄托了對故鄉的思念。古代嶺南文學就是在令人魂牽夢繞的越吟聲中揭開了帷幕。
第二節 先秦時期嶺南文學中的中原因素
從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古代嶺南是一個獨具特色、自成體系而又相對封閉的地區。這一地北有南嶺山脈,成為與中原地區交通的天然屏障;西北有云貴高原,阻隔了通往云貴川的道路;東南臨浩瀚的南海,對外陸路至此而斷絕。在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和交通工具極其簡陋的狀況下,嶺南與外界的聯系和交往是非常困難的。從考古發掘的原始遺跡來看,這一地區的原始社會文化具有明顯的特色,如干欄式建筑,廣泛使用蚌器,漁獵采集也發達,等等。[14]干欄式建筑適應了嶺南潮濕多雨的氣候,蚌器的廣泛使用和漁獵采集經濟的發達也是本地氣候溫熱、動植物資源尤其是水產資源豐富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由于閉塞隔絕和崇山峻嶺的自然地理環境,古代嶺南地區社會發展緩慢,文明遠較中原落后。早在公元前21世紀,中原地區已出現了國家,建立了夏朝。在物質文化上,已進入青銅時代,經歷夏、商、周以及春秋時期,約一千五百多年。可是嶺南直到殷商晚期,才產生青銅文化的萌芽,比中原要晚一千多年。[15]秦漢時期的中原內地,青銅時代已經遠去,青銅器使用已退居于次要地位。廣西的越人社會則是另一種情形,青銅文化的傳統依然濃烈,生活中還廣泛使用青銅器,除了大量生產銅鼓以外,還創新羊角鈕鐘、附耳銅桶,漆繪銅器和鏨刻花紋銅器也別有風格。[16]
盡管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造成了嶺南相對閉塞隔絕的狀態,但這一地區與中原地區的聯系和交往卻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開始了。這一點在歷史文獻資料上有記載,在考古實物資料上也有證明。我國不少古籍都有關于“南交”、“交趾(阯)”情況的記載。《淮南子·主術訓》說:“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大戴禮·五帝德》引孔子的話說,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史記·五帝本紀》也說顓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厲”。《尚書·堯典》記載:“申命羲叔,宅南交。”《墨子·節用中》:“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非子·十過》記由余答秦穆公:“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淮南子·修務訓》:“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帝堯者,放勛。……申命羲叔,居南交。”又說舜命禹“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還說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據《淮南子·修務訓》所說,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古本竹書紀年》則更明確地說舜葬于蒼梧。關于夏禹,《呂氏春秋·求人》說:“禹東至欂木之地,……南至交趾孫樸續樠之國,……”上述多種文獻,都提及神農、顓頊、唐堯、虞舜、夏禹撫有交趾或南交之事,或謂他們曾親到該地,或謂他們派人前往該地。還特別記載虞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葬于九嶷山的一段史事。所謂“南交”或“交趾”泛指嶺南地區。“蒼梧之野”,一說在湘、桂、粵交界的九嶷山,一說在廣西的蒼梧。有些學者根據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地圖《長沙國南部地形圖》中,在九嶷山旁邊標注有“帝舜”二字,認為“舜死葬的蒼梧已接近廣西,甚或已深入廣西北境”。[17]傳說舜南巡守,有兩個妃子娥皇、女英隨后南下,途中聞舜崩,乃投水而死,成為湘水神。她們哭舜淚灑染竹成斑,此即斑竹之由來。斑竹亦稱淚竹、湘妃竹,產于湘桂地區。九嶷山有舜源,有娥皇、女英等峰,顯然是為了紀念虞舜及其二妃而得名。桂林市東郊有堯山,唐時曾在此建有堯帝廟。城北又有舜山,亦稱虞山;山麓有潭,名舜潭;山中有巖洞,名韶音洞。在廣西、廣東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紀念舜的文物遺址。從這些民間傳說和文化遺跡來看,我們雖不能確指舜所死葬的“蒼梧之野”的具體地點,但可以推斷其大致范圍當在今湖南南部、廣東西北部、廣西東部及東北部一帶地區。按照以上說法,則在三皇五帝和夏禹時代,中國疆域已至嶺南,嶺南和中原之間的門戶已經開啟,嶺南地區的居民與中原的聯系和交往已漸次開始。
三皇五帝都屬于傳說中的人物,我們自然不能把傳說當作信史看待,以為三皇五帝時代中國的疆域果如以上文獻所言。顧頡剛先生說:“秦漢以前的中國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他們爭戰并吞的結果,從小國變成大國,才激起統一的意志;在這個意志之下,才有秦始皇建立四十郡的事業。”“《禹貢》上的九州,一般人都認為夏朝的制度;其實夏朝的地盤只占得黃河的一角,哪能有這樣偉大的計劃。九州乃是戰國的時勢引起區劃土地的一種假設,這種假設是成立于統一的意志之上的。”[18]夏至戰國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夏以前的遠古時期。很顯然,當時堯舜禹的統治范圍還遠沒有到達嶺南地區。關于堯舜禹等“南至交趾”、“南撫交趾”的傳說,“在一定范圍內,反映了我國南方越族地區與中原地區的相互往來,以及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的史實”。[19]因為是傳說時期,如果把嶺南和中原之間的聯系和交往看作某帝王或某時之事,自然不完全可靠;如果把它們看作某個較長歷史時期內發生的現象,則是可能的事實。
《淮南子·泰族訓》:“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據《逸周書·王會解》記載,商初大臣伊尹曾受湯之命,下令四周各方國貢獻土特產給商王朝:“伊尹受命,于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發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斷狗為獻。”這里提到的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都屬于江南百濮、百越系統的先民。《呂氏春秋·本味》篇載伊尹說湯,亦曾提到“越駱之菌,鱣鮪之醬”、“南海支秬”。商朝勢力遠及東南沿海和嶺南,這一點得到了考古發現的證明。在江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區的商代遺址中,都可見到殷墟文化的成分。尤其是東南、華南地區分布于長江下游兩岸的“湖熟文化”和江西北部的“吳城文化”,更明顯地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湖熟文化的特征與中原文化多相似之處,它是一種受中原商文化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土著文化。江西省清江縣吳城遺址出土的大部分陶器,如鬲、甗、豆、罐等,與中原商文化的同類器形相似;青銅器中的工具、兵器和禮器,器形也與中原地區的相同。在湖南發現商代文化遺址有二十余處,出土商代晚期青銅器多達三百多件,地點遍及湘北、湘中和湘南,最南已到衡陽和常寧。從衡陽、常寧溯湘江而上到達廣西,不過幾天的水路。在漫長的年代里,商文化包括青銅器,由黃河流域依次向南傳遞,傳入嶺南是完全可能的。在廣西興安、武鳴等地,曾先后發現商代銅卣,其造型、文飾和銘文,均為黃河流域風格。這些器物很可能是從中原經兩湖而傳入廣西的。
降及周代,嶺南與中原聯系更加緊密。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武王伐紂滅商,周康王時發動對邊遠方國的戰爭,其子昭王更親征荊楚,結果溺水而死,全軍覆沒。宣王中興,又對西戎、淮夷和荊蠻用兵。《詩經·大雅·江漢》:“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當時周朝疆域很廣,以至于周人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的觀念。為了加強對廣闊疆域的管理,西周建立了畿服制度,將王畿以外的地區,按其與王朝關系之親疏和距離王都之遠近,劃分為若干等距離的大區域,各負責輕重不同的職貢。自王畿向全國四周輻射,直至周勢力所達到的邊遠地區,依次為甸服(王畿)、侯服(王朝所封諸侯)、賓服(方國服屬王朝者)、要服(少數部族接受約束者)、荒服(少數部族居荒遠者),合稱五服。關于服數,還有九服之說。《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廣西通志》:“廣西輿地,三代時蓋藩服。”[20]有向周朝進貢的義務。
《韓詩外傳》卷五記載:“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于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黃發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來也。’”《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也記載:“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往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圣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于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越裳獻白雉的故事說明,西周初期的政治影響遠及于嶺南的邊遠部族,邊遠部族也對中原王朝心向往之。為此,周朝特設職方和象胥二職掌管四方之事,《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貊、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才用九谷、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又《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貊、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逸周書》和《竹書紀年》都曾記載成周之會的盛況,《竹書紀年》卷下:“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01年),于越來賓。”于越為古越族的一支,活動于今浙江境內。接著,周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1000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四夷之中,自當包括嶺南的越族在內。這里說的“來賓”,并不是普通的應酬交往,而是含有政治上的附屬和經濟上的納貢。《逸周書》就具體記載了成周之會各方的貢獻,其中提到“歐人蟬蛇”、“且甌文蜃”、“若人玄貝”、“自深桂”、“倉吾翡翠”,“歐人”、“且甌”、“若人”、“自深”、“倉吾”,據孔晁注皆為越人,《逸周書》稱他們為“南人”,并特別強調“南人皆北向”。[21]
和商代相比,西周的青銅器文化以更大的規模傳入嶺南地區。例如廣東信宜出土了西周銅盉,廣西忻城出土了西周銅鐘,都不是本地鑄造,而是從黃河流域傳入嶺南的。廣西全州縣零陵故城遺址發現的陶鬲,其形制與文飾特征和西周同類器物基本相同,顯然是從中原傳入。此外,廣西北部地區還有大量幾何印紋硬陶文化遺存,不少陶器的文飾也是模仿中原西周青銅器。至于兩廣地區受中原西周文化影響而自制的器物,那就更多了。如廣西荔浦、陸川出土的銅尊,灌陽、橫縣出土的銅鐘,都和中原出土的同類器物相似。
春秋戰國時期,越族更積極地參與中原的政治和經濟活動。百越民族聚居的吳國和越國,崛起于我國東南,令各諸侯國矚目。春秋晚期,吳國曾稱霸一時。孫武原為齊國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吳王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在巫臣、伍子胥、孫武、伯嚭等人的努力下,吳國日益強大,曾經北上黃池,爭霸中原。[22]勾踐滅掉吳國,也曾與諸侯國家會盟,雄視江淮地區,成為一時霸主。楚威王(公元前339年—公元前329年在位)時,越王無彊伐楚,兵敗被殺,越為楚吞并,“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另有部分越人則遷入嶺南,與當地土著越人融合。春秋以后嶺南與中原地區的聯系,楚國應該是主要的媒介。
第三節 楚文化對嶺南先秦文學的影響
根據《史記·楚世家》記載,楚人是祝融的后裔。《詩經·殷武》記載:“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說明楚人最早活動在荊山,早在湯建立商王朝時,楚就臣服于商,承擔起朝貢義務。但那時的荊楚僅僅是一種地域概念,居住著許多部落和大小邦國。從楚國的歷史來看,楚應是商朝荊楚的主要部分和核心力量,說明楚有綿長的傳說史。西周初年,楚與周王朝關系比較密切。《史記·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可見早在周滅商前,楚就歸附于周了。鬻熊卒后,其子孫奮發努力。《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楚人的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于天子”。《史記·楚世家》載:“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周天子的冊封,實際上是對楚人久住丹陽的既成事實的認可,名雖為國,實際上是一個部落聯盟。雖然如此,楚人總算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認,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名正言順地得到了開拓、發展的契機。自熊繹從荊山定居到丹陽,是楚國早期發展的重要標志。楚國所處的丹陽,實際上是百越等少數民族與楚人的共同雜居之地。周成王將這塊鞭長莫及的荒涼之地封給熊繹,實際上也是深知熊繹熟習各少數民族風俗,對鞏固南方能起到一定作用。楚人正是利用這塊無人問津的蠻荒土地,發展自己的事業。早在楚人先君鬻熊在荊山創業之時,楚人就與臨近的越人交往密切。楚人也以蠻夷自居,“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史記·楚世家》)。說明楚人在生活習性、文化品位上與中原保持一定距離,而與百越民族極為相似。正因為楚人在文化上接近百越,因此“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百越之地廣袤千里,政權又極其分散,這給楚人拓展疆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熊繹五傳至熊渠,拉開了拓展疆土的序幕。《史記·楚世家》載:“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楚國就是在不斷征服這些百越部落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楚武王時,國力加強,自尊為王,進一步開拓疆土,“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吞權、州、蓼等國。文王繼承武王遺志,遷都于郢,伐申伐蔡,滅息滅鄧,楚國逐漸強盛起來。楚成王即位后,“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周天子眼看著眾諸侯相互吞并,卻無力制止,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暫時的統治,也只好聽之任之。對于楚國的尊崇和進貢,周天子也很高興:“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楚國的擴張使得中原諸國為之側目,尤其是向北發展、問鼎中原甚至使周天子感覺到強大的壓力和恐懼。中原諸國只希望遏制住楚人向北發展的趨勢,而對楚人向南的擴張卻聽之任之,甚至幻想楚人能撫有夷越而“無侵中國”。就這樣,楚人不但逐漸將疆域擴充到中原腹部,也漸次將百越納入自己的版圖。至楚莊王時,楚國勢力達到頂峰,曾觀兵于周郊,問鼎中原。楚威王時,更是“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馬萬騎,粟支十年”(《戰國策·楚策》)。楚國是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最強盛時疆域據有湖北湖南兩省的全部及河南、陜西、山東、四川、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的一部或大部,其影響及于廣東、廣西、貴州、云南。《淮南子,兵略訓》說:“楚之強,大地計眾,中分天下。”勢力可與中原諸侯相抗衡。楚成王時,在周天子的認可下,楚國對今湖南、江西兩省的越族大舉進攻,“于是楚地千里”。楚悼王時期,“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后漢書·南蠻傳》)。今湖南全境并入楚國版圖。楚威王時,“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吳地至浙江,北破齊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此時江南百越之地,大部分已為楚所有。
楚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周初楚國所處的丹陽,實際是百越等少數民族與楚人的共同雜居之地。春秋戰國時期,與楚國經常發生關系的土著民族主要有“濮”、“越”、“巴”、“蠻”。周宣王時,楚君熊霜之子叔堪曾“避難于濮”(《史記·楚世家》),蚡冒時,楚國“始啟濮”(《國語·鄭語》),也就是說開始侵奪騷擾濮人。到了武王時,“始開濮地而有之”(《史記·楚世家》),也就是占領了濮人的土地。《史記·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楊粵即揚越,鄂在今武漢附近。劉向《說苑·善說》載鄂君子皙泛舟時,有“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楚悼王時,吳起在楚變法,國力大振,“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史記·蘇秦列傳》記載,戰國后期楚國“南有洞庭、蒼梧”。《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亦云:“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蒼梧的范圍,一般認為未逾南嶺,但已達南嶺山脈的九嶷山附近。考古發現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所制的“鄂君啟舟節”銘文也載:“上江,內(入)湘,庚(商),庚(商)陽;內(入),庚鄙;內(入)資、沅、澧、(油)。”這其中有關湘水沿岸的交通路線記載較詳,反映出當時湘水比資、沅等其他幾條水道更為重要,應是楚人南下五嶺的主要水道。據譚其驤先生考證,見即今湖南湘陰縣湘水西岸濠河口與喬口之間;陽即漢洮陽縣,今廣西全州湘水上游支流洮水(今黃沙河)北岸;鄙當漢代便縣,即今湖南永興縣耒水中游北岸。鄂君的水程西南路入湘、入耒,航線遍布于今鄂西南、湖南大部分,遠至廣西邊境。楚國在湘水、離(漓)水分水嶺附近設有陽(鄂君在此地免稅),這與西漢馬王堆帛畫地圖所記桃(洮)陽當指一地,此說應無誤,則楚南界已達南嶺。可見,早在戰國中晚期,楚國的官商船隊就經由湘、資、沅、澧諸水,遠達沅湘上游及五嶺地區經商,最遠可達陽等五嶺關口。結合包山楚簡來看,楚人主要是由環洞庭湖各縣邑和湘水沿線而南達五嶺的。值得一提的是,《史記·甘茂列傳》載,公元前305年,楚滅越國,“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厲門,《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瀨湖”;《史記正義》引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讀史方輿紀要·江西南安府橫浦關》:“或曰即楚之厲門”,并認為徐廣注釋“似誤”。實際上,楚之厲門不在粵贛交界的橫浦關,而在離(漓)水支流懶水(荔江),即今廣西荔浦南。《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相關圖頁也標繪于此。果真如此,則楚南界關口已過南嶺,湘水——離水通道已經形成,楚人勢力已經深入現在的廣西地區,廣西地區的越人成為楚國眾多民族中的一部分。
先秦時期,百越在揚州之南,故又被稱作揚越。《尚書·禹貢》載禹敷布九州,“荊及衡陽惟荊州”。古代廣西屬于九州中的荊州。《桂林風土記》:“按《地理志》:桂州,《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越,七國時服于楚。”《史記·楚世家》載楚莊王克鄭,鄭襄公肉袒牽羊求臣于楚,“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鄭襄公說“賓之南海”,說明當時嶺南已納入楚國的勢力范圍。在長年的征戰中,楚人與百越民族相互往來,促進了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給越人帶來了先進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文化知識。首先,楚國境內的百越民族與嶺南的百越民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在生產方式、生活習俗、民族信仰方面極為相似,楚國境內的百越受華夏文化的影響,會通過各種渠道傳播于境外百越,使境外百越對華夏文化有所認識,從而加強了對華夏民族的聯系。其次,隨著楚國軍事實力的強大,楚人也常想征服嶺南,進一步擴大自己的版圖。在楚國與百越交界的邊境上時有戰爭發生,有些地方是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在軍事力量抗衡的時段里,楚國也同境外百越保持政治外交,商賈貿易的往來。在戰爭和和平的各個環節中,許多楚物流入南越,而南越諸物也進入楚國。再次,在秦軍并吞楚國的同時,許多楚人逃入境外百越之地,與百越人民雜居,百越民族接納了華夏民族,更進一步加強了百越民族與華夏民族的結合,在廣西、廣東的出土文物中,也常有楚國器物甚至中原器物出土,這都是通過各種渠道進入百越之地的。
先秦時期,百越民族仍處于原始社會末期,他們沒有國家觀念,只有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部落觀念。楚人把他們納入以國家為機構的奴隸社會行列,迅速改變其社會結構,對他們進行“王化教育”,灌輸他們“大一統”的思想,使他們從原始部落迅速進入奴隸制乃至封建制度的國家。楚人也給越人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楚、越的交往是多方面的,既有戰爭時期的攻城略地、物質爭奪、人才得失,又有和平時期的結盟交往、禮品贈送、嫁娶婚約。這些人才、物質的得失,促進了雙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的交流。文種是楚國人,后為越王勾踐重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文種之言:“因越踐臣種奉先人藏器,甲十二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文種赴越,帶去了鐵器,導致了鐵制農具的運用和耕作技術的變革。楚人伍子胥輔吳時,曾領導筑城。《廣東新語·宮語》云:“越宮室,始于楚庭。”城市建設與設計恰恰楚是能者,伍子胥赴吳帶去了楚國的經驗。《史記·楚世家》記載楚越通婚事例:楚莊王“左擁鄭姬,右抱越女”,《列女傳》記載有“楚昭越姬”,“楚昭越姬”是越王勾踐的女兒。楚越通婚是兩國結盟的產物,隨著通婚而來的是兩國婚俗、禮樂的交流,珍奇寶物的交換。血緣關系的確立,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文化現象。從考古資料中也可以看到楚文化對吳越文化的影響。楚式鼎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春秋中期以后,楚式鼎為束頸、折肩、高足、壁漸改直、體態精巧,與吳越銅鼎有明顯區別,但到春秋晚期,已有吳國貴族仿造楚式鼎,如陜西鳳翔高山王壽出土的“吳王孫無土之月豆鼎”,鼎附耳、子母口、深腔、蹄足,蓋的中心有環。從銘文看是吳器,但上述形制則是楚的風格。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的交流往往是雙向的,楚文化不是封閉體系,而是開放體系。早先它接受了商周文化和吸收了江漢流域的蠻夷文化,逐步造就了自身的特征。楚文化在影響百越文化的同時,越人的先進技術和文化知識也常為楚人所吸收。早在楚國軔起之時,楚人就懂得利用百越的資源武裝自己。熊渠伐揚越,至于鄂,鄂是揚越的經濟中心,這里有最大的紅銅生產基地,楚人得到了揚越提供的大量紅銅,從而促進了楚國青銅冶鑄業的發展。春秋時期,吳越兵器甚為精良。吳戈,又稱為“吳鉤”,是盛行吳越地區的銳利兵器。楚人為了富國強兵,也學習吳人的先進技術。《楚辭·國殤》云:“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描寫楚人手執吳戈縱橫中原的戰斗場景。這里的吳戈不應理解為戰利品,而應該看作楚人仿造的吳式兵器。在《楚辭》的《涉江》中,有“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的詩句。越人善于用舟和習于水戰,《淮南子·齊俗訓》云:“越人善于用舟。”《越絕書》卷十則有著更生動的描述,他們“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楚人征戰江南,必須學習吳人的造船、駕船技術。
古代楚粵(越)同屬“南蠻”,且地域相連,族群文化交流頻繁,以至于后人將粵歌也稱作楚歌,如宋代做過番禺縣尉的詩人方信孺《南海百詠》,其中有詩云:“石鼓嵯峨尚有文,舊題銅鼓更無人;寶釵寂寞蠻花老,空和楚歌迎送神。”這里的“楚歌”當為粵歌。嶺南越族積極參與楚國的政治文化活動,先后出現了一些出類拔萃的知名人士。《廣西通志》說:“自會稽以南,踰嶺皆粵地也。秦漢之先,蓋已有聞人者。”其中南海高固曾為楚威王相。《讀史方輿紀要》:“相傳南海人高固為楚威王相,時有五羊萃谷于庭,逐增南武城,周十里,號‘五羊城’。”“五羊城”即“南武城”,又稱“楚庭(亭)”。萬歷《廣東通志》曰:“開楚庭,曰南武。”嘉靖《廣東通志》曰:“楚亭郢在番禺。”嶺南古城“五羊城(廣州)”的出現正是楚越(粵)文化交流的結果。《廣東通志》卷四十四:“周高固,粵人。周顯王時,楚子熊商滅越,兼有南服,是為楚威王。固以才能歸楚,為威王相。時鐸椒為威王傅,以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凡四十章,為《鐸氏微》,由固進之。以故文教日興,五羊銜穀,萃于楚庭,南海人畫圖以表固功。”《百越先賢志》卷一:“高固,世在越,稱齊高傒之族。”高固的先祖是齊國人,高氏先后數代人漸次由中原遷往嶺南,至高固為楚威王相,參與楚國高層決策。屈大均《廣東新語》嘗云:“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但屈氏所謂的“文事”并非著述,更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他說:“即高固為相,嘗以《鐸氏微》進楚王,亦未聞有文可稱。吾嘗謂廣東以文事知名自高固始,謂其能以《春秋》事君也。”[23]《漢書·藝文志》著錄《鐸氏微》三篇,并云:“楚太傅鐸椒也。”屈氏所謂的“文事”乃是儒學的傳播。高固一生固然“未聞有文可稱”,但他將鐸椒《鐸氏微》推薦給楚威王,至少說明高固對于歷史典籍《春秋》應該是相當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