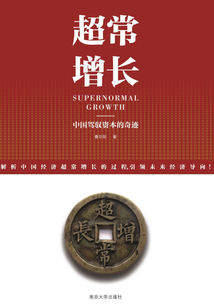
超常增長:中國駕馭資本的奇跡
最新章節
- 第10章 注釋
- 第9章 農民工市民化和新的農村建設
- 第8章 資本運營:投資銀行爭奪貨幣和駕馭資本
- 第7章 金融改革:在市場經濟中駕馭金融資本
- 第6章 從高速鐵路談到技術引進要保持主動權
- 第5章 城市政府掌控城市資本駕馭城市經濟
第1章 序
2012年出版了《資本是個好東西》,是嘗試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直至20世紀90年代大約四十多年諱言資本之后重塑資本形成機制的一個回顧。現在這本《超常增長——中國駕馭資本的奇跡》,是想從政府和市場經濟這個層面,探討中國經濟是如何駕馭資本實現超常增長的。
中國經濟是如何實現超常增長的?從根本上說,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明確方針。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重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更明確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
但是,在某些經濟學家看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功,都是市場的功勞,如果沒有政府的作用,可能還會更好。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人福山一度把自由民主看作“歷史的終結”,有些沉迷于西方經濟學的人士借著這股“西風”,更是不遺余力地批評這個“宏觀調控下”,說它是半統制、半市場的畸形格局,質疑這是給“市場”設置了一個“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前提,爭論究竟是在政府的作用下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還是在市場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有人就嚴詞批判“以強勢政府為主要特點的中國模式”,總是擔心會“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多次強調只能是“有限政府”。
作者研究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軌跡,發現有五個突出因素:
第一個突出因素是中國延續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主要是在最重要的國民經濟領域和創新型國家建設領域,如過去的“兩彈一星”這類重大項目,無論是建設、投資、技術引進、運行管理,乃至重要的話語權,都要牢牢地掌握在國家手中。惟其如此,中國才創造出高速鐵路、超級計算機、神舟飛船空間技術、軍工、核電、新一代通信標準等戰略產業的輝煌奇跡。中國修建了世界上最大最好的高速鐵路網、最大的高速公路網;所有能建地鐵的城市都在修建地鐵,上海已經修建了688公里的地鐵,這是世界上最長的城市地鐵線。最新的喜訊是C919大飛機在上海成功首飛。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把我們的高速鐵路與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和超級計算機一起,并稱為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大突破”。這個評價,高屋建瓴,令人振奮。
第二個突出因素是,我們毫不猶豫地緊緊抓住國有企業進行的脫胎換骨的改革。沒有聽從那些休克療法的誤導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論者食洋不化的書生之見,沒有把國企“一賣了之”、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而是對相當部分的國有企業力推產權多元化和公司上市,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使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為核心的公有經濟成為市場的主體,并具有了當代發達國家現代企業的最先進的財產組織形式,當然也是最具活力的管理形式。
第三個突出因素是在發展民營經濟方面,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聯合和并購,通過抓大放小,國有經濟的布局結構有了實質性的變化,正如邵寧所說,主要就是“我們的國有經濟從中小企業層面實現了退出”,由此推動了國退民進,也推動了民營經濟的成長,而放掉的一大群中小企業恰恰為民營資本的進入和發展提供了機會。現在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50%,民營經濟的就業占全國的75%,成了中國“出人意料發展的推動力量”。
第四個突出因素,是在城市化方面,城市政府突破了西方國家政府“只能管理、不應參與經濟”的框框,既不同于西方國家“小政府+大市場”的經典的市場經濟模式,也不同于那種強調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更不同于后來興起的極力主張貿易金融投資自由化和國家干預最小化的“華盛頓共識”的市場經濟,而是別出蹊徑,通過成功地掌控中國特色的城市資本,即利用政府所控制的“土地”加上“三通一平”(指通水、通電、通路、平整土地)、“七通一平”(指“三通一平”再加通郵、通訊、通暖氣、通天然氣或煤氣)以及基礎設施的資本,我通稱為城市資本,在招商引資上引導外來資本的競爭,駕馭外來資本,發展了城市經濟。由此,我發現正是城市政府的駕馭資本,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
第五個突出因素,是資本化為我們建立了一個能鼓勵金融創新和持久地擴張資本的機制。
什么是“資本化”?資本化的真正奧秘就在于,如何把企業具有創造未來收入能力的資產“開發”成為資本市場上可以交換的資本。中國長期以來資本極度短缺,1990年證券市場開放,正好有了一個“資本化”的機制,給企業和市場提供了一個在銀行之外直接融資的機會,通過股市融資、債券融資、資產證券化、私募和金融創新,成為分流銀行資金的重要渠道。到2010年末,20年來累計為2000多家上市公司實現股本融資2.5萬億元,債券融資2.9萬億元;募集投資基金2.51萬億元,合共近8萬億元。到2015年,中國證券市場開放25周年,滬深兩地已有上市公司2827家,總市值53.13萬億元。2016年度A股市值收于50.62萬億元,滬深兩市市值整體小幅縮水。人們習慣于把企業上市融資說成“圈錢”。證券市場并不是“點石成金”,但由此具有了一個從市場上開發資本并能以較高的收益作為回報的機制,為經濟的超常增長增添了一個重要支柱。
應該說,中國在列強環伺下,成功地運用強勢政府,通過股份制改造,力推產權多元化和公司上市,改革和發展了具有強控制力的國有經濟,從無到有地扶植非公有制經濟,成功地掌控城市資本駕馭外來資本發展城市經濟,從容應對加入WTO以后國際競爭的嚴峻挑戰,正是強勢政府駕馭資本推動市場發揮了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而且,正因為計劃經濟時代有30年對諱言資本的抑制,改革開放后重新認識了資本,這才有了這三十多年政府、企業一齊忙于引進資本和擴張資本的駕馭資本的活動,推動了這二十多年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
至于強勢政府有什么負面影響?我以為,最大的負面影響就是60年的工農業產品價格上的剪刀差和2.7億農民工不能市民化,沒有公平地對待8億農民這個最大的弱勢群體。還有追求經濟業績,忽視了對環境的保護,助長了污染,乃至區域分割,割裂了全國統一市場。
同時,必須強調指出,政府的強勢并非一成不變。政府在強力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之后,要懂得退場,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面的說法,就是“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是,中國的強勢政府是從計劃經濟的全能政府演變過來的,它在干預經濟方面,往往存在著一種過度干預,即所謂錯位和越位,或不懂得退場的毛病,這是中國的強勢政府與生俱來的某種惰性,或者說是固有弱點。因此,我們在正視強勢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也必須正視這種惰性或固有弱點。我以為,正如西方在政府干預上往往有畫地為牢過分猶豫的惰性一樣,中國則往往有政府當家慣了、干預過多和不愿退場的惰性。中國和西方國家在完善市場經濟方面都必須克服各自的惰性。
還要看到,最近這1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中有一個新的特點,即具有中國特色的高速鐵路加城市群,充分發揮了級差收益原理在產業結構高度化方面的作用。以長三角的無錫市來說,2011年無錫的人口是467萬人,2015年達到651萬人,4年增加了將近一半的人口,這都是得益于高速鐵路推動了長三角大城市、特大城市產業結構高度化帶來了無錫市的地域擴大和經濟繁榮,因而才帶來了人口的增加。但是,在經濟學界,很多談論經濟增長的文章卻很少談到高速鐵路加城市群和級差收益原理在產業結構高度化方面的推動作用,幾乎成為當前經濟研究的一個盲點。應該說,正是在這個方面,給有志研究者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本書的出版,要感謝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榮衛紅女士不辭辛苦,特別是對本書書名反復商討,提出不少寶貴意見。還要感謝鄭捷同志為本書穿針引線,侄女邵鳴為本書出版奔波,在此一并致謝!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