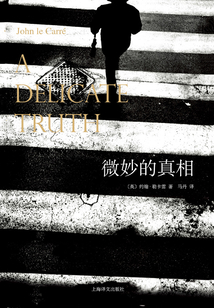
微妙的真相(勒卡雷作品)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保險箱和腹語術
代約翰·勒卡雷《微妙的真相》前言
突然之間,似乎覺得不應再背負秘密,八十過后的勒卡雷決定向追隨他多年的讀者揭露自己。繼2015年出版迄今為止最完整翔實的個人傳記后,今年九月他又將出版一部回憶錄The Pigeon Tunnel,其所記或人物事件,或器物場景,看似零星,卻很可能會成為理解其作品完整意義的關鍵編碼片段。
The last official secret(最后的官方秘密)一節中,勒卡雷從年輕時他頭腦中一個古怪信念講起——多年來他一直認為這個國家最“火爆”(hottest)的秘密鎖在一只破舊的綠色保險箱中。保險箱放在一間頂樓辦公室內,這間辦公室所在大樓位于圣詹姆士公園地鐵站附近,樓道復雜幽暗,只有獲得特許的極少數人才有機會進入。大樓是軍情六處總部,頂樓是首長辦公室。勒卡雷二十出頭剛剛加入間諜機構時就聽人家說,那保險箱內的秘密文件只有情報處主管本人能夠閱讀。
歲月匆匆,事情來了。大樓要拆遷,新總部將坐落于泰晤士河岸,丑,而且現代化,在此之前情報處所有人員和動產先搬到臨時駐地。關于那只保險箱展開了激烈討論,讓起重機、撬棍和沉默的人們護送它完整抵達下一個時代嗎?高層反復爭論,終于達成決議:無論保險箱中的東西多么神圣寶貴,也已不再適合現代世界了,打開它。不管那會帶來多少麻煩,宣誓、詳細歸檔、根據其敏感性重新授權,開無數會簽無數字,總之,打開它。
但是,那把鑰匙呢?現任首長不知道,他從未動過打開保險箱的腦筋,對其中秘密毫無興趣。他的生活哲學是不知者不會泄密。前任呢?前任的前任呢?誰也不知道鑰匙在哪兒。登記處、秘書處、內保部門,問了一大圈,沒有人知道,永遠板著面孔坐在廚房椅上的看門人也不知道。大家只曉得保險箱根據“蒙塞”(Menzies)先生的命令安裝,“蒙塞”是二戰時期情報處的領導人。鑰匙在他那兒嗎?是他從字面意義上嚴格履行了誓言:把秘密帶進墳墓么?他有理由那么做,是他創辦了英國戰時密碼破譯機關“布萊切利公園”,他上千次密會丘吉爾,他既聯絡歐洲地下抵抗組織,也接觸納粹德國情報機關頭子,天曉得那保險箱關著什么魔鬼,放出來也許就是世界末日。
情報處有能人,他們找來開鎖專家。稍一擺弄就打開了,速度快得讓人意外——那也太容易了吧?但保險箱內是空的,什么都沒有。等等,這地方可全都是陰謀家,訓練有素,不會輕易上當。這個保險箱會不會是個假餌?它有沒有夾層?它是不是掩蓋著真正的秘密洞穴?一根鐵撬棍送進房間,輕輕地從墻上撬下保險箱,高級長官親自伸頭過去,檢視保險箱與墻壁的夾縫。哇,傳來一聲驚叫,甕聲甕氣,像是來自遠方。他伸手進去,慢慢抽出來一團東西,灰撲撲,仔細看是一條舊褲子,有一小片檔案標簽,用尿布別針釘在褲子上,打字機字體清晰可辨,宣告褲子的主人是魯道夫·赫斯,納粹黨副黨魁,元首希特勒的親密同志。當時他自己駕機降落在蘇格蘭,試圖與漢密爾頓公爵單獨媾和,因為他得到錯誤情報,以為漢密爾頓公爵同情納粹。標簽下方另有一行手寫體,是情報處首長傳統上使用的綠色墨水:請送實驗室分析,也許能提供一些有關德國紡織工業的重要信息。
最大的秘密是沒有秘密,加上一條臟褲子。不知勒卡雷是從什么時候起猜到保險箱中其實沒有什么秘密的。他小說中那些情報機構,從來都沒有完成過什么有意義的情報業務。書中人物永遠都陷入假情報或者反情報陷阱中,希望渺茫,努力脫身。“巫術情報源”是《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故事最大的秘密,最終卻證明都是毫無價值的偽造情報。五十年后,八十高齡的勒卡雷出版了《微妙的真相》,小說中事件的緣起仍然是一條假情報。
與史邁利的對手不同,《微妙的真相》中假情報的提供者是國防承包商。“巴拿馬裁縫”們,以及格林筆下那種“我們在哈瓦那的人”們,如今早已企業化。合法的情報騙子專項承包國家機構情報業務,假情報引發的行動和災難結局被鎖進國家最高機密的保險箱中,誰都不想打開它。在后冷戰國際政治機制下,此類外包業務漸成慣例。針對敏感地區的間諜活動由私人公司承保,各國政府借此可以免除國際法責任。有關當代間諜活動的報刊報道中偶或見到一個詞組,據說是情報業內行話,“cut-off”可以用來指稱這種秘密行動或這類私人情報機構,因為對官方機構來說,把敏感業務(臟活)交給此類公司操作,目的就在于讓它們成為一道防火墻,或者說一副白手套。爭議、失敗和丑聞一旦出現,官方便能切割關系,撇清責任。
在小說中,災難事件真出現了。雖然是假情報,可是按預計沒什么要緊。行動小組撲個空,寫個報告上呈,總有理由可循,行動中偶然疏漏被對方發現,對方無故突然改變計劃。一個小小失敗,很正常,事情會完全掩蓋起來,鎖進保險箱。因為相關各方已提前兌現了利益。可誰也沒有事先估計到小說中出現的那種情況,小失敗變成大悲劇,當然在大部分參與其中者(包括部長、公司老板、雇傭兵頭領)看來,那仍舊不過是一個小小意外,但有人就不同意了。
其中包括一名特種部隊戰士、一個老外交官和一位高級文官秘書。后面兩位多少能看到一點作者本人的影子。勒卡雷年輕時也曾派駐使館,工作業務范圍與托比·貝爾差不多。老外交官基特·普羅賓退休后住在康沃爾,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樂無邊。勒卡雷自己也長期住在康沃爾,附近居民都記得他,下午獨自步行在山谷坡地間,嘴里喃喃自語,不知道他在說什么,激動起來甚至站在面對大海的峭壁上朗誦,看樣子好像都是些戲劇臺詞。
這些不同意把悲劇僅僅視作小小意外的人們想要揭露真相,可大人先生們認為真相十分微妙,必須掩蓋起來。真相也是脆弱的,一不小心就會碎裂、溶解、消失。在勒卡雷自己那個時代,政府機構人員常常在說話中用到delicate這個單詞,意味某種特別敏感的秘密,一旦揭露會引發政治危機,必須把它們牢牢鎖進保險箱。能不能打開這個整個英國統治階級(establishment)精心維持著的秘密保險箱,只能依靠這少數幾位反對者。
勒卡雷曾對《電訊報》采訪記者說,他確實變得越來越激進。他甚至改變了政治立場,不再給工黨投票。因為新工黨傾向富人的政策,因為新工黨在外交政策上無所作為。他覺得把國家權力讓渡給私人公司企業,很可能讓英國變成一個法西斯國家。在《微妙的真相》中,他設計了一個新工黨部長,充滿野心和私欲,是他讓英國政府卷入一個行將暴露的丑聞之中,讓整個國家機器無可奈何地幫他一起掩蓋真相,收買、暗殺知情人。
勒卡雷的后冷戰間諜故事確實反映了作者某種更為激進的態度,與從前史邁利們不同,勒卡雷筆下這些新時代正義戰士不再有各種精神困擾,他們不是為某種意識形態而戰,只是勇敢地、幾乎本能般地選擇了某種道德立場。這確實讓故事和人物變得簡單了。甚至這也可能跟故事本身某種內在邏輯必要性有關,因為抽離了冷戰這個大前提,故事中人也許需要更鮮明的立場才能投入戰斗。然而歸根結底,那是勒卡雷一以貫之的想法。在勒卡雷的間諜世界里從來就有兩種敵人,一種站在冷戰敵對那一方,另一種則躲在己方內部,冷戰結束后,他們成了最大的敵人。他們是腐敗機構和僵化體制、階級、公學教育、利欲以及“微妙的真相”。是他們給世界帶來傷害,是他們傷害了他的托比·貝爾和普羅賓們,是他們讓他的史邁利們徒勞無益地付出代價,成為犧牲品。
勒卡雷回憶錄的書名是The Pigeon Tunnel(《鴿子隧道》)。勒卡雷特別喜歡這個名字,多次考慮以它作書名,《純真傷感的情人》、《榮譽學生》、《史邁利人馬》,不知為何全都作罷。一直到八十多歲出版回憶錄,才有機會用上。
多年來,“鴿子隧道”的意象始終縈繞在勒卡雷心中,他終于有機會用它做了書名,并且在序言中講述了那個故事。在勒卡雷快過二十歲生日時,他父親決定把他帶進自己的生活——到蒙特卡洛來一場賭博狂歡。他們入住的賭場酒店外有一片草地,面對著地中海。賭場管理人把它設計成射擊訓練場,紳士們午飯后便來這兒打幾槍。草坪底下埋著成排細窄管道,管道另一端在大海岸邊露出地面。賭場在樓頂上飼養了大群鴿子。成群的鴿子被人從草地一頭塞入管道,它們順著這條地下隧道擁擠前行,終于來到大海邊。它們振動翅膀,騰空而起,射擊場紳士們手中獵槍齊齊開火。這時候最讓勒卡雷感到震驚、讓他無法忘記的一幕發生了,那些未被獵槍打中的鴿子并沒有就此逃逸,反而再次回到賭場樓頂,因為自出生以來它們便棲息于此。等待它們的將是下一條隧道。
也許對于勒卡雷來說,意識形態敵人并不是最大的敵人,官僚機構中幾名腐敗高官也不見得能給世界帶來多大災難。是那個類似“鴿子隧道”的社會結構,讓他的小說中人陷入某種永恒夢魘——努力前行,卻永遠只不過擠向犧牲品命運。
盡管已是八十高齡,勒卡雷在《微妙的真相》中仍舊展現了嫻熟的敘述技巧。時間線、視角、尤其是人物對話。勒卡雷小說中的對話獨具作者個人印記,有人將其形容作某種“腹語術”風格。那些說話聲像是被竊聽者記錄,看不見對話者,聲音卻清晰可辨。那些聲音疏離、斷續,有時候需要在不同場景中多次回味才能辨識其意義。那些對話甚至總是跟正在說話的書中角色不在同一個時空中,具有它們自己的獨特戲劇魔力。這也許跟勒卡雷的寫作方式有關。我們先前說過,康沃爾的鄰居們常常看到勒卡雷獨自散步,口中自言自語,那正是作者在構思人物對話。勒卡雷寫作時往往在書桌上先寫好敘述部分,隨后才重寫對話。這部分工作他通常在散步時完成,他有戲劇天賦,會導會演,他想象對話場景,獨自扮演小說中不同角色,讓他們互相對話,回到家中用打印機記錄那些聲音。
小白
2016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