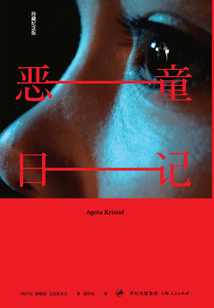
惡童日記(珍藏紀(jì)念版)
最新章節(jié)
- 第6章 附錄 雅歌塔:我寫的是自己的真實(shí)童年
- 第5章 Le Troisième Mensonge 第三謊言
- 第4章 La Preuve二人證據(jù)(2)
- 第3章 La Preuve二人證據(jù)(1)
- 第2章 Le Grand Cahier惡童日記
- 第1章 譯序
第1章 譯序
◎ 簡伊玲
就如同一位認(rèn)識多年的朋友。我們共有的記憶,僅止于最初共事的那幾個(gè)月,雖短暫,卻相當(dāng)深刻,如今回憶起來,在歲月蒙上的淡淡光暈下,一切是顯得如此美好,如夢般地不真實(shí)。這些年來,看見這位朋友的成就與廣受大眾喜愛的那道熠熠光輝,我真心為此感到歡喜,但我只想不發(fā)一語,靜靜地在一旁看著……
這就是我和“惡童三部曲”這么多年來僅存的關(guān)系。雖身為譯者,但我始終不覺得其成就與我相關(guān),自然也不認(rèn)為自己能為它說些什么,因?yàn)榫瓦B當(dāng)年從出版社手中拿到剛印好的三部曲之后,我也鮮少再去翻閱它,談?wù)撍豢桃馊ラ営[網(wǎng)絡(luò)上相關(guān)的評論與討論。
即使如此,這些年來仍免不了遇到這樣的介紹詞:“這位是‘惡童三部曲’的譯者。”而最常面對的疑問就是:“當(dāng)年你譯這小說時(shí),有料到它會這么暢銷嗎?”我的回應(yīng),也是總簡單一句:“從沒有。”
的確,那是二十年前的我,一個(gè)剛從法文系畢業(yè),對于翻譯、文學(xué)都還僅止于課堂上的習(xí)作與淺薄閱讀經(jīng)驗(yàn)的年輕人,只是憑借著對文字與閱讀的喜好便自不量力地參加試譯,而得到這樣的翻譯機(jī)會。那樣的我,能有什么預(yù)期?別說預(yù)料它會暢銷,就連自己因?yàn)樽g了這套小說而一腳栽進(jìn)翻譯書的領(lǐng)域,至今編輯一做就是二十年,這也是當(dāng)年我從沒預(yù)料到的轉(zhuǎn)變。我惟一能肯定的是:我的運(yùn)氣很好。有些譯者接了一輩子的稿,能談得上喜歡的書沒幾本,然而我,卻在第一次翻譯,便交上好運(yùn),遇見這三本讓我傾心不已的小說。如今回想,縱使自己后來也譯了幾部小說,在編輯工作上也接觸過不少外文書,但“惡童三部曲”幾乎可以說是最精彩、最令人難忘的作品。
就是這樣的難忘,盡管二十年來我不曾再去重讀自己的譯作,也能清楚鮮明地憶起那段譯書時(shí)期它所帶給我的悸動、震撼、驚恐與不舍。那是一道極為深刻的烙印,已是我不須努力思索便能輕易想起的經(jīng)歷。
那是一個(gè)網(wǎng)絡(luò)未興、計(jì)算機(jī)尚未普及的年代。一開始我拿到的《惡童日記》,除了一份原文復(fù)印稿之外,什么都沒有。不似現(xiàn)今的譯者,也許可以先上網(wǎng)查查作者的背景,寫作的動機(jī),或是國外評論、讀者評價(jià),甚至多看幾眼作者的照片,好清楚未來幾個(gè)月即將跟你相處的文字是出自何人之手。對于作者的認(rèn)識,我則全來自書封復(fù)印的那張照片及幾百字的介紹文。那是一張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臉部轉(zhuǎn)左看著鏡頭的相片。鼻梁上架了副圓形細(xì)框眼鏡,嘴角若有似無地上揚(yáng)。鏡片后方是一雙犀利、帶點(diǎn)冷漠、無所畏懼,像已看透世事的眼睛。我盯著那張照片好久,再對照著法文書名LE GRAND CAHIER幾個(gè)字看,竟感到那神情深不可測。
而后進(jìn)入翻譯,不時(shí)地,我也會望著那張臉,它的神情總是隨著書里的情節(jié)而不斷轉(zhuǎn)變。不可否認(rèn),這三本書帶給我的震撼,無論是驚駭、悲傷、冷酷、邪惡或憐憫,我都曾經(jīng)試著不與作者畫上關(guān)聯(lián)。但是太難了!雖然在當(dāng)時(shí),我對于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了解極少,僅知她是匈牙利人,這是她第一次用法語寫作,可當(dāng)我讀著、譯著她的小說時(shí),主角雙胞胎兄弟那般驚世駭俗的行為、超乎我們能理解的冷血,或他們接觸到的變態(tài)人事,在在讓我不得不將其視為作者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真實(shí)經(jīng)歷。因此這張臉,有時(shí)詭異得令我害怕,有時(shí)卻又顯露出歷經(jīng)悲慘歲月淬煉的那種冷漠而令我憐惜,我始終覺得它隱藏了更多秘密,或許是比“惡童三部曲”所揭露的更讓人難以逼視。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曾經(jīng)坦言,她的法語不好,是跟小孩一起學(xué)的,而在創(chuàng)寫這三部小說時(shí),曾運(yùn)用了兒子的習(xí)作,以兒童的語言來寫。這也是一開始我在翻譯時(shí)遇到的難題。沒錯(cuò),整本《惡童日記》全是以最簡單的文字寫就,但就是因?yàn)樗暮唵危旁斐煞g上的難。那種難度不在語意上的理解,而是口吻的拿捏。這對雙胞胎兄弟用“我們”講出了他們的故事。在那戰(zhàn)爭侵?jǐn)_的背景下,為了生存,每個(gè)人都有不得已的選擇與轉(zhuǎn)變。有的是雙胞胎兄弟眼中所見的他人惡行,有的是他們自己所做的惡行,也有悲傷、惡心、變態(tài),但是經(jīng)由兩兄弟的描述卻是這么的平靜、冷漠、事不關(guān)己,就連傷害、驚恐或荒謬,在他們的語氣中也見不到一絲的起伏與擺蕩的痕跡。
我想,真正的“惡”就是在面對“惡”時(shí)的無感與冷漠。更何況,他們還只是一對年幼的孩童。光是這點(diǎn),就令我不寒而栗。然而我卻深知,這對雙胞胎的“惡”不是來自本質(zhì),而是不得不的選擇。因?yàn)樗麄冞€是會難過、悲傷或憐憫,只是在那處境下,他們從生活經(jīng)驗(yàn)學(xué)到:悲憫無法讓人存活;而身為人,沒有哀傷的權(quán)利。所以,他們學(xué)習(xí)對生活無感,對他人無覺,學(xué)習(xí)不被哀傷擊倒,甚至要學(xué)習(xí)“惡”。于是,我也一路學(xué)著他們,觀看他們的內(nèi)心,在那看似單純童稚的語氣下,要自己再激動也必須維持筆調(diào)的冷靜,用字要冷漠,要壓抑,更不能有一絲的情緒。甚而到了《二人證據(jù)》《第三謊言》,我也以此為基調(diào),隨著作者敘事風(fēng)格的轉(zhuǎn)變、主角年齡和歷練的改變而逐一揣摩,在一個(gè)適當(dāng)?shù)木嚯x之間貼著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文字,而至真相漸明的時(shí)刻。
當(dāng)時(shí)的翻譯,我是一字一句在五百字稿紙上寫的,寫錯(cuò)了、要改的,就用立可白涂掉;涂改太亂的,便剪貼文字塊或重新謄寫。有時(shí),我的筆趕不上我的腦子,是帶著手快抽筋、手腕酸痛的力道在追寫;但有時(shí),我的筆卻慢得不得了,那往往是又一幕比之前更令我驚駭?shù)漠嬅娉霈F(xiàn),它讓我愣在那里,不停地自問:“有那么慘嗎?”“會這么變態(tài)嗎?”“是我會錯(cuò)意了嗎?”總是要等自己接受了,平撫好情緒,我才能好好地再繼續(xù)譯下去,或是重新再譯。
翻譯這三本書時(shí),我白天有一份與外貿(mào)相關(guān)的工作,但總是惦念著前一晚翻譯的情節(jié),時(shí)時(shí)都迫不及待想下班,像著了魔似的想盡快進(jìn)入惡童的世界。如今回想起來,那樣的我真像中了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魔,隨時(shí)隨身都帶著一疊稿紙和復(fù)印稿,只要逮到機(jī)會,無論是火車上、候車處、咖啡廳……任何一個(gè)能寫字的平臺,我都不會放過地?cái)[出稿紙和復(fù)印稿,立刻和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文字進(jìn)行交流。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gè)二月的夜里,當(dāng)我翻到《惡童日記》的最末章,沒寫兩行,竟然筆沒水了,房間里也找不到任何可寫的筆。情急之下,我什么也不管,披了衣服便出門買筆。偏偏那晚陽明山上很冷,霧又特濃,當(dāng)我一站到濃霧中時(shí),發(fā)現(xiàn)時(shí)間已近兩點(diǎn)。任誰都知道,這時(shí)間所有的商店都關(guān)了,再加上這濃霧,我簡直寸步難行。惟一可能有筆賣的,卻是離我?guī)缀跤幸还镞h(yuǎn)的7-11。那一刻,我不管冷也不管霧,或許是整個(gè)人的心思沉浸在惡童的惡行中,那般不可思議的惡行讓我腦門發(fā)熱而急著將它寫下,所以我不多想,便立刻往7-11的方向快步走去。一路上,翻譯并未在我腦子里停擺,我不停在心里問著那對惡童:“你們怎么能這么冷血?怎么能這樣對待你們的父親?怎么能!……”
那是個(gè)我不認(rèn)識的自己,翻譯翻得如此入戲,如此無可自拔!但如今回想,我卻也覺得那是理所當(dāng)然的反應(yīng)。因?yàn)槲蚁嘈牛绻麚Q成另一部作品,不是這么章章節(jié)節(jié)都精彩、讓人讀了譯了就上癮的作品,我應(yīng)該會理智許多,也絕不會在深更半夜急忙跑出門,只為了買一枝筆。
二十年前的我,從未預(yù)料這三本讓我翻譯到入迷的小說會在后來的書市引起如此暢銷及長銷,這是實(shí)話,卻也是句粗心的話。都說譯者是原著的第一個(gè)讀者,也是和作者相處最久的人,如果當(dāng)時(shí)我能意識到自己翻譯時(shí)的著魔反應(yīng),應(yīng)該就不難想像這三本書在未來書市將會引起的巨大震撼。
“惡童三部曲”是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大器晚成之作,是她第一次著手創(chuàng)作的小說,也是她生前最暢銷的作品。有些作品的暢銷或許是靠時(shí)勢,靠運(yùn)氣,或靠炒作而起,或是連什么原因暢銷也不得而知,但是“惡童三部曲”完全不是。它確確實(shí)實(shí)是靠著作品的本質(zhì),靠著它的口碑,從二十年前網(wǎng)絡(luò)未興的年代一直長紅至今,它甚至不靠任何的宣傳口號便虜獲各個(gè)年齡層的讀者。在法國如此,在二十年來的臺灣也是一樣。
從“惡童三部曲”的譯者,而至今天外文編輯的身份,我也曾經(jīng)試著回顧在過去二十年,有哪些作品能夠在書市長命存活?“惡童三部曲”即是少數(shù)之一。每一回遇到法國出版商,他們總免不了問我既然從事法文翻譯書的引介工作,是否也譯過法文書。而當(dāng)我說出“惡童三部曲”時(shí),從他們臉上的驚訝表情,我也幾乎能肯定雅歌塔·克里斯多夫這個(gè)名字,以及“惡童三部曲”這書名在法國文壇擁有多么響亮的名聲及重要的位置。
我很慶幸,在年輕時(shí)即遇上“惡童三部曲”,讓我能走入法文小說的迷人世界,而看見文學(xué)的另一番景致。就如同從未預(yù)料它的暢銷,我也不曾想及它能在臺灣書市火紅存活二十年之后,如今竟在簡體中文市場掀起另一波高峰。而在此時(shí)此刻,我相信這絕對是另一次閱讀熱潮的起點(diǎn),而且將會長長久久地持續(xù)下去,因?yàn)槲以?jīng)那么無可自拔,深深走入了“惡童三部曲”的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