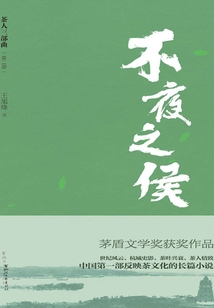
“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
兩千年,一花獨放,唯我獨尊,爾后,華茶的下一個大時代,便以與以往迥然不同之命運開始了——
有世紀初皖地民謠為證:
三月招得采茶娘,四月招得焙茶工;
千箱捆載百舸送,紅到漢口綠吳中。
年年販茶苦價賤,茶戶艱難無人見;
雪中芟草雨中摘,千團不值一匹絹。
錢少秤大價半賒,口喚賣茶淚先咽。
官家榷茶歲算緡,賈胡壟斷術尤神;
傭奴販婦百苦辛,猶得食力飽其身。
就中最苦種茶人。
這首載于中國安徽《至德縣志》的1910年間傳唱的民謠,其中不但出現了歷代民間茶歌中的譴責對象——官家,還出現了另一個名詞——賈胡。
賈胡,即來華經商的外國人,而由賈胡生發,另一個有關茶業行的名詞——洋行,便要被我們引入20世紀初的視野之中了。
中國官方專門對外做生意的機構,古來有之。只是到得清代,方被稱為洋行。洋行可以做各種生意,比如毛織品、洋布、鐘表等,但最大宗的生意,到底還是國之瑞草茶葉。
追本溯源,人類與茶的親和,正是從華夏民族對人類的親和開始的。恰如茶圣所言:飛禽、走獸和人類,都生活在天地之間,依靠飲食維持生命活動,飲食的意義是多么的深遠啊!要解渴,就得飲水;要消愁,就得飲酒;要消睡提神,就得喝茶。(《茶經·六之飲》)
茶的發現和利用,是一個真正的東方傳奇故事。《神農本草》中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這個荼,就是茶。
神農在中國古書中,被描繪成一個頭上長牛角缺一顆門牙的男子,一位距今四五千年前的上古時期的部落領袖。因為勸人們種百谷、植桑麻,被尊稱為神農氏。他正是那種類似于古希臘普羅米修斯和俄國丹柯那樣的受難英雄。他遍嘗各種草木,不幸中毒倒下,恰有水珠從茶樹上落下滴入口中,方才得救。
這個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因此,神農不但成了中國農業和醫學的創始者,也成為世界上最早的茶葉發現和利用者。
中國最早的地方志書之一《華陽國志》告訴我們,三千年前,在現今中國的四川地區,人們就開始人工栽培茶樹,并把它作為地方特產獻給了當時的天子周武王。
戰爭打破了寧靜的茶葉世界。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關中地帶的秦國人攻下了重巒疊嶂的巴蜀,中國西北部粗獷的士兵們驚異地發現了這種可以煎煮飲用的綠葉。這樣,茶葉就裹在他們的馬革中,翻出蜀道,被帶向廣闊的天地。
戰國之前,中國的茶葉種植已從湖北延伸到湖南、江西地區。自此以后,便在長江中下游擴展。
茶,興于唐而盛于宋。唐貞觀十五年,茶作為文成公主的陪嫁品,不遠萬里,長途跋涉,來到了吐蕃松贊干布的故鄉。飲茶習俗,從此傳入西藏,成為邊疆少數民族不可或缺的飲料。
在這個茶葉文明大傳播的時期,茶在被架在馬背上走向雪山草地的同時,也被僧侶們負在肩背上,帶往寒冷的北方;然后,它又被盛入精美的器具,在宮廷達官貴人們的手中相互傳遞。公元8世紀初,北方飲茶習俗開始蔓延傳播。
明代,中國著名的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把茶帶到了遙遠的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
茶的羽翼已經豐滿,下一個歷史時期,它將在全世界翱翔。
英語中茶(Tea)的發音和法語中茶(Thé)的發音,恰與中國海路傳出的福建方言“茶”字的音Te相似;而由陸路傳向西亞、東歐的“茶”字音,則來自中國內陸地區的“茶”字發音——比如俄語中的Чай,土耳其語中的?ay——它們多少也從語音學的角度,向我們射來了一道悠遠的茶葉文明之光。
西漢時,茶沿絲綢之路至西域各國。阿拉伯商人在中國購買絲綢的同時,也帶回了茶葉,并把它們運往波斯。與此同時,土耳其商人在中國邊境也開始了以物易茶——“有一葉,作三葉草狀,其葉數,其香亦高,唯其味苦,水沸,沖飲之。”這是公元9世紀時一位名叫蘇萊曼的北非商人在他寫的一本名叫《印度中國紀行》的書中,對茶的形容。
公元9世紀初,茶離開故鄉,揚帆起航,東渡扶桑。日本最澄禪師和他的弟子空海先后從中國帶去茶籽和制茶工具。從此,中國的飲茶方法和習俗開始在日本傳播開來。至宋,日本高僧榮西兩度來華,歸國時帶去茶籽和飲茶法,著漢文著作《吃茶養生記》,為后來日本茶道的產生奠定基礎。
六個世紀以后(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馬西沃所著《中國茶》和《航海與旅行記》二書,把茶介紹到了歐洲。一位名叫克羅茲的葡萄牙神父,在那個時代成為中國最早的天主教傳播者。同時,他在1560年把中國茶葉知識傳播回國,而他的同胞海員則仿佛為了印證他的知識一樣,從中國直接帶回了茶葉。
就這樣,16至17世紀始,茶先后到達了荷蘭、俄國、法國和英國。
華茶在歐洲,尤其在英國受歡迎,與一位葡萄牙公主凱瑟琳出嫁英國(1662年)密切相關——世界在出現一位飲茶皇后之后,也增添了一個以往從來不種茶葉的飲茶大國。
在此之前,英國基本上還是一個咖啡的王國,但茶葉的品質非常符合英國人據以自豪的紳士風度,故而朝野開始交相提倡。相傳1657年倫敦一家極有名的“嘉拉惠”咖啡店,已經在廣告上赫然寫道:
可治百病的特效藥——茶,
是頭痛、結石、水腫、瞌睡的萬靈丹!
飲茶皇后以為酒傷身體,不如茶好,從此以茶代酒,成為英國宮廷中的禮儀。達官貴人爭相效仿,茶遂成為豪門世家的高貴飲料。貴夫人在家中設精致茶室,論茶媲美,一時成為時髦。1669年,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購得“功夫茶”,獻呈皇后,以博歡心。當年英國就停止從荷蘭進口茶葉,由東印度公司獨占專營權。
茶在英倫三島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出現。英國詩人蒲伯是這樣贊美女王喝茶的:
您,偉大的安娜,三個國家齊向您低首。
您有時和君臣商談大政,有時也在茶桌旁激勵朋友。
這個島國的人民,成了世界上飲茶的冠軍。上午十時半和下午四時的飲茶習俗,成了生活中雷打不動的制度。學術界的交流被稱為“茶杯和茶壺精神”,電視臺下午四時的節目謂之“飲茶時間”。蕭伯納曾調侃說:破落戶的英國紳士,一旦賣掉了最后的禮服,那錢往往還是用來飲下午茶的。
當那時鐘敲動第四響,
一切的活動皆因飲茶而中止,
……
茶葉貿易史上,英國留下了不少的篇章和逸事。比如中國的平水珠茶,向被稱為綠色珍珠。但,據創建于1706年的老牌英國茶商團寧公司印發的宣傳冊載,當時的英國人不識此茶,稱其為“gun powder green tea”,火藥綠茶,一直流傳至今。
還有一種老牌加香茶“格雷爵士茶”,說起來也有點意思。這位爵士本為20世紀初出使中國的外交大臣,從清朝一位官吏手中得到了代代相傳的花茶配方,帶回國去,交一家公司試制。該公司為了感謝他,把該茶命名為“格雷爵士茶”。此茶上市,包裝上無不注明源于中國清朝某高級官吏的字樣,以為行銷之號召。
18世紀,茶在英國國民經濟中,成了一項重大收入。19世紀的英國大臣羅斯托倫說:“國家不可缺乏的糧食、鹽或茶,如果由一國獨攬供應權,就會成為維持其統治勢力的有力砝碼。”
茶由此而直接介入了政治。公元1773年,英國議會通過了《茶葉稅法》,規定每磅茶葉征收三便士茶稅,波士頓茶葉事件——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由此引發,至今波士頓碼頭還有碑文如下:
此處以前為格林芬碼頭。1773年12月16日,有英國裝茶之船三艘停泊于此。為反抗英皇喬治之每磅三便士之苛稅,有九十余波士頓市民,攀登船上,將所有茶葉三百二十四箱,悉數投于海中,以是而成為世界聞名之波士頓抗茶會之愛國壯舉。
在歐洲,只有一個國家在飲茶方面可以與英國相提并論——西伯利亞的寒風也無法抵擋華茶對俄羅斯人的誘惑,茶馬交易使茶從蒙古進入俄國。19世紀初,俄國人從湖北羊樓洞運去茶種,成功地栽種在格魯吉亞的土地上。一位專和俄國做茶葉生意的劉姓中國人,被沙皇賜名為“茶葉劉”。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中這樣寫道:
天色轉黑,晚茶的茶炊閃閃發亮,
在桌上咝咝作響,它燙著瓷茶壺里的茶水,
薄薄的水霧在四周蕩漾……
放眼全球范圍內的華茶貿易,我們大約可知,公元10世紀前,華茶已到了亞洲諸多鄰國及西北非等地;16世紀抵達歐洲;18世紀,茶與英國移民同坐五月花船漂洋過海,直抵美洲。而茶的另一支大軍,則于17世紀南下,定居于被海洋擁抱著的南洋諸國。
華茶既被如此青睞,公元1840年的中國鴉片戰爭之前,清政府便派官商十三人至廣州,行辦茶事,人稱十三行。從此,官僚、豪商、洋人,壟斷出口貿易,尤以茶葉為甚。生意之有利可圖,連皇帝見了也眼紅,直接插手進來,人稱皇商。
此等格局,直到鴉片戰爭之后方被打破,十三行與英商獨霸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局面從此一去不復返,洋行,變為各國實業家獨占的商行。五口通商之后,“千箱捆載百舸送,紅到漢口綠吳中”——福州、漢口、九江、寧波,成了當時中國茶葉出口最多的港口所在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再次改變中國經濟的格局。從此洋行多遷于滬上,盛時曾達四五十家,而上海的茶葉輸出,竟占全國總輸出之一半以上了。
洋行壟斷中國對外茶葉貿易近百年,至20世紀上半葉,中國茶業已落得奄奄一息之地步。此間,中華茶界有識之士自不甘于消沉,種種努力,艱苦卓絕,在漫長跋涉之中,企圖恢復昔日祖先之榮光。其中最杰出者,當屬吳覺農先生。
1897年出生于中國浙江上虞縣豐惠鎮的吳覺農先生,真正從實踐中走上為振興華茶而奮斗的道路,乃是自20世紀30年代初,應中國著名農學家、農業教育家、當時的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鄒秉文先生之約,籌辦茶業出口檢驗開始的,爾后,吳覺農又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門、浙江三界等地建立茶葉改良場,中國現代茶業,自此粗現雛形。
與此同時,吳覺農先生四處奔走,出入茶區,出國考察,撰寫大量調查報告,揭示茶葉貿易中洋行洋莊茶棧之壟斷操縱,譴責通事、茶號、水客等的重重剝削,描述中國茶農之悲慘處境,介紹國外茶界之先進技術和經驗,實踐中國茶業進步之種種方案——先生于不可為之時而為之,嘔心瀝血,慘淡經營,長夜彌天,大聲疾呼之聲,似乎終有回音——
1936年間,皖贛兩省議定并成立了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統籌運銷兩省之祁門與寧州紅茶,時稱“茶業統制”。
此舉霎時間翻了中國茶業行近百年的天。上海洋莊茶棧同業行會,聽到彼聲,不啻晴天霹靂,都一個個地突然“鄭重將來,顧慮意外”起來,一份《痛切宣言》公開發表,被眾多中國茶人看作為實踐先生“打破中間剝削,謀茶農之真正利益,復興茶業”之理想的大行動。最終,此次風波以政府妥協讓步而告終。
1936年,吳覺農先生在《中國農村》雜志二卷六期上,以施克剛為筆名,撰《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劇》一文,表達他對這次半途而止的茶業革命的認識,說:
在現社會中,大資本驅除小資本,也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此次統制糾紛的背景,實在不過是這樣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而已。……茶業統制的結果是茶業受了帝國主義金融資本與茶棧的統制,貧困的茶農因之而被統制于死地。反帝反封建的戲劇,本應當轟轟烈烈演下去,然而因為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農——被壓在舞臺下,因此演不到半幕便匆匆收場了。
作為半幕戲劇的皖贛茶業統制,卻成為吳覺農先生后來的正劇的序幕。當此時,實業部開始試圖采納吳先生的建議,成立較大規模的茶葉公司。又不知幾多周折,1937年6月1日,由實業部和皖、贛、浙、閩、湘、鄂六個茶區省政府集資,少數私人資本參加的中國茶葉公司,于上海北京路墾業大樓正式成立,吳覺農先生被聘為總技師。
僅僅三十七天之后,遙遠的北方,盧溝橋邊,日本軍隊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面入侵。剛剛開始事業的中茶公司,被迫于上海輾轉遷徙,由武漢而終往陪都重慶。向被稱為“不夜侯”的中華茶葉,這向往溫暖與光明的綠色和平之舟,在數百年劫難之后,陷入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兇險的驚濤駭浪之中。
真個是:
出我幽谷,上我喬木,茶兮葉兮,鳳凰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