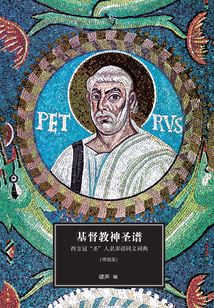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11章 主要參考書目
- 第10章 基督教神圣譜——西方冠“圣”人名多語同義詞典(6)
- 第9章 基督教神圣譜——西方冠“圣”人名多語同義詞典(5)
- 第8章 基督教神圣譜——西方冠“圣”人名多語同義詞典(4)
- 第7章 基督教神圣譜——西方冠“圣”人名多語同義詞典(3)
- 第6章 基督教神圣譜——西方冠“圣”人名多語同義詞典(2)
第1章 前言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信息化時代,各國、各民族之間在時空上的距離越來越近,彼此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我們生活在其中,必須更好地了解別人,了解別人的文化。
可是,在我們認識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始終存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給我們的介紹研究工作造成了驚人的混亂。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了解西方恐怕只能是一句空話。
眾所周知,由于歷史的原因,西方文明是以基督教文化為主要支柱的。正是因為基督教在西方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作用,西方文化中便有許多稱“圣”的人物,亦即基督教的神圣和圣徒。他們出現在歷史、政治、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既是杜撰的故事或真實事件的主角,又是各類思想和各種品德的象征,從而成為西方文化的重要載體。要了解西方文化,就不可能越過這一族群。
然而,基督教賦予西方各國文化的這種同一性,卻被掩蓋在源流演變中出現的不同民族語言的差異性下面。也就是說,同一冠“圣”人物的名字,會在不同語言中演化出不同字形和不同發音。這便是冠“圣”人物的“人同名異”現象,亦即上面所說給我們制造了驚人混亂的意想不到的問題。這個問題,自從我們與西方文化接觸以來,就開始困擾著我們;而且,隨著交流的日益擴大和深入,已經成為阻礙我們溝通的一道主要屏障。我們先來看幾個實際發生的事例。
第一例。《中國旅游》雜志在其2000年的五、六期合刊上,集中介紹了西班牙,其中自然以相當的篇幅談到舉世聞名的“圣雅各朝圣之路”。雅各者,是基督的第三門徒,據稱傳教到今天所稱的西班牙。9世紀,其墓在孔波斯特拉被“發現”,于是在墓上建教堂,并一再改建擴建,稱圣雅各大教堂。至11世紀,到孔波斯特拉圣雅各大教堂朝圣,已形成世界范圍的熱潮。圣雅各因此也成為西班牙舉國上下的主保圣人。通常,朝圣者走陸路,通過穿行法蘭西的四條路線,到西班牙境內匯成一條,直抵孔波斯特拉。這便是“圣雅各朝圣之路”,又稱“法蘭西之路”。這條路,由于近千年的建設和交流,實際上濃縮了西班牙的歷史和宗教,凝聚著西班牙民族文化藝術的精髓,堪稱一篇宏偉史詩、一幅歷史畫卷。將圣雅各之路與我國的絲綢之路相提并論,是再恰當不過的。
問題出在雅各的譯名上。雅各的中譯名早已約定俗成,是更改不得的。《中國旅游》雜志用的文章顯然是從英文譯出,譯者將正文中的Saint James譯成“圣詹姆斯”,而將題目《圣雅各朝圣之路》中的西班牙文Santiago譯為“圣地亞哥”。這樣,文章與標題不但自相矛盾,而且全然與雅各無關,完全封閉了本應該傳遞出來的重要信息,非但沒有起到介紹知識、交流文化的作用,反倒制造了混亂,把讀者拋到重重迷霧之中。試想,如果外國譯者將我們的絲綢之路也如法炮制,譯得面目全非,不也是一場荒唐的鬧劇么?
究其原因,在兩方面。一是譯者缺乏必需的知識,至少也是作風馬虎。嚴肅的、有經驗的譯者,在遇到人名或冠“圣”的人名時,必會到專名詞典或大百科之類的工具書查閱,而不會簡單地進行音譯了事,不會像我們的這位譯者那樣。二是畢竟我們缺少一部冠“圣”人名的多語同義工具書,但凡遇到類似情況,不但極費周折,甚至無處查尋。這里,繼續以雅各為例。正因為有“人同名異”現象,雅各在不同語言中有不同的字形和發音:英文James,法文Jacques,西文Santiago或iago或Jaime或Diego,德文Jacob或Jakobus,意文Giacomo或Jacopo。倘若不是冠“圣”的人物,則分別按有關語言發音規則譯作詹姆斯、雅克、圣地亞哥、亞戈、海梅、迭戈、雅各布、雅各布斯、賈科莫或雅各布,都并無錯誤。但是,雅各之前冠“圣”,只能是同一個人,只能統一譯成雅各—實際上《圣經》中有三位雅各,即《舊約》中以撒和利百加之子、以掃之弟,《新約》中的耶穌門徒西庇太之子即這里所提這一位(又稱長雅各)和耶穌另一門徒亞勒腓之子(又稱幼雅各),三人同名,均譯雅各。由于沒有這樣一部專門工具書,而且我們的譯者往往只從自己所使用的那種語言去音譯,于是就難免會出現同一個人在中譯名上莫名其妙地變成許多人的情形。
第二例。中譯本《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有“圣米歇爾山”的條目。這是法國諾曼底近海一座舊名為坦布山的小島,退潮時與陸地相連,漲時孤立海中,山頂有修道院,風光旖旎,現為旅游勝地。該島的法文名稱le Mont-Saint-Michel,其實不能譯作“圣米歇爾山”,而應譯作“圣米迦勒山”,因為其中的冠“圣”人物,原本是基督教神圣譜上的天使長米迦勒(此譯法早已約定俗成,見于《圣經》中譯本及其它許多典籍)。《新約·啟示錄》敘述了他“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并將大龍即魔鬼撒但及其使者從天上打落的功績。后來,又有傳說,稱這位天國衛士的首領,在坦布山再次戰勝作惡的撒但,并托夢給當地的主教,令他在山上建教堂供奉自己,以便護佑這方信徒。據稱,這便是自8世紀起將坦布山改名圣米迦勒山的緣由。再后來,傳說這位赫赫有名的天使統帥果然在英法百年戰爭中,幫助法國人抗擊強敵,以至于在法國大半國土淪喪之時,這座在敵人眼皮底下的孤島居然從未讓英軍占領。由此可見,此地的名稱源于這些歷史和傳說。中文取米迦勒的固定譯法,則事跡全顯,否則島名傳達不出應有的信息。更何況,米迦勒在不同語言中也同樣是異形異音的。一位英文譯者把Saint Michael譯作“圣邁克爾”,亦屬同類錯誤。
第三例。佛羅倫薩大教堂對面有一座十分著名的洗禮堂,意大利名稱是San Giovanni,在意大利文譯者筆下,幾乎都毫不猶疑地譯成“圣喬瓦尼”洗禮堂。殊不知,這位“喬瓦尼”一旦冠“圣”,則只能是《圣經·新約》的二位同名的“約翰”,即施洗約翰和福音約翰。前者是耶穌的表兄,曾為耶穌施洗禮;后者為耶穌的門徒,撰寫《約翰福音》和《啟示錄》。洗禮堂以施洗約翰(簡稱約翰)命名,是順理成章之事;倘若譯成“圣喬瓦尼”,則事出無因,是將文藝復興之都這一重要人類文化遺產與一個毫不相干的名字捆在一起。約翰在法文中的字形是Jean,在西班牙文中是Juan,在德文中則是Johannes或Hans。我們的法文、西文和德文譯者,也因為不明所以,往往犯下類似的錯誤,將供奉圣約翰的教堂譯成“圣讓”“圣胡安”或者“圣約翰內斯”“圣漢斯”教堂。只有英文譯者最幸運,這全靠John譯作約翰已成定規。
以上三例,僅僅指出問題的性質,而遠不能概括充斥報紙、雜志、書籍、廣播、電視、網絡等各種媒介的混亂的程度。
“異名歸一”,已刻不容緩。這是了解西方、走向世界的“基本功”之一。
為此,有十分的必要編撰這部《基督教神圣譜—西方冠“圣”人名多語同義詞典》。
這部工具書,旨在解決三個問題。
一是名。全書共收290條目,每條均以中、英、法、西、德、意、俄七種文字(少數兼收其它文字)的異名相互參照,使其它六種外語的異形統一于中文的音譯名字。
二是實。在每一條目的名下,對人物記其傳略,對事件指其出典,對少數象征作出注釋,向檢索者提供統一名稱之下的實質性信息。
三是相。鑒于同樣作為人類精神財富的西方造型藝術與西方文化中這一冠“圣”人物群體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全書選入西方有關經典藝術品544件,既幫助讀者獲得他們的直觀形象,又使這些藝術品的內涵得到明白的揭示。
《基督教神圣譜—西方冠“圣”人名多語同義詞典》正是這樣一部旨在從名、實、相的立視角度,全面介紹西方冠“圣”人物基本群體的詞書,以期解決人物譯名混亂、生平事跡難查和藝術表現費解這三個長期困擾我國學術界的難題。
關于本書,還有四點說明。
第一點,中譯名遵從“名從主人”和“約定俗成”兩條原則。前者是將在不同語言中有異形異音的冠“圣”人物,只按其原籍的語言發音規則作規范的轉譯。例如,英文的Saint Lawrence、法文的Saint Laurent、德文的Hl. Laurentius或Hl. Lorenz、西文和意文的San Lorenzo、本是同一人,出生在西班牙的韋斯卡,便只按西語發音譯成“圣洛倫索”,而不在“圣”后譯勞倫斯、洛朗、勞倫丘斯或洛倫茨、洛倫佐等。又如,方濟各的同鄉女徒Chiara,既然是意大利人,便不能按英文的Clare、法文的Claire、西文的Clara、德文的Klara譯成克萊爾或克拉拉,而譯作“加辣”— “加辣”的字形雖不雅,但已有定譯(見任繼愈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宗教詞典》),為遵守“約定俗成”原則,不改。
第二點,對本書中的人物或事件,由于傳說不一,版本各異,只能略加綜合,作出大致介紹,而無法詳細考證,也不可能進一步給予科學的評說。
第三點,本書中文條目,按照基督教的神界(1—13)、《舊約》(14—69)、《新約》(70—188)和后世(189—290)四部分順序編排。其中,《舊約》《新約》的人物事件,按其出場先后排列;后世圣徒,以其英語名首字母為序。漢語(拼音)索引,則遵從中譯名拼音字母順序。
第四點,所選544幅圖片多為歷代名作,其中154幅圖由編者本人在考察中世紀西方文化藝術過程中從原作拍攝。
《基督教神圣譜—西方冠“圣”人名多語同義詞典》是初創性的嘗試,必不完備。但是,編者深信,隨著它的出現和不斷完善,我們對西方文化的研究會更踏實,更深入。
嘯聲
2003年1月1日于北京百萬莊
2011年1月14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