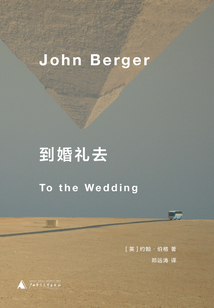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據(jù)英國Bloomsbury出版社1995年版本譯出
妙呀雪團兒
被難耐暑熱的人們含在口中
妙呀春風吹向那些
渴望起航的水手
妙不過一床被子呀
讓兩個情侶同衾相依
我喜歡不失時機地征引古老的詩句。我?guī)缀踹^耳不忘,又成天到晚地聽,只是我有時不知道這些片段怎樣搭配。這時候,我會抱著那些真切入耳的詞句或說法不放。
大約一百年前,普拉卡周邊的街區(qū)是一片沼澤,現(xiàn)在是趕集的地方,這兒的人叫我佐巴納科斯。意思是牧羊人。大山里出來的人。是一首歌讓我得名的。
每天清早去趕集前,我都會擦亮我的黑皮鞋,撣掉我的斯泰森牌[1]遮陽帽上面的灰塵。城里灰塵大,污染重,給太陽一曬更是變本加厲。我還打領(lǐng)帶,對一條藍白色反光的領(lǐng)帶偏愛有加。一個盲人永遠不應(yīng)該對外表粗枝大葉。不然的話,有些人會匆匆忙忙誤會他的。我的衣著像個珠寶商人一樣,我在集市上賣的倒是塔瑪。
塔瑪這樣的東西,盲人來賣是合適的,因為摸一摸就能分辨出這個和那個不同。塔瑪有錫做的,也有銀做的,金做的。它們?nèi)枷駚喡橐粯颖。叽缍枷裥庞每ㄒ粯哟蟆K敚╰ama)這個詞源于動詞tázo,意思是許愿。人們許下一個諾言,希望以此換來保佑,得到解救。年輕人要去服兵役,會先買一個刻印一把刀的塔瑪,這是一種祈求:愿我不曾受傷就可以退伍。
不然就是某人身上發(fā)生了一件壞事。比方說生病或飛來橫禍。一個人身處險境,愛護他的人在上帝跟前許愿:如果他們愛的人康復(fù),他們會做一件好事。假使你在世界上孑然一身,你也可以自己給自己許愿。
光顧我生意的人去祈禱前,會先買個塔瑪,用絲帶穿過它的小孔,然后把牌子懸在教堂里神像前的欄桿上。他們這么做,是希望上帝不會忘了他們的禱告。
每個塔瑪?shù)能浗饘偕隙纪褂≈粋€圖案,是處于險境的身體部位。胳膊或腿、胃或心臟,或者像我這種情況:一雙眼睛。我有過一個狗的塔瑪,但是神父看不過去,說這東西褻瀆神圣。這神父無知透了。他在雅典住了一輩子,不知道一條狗在山區(qū)可能比一只手還要重要,還要有用。他想都想不到,失去一頭騾子的慘痛也許會大過失去一條久傷不愈的腿。我給他引了福音書的話:你們看,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上帝尚且養(yǎng)活它……我對他說完,他扯扯自己的胡子,像躲避魔鬼一樣背過身去。
男人女人需要什么,布祖基琴手比神父清楚。
我失明以前干什么,我不打算對你說。如果你猜三次,保準三次都錯。
故事從上個復(fù)活節(jié)開始。就在過節(jié)的禮拜天。早晨九、十點鐘,空氣里飄著咖啡香。出太陽的日子,咖啡香飄得更遠。有個男人問我有沒有可以送給女兒的禮物。他講著話不成句的英語。
是個寶寶?我問。
她是成年女子了。
她哪兒受苦?
哪兒都受苦,他說。
心臟的,成嗎?我終于提議,一邊從托盤里摸索著找到一個塔瑪,遞給他。
這是錫做的?憑他的口音,我猜他是法國人或意大利人。年紀估計和我差不多,也許大一點。
我用法語說,我還有一個金子的,如果你想要的話。
她康復(fù)不了了,他回答。
最重要的是你許的愿,有時候也別無他法。
我是個鐵道工,不是個巫師,他說。給我最便宜的、錫做的吧。
我聽見他從衣兜里掏錢包的窸窸窣窣。他穿的是皮褲皮夾克。
錫和金子在上帝那里沒有分別,是吧?
你騎摩托車來?
帶我女兒來玩四天。昨天我們開去看了波塞冬神殿。
蘇尼翁那一座?
你去看過?對不起,我是說你去過?
我用一只手指敲了敲我的黑眼鏡,說道:在這以前,我看過那座神殿。
錫做的心臟要多少錢?
他跟希臘人不同,沒有砍價就付了款。
你女兒叫什么名字?
妮農(nóng)。
妮農(nóng)?
N-I-N-O-N。他拼出每個字母。
我會想著她的,我一邊歸整鈔票一邊說。就在此時,我忽然聽見一個嗓音。他女兒定是去過了集市里別的攤位,現(xiàn)在回到他身邊來了。
我的新涼鞋——看!手工做的。誰能猜著我是剛買的呢。沒準穿了好些年。也許我是為了我那場沒有舉行的婚禮買的。
指頭中間的絆帶不硌腳?鐵道工問。
吉諾會喜歡的,女兒說。他對涼鞋有品味。
這鞋子系住腳踝的樣子很好看。
走到碎玻璃上,這鞋子可以護腳,女兒說。
過來一下。嗯,這皮子又好又軟。
爸,你記得嗎,我小時候洗完澡你幫我擦干身子,我坐到你膝頭的浴巾上,你會跟我說,每個小腳指頭都是一只喜鵲,偷這偷那,偷完就飛走了……
她說話的節(jié)奏明快清楚。沒有懶音,沒有拖腔。
嗓音、聲響、氣味,現(xiàn)在都給我的眼睛帶來禮物。我聆聽,我吸氣,然后就像在夢中一樣觀看。聽著她的嗓音,我看見一片片瓜果工整地擺在盤子上,我也知道,假使我再次聽見妮農(nóng)的嗓音,會立即辨認出來。
幾個禮拜過去了。人群里某個人說法語、我又賣出一個心臟塔瑪、一輛摩托車駛離交通燈前發(fā)出呼嘯——這些事情,時不時就會讓我想起那鐵道工和他的女兒妮農(nóng)。他倆只是路過,沒有停留。然后,六月初的一天晚上,有點什么變了。
每天晚上,我從普拉卡走路回家。失明有個效應(yīng),你會產(chǎn)生一種玄妙的時間感。手表固然無用——雖然我有時也賣手表——我卻也知道當下是什么時間,準確到分鐘。回家的路上,我照例會從十個人身邊經(jīng)過,和每個人閑聊幾句。對他們,我是提醒時辰的人。一年以來,科斯塔斯是這十人之中的一個——不過我和他說來話長,改日再敘了。
在我房間的書架上,我放滿了塔瑪、我的很多雙鞋、一套帶托盤的玻璃壺和玻璃杯、我的大理石殘件、幾塊珊瑚、幾個海螺殼、放在最上層的巴拉瑪琴——很少會取下來——一罐開心果、許多鑲了框的照片——真的有——以及我的盆栽:木槿花、海棠花、日影蘭、玫瑰。每天晚上我都會摸摸它們,查看它們長得如何,最近又開了幾朵。
喝上一杯,沖了澡,我喜歡搭火車去比雷埃夫斯。我沿著碼頭走,時不時打聽打聽,哪些大船靠岸了,又有哪些會在當晚起航,然后就去找我的朋友雅尼消遣。他現(xiàn)在開著一家小酒館。
景象是無時不在的。所以眼睛會疲倦。嗓音不同,它就像一切和詞語有關(guān)的事物那樣來自遠方。我站在雅尼的酒館里,聽老人聊天。
雅尼跟我父親年紀相仿。他從前是個藍貝蒂卡[2]音樂家、布祖基琴手,戰(zhàn)后挺受人歡迎,跟偉大的馬爾科斯·瓦姆瓦卡里斯[3]一同演奏過。如今只有老朋友出面邀請,他才會抱起他的六弦布祖基琴了。他們大多數(shù)晚上都請他彈奏,他也還都記得。他坐在一張?zhí)倬幾鴫|的椅子上彈琴,左手無名指和小指中間夾一支煙,撫動品絲。有時他彈琴,我也會隨興地跳起舞來。
當你隨著一首藍貝蒂卡歌謠起舞,你會踏進音樂的圈中,那節(jié)奏就像一個鐵條圍住的圓形籠子,你跳著,就在那個曾經(jīng)活過歌曲中的人生的男人或女人面前。音樂揮灑出他們的哀愁,你的舞蹈是一種致敬。
將死神趕出院子吧,
好讓我不必見他。
墻上的鐘呀
領(lǐng)起了葬禮的挽歌。
夜復(fù)一夜地聽藍貝蒂卡,就像在身體上刺青。
*
在那個六月之夜,兩杯茴香酒下肚,雅尼對我說,朋友啊,你為什么不跟他一塊兒住?
他眼睛不盲,我說。
你又來了,他說。
我離開酒館,買了一點烤串在街角吃。之后,我照舊請雅尼的孫兒瓦西利替我搬來一張椅子,把自己安頓在窄巷深處的人行道上,那里對著一些樹木,是一波波喧鬧中獨享幽靜的所在。我背靠朝西的空墻,感覺到它儲備了一整天的溫暖。
遠遠地,我聽見雅尼彈著一曲藍貝蒂卡,他知道那是我偏愛的:
你的眼睛喲,小妹妹,
敲開了我的心扉。
不知為什么,我沒有回酒館去。我坐在藤編坐墊的椅子上,背靠著墻,手杖倚在雙腿間,等待著,就像準備慢慢站起來跳舞的人一樣。那首藍貝蒂卡彈完了,大概始終沒有人起舞。
我坐著,聽見起重機在卸貨,它們要卸一整夜的貨。然后有個寂靜無聲的嗓音說了起來,我認出是那個鐵道工的嗓音。
費德里科,你怎么樣呀?他在說。聽到你的聲音真好,費德里科。對,明天我大清早出發(fā),就是幾個鐘頭以后,禮拜五咱們就在一起了。別忘了,費德里科,香檳都歸我付錢,都歸我,所以訂它個三四箱啊!你看著辦。我只有妮農(nóng)這一個女兒。她馬上要出嫁了。對,一定。
鐵道工對著電話用意大利語聊天,他在有三個房間的自家屋子里,在廚房,屋子坐落在阿爾卑斯山麓的法國市鎮(zhèn)莫達訥。他是二級信號工,信箱上的名字是尚·菲列羅。父母是移民,來自意大利產(chǎn)稻米的小城韋爾切利。
這廚房不大,臨街的前門后還有一輛碩大的摩托車停在停放架上,因此更顯窄小。平底鍋擱在瓦斯爐上的樣子表示掌廚的是個男人。他這地方,正如我在雅典的房間一樣,沒有絲毫女性的印記。這是個男人獨立于女人生活的地方,人和地方都習以為常。
鐵道工掛了電話,走到攤開一張地圖的餐桌前,拿起一份單子,上面寫有道路的編碼和城鎮(zhèn)的名字:皮內(nèi)羅洛、隆布里亞斯科、都靈、蒙費拉托堡、帕維亞、馬焦雷堡、博爾戈福爾泰、費拉拉。他用透明膠帶把單子貼到摩托車的表盤旁邊。他檢查了剎車油、冷卻液、燃油、輪胎壓。他用左手食指掂了掂鏈條的重量,測試它夠不夠緊。他開了點火開關(guān)。表盤亮起紅燈。他驗看了兩個前燈。他的動作是仔細的、有條理的,尤其該說是輕柔的,仿佛車子是個活物。
二十六年前,尚和妻子妮戈爾一起住在這個有三個房間的屋子里。有一天妮戈爾離開了他。她說自己受夠了他夜間工作,他一有空閑就給法國總工會做組織策劃,他在床上讀宣傳冊——她想要生活。然后她砰上前門,再也沒回到莫達訥來。他們倆沒有孩子。
同一天夜里返回雅典的火車上,我聽見了另一個城市播放的鋼琴音樂。
一道寬寬的樓梯,沒有地毯也沒有墻紙,只有一道光滑的木扶手。音樂從五樓的一個套間傳來。這棟樓的電梯很少有開工的時候。不會是唱盤也不會是CD,只是一盒普通的磁帶。上面的聲響全都蒙著一層薄薄的灰塵。一支鋼琴夜曲。
套間里有個女人坐在一張挺直的椅子上,對著一個通向陽臺的高高的窗戶。她剛掀開了窗簾,久久地俯視著夜色中整個城市的屋頂。她的頭發(fā)朝后梳成發(fā)髻,雙眼疲倦。她埋頭工作了一天,繪制一個地下停車場的工程詳圖。她嘆了口氣,揉了揉疼痛的左手手指。她的名字是澤德娜。
二十五年前她在布拉格念書。1968年8月20日夜間紅軍的坦克開進城中,她一度上前和那些蘇聯(lián)士兵講理。次年,坦克之夜的一周年紀念日那天,她加入了瓦茨拉夫廣場的群眾隊伍。一千人被警察拘押載走,五人被殺。數(shù)月后幾個親密朋友被逮捕了,到1969年圣誕節(jié)那天,澤德娜成功越過邊境去到維也納,又轉(zhuǎn)程去到巴黎。
她跟尚·菲列羅相遇在格勒諾布爾的聲援捷克難民的一場晚會上。他走進來,澤德娜一眼就注意到他,因為他長得像她在一部關(guān)于鐵路工人的捷克影片里看過的某個演員。稍后她發(fā)現(xiàn)尚真的在鐵道工作,馬上覺得他和自己注定會變成朋友。他問澤德娜怎么用捷克語說:波希米亞是我的國家。她聽了笑起來。他們成了情人。
鐵道工每次在莫達訥有兩天休假的時候,都會開摩托車到格勒諾布爾探望澤德娜。兩人騎著他的摩托一起出游。尚帶她去到她從未見過的地中海邊。薩爾瓦多·阿連德[4]贏了智利總統(tǒng)大選,當時他們談過要遷居圣地亞哥。
然后,十一月時,澤德娜透露她懷孕了。尚說服澤德娜留住他們的孩子。他說,我會照顧你們倆的。來我莫達訥的家一塊兒生活吧,有三個房間,一個是廚房,一個臥室給我們,另一個臥室給小男孩或小女孩。我想我們的寶寶會是個女孩,澤德娜忽然心醉地說。
在雅典的火車站月臺上有人說可以陪我行走。我假裝自己既瞎又聾。
他們的女兒妮農(nóng)六歲時,一天晚上,澤德娜聽見電臺上說,布拉格有一百個捷克公民聯(lián)名簽署請愿書,要求人權(quán)和公民權(quán)利。她問自己,這可會是個轉(zhuǎn)折點?她出國已有八年。她需要了解多一些。
你去吧,尚坐在廚房的餐桌上說,妮農(nóng)和我沒事兒的。你慢慢來,也許還能弄到延期簽證。回來過圣誕節(jié)吧,咱們一家坐雪橇去莫里耶訥!噢,不要傷感,澤德娜。這是你的本分,同志,你會高高興興回來的。我們會很好。
澤德娜依然在五樓的房間里聽那支夜曲,她掩上窗簾,走到藍白瓷磚的壁爐旁的貼墻鏡子前。她望著鏡子出神。
十七年前那天晚上,她對尚問及簽證的時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們是否像著魔的人、瘋狂的人那樣,同意他們?nèi)齻€不再擁有一個共同的家?
我們究竟如何抉擇?
鏡子的底角嵌著一張汽車票:布拉迪斯拉發(fā)[5]——威尼斯。她用手指疼痛的左手撫弄票子。
一張?zhí)鹤訌哪ν熊嚨陌白吓麙煜聛怼L鹤由嫌腥凰呢垺?
尚·菲列羅一身黑皮革、皮靴,走下樓梯,走進廚房。他打開后門底部的一扇小活門,拍拍手,貓兒便跳下車子,溜到花園里去了。活門是他十五年前做的,當時妮農(nóng)得了一只她喚作偉偉的小狗。
然后我聽見了那個令我想起瓜果切片的嗓音。是同一個嗓音,但這時它吻合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她說:我走過我們的火車站,偉偉在我的外套下面。每二十四小時,我們的站有六十一班火車通過。任何送往意大利的貨物都經(jīng)過我們的隧道。我把他抱在外套下面,他的下巴挨著我最頂上那一粒紐扣,他的耳朵蹭著我的翻領(lǐng)。如果不算蝸牛呀、蚯蚓呀、毛毛蟲、蝌蚪、花大姐和小龍蝦的話,他是我的第一個寵物。我叫他偉偉,是因為他才那么點兒大。
尚打開臨街的門,跨上摩托車,用腳蹬了蹬。后輪一抬上門階,車子就自動滑出路面。他舉頭望了望天空。沒有星星。黑暗,一種有能見度的黑暗。
我走過火車站,偉偉從我的外套里探頭探腦,每個人都停下來,指指點點,帶著笑容。有認識我們的人,也有不認識的人。他是個新生命。本堂神父先生問我他的名字,好像他打算安排一場洗禮似的!偉偉!我跟他說。
鐵道工去鎖上家門。他在門上轉(zhuǎn)鑰匙的動作,已經(jīng)像是擔保他下個禮拜就會回家。他手工的操作都有一種給人信心的風度。他屬于那種信賴手勢多過言語的人。他套緊手套,發(fā)動引擎,掃視燃油表,掛一擋,釋放離合器,便滑行而去。
火車站旁的交通燈亮著紅燈。尚·菲列羅等著它變換。沒有別的車。他可以輕易溜過去,毫無風險。但是他一輩子是個信號工,他要等。
偉偉七歲的時候,一輛貨車撞死了他。我接他回來那天,他的下巴歇在我的第一顆紐扣上,我把他抱在我的外套下面一路回家一路說:偉偉,我的小偉偉,從那一天起他就是個謎。
交通燈轉(zhuǎn)為綠色,騎手與機車發(fā)動之際,尚讓穿靴的右腳拖曳在后,同時用左腳腳趾掛二擋,到達電話亭時又加到三擋。
我是昨天看見它的,這條裙子掛在離貿(mào)易酒店很近的一個櫥窗里,裙子上有我的名字NINON!它是通身黑色的中國絲綢,點綴著白花。長度也合適,到膝蓋以上三個指頭的地方。領(lǐng)子是連幅剪裁的V形長翻領(lǐng),不是縫上去的。紐扣一路扣到底。裙子迎著光略有點通透,但不至于招搖。絲綢一向清涼。如果我晃動裙擺,大腿碰到裙子,就會像舔著冰激凌。我要找到一條銀腰帶,一條銀光閃閃的闊腰帶搭配它。
摩托車亮著前燈蜿蜒曲折地開上山去。車子時不時會消失在懸崖和巖石后面,一路不斷爬坡,逐漸變小。現(xiàn)在它的燈光忽明忽暗,像茫茫石壁前一支祈愿燭的火焰。
對車手來說不是這樣的。他是在黑暗中打洞,像鼴鼠鉆過土地,他的光束穿行隧道,隧道在扭擺,因為公路要避開大石也要上升,常常拐彎。當他回頭一瞥——他剛這樣做了一次——后面除了他的尾燈和茫茫黑暗,也一無所有。他的雙膝緊抵著油箱。每當騎手與機車駛進拐角,拐角都承受他們,托舉他們。他們徐徐進入,快速離開。進入之際,他們盡可能延宕,等待拐角把橫坡送過來,然后他們便疾馳而去。
他們攀山越嶺,一路越來越荒涼。黑暗之中看不見那荒涼,但是信號工從空氣和聲響中能夠感覺出來。他再次掀開頭盔的擋風鏡。空氣又薄又寒又濕。巖石把他的引擎噪音拋了回來,粗嘎刺耳。
眼睛第一年失明,最壞而一再出現(xiàn)的瞬間是我早晨醒來那一刻。睡與醒的邊界上昏暗無光,令我經(jīng)常想發(fā)出尖叫。我慢慢才習慣這樣的情狀。現(xiàn)在我一醒過來,首先就要摸到一點什么東西:我自己的身體、床單、床頭板上木雕的樹葉。
第二天,我在自己的房間醒來時,摸了摸我放衣服的椅子,又一次聽見妮農(nóng)的嗓音,很生動,好像她剛剛沿著一架梯子從街道攀了上來,就坐在窗臺上。不再是孩子了,卻仍然不算是女人。
今天——人生第一次坐飛機。我喜歡身在云端。無處落足之地,能讓我感覺到上帝無處不在。爸爸開摩托車送我去了里昂的機場。第一程越過阿爾卑斯山,飛到維也納。第二程飛到布拉迪斯拉發(fā)。以前這個城對于我只是個郵戳,或是媽媽地址的一部分,現(xiàn)在我總算親身來到這里了。多瑙河很美,沿岸的房子也很美。媽媽來接飛機。她比我心目中的樣子漂亮些。我都忘了她的嗓音有多美。保準很多男人都愛上她的聲線。她戴著她的婚戒。那個五樓的公寓套間有高高的天花板、高高的窗、瘦腳伶仃的家具。一個適宜長談的套間。所有的抽屜都裝滿文件。我看傻了眼!我回自己的房間得出門走到樓梯口,用鑰匙打開另一扇前門。我想,這個房間以前是屬于另一套公寓的。媽媽提到事情“跟可恥的告密者有關(guān)”,我不很明白她的意思。我喜歡我的房間。窗外有棵大樹。什么樹?媽媽用她美妙的聲線說,這你應(yīng)該認識,是金合歡樹。最美妙的是,這兒有臺機器可以播我的磁帶。
三天一字沒寫。我一定是太快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