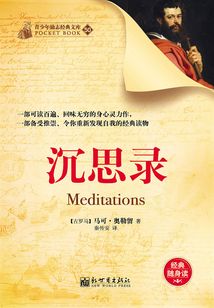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皇帝哲學(xué)家(代序)
1.關(guān)于《沉思錄》這本書
去世前6年,馬可·奧勒留端坐在他的營帳里,寫下了他對人類生活和命運(yùn)的思考。他的《沉思錄》是否打算發(fā)表,我們不得而知;多半是這樣吧,因?yàn)椋幢闶鞘ネ揭膊幻庥刑摌s之心,最偉大的實(shí)干家有時候也難免心血來潮,想寫本書什么的。奧勒留算不上寫作的行家里手;他在弗朗托(Fronto)門下所接受的拉丁文訓(xùn)練,如今已泰半荒廢,因此他用希臘文寫作;此外,這些“金子般的思想”,都是在旅行、打仗、叛亂和許許多多的磨難中寫下的;我們應(yīng)當(dāng)原諒它們的支離破碎和毫無章法,常常還有重復(fù),有時甚至是枯燥乏味。這本書之所以寶貴,完全是因?yàn)樗膬?nèi)容——它的溫柔敦厚,它的坦誠率真,以及它在有意無意中透露出來的一種介于異教與基督教之間、古代與中世紀(jì)之間的靈魂。
像他那個時代的大多數(shù)思想家一樣,奧勒留也并不認(rèn)為哲學(xué)是對無限時空的思辨性描述,而把它看作是一所培養(yǎng)美德的學(xué)校和一種生活方式。他很少操心信神的問題;有時他言談之間像個不可知論者,承認(rèn)自己一無所知;但承認(rèn)之后,他又以一種簡單質(zhì)樸的虔誠接受傳統(tǒng)的信仰。他自問:“生活在一個沒有神明或沒有神意的世界,對我來說又有什么好處呢?”他講到神的時候,一會兒用單數(shù),一會兒用復(fù)數(shù),全然不在乎神的來源。他參加公共祈禱和對古老神祗的獻(xiàn)祭,但就其個人思想而言,他是個泛神論者,宇宙的秩序和神的智慧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對人與世界的互相依存,有一種印度人的觀念。他驚奇于一個小小的精子竟會長成小孩,從少許的食物中竟產(chǎn)生出了器官、力量、心智和抱負(fù)等等神奇構(gòu)造。他相信,如果我們能夠理解,我們就會在宇宙中發(fā)現(xiàn)像人身上一樣的秩序和創(chuàng)造力。“一切事物都緊密相聯(lián),這種聯(lián)結(jié)是神圣的……只有一個由萬物組成的宇宙,也只有一個存在于萬物之中的神明,只有一種本質(zhì),一部法律,一個一切智慧動物所共有的理性,一個真理……倘若宇宙中沒有秩序,你身上怎么可能存在秩序呢?”
他承認(rèn),很難把邪惡、苦難以及表面上的無妄之災(zāi)跟善良的神意協(xié)調(diào)起來;但除非我們審視整體,否則我們就不能判斷任何元素或事件在萬物格局中的位置;誰能自詡有這樣的整體觀呢?因此,判斷整個世界對我們來說是傲慢和荒謬的;智慧在于承認(rèn)我們的局限,在于力圖成為宇宙秩序的和諧部分,在于試圖感知世界實(shí)體背后的精神,并欣然與之合作。一個人只要得出了這樣一種觀點(diǎn):“凡是發(fā)生的事情都是公正地發(fā)生的”——亦即自然的過程;對他來說,任何符合自然之道的事情都不可能是惡;一切自然的事物對理解的人來說都是美的。一切事物都取決于宇宙理性——整體的內(nèi)在邏輯;每一個部分都必須欣然接受其謙卑的角色和命運(yùn)。“平靜就是自愿接受整體本性分配予你的東西。”
宇宙啊,凡是與你和諧的,必與我和諧!凡是對你恰合時宜的,對我來說也正好不早不晚!自然啊,你的季節(jié)所帶來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果實(shí)!一切從你那里而來、存在于你當(dāng)中的事物,都將回到你那里去。
作為健全人生的一個工具,知識是唯一有價值的東西。“那么,在人生的旅途上能指導(dǎo)我們的是什么呢?只有一樣?xùn)|西,那便是哲學(xué)。”——不是作為邏輯或?qū)W問,而是作為一種堅持不懈的道德訓(xùn)練。“要挺然直立,要么就被人扶直。”神給了每個人一個引領(lǐng)方向的“守護(hù)神”,或內(nèi)在的精神——他的理性。美德是理性的生命。
理性靈魂有這樣一些特性……它走遍整個宇宙,并環(huán)繞著宇宙的太空,追蹤宇宙的計劃,伸展到無窮的時間里去,領(lǐng)悟萬物的循環(huán)再生,審視它,并認(rèn)識到,我們的子孫后代不會看到什么新鮮事物,正如我們的祖輩之所見并不比我們見到的更多。所以,一個40歲的人,如果他還有點(diǎn)常識的話,由于這種同一性,他也就看到了已有的和將有的一切。
奧勒留認(rèn)為,他自己預(yù)設(shè)的前提迫使他走向了清教主義。“享樂既不是有用之物,也不是善。”他鄙棄肉體以及肉體的一切工作,有時候,說起話來有點(diǎn)像在西貝德修行的安東尼:
不要忘記:一切肉骨凡胎,其有生之年如何短暫,其生命如何渺小——昨天還是一團(tuán)小小的黏液,明天就成為一具木乃伊,或一堆死灰……把這肉體從里到外好好審視一遍,看看它究竟是個什么樣子。
心靈必須是一座堡壘,擺脫了肉欲、激情、憤怒和仇恨。它必須專注于自己的工作,以致幾乎注意不到命運(yùn)的不幸或敵人的陰謀。“每個人的價值與他感興趣之事物的價值恰好相當(dāng)。”他很不情愿地承認(rèn),這世界上確實(shí)有壞人。對待壞人的方式就是要記住,他們也是人,是他們自身缺點(diǎn)的無助的受害人,而這些缺點(diǎn)由他們所處的環(huán)境所決定。“如果他做了錯事,受害的是他自己。”你的責(zé)任是原諒他。如果壞人的存在讓你感到悲哀,那么就想想你遇到過的眾多好人,許多混合在不完美品質(zhì)中的美德。好人也好,壞人也罷,人人都是兄弟,都是同一個神的親人;就連最丑惡的野蠻人,也是我們大家所屬于的那個父母之邦的公民。“作為奧勒留,我的城市和國家是羅馬;作為一個人,我的家國是整個世界。”這難道是一種行不通的哲學(xué)?正相反,沒有什么東西像好脾氣那么不可戰(zhàn)勝,只要它是真誠的。一個真正的好人不受災(zāi)禍的影響,因?yàn)椴还茉鯓拥臑?zāi)禍降臨在他的身上,留下的依然是他自己的靈魂。
發(fā)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還會妨礙你成為一個公正、高尚、純真、審慎、直率、謙遜、自由的人嗎?……他們殺戮我們,他們肢解我們,他們用咒語傷害我們!這如何能阻止你的心靈依然純潔、穩(wěn)健、清醒和公正呢?試想,一個人站在清澈甘甜的泉水旁,對它厲聲責(zé)罵;而它依然會汩汩地冒出有益健康的清水。丟進(jìn)泥巴甚或是穢物,它很快就會把它們沖走,潔身自凈,全無污染。……當(dāng)任何事情導(dǎo)致你覺得自己受到傷害的時候,別忘了堅守這樣一句格言:這并非不幸,泰然承受即是幸運(yùn)。……你要知道,一個人若想過一種平靜而莊嚴(yán)的生活,他需要掌握的東西多么少;他只要恪守這些規(guī)誡,神明也不會對他有更多的要求。
然而,奧勒留的一生過得并不平靜;在撰寫本書第五卷的時候,他不得不殺戮日耳曼人,到最后臨終之時,也沒有從繼承皇位的兒子那里得到安慰,無望得到死后的快樂。靈魂和肉體同樣都回歸了它們最初的元素。
正如地球上這些軀體在持續(xù)一段時間之后便會分解改變,化為烏有,為其他死去的軀體騰出空間,靈魂也是如此,當(dāng)它們在持續(xù)一段時間后被轉(zhuǎn)變?yōu)榭諝庵畷r,也經(jīng)受了改變、擴(kuò)散,化為火焰,被重新帶回到宇宙整體的創(chuàng)造理性中,給后來居住其中的靈魂騰出了空間。……你是作為宇宙整體的組成部分而存在。你將消失于那使你得以產(chǎn)生的東西之中,……那么,就依照自然之道度過這片刻的光陰吧,高高興興地走向旅程的終點(diǎn),就像一顆熟透的橄欖悄然落地,贊美那承載它的蒼茫大地,感激那養(yǎng)育它的蔥翠綠樹。
2.關(guān)于奧勒留其人
勒南(Renan)說,安東尼(Antoninus)“要是沒有過繼馬可·奧勒留作為他的繼承人,興許就沒有人跟他競爭最好君主的名聲了。”吉本(Gibbon)說:“如果你要一個人指出,世界歷史上的哪個時期人類種族最為繁榮幸福,他會毫不猶豫地說出圖拉真登基至奧勒留去世的那段時期。他們的統(tǒng)治時期加在一起大概是歷史上唯一的這樣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一個偉大民族的幸福是政府的唯一目標(biāo)。”(譯者注:吉本原文中所說的這一時期是“從圖密善被弒到康茂德登基”,意思大致一樣,不過杜蘭特為了突出奧勒留的名字而篡改了吉本的原文。)
121年,馬可·阿尼烏斯·維魯斯(Marcus Annius Verus,譯者注:奧勒留的本名)出生于羅馬。阿尼烏斯家族在一個世紀(jì)之前從科爾多瓦附近的蘇庫波來到羅馬;在那里,似乎是他們的誠實(shí)為他們贏得了“維魯斯”(意識是“真實(shí)的”)這個姓氏。這孩子出生三個月之后,父親便去世了,他被帶到了家境富裕的祖父(當(dāng)時是執(zhí)政官)家里。哈德良(Hadrianus)是祖父家里的常客,他喜歡上了這個孩子,他在他身上看出了當(dāng)國王的天分。很少有人帶給一個年輕人這樣的幸運(yùn),或者說這樣敏銳地意識到了他的好運(yùn)。50年后,奧勒留寫道:“感謝神明,讓我有了好的祖輩,好的父母,好的姐妹,好的老師,好的伙伴和親朋——幾乎一切都好。”時間老人給了他一個可疑的妻子和一個不中用的兒子,總算公平了。他的《沉思錄》列舉了這些人所擁有的美德,以及他從他們那里所學(xué)到的品格:謙遜、忍耐、剛毅、節(jié)制、虔敬、仁慈,以及“過簡樸的生活,遠(yuǎn)離奢侈的習(xí)慣”——盡管財富從四面八方包圍著他。
從未有過一個孩子像他這樣持續(xù)不斷地接受教育。孩提時代他就去神廟參加祭司們的宗教活動;他曾承諾要記住那些古老而難懂的祈禱書中的每一個單詞;盡管哲學(xué)后來動搖了他的信仰,但從未使他懈怠古老而嚴(yán)格的宗教儀式的踐行。奧勒留喜愛游戲和運(yùn)動,甚至喜歡捕鳥和狩獵,他曾做出一些努力來鍛煉自己的身體以及心靈和品格。但童年時代的17個老師是一個很麻煩的障礙。4位文法老師,4位修辭老師,1位法學(xué)老師,以及8位哲學(xué)家,把他的靈魂在他們當(dāng)中進(jìn)行了分配。其中最有名的老師是教他修辭學(xué)的馬可·科尼利厄斯·弗朗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盡管奧勒留很愛他,把一個充滿深情的帝王弟子的全部友善都傾注給了他,還與他有過一些引人入勝的私人通信,但這個年輕人不喜歡演講術(shù),認(rèn)為那是一門無用且不誠實(shí)的技藝,他沉迷于哲學(xué)。
他感激他的老師們讓他免去了邏輯學(xué)和占星術(shù),感激斯多葛學(xué)派哲學(xué)家狄奧格內(nèi)圖斯(Diognetus)讓他擺脫了迷信,朱尼厄斯·魯斯提庫斯(Junius Rusticus)讓他熟悉了埃皮克提圖(Epictetus),喀羅尼亞的塞克斯圖(Sextus)教會了他過符合自然之道的生活。他感激他的兄弟塞維魯(Severus)讓他了解了布魯圖(Brutus)、烏提卡的加圖(Cato)、特拉塞亞(Thrasea)和赫爾維狄烏斯(Helvidius);“從他那里我學(xué)到了國家的觀念,這樣的國家有一部基于個人平等和言論自由的法律適用于所有人;學(xué)到了君主的觀念,這樣的君主把臣民的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由此,斯多葛學(xué)派的君主觀念占領(lǐng)了王座。他感謝瑪西摩(Maximus)教會了他“克己自制,目標(biāo)堅定;在病中就像在其他所有環(huán)境下一樣,都要開心愉快;要有一種把溫柔和莊重結(jié)合得恰到好處的品格;要毫無怨言地完成手頭的工作”。很顯然,當(dāng)時最重要的哲學(xué)家都是沒有宗教的祭司,而不是沒有生活的玄學(xué)家。奧勒留對待他們的教導(dǎo)是如此嚴(yán)肅認(rèn)真,以致他一度因?yàn)榻嘈卸U些毀掉了天生虛弱的體格。12歲那年,他穿上一個哲學(xué)家的粗陋斗篷,睡在只胡亂鋪了些許稻草的地板上,長時間地拒絕母親要他睡長榻的懇求。在他成為一個男人之前,他已經(jīng)是個斯多葛派哲學(xué)的信奉者。他慶幸“我保持了我的青春之花未被玷污;直到恰當(dāng)?shù)臅r候,甚至有些延遲,我才一試身手,證明我的男兒本色。……我從未接觸過本妮迪克塔……后來,當(dāng)我陷入情欲的時候,我還是治好了這樣的激情。”
有兩種影響使他沒有成為職業(yè)哲學(xué)家和圣徒。一種影響是他所擔(dān)任的一連串次要的政治職位;一個行政管理者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與一個喜歡冥想的年輕人的理想主義產(chǎn)生了沖突。另一種影響是他與安東尼·皮烏斯(Antoninus Pius)的緊密聯(lián)系。他并沒有對安東尼的長壽感到不快,而是繼續(xù)過著他簡樸的生活,專心于哲學(xué)研究和公務(wù)職責(zé),同時住在皇宮里,繼續(xù)他漫長的學(xué)徒期;他的養(yǎng)父在國家治理上的奉獻(xiàn)和誠實(shí)為他樹立了榜樣,這一榜樣是他成長中的一個強(qiáng)有力的影響。我們用來稱呼他的那個名字——奧勒留——是安東尼家族的姓氏,馬可和盧修斯(Lucius)在過繼的時候都采用了這個姓氏。盧修斯成了紅塵俗世的一個浪蕩公子,一個玩樂場上的優(yōu)雅老手。146年,當(dāng)皮烏斯想要一位同僚同他一起治理國家的時候,他只點(diǎn)到了馬可的名字,而把盧修斯留給了他的風(fēng)流帝國。安東尼去世之后,馬可成了唯一的皇帝;但他想起了哈德良的愿望,于是便立即讓盧修斯與自己共同治理國家,并把自己的女兒露西拉(Lucilla)嫁給了他。在他的統(tǒng)治時期剛開始之時,就像在這一時期結(jié)束之時一樣,這位哲學(xué)家便由于慈悲心腸而辦了錯事。統(tǒng)治的分權(quán)是一個糟糕的先例,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繼承人那里,這樣的分權(quán)將分裂和削弱帝國。
馬可請求元老院表決,尊奉皮烏斯為神,修繕皮烏斯為他妻子建造的神廟,重新供奉安東尼和他妻子福斯蒂娜(Faustina)。他對元老院謙恭有禮,并十分樂于看到他的很多哲學(xué)家朋友成為元老院的成員。整個意大利及所有羅馬行省都對他歡呼致敬,視之為柏拉圖的夢想成真:哲學(xué)家成為國王。但他從未想到嘗試柏拉圖的理想國。像安東尼一樣,奧勒留也是個保守分子,皇宮里培養(yǎng)不出激進(jìn)分子。他是斯多葛派意義上的、而不是柏拉圖派意義上的“哲人王”。他曾告誡自己:“不要夢想烏托邦,只要有些許的進(jìn)步就該心滿意足,不要認(rèn)為做完手頭的事是小事一樁。誰能改變別人深信不疑的觀點(diǎn)呢?不能改變?nèi)藗兊拇_信,我們只不過讓人們假裝被說服,私下里卻不斷抱怨,就像奴隸被強(qiáng)迫一樣。”他發(fā)現(xiàn),并非人人都想成為圣徒,他滿腹悲傷地讓自己接受了一個墮落而邪惡的世界。“不死的神明從不抱怨在如此漫長的時間里,不可避免地要始終忍受那些毫無價值的人,這些人一直都是那樣,而且人數(shù)眾多;不,他們甚至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照顧他們。但是你,盡管注定很快就要死去,卻總是大聲抱怨,而且,何況你自己也是那些毫無價值的人之一。”他決定依靠榜樣而不是法律。他使自己在事實(shí)上成了一個公共圣徒;他肩負(fù)起了所有行政管理和司法裁判的負(fù)擔(dān),甚至擔(dān)負(fù)起盧修斯曾答應(yīng)承擔(dān)卻疏忽了的職責(zé)。他不允許自己奢侈,以簡樸單純的友誼對待所有人,因?yàn)槠揭捉硕棺约浩v不堪。他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把太多的公款花在了饋贈百姓和軍隊(duì)上,給禁衛(wèi)軍的每個成員2萬塞斯特斯,增加了可以申請救濟(jì)的人數(shù),經(jīng)常舉辦耗資不菲的競技比賽,蠲免了大筆稅負(fù);這種慷慨盡管不乏先例,但在這一時期,幾個行省和邊境地區(qū)明顯受到叛亂或戰(zhàn)爭的威脅,甚或正在發(fā)生,這樣做就很不明智了。
奧勒留繼續(xù)堅持不懈地推行哈德良發(fā)起的法律改革。他增加了法院開庭的天數(shù),縮短了案件審理的時間。他經(jīng)常親自充當(dāng)法官,對嚴(yán)重犯罪毫不手軟,但通常還是仁慈的。他設(shè)計出專門的法律措施,保護(hù)被監(jiān)護(hù)人免受不誠實(shí)的監(jiān)護(hù)人的侵犯,保護(hù)債務(wù)人免受債權(quán)人的侵犯,保護(hù)各行省免受總督的侵犯。他默許遭到禁止的長老會起死回生,把一些民間社團(tuán)(主要是喪葬協(xié)會)合法化,使它們成為有資格繼承遺產(chǎn)的法人,并為安葬貧窮市民建立了一筆基金。他對“供養(yǎng)政策(alimenta)”進(jìn)行了其歷史上范圍最廣泛的擴(kuò)展。在他妻子去世之后,他創(chuàng)立了一筆幫助年輕女性的捐助基金;有一幅淺浮雕表現(xiàn)了這點(diǎn):受到這種幫助的女孩子簇?fù)碓谀贻p的福斯蒂娜身邊,后者把小麥傾倒進(jìn)她們的裙兜里。他廢止了男女混浴的習(xí)俗,禁止給演員和角斗士過高的賞金,根據(jù)各城市的財力限制他們在競技比賽上的花費(fèi),要求在斗劍比賽中使用鈍頭劍,針對血腥殘忍的習(xí)俗所允許的所有競技比賽,消除了競技場上的死亡。人民愛他,但不喜歡他的法律。當(dāng)他為馬科曼尼人戰(zhàn)爭而征召斗劍士入伍的時候,平民百姓發(fā)出了不乏幽默感的憤怒呼喊:“他是在拿走我們的娛樂,他想強(qiáng)迫我們成為哲學(xué)家。”羅馬正在準(zhǔn)備接受清規(guī)戒律,但還沒有完全準(zhǔn)備好。
對他來說不幸的是,他作為一個哲學(xué)家的名聲,以及哈德良和安東尼治下的長久和平,鼓勵了內(nèi)部的叛亂者和外部的野蠻人。162年,不列顛爆發(fā)叛亂,卡狄人入侵羅馬日耳曼,帕提亞國王沃洛加西三世(Vologases III)對羅馬宣戰(zhàn)。奧勒留挑選了精明能干的將領(lǐng)去平定北方叛亂,但他委派盧修斯擔(dān)當(dāng)出征帕提亞的重任。盧修斯只到了安條克便止步不前。因?yàn)槊利惷匀恕⒍嗖哦嗨嚨呐宋鱽啠≒anthea)就生活在那里,盧西恩(Lucian)認(rèn)為一切盡善盡美、一切雕塑杰作全都集于她一身;除此之外,她還有曼妙迷人的聲音,熟練彈琴的纖指,以及飽讀詩書的頭腦。盧修斯見到她,便像吉爾伽美什(Gilgamesh)一樣,忘記了自己是什么時候出生的,他沉湎于享樂、打獵,最后是放蕩,與此同時,帕提亞人長驅(qū)直入,進(jìn)入了驚慌失措的敘利亞。奧勒留對盧修斯未作評論,而是給盧修斯的副手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Avidius Cassius)寄去了一份作戰(zhàn)計劃,他杰出的軍事才能幫助了這位自身也很有能力的將軍,不僅把帕提亞人趕過了美索不達(dá)米亞,而且還把羅馬的旗幟再一次插在了塞琉西亞和泰西封。這一回,這兩座城市被燒為平地,以免再次充當(dāng)帕提亞人發(fā)動戰(zhàn)爭的基地。盧修斯從安條克凱旋而歸,回到羅馬,他寬宏大度地宣稱,奧勒留應(yīng)該分享勝利的榮耀。
盧修斯帶回了這場戰(zhàn)爭中一位看不見的勝利者——瘟疫。它最早出現(xiàn)在被占領(lǐng)的塞琉西亞的卡西烏斯的軍隊(duì)中;瘟疫傳播得如此迅速,以至正當(dāng)帕提亞人為他們的神明復(fù)仇而感到高興的時候,他把自己的軍隊(duì)撤到了美索不達(dá)米亞。撤退的羅馬軍團(tuán)把瘟疫帶到了敘利亞;盧修斯讓其中一些士兵參加了他的凱旋行軍,他們把瘟疫傳染給了他們所經(jīng)過的每一座城市,以及他們后來被派駐的每一個地區(qū)。古代歷史學(xué)家所告訴我們的,更多的是瘟疫帶來的浩劫,而不是瘟疫的性質(zhì);他們的描述暗示了這場瘟疫可能是斑疹傷寒或腺鼠疫。蓋倫(Galen)認(rèn)為,它類似于在伯里克利(Pericles)統(tǒng)治時期蹂躪雅典人的那種疾病:在這兩種情況下,黑色的膿皰幾乎遍布整個身體,患者飽受嘶啞咳嗽的折磨,“呼吸中散發(fā)著惡臭”。瘟疫迅速席卷了整個小亞細(xì)亞、埃及、希臘、意大利和高盧;一年的時間里(166—167),它所消滅的人口超過了這場戰(zhàn)爭的損失。在羅馬,一天之內(nèi)就有2000人死于瘟疫,其中包括很多貴族;尸體被成堆成堆地運(yùn)出城外。在這個無形的敵人面前,奧勒留茫然無助,他盡了一切努力來減輕瘟疫所帶來的禍害;但他那個時代的醫(yī)學(xué)、科學(xué)給他提供不了任何指導(dǎo),瘟疫一路肆虐,直到它幫助人們形成了免疫力,或者殺死所有病毒攜帶者。影響是無窮的。很多地方的人口被席卷一空,以致重新回到了遍地蒿萊或一片荒漠的狀態(tài);糧食生產(chǎn)急劇下降,交通運(yùn)輸混亂不堪,洪水摧毀了大量糧食作物,饑荒緊跟著瘟疫接踵而至。標(biāo)志著奧勒留統(tǒng)治時期開始的“幸福歡樂”消失不見了;人們陷入了手足無措的悲觀主義,成群結(jié)隊(duì)地去尋求占卜師和神諭的幫助,用熏香和供奉把祭壇搞得烏煙瘴氣,到任何能夠提供安慰的地方去尋求安慰——到鼓吹人的不死和天國平和的宗教中去尋求安慰。
就在國內(nèi)陷入重重困難的時候,傳來了多瑙河沿岸各部落——卡狄人、夸迪人、馬科曼尼人、埃阿熱格人——渡過多瑙河的消息。他們打敗了一支2萬人的羅馬駐防部隊(duì),正暢通無阻地涌入達(dá)西亞、雷蒂安、潘諾尼亞、諾里庫姆;有些部落已經(jīng)越過了阿爾卑斯山,打敗了派來抵擋他們的每一支羅馬軍隊(duì),如今正在圍攻阿奎萊亞(威尼斯附近),威脅著維羅納,使意大利北方的富庶良田淪為廢墟。之前從未有過日耳曼部落如此團(tuán)結(jié)一致的行動,也不曾如此近距離地威脅過羅馬。奧勒留以驚人的堅決果敢采取了行動。他把哲學(xué)的快樂擱置一旁,決定親自披掛上陣,奔赴沙場,他預(yù)感到那將是自漢尼拔(Hannibal)以來羅馬最重大的一場戰(zhàn)爭。他征召警察、斗劍士、奴隸、土匪和蠻族雇傭軍加入因戰(zhàn)爭和瘟疫而兵力銳減的羅馬軍團(tuán),從而震驚了整個意大利。就連眾神也被征召來服務(wù)于他的目的,他出高價請來外族信仰的祭司,依據(jù)他們各自不同的宗教儀式,為羅馬祭祀神明;他本人供奉的獻(xiàn)祭是如此奢侈,以至一個風(fēng)趣之士傳播了一條據(jù)說是白公牛帶給他的口信,求他打勝仗時不要贏得太過分了:“你要是旗開得勝,我們可就遭殃了”。為了在不征收特別稅的情況下籌措戰(zhàn)爭經(jīng)費(fèi),他在廣場上拍賣了皇宮里的衣物、藝術(shù)品和珠寶。他采取了謹(jǐn)慎小心的防御措施——給從高盧到愛琴海的邊境城鎮(zhèn)修筑了防御工事,封鎖了進(jìn)入意大利的通道,賄賂日耳曼人和斯基臺人的部落,讓他們從背后攻擊入侵者。他拿出了在一個憎恨戰(zhàn)爭的人身上更加令人敬佩的干勁和勇氣,把他的軍隊(duì)訓(xùn)練成了一支紀(jì)律嚴(yán)明的武裝力量,率領(lǐng)他們打了一場艱苦的戰(zhàn)爭;他用自己的戰(zhàn)略技巧運(yùn)籌帷幄,從阿奎萊亞趕走了圍攻者,甚至一路把他們趕到了多瑙河,直至把他們幾乎全部俘獲或殺死。
他懂得,這次行動并沒有終結(jié)日耳曼人的威脅;但想到局勢暫時已經(jīng)安全,他便跟同僚們一起回到了羅馬。在回來的路上,盧修斯死于中風(fēng),像政治一樣沒有慈悲心腸的流言飛語悄悄傳開了,說奧勒留毒死了盧修斯。從169年的1月至9月,皇帝一直在家里休息,放棄了那些讓他虛弱的軀體瀕臨崩潰的種種努力。他患有胃病,這常常讓他虛弱得不能交談;他通過節(jié)食來控制胃病,一天只吃一頓,而且吃得很少。那些熟知他的身體狀況和日常飲食的人,都對他在宮廷里和戰(zhàn)場上所付出的勞動感到驚訝,便只好說,他在決心上的堅定彌補(bǔ)了他在體力上所缺乏的東西。有幾次,他召來當(dāng)時最有名的醫(yī)生——帕加馬的蓋倫,并稱贊他所開出的樸實(shí)無華的治療辦法。
或許,國內(nèi)一連串令人失望的事,加上政治和軍事危機(jī),加劇了他的病情,使他在48歲之年便垂垂老矣。他的妻子福斯蒂娜——她那漂亮的臉龐通過很多雕像傳到了我們手里——可能不曾跟這位哲學(xué)的化身分享過床笫和餐桌上的快樂;她是個充滿活力的女人,渴望快樂的生活,而不是他嚴(yán)肅的本性所能給予她的那種生活。城里的閑言碎語說到她的不忠;一些滑稽劇把他諷刺為一個戴綠帽子的男人,甚至提到了他的情敵們的名字。像安東尼對待母親福斯蒂娜一樣,奧勒留也一言不發(fā);相反,他還把那些被懷疑是奸夫的人提拔到了更高的職位上。他對福斯蒂娜極盡溫柔和尊重,在她去世(175年)之后把她祀奉為神,還在他的《沉思錄》中感謝神明讓他有“一個賢妻,她是如此溫順,如此柔情,如此大方”。現(xiàn)有的證據(jù)都不能證明人們對她的指控。他對她的愛飽含著激情,在他寫給弗朗托的一些信中,這種激情依然溫暖如初;她為奧勒留生下了4個孩子,其中一個女孩在童年時代就夭折了,幸存的那個女兒因?yàn)楸R修斯的放蕩生活而黯然神傷,在他死后便獨(dú)守空閨。雙胞胎兒子出生于161年,其中一個剛生下來便夭折了,另一個便是康茂德(Commodus)。那些傳播流言飛語人說他是一個斗劍士送給福斯蒂娜的禮物,他窮盡自己漫長的一生,力求證實(shí)這個故事。但他是個英俊瀟灑、精力充沛的少年;不難理解,奧勒留溺愛他,以提名繼承人的象征方式把他介紹給羅馬軍團(tuán),聘請羅馬最好的老師,為的是把他打造得適合君臨天下。但這個年輕人更喜歡獎杯、跳舞、唱歌、狩獵和擊劍;他發(fā)展出了一種不難理解的對書本、學(xué)者和哲學(xué)家的厭惡,而喜歡與斗劍士和運(yùn)動員廝混。很快,他就在撒謊、殘忍和說粗話上超過了自己的所有同伴。奧勒留太善良了,不可能給他足夠的懲戒,也不可能拋棄他;他依然希望教育和責(zé)任會讓他平靜下來,讓他成長為一個國王。這位孤獨(dú)的皇帝,消瘦憔悴,胡子拉碴,眼神因?yàn)榻箲]和失眠而疲憊不堪;他只能從妻兒那里轉(zhuǎn)過身來,埋頭于治理國家和指揮戰(zhàn)斗的任務(wù)。
中歐各部落對邊境的侵襲只停止了一段短暫的時間;在這場旨在摧毀一個帝國、使蠻族獲得自由的斗爭中,和平只不過是一次停火而已。169年,卡狄人入侵萊茵河上游的羅馬地區(qū)。170年,卡烏基人進(jìn)攻比爾及亞,另外一支大軍圍攻薩米澤蓋圖薩;科斯托博契人穿越了巴爾干半島,進(jìn)入希臘,洗劫了埃萊夫西斯的眾神殿,那里距雅典14英里;摩爾人從非洲入侵西班牙,一個新興的部落——倫巴第人——第一次出現(xiàn)在萊茵河畔。盡管被打敗了一百次,但這些繁殖能力驚人的蠻族人卻發(fā)展得越來越強(qiáng)大,而生育率很低的羅馬人卻越來越弱小。奧勒留認(rèn)識到,如今面臨的是一場生死之戰(zhàn),一方必須消滅另一方,否則就完蛋。只有一個在羅馬人和斯多葛學(xué)派的責(zé)任感方面接受過訓(xùn)練的人,才能如此徹底地把自己從一個神秘主義哲學(xué)家轉(zhuǎn)變成一個有能力的、成功的將軍。哲學(xué)家依然在,只不過隱藏在皇帝的甲胄之下;就在第二次馬科曼尼人戰(zhàn)爭的喧囂混亂中,在他駐扎在格蘭納河畔面對夸迪人的營帳里,奧勒留寫下了《沉思錄》這本小書,今天的世界正是憑借這本書記住了他。這個身體瘦弱、容易犯錯的圣徒,不倦地思考著道德與命運(yùn)的問題,同時率領(lǐng)一支大軍投身于一場改變帝國命運(yùn)的沖突,這篇文章對他曇花一現(xiàn)的展示,呈現(xiàn)出的是一幅最為貼切的圖景,從中可以看出時代是如何使它的偉大人物永存不朽。白天對薩爾馬提亞人窮追不舍,夜晚他能夠滿懷同情地寫到他們:“一只蜘蛛為抓到一只蒼蠅而洋洋自得;一個人為抓到一只野兔而洋洋自得,還有人為了捕獲到……薩爾馬提亞人而洋洋自得。……這些不都是強(qiáng)盜嗎?”
盡管如此,他還是與薩爾馬提亞人、馬科曼尼人、夸迪人、埃阿熱格人戰(zhàn)斗,整整六個艱苦的年頭,終于打敗了他們,帶著他的軍團(tuán)向北進(jìn)軍,遠(yuǎn)至波希米亞。很明顯,他的計劃是要用海西山脈和喀爾巴阡山脈作為新的邊界;倘若他成功了,羅馬文明可能就讓日耳曼人像高盧人一樣,在語言上是拉丁文,在遺產(chǎn)上是古典的。但就在他的成功達(dá)到頂峰的時候,他大驚失色地得知: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在平定埃及的叛亂之后,宣布自己為皇帝。奧勒留趕忙議和,讓蠻族人不由大吃一驚;他僅僅吞并了多瑙河北岸一條10英里寬的狹長地帶,并在南岸留下了強(qiáng)大的駐防部隊(duì)。他召集了手下的士兵,告訴他們,只要羅馬愿意,他會欣然把自己的位置拱手交給卡西烏斯,并承諾寬恕這次叛亂,然后揮師進(jìn)入亞洲,去跟卡西烏斯會合。在此期間,一位軍官殺死了卡西烏斯,叛亂瓦解了。奧勒留穿越了小亞細(xì)亞和敘利亞,來到亞歷山大城,像愷撒一樣為自己被剝奪了寬恕的機(jī)會而抱憾不已。在士麥那、亞歷山大和雅典,他獨(dú)自走上大街,身邊沒有一個衛(wèi)兵;他披著哲學(xué)家的斗篷,去聽當(dāng)時一些最重要老師的講課,加入他們的討論,說希臘語。在雅典逗留期間,他被許多偉大的學(xué)術(shù)流派授予教授之職——柏拉圖學(xué)派、亞里士多德學(xué)派、斯多葛學(xué)派和伊壁鳩魯學(xué)派。
176年秋天,經(jīng)過將近7年的戰(zhàn)爭之后,奧勒留回到了羅馬,羅馬城為他舉行了一個凱旋儀式,把他奉為帝國的拯救者。皇帝讓康茂德跟他一起出現(xiàn)在凱旋儀式上,讓這個15歲的少年作為他的共同統(tǒng)治者登上王座。這是將近一個世紀(jì)以來,過繼的原則首次被擱置一旁,世襲統(tǒng)治得以恢復(fù)的時刻。奧勒留深知,他給帝國招致了怎樣的危險;但如果拒絕把皇位傳給康茂德的話,康茂德和他的朋友們就會發(fā)動內(nèi)戰(zhàn),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他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我們千萬不要用后見之明來判斷他,羅馬也沒有預(yù)料到他對兒子的這種愛所帶來的后果。瘟疫已經(jīng)偃旗息鼓,人們開始再次感受到幸福快樂。首都遭受的戰(zhàn)爭損害并不大,財政開始好轉(zhuǎn),經(jīng)濟(jì)異常繁榮,稅收負(fù)擔(dān)不重;在邊境上戰(zhàn)事頻仍的同時,國內(nèi)的貿(mào)易卻繁榮興旺,到處都能聽到硬幣叮當(dāng)作響。這是羅馬大潮及其皇帝聲望的頂峰;全世界都向他歡呼致敬,稱贊他同時是一個軍人、賢哲和圣徒。
但是,他的勝利并沒有讓他受騙上當(dāng);他深知,日耳曼人的問題并沒有解決。他確信,未來的入侵只能通過積極的擴(kuò)張政策來阻止,必須要把邊境延伸到波希米亞的蒼茫群山。178年,他帶著康茂德啟程,奔赴第三次馬科曼尼人戰(zhàn)爭。他們渡過了多瑙河,在一次漫長而艱苦的戰(zhàn)役之后,再次打敗了夸迪人。抵抗力量已經(jīng)片甲不留,他打算吞并夸迪人、馬科曼尼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的領(lǐng)土(大致為波希米亞和多瑙河地區(qū)的加利西亞)作為新的行省;而就在這時,他在文多博納(維也納)的營地里病倒了。感覺到大限將至,奧勒留把康茂德叫到自己身邊,告誡他要繼續(xù)推行如今幾乎就要大功告成的政策,把帝國的邊界推進(jìn)到易北河,實(shí)現(xiàn)奧古斯都(Augustus)曾經(jīng)的夢想。接下來,他拒絕一切飲食。第六天,他用盡最后的一絲力氣,起身下床,把康茂德作為新皇帝介紹給軍隊(duì)。回到長榻上,他用床單蓋住自己的頭,片刻之后,安然辭世。當(dāng)他的靈柩運(yùn)抵羅馬的時候,人民已經(jīng)開始把他當(dāng)作神來祭拜,這尊神只是暫時同意生活在這紅塵俗世之中。
(本文摘譯自:Will Durant,1944. Caesar and Chri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Ltd.)